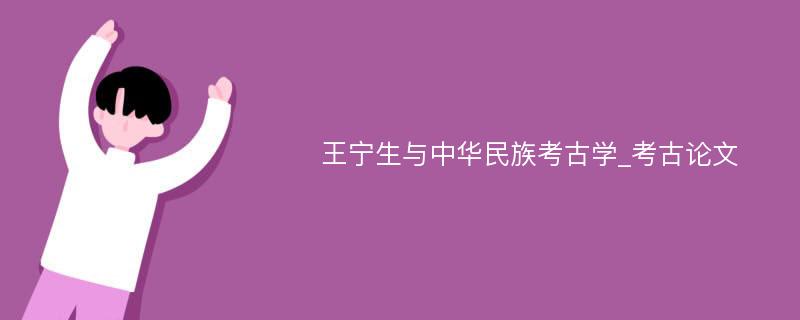
汪宁生与中国民族考古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中国论文,生与论文,民族论文,汪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汪宁生先生(1930.5~2014.2)多年从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兴趣在于搜集民族志材料以研究中国古史和中国考古学,其研究范围和方法论与欧美流行的民族考古学若合符节,经过近半个世纪以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创建了中国民族考古学。汪宁生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论文集、专著、日记等10余种。离休后,他主持恢复编辑、出版《民族学报》的工作。2013年12月,《汪宁生集》①出版,全书共4册,约400万字。 一、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 民族考古学在中国有着自身所固有的传统。中国古代学者常运用类似民族考古学的方法来观察社会、研究问题。例如孔子在《论语》一书中曾表示可去边远的少数民族(“九夷”)之中生活,因为那里还保留有他向往的古代制度。古代学者注释经籍,遇到已经消失的古代习俗时,就征引边裔民族尚存的相似习俗来加以解释。例如东汉人郑玄注释《周礼》、《仪礼》和《礼记》,晋人杜预注释《左传》,便常有这样的情况②。后人把这种方法称为“礼失而求诸野”,这是古代中国读书人熟知的一种治学方法。 中国现代新学术的倡导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首先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民族学的学者,他提出考古材料有待“用民族来证明,才能知道详细的作用”③。顾颉刚用中国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印证古代习俗和名物制度,写成一系列短文,后来编成专书《史林杂识》④。这些可看成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滥觞,但它们都还不是真正的民族考古学。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它们只是“民族志的对比”(Ethnographical parallel)或“早期类比”(Early analogy)。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汪宁生等一批考古工作者参加民族调查,发现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与考古发现的遗存相类似,曾加以报道并联系考古材料加以讨论,这可视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开端⑤。欧美虽于20世纪初年就有人提出“民族考古学家”一词,但作为一门学科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诞生⑥。当时中国与欧美考古学界尚处于隔绝状态,因而中国民族考古学诞生之初并未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民族考古学者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涉及制陶⑦、取火⑧、房屋⑨、埋葬⑩、占卜(11)及一些考古发现的遗物用途(12)等方面。 关于如何选取类比材料,由于中国学者探讨的考古遗存多分布在中国的中原地区,这一地区虽然可以找到残存的民俗可作民族考古学类比之用(13),但大部分地区早已进入现代社会,他们不得不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那里取得类比材料。这些少数民族与中国远古民族不一定有历史文化联系。西方民族考古学把类比材料的取得分为两种。一为“直接的历史方法”(Direct historical approach),即类比材料只能取自同一地区有文化继承关系的民族;另一种为“普通比较”或“普遍类比”,即任何地区的民族志材料均可使用。对此讨论颇多(14)。中国民族考古学使用的方法主要应属于普遍类比。这一点和西方民族考古学的主流是一致的,例如为了复原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美国学者宾福德(Binford L.B.)研究北美爱斯基摩人(15),加拿大学者理查德(Lee R.B.)等研究南非布须曼人(16),美国学者古尔德(Gould R.A.)研究澳大利亚土著人(17),以及为了研究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大量存在的陶器,美国学者郎埃克(Longacre W.)长期研究菲律宾卡林加人的制陶业(18),他们采取的都是“普遍比较”的方法。 研究方法方面,汪宁生早在1987年即参考西方民族学家的经验,提出类比-假设-验证三步骤,而且特别强调验证,他认为“普遍类比可以大量运用,主要即依靠验证这一手续”(19)。他的研究除主要依靠他几十年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同时还大量引用国内外的民族志材料,如利用因纽特人的“妇人刀”来解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三角形石刀”;用易洛魁印第安人的龟甲“响器”来解释中国大汶口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龟甲器(20)。他主张“普遍比较”,对类比材料取自什么地区和何种社会不必作过多的限制,但他认为研究史前时期和古代社会的类比材料只能从前工业社会取得。西方学者用当代城市垃圾的情况来讨论考古遗址堆积的形成,或以当代从“嬉皮士”到“庞克士”奇装异服的迅速改变来探讨考古遗物风格的变化(21),这一点他表示不敢苟同(22)。 虽然中国的民族考古学起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不算太晚,但至今仍停留在初创阶段。西方出版的民族考古学论著已有千余种,考古学通论著作中大多有专门章节介绍民族考古学。有些大学开设民族考古学专业和课程,还有专门刊载民族考古学论文的刊物。民族考古学家经常在一起聚会,报告自己的田野工作,对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探讨。而在中国,目前已发表的中国民族考古学论著只有几十篇,还没有专门的刊物,在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学中,很少有教师向学生介绍民族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民族考古学不仅成果较少,质量也不高。一般只停留在利用民族志材料对遗物和遗迹本身的解释,还不能透过考古学遗存探索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例如讨论居住遗址,只判断房屋的用途及建筑方法,很少就房屋的排列及其他有关现象探讨当时的居住模式、社会组织。研究在民族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制陶只着眼于器物的用途及制陶技术,而很少涉及贸易和交换、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组织等问题。这方面虽然也有个别人开始尝试(23),但尚未形成共识。至于像当前西方民族考古学经常讨论的遗址堆积的形成及废弃物的处理等问题,国内更是鲜有关注。 目前,中国民族考古学大多还只停留在研究者个人业余爱好的层次,多为研究者在进行民族学调查时偶然产生的副产品。像西方优秀民族考古学者那样,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一个民族地区做大规模的长期调查,从而揭示出某个考古遗址的全貌,或解决考古学上某个重大问题,在中国尚未出现。 随着中国与外界学术交流的深入开展,人们的视野会不断扩大。我国考古学者逐渐会认识到传统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局限,认识到民族考古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正如碳十四等自然科学技术可为考古学断代提供一种可靠的方法一样,民族考古学也可以为考古学的解释提供一套有效的方法。中国的考古学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有待研究的问题很多,而中国边疆尚有不少民族还停留在前工业社会的阶段,可以提供丰富、有用的类比材料。中国民族考古学将来是大有可为的。 二、汪宁生的学术贡献 汪宁生的研究总是从专题研究入手的,他创造性地利用民族志资料探索中国考古学和古史中的重大学术问题,为民族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做出重大贡献。他以民族考古学方法撰写论文数十篇,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世界上民族考古学家所普遍关注的诸如制陶、葬俗、居住方式、出土器物的用途等问题,还涉及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中长期聚讼的疑难问题,如文字、度量衡的起源,八卦、阴阳、明堂等问题的实质,甲骨占卜的具体方法等等,他还用民族考古学方法来考释古文字。后来他把这方面的文章分别编为两本书,属于考古学的收入《民族考古学论集》(24)(后扩充改编为《民族考古学探索》(25)),而与古代史或古文字有关的考证收入《古俗新研》(26)。他认为无论讨论什么问题,只要是通过运用民族志材料的类比而得出结果的,都应属于民族考古学的范畴。他赞同的是广义的民族考古学。 汪宁生根据几十年的田野工作经验,总结出一套系统的调查方法,提高了民族调查和社会调查工作的科学性。虽然民族考古学可以采用前人记录的民族志资料作类比研究,但中国已有的民族志资料很不完备,由于学术兴趣的差异,前人关注的重点不同,很少能记录对研究考古学有用的资料。在中国,民族考古学可用的类比材料主要依靠研究者自己调查、搜集。汪宁生为此不得不讲求民族调查的科学方法并逐渐积累自己的经验。 1983年后,汪宁生有机会到欧美一些国家访问、考察,所到之处,常找国外同行交流经验,请教问题,并收集、购置大批图书。归国之后,便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田野调查经验,写成《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27)一书。在此书出版以前,中国只有有限的几种文化人类学概论性著作,而且其中大多数又是国外著作的译本,没有关于调查方法的专著。此书的出版为在中国从事民族调查或社会调查的人如何询问、如何记录、应注意的事项等,提供了一套科学程序和方法,成为一本雅俗共赏的调查工作手册,保证了调查资料的可靠性。 汪宁生对中国考古学界和上古史学界有关“母系社会”的一些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人们对“母系社会”的认识存在着许多误解。如说“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是原始社会中相继发生的两个阶段。又如人们认为仰韶文化及时代相近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母系社会”,龙山文化及时代相近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父系社会”。人们大多想当然地认为在“母系社会”中,妇女总是掌握很大权力,男子则处于被统治地位。这些看法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占主导地位,甚至写进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汪宁生对作为仰韶母系说的重要证据的集体二次葬做了认真的研究。他搜集世界上大量民族志资料证明,集体二次葬是世界简单社会居民当时所普遍流行的葬俗,它是整个村落或社区为了禳解死者可能给活人带来的灾难,把在一定时期所有死亡者的骨骸集中起来再次埋葬,而不是所谓的把母系氏族成员埋葬在一起。因此集体二次葬不能作为仰韶文化属于母系社会的证据(28)。其他考古发现例如“大房子”遗址,也无法作为这方面的证据。大房子或长房的共居者既可以是母系氏族成员,也可以是父系氏族成员(29)。汪宁生关于仰韶葬俗和长房共居习俗的两篇文章,对仰韶母系论提出质疑,是我国最早质疑单线进化论的专题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母系社会”,汪宁生曾对云南几个族群的原始婚姻和家庭形态做过详细调查。1991年访问加拿大时,还专门到作为母系社会典型的易洛魁人聚居地进行考察,搜集前人的调查记录,与保留地首领及居民进行交谈。经过调查,他了解到当地母系社会中的妇女虽比其他社会中妇女的地位高,但在社会事务和政治方面仍由男子主导一切,易洛魁人从古至今都是如此(30)。 大量的民族志材料表明,实行母系的总是在农业已有一定发展的社会,而在农业社会之前的狩猎采集者却实行父系或两可系。因此,母系不一定必然在父系之前产生。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争论还可继续进行,但汪宁生的相关论著使人们对过去被奉为信条的单线进化论产生了怀疑,并对由此产生的仰韶母系说及其他有关母系社会的一些观念进行纠正,或至少引起人们去重新思考这类问题。 汪宁生对云南沧源崖画的研究为中国崖壁艺术研究赢得了国际声誉。云南沧源崖画是汪宁生在1965年初首先发现的,后来又陆续调查,共发现了10个地点。他自谦为这是自己做民族调查时的副产品,实际上则是云南考古及中国崖壁艺术的一项重大发现。现云南沧源崖画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像其他崖画上只有一个个孤立的图形,而是包括多幅连贯的生活场景图画,可直接反映出古代这一地区居民住宅、放牧、狩猎、战争、舞蹈、祭祀等场面。其中有一幅村落图再现了当时人们过着定居生活的情景,曾被很多书刊引用。1985年,《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和研究》一书出版(31),这是中国崖壁艺术的第一本专著。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各个地点的崖画,对大部分图形及画面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对崖画的年代、族属等作了客观合理的推断,而且总结出一套科学记录崖画的田野工作方法,为国内崖壁艺术研究者提供了自己的宝贵经验。该书确立了我国崖画研究的一些基本规范。1989年,该书被评为国家民委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 汪宁生对云南考古资料的考释和综合研究,推动了云南考古事业的发展。汪宁生根据云南地区宋代以来积累的金石学资料和近年的考古资料,写出一本综合研究著作《云南考古》(32),至今仍是云南考古工作者手边必备之书。他把云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不仅概括地介绍了每一阶段的重要遗物和重大发现,而且参考历史文献,指出该阶段的历史特点和考古学上的空白和缺陷。该书推动了云南考古事业的发展。 汪宁生还对云南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和文物,特别是以云南晋宁石寨山“滇”人墓为代表的云南青铜文化,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对青铜器及其上的图像所反映的民族关系、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权形成、艺术成就等分别进行探讨。由于充分利用文献记载及有关民族志资料,并大量参考外文资料,征引繁富,立论新颖,使得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居于世界前列。 三、汪宁生的治学特点 汪宁生的治学特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其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材料。民族考古学是从考古学视角对活的社会(living society)的研究,民族考古学家研究这样社会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考古发掘的物质遗存,特别是在物质文化模式和社会其他方面之间建立起系统的联系。民族考古学就是要用民族学材料来研究考古学问题。由于人类学者或民族志工作者多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特殊兴趣,很少记录对考古学有用的材料,特别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材料,其他的非专业作者,如商人、殖民者、旅行者或牧师等,所留下的民族志记录大多简略而含混。由于已有的民族志材料常常无法满足考古学者的需求,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汪宁生每每不辞辛苦,尽量争取多去民族地区做田野工作,通过自己的直接观察,有目的、有计划地搜集资料。汪宁生在调查过程中有意识地从“活的社会”中搜集和积累有助考证古史的有用资料,针对中国古史中长期聚讼的诸多疑难问题,如明堂、阴阳、八卦、耒耜、耦耕、媵、分胙、献帛、左衽等进行专题研究,且常常能得到不同于前人的合理解释。除上述古代社会、宗教、礼俗等重大问题外,他的调查还涉及日常生活、远古技术及古器物用途等前人不甚注意的方面。这些“小问题”看似繁琐、零碎,但对于复原古代社会生活而言却是必须要了解清楚的。汪宁生著有《西南访古卅五年——民族调查日记选辑》(33),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 其二,重视中外学术交流,并身体力行之。“文化大革命”期间,汪宁生翻译了《事物的起源》(34);改革开放后,他走出国门,在国外讲学多年,曾应邀在欧美10余所著名大学演讲,并应聘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和特罗姆瑟大学的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考古学、云南青铜文化、云南民族文化之类课程或做研究工作。其中,1986年6月,他赴美参加“古代中国及社会科学一般法则”会议,宣读《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研究》论文,后英文本刊于Early China(35),中文本刊于《文物》(36)。1998年6月,他赴马来西亚参加太平洋及亚洲地区史前学会(IPPA)第十六届会议,宣读《傣族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论文。2000年5~7月,他再访挪威,与挪威友人勃克曼(Harald Lars Bockman)合作翻译明清碑刻中的习惯法资料。他著有《始信昆仑别有山——海外游学日记》(37),记录了自己海外游学的经历。 汪宁生指出,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要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汉学家的看法不一定正确,既不能把政治人物神化,也不要把学术人物神化。二是要反对盲目自大,汉学家们的口语可能不如我们说得流利,但他们研究古文献的能力我们很多学者不一定比得上。他们有些问题钻研得很深。汉学家有几个特点注定他们的成果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他们可以几十年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没有外界干扰。二是他们大多具有全球的视野,研究中国的东西不是就中国论中国,而是具有全球的视野,并且常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看。比如他们研究道教,就觉得道教思想蕴含很多生态学的原理,反映出很多古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所以我们对待西方汉学应当像对待其他学问一样,用平视的态度,汉学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我们对待汉学也应当像对待世界所有文化一样,学习和继承它,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收集和利用(38)。 其三,提出考古学资料、文献记载、民族志资料相结合的三重证据法。民族考古学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史前时期的文化遗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进入文明社会,人类有了文字记载历史之后的文化遗存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用民族考古学方法进行分析。中国历史悠久,古代文献极为丰富,二十四史几乎都有“蛮夷”、“四夷”的传记,还有许多专门记录边裔少数民族的专著,当然不能将它们直接作为类比材料,但可为今天从事民族志田野工作提供线索,在解释和验证考古遗存时可作为一项参考资料。因此,中国民族考古学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时常引用历史文献资料。西方有些民族考古学者认为,历史文献记载的民族志材料已属于民族史范畴,不宜加以利用(39),但由于中国历史文献的特殊性,研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有关问题时,若摒弃大量的文献资料则是不明智的。 中国民族考古学和世界其他地区民族考古学相较,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研究过程中,除了民族志资料外,还要尽可能地搜集有关文献资料作为参考,这是因为中国有文字的历史较长,留下来的文献极为丰富,而其他文明无此优势。因此,研究古代的问题,应该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发展为“三重证据法”,即考古学资料、文献记载、民族志资料三者的结合,甚至还可发展为“多重证据法”,因为有些问题还要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 中国历史学上存在许多疑难问题,学者搜集民族志材料进行类比和讨论,甚至还可尝试运用同样方法来考释甲骨文和铜器铭文。汪宁生在这方面的成果较多,有关的文章已编成专书(40)。但由于所解决的已不是单纯的考古学问题,而属于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范畴,这类研究可视作民族考古学方法的广泛运用。 其四,重视对民族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努力构建民族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在大量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汪宁生开始了对民族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早在1987年,他就写出《谈民族考古学》(41)一文,第一次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中国古人早有的认识及当前中国民族考古学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全面的讨论。这篇文章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考古学形成的标志。以后他又陆续发表《再谈民族考古学》(42)、《三谈民族考古学》(43),介绍西方同行的经验,发展和扩展自己的认识。这三篇文章结合起来,可以说就是一本“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理论纲要,反映了汪宁生对这门学科总的认识和方法论。汪宁生认为,民族考古学方法的要点是民族志资料的类比,民族志资料可以来自自己的调查,也可参考前人的记录,但无论类比材料取自何处,当通过类比形成对某一问题的可能解释(汪宁生称之为“假说”)后,必须从考古学或文献本身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才能作出结论,这就是验证。他归纳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三步骤,即类比-假说-验证,而验证是重要的一环。只有通过验证,才能保证研究工作的科学性,不致沦为任意附会和胡乱推测。 民族考古学不仅可扩大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解决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中一些单凭物质遗存本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抢救和补充记录过去民族学者很少注意的材料,大大丰富民族志档案,而且通过探讨物质遗存和社会组织、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类问题,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也会有新的刺激和建树。 注释: ①汪宁生:《汪宁生集》,学苑出版社,2013年。 ②刘敦愿:《“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解》,《民族学报》1982年第2期。 ③蔡元培:《说民族学》,《一般》杂志1929年2月号。 ④顾颉刚:《史林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⑤蔡葵:《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思想战线》1992年第4期。 ⑥Hodder I.,The Present Past: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y,London:B.T.Batsford,1982. ⑦a.李仰松:《从瓦族制陶探讨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考古》1959年第5期。 b.汪宁生:《云南傣族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⑧汪宁生:《中国古代取火方法的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取火方法》,见《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⑨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住俗——兼谈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考古》1964年第8期。 ⑩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俗的看法》,《考古》1964年第4期。 (11)林声:《记彝、羌、纳西族的“羊骨卜”》,《考古》1963年第3期;《云南永胜县彝族(他鲁人)“羊骨卜”的调查和研究》,《考古》1964年第2期。 (12)宋豫秦:《“中柱盂”的民族志类比》,《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擂钵”的使用》,《华夏考古》1993年第10期;《石家河文化红陶杯与陶塑品之功用》,《江汉考古》1995年第2期。 (13)陈星灿:《长葛-长社-社——古代社的活化石》、《现代的古代——豫西灵宝埋葬风俗纪实》,见《考古随笔》,文物出版社,2002年。 (14)a.Chang K.C.,Major Aspect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Current Anthropology,8:3,1967. b.Kramer C.(ed.),Ethnoarchaeology:Implication of Ethnography for Archae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c.Longacre,W.,Ceramic Ethnoarchaeology,The University Press,1991. (15)Binford L.B.,Numamint Ethnoarchaeolog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 (16)a.Lee R.B.and De Vore,Kalahari Hunter-Gather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b.Lee R.B.,The Kung S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7)Gould R.A.(ed.),Exploration in Ethnoarchaeology,New Mexico University Press,1978. (18)同(14)c。 (19)汪宁生:《谈民族考古学》,《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20)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21)同⑥。 (22)同(19)。 (23)a.汪宁生:《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b.同⑦b。 (24)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5)同(20)。 (26)汪宁生:《古俗新研》,(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 (27)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1996年(2002年再版)。 (28)Wang N.S.,Yangshao Burial Customs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Organization,Early China.11-12:7-32,1987. (29)同(23)a。 (30)汪宁生:《易洛魁人的今昔》,《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31)汪宁生:《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32)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33)汪宁生:《西南访古卅五年——民族调查日记选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 (34)[德]Julius E.利普斯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 (35)同(28)。 (36)汪宁生:《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对仰韶母系社会说及其方法论的商榷》,《文物》1987年第4期。 (37)汪宁生:《始信昆仑别有山——海外游学日记选辑》,文物出版社,2008年。 (38)见汪宁生2004年在重庆师范大学做的《欧美的汉学研究》演讲整理稿。 (39)Nicholas David,Carol Kramer著,郭立新等译:《民族考古学实践》,岳麓书社,2009年。 (40)a.汪宁生:《汪宁生论著萃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 b同①。 (41)同(19)。 (42)汪宁生:《再谈民族考古学》,见《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43)汪宁生:《三谈民族考古学》,《考古》2007年第4期。标签:考古论文; 母系社会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物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人类学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志论文; 中国社会出版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