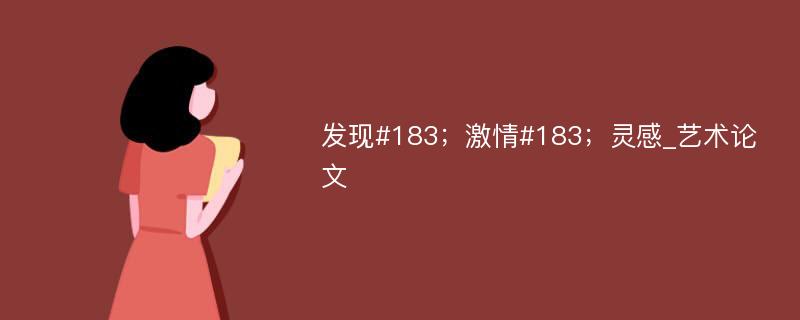
发现#183;激情#183;灵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灵感论文,激情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剧作家和领导戏剧创作的同志都增强了创作的精品意识,比过去更加下力气、花功夫,也比较地舍得投入,这很有利于创作质量的提高。但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些作品虽然比较精致,但却缺少感人力量,特别是对某些有基础作品的加工,往往只是增加包装,堵塞漏洞,或者增加一点有思想性、带哲理味道的对话和唱词,作品的感人力量并未增强。这样的作品恐怕不能成为艺术精品。
感人的力量从哪里来?这首先取决于创作者的思想水平和生活积累,同时也与剧作家创作时的思维状态紧密相关。艺术创作以形象思维为主,以理性思维为辅,但理性思维对形象思维起着重要的指导、制约和升华的作用。而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得最好的、富有创造性的状态即是灵感的迸发。精品应该是在灵感状态下创作出来的,或者说只有在灵感状态下才能产生出艺术精品!
我国古典剧论在评价作品时分为“神”、“妙”、“能”、“具”数品(吕天成语)。我想我们今天所说的精品应是神品、妙品;就是说作品中有一种精神、气势,有一股灵气。激情贯穿其间,显出作者才华横溢,不同凡响,这样的作品必是出自有思想、有生活的作家之手。
在这种状态下创作的剧作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对生活、对人有一种独特的发现
江西的剧作家姜朝皋说,创作或评论作品时,要想到和看它比前人新发现了什么?比别人多发现了什么?从生活中再发现了什么?这说出了欣赏者对创作者基本的、也是重要的要求。近年来一些优秀的、有影响的作品,对生活、对人都有独特的发现。刘鹏春的《皮九辣子》所以令人难忘,在于它深入地揭示了人的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皮九的性格在“文革”中被扭曲,后来又由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用正当的手段得不到应该得到的东西,用不正当的手段却可以得到超乎合理的东西,于是他灵魂中丑恶的东西继续膨胀;但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正确的诱导下,皮九灵魂中正义的一面又得到了复苏和张扬。
张福先的《三醉酒》是对一种新的人格力量的发现。村支书龙友本是代表着正义的力量。但在生活中他却变成了弱者,不得不屈从于小有权力、搞不正之风的人。但他屈从并不屈服,艰苦但却是倔强地斗争着。这是新形势下一种宝贵的性格。由于他的生存环境和斗争方式有现实依据,因此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
人的性格是社会造成的,也是一定时代精神的体现,因此发现并塑造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新的人物形象与艺术典型,对于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在题材上与《三醉酒》有共同之处的豫剧《能人百不成》(贾璐、安克慧、聂延军编剧)则反映了一种人生况味。由于生活中各种人有意无意的阻挠,要做成一件有益的、合理的事情却很难。主人公白世成尝尽了种种苦涩的滋味,经过许多努力又功败垂成,但他仍坚韧地奋斗着,这也是改革开放时代具有新的精神面貌的人物。
一些历史剧作品体现了作家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审视,这也是一种新的发现。譬如封建社会的文人。一些出自文人之手的传统剧目,常常流露着对文人习性的自我欣赏,对他们的弱点也曲意回护。在“左倾”思想严重时期,一些作品又对文人肆意丑化。近年郭启宏在话剧《李白》、《天之骄子》、昆剧《司马相如》等作品里则对李白、曹植、司马相如等文人在赞颂、同情的同时,又充满理性自省的批判精神。郭启宏说:“面对司马相如这样一个传统文人以及司马相如们所遗泽于后世的文人传统,我的心情并不轻松,一份褒,一份贬,一份理解,一份无奈,我看到现代文人……于是,似有一根鞭子在轻轻地抽打着,不见鞭影,没有血痕,却真实地感到灵魂的震颤。”(《司马相如未尽墨》,《剧本》1994年第10期)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发现,需要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结合。出乎其外,方能古今贯通,做出历史的、客观的评判;入乎其内,方能设身处地,感情激荡。自己灵魂震颤,才能引起读者和观众的灵魂震颤。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剧还以对人的关系的深刻揭示为特点。较早是福建的《新亭泪》、《魂断燕山》、《秋风辞》等,在封建君臣、父子、朋友关系的描写中,对人的灵魂有鞭辟入里的透视。稍后湖南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对精明的统治者曹操与有才能的文人杨修之间的关系写得更为微妙、曲折,二人本来都想倚重对方,但在精神上却总无法契合。近年湖北女作家沈虹光的话剧《同船过渡》写出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美好关系,是真情使误解与隔阂消融,使人们由互相排斥变为互相依靠,互相亲近。剧本写得这样真实,说明写真善美同样可以达到深刻;当然,这首先依赖于作家对人与人关系中真善美感情的独到发现。
二、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
对生活的独到的发现需要作家有理性的思考,但只有理性的思考,还不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要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作家必须有欲罢不能的激情。
为先进人物、英雄人物造像,是时代赋予剧作家的重任。但只有剧作家们熟悉了这些人物,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感情,才能写出感人的作品。话剧《甘巴拉》的作者们(丁一三、王向明、张子影)和艺术家们正是为高原雷达兵们的精神所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以至排完这部话剧,心潮仍在跌宕,心灵一次次受到撞击!”所以他们才能谱写出这样一首崇高、神圣、纯洁、忠诚的颂歌。读剧本,我不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最近出现了一批写真实英雄人物的作品。这类作品难写,因为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群众早已熟悉,群众对他们也早有感情。剧作家必须对他理解得更透,爱得更深,才能写出吸引观众、征服观众、提高观众的作品。在这方面,话剧《徐洪刚》(陈志斌、殷习华编剧)以及《张鸣岐》、《孔繁森》等作品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山东剧作家牟家明的《根的呼唤》描写了新时期农村党员为发挥党员应有的作用所遇到的艰难。一方面,那些腐化变质的干部(有的曾是老区人民用生命救出来的)为了自己的私利,阻挠有利于群众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的消极影响也使群众对好党员真诚无私的做法产生怀疑,增加了他们发挥作用的难度。这个戏也和前边讲过的《三醉酒》一样,饱含着作者对优良作风的赞颂、祈盼和对不正之风的强烈批判及痛恨。
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几种感情常常交织在一起。在作品里,作家的感情表现得越真实,越有感人的力量。话剧《警钟》(李景文编剧)写一个曾有过功劳的公安局长蜕变为罪犯的故事。对此,人们的感情是不同的。剧中有一个场面,当初这个局长曾缉捕过的强奸、抢劫犯看到局长与他同站在被告席上,感到解恨,并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确实,此时那位前局长在本质上与他曾缉捕过的罪犯已无不同,而剧作家在这些情节的描写中,则饱含着对他笔下走向堕落的主人公的谴责、痛恨与惋惜交织的感情。这样的感情能够诱导观众更深入的思考,增强作品批判的力度。
激情,也不一定溢于言表,“却道天凉好个秋”比起“为赋新诗强说愁”(辛弃疾《采桑子》)来更耐人品味。杨宝琛的《大江人》写几个知识分子蒙冤被发配到北大荒,作品没有写他们与工农结合的“痛苦”,也没有写他们如何受迫害,却写他们平反后的心态。看似湖平如镜,水波不兴,但水底却激荡着滚滚的洪流。这是作家长期生活磨砺而形成的深沉情感的体现。
激情来自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又是一种创作冲动。王仁杰写《董生与李氏》并非着意在愤怒地批判封建思想,也不是热情地歌颂反封建的行动,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是采取一种幽默的、调侃的态度,但创作的欲望是强烈的,感情也是浓厚的,因此作品别有一番风致。
三、一种奇妙的构思
在编剧理论中,构思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我这里主要指以下几点:一是由生活触发的一种联想、猜想甚至幻想、奇想。作者设想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偶然事件后会怎样,在偶然中体现必然,使之具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趣味。比如湘剧《山鬼》(盛和煜编剧),作者设想具有理想人格、受到人们尊崇的屈原到了不懂礼法的蛮荒部落会怎样,作者和这位老先生开了个小玩笑,也便表现出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再如西施是人们熟知的古代的美女,她的悲剧命运令人同情。罗怀臻的《西施归越》又进一步设想,在越国灭吴的时候,西施已怀上了吴王夫差的“孽种”,那么,她的悲剧命运就更惨重了。
这些设想、联想要有生活的根据,但它必然是作家的创造。
二是一种新颖的“局式”。大凡雅俗共赏的作品多以局式胜。好的局式必须不落窠臼,使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中国的传奇和民间艺人创作的作品,有许多具有这样的特点。当代的作品,从陈仁鉴先生的《春草闯堂》,到叶一青、吴傲君的《喜脉案》、李志浦的《张春郎削发》等,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局式是对剧作家才气、功力的一种考验,要写出好局式必须有灵感。
三是一种新的视角。“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可以得出不同的印象。不同的视角可以有新的发现,新的发现又可引起创作激情。前几年人们说革命历史题材难写了,说难以跨越“五老峰”(老故事,老人物、老主题……),江西的《山歌情》(谢干文、江洪涛、盛和煜编剧)和福建的《山花》(陈欣欣编剧)别开生面,它们分别写了老区一些平常的农民、妇女,在革命与反革命较量的严峻时刻,在生死关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敢、坚定和献身精神。作品写了这些人物的成长过程,也写了他们特有的牺牲与痛苦,真实感人。但这种寻求新的视角又不能离开大的历史环境和基本矛盾,譬如有的作品侧重写战争年代人们生理的渴求,似乎这种欲望决定了他们(她们)行动的方向,恐怕就值得斟酌。
近读广西彩绸戏《哪嗬咿嗬嗨》(张仁胜、常剑钧编剧)写一班彩调艺人在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这一很长的历史跨度中的命运,战争使情人们分离,但他们执著思恋着,一出《王小打鸟》贯串全剧,演员们与他所扮演的剧中人在感情上是契合的。生活与艺术交混在一起,人们追求民间艺术中所呈现的美好感情,更反映出军阀战争和国民党挑起内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新的视角和新颖的形式更加强了剧作的社会与文化意蕴。
当然,古人所说的神品、妙品,或今人所说的精品,都有较高的要求,应能做到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技巧比较完善的统一。前面例举的一些作品有的还只是一个方面突出,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不一定都是神品、妙品或精品,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说明,一部有特色的、能够给人震动的作品与平庸的作品区别在于:后者把生活也都摆出来了,甚至在结构、章法等方面也无可挑剔,但却缺少点睛之笔,不能使人得到特别的惊喜、愉悦和启示。而前者所以能有这样的效果,在于创作时,作者在生活感受的基础上,经过了一个认识的升华、一个感情的激荡、一个思维的顿悟、一个想象的形成。也就是说有积极的、创造性的思维状态的出现,即灵感的迸发。
由于灵感一词至今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所以还需补充以下几点:
一、灵感需要天才,但并非天赋的东西,它是长期生活积累与艰苦劳动的结果。只有经过“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痛苦寻觅之后,才能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灵感不能强求,但可以和需要培养。邓小平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精神来哺育自己”,这也是创作灵感产生的源泉。灵感与“玩艺术”、“游戏人生”不相干。
二、灵感不排斥“推敲”,恰恰相反,灵感常常是推敲的产物。中国古代诗人最讲灵感,也最讲推敲。当代的许多优秀剧作也都是反复修改锤炼出来的。但这种推敲和修改应是在活跃的思维状态下进行。鲁迅说过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是否还可以说,改不动的时候不硬改,这时应到生活中去汲取营养,从而唤起创作的灵感,再去修改作品。
三、要使剧作家能经常文思泉涌,就要引导他们认识艺术创作规律,为他们创造积累生活、增长见闻、感受时代精神的条件。近年不少地方重奖优秀作品,这对戏剧创作是有促进、鼓舞作用的。但也要看到,重奖还只是对天才的表彰,重奖却不能造就天才。我们必须在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基础上,精心选拔和花力气培养,尔后才可能出现若干破纪录的尖子运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