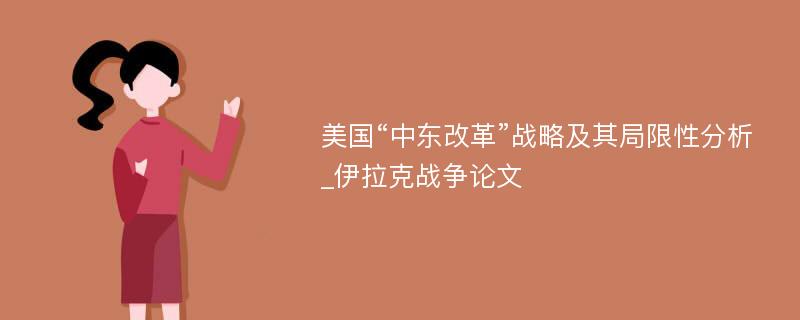
试析美国“改造中东”战略及其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美国论文,限度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事件”后,“改造中东”(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成为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伊拉克战争无疑对美国改造中东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对改造中东战略的基本设想是什么?该战略具备哪些特点?其发展前景如何?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改造中东战略的“双引擎”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经历了冷战、冷战后以及“9·11事件”以来三个阶段。冷战的两极格局限制了美国在中东的能力,当时美国在中东主要追求三大目标:一是防止苏联扩张势力;二是维持中东地区稳定廉价的石油供应;三是维护以色列和温和阿拉伯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注:参见1987年及198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关于中东的论述。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119—120页。)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与沙特维持特殊关系、伊朗革命后对伊实行遏制等政策均服务于这些目标。海湾战争胜利及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中东拥有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中东区内外没有能够挑战美国优势地位或直接严重危害美国利益的力量,因此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选择了相对超脱的“东遏两伊、西促和谈”政策,也就是尽量不以军事手段直接卷入中东,而是通过遏制敌手、推进和平进程来保持美国的优势,其本质是在维持中东地区现状的基础上,寻机继续扩大美国的优势与利益。“9·11事件”后,美国的中东政策进入第三阶段。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头号威胁。中东地区本身的环境并不是在“9·11”一天之内发生了本质变化,但美国“感受”到的环境似乎突然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直接催生了美国改造中东战略。布什政府在寻找恐怖主义根源时,并不是着眼于检讨美国的中东政策,而是从中东国家本身的政治体制入手。其逻辑是:策划“9·11”的恐怖分子并非因为贫穷而参加恐怖活动,美国真正的敌人是“大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各种反美极端主义思想。要反恐就要消除反美的极端主义思想;要消除各种反美极端主义思想就要彻底改造中东国家,使中东国家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也就是让中东地区实现现代化。
尽管布什政府从未正式提出书面的改造中东战略,但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已有不少学者论及美国正在实行改造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如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教授认为,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是“改造整个穆斯林中东,将其一劳永逸地带入现代世界”。(注:John Gaddis,“A Grand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Foreign Policy,November/December 2002.)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福阿德·阿扎米认为,美国之所以要在伊拉克冒险,目的就是“使阿拉伯世界现代化”。(注:Fouad Ajami,“Iraq and the Arab's Futur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3,pp.2—18.)伊拉克战争前后,布什及其政府高官也多次表示,伊拉克战争背后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东”。布什2002年9月12日在联大发表讲话时宣称,“伊拉克人民将挣脱身上的枷锁。他们有朝一日可以同民主的阿富汗和民主的巴勒斯坦一起,促进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改革”。(注: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9/20020912—1.html)今年2月26日他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讲话,更将改造伊拉克与二战后改造德、日相提并论,并称“中东有充满希望的渴望自由的迹象……伊拉克的新政权将为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自由树立一个鲜明和令人鼓舞的榜样”,美国要在“经历了世代纷争的中东……开创自由和扶持和平”。(注:“President George W.Bush Speaks at AEI's Annual Dinner”.http://www.aei.org/news/newsID.16197/news-detail.asp)2002年12月4日,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理查德·哈斯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表示美国要结束穆斯林世界“民主例外”的历史,因为美国相信“民主和平”论和“民主繁荣”论,只有中东实现民主化,美国的安全才有保障(注:Richard N.Haass,“Towards Greater Democracy in the Muslim World”.http://www.state.gov/s/p/rem/15686.htm)。2003年8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对美国全国黑人记者协会发表演讲,并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改造中东》的文章,对布什政府改造中东的战略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明确的概述(注:Condoleezza ice,“Transforming the Middle East”,Washington Post,August 7,2003,p.A21;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Condoleeza Rice Delivers Remarks a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lack Journalists Convention”,Washington Post,August 7,2003,p.A21.)。可见,从官方、民间这两个层次来看,美国彻底改造中东的战略确实是存在的。
当然,在如何落实“改造中东”战略上,美国国内并非没有分歧。比较温和与传统的一派观点认为,改造中东的“钥匙”是巴以和平进程问题,只有在中东实现了和平,才能逐步消除穆斯林世界的反以、反美情绪。至于伊拉克,由于海湾战争后萨达姆政权一直处于孤立和虚弱状态,因此只需要继续或者强化“遏制”政策即可。伊拉克问题并不是反恐斗争中的关键。(注:可参见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的观点。Brent Scowcroft,“Don't Attack Iraq”,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15,2002,p.A12.)这种方法能够抓住中东人民心中“巴以和平问题”这个“心病”,也是一种“治本”的反恐方法,但同时这也是一种相对缓慢的过程。比较强硬的观点则强调改造中东的重心应放在伊拉克,因为:(1)伊拉克这个由“非理性独裁者”控制的国家一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将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注: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an/Feb,2000.);(2)为了防止在中东及附近地区驻扎的美军遭受恐怖袭击,缓和中东人民对美军驻军沙特的愤怒,即使不考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美国也必须改变仅限于对伊遏制的政策(注:“Deputy Secretary Wolfwitz interview on NBC Meet the Press with Tim Russert”.http://www.dod.mil/transcripts/2003/tr20030727-depsecdef0462.html);(3)美国惟有“越来越多地干涉,竭尽所能地干涉”,才能推动民主的扩展,而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政权更迭”。(注:William Kristol,Lawrence F.Kaplan,The War over Iraq:Saddam's Tyranny and America's Mission,Encounter Books,2003.此书代表的新保守派对伊拉克的看法,可以代表强硬派对改造中东的思路。)鉴此,伊拉克可以成为改造中东的“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然后让伊拉克“启发穆斯林世界和阿拉伯世界,证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也可以创建民主国家”。(注:Michael Dobbs,“For Wolfowitz,a Vision May Be Realized Deputy Defense Secretary's Views on Free Iraq Considered Radical in Ways Good and Bad”,Washington Post,April 7,2003,p.A17.)
布什政府在中东问题上设定了两个假设:其一是对美国的安全、政治、经济、军事利益而言,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政体比不建立好;其二是推翻萨达姆政权是在中东实现民主化的前提条件。(注:Nikolas Gvosdev,“A Misplaced Faith? Arab Democracy and American Security”,In the National Interest,Vol.2,Issue 9,March 5,2003.http://www.inthenationalinte.com/Articles/Vol2Issue9/vol2 issue9realist 1.html)第一个假设是温和与强硬两派的共识;第二个假设则是强硬派的主张。应该说,强硬派的观点符合“9·11”后多数美国人的心理,也是一个能迅速“见效”的方法。在“9·11事件”的刺激下,在占据国内政治优势的强硬派的推动下,布什最终决定顶着世界多数国家的反对发动战争,表明强硬派的观点占据了上风。与此同时,温和派观点也并没有被湮没。2002年6月布什宣布将推出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此后也多次与有关各方讨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既用很大篇幅阐述了伊拉克构成的威胁,也提及扶持穆斯林温和政府以及解决巴以冲突的必要性,这正是两条路线的折衷和综合的结果。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正式宣布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布什、鲍威尔、赖斯先后出访中东,推动和平进程。
可见,美国改造中东的战略同时存在两个“引擎”:一是在东线发动伊拉克战争,主要由以国防部为核心的强硬派推动;另一个则是在西线推动巴以和平,主要由以国务院为核心的温和派推动。“双引擎”思路不同,重点不同,运转速度不同,但又统一在“按照美国价值观改造中东,实现反恐与维持美国优势双重目标”的思路之下。
二、战略特性
尽管美国的改造中东战略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从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大手笔”到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的出台,再到“美国—中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的缓步推进等等,我们已能清楚地看到这一战略的几个突出特性。
首先,是其体现的战略重要性。这主要反映在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表现为改造中东战略已上升为美全球战略的一个核心环节。如前所述,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从冷战结束到“9·11事件”之前这段时期,中东尽管对美国很重要,但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大棋盘中还算不上一个核心的棋子。特别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因素的消失和美国在中东主导地位的确立,中东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是相对下降而非提高了。克林顿时期美国对中东的若即若离以及布什上台之初对中东所奉行的“超脱”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东战略地位的下降。然而,“9·11事件”后,由于美国的安全关切发生本质性变化,反恐和防扩散成为“压倒一切的战略重点”(注:Samuel R.Berger,“Power and Authority:America's Path Ahead,”Brookings Leadership Forum,June 17,2003.),作为美国眼中恐怖主义“重要源头”和“无赖国家”“重灾区”的中东自然被其视为当前威胁的一个主要来源,该地区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分量明显加大。赖斯8月份的那次重要讲话实际上确认了改造中东战略的这一核心地位。她在演讲中将改造中东与二战后美国改造欧洲相提并论(注:“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Condoleeza Rice Delivers Remarks a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lack Journalists Convention”,Washington Post,August 7,2003,p.A21.),而此前包括布什本人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官只是将重建伊拉克与二战后重建德、日相提并论。赖斯的讲话无疑向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即美国改造中东是从重塑世界秩序的角度出发的,它是“9·11”后经过调整的美国全球战略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且核心的一步。另外,从美国两年来对中东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也可看出,中东已成为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第二个层次表现为改造中东战略是美全球战略的“试金石”,即前者的成败实际决定着后者的走向。“9·11”以来,布什政府的大战略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帝国主义”的特征,即基本依靠单边手段、通过改变现状来维持美国的“一超”地位或所谓的“单极体系”。显然,美国的改造计划绝不止于伊拉克、巴勒斯坦甚至是整个中东,美国要改造的其实是整个世界,美国要打造一个能确保“美利坚帝国”长盛不衰的世界。美国之所以选择中东作为改造的首选对象,一方面是出于该地区被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则出于可行性,因为与其他地区如朝鲜半岛相比,美国在中东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冲突不是非常尖锐,美国的战略推进空间相对宽广。因此,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第一步,改造中东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的一种战略尝试,其成败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未来走向影响深远:如果成功,肯定会增强美国进一步推进其全球战略的信心;但如果失败,难免会引发对美国大战略可行性的质疑。
其次,是其战略实质的代表性。改造中东战略既是当前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缩影,体现了美国大战略的单边主义属性。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组织了“志愿联盟”(Coalition of Willingness),但是这个号称数十个国家参与的“联盟”本质上并不是多边体系。根据约翰·鲁杰的研究,多边主义要建立在“一套明确的、普遍的行为准则之上”,这套准则应“与参与者的利益或所处环境无关”。(注:John Gerard 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No.3,Summer 1992,p.567 & 571.或参见约翰·鲁杰主编,苏长河等译:《多边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2页。)而美国的“志愿联盟”显然建立在美国单边的利益基础之上。即使就“反恐”或者“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样的“由头”而言,这一联盟也不是将一套准则一以贯之的多边体系。“联盟”要打击哪一国,如何打击,何时打击,完全取决于美国一国的利益和其对战略环境的判断。因此,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奉行的仍是单边主义,或至多是一种为某一具体问题而形成的“特定多边主义”(Ad Hoc Multilateralism)或“单一问题多边主义”(Single-Issue Multilateralism)。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美国虽与俄罗斯、欧盟、联合国一起推动,但是这也是一种特定多边主义,而且俄、欧、联合国在和平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实在非常有限。
改造中东战略也凸显了美国大战略的强意识形态色彩。布什政府在攻打伊拉克、改造中东的过程中反复攻击萨达姆政权和极端伊斯兰势力的“非道德性”,鼓吹美国式自由民主政体下个人自由、男女平等、宗教宽容等价值观的道德性,可见美国不仅是要“攻城”(推翻萨达姆政权),更是要“攻心”(以美国的“普世价值观”改造中东的价值体系)。布什政府在推行改造中东战略过程中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强调源于三个因素:一是恐怖主义本身的“非道德性”强化了美国以其价值体系改造中东的“道德性”。二是布什本人强烈的宗教信仰强化了其政策的道德因素。(注:肯尼斯·米诺格认为,布什政府正在试图以一种西方式的、现世思想的、后基督教版本的救赎思想征服世界。参见Kenneth Minogue,“Religion,Reason and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National Interest,Summer 2003,pp.127—132.)他的“弥赛亚情结”使其产生一种极其宏大的抱负,“他可以放弃‘十字军东征’这个词,但是战争的确使他成了一个十字军战士”(注:“Bush's Messiah Complex”,The Progressive,February 2003,pp.8—10.)。三是布什政府中影响很大的新保守主义哲学对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所赋予的强烈的道德性。
另外,改造中东战略还体现了美国大战略的进攻性。一方面,美对伊动武实际上是布什主义“先发制人”主张的具体实施,表明美国在必要时为保护自身利益、推进战略目标会毫不犹豫地主动出击;另一方面,美国将萨达姆赶下台并主导包括成立新政府在内的伊拉克战后重建,说明布什政府在中东实行的已不再是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相对消极的“维持现状”政策,而是一种试图彻底改变中东现状的进攻性政策。
再次,是其战略对象的整体性。众所周知,“9·11”前,美国将中东国家大致分为三类,即:以色列、土耳其、埃及、沙特、约旦、摩洛哥等传统盟友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等敌对国家,处于两者之间的“非敌非友”国家。对于不同类别的国家,美国采取的政策截然不同,可谓“爱憎分明”,具体而言就是美国对中东盟友基本持无条件支持的立场,而对敌对国家则予以无情打压。但“9·11事件”发生后,这三类国家的区别在美国眼中似乎已不如以前那样明显。最突出的例证就是“9·11”以来美国与沙特关系的微妙变化。许多美国人认为,像沙特这样的“独裁的”君主国,其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可能不亚于萨达姆的威胁,因此要求重新审视美沙关系的呼声不绝于耳(注:Romesh Ratnesar,“Do We Still Need the Saudis?”.http://www.time.com/time/word/article/0,8599,331980,00.html)。“双引擎”虽集中于两个“点”,其意则在“面”。2002年12月12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正式宣布启动美国—中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该计划试图以开放经济、开放的政治体制和教育改革推动中东的民主化,它实际上成为继伊拉克重建、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之后,美国改造中东战略的第三大支柱。由此可见,过去所谓的三类国家实际上已被美国视为一盘棋,尽管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即美国最终都要将它们改造为民主国家。
最后,是其战略手段的多样性。如果说伊拉克战争给人留下美国改造中东战略具有很强军事色彩的深刻印象,那么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巴以和平路线图计划的推进更突出外交手段,而美国—中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则强调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的多管齐下。对于伊朗和叙利亚这样的所谓“无赖”国家,美国目前仍限于依靠外交和情报手段加强遏制与打压。换句话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随着美国投入伊拉克重建,围绕巴以和平进程与伊朗核问题展开外交努力,继续推动美国—中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提出中东自由贸易区的经济设想,以及对伊朗大搞情报渗透等等,美国改造中东战略的手段已从前一段时间以军事当头回到了军事、外交、情报、经济几手更加平衡的方式。
三、优势与限度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速胜确实使其改造中东战略获得实质性推进,但近来伊拉克安全局势的恶化以及巴以关系的反复又让人看到美国在该地区面临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改造中东战略的前景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鉴于改造中东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影响,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显然,改造中东是布什政府的既定意愿,但战略意愿要受到战略能力、战略环境以及战略特性等多重因素的限制和修订。从目前看,影响战略意愿的这些因素几乎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两面性,因此很难以成功或失败来简单地预测美国改造中东战略的走向,而只能说它将是一个在曲折中前行的漫长过程。
从战略能力上看,美国一方面从理论上完全具有改造中东的能力,而且这一能力还因美在伊战中的获胜而有所加强;而另一方面美国的这种能力本身又确实存在限度,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雄厚的实力基础已成为其对外战略能力的坚强后盾,无人怀疑美国实施其改造中东战略的严肃性和能力。但其能力的限度也是明显的。军事上,拉姆斯菲尔德原本宣布11月份将换防4万名驻伊美军,但据说现在他很难找到能够接受这项任务的美国军队(注:朱锋:“新决议草案未改变美重建战略”,http://www1.chinadaily.com.cn/gb/doc/2003—09/05/content-261451.htm)。经济上,尽管布什政府继今年4月获国会700多亿美元战争拨款后,近日又提出追加870亿美元,而且看来获国会批准的可能性很大,但考虑到美国现在完全是自己掏腰包,填充这个无底洞对美国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心理上,随着驻伊美军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增大,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美国公众对布什当前伊拉克政策的支持正经受严峻考验。9月4日,美国向安理会提交伊拉克问题新决议草案,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其在上述三个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这样,从美国抛开联合国单独对伊开战,到战后美国将联合国的作用限定于人道主义领域,再到目前要求联合国与美国分担“负担”,已清楚地说明美国战略能力的限度。
从战略环境上看,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包含正反两个方面,为布什政府的改造中东战略既创造了新的机遇,也带来新的挑战。就国际环境而言,伊战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制约能力进一步下降,但同时又未完全失去这种制约力。在此次伊拉克战争之前的外交角力中,“反战轴心”未能阻止美国发动战争,显示国际社会在中东问题上基本无力制约美国按其意愿行事。欧盟和俄罗斯在战后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也在伊朗核问题上不同程度地与美进行了合作,并在推动巴以“路线图”上与美积极配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它们已接受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中东霸权的强化。不过与此同时,此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严重损害了美欧关系,土耳其等中小国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也受到损害,美国陷入了一种“霸权孤立”的状态。近日,法、德对美新伊拉克决议草案提出的异议以及鲍威尔所表现出的愿意听取法、德意见的“谦逊”态度,说明连美国自己也认识到国际制约的存在和不容忽视。就地区环境而言,伊战后美国在中东的强势地位进一步巩固,但也面临战略困境。战前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虽“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在中东形成了一种地缘上的“板块”。而伊拉克战争从中心打碎了这一整体,美国得以分别“钳制”住伊朗和叙利亚等国。而且,萨达姆政权的垮台和美国在中东军事部署的调整使得沙特等美国中东传统盟友的战略重要性明显下降,这些国家抵制美国压其改革的能力弱化。战后的伊拉克、甚至可能还有正在进行内部民主改革并将最终建国的巴勒斯坦,正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新战略支点。由于它们地处中东和阿拉伯的心脏地带,美国在这两地所推动的变革将会对整个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不过与此同时,必须看到伊拉克重建给美国带来的困境。2003年6—7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伊拉克陷入混乱的可能一天比一天大”,美国要作好“在伊拉克呆上好几年的准备”。(注:CSIS report,Iraq's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http://www.csis.org/isp/pcr/IraqTrip.pdf)这将在一段时间内束缚美国在中东的手脚。就美国国内的外交决策环境而言,伊战的胜利强化了美国决策层中的保守力量,而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又将对布什政府的政策选择形成限制。一般来说,美国总统选举周期必然影响其中东政策。有研究表明,美国总统会尽量避免在任期第四年推出新的行动和倡议。(注:Maria do Ceu Pinto,Political Islam and the United States:A study of U.S.Policy towards Islamist Movement in the Middle East,Reading:ITHACA,1999,p.36.)面对越来越近的总统大选,布什可能会倾向于在中东采取较少冒险色彩的活动,选择在既有框架内改造中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策略。
从战略特性上看,美国改造中东战略本身有其固有的优势和限度甚至是缺陷。改造中东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将确保该战略的生命力,即使美国在战略实施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也不会轻言放弃,这也正是当前美国在求助于联合国时坚持只分享“负担”而不分享“权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同时,美国改造中东战略手段的多样性实际上增加了该战略的灵活度。为美国在应对不同或同一战略对象时都能有较多的政策选择。然而,美国改造中东战略对象的整体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战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东地区共有22个国家,其中只有以色列和土耳其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这就意味着美国至少要在中东改造20个国家。目前,单是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已把美国搞得焦头烂额,它们何时以及能否发挥“辐射”作用都还是未知数,加上其他18个国家又各有各的特点,因此美国的改造中东战略绝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难怪赖斯说美国要为此付出“一代人的努力”(注: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Condoleeza Rice Delivers Remarks a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lack Journalists Convention”,Washington Post,August 7,2003,p.A21.)。另外,在美国大战略支撑下的改造中东战略很难走出本身所固有的困境。一方面,单边主义使美国的行动往往“师出无名”,而其他大国或与美国保持距离或发出反对声音,这就很容易凸显美国的霸道与进攻性,从而破坏美国的国际形象,削弱美国的软实力。民意调查显示,与2002年相比,目前对美国有好感的英国人从75%下降到48%,法国人从63%下降到31%,德国人从61%下降到25%。(注: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American's Image Further Erodes,European Want Weaker Ties”.http://www.people-press.org/display/reports/display.php3?PageID = 175)反过来,美国修补大国关系的需要、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开展修补形象的公共外交的需要都将限制美国在中东的政策选择范围。另一方面,美国大战略的强意识形态色彩有可能激化美国与中东穆斯林的矛盾,从而增大美国改造中东的难度。由于布什政府将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赋予了高度的道德性,而与此同时,中东穆斯林国家的人民认为自己的伊斯兰价值观和政治社会体制更具有道德性,两套自足的价值体系“相撞”,轻则可能激化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干扰美国的反恐战略,重则可能酿成“文明的冲突”,使中东地区陷入持久的混乱。
综上所述,改造中东是布什政府既定的长期战略目标,美国非常自信拥有改造中东的战略能力,同时伊拉克战争也确实为美国创造了一定的战略机遇,而美国的大战略则为其提供了战略支撑。但由于美国的战略能力存在限度,战略环境不乏挑战因素,加之大战略的自身缺陷,美国改造中东战略的推进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评估与修正的过程。
标签:伊拉克战争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中东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乔治·沃克·布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