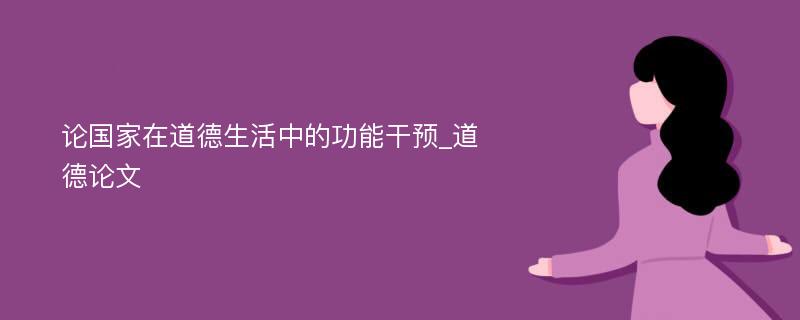
论国家对道德生活的功能性干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功能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对道德生活的干预这一职能日臻完善,并通过不同的功能性活动来支持其职能的实现。这些不同的功能性活动包括:调节日常道德生活,构建道德秩序,缓解道德危机,推进道德变革,营建高尚社会。现分述如下。
调节日常道德生活
在现代,国家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几乎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个人作为一个公民的所有的生活领域。这些影响是通过现代国家的干预而发生的,它可以决定我们的日常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学校教育的性质、纳税的数额、住宅的居住规模、退休人员的生活,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私生活、夫妻关系和家庭规模、娱乐方式和社区生活等。
政府对人们的日常道德生活进行控制和干预,主要地是通过调节道德关系、安排道德行为和分配道德利益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的。
道德关系的调节,是国家对人们的道德生活进行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的道德生活的背后有某种东西存在着,它能够引发行为,并通过这些行为而形成特定关系。这种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欲望。但是,国家不能直接地限制人类的欲望,它只能通过一种外在的途径,即围绕这些欲望而形成的道德关系来调节和控制,使之沿着一定的方向,按照规定的路线来加以满足。这些关系经过历史的发展之后,形成一定的体系化的道德制度。
道德行为的安排,是国家对人们的道德生活进行干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在道德生活中进行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特定的个体行为来完成的。这样,对人们的道德行为加以限定,就成了国家对个人日常道德生活进行调节的重要途径。国家根据对人们道德生活的划分来对其行为加以安排,设定可以行动的和不可以行动的行为,并对好的行为加以认定和奖励,对不好的行为加以制裁和惩罚。
道德利益的分配,也是国家对日常道德生活进行干预的一个方面。一个人的道德需求,会在国家干预中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的需要。这种需要,就其客观性来说,就是具有国家色彩的道德生活的公共利益。按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界定,“‘公共利益’是由公民们的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愿望构成的”(注: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6页。)。法学家庞德对利益所下的定义是,“个人对享有某些东西或做某些事情的要求、愿望或需要”(注: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5页。)。他还把利益区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直接包含在个人生活中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它又被分为人格的利益、家庭关系方面的利益和物质利益。人格的利益是包含个人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利益。具体而言,包括:保障个人的肉体和健康方面的利益、自由行使个人意志的利益即免受强制和欺骗(那些使人被迫在不了解真相时去做)、自由选择所在地的利益、一个人的名誉(诽谤)、契约自由和同别人自由地发生关系、自由信仰和自由言论。对于公共利益加以区分是重要的。从本体论上说,道德的利益完全不同于经济的利益,这是因为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对象领域。经济利益的对象是物或货币,而道德利益除了物之外,还有人,譬如家庭中的夫妻性行为以及朋友间的友谊行为,其对象都是人。在所有利益当中,只有一部分是属于道德生活的,而其他一些则不属于这一范围。道德方面的公共利益,也被视为一种公共福利,它是人们在实现自身的道德需求时所必需的。英国学者格林指出,公共福利就是人们设想与他人共有的东西,与他人共享的善,而不管这善是否适合他们的嗜好。对于这些道德方面的公共利益,国家是通过干预来加以分配和调节的。
构建道德秩序
国家对人们的道德生活进行干预,还通过构建某种道德秩序来进行。我们说,在人们的群体生活中存在着某种“秩序”。有人断言,秩序被认为是一种与事物本性相关的东西。但这一看法为哲学家斯宾诺莎所反对,他说,秩序并非自然本身所固有,而是与我们的想象有关的(注:引自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8页。)。此外,秩序还被一些学者看成是有规则的模式,它为人们加以利用提供了便利。弗洛伊德说:“秩序是一种强迫性的重复。当一条规律被永久性地确定下来时,秩序就决定一件事应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做,这样在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必犹豫不决了。秩序的好处是无可争议的。它使人们能够在最大限度内利用时空,同时又保持了他们的体力。”(注: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秩序是事物和行为之间即时发生的均衡状态。哈耶克对此论证道,“均衡是一种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且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必然是即时相继发生的。只要想赋予均衡这个概念任何意义,时间的描述都是极其重要的。这点值得一提,因为很多……在均衡分析中似乎都没能发现一个处在均衡当中的时点,所以他们声称均衡必定是个没有时间概念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好像是无稽之谈。”(注: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实际上,在人们的群体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秩序。这种秩序可以区分为两种,这就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秩序和存在于国家中的公共秩序。
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秩序,也就是在传统的市民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表现出一种接近于自然的秩序,它由在自然需求基础上形成的礼俗和习惯调节着,并在其中形成一种等级制。这种礼俗和等级制造就了某种自然秩序。哈耶克说:“在社会关系中的非强制性惯例仍被认为是保持人类社会有秩序运行的本质因素。”传统和惯例生成了自然状态的社会秩序,是因为人们在许多场合仍然方便地按照某种运行已久的行为方式而行动。对于这些惯例,“参加社会过程的个人一定时刻准备并且愿意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并且随时愿意服从并非智力设计结果的惯例;尽管这些惯例在具体场合的公正合理性也许无法承认,并且对他来说也许是难以理解和非理性的”(注: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22页。)。存在于国家中的公共秩序,表现出了一些极其明显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它表明了当前公共生活具有一种法定的性质。公共秩序与法律、政策密切相关,其秩序化的程度和对个人的法定的限制程度是相关联的。在影响这种秩序化程度的诸因素中,国家的强制措施及其手段,其中包括政府的法律、公共政策的体系化水平、执法官员的能力水平等是相当重要的。公共秩序的法定性是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社会的自然秩序转化为国家的公共秩序时,作为由法律和政策支持的这种公共秩序,其框架便是制度。法学家庞德说:“现在所称的法律秩序——即通过有系统地、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制度。”(注: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第22页。奥罗姆说:“社会秩序包括经济基础、宗教和家族制度,政治秩序只是包括国家及有关制度。”(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从本体论上说,这是一个含义模糊不清且区分混乱的论断。)制度被包括在秩序的概念之中,表明被合法化过程所确立的制度构建了公共秩序。换句话说,建构公共秩序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公共生活诸要素之间建立起一种有序化的制度。
一方面,道德秩序的建立过程是在历史中完成的,即它是从自然伦理、习俗、自然法,最后才前进到由法律与道德公共政策来创立的阶段。另一方面,道德秩序是国家干预的直接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把“国家”理解为“社会秩序”。他说:“可以把国家界说为一种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国家是一套约束个人之间彼此行为的规则,一种可以用下列要点来表明的秩序,它是一种强制的秩序,那就是说,它企图用强制措施来制裁所不期望的人类行为,从而实现所期望的人类行为。那就意味着这个秩序是一个法律秩序。”(注:凯尔森:《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页。另一位政治学家普朗查斯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国家是调和一个社会形态的统一因素,……即国家是一种社会形态的‘秩序’或‘组织原则’;但这并不是指现代意义的政治秩序,而是就它能够起着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的所有各个方面调和的意义而言,并且是作为调节这个体系综合平衡的因素而言。”(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这表明,道德秩序是可以被营造出来的,可以加以维护,也可以被破坏,最后,它也是可以重建的。这种有序化及其调适,对于道德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现代,法律与道德政策就是用于构建道德秩序的手段。
缓解道德危机
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有时会出现一种短期的道德危机。在危机发生时,由异常行为,到社会风波,再到骚乱,原先潜在的威胁变成了明显危及公共生活的事件,直接使道德生活的有序化变成紊乱的和失调的,有时甚至变成失控的,道德生活陷入瘫痪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一般人在当前的道德生活中丧失了以往的标准,同时又没有新的标准作为日常行动的依据。道德危机是可以加以控制的,它在某种规律的支配下,可以为政府所控制。在危机发生的时期,国家可以通过对道德生活的干预,提供某种道德上的解决方案,确立起保障人们安然度过道德危机的有效机制。因此,缓解道德危机,就成了国家的道德职能的一个方面。
道德危机的种类,按其引发的原因不同可以区分为多种。
1.高危行为失控型道德危机。在道德生活中,在一定时期或一个地区会出现高危行为群体,形成一股社会风潮,从而引发道德生活危机。这些高危行为群体,如异常行为群体、“另类”颓废群体、流氓团伙、黑恶势力等。他们在道德生活上放荡、酗酒、吸毒、淫乱,制造一系列邪恶的生活事件。这些堕落行为常常会在短时期内迅速蔓延到道德公共生活的各个角落,使家庭破裂、性关系紊乱、凶杀案增加,进而引起道德生活和道德关系的混乱。
一般地说,这种类型的道德危机具有统计学的特征,它本身是发生频率高的高危行为,其数量可以通过指数标示出来。加拿大学者哈金指出,“正确的和良好的位于正规曲线的右手端,那里才是天才或德行所在。”(注:哈金:《驯服自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作为另一端,便应是恶棍或恶行所在。当把这些加以统计,其测定超过平均值时,道德危机就会发生。
2.变革型道德危机。在变革时期比在平稳发展时期更容易发生道德方面的“社会流行病”。在变革时期,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带来了繁荣,也使各种新的道德价值观念迅速传播,不同的道德利益冲突加剧,人际关系越来越不稳定,家庭关系也处于变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道德生活无形中增加了更多的风险,诸如离婚率、自杀率和犯罪率的增加,都是由这种变革引起的。
3.转移型道德危机。一种危机可以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这是危机的一个共同特征。在公共生活中,当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发生时,它们可以通过某种形式将其转移到道德生活的领域,引发道德危机。古罗马帝国和中国东汉末期汉王朝的崩溃过程,就是明证。
那种相信道德危机在最后会自动恢复平衡的观念,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应该相信,在偏离正常、出现风波与道德危机的情况下,干预是一种必要的和有利于使平衡得以恢复的政府行动。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国家的道德干预才能最后缓解和消除道德危机。在道德发展史上,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政府管制来创造一个较好的公共道德环境,并掌握了如何有效地控制堕落扩散的方法。
推进道德变革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道德进步,只有在国家的干预下才能顺利地得以实现。这一过程,就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表现出来的道德变革。人类是怎样由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的伦理状态,然后又过渡到国家的道德状态的,怎样由最初的约定发展到公约,再发展到法律和道德政策,这完全是经由道德生活本身不断的变革来实现的。
公共领域作为包含人际关系在内的一种结构,作为个人生存环境的存在方式,它本身也处在一种成长与变迁的过程之中。在公共道德领域,道德变革在许多重要的道德组织结构中是有所体现的。作为一个渐进的变革过程,(1)它促进了社会中各种道德性质的组织结构和其领域的逐步扩大。在实际变革中,某些组织为了适应周围环境的压力,确实发生了多种形式的演变。(2)合格的道德公民人数的增加。人在伦理和道德的领域内发生的这种向前的变化,作为一种人文环境的存在,对此我们称之为道德生活的历史化。经过这一历史化过程而形成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或“文明化”。哲学家康德曾对此加以分析说,“我们由于艺术和科学而有了高度的文化。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礼貌和仪表方面,我们是文明得甚至于到了过分的地步。但是要认为我们已经是道德化了,则这里面还缺少很多的东西。因为道德这一观念也是属于文化的;但是我们使用这一观念却只限于虚荣与外表仪式方面表现得貌似德行的东西,所以它只不过是成其为文明化而已。……任何一个共同体为此而塑造它的公民时,却需要有一场漫长的内心改造过程。然而,凡不是植根于道德上的善意的任何一种善,都无非是纯粹的假象与炫惑人的不幸而已。”(注:转引自哈金《驯服自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道德发展,经历了长期的道德上的变革。
在道德变革与整体的公共生活变革的关系方面,两者是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状态之中的。在道德公共生活领域内发生的变革,是整体的公共生活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道德生活的进步本身作为公共生活变化的原动力之一,作为一种变量,对整体的公共生活来说,有时它是自变量,有时则是应变量。具体地说,道德变革的推进涉及到公共场所的变革,涉及到风俗、时尚的变革,还有时作为道德生活之物质基础的变革,都将直接地或间接地与整个公共生活的变革相联系。这表明,在道德领域内发生的新的变化,有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其他领域随之发生变迁。道德变革在推动公共生活整体发展的同时,也改进了道德自身。
在道德变革的过程中,作为道德变革的心理倾向,人们内心存在着“逐渐过时的因素”和“对新事物的恐惧”。后一种恐惧的产生,是基于他对将受制于普遍的不适应的担心——对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来的经常性危险的忧虑。变革作为一连续性的创新,意味着用一个人并不熟悉的生活来对已经熟悉的旧生活方式实行革新和替代。这种革新和替代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多么愉快的生活经历以及必要的变动。而且,这也会对人造成短期的道德生活上的失调。特别是都市化,以及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不同文明间的冲突,都对道德生活领域的变革产生重要的影响。都市化给人们的道德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新的联系,特别是经济变革给道德变革带来某种直接的动力。从为人们提供最现代的住宅、交通、传播媒介条件,如电视和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等,到为人们提供现代化的家电,如冰箱、空调、微波沪、洗衣机,还为人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家庭生活、公共交往场所。这些新的联系和新的沟通手段。对于改进旧的道德关系和旧的道德交往方式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传播新的价值观念、改变旧的价值观念方面,大都市在整个国家控制的道德生活中具有重大的积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社会学家帕森斯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发展为连续的社会生活合理化过程的理论,认为在任何具体的(社会活动)体系中,变革过程只能朝着在该体系中对活动者具有约束力的理性准则的方向发展。正是那些新东西和新观念每天都出现在人们的身边,为人所亲眼目睹,为人所感受,它们给人们带来道德生活上的进步。
我们不能忽略对道德变革的研究。提示这种道德变革是由什么原因引发的、用什么方法来促进其变革,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中,道德公共政策作为国家实施控制的一种手段,它的成功运用可以有效地推进道德变革。
营建高尚社会
国家对道德生活实施控制的目的,是营建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人类一直努力创建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在这个高尚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要素,譬如,需要有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责任感、个人的优雅与教养程度、成员间广泛的互助、政府对个人尊严的尊重程度、社会生活本身的道德化进程等。这些因素可以经由良好的道德政策而在公众中将它培植起来,形成风尚。这些道德政策体现了公众的共同意志,经由某个政治领袖或政府机构提出和认定,体现了当前道德生活的发展水平,这是国家的道德职能所要实现的。在实现这个职能的过程中,道德政策为教导人们过一种规范化的道德生活而创设,为了公众的幸福,为了他们享有繁荣而被制定出来。
营建一个高尚社会,与国家的道德职能有关。国家履行道德的职能和它所营建的善的生活形态,既是一种道德上的最终目标,也是国家实施道德控制的最终目标。在此,国家营建的高尚社会,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道德制度。一个好的道德制度是这样的:在这种制度之下,道德生活的秩序能够得到保障,生活于其中的公民特别期望自己对国家与社会能有所贡献;他们自由而健康地生活,并且还能使他们从适应历史进化本身得到好处。在这一道德制度中,以人性的与理性的因素为其核心,使人民勤劳、和睦地生活,迸发出对于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热情。在这个由道德政策所营造的高尚社会里,公民由于受道德政策的指导而有更多的良好行为,更少的纠纷与冲突。做出这些好行为,一部分出自于荣誉心,另一部分则出自于对道德政策所界定的行为规则的自觉遵守。在这个道德制度中,一个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人,可以享受到追求社交生活的乐趣,更好地理解到自己的道德利益是社会性的。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道德制度,可以促进当前社会的伦理生活和国家的道德生活,使之成为和睦、和谐与富有建设性的。与此相反,不好的道德制度则使人民彼此不睦。因此,一项好的道德政策是自由与和睦生活的重要条件。
营建高尚社会,还需要建立起良好的道德关系。理想的道德关系,是和睦、相互谅解、友好、合作和有真挚情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的公众幸福与公共秩序,是国家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不但是政治的、经济的目标,它还是道德的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国家的作用是重要的。它将个人的需要纳入一定的范围之内,一旦削弱政府对个人的作用,就会使人际交往的基础遭到破坏,就会出现社会与个人的分裂状态。这种状态一旦出现,就会在个人交往中出现自然力量压制文明力量并占上风的倾向,使个人道德生活的基础解体,进而会加速道德公共生活的解体。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人需求和情欲标准的调节系统就会发生紊乱,就会导致个人的个性被扭曲,丧失维持道德生活所必需的集体感、纪律性、社会团结和社会责任感等,最终导致各种个人的越轨行为和相互伤害行为的增多,导致个人的道德生活走向分裂。因此,在社会未发展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也即在国家消亡之前的历史时期,国家对道德生活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由此种干预过程而产生的国家的道德职能,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政府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