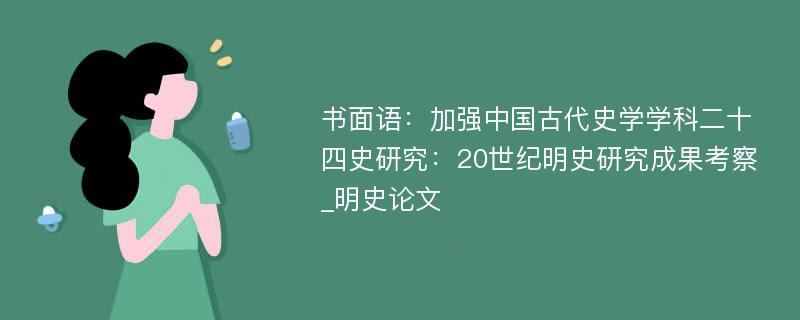
笔谈:加强对中国古代史学主体二十四史的研究——20世纪《明史》研究成就巡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加强对论文,二十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史学史研究角度而言,《明史》作为二十四史之一,与其他正史相比,有两个特点:
一是该书的修撰用时最久。从清顺治二年(1645)开局诏修,到乾隆四年(1739)书成刊印,阅时达九十五年。撰修期间,凡四次开馆,五换监修,七易总裁,撰修官更进进出出,见于记载的将近百人,其写写停停,一波三折。史稿改动也较大,从编修人的底稿,到主编的删削增润,以及后续主编的再次加工改动,内容和体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有人说,《明史》也是官修史书中最难产的一部。
二是该书是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其修撰时间距今最近。该书的底稿和涉及的资料保存至今的最多。《明史》的撰修,依据明实录等官方文献,也间采野史、笔记、文集、方志等,这些文献还有许多留存于今世,为人们对《明史》的撰修过程、体例设置、记事真伪等等做详细考察提供了条件。
因此,在清亡之后的20世纪初,对《明史》进行研究似乎已是一种学术上的迫切需要,也是学术发展的应有之义。
清亡之后,继承中国史学的兴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1914年即成立了清史馆。刘承幹于1915年编集刊刻《明史例案》,把当时可以找见的关乎《明史》纂修的文献,诸如诏书、上疏、信札、移文、凡例等,搜罗殆尽,本是为供清史馆借鉴之用,却为日后研究《明史》的撰修过程提供了集中的资料。
稍后,专门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明史》研究大致呈两个主要阶段,即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
20世纪30年代初,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金陵学报》,1卷2期,1931年)和李晋华《〈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二文发表,对《明史》的编纂过程作了详细考辨,标志着系统研究《明史》的开始。30、40年代的研究除着力理清《明史》的修撰过程、参修人员、组织结构、运作方式等问题,还集中研究了《明史》稿本及王鸿绪是否攘窃的问题,一时俊彦硕学纷纷就此问题发表意见,柳诒徵、孟森、吴晗、张须、侯仁之等大家,都在报刊发表了相关文章。这个讨论的余波,延及40年代。
1949年以后,《明史》研究在港台继续进行,包遵彭编辑的《〈明史〉考证抉微》(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和《〈明史〉编纂考》(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两本书,集中了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的主要研究论文,其于《明史》研究的贡献可与民国初年刘承幹刊刻《明史例案》相埒。
而在大陆,自1949年至文革结束前的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陷于沉寂,几无力作问世。只有个别学人在私下坚持研究,如黄云眉《〈明史〉考证》一至八册,虽是在1979-1986年整理出版,但其初稿就写于文革以前。这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郑天挺先生主持下,由对《明史》素有研究的汤刚、付贵久等人完成了《明史》的标点和校勘,并于197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进入新时期以来,《明史》研究在大陆兴盛起来。在继续致力于编纂过程的梳理和稿本的辨证的同时,研究视野不断向纵深发展,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开始注意撰修者及其思想,注重对《明史》各组成部分(纪、志、表、传)进行个案研究。汤斌、徐元文等总裁官,姜宸英等撰修官,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等与《明史》撰修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学者,皆被纳入研究视野;《明史》的《食货志》、《艺文志》、《刑法志》、《文苑传》、《道学传》等也被专门研究。
在历时百年的研究中,从史学角度看涉及的问题主要有:《明史》修撰的指导思想以及历史观;体例体裁的特点;编修进程的阶段划分;总裁、史官的分工、进退和贡献;各种志传稿本及其分撰诸人的作用;各种版本的流传与收藏,等等。从史料与史事考证看,有对《明史》记事内容的具体批评,也有对《明史》的标点、整理。十几部研究专著和近300篇论文的问世,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明史》、读懂《明史》、进而研究《明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明史》研究是深入的,成绩是辉煌的。这是经过几辈学者艰苦努力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当然,《明史》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对于《明史》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研究,有分量的文章还不多,不仅比不过对《史记》《汉书》的研究,甚至比不过《新五代史》等的研究;对《明史》诸志的研究也还刚刚起步,与《史记》等正史的有关研究也存在一定距离;《明史》作为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其在纪传体上的因循和创造,也未曾得到认真的总结。
进入21世纪以后,《明史》研究的脚步并未停歇。在新世纪之初,就有许多新著问世。研究范围明显扩展,如对《舆服志》《兵志》《礼志》《选举志》等的研究,扩大了对诸志的研究范围。但是,我们期待的新世纪的《明史》研究应该是更富有生气和活力的。即便是在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时,研究传统课题时,也应当展开新的视角。《明史》作为最后一部正史,负载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我们应当跳出既有的思维模式,尝试从新的视角和范围去认识《明史》。比如,能否不再局限于对谁剽窃了谁的追究?《明史》的撰修本是由撰修官初拟、由总裁或其他学者受总裁之托审改的,一个环节也不可缺少,以往就欠缺了对初拟稿的关注,现在的《明史》哪些使用了初拟稿,哪些才是经总裁该定的?注意及此方可捕捉到史馆的思想与史官个人的思想的不同,才可以看出官方的思想倾向是什么。再如,能否不再就稿本谈稿本,怎样才能把《明史》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联系,通过研究《明史》了解清代的学术氛围和社会意识,这也是一个以前所忽视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史记》所关注的问题,未必应该是《明史》所关注的。透过对《明史》所记内容、取材视角的独特之处的分析,可以了解清代史家的关注点,了解清代史学的特色。
总之,新世纪的《明史》研究应该是百花齐放、色彩斑斓的,应该在继承传统学术的基础上走出新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