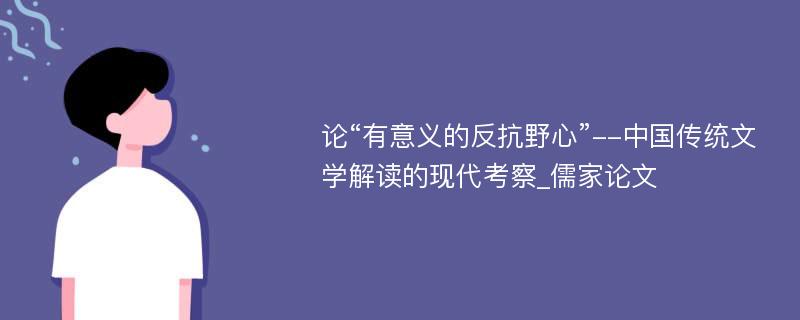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意逆志论文,释义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方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2)04-0106-07
“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首先是由孟子在和弟子讨论如何正确理解《诗》义时提出来的: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
在孟子看来,咸丘蒙是一个不能正确理解《诗》义的人。咸丘蒙的疑问是:俗语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但《北山》诗却说普天之下都是天子的臣民,那舜的父亲怎么办,他是否也是舜的臣民呢?孟子认为,咸丘蒙的问题就出在“断章取义”上,他只抓住个别的词句,而忽略了对《诗)义的整体的理解。由此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事实上,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的释义方式不仅仅是一种理解和解释《诗》义的方式和方法,经过后世诸多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实践和总结,它已经上升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释义原则和释义方法,其中甚至还蕴涵有某些可与西方现代解释学理论相沟通的理论因子,应该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总结。
一、“以意逆志”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
作为中国文学解释学最重要的文学释义方式之一,“以意逆志”中的“意”、“志”、“逆”三字十分重要,是我们把握其文学解释学思想意蕴的关键,应加以阐释。
首先说“意”。孟于提出的“以意逆志”的“意”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以意逆志”之“意”是作者之“意”,也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情感。如清代学者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以意逆志节》,就将“以意逆志”理解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今人赵则诚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和彭会资主编的《中国文论大辞典》等也持此这种观点。但这种观点颇有令人疑惑之处,因为如果按照吴淇的解释,既然解释者已经弄清楚了古人之“意”,那么解释者对作品所传达的古人之志”的把握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然而对于文学释义者来说,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从文学释义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年代的久远、作者的湮灭、历史背景的模糊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多数时候对于诗作品的接受者和阐释者来说,所谓“古人之意”,是并不清楚而且难以弄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谈“以古人之意逆古人之志”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赞同把“意”理解为作者的情感和志意。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以意逆志”的“意”乃说诗者之“意”,汉宋两代的学者大多持这种看法,现当代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看法表示认同:
汉代赵歧《孟子注疏》解释说:“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宋代朱熹《孟子集注》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近人朱自清《诗言志辨》云:“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
今人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亦云:“‘意’是读诗者主观方面所具有的东西,……所谓‘以意逆志’,就是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去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1](P194)
需要特别补充说明的是,近年来王先霈和赖力行二位先生对“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法提出一种极富启发性的新见解,他们认为:“以意逆志”中的“意”不应该作为名词训释为志意,而应该作为动词理解为意度、揣测和体悟,“以意逆志”就是指接受者和阐释者用推想、推理、玩味、体悟的方法来获取诗人的创作旨趣。[2][3]二位先生的见解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以意逆志”文学释义方法的理论本义作出更为精确的把握。
那么,对上述两种看法究竟应该作怎样的评价呢?我们认为,把“意”理解为接受者和阐释者的心意,或者理解为接受者和阐释者对作品的意度、推想和体味,都是基本符合孟子的理论本义的,因为孟子自己的文学释义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在《孟子·万章上》中,孟子和咸丘蒙讨论《诗经》中的《北山》和《云汉》,在《孟子·告子下》中,孟子和公孙丑讨论《诗经》中的《小弁》和《凯风》,都是根据“己意”,即孟子自己对作品的意度、推想和体悟来纠正咸丘蒙和公孙丑的片面看法,从而达到对作品意旨的正确理解的。
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提出以“己意”来探求作品的意旨,反映了他对文学释义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因为文学释义活动从来就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完全没有释义者主体意识的介入是不可能的。在文学释义的过程中,接受者和阐释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阅历、思想情感和审美需求对作品进行感知、体验、思考和评价,接受者和阐释者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解释也总要打上自己思想的印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文学释义活动最终所获得的都只能是“己意”,而决不是“他意”。孟子以后的许多文学批评家和文学释义学家正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和运用“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法的,如宋人朱熹说:“书用你去自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朱子语类》卷十)清人章学诚亦云:“文章的妙处,贵在读者的自得。如食品甘美,衣服轻暖,各自领会,难以告人。只能让人自己去品味,自会得到甘美的味道;自己去穿着,自会产生轻暖的感觉。”(《文史通义·文理》)
总起来看,孟子及其后学强调以“己意”来意度、推想和体味作品的意旨,是对文学释义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它强调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参与,突出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在文学释义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肯定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这种解释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说“志”。尽管孟子的“以意逆志”之“意”如我们所理解的是解释者的主体意识,但在孟子看来,解释者的这种主体意识绝不是像天马行空那样不受任何限制,恰恰相反,解释者主体意识的释放总是要围绕一定的目标来进行的,这个目标就是“以意逆志”的“志”。不过,孟子所说的“志”究竟指什么,目前学界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志”为作者之志,也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怀抱。如汉代的赵歧将“志”解释为“诗人志所欲之事”(《孟子注疏》卷九上),宋代的朱熹释“志”为“作者之志”(《孟子集注》),现代学者朱自清也以为“志”乃“诗人之志”(《诗言志辨》)。
第二种意见认为“志”为作品之志,也即作品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如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和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就指出:“诗人的‘志’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而是蕴涵在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之中”,所以孟子所说的“志”就是“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1](P195-196)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志”是“记载”的意思,即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如郭英德等人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就持这种观点:
“志”的本义是记忆、记录,“诗言志”的原始意义即是向神明昭告功德、记述政治历史大事,而不是指抒发个人志意、情感。在孟子的时代,尽管“志”已经有怀抱、情志之意,已经有“诗以言志”、诗“可以怨”、“盍各言其志”(《论语·公冶长》)等说法,但“志”的记事之意和“诗言志”的原始意义仍然保留着,将诗歌创作真正看成个人志意的表达,还是孟子以后的事情。孟子本人的说诗方法,……恰恰是着重于诗对历史或现实现象的说明,即诗的记事之义。[4](P27)
另外,陈望衡先生新出的《中国古典美学史》也持相同的看法:
如果把“志”训作记载,把《诗经》的本质看作史,孟子的“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好理解了。“不以文害辞”,即不因诗经用了一些夸张、比喻、象征之类的修辞手法而影响对辞义本身的理解。……“不以辞害志”,即是说,在《诗经》主要是记事,要善于通过言辞去了解所记载的当时的史实,……而不要为辞的表面意义或歧义所误导。“以意逆志”中的……“志”是《诗经》所记载的史实……[5](P146-147)
那么,关于“志”的这三种理解到底孰是孰非呢?这三种意见尽管有细微的差异,却并无本质的不同。因为无论是把“志”理解为作者之志,还是理解为作品之志,抑或是理解为作品所记载的史实,从总体上看,它们都可以归结为作者或作品所表达的原意。这即是说,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学解释学方法,“以意逆志”是把“志”也就是作品的原意当作自己探求的根本目标,而作品的原意既可能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可能是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还有可能是作品所记载的史实。这一点,从孟子对《诗》的解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如他批驳弟子咸丘蒙对《北山》诗的误解,提出该诗表达的是“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的怨情,就是对作者之“志”的探求;而他不同意咸丘蒙对《云汉》诗的误读,认为诗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的描述属于艺术夸张,旨在说明“旱甚”,而非真的“周无遗民”,这显然又属于对作品所记载的历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随着文学释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后世的注释家和批评家越来越倾向于将“以意逆志”的“志”理解为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之“志”)和作者在作品中所抒发的个人情感、意志和怀抱(作品之“志”),而作为政治历史事实记载之义的“志”则慢慢地消弭了。清代著名的杜诗学者、文学释义家仇兆鳌在《杜诗详注·自序》里就表达了这种意见:“是故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事,面接其人,而概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6](P2)这段话实际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注释家和批评家对文学释义根本目标的普遍看法:在他们看来,文学释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探求和寻找作品的原意。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阐释者必须“反复沉潜”于作品之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追溯出作者创作时的精神状态,一直达到“恍然如身历其事,面接其人”的程度,否则就无法做出符合作者创作意图和作品原意的解释。由此可见,“以意逆志”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学解释方法,是十分重视对“志”即作品原意的追寻和探求的。
最后再说“逆”。如前所论,孟子已经认识到,在文学释义活动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方面是作为释义客体的“志”(作品的原意),一方面是作为释义主体的“意”(读者之心意或读者对作品的意度和体悟),没有这两个基本要素,文学解释活动就无法进行。但是,从文学解释活动的实际来看,仅有“志”和“意”这两方面的要素仍然是不行的,这是因为在文学释义的过程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由于时间、环境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原因,往往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释义者要求得对作品原意的理解和把握,绝非易事。也因于此,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们才普遍发出“知音难觅”的慨叹: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栽其一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仆之为文,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人必大怪之也。(韩愈《与冯宿论文书》)
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以知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欧阳修《唐薛稷书》)
由此可见,要使文学释义活动正常而有效地展开,释义者必须消除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这种时间间距和文化间距。孟子显然意识到了文学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所存在的这种时间间距和历史文化间距,所以他才提出了“逆”的文学接受方式和理解方式。
什么是“逆”的文学理解方式和释义方式呢?《说文》注云:“逆,迎也。”《说文解字注》云:“逆迎二字通用。”《周礼·地官乡师》郑玄注云:“逆,犹钩考也。”总起来看,根据前人的解释,“逆”大体上有三个义项:一是迎受、接纳;二是钩考、探究;三是追溯、反求。按照“逆”的上述三个义项,“逆”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释义方式至少蕴涵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思想:第一,“以意逆志”的活动,是一种以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原意作为旨归的文学释义活动,因此它首先要求解释者必须充分地尊重释义对象,以自己全部的热情和智慧去迎受和接纳释义对象,从而对释义对象作出正确、合理的理解和解释。后来朱熹曾这样解释“逆”:“逆是前去追迎之意,益是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朱子语类》卷三十六)朱熹在这里显然强调的是“追迎”、“等候”,即在释义者与作为释义对象的文本之间,文本居于主导、支配的地位,释义者必须充分地尊重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原意,这种解释完全符合孟子的理论本义。第二,“以意逆志”的活动又是一种极富探究性的文学解释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解释者被给予极为自由的释义空间,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调动自己的一切生活积累、艺术经验和审美心理动能对释义对象作出主动性的推究和创造性的探索。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以意逆志”的活动还是一种追溯和反求性的活动。这种追溯和反求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理解的那样简单,仅仅是指对创作过程的逆反,它实际上还包含有解释者立场和视角的逆向性变化。这即是说,孟子所理解的文学释义活动正是通过“逆”这一特定的行为方式(即解释者的立场和视角的逆向性变化)来沟通读者之“意”和作品之“志”,从而达到对释义对象的理解和解释的。孟子对“逆”的这一层理解,无意中暗合了西方现代释义学大师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观点。根据伽达默尔的看法,任何释义对象(包括各种文本和典籍)都蕴涵有原作者的一定的视域,他把这种视域称之为“初始的视域”。这一视域反映了作者思考问题的独特的范围和角度,它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境所赋予的。而一个试图去理解前人典籍或文本的后来释义者,也有着在现今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形成起来的独特的视域,伽达默尔称之为“现在的视域”。显然,蕴涵在“文本”或典籍中的原作者的“初始的视域”与作为释义者的今人的“现在的视域”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境的变化所引起的,是任何释义者都无法回避的。因此,伽达默尔主张,理解不应该像古典释义学要求的那样,完全抛弃自己“现在的视域”而置身于理解对象“初始的视域”,也不能把理解对象“初始的视域”简单地纳入自己“现在的视域”,而应该把这两种不同的视域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视域。这个全新的视域把二者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超越了各自独立的状态和相互间的距离,从而形成新的意义。所以,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立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7](P400)。孟子当然不可能使用“视域融合”的概念,但他以“逆”的方式来沟通解释者与解释对象,认为只有通过“逆”,才能消除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在时间和历史情境方面的距离,才能最终获得对作品意义的理解和把握,这与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理论观点在精神实质上无疑是相通的。孟子以后,我国有许多文学释义学家都按照这种思路来理解文学解释活动,如清代的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一书中说:“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矣。”浦起龙的话可以视作他对自己成功地运用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进行文学释义活动的生动、形象的总结:他在以“己意”“逆”作者和作品之“志”的过程中,既没有完全抛弃自己“现在的视域”,也没有把理解对象“初始的视域”简单地纳入自己“现在的视域”,而是把这两种不同的视域融合起来——“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二者相互交融形成一个全新的视域——“吾之解出矣”,从而最后完成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
总而言之,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既充分尊重解释者的主体意识——“意”,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不能背离对作者原意和作品原意——“志”的理解和把握,并且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种文学解释学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二、“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之比较
西方解释学的最初形态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产生。作为一种单纯的解释文献的具体方法,它主要被用来对荷马及其他诗人的作品作文字的解释。到了中世纪,它则专门用来对《圣经》经文、法典和其他年代久远而难以理解的文献进行研究和考辨,从而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文献学”。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则第一次把解释古代文献的释义学传统与解释圣经的神学传统统一起来,建立起总体的解释学理论。施莱尔马赫认为,由于作者和解释者之间的时间距离,作者当时的用语、词义乃至整个时代背景都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误解便自然会产生,而理解必须在每一步都作为目的去争取”[8](P175)。这样一来,避免误解就成了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这一点,正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理论与以伽达默尔的理论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理论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美国批评家赫施正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理论在现代文论中的典型代表,他在《解释的有效性》这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文学解释学理论。把中国古代“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与赫施的解释学理论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段的理论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中国古代提出的“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与赫施的解释学理论一样,都把作者或作品的原意作为释义的根本目标,把对释义过程中解释者所持有的种种误解的避免和消除作为达到释义目标的基本途径。
赫施作为西方客观解释学理论在现代文论的代表,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主张以作者的原义作为释义的根本目标,他以“保卫作者”作为《解释的有效性》一书第一章的标题就再充分不过地显示出这一点。赫施认为,惟一能决定作品本文含义的只能是创造该本文的作者:“一件本文只能复现某个陈述者或作者的言语,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含义能离开它的创造者而存在。”[9](P26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施才断定作者的原意才是本文真正的意义,“本文含义就是作者意指含义”[9](P35)。他还说:“当我们认为证实文本就是证实作者原意,亦即我们所要解释的意义时,那么,我们就不会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标准最终所指涉的都是一种心理结构。释义者的任务主要是在自己内心中重现作者的‘逻辑’、态度以及他的文化素养,简言之,重现作者的整个世界。”[9](P171)在赫施看来,解释者在释义的过程中惟一要做的就是完全消除自我,包括自我对本文的种种误解和曲解,而进入一个真正的精神世界——作者的意图和心境之中。
中国古代理论家和批评家提出的“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和赫施的解释学理论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当接近的,它也把作者之“志”即作者的创作意图或作品所表达的原意当作自己的探求的根本目标,试看宋代学者姚勉在阐发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时讲过的一段话:
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文之为言,句也。意者,诗之所以为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者,志之所之也。〈书〉曰:“诗言志。”其此之谓乎?古今人殊,而人之所以为心则同也。心同,志斯同矣。是故以学诗者今日之意,逆做诗者昔日之志,吾意如此,则诗之志必如此矣。〈诗〉虽三百,其志则一也。虽然,不可以私意逆之也。横渠张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诗。”夫惟置心于平易,则可以逆志矣。不然,凿吾意以求诗,果诗矣乎!(《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七《诗意序》)
在这里,姚勉对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私意”作了彻底的否定。姚勉所谓“私意”,其实就是指解释者个人一己之心意。为什么姚勉如此排斥“私意”呢?道理很简单,就因为解释者的这种“私意”是得作诗者之本义的最大障碍,是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根源,所以必须坚决予以摒弃。为此,姚勉提出了“置心平易”之法,而他所谓“置心平易”之法,即是指解释者消除个人的主观成见,以透彻澄明之心去重现作者的原意,这其实还是从另一侧面对解释者“私意”的否定。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与赫施的解释学理论在追求作者原意这一点上是完全相通和相似的。
但是,中国传统的“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与赫施的文学解释学理论又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种释义理论对作品意义和意味的不同侧重上。
赫施为了捍卫作者原意的存在,他在《解释的有效性》这部著作中所做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对“意义”(meaning)和“意味”(significance)的区分,他有一段话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意义是一个本文所表达的意思,它是作者在一个特定的符号顺序中,通过他所使用的符号表达意思。意味则是指意义与人之间的联系,或一种印象、一种情境,即任何想象中的东西。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在时间行程中解释者的态度、感情、观点和价值标准都会发生变化,因此,他经常是在一个新的视野中去看待作品的。毫无疑问,对解释者来说,发生变化的并不是作品的意义,而是解释者对作品意义的关系。因此,意味总是包含着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一个固定的、不会发生变化的极点就是本文的意义。迄今为止,释义学理论中所出现的巨大混乱,其根源之一就是没有作出这个简单的然而是重要的区分。[10](P8)
在赫施看来,“意义”即指包含在文本中的作者原意,而“意味”则指解释者在对意义的历史性理解中生发的新意;意义是恒定不变的,而意味则变动不居。赫施认为,对作者原意的客观存在性的否定主要起因于批评家对作品的意义和意味的混淆,所以他明确提出,文学释义的目标不应该是分析意味,而是复制意义。这样一来,赫施的释义学理论就把追求恒定不变的作者本意当作了释义的终极目标,而这一点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是无法做到的,它永远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所信奉的“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则不同,虽然它看起来也把作者之“志”,即作者和作品原意作为自己探求的根本目标,但在具体的释义活动中,富有智慧的中国古代批评家们并没有把本文的意义牢牢地拴在作者身上,而是非常注重对作品“意味”即作品本文所包含的超出于作者创作意图之外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意蕴的探求和挖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提出的逆志于“言外”、“味外”等理论口号即是明证。如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章纲领·论诗》引皇甫汸云:“评诗者,须玩理于趣中,逆志于言外。”清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亦云:“诗有为而作,自有所指,然不可拘于所指,要使人临文而思,掩卷而叹,恍然相遇于语言文字之外,是为善作。读诗者自当寻作者所指,然不必拘某句是指某物,当于断续迷离之处,而得其精神要妙,是为善读。”南朝齐梁时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则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从总体倾向来看,刘勰把文学释义的根本目标明确锁定在作者的原意上,这就是他在《知音》篇所说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及,观文者披文以如情;沿波讨源,虽幽比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清代学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序里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断定《文心雕龙》“大而全编,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但是,刘勰却没有像赫施那样把作品的意义完全等同于作者的原意,更没有像赫施那样看重“意义”而忽视作品的“意味”,而是相反:在刘勰那里,赫施所说的“意义”(即作者的原意)被称为“志”,而赫施所说的“意味”(即解释者依据自己的历史境况对作者原意的理解)则被称作“味”,《体性》篇在评价扬雄时所说的“志隐而味深”,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刘勰看来,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作者之“志”通常是以暗示和象征的方式来加以表现的,所以它往往隐而不彰。而文学作品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暗示性和象征性,它才给解释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解和解释的空间,也才更加耐人寻味。《隐秀》篇讲“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练字》篇讲“趣幽旨深”,《原道》篇讲“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都是强调的这一点。由此可见,在“意义”和“意味”二者之间,刘勰更看重的是作品的“意味”。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认为作品的“意味”高于作品的“意义”,把对作品“意味”的探求和追寻视为文学释义的最高目标,这种看法比赫施只看重作品“意义”而排斥作品“意味”的解释学理论无疑更能接近和把握文学艺术的底蕴。
收稿日期:2001-12-26
标签:儒家论文; 解释学论文; 阐释者论文; 文学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北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