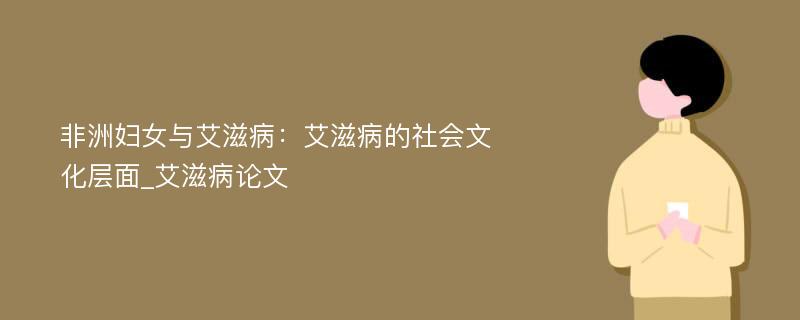
非洲的妇女与艾滋病: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滋病论文,非洲论文,社会文化论文,妇女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论
艾滋病成为全球性疾病以后,社会态度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说起这个话题时人们自然会想到艾滋病传播中的“高危”人群:同性恋者、海地人和血友病患者。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戳记有危险:它延误了应对普通民众采取的行动(Bailey and Mann,1988)。10年前,人们对艾滋病患者充满恐惧和敌意;今天他们却唤起人们的同情,让人产生休戚相关的感觉。不论个人还是政府,对艾滋病一开始常是否认其存在,而现在人们头脑更加清晰,对之有了更多的理解。
但是如果不充分了解HIV(艾滋病病毒)阳性、医学因素、文化和社会价值以及人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不可能促使人们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而控制这种全球性疾病需要这种变化。与这种疾病做斗争时,应特别考虑到妇女的需要。我们采取行动时当然得动员社会的每一个部门,但绝不能小看社会组织中的某些方面以及社会经济中两性的不平等,它们影响着防治HIV/艾滋病的政策,可能阻碍人们与这种疾病的斗争。
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防治HIV/艾滋病联合计划最新发布的《世界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有3 300万人感染了HIV,到1998年年底已有1 370万人死于艾滋病。现在病毒仍在以每天感染16 000人的速度传播,处于性活跃期(15岁至49岁)的成年人有1%携带着HIV,尽管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自己是HIV阳性患者。世界一些地区的政治、宗教和社群领导人很容易忽视艾滋病的规模,他们还得对付其他一些火烧眉毛的问题;但有时故意低估这种疾病的规模却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
1997年有近60万儿童受到HIV感染,他们大部分是在出生前、出生时或吮奶时从其母亲身上传染的。世界上4/5HIV阳性的妇女住在非洲。非洲育龄妇女中受感染的人数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非洲妇女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亦高于其他大陆的妇女,因此每一位受到感染的母亲可能传染的子女人数也高于平均水平。而且,大多数非洲儿童靠母乳喂养,据估计母子传染的病例中约有1/3到1/2是由母乳喂养造成的。
没有任何非洲国家能免受艾滋病之苦。南部非洲国家的感染率更是非常之高。如1997年博茨瓦纳的主要城市弗朗西斯敦的怀孕妇女有43%的人经检查确定为HIV阳性,而1995年哈拉雷已有32%的孕妇受到感染(UNAIDS,1998)。
妇女感染率上升,说明异性传染越来越多。1986年非洲1/17的艾滋病患者为女性,如今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1/2(UNAIDS,1998)。人们大多认为受到感染的是人口中最贫穷受教育最少的那些人;如事实并非如此。
事已至此,而系统监测仍然限于人口中的个别群体,这应该引起注意;现有的数据只是冰山的顶尖,根本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就拿妇女来说,一般只有孕妇才受到监测,使之接受检查,并有幸接受健康教育。而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妇女大部分人的性行为无异于妓女。她们对于自己受到的检查一无所知,而这种做法也极端地不道德,并且使母子间的传染无法得到治疗。
妇女即使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检查,得知自己是HIV阳性,也往往瞒着自己的性伙伴,因为她们害怕被人抛弃(Carael,1993)。还有一些男女经常更换性伙伴,这种关系使双方都面对“危险”,他们可能已经受到感染,只是未被发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仔细分析非洲妇女之深受艾滋病的侵害,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社会文化习俗、妇女与HIV
非洲是受艾滋病侵害最严重的大陆。非洲国家传统的行为方式纷繁混杂,尤其受殖民国家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一国之中民族未必单一,文化未必相近。
非洲HIV最为肆虐的地区沿赤道形成横贯东西的地带,还有就是稍远的地方诸如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尽管各种调查五花八门,质量也参差不齐,但仍能从中看出HIV传播的大致情况。HIV感染率最高的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湖区的城乡居民。北部、东部和南部的感染率较低,但不包括城市地区,也不包括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主要公路沿线的聚居点以及赞比亚和马拉维。高流行地区包括赤道非洲中部的国家,其中以卢旺达、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刚果共和国最为严重。这些国家近50年来饱尝动荡和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流动和性侵犯之灾。
西非沿海地区的HIV感染率低于维多利亚湖区,但也足以引起关注。整个非洲经历着严重的政治动荡,高感染率的势头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就人类学家而言,谈论非洲的传统习俗已经没什么意义:尽管农村一直顽强地抵制外来文化,而城市里传统习俗却已越来越被人淡忘。因此我们使用“社会文化习俗”一词。搞清这些习俗就能够解释妇女特有的一些问题,而导致HIV传播的行为可能就是由这些问题引发的。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是个人或群体的流动、生育习俗及观念、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传统的保护网,这些传统有些是社会所遵守的,有些却未必遵守。
这些国家及其主要城市内居住的人口群体互不相同,他们各有各的文化信仰和社会习俗。对非洲国家HIV血清传播的研究,常常忽视族属与地区间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而这些却很可能是导致HIV感染的重要因素。目前所得到的信息大多零星散乱,无法反映地区差异。
艾滋病的分布差异在非洲其他一些社会特征中也有所反映,诸如嫁妆、婚姻、婚姻形式(母系还是父系)以及弟娶寡嫂的习俗。但是目前艾滋病的横行,主要原因还是普遍的社会文化因素将妇女推到了最为不利的位置。
妇女是家庭的核心,但我们无法得知艾滋病一旦入侵,她们的角色会发生何种变化(Anderson et al.,1995)。妇女要相夫教子,还要满足家庭的各种需要;但如果她与夫家的人相处不好,夫家人可能会怪她把恶运带进了家门。因为一般人总是觉得自己家里很“干净”,病痛或其他不幸都是由外面带进来的,例如由别处的女子带来,这样的女子,尤其是外国女子,是最合适的替罪羊。
大部分HIV阳性的女子是被丈夫传染的。这说明妇女的自我保护很成问题:她明知自己的伴侣或丈夫有其他性伙伴(Ankrah,1993),也很难要求他们在性交时使用安全套,因为她的教养使她绝不开口谈论这个话题。对性传染病所做的研究表明,只有1/3的性病患者把自己的情况告诉配偶,并且真正停止夫妻性关系(Orobuyole et al.,1993)。在阿比让就一方为HIV阳性的夫妇进行的一次定量调查表明,HIV阳性患者可能向性伙伴隐瞒这一事实(Vidal,1994)。这些重要信息说明我们需要关心每个受艾滋病威胁的人,尤其是妇女。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HIV如何通过传统习俗得到传播,例如割礼、对妇女的性残害、传统治疗者在贡献牺牲以及在保护妇女和胎儿的仪式上施行的各种皮肤穿刺。
非洲下撒哈拉地区通行结婚时索取聘礼,聘礼多少因地而异,但总是代表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在父系社会中,聘礼送过门,两家也就完成了女子的生育和繁殖能力上的交割。一般聘礼越丰厚,女子就愈加迅速地在娘家被剥夺权利而在夫家获得权利。但如果女子来自另一个族群,丈夫死后她还得住在夫家,她就毫无权利可言了,他本人和其子女的生存也就成了问题。
母系社会中聘礼一般少一些,丈夫得不到任何权利,孩子归娘家所有,妻子与娘家保持密切的关系。在这些社会中,只要退回聘礼男女就能离婚。大部分母系社会离婚率都很高,因为妇女很容易搞到钱,偿还聘礼;而在父系社会中离婚就少多了。但是不论怎样,离婚总是增加妇女染病的机会,因为离婚女子为了生存,有时自愿有时被迫接受多配偶婚姻或多边性关系。
许多国家的社会规范倾向于一夫一妻制以及夫妻间相互忠诚,但这并不能为妇女提供实际的保护。因为社会只要求女子严格遵守这条规则,对男子的不忠却不闻不问,例如容忍男子设“外室”,与其他女子共度时光。女子一辈子得从一而终,男子却可以、甚至被怂恿着去寻花问柳。只有男子的众多性伴侣威胁到家庭统一,非洲社会才出面干涉男子的这种不忠。但男子的性放荡已把HIV带进了家庭。
一夫多妻制在非洲许多国家是合法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多哥和科特迪瓦)试图通过立法抵制这种婚姻形式。传统法律规定所有妻子地位平等,甚至像列值日表一般规定丈夫与诸位妻子之间的性关系。一夫多妻制加速了HIV的传播。丈夫在城里工作,但定期回家探亲,于是带回了病毒。迁徙也是造成HIV传播的一个原因。妇女则通常是受害者而不是主动的传播者。
尽管多配偶婚姻加速了HIV在性伴侣间的传播,但如果没有人感染上病毒,也就没有危险:这是塞内加尔的说法,那里的社会实行多配偶婚姻,但艾滋病流行率目前并不算高。
老夫少妻也会带来危险,因为丈夫可能在以前的性关系中染了病,又传染给他的妻子。老夫少妻在大多数社会都很普遍,不过也别以为仅仅嫁个比自己小或年龄相仿的人就能防止艾滋病在性伴侣间的传播。
农村的社会控制较强,对女子的性行为控制得尤为严格,因为妇女是用来给夫家生孩子传宗接代的。这种控制不仅由丈夫实施于妻子,而且由兄弟实施于姊妹。非洲一些社会的人认为胎儿来自男子的血液,因此父子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有些社会允许年轻人发生婚前性关系,有些社会则仅仅让他们亲热亲热,但并不真正性交。有些社会男女结婚时不怎么看重童贞:能生儿育女才是真格的,因为做了母亲才算完整的女人。婚前性关系使妇女更容易感染HIV或其他性传染病,这是女孩子的生理结构造成的。但婚前性关系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尽管父母还是担心闹出未婚先孕的丑闻。
此外,出于经济原因,村里人家如果有女孩子住在城里,他们就毫不犹豫、甚至不顾廉耻地让她帮家里挣钱。各地对未婚女子的性游移和性行为的控制也有松有紧。有些做法很极端,如北部非洲穆斯林社会将这样的女子驱逐出去,在贯穿非洲大陆的很宽的一个地带里,许多社会则对妇女实行各种各样的性残害,例如封锁阴部。
加上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高移民率和两性在获得土地上的不平等,妇女的位置就更为不利了:许多离异或未婚妇女没有使用土地的权利,为了生存,她们除了做妓女别无他路(Keogh et at.,1994)。
最后,父系社会普遍有兄终弟娶的风俗:女子是丈夫的财产,她的繁殖能力属于丈夫的家庭。因此寡妇得嫁给亡夫的一个兄弟,他们认为这样才能让这家的烟火通过她得以延绵不断。如果丈夫死于HIV/艾滋病,又没有告诉别人,哪位兄弟娶了寡妇,就可能传染上病毒,特别是寡妇通常很快再嫁,根本来不及体检验血。夫家人关心的是如何能不退还嫁妆,因为寡妇若离开亡夫的家庭,夫家是要把她的嫁妆退还的。
母系社会中有一系列因素使妇女较为独立:她们对财产和经济资源有一定的控制权;离婚后孩子的监护权归女方娘家;随着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子成为一家之长,社会对独立女子的歧视也就相对少一些。城市居住环境的构成使个人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受到社会束缚了;传统的权威由长辈体现、社会准则由长辈实施,而这些长者一般都留在农村。
刚进城的人会遭遇各种新思想,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直接接触。现代非洲社会,尤其是城市里,家庭结构正在改变,由于婚姻不稳定,为了工作不得不频繁地更换地方,妇女索性躲开家乡的男人,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如果多配偶婚姻中男子的数位妻子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也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
社会经济因素、妇女与HIV
看来,非洲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方面对HIV传播产生了影响。不论夫妻是同时还是先后搬到城里或城郊居住,他们都会发现自己面对的社会结构与家乡很不一样(Udvardy,1988)。妇女受教育较少,资历较浅,尤其不容易找到固定的工作。在城里则一般只能做小贩当女仆或帮人做家务,有时实在找不到别的门路挣钱,只有做妓女。城市里没有家室的男子就是她们潜在的顾客。
可以说受过一定教育的男女对HIV有更多的了解,知道它的传播方式以及如何预防。他们的工资较高,买得起他们所知道的那些预防艾滋病的商品或服务。因此在识字率较高的国家HIV感染率应该较低,但也不总是这样。
尽管教育水平与对HIV的了解甚至预防相关联,这对于男女都一样,但单靠教育却不足以抑制其流行。人们研究了赞比亚不同城市地区的大量怀孕妇女,发现受教育时间较长的城市妇女总体上比很少或根本没有上过学的妇女更容易感染HIV。关于HIV与教育水平的数据目前仍不充分,但是看起来女孩子进入性活跃期后,如果急于结婚而伴侣的行为又属于容易导致艾滋病传播的一类,她们所受的教育未必能使她们在生活中采取行动,例如坚持使用安全套、忠贞或节制,以降低感染HIV的危险。
而且,受教育多的女子社会流动性较大,在疾病流传率高的社会里受感染的比例自然也就更高。而西非的女小贩受教育不多,其商业活动却使她们流动性极大,因此社会接触和性接触面都很广。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其实都是危险人群(Caldwell et al.,1993)。
对艾滋病与教育、经济增长或男女平等诸因素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全世界适用的结论,这当然很有意义,但我们不能忘记艾滋病在不同社群、国家和地区的流行各具特色,这样的分析可能会掩盖其间的巨大差异。
展望未来
我们认为,若不考虑信仰和行为这些社会文化背景,就无法弄明白HIV/艾滋病在非洲的分布。然而对第三世界国家HIV流行所做的比较研究却很少包括基本的社会文化因素。用看待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非洲的艾滋病,不考虑非洲人历来认为疾病并非出自偶然、而是有某种超自然的原因,那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艾滋病在非洲的某些传染方式无疑具有特殊意义,尽管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这些传染途径包括分娩过程中发生感染,因为非洲妇女生孩子时一般没有现代专业人员在场监护。
在这种情况下,为妇女提供保护的政策必须考虑上述所有因素,并一一解决这些问题。保护不论是对女子、男子还是整个社群,都必须覆盖边缘或不易保护的人群,例如移民和在校、不在校的少年: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成员。传递给男子和女子的信息必须清晰准确,让他们知道使用安全套的必要,知道安全套目前是惟一能防范HIV和其他性传染病的措施。必须让大家知道,每个人都应该采取安全的性行为。
现有的调查表明,如果夫妻中有一个感染了HIV,他或她很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给伴侣(Vidal,1994),两人继续若无其事地生活。而采取预防措施需要双方都了解他们面临的危险。在基加利对感染了HIV的夫妇所做的研究发现,如果未受感染的一方得知了另一方的情况,使用安全套的人数会翻一番。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两个决定性的社会变化:教育,尤其是对女孩子进行教育,以及妇女完全能够决定自己的性生活。
教育尤其要针对少女
保护妇女免受HIV的侵害,关键在于及早动手,从少女抓起。原因很简单,非洲少年开始性生活的年龄越来越小。据25个国家的数据,19个国家少年首次性经历的平均年龄在15岁至20岁之间:尼日尔为14.9岁,纳米比亚为19.1岁(Kishor and Neitzel,1996)。
尽管在艾滋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里未出现教育水平与HIV流行之间的负相关,但宣传预防措施,让少女们从小懂得如何进行安全的性活动,这一切还得靠增加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才能达到。我们不能忘记,教育曾使生育得到控制,如果与其他相关的发展因素结合起来,它也可能减少HIV的感染。
要在校内校外组织对少男少女的HIV/艾滋病教育,使他们人人知道过早开始性生活容易感染HIV。
但近几十年来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一些传统方法竟然被摒弃,实在令人吃惊。原先青年人能在成年庆典和有关的仪式上受到性教育。而且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整个社区都要参加。现在一部分社会依然举行成年的庆典和仪式,但是原有的内容已所剩无几。应该提醒这些仪式的组织者,保证其在与艾滋病全力搏斗的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一批国家在学校课程中增加了家庭教育的内容,但是现在这些计划似乎大多失去了动力;而与此同时,第三世界教育水平呈下降趋势。其实只要政府积极推广适当的教育政策,在校内校外对少男少女进行性教育和HIV/艾滋病教育,只要负责这方面的教师尽心尽力,就能实施有效的性教育。可惜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结束妇女性依赖的历史
由于艾滋病在非洲肆虐,生育的决定变得复杂起来,以至给人们对生儿育女的向往蒙上了一层阴影:害怕传染上艾滋病,或者害怕孩子小小年纪就成为孤儿。HIV阳性的妇女即使知道自己不能要孩子,却几乎无法掌握自己的性生活,因为她无法说服丈夫在与其他女子发生性关系时使用安全套,更无法拒绝他的要求,也无法不给他生孩子。因此HIV感染率高的国家人人自危。有些研究者提到乌干达的青年人甚至拒绝结婚,因为害怕“结了婚会死掉”(Mukiza-Gapere and Ntozi,1995)。
多数妇女在经济上要依赖男性伴侣,才能保证自己和孩子不至沦于贫困。因此,对妇女的教育应该力求能使其克服障碍,找到工作维持生计,只有这样她们才能不致成为出卖肉体维持生存的“暗娼”。实行教育时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即不能让年轻女子为了付学费而卖身。
妇女参加农业活动是由社会组织的,得到了普遍承认,但她们的工作很少能得到公正的回报,因为土地一般属于男子。一些国家的法律实际上加深了妇女对男性的依赖,如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只属于男子——有时甚至禁止妇女以自己的名义单独签协议或获得贷款,即使得到丈夫的允许也不行,这便剥夺了妇女对收入或财产的支配,使她们在经济上只能依附于男性。
妇女在经济上处于完全依附的地位,则很难拒绝有可能使她们感染HIV或其他性病的性行为。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妇女的地位。
明确保健战略的重点
妇女的地位还会受到保健政策的影响。保健部门往往被呈现为以严格的理性和深切的同情见长,但其做法中也有出人意料的不平等。例如非洲尽管有政府规定的公共医疗底线,却只有有钱的妇女才能负担得起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而无钱的妇女就连最起码的医疗也难以得到。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在同一个国家里,一些母婴诊所只能勉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例如在卫生保健条件不好的地区,连安全分娩都尚为遥远的理想),换一个地方却能找到最先进的技术和抗反转录病毒的治疗。
以此为背景,向医疗机构提供的血液产品尤其直接影响着妇女的健康。分娩过程中可能需要输血,而分娩往往突如其来,事先大多来不及验血。因此只有对提供给诊所的所有血液产品进行HIV检测——这应当成为一种制度——才能保证安全。还应该通过加强孕妇的营养,防治贫血、治疗感染和孕期并发症引起的失血,以减少输血的需要。这些安全措施决定着妇女的健康,而且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只要能得到必要的资源,实施起来并不困难。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做到。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至今有人、包括一些医疗专业人员,认为心脏病、癌症和HIV感染等等主要影响男性。他们认为男性的生命比女性值钱。医疗体系本身就隐含着重男轻女的现象:对女性心脏病患者的治疗不如对男性精心,生存率也较男性为低;癌症患者中也有同样的情况,而且女性发现患病往往较男性晚。
这种心态很可能使人们不能及时对女性艾滋病预防给予认真的重视。例如对女子进行性传染病普查至今仍困难重重,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受到忽视。传统治疗者是非洲医疗的主力军,他们认为性对女子吸引力更大,因为女子从中得到更多发泄,但是如果认为持有这种看法的仅仅是传统治疗者,那就大错特错了。情况如此混乱,在那些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就尤其需要对医疗质量加以控制,使妇女能多享受一点抵抗性传染病的医疗保健,以减少性传染病以及HIV在妇女中的感染和流行。
寻找具体途径,减少性接触感染
控制HIV感染的最基本途径是使用安全套,推广安全性行为,加强对其他性传染病的防治。目前女性的保护方法必须有男性伴侣的合作才能生效,但是男性并非时时处处愿意合作;况且非洲妇女对安全套不太了解也不太接受。因此需要找一些适当的方式,使妇女在保护自己时不必过于依赖男性。各种研究提出了许多好办法,诸如女性使用的保护器具和杀菌剂;但这些研究大多没有看到HIV流行的社会文化因素,即使看到了,也没有就保护妇女而对公共医疗明确提出目标。
向妇女提供有效的保护措施,使她们不必依靠别人就能实施,能够更好地抑制HIV和其他性传染病的传播。但是如果对这些方法不做充分的解释,结果很可能是只有城市地区受过教育的妇女才会使用。
在联合国防治艾滋病计划资助下,人们对泰国母子传染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者在34个妓院使用这些有助于向妇女提供保护的方法,将这组妓院中性传染病平均发生率降低了34%,而在仅使用男性安全套的对照组中,性传染病发生率只降低了25%。
女性安全套的缺点是过于昂贵。阴道杀菌剂倒是一种女性不依靠伴侣就能使用的方法。数十年来阴道杀精剂一直是妇女可以自己掌握的避孕方法。这些产品具有抗生素的性质,也能降低感染某些性传染病的危险;它们能够降低HIV的活跃程度,至少在试管里是这样。问题是杀精剂似乎会导致阴道发炎,如果一天使用数次就更为明显,而这种炎症可能增加感染HIV的危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目前的两个研究重点,一是鉴定现有杀精剂的无害性和保护性,一是研制不会导致炎症而能预防HIV和其他性传染病的产品——甚至不含杀精剂的产品,供想要孩子的妇女使用。
要让妇女明白即使精液带病毒,也不一定影响她们生孩子,从社会的角度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她们总觉得这是命运的诅咒。因此,提供这方面咨询的医务人员一定要了解该地区传统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性传染病的传播这类事情解释清楚。最后,不能排除HIV感染可能严重影响今后的生育率。因为受HIV感染的妇女通常是单身,她们在病中会减少性关系,并且可能经过认真咨询采取避孕措施(Desgrees du Luo,1997)。
联合国防治艾滋病计划资助的一项研究在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塞内加尔发现,使用女性安全套的妇女觉得与伴侣谈论安全性生活时较为轻松。面对伴侣的反对时她们也较有信心。因此必须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向更多的人进行宣传。
减少母子传染的危险
在泰国和科特迪瓦进行的研究表明,如果在HIV阳性妇女怀孕32周至36周间给她们服用AZT,能减少HIV对胎儿的传染。泰国由HIV阳性母亲生育但不吃母乳的婴儿感染HIV的可能性减少了一半。
减少母子传染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咨询和HIV普查应该得到改进,对希望检查HIV阳性状况的妇女,应该为她们严格保密,检查最好在她们怀孕前进行。因此怀孕期和产期保健应该更为普及。下一步就是扩大治疗。紧随疗程之后必须给她们提供有效的调养以保证其生存,还得保证她们不受歧视。非洲环境复杂,应该想到妇女生完孩子以后一般便要参加许多仪式,这个时候服药不免让人生疑。
在非洲防止母婴传染非常困难。因为治疗需要大量清洁用水:要保证清洁用水,这种保护性治疗就只能用于水质好的地区的妇女。泰国通过制止母乳喂养取得了成果,在非洲也必须找到母乳的替代品,并且想办法使母亲不会因为停止哺乳而受到家人、尤其是夫家人的歧视和排斥。这件事瞒不了朋友和家人,并可能对非洲大部分社会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因为人们会认为母亲拒绝哺乳就是拒绝强化父子相传的血缘关系。
总之,非洲妇女的日常生活环境使她们无法预防艾滋病,也无法对之做出正确反应。如果不废除某些传统,诸如兄终弟娶的习俗以及妇女在文化、社会、经济和性上对丈夫以及夫家人的依赖,如果没有得力的法律提高妇女地位,就很难在预防艾滋病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艾滋病的流行本身就是对有害的传统习俗的诘难,而预防艾滋病亦可成为对传统中的糟粕做出的有力的社会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