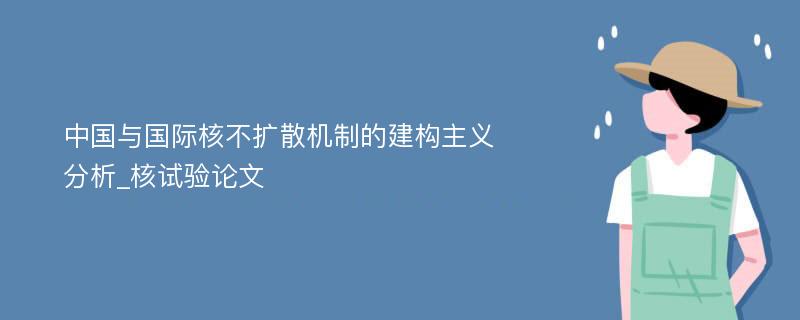
中国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一种建构主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机制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核不扩散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二战结束以来,为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的核不扩散机制。(注:Emily Bailey,Richard Guthrie,Darryl Howlett and John Simpson,"The Evolution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in Programme for Promoting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PPNN)Briefing Book,Volume I,Sixth Edition 2000,p.3.See http://www.ppnn.soton.ac.uk/bbltable.htm.)作为一个在1964年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对这一机制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当长时间的基本抵制,到8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参与,再到90年代初期以后的全面参与。(注:李少军:《中国与核不扩散体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60~63页。)对于这一变化过程,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各自的解释。多数学者将其归因于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军控形势)的变化与国内中心任务的转移,(注:例如,夏立平:《中国军控与裁军政策的演变及特点》,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2期,第36~38页;潘振强:《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435页;Bates Gill,Evan S.Medeiros,"Foreign and Domestic Influences on China's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on policies",in The China Quarterly,Vol.161,No.1,2000,pp.67-94.)有一些西方学者将其归因于中国的“实力政策”,(注:[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著,华宏勋等译:《中国参与世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也有少数学者将其归因于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注:李少军:《中国与核不扩散体制》,第63~65页。)应该说,这些解释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些解释并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如果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军控形势)的变化导致中国态度的变化,那么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军控形势)也应该呈现相应的阶段性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国内中心任务的转移导致中国态度的变化,那么中国的态度应该是两个明显的不同阶段,而不是上述的三个,因为国内中心任务是以1978年划分为两个明显的不同阶段的;如果这种态度是由于中国的“实力政策”造成的,那么中国应该在1968年或稍后即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如果考虑到当时盘踞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当局的加入,(注:田进等:《中国在联合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137页。)那也应该是1972年或稍后加入——因为根据该条约规定,有核国家指的是在1967年1月1日之前制造和爆炸了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而中国是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也就是说该条约承认中国的核国家地位,从“实力政策”来讲是有利于中国的;如果中国的态度是其战略文化传统决定的,那么在同一战略文化传统下为何出现前后不同的态度演变?
上述解释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的分析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物质主义分析,忽视观念等非物质因素的存在,忽视国家的身份认同对其对外政策所起的作用;即便注意到战略文化这一非物质的因素,其分析也过于笼统,没能结合政策的演变进行详细、具体的分析。或许这正是导致他们上述缺陷的原因所在。
冷战后崛起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张用“观念”、“身份”、“认同”(注:英语中“身份”和“认同”指的都是Identity,但汉语中它们是有区别的。身份指的是:(1)人在社会上或法律上的地位、资格;(2)受人尊重的地位;(3)人在特定的环境、场合或事件中所处的地位。认同指的是:(1)承认是同一的;(2)认可,赞同。(分别见《现代汉语大词典》,北京: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5页和第503页。)所以在本文中,根据不同的语境,分别使用“身份”、“认同”、“身份(的)认同”“身份(的)认定”这样的词语,表达的都是Identity的意思。)等非物质的社会学概念来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认为规范、法律、习俗、技术发展、学习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为和利益,因为世界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特定不变的”。(注:参见: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中的相关章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239页。)身份认同是指“某个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225页。)独特的身份认同是界定国家利益和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正如Ted Hopf所指出的:“独特的身份认同在社会中具有三个基本功能:即它将告诉自己我们是谁、告诉他人我们是谁和告诉自己他人是谁。在告诉自己我们是谁的过程中,独特的身份认定强烈地显示了一整套涉及特定的有关行为和有关行为者的利益抉择和偏好取向。”(注:Ted Hopf,"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8,pp.174-176.转引自陈东晓:《浅议建构主义对东亚安全前景的再认识》,载《国际观察》,2000年第4期,第30页。)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态度的演变。以下将对此做一尝试。
在做出具体的阐释之前,为便于讨论,先对本文中涉及的三个重要概念(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一般核国家”身份、“特殊核国家”身份)做一界定。
核武器诞生以后,国际社会多数国家在这样一个问题上逐渐达成了共识:核武器扩散到更多行为体将危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核武器的改进不利于防止核武器在行为体间的扩散,它同样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危害。(注:Emily Bailey etc.,"The Evolution of the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pp.3-6.)相应的,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核不扩散机制。它指的是,二战结束以来,为应对核扩散所带来的可能威胁,国际社会逐渐形成的一个全球性的机制,这一机制是由为防止核武器的扩散而出现的所有单方面的安排、双边与多边的条约和其他安排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网络。(注:Emily Bailey etc.,"The Evolution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p.3.)它既包括防止核武器、其他核爆炸装置、对核武器或其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从有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扩散(即横向扩散)的国际机制(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区),也包括防止有核国家对其核武器、其他核爆炸装置进行改进(即纵向扩散)的国际机制(如《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其中,1970年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初步确立的标志和法律基础。(注:"NPT Tutorial",见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网站http://cns.miis.edu/research/npt/.)该条约就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和推动核裁军做了明确的规定。1995年该条约得到无限期延长。在本文中,“一般核国家”身份指的是,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有核国家承认通行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其他多数有核国家有共同的认同,认为应该承担有关义务、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的义务。“特殊核国家”身份指的是,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有核国家不承认通行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其他多数有核国家没有共同的认同,不认为应该承担有关义务、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的义务。
一 1964年~1983年,基本抵制阶段:“特殊核国家”身份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核问题上中国从此就认同其他有核国家,或者说认定自己是“核俱乐部”成员。事实上,在其后的长时间里,中国的身份认定并不同于美国、苏联、英国等有核国家,而是“特殊核国家”。在核试验成功之后中国即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载《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7日,第1版。)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核武器从根本上来讲是为了与核大国的核威胁相抗衡,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因此中国对于核大国反对别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允许有核国家保持和发展核武器,却不允许无核国家再搞核武器,是不公平的。”(注:吴展:《核武器的五十年》,载胡国成、赵梅:《战争与和平: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中国政府指出,“核武器越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载《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7日,第1版。)
中国的这一身份认同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美、苏等有核国家对中国的敌视政策。自1949年以来,作为“核俱乐部”主要成员的美国一直对中国奉行敌视政策,在核问题上不仅多次扬言要使用核武器,而且极力阻止中国的核力量发展。(注:徐宣全:《美国对华核打击多次胎死腹中》,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1月23日,第6版。)作为“核俱乐部”主要成员的苏联,1957年10月曾与中国签署《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答应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但是,1959年6月苏联却单方面撕毁这一协定。1962年8月苏联正式通知中国,苏联政府答应美国政府的建议,即核大国将承担义务,不把核武器及其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无核国家将承担义务,不生产、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在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建议下,1963年7月,苏联同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注:《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评苏联政府八月三日的声明》,载《人民日报》,1963年8月15日,第1版。)这一条约不禁止地下核试验。也就是说,美、苏等有核国家要通过这一条约剥夺中国及其他无核国家进行一般核试验来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的权力,而它们自己却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和发展其核武器。1963年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一条约其目的在于巩固那些核大国的垄断地位,束缚别人的手脚,而它们自己却可以继续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载《人民日报》,1963年7月31日,第1版。)核大国的敌视态度,使得中国在核问题上很难在拥有核武器以后即对它们有共同的认同。
第二,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在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奉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认同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军控与裁军政策上也是如此。(注:夏立平:《中国军控与裁军政策的演变及特点》,第36页。)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又称“两个拳头打人”)。(注: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帝国主义的代表是作为核大国的美国,修正主义的代表是同样作为核大国的苏联。而在当时的中国看来,如果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力量也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其斗争的实力将会壮大,从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
身份界定利益。中国对“特殊核国家”身份的认定界定了其利益的所在。中国认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从而在政策上基本上是予以抵制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参加1967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尽管这一条约承认中国是有核国家,是“五大核俱乐部”成员之一,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说,它是有利于中国的安全利益的。
对“特殊核国家”身份的认定,也并非导致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完全抵制。事实上,由于其他原因,此间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也有一些低层次的参与,这主要体现在对无核区的参与上。1973年8月,中国政府应墨西哥和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2号附加协定书,保证不对拉丁美洲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在这些国家和这一地区试验、制造、生产、储存、安装或部署核武器,或使自己带有核武器的运载工具通过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土、领海和领空。(注:潘振强:《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第415页。)这是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最早参与。中国的这一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态度,是基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的立场,是基于中国在核问题上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的肯定与支持。在签订这一条约的附加议定书的同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并不影响中国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立场。(注:田进等:《中国在联合国》,第121~123页。)
二 1983年~1992年,部分参与阶段:从“特殊核国家”身份到“一般核国家”身份的转变
身份一旦形成便难以轻易改变。但是,“身份总是在发展,总是在受到挑战,也总是实践活动的结果”。(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27页。)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转变到认为战争可以避免。这一思想的转变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军控与裁军问题上,“从认为军备控制是与中国无关的东、西方斗争的附属品转变到中国应该直接参加到国际军备控制机制中去”。(注:Banning N.Garrett,Bonnie S.Glaser,"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Arms Control."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3,1995,p.46.)这一转变的标志是1980年中国政府首次派代表团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而以前是不参加多边的裁军谈判的。
随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和国际军控实践的进行,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认知也开始发生变化。1983年9月,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在会见墨西哥裁军大使时指出:“中国对片面维护少数国家利益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评立场;但我们尊重无核区国家不试验、不使用、不制造、不生产或不取得核武器的愿望。中国不主张,也不鼓励核武器扩散。我们理解扩散问题的敏感性,我们对此是采取负责态度的。”在1984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也做了相同的阐述:中国对歧视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评态度,不参加这个条约,但是并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注:《政府工作报告》(1984年5月15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日报网站:http://www.people.com.cn/zgrdxw/zlk/rd/6jie/newfiles/b1090.html。)这表明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立场已正式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一新的立场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身份的表现。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评态度,认为它是歧视性的,这反映的是“特殊核国家”身份;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这反映的是“一般核国家”身份。从此之后,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已正式迈入从“特殊核国家”身份向“一般核国家”身份转变的缓慢过程。
1986年中国政府宣布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注:《政府工作报告》(1988年3月25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88年4月15日,第1版。)这在事实上承担了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对核试验的约束。这一点如果没有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身份认同的转变是难以发生的。在没有转变之前,即认定“特殊核国家”身份之前,中国是极力谴责这个条约的;即便是事实上已经停止大气层的核试验也不会公开宣布。事实上,中国在1981年便已经停止了此种核试验。(注: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等:《中国参与世界》,第106页。)
三 1992年至今,全面参与阶段:“一般核国家”身份
经过1983年以来长时间的“认知—实践”,1992年中国最终将自己的“特殊核国家”身份转变到“一般核国家”身份,其标志是1992年3月正式加入作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法律基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诺奉行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武器扩散,不帮助别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注:《中国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加入书》,载《新华日报》,1992年第3期,第150页。)
中国在1992年完成身份的转变,其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随着中国的国际军控实践的推进,出现了一个“学习的过程”,即随着军控实践的进行、军控专业技术的熟悉与改进、专业人员的增加等而出现的军控观念的变化与政策的调整;(注:参见王逸丹:《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38页;Weixing Hu,"Nuclear Nonproliferation",in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Lanham,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9,p.121;Alastair Iain Johnston,"Learning Versus Adaptation:Explaining Change in Chinese Arms Control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in China Journal,No.35,January 1996.)第二,1983年身份开始转换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发展,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不断向前迈进,同美国、苏联(后来的俄罗斯)等核大国的关系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第三,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军事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主流继续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减少。于是,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斗争的重点由过去东西方争夺军事优势和防止核战争转向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注:潘振强:《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第421~422页。)此外,1989年“六·四”风波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以及长期与中国一道抵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法国1991年宣布加入该条约,对中国完成身份的转变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注:Weixing Hu,"NuclearNonproliferation",p.122.)
身份的改变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界定,从而出现政策的调整。对“一般核国家”身份的认同,导致中国认为防止核武器的扩散符合中国利益这一新的利益界定,从而在核不扩散政策的取向上,保持与其他“一般核国家”大体的一致。由此就不难理解1992年以后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政策。
在防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问题上,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与“一般核国家”相一致的政策。1993年7月中国正式承诺,在自愿的基础上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所有核材料、核设备及相关非核材料的进出口情况。1997年9月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载《人民日报》,1997年9月12日,第3版。)规定不得向未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供任何帮助。同时,参考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核出口控制清单制定了中国的《核出口管制清单》。1998年6月中国颁布了《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对与核有关的两用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实行严格控制。1998年10月中国加入作为国际核出口控制机制之一的“桑戈委员会”(Zangger Committee)。(注:《中国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8日,第7版。)在防止核武器的纵向扩散上,中国同样表现出对“一般核国家”身份的认同。1993年中国政府表示,希望早日谈判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将积极参加谈判过程,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争取在不晚于1996年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注:《中国政府关于核试验问题的声明》,载《新华月报》,1993年第10期,第25~26页。)1996年10月中国签署这一条约。而这一条约被认为对中国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的实力削弱。(注:[美]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和罗伯特·罗斯著,黎晓蕾和袁征译:《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1994年10月,中美两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愿意共同努力,推动尽早达成一项多边、非歧视性和可有效核查的《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公约(禁产公约)》。1997年4月,中国与美、俄、英、法四个核武器国家发表声明,重申五国关于支持在香农报告所载授权的基础上尽早谈判缔结《禁产公约》的立场。(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载《人民日报》,1998年7月28日,第1版。)
当前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本态度与美、俄等其他“核俱乐部”成员是一致的: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任何国家如果为了谋取政治、经济或战略上的短期利益,而无视核武器扩散的严重后果,甚至做出损害别国和国际团结的事情,最终本国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注: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发言汇编》(1999年),第281页。)
结语
几十年来,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态度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对此,仅从现实主义等物质主义的传统视角去分析难以得到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因为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因素。(注:Peter J.Katzenstein,The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Politics,p.33.)从身份认同的转变去理解态度的演变,并不是要否认客观物质因素的作用,也不是要完全否认现实主义等物质主义对此所做的分析。事实上,如果没有物质因素的存在,非物质因素便难以发挥作用。上述中国不同阶段身份认同的形成,如果没有物质因素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但是,物质的因素惟有通过非物质的因素才能产生它所具有的作用。(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41页。)上述中国不同阶段身份认同的形成,如果没有非物质因素(比如“解放思想”)的支持,物质因素便失去意义。利益的界定和由此决定的政策的选择是身份认同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物质因素直接作用的结果。据此,我们对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态度的演变就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一演变是伴随着中国从对“特殊核国家”身份的认定到对“一般核国家”身份的认同的转变而进行的。当然,对“特殊核国家”身份的认定和对“一般核国家”身份的认同只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绝对的。对“特殊核国家”身份的认定并非指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与其他“一般核国家”绝对没有一致的认同,从而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采取绝对抵制的政策,它也包括像对无核区这样低层次的参与;对“一般核国家”身份的认同也并非指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与其他核国家具有绝对一致的认同,从而采取绝对相同的政策。比如,中国认为防止核武器扩散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过程中的措施和步骤;再比如,中国主张所有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关切,都应严格按照有关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和程序寻求解决;不应以反扩散为借口,限制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与其他核国家的政策还是有差别的。因为,认同是复杂的,其转变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