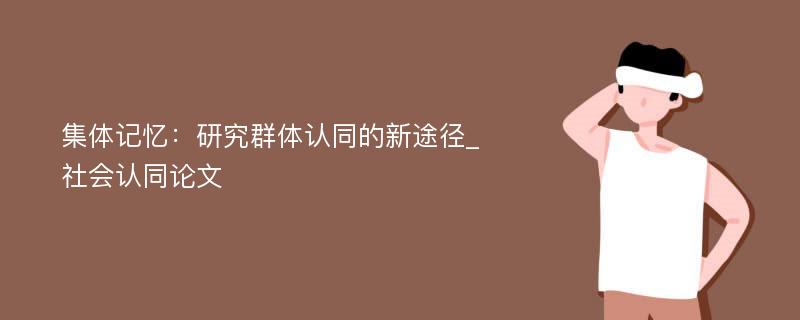
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群体论文,集体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1)02—0121—06
一、争议与统一:回观群体认同研究
认同的种类有多种,在群体层次上的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群体认同、民族认同和族群认同三个方面。随着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关于群体认同的研究引发了学者对其更加深入的探讨。群体认同其实是一个群体共享的概念,是用来指称来自于集体成员共同的旨趣、经历以及稳定团结。群体认同既不是天生就有的,也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作为不同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在相互之间的作用过程中而产生的。某种明显的群体认同现象能够深刻影响到社会运动过程中对于其成员的动员和调动,进而影响到社会运动的发展轨迹甚至是最终结果。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群体认同的研究热潮伴随着新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出现而被点燃,可以说,群体认同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①。总结以往研究资料认为,长期以来关于认同出现过三种典型的研究范式,其研究重点、分析视角都各自有别。
意义作为认同的核心:此类研究重视认同的形成如何可能。通常认为,被个体或者群体所建构和赋予的意义是构成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这其中首先体现出认同的建构性特点。认同并非是个体或者群体所固有的特质,而是在特定的、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通过人际、群际间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建构、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与结果。其次是体现出认同的能动性特点。作为认同主体的个人或者群体并非是被动的意义接受者,相反,为了寻找心理确定性,他们在认同的建构和形成上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突出的能动性和建构权利,能够对各种外界因素作出适当的诠释,作出接受或者拒绝的选择。但强调认同主体的能动性并不等同于忽视认同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作用。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在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享有选择和建构认同的绝对自由的权利。
行为作为认同的表现:此类研究关注认同如何作用的力量。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认同对于个体成长的重要作用。泰勒认为,认同和道德的方向感具有紧密的关系,只有形成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个体才能在社会行动中掌握“正确”的方向②。埃里克森明确指出:个体自我认同的形成与获得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发展以及健康心理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从而也能够保证个体在社会环境中顺利的生活下去。从群体角度上讲,随着社会表征、社会认同理论的出现以及叙事、建构以及话语等后现代基调的明确,对于认同的群体性形成与作用也随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群体认同这个主题之下萌生出一系列问题,群体借由什么原因建立认同、群体如何建立认同等成为研究的重点,群体间的相互作用、群体自尊的影响作用等也因此被研究者加以探讨。“从个体层面上看,具体的社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和基本偏好;从社会层面上讲,认同是确定群体的符号边界、实现群体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确立群体的内向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③
认同的变迁过程:此类研究重视个体与群体的认同发展。随着认同形成过程中时空边界与参照群体的不断变更,由此造成认同的动态性发展,出现了诸如认同危机、认同威胁等现象。时空边界的形成与确定、变迁与流动对自我和群体认同的获得与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时空边界的变动和参照群体的变更并不是认同解构的充分条件,因为认同的解构主要取决于心理意义上认同感的动摇。也就是说,认同的形成更多是一种心理意义的获得,是一种心理符号、心理共同体的形成,真正的认同解构是心理意义上的认同瓦解。
二、分离与整合:群体认同的理论取向
对于认同主题的研究都具有各自的不同立场和视角、不同的分析侧重点、不同的学科解释权,所以,对于认同的研究趋势以及研究取向也就不尽统一,关于认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不能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范式。“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中形成了多种有关认同的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导源于符号互动论的认同理论和由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反叛”形成的社会认同理论。”④ 认同研究具有不同的学科根源,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严格来讲,社会科学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认同理论路径。
源于社会学的认同理论比较重视研究自我与社会结构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条件、社会环境等方面出发来探讨社会性认同的形成,来分析群体层次上的认同建构路径。通常认为,社会学的认同研究最初源于库利和米德二人的思想,米德等人关于认同的诸多研究工作和相关观点陆续出现在各类学术杂志与著作中,主要关注“我”在社会环境中的形成过程,并探索这个过程中人际间的相互关系如何铸就了一种个体自我感。黄玉琴等人指出,虽然微观视角的社会学认同研究曾经因为研究自我认同而被重视,但是总体来讲,认同研究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倾向于向过程性、建构性和群体性的观点发展,在“我是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讨论“我们是谁”的问题⑤。李友梅等人也指出,应该将认同看做是社会背景中的一个不可能被剥离的发展过程,以此能够分析社会认同何以可能的支撑体系。他们认为,“当前国内外的社会认同研究,要么停留在具体的微观研究层面,要么醉心于宏大叙事,缺少的恰恰是中观层次的学术考察”。在这里他们所强调的所谓“中观”并非是认同者的范围和规模,而是对于认同形成的中观因素的分析⑥。在现实意义上,这是种研究理路主要是通过对中观层次上社会制度、结构以及系统环境的分析达到对于社会认同何以能够建构的理解。
偏重于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性认同研究则主要关注一种心理层面上的认同形成过程,强调群体心理的社会性形成过程以及群体内外与自我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重分析心理上归属感的获得,探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和建构过程,寻找互动过程中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过程机制与路径。20世纪末,随着社会科学领域内多学科问的交叉融合,加之各个学科自身的不断完善,很多研究趋向于更加整合的方向发展。在认同研究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社会认同理论的提出。当代欧洲社会心理学家们在学习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又在积极批判这种个体主义研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他们试图在吸纳美国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精华的基础上,挣脱微观心智研究的束缚,超越个体主义的藩篱,从更大的群体层面出发来探索一条与众不同的群体心理研究路径,建立一种人际—群际水平上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模式。延续欧洲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传统,博个体心理学研究的长处,欧洲社会心理学家们提出了社会表征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旨在了解个体心理和群体社会之间相互建构、相互阐释的关系本质,以促进心理和社会、个体和群体之间深层次上的整合。社会表征以及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某一群体认同的必要条件是形成基本的心理认同,具备认同的心理成分和心理结构。相比源于正统社会学的认同研究范式,心理学视域的社会认同理论更加重视微观和中观层次上的心智形成过程,相对忽视了对客观认同结构与条件的探究与分析。
长期以来,虽然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两种认同研究范式,在理论来源、发展轨迹以及研究重点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之处,但同时也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的观点交叠。如今,很多研究者正在尝试着在当今的工作中努力去构建一种能容纳两种思路和观点于一体的认同研究模式。近期的文献也表明,有的研究将注意力从个体层面转向集体定位;有的研究则将话语置于比行为的系统审查更为优先的地位;有的研究者将认同看做是一种过程性资源而不是一种结果或者是产品;有的研究则旨在突破以往的“虚拟现实认同研究”,转而使得“真实认同”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发展主流与研究方向⑦。可以说,两种理论范式的融合发展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多种认同研究模式的整合也必将产生较以前更加新颖和综合的认同理论。
三、超越与突破: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
20世纪20年代,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首次明确提出⑧。如今,集体记忆已被很多学者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虽然他们对集体记忆内涵的解释各异其趣,但也有较为一致的观点:所谓集体记忆是各种各样的集体所保存的记忆,它是关于一个集体过去全部认识(实物的、实践的、知识的、情感的等)的总和,可以在文化实践活动(比如仪式、风俗、纪念、节日等)或物质形式的实在(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献图书资料等)中找到集体记忆的存在,可以在我群体与他群体的互动中感知到集体记忆的力量。集体记忆研究指向时间维度,聚焦于集体层面上的过去,重视记忆的传承延续与发展变化,关注作为整个大我群体的记忆如何被选择与建构。集体记忆体现出整个群体较为深层的价值取向、情感表达以及心态变化等方面⑨。由此形成的群体意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群体的凝聚和延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迪尔凯姆先前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都具有这种延续自身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群体认同、道德与宗教,是个人对社会的体验,是比个人更大的力量,又是需要人们维护的意识。
(一)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研究视角
在诸多集体记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当下学术界就集体记忆问题已经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首先,记忆绝不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感官行为,它并非只属于个体,还与社会有关,存在着一种叫社会记忆、集体记忆或者历史记忆的东西;其次,社会记忆的形成过程并非是一个恢复或者完全再现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再次,有一些因素决定着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决定着哪些东西被删除、保留或修改;最后,社会记忆的延续方式是多样的,类似纪念仪式和身体时间这样反复操演的方式,往往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⑩
在历史文化学领域内,台湾著名的历史文化学家王明珂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集体记忆为分析视角,以华夏民族为研究对象,解读了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及其过程机制。他认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此,该群体才得以凝聚及延续;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集体记忆依赖媒介、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11)。在社会学领域内,与集体记忆相关的研究也曾出现过多例。景军早在1995年就已将苦难记忆作为一个现象提出来,并对西北农村政治运动“左倾”政策所造成的苦痛记忆进行了研究。其次,李放春与李猛(1997)的《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钟年(2004)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从〈评皇券牒〉看瑶族的族群意识》,他们都立足于本土文化环境,从不同的层面入手深入探讨了集体记忆相关的群体认同问题。
(二)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分析路径
为什么研究认同要把集体记忆的概念引入进来?集体记忆与认同的关系是怎样的?其实,集体记忆与认同的关系研究早已经被众多学者所重视(12)。迪尔凯姆在“集体意识”的概念中就蕴涵了群体认同现象的存在以及群体认同对于群体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但是,以集体记忆作为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深入而系统地去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较为少见。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集体记忆理论本身不够完善。集体记忆从提出至今,虽有大量研究,却没有形成关于集体记忆自身的系统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发展,也阻碍了它与其他相关研究主题的沟通。其次,认同研究多以心理学意义上的微观和中观机制为主,在群体层面上的认同研究相对较弱。集体记忆本身是一个群体层面上的概念,如若尝试着将集体记忆和认同加以整合来探讨其关系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但仍有研究指出,集体记忆的创造和维持是一种动力性的、社会与心理相互作用的过程,对于群体共同体以及群体中的个体而言,集体记忆是强有力的“意义创造工具”,它不但为个体界定和认同自己提供了一种非常必要的意义背景或情境,同时也为后继一代提供了认同的基础(13)。集体记忆对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彰显出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两个方面的有机融合。个体记忆是人的一种心理功能,而集体记忆则是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和活动,这种行为是建立在人类记忆功能的基础之上,对人类群体认同的形成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透过集体记忆这个视角或者将其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群体认同,可以更加有效地分析个体—群体、历史—当下、个体—群体—社会之间的深层关系。
把集体记忆作为认同研究的主要工具是一种新的尝试,要解决“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宣称我们是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相信那是真的!”、“我们与你们不同!”等一系列与认同相关的问题。在群体认同分析中,集体记忆不再是作为一种背景解释变量出现,而是作为一种与认同相互作用的重要分析工具被认可,群体认同可以通过集体记忆为中间媒介而得以建构和完成。集体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变迁与重构与群体认同的边界规定、资格获得、叙事表征过程都具有密切的关系。同时,群体认同也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和维护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群体认同促进集体记忆的发展,反之,则阻碍集体记忆的发展。集体记忆所提供的事实、情感构成了其群体认同的基础,以材料为基础的集体记忆是一种作为群体认知表征的集体记忆,是由群体来生产、体制化、守护的并在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和传递的关于群体的过去。个体成员所获得的关于集体记忆的了解,通常是以一种隐蔽的、潜在的方式来作用于个体自身,可以影响其个体记忆,也在为个体的回忆提供相应的叙事框架。集体记忆的建构和维护过程也引导着群体认同的发展方向,而以集体记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意义系统则可以提供给群体成员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集体记忆是通过各种形式得以建构起来的、带有群体性认知和情感特点的一套综合体系。它不仅仅是在传达一种群体共同的认知,也在共享和传播一种群体的价值观和情感取向,在特定的互动范围之内,这些群体认知指引着成员的行为和体验,并借用情感认同力量用来维持和组织群体成员。哈拉尔德·韦尔策指出,记忆研究不能忽视人类的心智参与、情感品质以及身份认同等心理因素与集体记忆的密切联系,忽视了感情品质不仅为回忆的重要性和持久性提供了底蕴,因为它们在传承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14)。集体记忆是一个创生、建构、发展、变化、维护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和集体在此来认知、评价、共鸣、认同的过程,形成群体认同感的个体会在认识、评价、态度、情感和行为等方面发生着与群体发展基本一致的走向,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和维护表现出相当大的积极主动性,会在某一群体的集体记忆中发现其成员思想和态度的整体倾向和特征。
同时,集体记忆的遗忘和新的建构过程会影响群体认同的发展过程。集体记忆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忆,会在建构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某些记忆内容,遗忘和淘汰另外一些内容,由此建构的“选择性记忆主题”会引发群体认同的变化。再加之各种形式的集体记忆实践活动也参与其中,成为维护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不断强化着集体记忆的主题,重复激活着群体成员的共享情感,集体记忆由此成为群体认同形成、发展和巩固的有效策略。
(三)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关系研究的争论
在群体认同过程的分析中,始终都应该秉承一个基本且重要的原则,即研究集体记忆要时刻照顾到个体—群体层次上的相互联系,研究群体认同要时刻关注人际—群际层次上的相互作用,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之间并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关系。在集体记忆的视角下分析群体认同的形成,必须要自觉地将个体—群体—社会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群体认同的获得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集体记忆是一种有效的中介或者桥梁,透过它可以看到群体如何规定了群体边界以及获得了群体资格。由此可见,只有同时兼顾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二者彼此具有的本质性特点,巧妙地将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的内部过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可以在研究中做到尽可能全面、尽可能深入地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但是,关于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的关系研究也招致了很多质疑。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持有不同的态度,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集体记忆和认同的关系应该更加深入的研究。不管是从个体还是群体层面上,集体记忆对认同的产生、巩固和维护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的作用。如若说,欧洲的社会认同理论呈现了一种与个体主义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实现了从“社会不过是一种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具体社会情境”到“社会则是个体置身于其中的群体关系背景”的巨大转变(15)。可以认为,将集体记忆引入认同研究,是将这方面的研究引向了更高、更复杂的层面。“尽管知识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做了一些工作,但社会记忆基本上是一个被解释变量,而没有成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基本概念。社会记忆不是知识社会学一个狭窄的分支,它是社会学这个整体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传统和视角。”(16) 所以,集体记忆不再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而是作为一种与认同相互作用的重要参与变量出现。集体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变迁与重构与认同的过程是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而认同也对集体记忆的创造和维持具有重要的作用。
反对者则认为,过分重视二者的关系会造成两方面的后果,即过于高估集体记忆在认同形成和维持中的作用,同时也过于窄化了认同研究,从而忽视对于认同所包含的其他主题的探讨。他们认为,集体记忆与认同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将集体记忆看做是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值得提倡的,因为认同的产生还有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正如社会认同理论所指出的,其实哪怕是最简化的群体,只要是他们在心理上产生认同感就可以看做是具备了社会认同感,而似乎与曾经的集体记忆关系甚远。
应当慎重对待集体记忆与认同的关系研究问题,既不能否定集体记忆与认同之间存在的重要关系,也不能将集体记忆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夸张。因此,今后在二者的关系研究方面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首先,对群体认同和集体记忆的概念界定更加深入,将集体记忆看做是一种至关紧要的群体认同的文化资源。其次,将群体认同和集体记忆与文化以及社会的结构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其三,在功能上讨论以集体记忆为基础的群体认同现象(17)。可以说,以集体记忆为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为进一步探索群体认同的机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但关于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仍在继续,并尚存在着可以去开拓的研究空间。鉴于在社会科学领域对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关系的论述并不完整和系统,我们希望以群体为例进行具体研究才能够更加深入地阐述二者的关系,探讨群体认同是如何通过集体记忆得以建构起来的,并希望通过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能够进一步深入了解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之间的关系本质,为这方面的后续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邱芝:《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集体认同的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4期。
②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5~37页。
③⑥李友梅、肖瑛、黄晓春等:《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2页。
④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⑤黄玉琴:《“青春无悔的老三届”:从自我认同到群体肖像》,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3年,第5页。
⑦Karen A.Cerulo,1997,Identity Construction:New Issues,New Direction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5:385-409.
⑧[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⑨汪新建、艾娟:《心理学视域的集体记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⑩陈宁:《社会记忆:话语和权利》,《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
(11)王明坷:《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12)Jeffrey K.Olick,Robbins,Joyce,1998,Social Memory Studies:From“Collective Memory”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James W.Pennebaker,Becky L.Banasik,1997,On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ollective Memories:History as Social Psychology,pp.1-19: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Soci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
(14)[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15)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
(16)郑广怀:《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2005年,http://www.studa.net/shehuiqita/060120/16172626.html.
(17)Klaus Eder,Willfried Spohn,Collective Memory and European Identity:The Effects of Integration and Enlargement,Ashgate Publishing,Ltd.,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