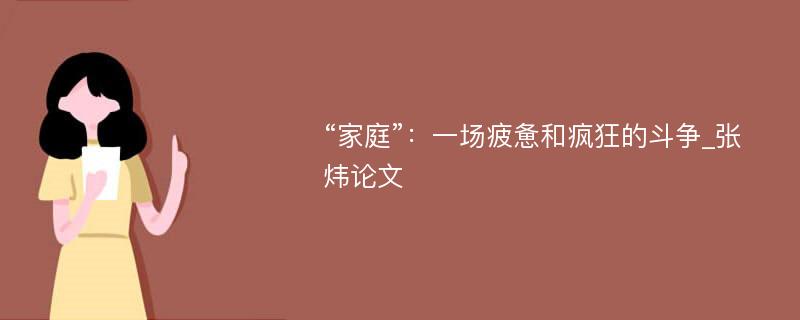
《家族》:疲惫而狂躁的挣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狂躁论文,疲惫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炜的最新长篇小说《家族》的发表业已变成了一个戏剧化的事件。它被一些批评者称为“圣者”的言论或是“特立独行”的伟人的杰作,被以最为热切的语言加以赞美。这使得一直热衷于以一种极为高蹈的、隐士式的姿态处于大众传媒的中心,而在1995年的文化论争之中极为执着地扮演了一个“抵抗投降”的孤独的堂吉诃德式的英雄的张炜,再次被一些人确认为一位除了张承志之外唯一的伟大的作家。《家族》好象一张即将兑现的支票,被一些批评家以最奢华的语言预支了最辉煌的成功。因此,对于这本已被热切地赞美所成功地加以包装的小说进行一些冷静的分析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部相当冗长的小说所喻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了对当下文化的仇恨与愤怒的知识分子的绝望的战叫,也是他的迷乱与狂躁的文化选择的一个极为有趣的纪录,也是一位业已由小说作者蜕变为原始自然神的膜拜者和文化冒险主义的精神偶像的人物试图抓住小说这一形式的一次最为绝望而痛苦的努力。它的出现所标明的乃是一个双重的困境:这个困境一重是“小说”本身的,它告诉我们沉浸于某种迷狂和狂躁中的作者会把小说带向一种怎样的枯竭与干涩之中;另一重是文化与历史的,它说明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张炜对“中国”现代以来的全部历程的无限的绝望。
《家庭》是张炜的另一部小说《柏慧》的姊妹篇,这两部小说的内容多有重叠与交叉之处。只是《家族》不仅仅如《柏慧》那样充塞着绵绵无尽的狂放“独白”,而是在大段的“独白”的空隙之中,插入了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十分诡异的表述。他试图提供几个家族在中国现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的命运,为《柏慧》中的狂放的“现实观”添加一个来自中国历史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家族》也重复了《柏慧》中有关03研究所的若干片断。而《柏慧》中的隐居海边葡萄园中的那个隐士式的“我”的狂放的宣泄在《家庭》中仍然以一种中心化的权威的姿态凌驾于小说中的不同的声音而成为一种绝对的“神”的宣谕。张炜的这个叙事者“我”如同一个隐秘的乡村巫师或是炼金术士,以一种人类的生活的最后审判者的身份出没于这本小说之中,给予历史与现实以最后的结论。这是一部以巴赫金所言的“史诗”的形式对于“中国”的一次独白式的热切而激烈的倾诉。它不是一部面对当下及中国历史的种种复杂性,容纳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其中作出复杂的思考的小说,而是以一种绝对的“神”进行一次最后的审判的小说,一部以原始自然神的“代言者”的身份进行的向神进行膜拜的言语的狂舞。在这里的“我”既宣判了中国现代历史的革命及变化是丑恶的,又宣判了当下的文化的丑恶。无论是殷弓的那支“八一支队”还是那个被“瓷眼”之类的恶霸垄断的03研究所,都只是一些人间的地狱。而这些对于“现代性”的整个进程的无限的绝望却导向了作者对于自己和由极少数人构成的“神圣”家族的极端自恋的情绪。“我”乃是绝对真理的发现者,又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审判者,又是一个巫师式的自然的守护者。张炜如同一个当代的“那喀索斯”,以最热切的语言宣布了一个“我”的家族的不容置疑的伟大性和圣洁性。在这里最为有趣的是这种的极端的自我陶醉和自我表演不仅仅存在于张炜的小说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他的一般性的散文之中。叙事者的“我”与现实中的“我”业已合二而一。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有关《家族》和《柏慧》写作的随笔中,他指出:“不需要赢得他们的赞同。我与之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我与他们不能对话——彼此既无法倾听又无法诉说。所以二者不必试图沟通。他们对我的打扰是无端的,是一种侵犯。我从来没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86页)而在《家族》中, 叙事者“我”的这种自恋也已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我们的单薄的肩头要承担没法想象的沉重,我们在保护一片平原,一片土地——它是我的母亲,好多好多人的母亲,这个担子怎么落在了我的身上,也许冥冥中有谁选中了我。”极端的自我夸大和自我幻想,使得张炜以一种异常的自信表演着一个神的代言人的身份。他极为夸大地向他的读者进行了十分放肆的承诺:
“它没有半点虚妄,它正是一个真实。亲爱的,你相信我吗?你愿意和我一起守住什么吗?在那些数不清的蛊惑与欺骗中,你能目不转睛地守住吗?”
这里有自我的幻想,幻想自己能够以语言发出神一样让人无条件地崇拜的“真实”之声。而“你”则只有与“我”有同样的信念和价值观,才能超越其它的“蛊惑与欺骗”。其它非“我”的思想皆是一种不良的东西。张炜在自我陶醉和夸大中也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攻击性,一种专断而狂暴的、阴郁的灵魂之声。
在对自我的神的代言人的伟大与神圣的热烈的歌颂之中,张炜的《家族》所表达的却是一种对于“作者”的极端的仇恨的心态。与之观念与价值有差异的其它群体均是应被“仇恨”的,而只有这个被“神”所特选的家族才有权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互相认同,互相依赖一种对“神”的膜拜而构成的有序的群体。(其中的“我”由于是神的代言人而居于话语中心,而其它的“你”则依赖对“我”的崇拜而获得进入这个家族的权利。)在这个群体中,共同依赖对于“我”和“神”的无限的景仰而形成一种等级关系。在这个狭小的“家族”之中,“我”乃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和支配者,他是血缘关系或土地的神圣性的唯一的阐释人,也只有“我”才能解释谁属于这个家族,谁被允许进入这个“家族”之中。这里的“家族”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纽带成为一种文化及思想的无上的权力。这依靠某种“血统”的(这里主要是精神血统,但也涉及十分具体的血缘关系)延续建立一种“清洁”的合法性,而对这个“家族”的神圣群体之外的人则以“仇恨”作为基础加以斥责和辱骂。小说的第4章的第4节乃是一首歌颂人与人之间仇恨的长篇赞美诗,乃是对于“他者”加以攻击的合法性的十分具有魅惑性的宣谕,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分裂的幻想曲。张炜热切地宣布:
“我懂得了仇恨是一种了不起的本领。只有真正的人才会仇恨。仇恨不是嫉,不是怨,而只是仇恨。永远也不忘记,不告饶,不妥协不后退。”
这种仇恨的锋芒所向,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种种变化与发展中的各种不同于这个狭小的“家族”的所有其它价值观。在这个“家族”的“土地”的自然神崇拜之外的任何思索或行动都要被这个“神”的宗教法庭所审判。无论是“革命”的“现代性”价值选择抑或是经济发展的“现代性”选择,其代表者都是象殷方式的凶暴之徒或是“瓷眼”式的无耻之徒。于是,这些价值观自然应该被无情地加以“清扫”了。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社会敌意与分裂的热切的呼唤,对于当下和现代历史中的各种价值选择的异常狞厉凶悍的攻击,也是对于普通人的历史选择与历史位置的最粗暴的否定。
在这里,《家族》延续了《柏慧》对于“现代性”的十分深刻的绝望的情绪。(有关《柏慧》的“反现代性”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进行过分析,可参阅《作家报》1995年5月27日。)这种情绪的出现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表现出对于“现代性”的全部历史的绝望。“现代性”在其历史的发展中的胜利者被指认为殷弓或“瓷眼”这类的恶人,而置身于“现代性”之中的普通人或是象许予明、李大侠一样被人利用,或是如柏老等人一样随波逐流。“中国”已被张炜确认为无法以“现代性”加以拯救的,他将整个中国现代的历史阐释为一个退行的历史,一个由“黄金圣世”向着精神的崩溃与毁灭趋近的历史。从殷弓到“瓷眼”,历史没有给我们任何亮色和光芒,只有堕落、崩溃与死亡。而另一方面这里唯一清洁的“家族”就获得了一种天然的合法性。他们是“神”特选的不受污染的人,闪烁着无限圣洁的光芒,他们是圣徒和天使,是“神”规定到此拯救迷途的羔羊的“圣者”。在这里,张炜采用了一种靠自我“贱民化”来支配他人的强烈的暴力的欲望。新历史主义的著名学者阿姆斯特朗和坦纳豪斯曾通过分析小说《简·爱》,分析了这种通过自我的“贱民化”取得支配他人的权力的方法:“直到小说末尾,简·爱经常被排斥在一切社会权力之外……她作为模范主体,一如她作为一个叙述者的身份一样,似乎只有依赖一种贱民的位置才能获得真理。勃朗蒂通过塑造这样一个讨厌的女主角并使她经受一连串的磨难,揭示了语言特有的权力”。(《表征的暴力》)阿姆斯特朗和坦纳豪斯揭示了简·爱通过“贱民”的“正义”与“道德”获得的权力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在这里,“贱民”的身份具有“真理”发现者的地位,没有权力变成了发现真理的唯一条件。在张炜这里简·爱式的西方宗教的激情化作了一种来自本土的“神”的召唤。而这个“家族”也正是通过这种召唤获得了宣谕真理的特权。炫耀苦难变成了消灭和清扫“他者”的合法性的论证。无权变成了天然的历史和话语的资源,于是“仇恨”变成了人间最美好的事物。这样的历史的阐释和自我身份的想象既无力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也无法真切地了解知识分子的当代命运和选择。而是把这个所谓“圣洁”的家族变为一个利益集团,进行一种社会敌意的制造和文化霸权的争夺而已。这只是一些知识分子在近百年来中国巨大的社会转变中在当下新的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过程中,既失掉了对历史的把握,又失掉了对于当下的认知,最终被历史的进程所抛弃而无力做出解释的结果。张炜只能通过《家族》的狂放的文化冒险主义的宣谕进行疲惫而又无奈的最后的挣扎而已。他以这个小说摆出的堂吉诃德式的“抵抗投降”的决斗姿态不过是一种向今天,向普通人宣战的凶狠和狂躁,是一种无法与社群沟通的文化冒险主义“家族”的狂舞。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独白”式的小说的形式本身的干枯和无力。这本小说启示录式的宣泄和以时空变幻借用八十年代小说实验的成果进行叙述之间进行某种拚合的努力,并未引出任何超出作者“独白”的效果。所有的故事和言论都是一个已对小说本身充满厌倦和对人生充满仇恨的语言巫师的疲惫而苍凉的努力。他试图再次抓住小说,却发现他只有政论;他试图实验形式,却发现他只有怨愤;他试图抒情,却只有观念;他试图讲故事,却只有说明他的意图的几个牵线木偶。我们从这里获得的只是巴赫金所说的那种“史诗”;“不论其来源如何,流传到今天的史诗在类型上是一个绝对完全和终结了的形式。这个形式的基本特征是将其描述的世界转换成一个民族起源和巅峰的绝对过去。绝对过去乃是一个特殊的价值判断与等级制的范畴。”而绝不是巴赫金所说的那种“小说”:“小说……否定了单一和统一的语言的绝对权威,拒绝承认其自身语言为意识形态世界的唯一语言语义中心。”“文化语言与情感意向从单一和统一的语言霸权中获得了根本的解放,从而使语言的神话性趋于消失,语言不再是思想的绝对形式”。(引自刘康著《对话的喧声》)在《家族》中我们看不到多元的文化与社会选择间的对话与交流,看不到人类之间的沟通,看不到众声喧哗,而只能在一片苍白干枯的讲述中看到疲惫而狂躁的挣扎。
在这种挣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后现代”与“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之中,知识分子的位置选择的重要性。我们的确象需要食品、阳光和水一样需要理想和崇高,但这并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式的靠着某种精神的血缘关系凑在一起的小“家族”的私利,而是我们所共有的社群和生活在这个社群中的包含着差异的普通人的共同的关切;这更不是“神”的宣谕,而是一种世俗的关怀,一种真挚的人间的情意;这也同样不能是“我”对“你”的训导和呵斥,而是对话与沟通。在中国社会目前的急剧的转变、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矛盾正在加深的时刻,歌颂“仇恨”和敌意,歌颂清扫他人,绝不是对人间仍有一份关切的知识分子所应该选择的方向。《家族》所代表的是一种没有活力的,制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分裂的造“墙”的文学;它是没有前途的文学,是衰朽的和无奈的文学。这种写作早已失掉了自己最后的生机而变成了一种惯性的滑动,变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小“家庭”对欲望和权力的争取。但让张炜这样的作家感到无奈的是,一种面向当下的状态,面向当下的普通人的文学,一种造“桥”的文学正在创生之中。我们目前面对的挑战,绝不是有理想的人和无理想的人之间的争论与分歧,而是仇恨普通人的“家族”的理想与和普通人相沟通的理想之间的争议和分歧,是造“墙”者与造“桥”者之间的争议和分歧。
我们必须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