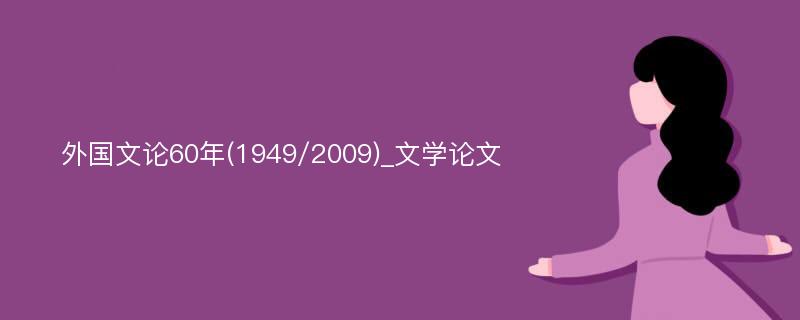
外国文论在中国六十年(1949—200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论文,六十年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置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这一特定时刻回望,可以清晰地见出外国文论在中国现代文论历程中刻下的深深印记。当然,严格说来,这与其说是外国文论自身留下的印记,不如说是中国文论家利用外国文论所留下的印记。我们知道,进入晚清以来,特别是梁启超在西方影响下标举“小说界革命”以来,中国文论面向外国文论不断开放和由此产生的相应变化,都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影响和变化究竟如何,则是需要回顾和思考的,同时也是见仁见智的。无论如何,要完整地认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如果不尽力弄清外国文论在中国的具体情况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1949年至今的六十年间,外国文论在自新生而届花甲之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历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究竟有何作用,都需要予以认真分析。但限于篇幅和水平,这次分析也只能是初步的。
一 六十年里四次转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国家统一为中国现代文论的生长提供了新的整合的体制土壤和发展目标。如果说,之前由于国内革命与战争形势的作用,中国现代文论置身在一个零散、分裂及不确定的国家体制框架中,那么,正是从此时起,中国现代文论终于拥有了统一的国家体制的规范,而相应地,外国文论在中国的作用也开始服从于统一的国家意志的节制和新的文化建设任务的要求。具体说来,从外国文学理论范式在中国的影响轨迹看,这六十年中国文论大约经历了两次明显的大转向:第一次转向是1949年起的苏化转向,第二次则是1979年起的西化转向。不过,如果从更具体的层面看,西化转向内部其实还可以细分出若干转向,这是因为,越来越深入的改革开放进程,把越来越近便并且正在进行中的当下西方文论引进中国。这样,总的看来,两次转向之说需要让位于更加具体的四次转向之说。
第一次转向为1949至1977年苏联文论范式主导期。那时期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根据1949年7月2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统一表述,是建立和发展“人民的文学艺术”①,而这正是新的国家政治与社会体制所需要的。文论的任务就是为“人民的文学艺术”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诞生提供思想资源。这种文论在当时条件下只能从苏联范式中寻到合适的范例。这一点加上此后陆续发生的“创作方法”、“真实性”、“典型性”、“形象思维”等理论争鸣及“美学大讨论”,都无一例外地是面向苏联文论范式获取思想资源的。当然,由于不满足于苏联文论这一单一资源,人们也注意向马克思所推崇的德国古典美学以及列宁所重视的俄罗斯19世纪文论家“三斯基”(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求助。
第二次转向是1978至1989年西方前期现代文论范式主导期。由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饱受“文革”浩劫困扰并企望摆脱苏化范式束缚的现代文论,得以向外寻求新的思想资源。于是,过去一度被禁锢的西方生命美学、直觉主义文论、心理分析文论、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等文论与美学资源,便从敞开的大门蜂拥而至,一时间蔚为大观,给予中国现代文论以极大的冲击和启示。
第三次转向是1990至1999年间的西方后期现代文论范式主导期。以“符号学”、“后现代”、“文化研究”、“后殖民”等为主要热点。这时期出于国家政治与经济工作的特定需要,对西方文论的开放度有所收缩,并对业已引进的西方文论加强了分析,例如对生命美学、直觉主义、心理分析学、存在主义等思潮中存在的非理性主义偏向进行了严峻的批判;不过,对依托符号学或语言学而生成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薄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新批评等西方文论思潮则予以默许,从而为学者们修炼专业文论素养、加强文论学科建设提供了范式借鉴。
还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属于第四次转向期,表现为以全球消费文化等为热点的新近西方文论范式主导,带有明显的跨学科话语特征。这时期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家在文化产业上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因而允许包括文论在内的外国学术论著大量引进,这其中既有汉译论著,也有外文原著影印版,还有教材原版等。正是这种更加开放的文化政策给外国文论在中国的影响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需要看到,这四次转向之间实际上是彼此交错、重叠的。例如,从第二次转向的起始浪潮中可以辨识出第一次转向的浪花,1978至1979年兴起的“真实性”、“典型性”、“形象思维”等论争就可以在“十七年”文论主流中找到渊源,它们只是由于“文革”十年浩劫而断流了。至于第二次转向与第三次转向之间、以及第三、四次转向之间,更具有可谓千丝万缕或藕断丝连的复杂关系。这四次转向的划分,只是相对来看的,目的只在于分析问题方便。
二 四次转向的动力与特色
任何一种现代文论转向的发生,必定是受制于特定的动力的,这动力既来自文论内部,更来自文论所从中产生的远为宽泛而深广的社会文化语境,正是这种社会文化语境给予文论转向以深厚的动力。中国现代文论在六十年里发生四次转向,其动力与特色何在?
第一次转向,其动力主要来自当时以冷战为标志的国际政治与文化格局。由于处在中苏结盟和中美敌对的特定形势下,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文论只能求助于苏联范式的文论。随着50年代初一批批苏联文论家应邀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讲学以及出版汉译教材和专著,苏联文论渐渐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些来自“老大哥”的先进文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艺论著的结构性基础上发生综合作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论的发生和发展。这时期社会主义文论的主要特色,可以简要归结为政治论范式主导,这就是说,文学或文艺是为特定的国家政治服务的,是具有阶级性、倾向性和实践性的。在“文革”十年中,当这种文论范式被当时的极端政治斗争无节制地加以延伸和发挥,反过来变成扼杀文论家和作家自身的政治生命及艺术生命的罪魁时,它们的威信受损就是毋庸置疑的了。它们的在今天从理论上看来仍然具备的那些合理性,在极端政治斗争的残酷打击中也不得不趋于瓦解,从而在新时期文论中内在地和自发地分离出反苏化的力量。不过,如果没有随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进程,反苏化力量是不可能演变成实际的西化动力的。
第二次转向的动力,就来自改革开放时代新的变革需求与西方前期现代文论影响交织成的合力。开放,在中国新时期主要就是面向曾封闭长达三十年的西方或欧美开放。1979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编选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出版,所录不仅有苏联和俄罗斯的、也有欧美古典及现当代的,及时配合了兴起的学习毛泽东有关“形象思维”语录的热潮。此书的出版及阅读可能正代表了新时期西方文论译介与研究的初潮。那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也是正式推进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面向隔绝长达近三十年的西方文论重新开放,此次转向实在不同寻常,意味着把此后三十年中国文论导向一个判然有别的新里程。虽然说改革开放头几年,苏联范式中的美学方面重新产生了影响,有力地激活了中国现代文论的美学化趋向,但是,随着欧美文论与美学的大量引进,加之当代苏联文论与美学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苏联范式的影响力就逐渐地衰退了,于是,反苏化力量终于迎来了西化时期。
取而代之,我们看到的是西方文论范式成为新的主导。这一点可以下面几位论者的活动为代表。美学家朱光潜在此时期不仅完成了黑格尔《美学》全三卷翻译出版,还重新提笔翻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以80高龄之精力勉力翻译意大利学者维柯的巨著《新科学》,体现了重新介绍西方文论与美学的雄心。美学家李泽厚在1980年发现,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原因在于,“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外现在的研究成果和水平”。因此,他倡导“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著作大量地翻译过来”,“这对于彻底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研究状况具有关键的意义”。他随即着手主编“美学译文丛书”②,到1982、1983年先后推出桑塔耶纳《美感》、苏珊·朗格《艺术问题》等。李泽厚所说的“国外现在的研究成果和水平”十分重要,其所指正是当时的西方美学而非过去三十年里持续影响中国的苏联美学。这一点其实也适用于文论界,因为那时的中国文论学者们多是把美学视为文论的拯救性学科来崇尚和研习的。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继倡导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和比较文学研究会之后,又于1981年发起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主张“先从翻译外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论文开始”,也就是“先做一些启蒙工作,其中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启蒙”,其孜孜以求的目标则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③,而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就是由其时北京大学西语系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1982)。张隆溪还在钱钟书先生“勉励”下研究“现代西方文论”④,并于1983至1984年在《读书》杂志分11期连载系列论文《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后于1986年结集成书),激发了读者对现代西方文论的浓厚兴趣。198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该书介绍了小说的演变、叙述语言、人称转换、意识流、怪诞与非逻辑、象征、艺术的抽象、语言的可塑性、时间与空间、真实感、距离感、现代技巧与现代流派等,向国人展示了久违的现代西方小说理论新风貌,引起了热烈反响。
仔细分析,这时期在影响我国文论界的西方文论中占据主导范式的,应当说是以康德主体性理论、生命美学、心理分析学和存在主义等思潮为代表的审美论文论范式。相应地,文论家则被要求首先成为美学家。与前一时期的政治论范式竭力崇尚文学的政治性不同,这种审美论范式转而针锋相对地标举被政治论文论压抑的人的审美主体性。而人的审美主体性则被视为人道、人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或“大写的人”的完满的感性显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陆续亮相的“康德与建立主体性”、“审美特征论”、“审美体验论”、“审美价值论”、“文学主体性”、“向内转”等命题,正是这种审美论范式在中国现代文论中的一种具体体现。
第三次转向,其动力主要来自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界自身的改革反思与西方20世纪后期文论影响产生的合力。面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知识界发现自身面临新的角色转变:国家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学活动所需要的更多的,不再是80年代人们自以为是的那种专家加政治家形态的文论家,或者思想型文论家,而是具有专业意识和学术素养的学者型文论家。正是这样,在80年代中期就先后登陆中国的符号学或符号论,其中尤以恩斯特·卡西尔和苏珊·朗格师徒的符号学美学专著《人论》和《艺术问题》的汉译本分别于1985年和1983年出版为标志,加上其时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汉译著作,就被重新发现,一跃成为人们信奉的主导性文论范式。于是,受到符号论支撑的符号学美学、结构主义、叙事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和杰姆逊)等就成为新宠。与此同时,面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新变化,人们敏感到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也意识到需要重新反思现代性问题,于是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又成为另一新热点。可以说,这时期文论的特色在于:一方面是符号论范式的主导,另一方面则是后现代及现代性范式的主导,这两者交织一体而难以分离地存在。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构成理论的支撑原型,那么后者更多地构成理论的应用领域,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地发生作用。
第四次转向的动力,大体来自新世纪全球性文化消费主义浪潮与西方当下跨学科形态文论的影响交织成的合力。在全球性文化消费主义支配下的文学创作、生产、消费、阅读与批评新潮,特别是越来越活跃的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等,越来越清晰地证明,文学常常不仅不是单纯地审美的、个性的,反而是商品的、消费的、政治的、时尚的、从众的、无个性的等等。这促使人们认识到,不仅审美论文论范式不能完全把握现实中的文学,而且连符号论文论所设想的独立的专业视野也不过是心造的幻影,而与此同时,强调文学的社会关联性的政治论文论被重新证明并非没有合理性,文学实际上依赖于跨越单一学科界限的更为宽泛的多学科视野的综合考量。正是在如此情形下,来自西方的跨学科文论范式及时地起到了影响作用。这种跨学科范式强调,需要调动两个以上学科的综合视野的考察,才能对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予以阐释,否则只能产生对于文学现象的单薄的或片面的认识。卡勒的《文学理论》(汉译本于1998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对文学理论的特征加以解说时,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文论具有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y)——“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⑤ 当对文学现象的理解总是依赖于“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时,文论就越来越具有跨学科特性了,也就越来越难以确定自身的学科特性了。随着来自西方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论著被以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大量地译介进来,今天的文学理论无疑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跨学科性冲击。由此可见,第四次转向造成的文论特色主要表现在跨学科性的展示上。跨学科性,意味着文论不再具有大致确定的学科边界,而可以面向任何一种学科话语开放;同时,运用超出一种原始学科的资源去做综合考察已成为文学研究的常态。相应地,被构拟出来的理想的文论家,不会再是过去三次转向依次有过的政治家、美学家和专家,而变成善于运用跨学科视野去分析文学的社会属性的批评家,拥有渊博学识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或者处处寻求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等的公共知识分子等。
三 外国文论与中国现代文论走向
透过以上外国文论在中国影响的四次转向,实际上已可以大体见出中国现代文论的走向。但问题在于,如何予以外国文论对于中国现代文论的影响力以合理的评价,而这同时也等于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自主性状况做出合理评价。
对此,只要对四次转向做出具体理解就明确了。第一次转向诚然吸纳了苏联文论范式而拒绝了西方文论范式,但其结果却并没有简单地跟在苏联范式后面亦步亦趋,而是终究走自己的路,满足自身的文学活动的需要。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艺界整风学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批丁玲、美学大讨论、反右等,都表明中国现代文论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而这些都是由现代文论所生长于其中的国家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机制的规范的,从而都直接体现了文艺为国家政治服务的特质。而与此同时,苏联文论与政治论范式中同时存在着的审美论取向,在50年代到70年代却没有获得充分地吸纳,这正是由其时中国现代文论的特定语境要求所制约的。第二次转向,在大方向上是顺应了国家的改革开放机制的,而急切地吸纳西方文论中的美学资源和现代文论资源,则一方面是要弥补过去三十年与西方隔绝带来的巨大耽误和损失,而另一方面,更主要地是要满足文论对于被政治论文论所长期放逐的审美与人道的强烈渴求。第三次转向发生于1989年之后,新的政治格局和市场经济体制对文学和文论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来自西方的符号学范式和后现代话语不无道理地成了新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以卡西尔符号哲学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符号学文论范式虽然早在80年代中期陆续被介绍进来,但真正受到重视和借鉴却是在90年代初,显然延滞了数年之久;另一件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作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讲演录,虽然早在1986年就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但也是推迟到90年代初才逐渐地受到中国学界的正视和普遍青睐的。只是当90年代文学界的特定状况需要借重符号论范式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时,这两种思潮才突然交了好运,成为学界时髦。这两件被延滞接受的案例并非巧合,它们共同地表明:中国现代文论总会以自身的需要和方式去过滤任何外来文论资源,也总会按自己的需要、方式以及节奏去自主地吸纳外来文论的影响。第四次转向虽然发生在中国现代文论可以同西方文论展开平行对话之时,但当具体面对西方文论时,总会体现出自身的自主需求。例如,中国现代文论对于跨学科范式的吸收,实质上根本上导源于中国当代文学产业中出现的一系列依赖于跨学科话语去加以阐释的新现象、新问题,例如畅销书现象、网络文学现象等。这表明,中国的特定国家体制及其文化产业政策仍然在总体上规范着现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遇的具体方式。
四 外国文论在中国——利用规范影响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对外国文论在中国的作用方式作出一些理解。外国文论在过去六十年里无疑渗入到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进程中,但是,这种渗入常常只是在经过中国现代文论的特定需要的过滤或变形后才发生实际作用。可以说,外国文论渗入我国文论,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总是长驱直入、无孔不入、所向披靡,而是根据我国文论的实际需要而受到取舍、变形或改造的。例如,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起初被直接照搬为我国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批评原则,但随着中苏政党与国家间关系交恶,这一理论就逐渐地让位于毛泽东提出的“两结合”方法(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了。这表明,外来文论总是在本土利用中被加以改写的,利用就意味着变形和创造。利用,总是出于本土文论需要而对外来文论加以有选择的取舍、改造、变形或重组的过程,是带有以我为主意味的对于外部思想资源的一种改造性移植。由此,不妨得出这样一种推断:就外来思想资源在中国现代文论中的影响来看,并非影响直接决定利用,而是利用规范影响。规范,在这里是规定、引导和制约等含义。这就是说,本土文论对外国文论的具体利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规定和制约这种外国文论的影响方式及其影响力。很多时候,中国文论家利用外国文论往往是用其一点而不求甚解、不及其余,或是借助外国文论的某些方面而说自己的事,这正是由于,他们总是出于自身的本土考虑而有选择地利用外国文论。利用外国文论,为的是建设中国自己的文论。
由此,我们可以有勇气地承认说,中国现代文论是利用了外国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的影响的,因而如果没有对于外国文论的影响的自主利用,中国现代文论肯定是不会以现在的方式呈现的。但是,这并不能简单地推导出中国现代文论完全是外国文论的复制品的轻率结论。那种关于中国现代文论由于“西方文论中国化”而患“失语症”的判断,是轻率的和不切实际的。实际上,就中国现代文论而言,任何外来影响总会受到本土文化的抵抗和变形的,这种抵抗和变形过程,其实正意味着中国现代文论自主地吸纳外来资源并建构自身自主品格的特定方式。
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利用外国文论,而在于如何利用它。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现代文论继续面向外国文论开放是必然的,如果没有这种开放,特别是开放中的中外自主与平等对话,中国现代文论必然会变成死水一潭、井底之蛙。但与此同时,在这种对话情势下,目前更加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则是:如何在中外对话中努力探寻和建构属于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的与自主的品格。这一点可能正是今天反思外国文论在中国六十年的一点启示。
注释:
① 毛泽东:《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② 李泽厚:《美学译文丛书序》,据[美]桑塔耶纳《美感》,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③ 季羡林:《序》,据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④ 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页。
⑤ [美]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