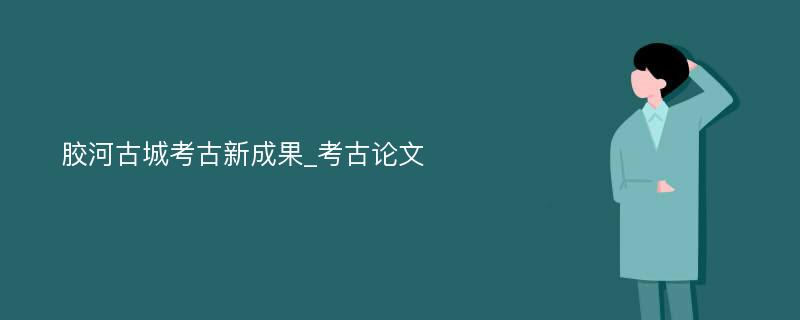
交河故城考古新收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是丝绸之路上一座驰名中外的古代城址。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前后开始, 活跃在天山中部的车师前国率先在此建都,后历经麹氏高昌、唐西州、高昌回鹘,前后长达1500年之久。其间,交河或为王都,或为郡、县,但始终是西域东部军政中心,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13世纪末叶,蒙古贵族围攻高昌,交河城难逃劫难,沉落于烽烟战火中。此后,交河在史家笔下渐渐被淡忘。
2 000年风雨沧桑,令人惊异的是交河城的主体建筑、 基本格局至今尚存,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上保存状态最好的生土结构的大型遗址。更让人难以置信,如此规模巨大的古代城市,并非一砖一瓦平地筑起,而是在两河相抱的一处险峻峭拔的土岛上,向下挖出街道、官衙、民居、寺院、城门……墙体大部分是生土,整个城市仿佛一组庞大的雕塑,巍然壮阔,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1992~1996年,由日本政府投资,中、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调,中外各方面专家通力合作,对交河故城实施了大规模的保护维修工程,考古发掘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这一任务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集中力量第一次有计划地对城内寺院、民居、城门、古井、城外墓葬、旧石器地点等几处不同性质的遗存展开考古会战,取得了空前的收获。下面择要介绍几项重要发现,以飨读者。
发现确凿无疑的旧石器 填补了新疆考古的一项空白
旧石器地点位于交河故城西,与故城隔沟相望。它的发现,填补了新疆考古的一项空白,把吐鲁番盆地乃至新疆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
这次发现的沟西旧石器分布于东西绵延数公里、南北数百米的山前台地上。邻河床地表石器散布较多,对这些地表石器,以往也有学者获得少许,但因工作不够系统以及受传统认识的局限,未能认定这里是一处细石器时代遗址。1995年秋季,考古工作者对遗址区进行了详尽全面的调查,采集标本达600余件。在距地表10 米左右的地层断面上意外采集到一件手镐(Pick),这是新疆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第一件石器。学者们无不为这一收获而欣喜,设想进一步观察这一地点的地层情况,研究其环境和形成过程,或许缘此将解开新疆旧石器的谜团。
沟西的旧石器标本,经著名旧石器专家张森水先生鉴定,认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确凿无疑。这一发现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从而真正结束了新疆地区无旧石器的历史。考古工作者们对这批珍贵资料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存在两种类型,一是以石叶——端刮器为代表的石器工业类型,从其形态到制作工艺看,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有580件标本,占采集石器总数的95%。其中旧石器类型繁多,表明当时生产的多样性和石器制作的水平。另外还发现有界于新、旧石器之间的一种工业类型——细石器。有30多件标本。这种类型广泛存在于亚欧大陆北部草原地区,是以狩猎经济为主体的人们的遗存。数千年前,有一支这样的古代部落,曾在交河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发掘车师统治者墓地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在交河故城北,隔沟相望,有一面积很大的南北向台地, 编号为1号台地,台地东南部分布有20多个凸起的圆形石堆。1994年9月至11 月间,对其中两座进行了发掘,证实这里就是车师前国上层统治者墓地。车师是古代西域36国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当西域门户。当时北方匈奴和汉王朝欲进入西域,必先控制车师、著名的“五争车师”,就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惊心动魄的历史剧。
治西域史者,多凭借有限的典籍,而陷于史载的迷茫中欲求突破,则往往寄希望于考古发掘。车师史的研究也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车师统治者大墓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它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车师以及新疆考古、历史、民族史、交流史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20多座统治者墓葬集中于一地,虽比不上中原历代王陵气派,但相对于一个人口不过6 000多的绿洲小国来说,已算得上气势恢宏, 非同一般了。
从已发掘的两座墓葬看,其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在新疆考古中尚无前例。地表的封石堆最大的直径达40米,去封堆,露出高1米余、 直径近10米的环形土坯围墙。围墙内见埋葬墓主人的中心墓室,长方形,竖穴,最深的近10米,与安阳殷墟商王墓的深度相差无几。在竖穴的底部向一侧或两侧掏挖偏室,尸体就放在偏室中。与中心墓室相邻往往陪有小墓或殉马坑,小墓中所葬者想必与墓主人关系甚为亲近,是其亲属或近臣;旁侧的殉马则可能是墓主人游牧、出猎、驰骋杀场的坐骑。在围墙之外,环绕着大量陪葬墓、殉马坑(有的为殉驼)。陪葬墓多合葬,其中有些可确定为夫妻,显然这是以家族或家庭进行陪葬的一种形式,陪葬者生前在人身关系上完全隶属于墓主人。众多殉马坑排列在围墙的西侧,犹如浩浩荡荡的出行马队。一个马坑中一般殉马(或驼)1~4匹,其中一墓殉马(驼)总计32匹。在一马坑中还发现一蜷卧的老妪与马同葬一室,其身份极低,是社会最底层的奴隶。统治者的显赫、富有,被剥削者的卑微、贫穷,在这里体现得一清二楚。
车师大墓给我们的启示不止这些。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尚处于人与人平等、没有明显贫富差别的氏族社会。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一些地区社会出现了阶层。大概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陆续出现了一些绿洲小国。至汉,形成了更大的政治中心,进入了十分复杂的等级社会。而这一文明进化脉络的确定,以往某些环节特别是最后一环还缺乏相应的考古资料,发现车师统治者大墓,正好补上了这个缺环。研究新疆地区游牧民族最终是怎样步入文明的,从此有了一条基本可靠的考古依据。
像以往一些考古发现一样,车师墓葬也带给我们不少神秘的悬念。“尸骨不全”就是很突出的一例。打开墓穴,发现尸骨已不完整或者是空墓,这在新疆考古中并非鲜见,现场证据也多足以解释其中缘由。车师大墓,绝大多数墓内不见完整的尸体,仅剩残骨和少量的随葬品,殉马坑则基本未动。这种情形颇让人们费解,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竟敢触动统治者的赫赫威严,是掘墓觅宝的盗墓贼还是泄愤报复的敌对异族?
从现场迹象看,墓葬地表并未见肆意盗掘和破坏后留下的痕迹,填土中也不见盗洞。而且只掘墓葬不动马坑,这也不像对地下埋葬情况一无所知的盗墓贼、报复者的盲目行为。在发掘的M01的中心墓室中, 厚近10米的填土大部分是较纯净的黄土,可以肯定是未经扰动的原始填土。墓底一侧偏室尸骨无存,另一侧偏室仅不见头骨,随葬品摆放齐整,不少珍贵文物如铁剑、铜镜等都出自该墓室中。
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明白无误地昭示着答案。笔者的思路是,在车师统治者坟茔动土的不是旁人,正是车师人自己的后裔。历史上某时期,车师人因某种变故不得不放弃交河城池,他们打开祖茔,取出先祖遗骨(取某部分骨殖,一定有着特殊的喻意),重新回填掩好墓穴,远走他乡。这种揣想有多大程度接近历史的真实,笔者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又有谁能否认,向未知的远古穷究不舍,正是考古学之魅力所在呢!
也许正因为是车师人自己的后裔,大墓之“劫”才显得如此彬彬有礼——仅取所需,一批尚算可观的随葬珍品得以幸存下来。粗略统计仅发掘的两座大墓,出土文物就近300件,有骨、陶、木、金、银、铜、铁、石器以及丝、毛织品等10余种。作为历史的物证,它们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产能力、经济形态、风俗习惯、审美心理、文化交流以及劳动者的才智、统治者的奢华。
陶器多红陶、夹砂,灰陶很少。器物造型、制作工艺与吐鲁番地区已发现的“车师文化”相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同一文化集团的共同创造。随葬的木器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除了盛物用的木钵、木盆、木豆外,就连箭镞、刀、锥之类也以木制成。木器中还发现四件小巧的木俑,都是用圆形或扁形木头雕成。仅有人的头颈部分,朴实稚拙,简约粗放。木俑在新疆这一时期的遗存中不是首次发现,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颇耐人寻味。车师人的骨雕非常发达,这次仅骨器就出土近百件。从工艺美术的角度看,骨雕属小器,但一器之微,往往穷工极巧,代表着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发现一件鹿首状骨雕,巧夺天工,令人赞叹。其长11厘米,中空,鹿首圆雕,鼻眼间饰以凹水滴纹和变形三角纹,颈部透雕出圆孔和丫形纹饰,构思精巧,造型洗练素朴,刀法圆润有力。由此可推知,骨雕业在当时已高度专业化。引人注目的还有出土的10多件金银器。自古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把黄金白银视为珍宝。它们稀有贵重,色泽富丽,耐腐,而且具有良好的延展性,非常适宜制作工艺精细的饰品。生前拥有、死后随葬这种金银饰品,就成了财富、地位的象征。车师墓的金器多为动物纹样的牌饰,系用金片模压或打压成浅浮雕状的各种动物形象,有骆驼、鸟、虎、怪兽等。M01出土的怪兽搏虎牌饰是非常精致的一件,怪兽造型奇特,鹰喙、龙身,正跃起撕咬老虎后颈,而一向凶悍的老虎,垂尾俯首,似毫无抵抗之力。这件作品,动物特征刻画细腻,富于动感,异常生动。银器不多,一件银牛头饰件具有代表性,铸制,大耳,扁嘴,双目有神,高只有3.2厘米,形象极为乖巧。青铜器中也有一些动物纹饰件,其中一件狼首状铜饰,造型抽象、夸张,富有特色。以各种题材的动物纹为特征的饰牌、饰件,在北方草原民族中十分流行,它从侧面反映出草原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艺术。车师墓中这类艺术品的大量出土,表明曾以游牧经济为主体的车师人在文化上与草原民族有不少相通之处。青铜的直柄、曲柄镜也值得一提,这种带柄镜与中国古代圆形具钮镜截然不同,属西亚、埃及、希腊、罗马系统。中原汉文化风格的遗物也有发现,诸如漆器、丝织品、钱币等。
车师人生息的这片土地,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枢纽。车师墓葬异彩纷呈的出土文物,让人们不难想象,当年车师人已在开放交流的大趋势中蹒跚起步,它的历史、文化、艺术清晰地显现着那一黄金时代的声色与光彩。
奇特的地下佛寺 在新疆独一无二
1994年初夏,在交河城北发现了一处暴露出口部的地下建筑。最初怀疑是墓葬,待遗址被一点点清理出来后,方揭开谜底——是一所佛寺,新疆独一无二的地下佛寺!这一发现颇不寻常,引起了行家们的浓厚兴趣。由于寺院构筑在地下,废弃后又逐渐被风积沙土掩埋,所以内部的构造设施及部分遗存保存较好,对于交河佛教建筑及相关研究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地下佛寺主体挖在地下,最深处4米多,依靠一个有10 级踏步的阶梯上下出入。寺院的规模不大,总面积约70平方米,有一间佛堂,两间僧房,两间小龛室。佛堂是礼佛场所;僧房供僧人生活起居;小龛室当是贮藏间,用来贮藏粮食物品。这处不大的佛寺,各区间功能明确,各有专用,显得井井有条。从始建到废弃,寺院经过一次大的改建,始建时期的面貌已难以复现,而改建后使用的只是一间佛堂和一间僧房,空间更为狭小,设置也相当简朴,与交河城中那些高大宏阔的寺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佛堂是寺院的核心建筑,长方形,半边穹窿顶,半边开放,似露天天井。在佛堂内东、西、南三墙下都设有通壁长的台阶式像台,像台上塑像多已坍毁。四周墙面上原应是丹青满壁,而现在仅在南壁上隐约可辨七身斑驳的千佛图像。当年的圣像尊容、彩笔粉华,如今都已不复存在。
寺院的出土文物颇丰,主要出自厚厚的坍塌堆积中。有龟兹遗风的菩萨头像,身穿蒙古式长袍的供养人壁画,回汉两种文字合璧的题记残片,精美的泥塑饰件,珍贵的舍利海珠以及木板画、纸文书、钱币、陶器等。从这些残品中能够捕捉到寺院时代特征、艺术风貌等方面的不少的信息。
这处地下佛寺兴于何时,衰于何时,文献中无从稽考。考古工作者依据出土文物及相关的遗迹, 基本框定了它的上下时限——建于公元9世纪中晚期,近14世纪被毁,历时400余年。
400多年间,这样一个简陋的小寺院, 不知寄托了多少信徒的心愿与企盼。在寺院南像台后侧的一个小方坑中,发现60多件小泥佛、小泥塔,因其制作和今天脱土坯的方法差不多,故又称脱佛、脱塔。脱塔,高不过八九厘米,塔身凸起多层象征性的小千佛,其下刻有古藏文、梵文符号。脱佛,直径六七厘米,上印有神佛、佛塔、经咒。脱佛、脱塔都是用模具制成,可以大批量生产。佛教徒把它们供奉在寺院、佛塔等神圣之地,以求累积功德,修身建福。这种习俗早在南北朝之际,就由印度传入我国,至今西藏等地仍很流行。地下佛寺的脱塔造型与莫高窟元代洞窟所出酷似,脱佛则带有藏传佛教密宗的风格。
据分析,13世纪中期以后,地下佛寺的使用已到了最后阶段。不久,寺毁僧去,香火断绝。当年,蒙古贵族进犯高昌,席卷高昌回鹘辖境的战火,撼动了回鹘王国历时近500年的统治, 曾经光彩夺目的高昌佛教艺术渐渐黯淡衰落,交河及其佛教也终难摆脱这最后的命运。
地下佛寺发现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它的形制、样式在交河城中是唯一的一例,这对于研究交河佛教建筑的发展、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