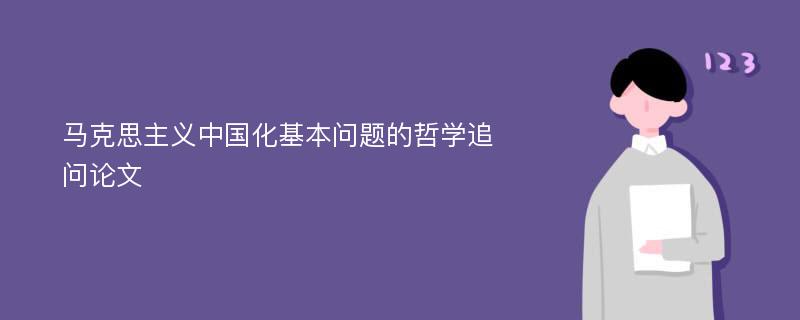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哲学追问
周全华,黄晓通
(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0275;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拷问,包含三个可能性前提: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是何”,即中国化所指“是什么”?实质问的是“被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本真”的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差异属于什么性质?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可能”,即中国化“为什么”可以成立?实质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可能移植中国吗?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可能”,即中国化“应当怎么化”才是有效的?实质问的是中国人如何解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本文就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一系列的哲学追问,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前提;基本问题域
哲学对任何一个宏大命题都要追问它“何以可能”。围绕“何以可能”的哲学追问,构成一个宏大命题的基本问题域,这是由一组相关命题构成的问题体系:先追问“可能是何”,从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入手,拷问命题有无真实性,再追问“为何可能”和“如何可能”,将问题域的研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这是继用其他各种方法进行更细化研究的基础。哲学提出以上三个问题,指导着逻辑的、历史的、实证的、规范的等各种层次研究的视域和方向,使这些不同方法的研究也围绕哲学所规定的问题域进行,各层次的研究如无哲学问题意识的引导是不会有深度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的“哲学思辨三问”: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所指“是什么”?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因即“为什么”?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怎么化”?在这三大基本问题之下又各自聚集若干的派生问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是何”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的第一个哲学拷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是何”,即它“会是什么”,实质问“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本真”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差异是否影响它们性质上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被民族化”的实在性,可以轻易地以马克思主义被多国化、被多民族化的思想史事实来证明。但是,对于事实上“被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要追问它“可能是什么”,追问它们与本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以及属于“什么性质”。
取款人身份证复印件上的名字明白无误是宋月芝,照片黑乎乎的看不清楚,老福很难确认那是不是他见过的小宋。他把这两张纸装进塑料袋交给高超,叫他去做指纹鉴定,然后三个人离开银行,直奔罗家。
那么,“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固化在文本中的历史存在,还是一种生长在现实中的生命存在?如果认定是前者,就必然以文本上的教条来检验鲜活的实践,这就是教条主义,它不承认实践的优先性。如果认定是后者,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堆死的文字而是活的生命,它活在革命实践中,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在革命实践中“被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本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并不是问题,它在性质上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发展与调适。因为生命在生长着而与原体可能发生差异,但又保持着同一生命的同质性。马克思主义因发展而与“原本”发生差异,但又保持了自身的同一性而并没有变成别的东西。以下所列举的几种民族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尽管与原本马克思主义有差异甚至有误读,但并不妨碍它们与后者“可能是”同一的,是同一生命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延续,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本真马克思主义”具同一性质而只有民族文化形式和时代条件的差异。
第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出于阶级斗争、革命、权力集中的需要,以恩格斯后期的哲学著作《反杜林论》(1876)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等为主要理论依据,建立了以强调世界的物质客观性、规律必然性、真理可知性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其精神是确立科学理性的最高地位。20世纪上半叶,启蒙、科学理性是中俄两国社会的急需,历史被要求选择能“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领袖,中俄革命实践分别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这是同根二枝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1]
威尼托有着令爱酒之人为之着迷的意大利最贵葡萄酒之一——阿玛罗尼(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还有意大利最知名的起泡酒——普塞克(Prosecco)。两种性质与口感截然不同的葡萄酒和谐共存,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口味,相信当你来到这里,便难以自拔。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异化,他们的问题和需要与中俄两国是不同的,1932年以德文版在苏联问世、被西方学者惊呼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成为他们批判异化的主要理论资源,并由此形成了与苏联哲学截然不同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文化批判哲学流派。[1]而马克思的这本早期著作虽在苏联公开出版,却没有引起苏联哲学家应有的注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个中文译本,也早在1956年就由何思敬、宗白华完成并出版了,但一直没有在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就像该书在苏联出版后悄无声息一样。欧洲的文化土壤和时空条件,产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可能”,即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如何‘化’”,才使它有“可能”?此“可能”是指“应怎样化”才具有效性。“应当怎么化”,是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这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应如何”中国化,才具有理论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主观需要上的有效性,客观事实上的可能性。
第三,20世纪中国历史,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政治实践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经了“理论哲学”“实践哲学”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到毛泽东创立独立的理论形态,才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毛泽东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和马克思的两种实践哲学,并将理论转变为方法、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理论,由此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第四,1979年以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经济学手稿》及其他一些马克思著作在中国的再翻译出版,就产生了与五十年代迥然不同的影响,马克思的人学、人的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等理论观点,成为学界最热门议题。[1]这是因为,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新的时代、新的问题、新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新的理解与新的应用,这就成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超越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结合”和“第二次中国化”问题,由此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2)分析条件确定定的点,明确需构点.由条件可知△ACD的形状确定,是一个顶角为138°的等腰的三角形,即可以先确定A、C、D三点,故只需构造点B;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可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可能,实质是问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最先进文化,有“被落后”的中国人理解的可能吗?它有被移植到中世纪中国的可能吗?如果没有这双重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可能在中国发展,那么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
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可能性的问题,实际提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设问题。这出自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解论”,这种理解哲学认为:人永远不会理解他人,因为人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各有“成见”,人的生活不同而各有目的。“一千人一千哈姆雷特”,说明理解不同一。既然理解不同一,各有各的理解,也就是不理解。这种“抽象理解”论,是妄求理解达到认识论的标准:既然人对自然的认知同一于科学,人的理解也要求同一于“客观”。而实际上理解活动与认知活动,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活动范式,理解活动只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在人文领域。而“抽象理解论”所抽象出来的“理解”,实质是一种无目的、无需要的“理解”,这种“理解”只存在于纯思辩、纯理念之中,而现实中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因为无目的、无需要就不会产生理解活动。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哲学认为:没有“前见”、没有目的、没有需要,就不会产生理解活动,一切现实中的“理解”,统统都基于某种前见、某种目的和某种需要,统统都是“具体理解”。[2]362-516海德格尔也指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3]“抽象理解”论的唯一作用,是可以反对“具体理解”的合法性。
关于“化”成物性质的问题,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二者孰重孰轻的问题,用西方哲学概念就是“第一性”“第二性”问题,用中国哲学概念则是“体”与“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经中国共产党而产生结合关系,其产物之一,就是发生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实践运动,在此,实践是“体”,马学是“用”。其产物之二,就是发生中国人以中国特色“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动: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用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于是又发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这两种文化的“体用”关系。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主体,在其前见的“显在”层面,对西方文化是认同性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批判性理解,这就发生“全盘西化”以及对立而起的“中体西用”两种文化关系观。“体”“用”关系与两种文化关系交错,又产生更多关系观:一是体与用不可分,“牛体只能配牛用不能配马用”,所以中西文化不能“杂交”,中国人只能在西体西用(全盘西化)或中体中用(全盘排外)中择一;二是体与用可分,但是体之内不能中西并存,用之内也不能中西并存,所以中西文化的结合,只能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显然,以上种种中西文化关系观,或陷于体用对峙,或陷于中西对峙,缺乏实践意义。
正如德国人、俄国人和革命时代的中国人都有权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当今时代的中国人也有权解释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不是一大堆具体结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是什么,其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是什么。新时期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提炼为“实事求是”。有学者据此提出一个最简洁的归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两句话:实事求是,一切为了人民。[8]
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某一个地域,但它的视域是被航海大发现而全球化了的世界历史和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它不是为某一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而创的理论,它是为全世界全人类解放和幸福而创的主义,因此它超越了一切以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最终目的的理论,具有普遍性性格。中国的特殊性会变通马克思主义,但不是相反的变通而是发展性的变通。理解主体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和需要,来读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如果经典中没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如果不能满足理解者的应用需要,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被主体移植到、运用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被应用到各国的世界性历史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是实在的,真确的。
另外,还有一个“移植的水土变异”问题。“淮橘北枳”派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搬来中国”,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产物,是离不开西方土壤的,一移植到中国就变形走样,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实际在中国发挥作用的也并非“本真”马克思主义,因为主义自身在时空移植中已经变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叫“中国特色主义”。[5]其实,橘演变为“枳”,以生物学和基因学原理观之,并未引发基因的质变,二者仍属同一物种和同一性质。水土不同,只是引起若干生物特征的变化,种性未变,“枳”仍是橘的一种,它适应了淮北的水土,变成有淮北特色的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可能”
针对偏瘫性肩关节周围炎,通常应用肩痛穴平衡针灸治疗方式。本研究选取了2015年9月—2017年9月到我院接受治疗的168例偏瘫性肩关节周围炎患者,将其分为常规针灸治疗组和平衡针灸治疗组,平衡针灸治疗组采用肩痛穴平衡针灸治疗,分析了肩痛穴平衡针灸治疗偏瘫性肩关节周围炎的方式和效果。
(一)主观上“可化成何物”:如何理解和提炼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才具合法性
当然,首先是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最初是依照苏联的方法,以恩格斯《反杜林论》和列宁《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经典文本为根据,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三个学科。[6]新时期以来有整体性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整体,不能作学科划分,它是一种“理想学说、现实社会的批判学说和历史哲学”。[7]有人主张全盘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溯源归本,重新出发。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就是马克思文本上说了什么”吗?如果是这么简单,中国人作为理解和运用的主体地位,就完全缺席。按照现代解释学,理解是文本历史视域与读者当下视域的“视域交融”,文本只有通过读者主体的实践活动,才可能发生历史作用,这就是“效果历史”。[2]362-516因此主体的理解是最重要的。读者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只理解为文本,他就成为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如果强调理解只能是主体的理解,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和实践性,这就是实事求是者和中国化主张者所理解的“理解”。
“抽象理解”论认为“中国人所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中国式的”,而不是那个原本的马克思主义。[4]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整个西方文化发展和现代工业化的产物,以中国小农自然经济水平的思维方式不可能理解。这就将“理解”绝对化了。现代解释学认为不存在“读者与作者的绝对同一”的理解,“中国式的理解”恰恰就是理解。人基于共同的人性,可以互相沟通、理解、对话。没有“纯粹理念式理解”,只有“现实具体的理解”。后一种理解并不要求达到“本真”,但要有中国主体的“前见”,有中国主体的目的与需要,才可能有理解。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定是“中国式的理解”,理解本身就已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中国化。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本真的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正是中国化的结果。此外不存在什么“完全还原”的理解。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马克思哲学的三大争论问题就好解决,即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还是“解释世界”的? 马克思学说是“哲学”还是“科学”? 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把传统哲学对“世界何以可能”和“自由何以可能”的追问,变革为“解放何以可能”。解放主题实现了哲学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换,实现了马克思学说的“哲学性”与“科学性”的融合,实现了马克思学说的解放旨趣、道路和尺度的统一。[9]只要遵循精神实质,其他的具体问题,可以也必须由我们自己来作出时代的解释,并找到解决的方法。
至于对“造反有理”、革命原则方法的的论证,对专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限度的论证,对专政的原则方法的总结,对社会制度的改造和公有制的建构,这些都只是手段层面的学说。“一切为了人民”,才是价值立场,才是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和最高目的、最高理想。“实事求是”,是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遵循了这两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二)客观上“已化成何物”:为何要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所“化”什么、“化”是什么,就决定了“化”成什么。我们知道是“化”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对此人们没有多少分歧需要辩论。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能自我定义自己的性质,它的性质是由所“化”什么和“化”是什么来决定的。“化”成了什么的追问,本是一个事实判断的追问,一旦转换成对“化”成物的性质的追问,就衍生出两个新问题:一、“化”成物的性质是什么?二、应当“化成什么”,即“化成什么”才是合法的?其合法性标准是什么?这样就变成对两个争讼不断的价值判断的追问了。
在党的组织原则上,李达宣传了列宁关于党应该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原则,指明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以取全体一致作革命的运动,行统一的计划。”李达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的谬论时,强调无产阶级集中制的重要性,指出“必须将劳动阶级权力集中起来,才免得中资本阶级各个击破的毒计”。它强调党内的选举和讨论,“意见虽或不能划一,但既经多数取决,少数也应该服从”。
关于“化”成物的性质,包含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个方面。其中,与事实判断相关的方面,分歧不大,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及中国文化的结合物。但是,与价值判断相关的方面,则是歧见多多。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结合。[10]1943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内容有明确的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1]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根植于中国的现实革命运动,而且要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国外许多研究者如费正清、列文森、罗兹曼等,也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儒学传统思想的延续,是“同化”了马克思主义。[12-14]窦宗仪等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有许多一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是发展了那些与儒学传统相符合的因素。[15]有的学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成”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6]这些判断看似事实判断,而实际上都含有价值判断的“前见”,也就是判断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事实关系作判断之前,就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作过价值判断,也对儒家思想作过价值判断了。于是,争论的实质不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有无关系,而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对儒家文化的价值判断的分歧。
所有种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化简为约,纳入四种模式:其一,目前国内的主流看法,认为二者都好,是好与好的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局限,民族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掺杂到“相结合”中去,“相结合”的主流是产生正效果,负效果作为支流仍然是存在的。其二,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二者都不好,不好与不好的结合还是不好。其三,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好,儒家文化落后,二者的结合导致马克思主义变异,所以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结合的事实。其四,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建设性的而中国文化好,“儒家化”“中国化”是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很明显,这四种意见表面都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事实关系,都在为二者的事实关系而争得不可开交,而实际的分歧,却都是源于对二者的价值判断不同。
李太嶂带头表态:“义父所言极是。义父多保重,小心歹人加害。”心里对老太监的推论却不敢苟同:不是冲我们来的?那四弟的惨死又作何论?
而在所有中国人的“前见潜在”层面,本来就预先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这就必然要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作中国式理解,这就是发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内在机制、心理原因、文化原因。由于不管哪一种“化”的主体都是中国人,即是中国文化“教化”“型塑”出来的人,在这种中国人身上中国文化是先于一切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然先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如毛泽东以“变易”和“实事求是”解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新命题,打破了思想文化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对子。毛泽东没有套用这些著名的中西文化关系对子,没有陷入“中体马用”或者“全盘马化”这个二者择一的老陷阱,而是跳出对子套路,另辟思想蹊径,提出新命题:“马学中国化”,也就是“马体”和“马用”都要引进,但都要中国化,即与中国特色的“体”和“用”相结合。[17]这一思路解决了体用对峙和中西对峙的双重难题,其用以解决中西之争也是有效的,即“西学中国化”。
(三)价值上“应化成何物”:两个规范判断谁更具合法性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化成什么”,是有不同标准的,哪一个标准才具有合法性呢?龚育之曾专门讨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说裁判是否“异端”、是否“合法”的标准,不是经典,而是实践。[18]即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标准,与真理标准是一致的,或者说就是真理检验标准——实践。实践标准,实际指实践的成功。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标准,不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而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因为在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与真理是同义词,它的中国化的产物也应当是真理。而科学真理是战无不胜的,是用于实践并保证实践成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如用于实践,能获得成功就是合法的,就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胜利的旗帜。而如果用于实践遭致失败,就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了,因为把人们引向失败的理论其真理性和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的质疑和挑战,并被革命所抛弃。如王明教条主义,如果只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检验,的确难以断其真假,但是从中国革命实践来检验,导致革命失败的理论能是真理吗?
2) 跨移动平台适配能力,基于React Native,通过封装或引入基础组件形成基础组件库,实现“一次编写,分别编译,多端运行”的跨平台目标;
不过,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合法性问题一直存在二元标准:一是上述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即实践成败标准,这是绩效合法性;二是理论权威检验标准,即是意识形态标准,这是意识形态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标准,一直是强势的,其指导地位不可丝毫弱化,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化”“与时俱进”“自主创新”“一脉相承”“开放发展”等话语,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最好调适。
此外,西周燕国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铸铜所用的陶范[8]38。1995年在琉璃河居址在F10和F11区内发现了陶范,其中有青铜容器范。标本F10T1324⑨:14夹细砂,红色,刻有卷云纹,残高4、残宽3.7厘米、厚2.5厘米[9]12-15。这说明古城址中有规模不小的铸铜作坊存在,极可能为王室所有。在北京的镇江营与塔照遗址,也发现1件残陶范,残长8厘米、残宽4.6厘米[10]364。说明此地亦有铸铜作坊存在过。众多的铸铜作坊,势必需要充足的矿源,亦从侧面说明燕国境内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正因西周燕国境内,铜、铅、锡等矿产资源丰富,才使得燕国青铜铸造业迅速发展。
正因为合法性的二元标准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人们总是对实践标准或者绩效合法性不屑一顾地发问:如果所“化”不全来自马克思主义,而“化”又只是在话语合法性层面,那“化”成物中就只剩下“中国化”或“中国特色”了,这是合法的吗?但是也有学者反问:难道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相上来理解二者的同一性,以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吗?[19]有人说必须如此,一切以马克思主义名义的言说和理论创新,都必须以马克思的文本予以检验,否则都不具有合法性,只能说是“独立创新”而不能说成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0]
我认为这种做学问的“纯客观、纯中立、纯学术态度”,恰恰是与教条主义取同一价值立场,而中国人民的价值立场只能是实践标准。
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这两个规范判断或者说两个合法性标准,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走向。教条主义的“应然规范和合法性标准”,一度主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可能走向,结果导致中国革命失败和建设挫折。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可能”中,如果让教条主义的“规范和合法性”标准占了上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蕴含着失败的可能性。革命中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和改革中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应然规范和合法性标准”,则主导中国革命和改革取得成功。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可能”中的“如何”做,很重要,它决定“可能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规律和形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3).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84.
[4]肖安宝.世界历史进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J].理论探讨,2006(4).
[5]陶德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
[6]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
[7]郝敬之.论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J].山东社会科学,2005(2).
[8]李德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则——从一个平常问题引发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5).
[9]王福生.范式转换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学术综述[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5).
[10]郭英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历史考察与启示[J].学术探索,2017(7).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18-319.
[12]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79.
[13]约瑟夫·R.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05.
[14]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35.
[15]陈名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1).
[16]金观涛.《实践论》与马列主义儒家化[J].二十一世,2003(12).
[1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2-83.
[18]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07(3).
[19]袁辉初.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2).
[20]张传开.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路径[J].学术界,2006(2).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Zhou Quanhua,Huang Xiaotong
Abstract : The ques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ncludes three possibility Premises:First, What i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ationalized" sinicized Marxism and "authentic" Marxism ? Second, why is it possible to localize Marxism in China ? Whether Marxism can be transplanted into China?Third,How to realize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legitimacy and possibilit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This paper makes a series of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on these three basic issues, and probes into the possibility, legitimacy and validit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 :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possible premise;basic problem domain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81(2019)04-0013-07
收稿日期: 2019-04-30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两个范式’‘四对范畴’‘多种理论形态’之探析 ”(项目批准号:15YJA710023)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周全华(1952-),男,博士,江西抚州人,广西民族大学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与文化哲学。
黄晓通(1983-),女,博士,广西柳州人,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王廷国
标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可能前提论文; 基本问题域论文; 中山大学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