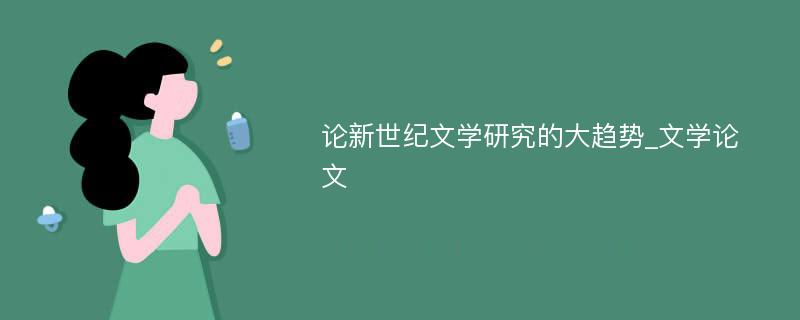
新世纪文学研究大势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大势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文学”概念将愈趋淡化,所谓现代将向下与当代联系,或向上同近代联系,形成所谓二十世纪文学的格局,或虽仍称“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中国文学”而含义已变,不是原来相对独立的三十年(1919—1949)文学了。这个苗头早已出现,八十年代初,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就对此提出倡议,此后有关论文不少,近年则已有《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孔范今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出现。不少有成就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突围而出,不再拘限于原称现代的三十年范围。下个世纪,“打通二十世纪”(包括上联下挂)将形成更大的气候,若再坚持原来的现代文学概念,则未免抱残守阙之讥。总之,1919—1949的三十年文学曾经独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已不再存在。
二、这个问题会对古典文学造成一定影响,有可能从古典文学中割去一块,即通常称之为“近代”的一块,但影响不大,“古典文学”仍将独立存在。无论是否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学割出去,古典文学仍有二千多年,足够研究者仔细耕耘。古典文学的分期也会有所变化,主要是打破按王朝起讫分期的传统方法,而探索一种根据社会性质变迁、跨度更大的做法,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但王朝分期方式仍将保留,特别是在断代文学史中。因为王朝分期大体能够反映中国历史的几个大段落:先秦(公元前221之前)、秦汉(前221—220)、 魏晋南北朝(220—581)、隋唐五代(581—960)、宋(960 —1279 )、 元(1271—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1)。这几乎可看作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分期,中国人对此已普遍接受,甚至耳熟能详。虽然文学的发展变化与王朝的更迭并无必然联系,王朝与王朝之间,也有所交叉,但这些都是能够在文学史的叙述中讲清楚的。
三、古典文学研究将出现强大的理论化的发展趋势。
文学研究其实就是两大块,一是文学史,一是文学现状,即尚未凝固而在变化之中的文学。文学理论就产生于这二者之中,既必须以这二者为基础,又必须能够阐释和指导它们。从事文学理论专业的学者,其成就的大小,与他们对文学史和文学现状把握的程度直接相关。如果说他们的研究道路可以概括为从理论出发不断地走向文学史实和现状,那么文学史和现状的研究者,就可以说是从史实和现状出发不断地走向理论。这是一个互动的、不断趋近的过程,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呼唤这两类研究者更好地携手共进。这既是文学研究的大势,也是新世纪文学研究有望取得大进展的关键。
说过了前提,仍回到古典文学研究上来。
首先,古代文学研究中理论色彩最强的文论研究将有更大发展,并日显其重要。
近年来,古文论研究取得明显进展,古文论研究者已从“史”的清理进到“论”的创建。以复旦大学王运熙等先生为代表,经过近四十年的积累,完成《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在此基础上,最近他们又完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一套三卷,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据介绍,该书是从原理、范畴、方法三个层面全面评述古人的文学观、批评实践,揭示传统文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以及文学批评的本质特征等。(据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99.10.30第7 版)相信该书必将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自己的看法,会在理论的建树上跨出一步。在最近的一次古代文论研讨会(1999.10月在河北大学举行)上, 有学者倡议:由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编撰大学文艺理论教材,以使文艺学教材达到中国化的目的。(见《中华读书报》1999.10.27第5 版)这是一个极具建设性、具有极大潜力的倡议。如果真能做起来,无论成败,均将对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因为直到目前,我国大学的文艺理论教材基本上还是相当“洋化”的。王先霈先生为总主编的《文学学系列教材》一套三部(包括《文学文本解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7)代表了这方面的最新水平,系统性、科学性和前沿性都很突出。该书对西方文论介绍比较充分,也努力运用一些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和范畴,但相比之下,份量要轻得多。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该书作者大都是文艺学专家,精于西方文论而对中国古代文论不是特别熟悉;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中国古文论本身的局限,许多问题古文论没有触及,许多概念和范畴也不明确、不统一。看来纯用中国古代文论构筑一部适用于今天大学教育的文艺理论教材,难度不小。但也不妨一试,古代文论研究者提出的上述设想,是有意义的,应该落实并尽量去做,没有开头,也就永远不可能成熟。这个建议说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已有了充足的学术信心和勇气,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他们终于向文艺理论发起了冲击,有了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上升为一般性的文艺理论研究的要求。迄今为止,所谓文艺理论,大都是借用外国文论的框架、概念乃至名词术语,今后自然也不能不用,但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文论融合进去,将更能使文艺理论贴近中国的文学历史和现状,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与世界文论接轨等问题,似也只有在这过程中可望逐步解决。
其次,文学史研究将与文论研究更紧密的结合。
这两个学科原来的分离状态是限制它们健康长足进展的大障碍。郭绍虞等前辈早就认识到二者应当结合为一,以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之效。郭先生1934年为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作序,一开始就说:他的本愿是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在研究中发现文学史的范围太大,“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最有密切的关系的。”可见,郭先生是认为文学史和批评史关系密切,他之研究批评史有为研究文学史打基础之意。但中国古代文论遗产太丰富了,郭先生对批评史的研究愈来愈深,终其一生没有能够亲手实现将文学史和批评史结合为一的宏愿。本世纪后起学者在知识结构上有较大局限,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久而久之,以至于文学史和批评史俨然成了两个单独学科。这无疑很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下个世纪这两个学科应努力融通汇合,也有条件这样做。只有如此,文论史研究才更加有血有肉,而不是从抽象到抽象;而文学史研究也才能从具体的现象、事实、作家作品层次上有所升华,而具有理论性和形而上学性,文学史研究也才能真正对探讨和揭示规律作出贡献。文学史研究本应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应该有理论的开掘,应该出思想。但如何提高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性,以往更多地寄希望于西方文论的引进和运用,今后则应两条腿走路,把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加以融通和结合,用之于文学史研究。
新世纪中,发掘新的史料和科学地整理史料,仍将是文学史研究取得新进展的一大途径,但更重要的突破,将会是理论的突破。其他新理论也会进入文学研究,局面将会是进一步多元化。种种理论观点的提出,将不再惊世骇俗,“各领风骚没几天”将被认为是很普通的现象,而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观点也将从中产生并经受考验。文学史还将继续重写,并将出现许多新的文学史品种。古典文学研究者“史”的意识在不断加强,文学史研究不仅仅体现于《文学史》的编写。文学史的重写,关键在于理论观念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深化,是与世界哲学、美学、思想之潮流接轨、呼应、对话或者撞击。
四、观念的变化不一定全都表现为追新,也有可能以回归乃至复古的面貌出现,但实质上是一种新变,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的螺旋式上升。如文学观方面,郭绍虞曾以传统的诗论文论为据,指出中国古代有两次大转变,从周秦至南北朝,是由含混趋于明晰,即由泛杂向纯粹变,文学脱离学术文章走向独立;而隋唐北宋时期,则是反向地由明晰变为含混,不少应用性很强的、一度被排除在文学之外的文体重新被视为文学。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复古,但并不是简单的复古,其中仍有创新的成份。南宋至清,正统文学观就在这两端之间摇摆,或偏于此,或偏于彼(参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初版)。至于小说、戏剧,始终地位很低,不受重视,但也有一些人为之力争,如金圣叹。也有一些文论家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对这一观点的进步意义和局限,需另作详论)。本世纪的趋势是西方纯文学观影响日大,文学的范围日益集中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这种文学观对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的面貌有很明显的影响。但现已发现,要讲清楚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不能不顾及中国古人的文学观,不能不注重文学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不能简单地用今人文学观去裁剪史料(说严重些,是削足适履)。如讲秦汉文学,不应略去碑铭和策论;讲唐代文学,不但应重视赋,而且不可舍弃诏策论判等诸体;讲明清文学,也应适当提及八股时艺。这些东西曾在历史上风行,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性(何谓文学性,就是一个需要结合中外文论来探讨的重要问题),虽然今天已经死去,但讲史时却不能不讲。如果说这就意味着一种回归,则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五、本世纪末已出现文学研究的跨领域交叉、综合的趋势,下个世纪当有所发展。一部分文学研究将摆脱“就文学论文学”的格局。狭义的文学研究将向广义的文学研究变化。狭义文学研究主要重视文学本身的内涵,特别是这内涵与表现形式、技巧、手法的关系,其实质是一种文学创作经验研究,其专长也在于此。近年来,文学研究已有向文化研究发展的态势,其主要特征在于将文学创作看作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将其放在社会文化的总背景之下来考察,因此与文学以外的学科,哲学、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等,发生程度不同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这也许会成为一个重点。
六、这种趋势将影响到学者的学术道路。二十世纪是出专家的时代,专家的长处是精通某一种学问,钻研得深;缺陷是范围较窄,视野有限。下一个世纪可望出一些通才。所谓通才,不是万金油,而是在本学科内范围阔大得多的专家,人们所渴望看到的学术大师,可能会在其中涌现。
七、学派的建设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一个尚未引起充分注意,而实际上对学术发展关系颇大的问题。学派当然不能勉强拼凑,更不能靠自我标榜。但学术的多元发展定将促成学派的涌现。学派可因种种原因、种种条件而产生,如因地域、师承关系等因素而成立,但只有因一群人都同用一种方法研究某一类问题而形成的学派才最有生命力。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不妨说有三派:考据、鉴赏、史论。这也是三种研究方法,三种研究路数,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亦有区别,但毕竟是各有专长。如果将每一种方法都用到极致,那就可以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派。每一学派能够成派,必有其特长,也会有其缺陷,这就需要学派间的取长补短,很可能是在论战中互补。为了发展中国学术,我觉得要有意识地去培养和发展学派。从学术史看,中国古代是有学派观念的,学派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昔日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以考据为特长,有人称之为清华学派。近数十年来,复旦大学几代学者研究文学批评史,成绩卓著,具备形成学派的条件。南京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有“考据与批评结合”的特点,似也可形成学派。学派形成后,会产生更大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也就会取得某一方面的学术优势,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