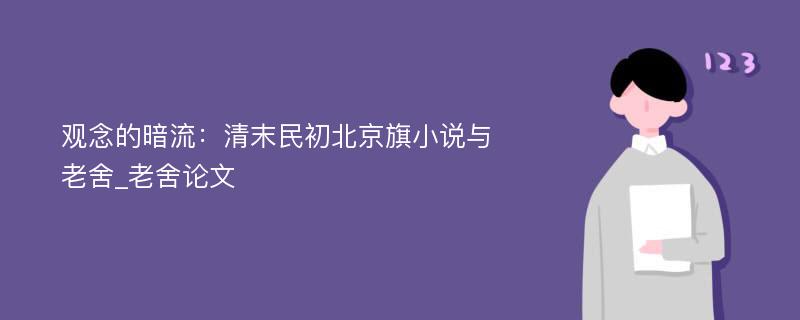
观念的潜流——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与老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舍论文,潜流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说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9)02-0079-09
在老舍文化背景与思想资源的研究当中,有关他在北京、伦敦、新加坡、济南、青岛、武汉、重庆、纽约等地的经历,以及他与传统儒家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宗教文化、地方性文化、民族文化等的关系,已为论者详述甚多。而“北京——满族——平民”文化作为老舍文学世界的初始母体,在研究者那里几乎已经达成了共识。目前清末民初京旗文学这一直接连接到老舍创作的层面,尚未被研究者太多涉及到,本文拟着手对既有研究继承、借鉴和发展的基础之上,考察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与老舍的关系的几个层面,或可管窥晚清至民国思想史、观念史与文学书写实践互动的一个侧影。
今日提及“清末民初的京旗文学”,仍不免给人以陌生之感,它一向处于被文学史书写遗忘的暗角。在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和“二十世纪文学”的思维框架中,一部分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以及清末民初转型期许多不太为之前主流文学史所关注的文学现象、作家和作品逐渐浮出历史幽深的水面。不过,清末民初的京旗文学——即是由一批活跃在北京报纸上的记者编辑作家书写的一批贴近民生和日常的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为主,杂以杂文和各类评论——之被“发现”,还是近几年的事情。他们活跃于《进化报》、《公益报》、《国华报》、《京话日报》、《北京小公报》、《京师公报》、《燕都报》、《官话政报》、《平报》、《群强报》、 《实事白话报》等大小报纸,代表人物和作品有蔡友梅(松友梅,损公)《瞎松子》、《赛刘海》、《曹二更》、《双料义务》、《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理学周》、《非慈论》、《方圆头》、《忠孝全》、《连环套》、《鬼吹灯》、《赵三黑》等,穆儒丐(都哩,辰公、六田)《北京》、 《梅兰芳》、《女优》、《笑里啼痕录》、《情魔地狱》、《落溷记》、《同命鸳鸯》、《鸾凤离魂录》等,冷佛(王咏湘)《春阿氏谋夫案》,徐剑胆(剑胆)《妓中伙》、《文字狱》、《王来保》等。数量颇丰,而从社会结构整体来看,实为当时舆论的民众趣味和心声的表达。[1]
如果从大的范围来说,有清一代的京旗文学可以分为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前者诸如已经日益衰微的子弟书、八角鼓词、书场说部等,后者则多是对现实不再产生影响力而作为自娱自乐的上层精英的旧体诗词。晚清以迄民国,在洋务、甲午、维新、拳乱、新政、革命等急剧递变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民间报刊蜂起并出、行之于世,形成舆论空场,京旗大众的通俗文学尤其是以京旗小说为代表即以报刊为发表场地,于前述二者之外渐成主导之势。
作为普通民众的自识,京旗小说在清末民初独特的舆论空间中带有公共性的一面,而作为前统治民族的“遗民”之思,它又是一种岐类话语。从制度背景、叙事源流、现实语境来考察,清末民初的京旗小说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艺术技巧和观念形态,它们所营构出来的文化语境和舆论氛围,构成了一种当时普通北京民众的平民教育、知识和娱乐资源。可以说老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初的启蒙和生成。从满族文学的系谱来看,清末民初京旗小说构成了满族书面文学流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成为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承上启下的中间体,于老舍卓然为满族一文学大家提供了启后之机。
文学作为一种人文涵化,更多的影响在于潜移默化的渗透与滋养。清末民初京旗小说的影响可能并没有直接体现在老舍的具体写作中,但是作为一种氤氲的氛围,则涵养了老舍文学世界的气质和风味。要证明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之于老舍的详尽而证实的影响需要更多细读的功夫,因为个案的文本讨论另文探讨,本文我将更侧重对于观念层面的分析。我仅拈出京旗小说三个核心的观念,透视其与老舍创作的关联,以小观大,对于今日我们重新省思晚清以来直至当下的文化文学观念转型也不无裨益。这三个观念是:群体、道德、白话。
一、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张力
清末民初的京旗小说所表述出来的观念有个共同特点是对于群体观念的强调,综观这些小说,几乎没有“个性”特别张扬的人物,被称道的主人公往往是符合公共价值预期的普通好人,标新立异、特立独行显然不符合这些作品认可的德行。形成这种美学品位的原因有多种,而当其形成之后,旋又成为一种文化定势作用于后来者,试析之。
首先,群体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内化于旗人心中的八旗制度所形成的秩序观念。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观察到,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观念是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共性。当满洲勃兴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不过是渔猎的原始民族,落后的生产技艺必须要将社会共同体的合作功能固化下来,以维持、发展和壮大族群整体。八旗制度起初是作为提高劳作效率的一种互助方式,而当自发的习俗变为制度(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努尔哈赤确立)后,在团结部众、培养民族意识上逐渐发挥出它潜在而深远的作用。军队建制的日常化、旗民兵丁化、生活闲暇化,促成了一种对于秩序的尊崇,相应于思想上则是守成大于创新,集体高于个人。其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重视组织的作用,纪律意识较强,同时也形成了保守意识,容易将个体淹没在组织中,主动性、创新性不足。[2]尽管八旗制度在晚清已经衰落,不过群体意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族性格的一个部分,从而作用于其精神生产的方面。
其次,清民转型时代的社会淆乱局面中,群体可以作为个体尤其是作为“遗民”的满族民众寻求安慰的心理依托。从内部来说,在“乾隆皇帝以后,清朝的八旗军力就滑向下坡,逐渐衰落,渐渐地一切都不行了。旗人,按他的老规矩,不许经商做生意;不许做农业;只许做官,只许当兵、打仗。所有的旗人,每月只靠发饷生活。”[3]“八旗生计”问题从清中期后一直成为困扰朝廷的大事,及其末世遭逢帝国主义入侵和帝国内部反叛斗争的兴起,更是雪上加霜。就外部而言,自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探索加之甲午战争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崩溃,使当时的知识精英意识到清廷也不足以凭恃,转而兴起文化民族主义。满洲建国之初,涂炭中原、屠戮江南所留下的心理创伤经过革命派的发掘和整理,汉人的旧痛暗伤再次复发,二百余年清政府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的现实加深了新仇旧恨的发酵。鼎革易代之际社会情绪往往易趋于极端,暴戾之气弥漫民间,在仇满、排满的宣传鼓动声势大涨之际,少数满洲权贵固然可以藉政治和金钱优势暂且回避尖锐的现实,而普通满人往往在这样的社会整体舆论中扮演了一个“替罪羊”的角色。[4]当然, “排满”的人群种类分殊,不可一概而论,更兼应势随时,前后变化较大。不过,他们却有个潜在的共通心理基础:确立汉民族乃至个人的历史优越感,可以或多或少抵消现实中汉人被满洲统治二百余年的耻辱以及中国人落后于西方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反过来,这样的话语氛围也就进一步加深了一大批满族人对于群体意识的向往。
以上两点还未尽全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和观念诉求,还需要从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挖掘。大的社会背景中,在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解体,社会权势发生转移,边缘上升,民气升扬。[5]而清末民初的京旗作家绝大部分正是在传统的科举道路上仕进无门,又无力或无法从事于新兴的革命浪潮的“零余人”。作为落魄文人,当其不得不投身于方兴未艾的新闻娱乐媒体报刊行业之中时,主要是情愿不情愿地为稻粮谋计,另外其实也自觉不自觉地带有维新派“群”的观念的影响。
如果说鸦片战争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兴起,而甲午的失败则是民族/国家主义的觉醒。中国的知识精英在那时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帝制的“天下”必然要成为明日黄花,中国如果要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下去必须要以一个“群”的归属——以民族国家的身份与各国竞争。早在1895年发表于《直报》的《原强》,严复就强调“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他借用荀子的话说: “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6]1897年严复着 手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Study of Sociology》 (社会学研究)翻译成《群学肄言》,陆续刊于《国闻报》,这个用进化论探讨社会演变的书冠以“群学”之名,自然有其强烈的群体意识。此后他翻译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On Liberty》(自由论)也译为《群己权界论》, “译者序”中说:“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7]。这些与他已经接受的西来进化论思想相一致。严复的言论其实代表了晚清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命题:以群而强,以孤而败;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群己并生,则舍己为群。为了在殖民帝国主义的丛林中求得中国的生存之道,群体的诉求就成为一种必需。
康有为作为经今文学大师、维新的先驱、立宪的主将同样也申论“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大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8]不过,严复和康有为其实更多是对精英群体发言,将这个观念辐射到更广泛的一般知识阶级层面,则有待梁启超的鼓吹和发扬。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1903)中,梁启超历数了国人诸多缺点,如奴性、卑屈、依赖、推诿、怯懦、不武、为我、好伪、涣散、旁观、保守、嫉妒、无国家思想、无公共观念,群体意识、权利和义务观念缺乏……因而“新民”显然是当时要务,启蒙、宣讲、感发、教化是期望国人能“翦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9]。而新民德的基本任务是, “纵观宇内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10]因为“人非群则不能使内竞发达,人非群则不能与外界竞争,故一面为独立自营之个人,一面为通力合作之群体,此天演之公例,不得不然者也。”[11]梁启超是在与“群”相对的“独”、“个体”、“己”等关系中去理解“群”、“合群”的, “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以一家论,则我之家兴,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祸;以一国论,则国之强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强,国之亡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亡。故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之义生焉。凡所以爱他者,亦为我而已。”[12]他是从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论证“合群”的意义,延续的是严复的功利道德主义。
梁启超反复强调了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并且从个体切己的利益入手论证个人同群体(他人、社会、国家、民族)之间命运的休戚相关。群体所具有的统一性、整合性、亲和性及凝聚力具有完全超出于个体的意义,从而也能由此群体意识发展出社会责任感、民族主义认同和爱国主义热情。这种基于社会达尔文原则的、为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和复兴寻找契机的群体观念,被历世以当兵卫国为惟一事业的普通旗人接受起来显得顺理成章:一方面,世代以来的八旗制度化生活已经形成了必要的集体文化心理积淀,另一方面,旗人依然具有“家天下”的观念,“群”的指向是“国家”,从利己的角度而言,群体观念也投合了他们对于国家的想象。而“排满”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心理阴影使得京旗作家很大程度上对于激进的言论和行动抱反感态度,在作品中对于民国之后的社会腐败、道德沦丧,以及激进知识分子的“新潮”时不时进行挖苦讽刺[13],老舍早期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因素,而其与新文化运动若即若离之关系也颇为耐人寻味。
但是,君主立宪始终是这些京旗作家所无法突破的天花板,穆儒丐、徐剑胆都有留日经历,日本明治维新的示范以及对大正时代(1912-1926)文化的羡慕,不自觉地表露于其作品之中。到了二十年代之后进入文坛的老舍那里,群体的观念在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紧迫局势之中,以三十年代的《小坡的生日》为标志,上升为真正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色彩的集体观念。老舍《骆驼祥子》的结尾为人们所耳熟能详: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14]如果从叙事美学来说,这样的卒章显志似无必要,反倒限制了文本阐释的开放空间。但是,如果从作者本人的态度来看,老舍在1936年写作时强调这一点同时代主潮需要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理念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渊源有自,对于个人主义的批评实际上隐含了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过于强调个人主义的反驳。这其实同京旗小说一以贯之的观念相通,勾连起由晚清到民国一个已经渐趋“落伍”的维新思想命题。从“七七事变”的外部刺激之下,从1937年底开始的许多散文议论,直到四十年代老舍与宋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就将战争情境下民族团结的“国家大义”作为主题来书写了。
老舍对于清末民初旗人作家的推进就在于此,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老舍实际上是个旁观者,但是如同论者所言,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一反常态’地表现出对于国家时政的超常热情和超常投入,正是他身后的那个民族——满族——上上下下共同表现出来的鲜明民族气节的缩影。”[15]这不仅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群体观念体现,同时也是在新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形成之后,让老舍有了群体的归属感。
二、道德的悖论与关注
鲁迅描述他所命名的“谴责小说”出现时的社会背景及其特色时说:
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16]
大略来看,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也可以归为谴责小说之一脉,优长与短缺都有相似之处,不过彼时各种名目的小说层出不穷,谴责小说至其末流就落入黑幕小说的泥淖之中,而京旗小说大抵还处于梁启超提倡的“政治小说”、 “改良小说”的余波。他们自述的办报、写作两大主要宗旨就是:一、维持原有社会的道德理想不变,以纲常名教维持人心世道。二、以循序渐进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改变现状,改造民众愚昧无知的现状。最早的旗人报纸之一《进化报》主办者言“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17]《燕都报》宣称要“与汪浊社会为敌,与困苦人民为友”,“一维持道德;二改良社会;三提倡实业”。[18]从后来的实际来看,提倡实业的效果固然不得而知,倒确实是一力以维持风化道德为主调。
在这些京旗小说的描绘中,整个社会都是晦暗颓靡、人心浇漓的恶之渊薮。政府、官场的不道德自不待言,而民间社会亦无操守,妓寮、赌馆、烟馆、迷信、父不慈、子不孝、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种种丑陋现象遍于国中。更有甚者,那些本身批判官场、鼓吹改良风俗的维新党人,公德是虚伪,也毫无私德可言。我们今日以后见之回首那段历史,自然可以得出诸如社会转型期,旧道已破、新德未立,因而造成种种道德滑坡、伦理沦陷的结论。然而,京旗小说的当事人却空怀一腔愤慨,只能枉自嗟叹。
晚清中国启蒙者引入西方的个人主义、公民意识、自由理念,意在提升国民意识,以促成国家建设和文化转型,而结果却是种下龙种,收获了跳蚤!这不仅仅是因为彼时岐语纷呈,源自各种理论资源的知识精英都试图给中国的未来开出诊断疗救的药方,从而形成了价值冲突与争夺的相持不下;同时,也因为破而不立,在传统的道统、正统坍塌之后,没有出现新的可供皈依的道德理想,所以出现了认同的空虚。“现代国民意识如果没有相应的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的约束,即会陷于极端个人主义的欲望泥潭,而对社会造成很大威胁。”[19]在这种情形下,就像黑格尔所说的, “恶”具有必然性, “当自我意识把其它一切有效的规定都贬低为空虚,而把自己贬低为意志的纯内在性时,它就有可能或者把自在自为的普遍物作为它的原则,或者把任性即自己的特殊性提升到普遍物之上,而把这个作为它的原则,并通过行为来实现它,即有可能为非作歹。”[20]民元之后,社会动荡、乱相毕出,也是势在必然。
道德信念和准则作为社会秩序的文化黏合剂,一旦面临危机,必然引起焦虑、恐慌、愤怒和寻找指责对象的合理诉求。如此情形之下,京旗小说由群体观念自然而然生出的是对于个人主义的鄙薄。由此生发出来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当大时代已然踏步向前,这些京旗小说作家却依然高举着道德的大旗,对曾经指引过他们的启蒙精英们大加挞伐——这实在是个极端吊诡的现象。从社会分层上来说,京旗作家不是他们时代最“先进”的人,他们其实从属于被启蒙的平民大众,处于权力和话语双重弱势的地位。而道德之所以成为这些弱者最后的批判武器,跟伦理的不同步有着莫大的关联。主流道德从来都是由上层精英制定并由他们作为表率来遵守的, 《礼祀·曲礼下》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也就是说道德对于底层民众其实并不具有天然的约束力:雅乐之下,逸乐并行;正祭之外,淫祀遍野。道德于此,其实有不同的分野,不同类型韵道德价值可以共存于一个社会结构的不同位置,即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道德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是“核心稳定,边缘流动”的范畴:某些根植于同理同情的人性深处的内容大体具有普适性,而涉及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诉求,就应时而变。
但是,作为“文化霸权”的必然行动,精英道德总是具有风行草上的教化功能,上层统治者会推行本阶层道德以维持统治的名教。宋代都城市民文化已具有这样的意味,明中期以后的发达的通俗文学、大众曲艺等等手段更是加速了精英道德下延的速度和范围。因而当底层接受精英道德的时候,他们的道德其实具有了“滞后性”。一旦某个统治阶层的精英道德陷入礼崩乐坏,上层人士改弦更张之后,依照原有惯性履行道德规范的底层就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道德沦丧的后果。[21]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传统,历来就有在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中棘刺世道人心的民间言论, “礼失而求诸野”之所以可行,原因正在于此。
不过,道德的滞后性坚守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如果它足够强大,或被另一类试图夺取话语权力的边缘人士挪用,它就会造成精英分子的普遍心理内疚,从而形成一种民粹主义(Populism)的取向。所谓“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 (明·曹学俭),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到民间去”的口号就反映出了这一点,而反对“愚蠢的文学革命”的辜鸿铭干脆就认为占中国人90%的文盲才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真正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人”,在他看来,在堕落退化的文明时代,“一个人越变得有文化或学问,他所受到的教育就越少,就越缺乏与之相称的道德。”[22]民粹主义同反智主义(anti- intellectualism)联系紧密[23],而京旗文学却既非民粹亦非反智,也不可视为全然的保守,而是显示出纯粹对于常识性传统道德的守望。老舍在这一点与他们几乎如出一辙。
新文学作品一大主题就是个人对于家庭的反叛,家庭作为不道德的象征与个人的自由、平等、民主追求总是发生冲突,构成了二元对立的模式:大家庭的幽暗背影与私自同居的涓生和子君(《伤逝》),周府和周府代表的资产阶级与鲁大海、周冲(《雷雨》),老太爷的家与出走的觉新(《家》)……有学者将其归结为“社会家庭伦理观念的超前和经济政治发展的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24],如果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则可以清晰发现旧道德的破坏在现代作家眼中几乎不成为一个问题,或 者至少在必须要矫枉过正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旧道德必须要被牺牲掉。这个历史代价论代表的无疑是一种精英论点,而京旗小说所体现出来平民大众的心声,唯独老舍依然视若珍宝。 《四世同堂》中尽管祁老爷子是“老中国的儿女”,但是老舍更多的是给予同情的理解和宽厚的体恤。而祁家的儿孙也并没有同家庭发生剧烈的冲突。钱默吟竟然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由吟风弄月的诗人成为秘密的反抗者。当然, 《四世同堂》中的“家”其实是“国”的象征——老舍事实上还是在“家国同构”的传统语法中书写一个民族主义故事。事实上,在“五四”运动后期,有识者已经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之外提出欢迎“穆勒尔小姐” (MissMoral,道德)的口号,伦理革命重返晚清“合群”的爱国与强国之道,只是关注之人较少,[25]而老舍毋宁在不自觉中暗合了这一转变轨迹。
老舍最重要的作品中,对笔下人物的态度基本都是从道德上进行评判的,而他所秉持的道德观念就是最基本、最常识的传统观念。新文化与旧道德曾经在胡适、鲁迅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都引起堪称惨烈的天人交战,而在老舍这里却是非分明、清清楚楚。同反智主义相区别的是,对于文化的尊重与执守;同民粹主义相区别的是,无论是贵族或者是平民,都不具有道德上的天然优越性,只要是不符合常识认知范围的伦理规范,老舍就会毫不留情。有些时候读者会觉得老舍的笔法比较类似于狄更斯那样的漫画化,人物性格比较扁平,缺乏变化以及更深层次和暧昧的中间地带,而这正是老舍接续了他的旗人前辈们一以贯之的道德标尺之所在。
满族的民族性格有论者总结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注重名与耻”,讲面子、重自尊。[26]关纪新先生注意到老舍出生于此种道德范畴,他作为独立个体走进社会时,免不了要按照自己耳濡目染、习焉不察的道德方式应对生活,这反映在其文学世界中就是对于伦理精神的执守,和对于国民道德衍变的持续关注。[27]较之于朝令夕改、变无常态的政治格局与社会风气,道德伦理作为稳固的心理深层结构,老舍同清末民初的京旗作家们可谓俩俩相望、前呼后应,并且植根于其性格内部。当不可逆料的罹难来临,老舍甚至不惜以一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践行祭殉自己的道德观念。
三、白话的权力流动
白话文无疑是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中一个重大节点。尽管运用古典白话写作的文本从元末明初就史不绝书,但是直到戊戌变法前,白话文运动的自觉才由维新的知识精英提出来,是民族主义的内驱力在其中发挥作用。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1887)正式提出语言与文学合一的问题,他说:“语言与文学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学合,则通文者多。”[28]梁启超大力提倡新文体,自觉地注意通俗化。1898年8月,裘廷梁的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发表,白话文作为变法事业成功的根本途径之一,得到了维新派充分、明确的肯定。陈子褒也发表文章提倡推行白话,并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明确提出报纸应改用白话,用白话文办报,使人人都能读。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白话报纸陆续出刊,白话书籍也印行。[29]京旗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应运而生。
京旗小说作者使用地道的北京方言写作,夹杂着古典白话的影响,就如同和它同时期在南方口岸城市风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从实际情形来看,这些作家是真正的“我手写我口”,不过这种白话可能未必是启蒙者最初所期望的,因为京旗小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兴趣。这提示我们思考白话本身,也即白话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民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它的字词句法形式可能并非那么重要,影响大小也非首要关注,而关键在于内容和观念的“新”。
白话文最初在晚清的使用与接受,就明显地含有等级意识。文化水平的高低,成为取得阅读文言或白话资格的关键因素。及至后来新文化的主将之一胡适清楚地发现, “这五十年的白话小说史仍旧与一千年来的白话文学有同样的一个大缺点:白话的采用,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民国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便是一种有意的主张。”而“无意的演进,是很慢的,是不经济的。”最近“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难道不能称为‘有意的主张’吗?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因而他最后特别申明“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30]更有甚者,整理国故,彰显国粹的文化保守者比如章太炎根本就认为白话的价值可疑,后悔自己曾经写过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31]。
这里潜藏着一个文学价值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的文化理路来看,文学不过是小道,不足为法,道、圣、经、学、理……这些范畴才是超越性的,具有恒久价值的。 “文”不过是可以“得意”而忘之的“象”和“言”。传统观念中,史书记载的“儒林”显然要高于“文苑”。章太炎等人更看重的其实是“儒林”, “文苑”都要等而下之,更何况原本连“文苑”都不屑的白话?至少到二十年代,文言仍保留着事实上的优越与尊贵,作为精英人士共享的文体而被欣赏。以白话为开通民智的工具,固然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也存在着根本的隐患。启蒙者的角色认定,使晚清白话文的作者自居于先知先觉的地位。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造成运动的不乏广度,却缺少深度。因此,实际发生作用的主流思想却是文言、白话并行不废。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未见得摆脱精英意识,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尽管他不停地标明“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发展取向,但在最初就已经伏下了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古典白话与新型白话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延续性,尽管从历史的谱系来说,胡适通过历史叙事(《国语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的拣选来提升白话的地位和权威,但是这只不过是策略的手段,并且也引起很多不满——从根底上来说,新文化运动的白话就是一种语言的断裂性诉求。
从底层的接收者一面看,绝大多数“一般人”本身对新潮流其实无动于衷,在飞扬的热闹和平凡的安稳之间,他们更多向往的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一点对于当时穷愁落魄的京旗作家而言更显得迫切。他们不怎么感受到文学革命的冲击,甚至隐约地怀有反感,他们对于文学并无明确地纲领与追求,而首先是个生计问题,白话的运用纯乎是一种本能。当新文学倡导者挟带有意识形态内涵的“白话”呼啸而来[32],他们这种白话也要成为被拉枯摧朽的一部分。
老舍刚一登上文坛,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老张的哲学》、 《赵子日》、 《二马》等等,无论从思想观念和白话技巧更多是延续了京旗作家的那种平民底色,不过吸收了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格调。幸运的是,新文学作家在彼时正需要一个带有大众趣味而又不沦为下流的作家,老舍适逢其会。瞿秋白在三十年代批评“五四”以来的文学是“五四式的新文言,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根本是口头上读不出来的文字,”[33]认为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产生的新文学是“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34]这虽然过苛,未尝没有道出一点实情,老舍作品的诞生正是在这种情形中的独树一帜。他的价值在于,以一种“超时空、超党派、超雅俗”的平民语调讲述普通大众自己的故事。
京旗小说承接的满族传统说部、汉文翻译小说的营养、北京地方性文化的遗产,广泛吸收了诸如评书、相声、子弟书、八角鼓词等等的语言成分。其白话处在高雅的官话同俚俗方言之间,更多倾向于下层百姓的语言。他们谙熟平民生活,刻画京城底层市井细民的行状容貌,穷形尽相,声口毕肖。而京旗小说的读者肯定不是大学或中学里接受新鲜思潮的学生,也不是完全没有多少文化的贩夫走卒,而是那些普通的北京城小市民,粗通文字,理解上没有障碍,却又不具有更高瞻远瞩的政治与社会思想。最主要的,这些读者阅读小说是为了娱乐和消遣,还有报纸的计日出版、作家无法做精细的处理等等,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对作家写作的模式和风格产生影响。口语人文的写作方式和通俗晓畅的美学风格之所以会成为一种特色性的表征,同这种文化积淀和现实处境是脱不了关系的。
老舍发挥京旗小说无意识中遗留下来的白话流风遗韵,将之变为一种“精致的通俗”:娱乐又不失品位,俚俗中蕴涵格调,悲中含笑、苦中作乐。而京旗小说为新文化运动者所不屑的陷溺于凡庸中的缺陷,也被源自西来小说的现实主义所升华,因而老舍的语言从价值上得到了确立,而有关幽默等种种一目了然的特色又被有限度的保存下来。老舍正好出现在现代白话文学在古代白话和欧化白话俱已有所推进而未臻完满的时候,在此基础上结合本人的天赋,成为通俗白话的典范。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在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老舍从京旗小说一脉改造而来的语言同“民族形式、中国气象”尽管貌合神离——老舍更多是城市平民的气质——但并不妨碍他同源自农民的美学趣味并行不悖,共同构成后来的新型民族国家所需要的语言形式。
概而言之,京旗小说在晚清维新启蒙运动中产生,更多的是从切身的底层出发书写大众文学产品,无论在文学理念和技法上都趋于传统的市民文学。在晚清向民国递进的唯新是趋的整体社会风潮中难免不呈现出“落后”的面相,对照于新锐、快速的文化革新运动,它们反倒更真实地呈现了城市平民的生存处境和思想现实。从文学史的命运上来说,京旗小说必然要成为后来渐成一统的线性进化论的牺牲品,但是作为带有大众品性的文化产品潜在地熏陶了同样作为旗人后裔的作家老舍。他们在急剧变动而又杂语纷出的总体社会背景中,浮现出另类的面孔,在大时代的洪波激流底部,形成了沉寂于浪潮下面的潜流暗涌。
标签:老舍论文; 文学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道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