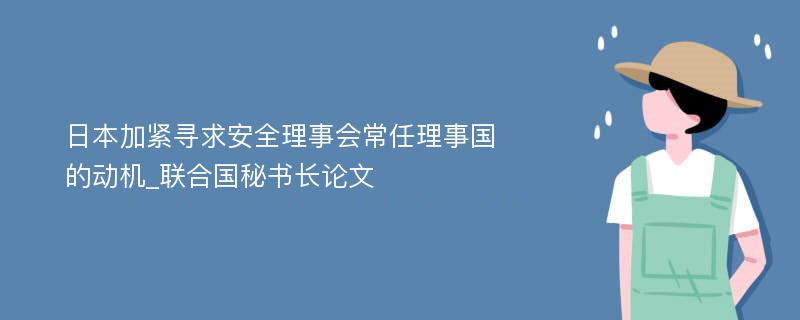
日本加紧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论文,动因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萌生于冷战时期,但由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联合国的改革等是日本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可逾越的先决条件,同时,以东西方冷战对峙为基本特征的两极世界格局也使日本在国际舞台上难以充分展露头脚,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调门并不高,也未正式提出申请。然而,在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不仅正式地提出了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而且大大地加强了谋求的力度:从舆论宣传到实际运做,从积累“实绩”到争取选票,无所不用其极,摆出了志在必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以2004年第59届联大为契机,日本为实现常任理事国之梦,又发起了新一轮冲击波。会前(8月),日本外务省设立了“联合国对策本部”,并积极向联合国及安南秘书长反映日本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建议;会上(9月),小泉首相亲自出马代表日本政府再次明确表示了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会后(12月),日本外务副大臣逢泽一郎邀请对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示理解的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召开讨论安理会改革的会议,呼吁支持安南秘书长提交给联大的“名人小组”的联合国改革方案。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政府为谋求常任理事国席位前所未有的紧锣密鼓、大动干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拟对其主要原因进行分析。
一、日本的国际政治空间显著拓展
日本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强国,到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同时也成为公认的世界科技大国、潜在的军事大国。无论就亚太地区,还是就世界来说,日本在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中都具有发挥重大作用的能力。但是,冷战结束以前,日本的国际作用并不是十分突出。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东西方冷战对峙,国际秩序和力量结构以两极为基本特征。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主要成员和美国的盟友以及受控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国际地位与国际作用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和限制,不得不长期处于“经济大国”和“政治小国”的境况。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秩序和力量结构发生了变化,两极世界格局退出了历史,多极化成为世界的发展趋势,国际事务将更多地依靠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来管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由美苏两大国来左右。因而原来两极体制中对日本发挥国际作用起到限制的因素迅速减少,在客观上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拓展了日本的国际政治空间;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使得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迅速提高,共同利益大大增多,自然也使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增加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和趋于严重,以及解决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更使日本显示出了较大的优势。这些表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社会使日本第一次真正有机会通过为国际社会做贡献来改变二战后的历史地位,进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大国。
以追求政治大国为战略目标的日本显然不会忽略这样的客观形势和机会。1990年3月2日海部俊树首相在日本第118次国会做施政方针演说时称:“在依靠力量对立来支配世界秩序时,日本难以作出依靠力量的贡献,而在开始摸索以对话与协调来构筑新的和平共处的世界的今天,我国就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1](P289)1991年海部俊树首相在访问东盟国家期间又指出:“随着冷战结构的解体,世界开始从两极结构向多极结构转变,西欧国家与日本同美国共同作为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其重要性日益提高。”[2](P403-404)时为日本外交政策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外务省事务次官粟山尚一也撰文指出:“90年代的日本外交必须积极参与旨在构筑世界新秩序的国际协调”,“90年代的国际新秩序的责任必须由日美欧等先进民主国家共同承担”。[3](P12)显然,90年代初,日本政府及其政治家就开始意识到,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时代条件已经到来,日本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92年1月,宫泽喜一首相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提出:“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应对安理会的机能、构成进行改革,”[4](P23)隐约流露出了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到1994年9月,日本外相河野在第49届联大演说时声明:日本“在得到多数国家赞同的基础上,准备作为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5](P357)从而正式代表日本政府提出了申请,拉开了冷战后积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序幕。
二、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更加明确
冷战结束以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和全球形势趋于缓和,使得联合国建立之初时所试图实现的大国协调有了可能;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地区热点和环境、人口、资源、核扩散、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开始突出,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的权威国际机构的协调加以解决。因此,冷战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作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舞台,而未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处理全球性事务方面发挥有效职能的联合国,再度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尤其是在海湾危机中,联合国通过了对伊拉克实施包括军事打击手段在内的一系列制裁决议,并组成多国部队将伊拉克入侵军队赶出了科威特,显示出了联合国的作用明显增强。日本政府及其政治家敏锐地认为:“联合国已从由于冷战对立难以发挥作用的危机时代摆脱出来,开始有可能迎来‘联合国的复兴’”。[4](P15)“以海湾危机为契机,冷战后的联合国在为维持稳定的秩序以多国间协调为目标而进行的国际努力方面,作为一个被赋予法律、政治权威、实现多国间协调的唯一的普遍论坛,正在发挥作用”。[6]
联合国已作为政治大国发挥作用的重要场所,而只有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才能真正成为政治大国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日本因而将政治大国的目标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挂起钩来。当初,日本提出政治大国战略时,其目标还是比较笼统的。1983年7月,中曾根首相首次宣称:“日本今后应同经济力量相称地作为国际国家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言,并履行义务”;[7](P213)“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强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其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8]“政治大国”也好,“国际国家”也好,其涵义并不是十分清楚的,更没有明确地将其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直接挂起钩来。而冷战后,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逐渐地得到明确,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了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基本标志。1991年12月,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就明确地道出了日本政府的心声: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等于被承认为世界政治大国。”[9]
日本还对自己履行了政治大国的“义务”而没有得到政治大国的“权力”和“待遇”感到强烈的不满。例如,尽管日本为海湾战争提供了130亿美元的经费,但却由于连非常任理事国也不是,未能参与安理会的决策过程。日本驻联合国代表曾对此抱怨道:“我们只能在会场外等待会议结束,然后从美英等国代表那里打听到消息,再记录下来。”[10]1991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也写道:“在海湾战争中,日本由于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而未能得到在安理会接连通过的决议中充分反映意见的机会”,并认为在“安理会占有席位”对日本来说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课题”。由于“只让出钱,不让说话”的待遇实在难以忍受,海部、宫泽、细川、羽田、村山内阁都在联合国会议上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念念不忘、时时感慨,直至在1994年第49届联大上日本正式提出了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
三、国际事务中“实绩”积累成效可观
日本将其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追求纳入到政治大国战略的轨道以后,为了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实现既定目标和意图,改变了过去远离国际事务的做法,转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多做国际贡献,以改善国际形象、扩大国际影响、提高国际地位。正如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所曾坦言: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重要的是“积累实绩”。[11]因此,日本于冷战结束前后开始比较广泛地参与了联合国主持的国际事务,并积极出钱、出人。
例如,不断加大对联合国及有关国际事务的财政投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多次出资承办联合国的有关会议;80年代末期以后,日本向联合国提供的经费一直位于成员国第二位,目前仅次于美国,超过其他四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供经费的总和,接近总经费的20%;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日本提供了多达130亿美元的作战经费,作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日本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份额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ODA提供国,此后一直保持着这一位置;1999年3月,日本倡议设立了联合国“人类安全保障基金”,到2000年末,日本就已经提供了近100亿日元的资金。
再如,积极参加联合国名义下的国际维和行动。80年代末,日本政府做出了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决定,并特别为此做出了派遣非自卫队员和不从事直接军事活动不违背国内法律的解释,克服了参加国际维和活动的宪法和自卫队法等有关法律障碍和国内舆论的压力,从而得以陆续向安哥拉、柬埔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阿富汗、南非、巴基斯坦、塞浦路斯、纳米比亚和尼加拉瓜等国派遣人员,参加和平斡旋、监督选举、战后重建等工作;90年代以来,积极地主持召开了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参与朝鲜半岛安全对话,参与处理朝鲜核危机问题等。
又如,热心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的日常工作。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不仅继续为联合国提供较多的资金,保持着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金负担国的地位,而且出任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高级职位官员的数量大量增加。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18个主要机构中,日本是担任理事等要职最多的国家;在90年代上半期,日本人担任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级职位就有三个之多,打破了联合国有关一个国家在联合国担任高级职位不超过两人的惯例。
不可否认,在“实绩”积累方面,日本的确表现突出,记录良好,印象深刻,从而也大大增加了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筹码。9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就因此而积极主张日本应该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政府也因此而踌躇满志。在2004年10月11日第59届联大以安理会扩大为议题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原口幸市就充满自信地表示说:“我确信,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起的作用正在为日本能够肩负起常任理事国责任提供充分依据”;[12]在10月21日联大发言中,小泉首相更是信心十足地宣称:“我们认为,日本已经发挥的作用为它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3]
四、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增加
由于有法西斯战败国的历史记录,在取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以前,日本实现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梦想是不现实的。所以,冷战结束以前,日本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并不十分张狂,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诉求也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只有美国从70年代的尼克松政府开始,表示过在原则上支持日本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没有也做不出什么实际的举动。英国、法国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削弱而持消极态度。苏联、中国从各自利益和立场出发态度也不积极。冷战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美国从克林顿政府开始提高了热情,明确表示:“安理会应该扩大,应该吸收德国和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10]而且英、法两国先后表示可以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不反对日本和德国担任常任理事国。2004年10月,在第59届联大上,日本已经第九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迄今为止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国家。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也有了显著的增加。据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2004年10月11日称:目前表明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有45个,未公开表明态度但实际支持的国家更多。[14]而据1990年11月日本《每日新闻》在对驻东京的108个国家大使进行的通信调查,当时赞成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仅有4个国家。[15]
日本取得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有明显增加,在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问题上也得到了体现。日本在上个世纪从进入90年代开始加强了删除“敌国条款”的攻势,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90年,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在第45届联大上明确提出删除“敌国条款”的要求后,美国国务卿贝克称“敌国条款”是“时代错误”,苏联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也称其“落后于时代。”[16](P372)此后,在46届、47届、49届联大上,日本都一再提出了同样的要求。1995年,第50届联大以155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了重新考虑联合国宪章,取消“敌国条款”的议案。虽然还没有实现删除“敌国条款”,但对于日本来说,这毕竟是朝着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从而为担任常任理事国扫除障碍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正如英国著名学者赖因哈德·德里弗特所评论的:日本之所以热衷于删除“敌国条款”,主要是因为它“与威望的问题紧密相关”,“删除这一条款意味着宽恕日本在历史上的侵略行为,日本才能最终恢复名誉。到那时中国这个过去受过日本侵略,而且又在地缘方面属于亚洲最重要的国家就不得不支持日本担任常任理事国了。”[17](P116)正因为如此,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仍在这一问题上锲而不舍、不遗余力。2002年9月,小泉首相在第57届联大的一般演说中表达了日本政府希望删除“敌国条款”的意向,声称“旧敌国条款”作为20世纪的遗产,是联合国宪章中存在的一个问题。[18]2003年9月,日本外相川口在第58届联大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一般性讨论发言中,再次表达了日本的愿望,指出“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中存在的重大问题,需要寻求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18]2004年2月,小泉首相和川口外相在会见访日的安南秘书长时,也表示日本希望能够重新评估并删除“敌国条款”。
五、联合国改革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日本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大障碍之一是联合国改革问题,但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而安理会的改革尤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安理会席位是否需要扩大、扩大多少、扩大后的新常任理事国是否拥有否决权,等等,都需要现有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取得一致意见,并需要联合国至少2/3的成员国同意。尽管在冷战时期,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多次提出过联合国改革的问题,但赞同的国家一直处于少数,加上冷战因素的存在,关于改革的呼声难以形成气候,实施改革也始终提不到联合国工作日程上来。这也是日本在冷战结束以前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调门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关系改善,国际形势趋缓,使得联合国最初建立时所试图实现的大国协调成为可能,而新的地区热点和日益突显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上升。国际社会关于改革联合国以适应时代需要的呼声因此大为高涨。尤其是由于成员国数量的大大扩展,成员国关于改革安理会职能、扩大安理会席位的要求日益强烈。日本政府自然也是推动联合国改革的急先锋国家之一。在1992年第47届联大上,日本就联合其他23个成员国共同提出了一项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提案,要求将扩大安理会席位问题列入第48届联大议事日程,不仅获得了一致通过,而且促使大会为此做出了关于安理会扩大与议席平均分配的决议。从1993年第48届联大开始,扩大与改组安理会问题基本上成为以后每届联大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表明联合国改革问题已经逐步进入了联合国的工作日程。
2003年11月,安南秘书长已任命了一个包括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在内的由16人组成的联合国改革问题“名人小组”。2004年11月30日,该“名人小组”提出的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报告已被公布,共包含101项改革建议。安南秘书长已表示,他将于2005年3月在“名人小组”报告的基础上提交一份有关联合国改革的纲要。据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2004年10月13日称,在第59届联大上各国代表的发言中,提到有必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的国家有148个,提到应该增加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有84个。[14]联合国改革问题被提到联合国工作日程上来,而且秘书长及有关机构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工作,这对于急于实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梦想的日本来说显然是再好不过的兆头和十分有利的机遇。
六、国家利益推动更高的国际地位追求
日本的外交动向和战略目标归根结底是由其国家根本利益决定的。日本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其经济是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日本经济的发展也因此离不开世界。恶劣的地缘环境、资源的严重贫乏和市场的相对狭小,是日本经济所具有的严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也就决定了日本经济对世界的十分严重的依赖性。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大大上升乃至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导致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强,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和国际依赖性愈加显得突出。国际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导致日本与美国、西欧国家等世界大国之间的经济摩擦频繁发生,本来就使日本的资源问题、市场问题趋于严峻,而像中东等地区这样的对日本经济发展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一些能源和原材料产地的局势不断恶化,以及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上升引发的国际局势动荡,使得日本的资源问题、市场问题更加趋于严峻。因此,对于日本来说,如何协调自己与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影响国际事务以确保国际局势稳定,如何保证拥有比较稳定的资源和市场,从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维持自己经济大国的地位,就成为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中的重中之重。冷战后,日本重新树立了冷战之初早已提出但后来陷入严重困境的“联合国中心外交”,迫不及待地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就是这一国家根本利益所驱使的。
由于日本毕竟还不是一个世界政治大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都还有限,没有足够大的国际事务发言权,因此,协调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确保国际局势的稳定、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能力也就有限。日本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形成的“经济大国政治小国”(“跛足式国家”)[20]的危机感,在冷战后自然更加十分深重,由此也就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提高国际地位的要求和更大的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力欲望。冷战后,日本外务省就一再明确提出:“国际环境本身正处在变动中,作为日本不能被动地接受这一变化,而必须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外交,与其他主要国家共同合作,参与构筑新的国际架构;”[21]“日本必须在尊重基本人权、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这些宪法所宣称的理念之下,为使这些理念在国际社会也得到实现,构筑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加深,发挥这一作用既是日本的责任,也有益于自己的国家利益。”[22]由于参与构筑新的国际架构,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必须借助于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作用日益增大的联合国的舞台才可能实现,所以,日本在冷战后及时地重新树立了“联合国中心外交”,加大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力度。正如日本学者神余隆博所指出:“冷战后新的联合国中心主义是实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国协调的手段之一,对我国而言,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它有可能加强我国在联合国的发言权,更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6]
标签:联合国秘书长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论文; 联合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