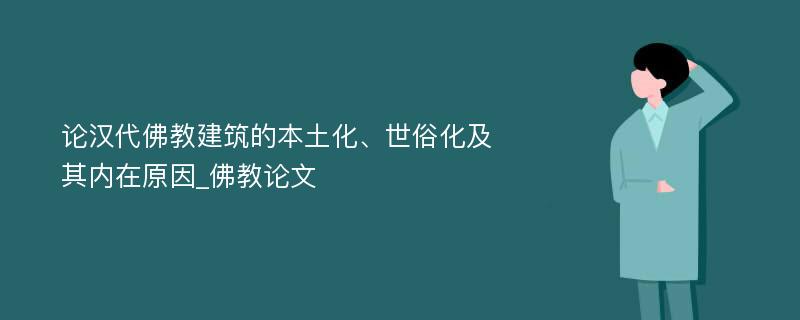
略论汉传佛教建筑的本土化、世俗化及其内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传论文,佛教论文,内因论文,本土化论文,世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4)06-0060-04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兴衰而绵延不绝。其间虽与儒道等本土文化、习俗相互激荡与融汇,却依然延续了其迥异于世俗的仪轨体系,在起居饮食、服饰器物、典章制度等方面均有体现。但佛教建筑却渐失其原貌,除佛塔外,在布局、形制和结构上与汉地宫室、衙署、宅第等建筑高度接近,呈现出本土化、世俗化特征。 一、汉传佛教建筑的本土化与世俗化 自频婆沙罗国王在王舍城始建竹林精舍,①供奉佛陀及弟子修行弘法,佛教伽蓝②逐渐发展起来。从现存的阿旖陀石窟和桑奇大塔等遗迹来看,古印度早期佛教建筑一般由窣堵坡和毗诃罗组成。窣堵坡是供奉释尊舍利的纪念性建筑,毗诃罗是供僧侣起居修行的功能性建筑,即僧舍、精舍。伽蓝以窣堵坡为核心,精舍僧房沿窣堵坡四周分布。目前来看,东南亚地区的小乘佛教寺院较多保留了印度原始佛教伽蓝的特征。 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携白马负经抵洛阳。第二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筑白马寺。《魏书·释老志》有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1]从文献来看,佛教入中国之时,其建筑尚大致保留印度伽蓝的特征,以佛图为中心,呈四方式布局。其后,随着造像的传入,佛殿开始出现。如《高僧传》中便有东晋兴宁年间(公元363-365年)“沙门竺道邻造无量寿佛,高僧竺法旷为之起立大殿”[2]的记载。由于印度伽蓝之中并无佛殿建筑,失去参照来源的佛殿便开始移植或转化汉地建筑。由于供奉高大佛像的需要,佛殿主要借鉴了空间宏阔的宫室建筑,故两者在形态上较为相似。北魏迁都洛阳后,所建佛教寺院不知凡几,《洛阳伽蓝记》描绘了这样一番景象,大型寺庙如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形制似今端门。”[3]浮屠乃“架木为之”,佛殿“形如太极殿”,寺院墙“若今宫墙也”,南门楼“形制似今端门”。由此来看,当时的佛教建筑在材料、结构、形态等方面已与世俗建筑颇为相似。这一时期礼佛之风日盛,舍宅为寺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风尚也加速了汉传佛教建筑的本土化进程。自隋唐以降,造像崇拜盛行,体量高大的佛殿与佛塔共同组成寺院核心,形成塔殿并重的格局。从唐代律僧道宣所著《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和《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可以了解到,唐代寺院设佛殿和佛塔共同组成中院的核心,周围建有法堂和僧房,佛塔的唯一中心地位逐渐开始改变。在图像资料方面,敦煌莫高窟中的几座隋唐石窟均有描绘寺院形貌的壁画,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寺院以佛殿为主,居于建筑院落的中轴线上,其后设后殿,庭院两侧布置回廊、角楼、门楼等,宛如皇家宫殿。及至宋元,佛殿代替佛塔成为主体,寺院布局一般沿山门南北轴线建若干佛堂,谓之伽蓝七堂。至此,汉传佛教建筑的格局与形制基本趋于稳定,之后的变化已日渐微小。 明清时期为寺院建筑在布局和形制上的成熟期,从现存明清寺院的布局来看,大型寺院基本为多轴线构图,在山门主轴线上依次建造天王殿、大雄宝殿和法堂;东西两侧轴线上分别设立钟楼、伽蓝殿、观音殿、鼓楼、祖师殿和轮藏殿等(各宗各寺配置略有不同),左右对称、布局严谨。 佛教寺院建筑不仅在布局上,而且在材料、结构等方面也均与世俗建筑高度一致,皆以木构架为主。早期的佛殿建筑实物至今已无遗存,但在同样供奉佛像且有模仿佛殿意味的石窟形制中仍可窥见端倪。如麦积山石窟第4窟雕凿有七梁八柱、平拱藻井的仿木单檐庑殿结构。③天龙山石窟第16窟前廊遗存的三开间仿木构建筑,中间设两根八角柱,柱头施栌斗、栏额及一斗三升,补间刻人字形叉手。④这些石窟均透露出当时佛殿的木结构形象。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南禅寺大殿为现存最早的佛殿建筑,面阔三间,进深四椽,南面明间设双扇板门,两侧设直棂窗,其余三面为土坯墙。而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和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民居明器则呈现出同一时期的民居样貌。其正堂基本也是面阔三间,木构架,面南开门窗,其余三面为土坯墙,与南禅寺佛殿十分类似。凡此种种,都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汉传佛教建筑在唐以后已具有高度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特征。 二、汉传佛教建筑的佛教宇宙观与宗教伦理问题 建筑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文化所建构的产物,因此也传递出相应的文化核心价值。汉传佛教建筑的本土化和世俗化,自然削弱了其作为佛教文化物质载体的功能,甚至在某些方面与之相悖,以致产生了宗教伦理问题。 1.汉传佛教建筑难以反映佛教宇宙观 佛教建筑作为佛法弘传、僧徒参学和法会举行的空间,也是宗教体验的重要场所。与中国世俗建筑无异了因其所承担功能之需要,往往以某种特定的叙事方式和象征性符号表达或映照佛教思想和观念,营造一种佛教宇宙景观的人间再现以感染信徒。但汉传佛教建筑的世俗化形态却与佛教所推崇的理想世界相去甚远。 在佛教宇宙观中,世界被分为永恒极乐的彼岸世界和痛苦污秽的此岸世界。此岸世界自不多叙,而彼岸世界在不同典籍中虽有不同描述,但大都为“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的神圣之境。[1]在佛教经典中,无论是《弥勒上生经》中的兜率天净土、《妙法莲华经》中的灵山净土、《华严经》中的莲花藏世界,还是《药师经》中的琉璃净土、《大宝积经》中的如来妙喜净土,都描述了佛教徒所信仰和向往的理想世界。例如,在《大乘密严经》中,佛国圣境有“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四边阶道,金、银、琉璃、颇梨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颇梨、车璩、赤珠、马瑙而严饰之。”[4]可谓宝相庄严,美轮美奂。 佛教宇宙观是佛教独特文化内涵的重要体现,蕴含了丰富的空间和图像信息。但在汉传佛教建筑中,很少将这样的场景进行表达。而在南传和藏传佛教建筑中,对佛教宇宙观的呈现却是一种常态。如柬埔寨吴哥建筑群中的巴扬寺,便完全遵循了胎藏曼荼罗图式的布局。寺院核心区域由三层寺山上十六座相连的宝塔构成,渐次缩小上升的矩形回廊组成三层平台,顶层平台中间为圆形大塔殿,塔殿内有四面辟门的圆形胎室,胎室周围环绕八个小室,形成一朵盛开的八瓣莲花状,寓意胎藏曼荼罗中的“中台八叶院”。而西藏山南地区的桑耶寺,也按《长阿含经》中四大洲、八小洲的世界中心理念进行寺院建筑的布局。其佛室内部柱梁遍布飞天、人物、禽兽等浮雕,墙面施以彩绘壁画,花窗、斗拱以金银饰之,力图营造出佛国圣境的神圣场景。相比之下,汉传佛教建筑沿用中国宫殿、衙署、居室等世俗建筑的样式,并未形成独特的空间和形态,更遑论再现佛教宇宙观中的种种景象了。 2.汉传佛教建筑的等级化现象与佛教平等观的矛盾 自创立之初,佛教便以反对种姓制度,争取根本平等为目标,平等观是佛教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汉传佛教建筑作为佛教文化的物质载体,本应传达出这种平等精神,然其沿用的汉地世俗建筑是礼制的产物,遵循严格的建筑等级制度,处处都试图构建上下、尊卑、贵贱有别的秩序体系,这种等级化与佛教平等观无疑是相当矛盾的。 佛教伽蓝是僧徒礼佛修行的场所,本无高下之分,但汉传佛教建筑的本土化和世俗化使其受等级制度的影响日益明显。据现存史料,唐代时佛寺在性质上已有官、庶之分,[5]皇亲贵胄敕令建造的寺庙地位最高,名僧大德奏请赐额的寺院次之,一般民众捐建的兰若、山房、村佛堂等再次之。敕建奏请的佛寺,经济由国家供给,分田地、赐寺额;兰若、山房和村佛堂却只能依靠僧人化缘或信徒捐赠。在会昌灭法废寺时,先废除村野山房、招提兰若,渐次才波及名寺古刹,而在大中复法时又反之。始建于清早期的黔灵山弘福寺,不少建筑都由地方官员捐建,并体现出官阶级别。寺中大殿、藏经阁之类的核心建筑多由总督巡抚捐建,次要建筑则由布政使等低一级官员捐建,寺院建筑已经成为社会等级的高度反映。 等级的差异在佛教建筑的形态上也得到直接的体现。现存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同为唐代遗构。南禅寺是在州府县志和佛教文献中均无记载的偏僻小庙,佛光寺则为燕宕昌王所立之五台名刹。南禅寺大殿面阔仅三间(11.75米)、进深四椽(10米),单檐九脊歇山顶;佛光寺东大殿面阔七间(34米),进深八椽(17.66米),单檐五脊庑殿顶。参照《唐会要·舆服志》:“三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6]佛光寺东大殿远超过“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的规模;而南禅寺却仅仅相当于六品以下及庶人堂舍。可见,汉传佛教建筑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已与佛教“一切平等,圆融互摄”的理想渐行渐远了。 三、汉传佛教建筑世俗化、本土化的内因 汉传佛教建筑既未延续其天竺故土的伽蓝旧制,终究也未形成有别于汉地建筑的独特形态。这一结果既无法反映佛教宇宙观,其等级化也有悖佛教的宗教伦理。究其内因,是多样而且复杂的,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以下的探讨和分析。 首先,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佛教的教义、教规有关。佛教的终极目标在于度脱众生,使其永离苦海,到达涅槃的理想彼岸。信仰者应不断闻思修慧,弃贪嗔痴念。众生在修行解脱的道路上,对于佛所说之法尚不应执着,何况修行的外在环境。因此,早期佛教徒并不在意修行场所,过着四处游方、居无定所的生活。随着僧团和信众日益壮大,出于安居制度、讲经弘法和礼仪崇拜等需要,佛教伽蓝逐渐产生。由于当时的印度佛教徒不事生产,佛教伽蓝如衣物和食品一般,多由有缘之人布施供养得来。供养人的情形各不相同,因此早期印度伽蓝的形式亦多种多样,并没有固定的佛教建筑形态。而佛教徒持不贪不痴的观念,对这种情况也并无苛求。正是这种宽容的态度,成为汉传佛教建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佛教初入中国时,由僧人自行建造寺院几无可能。因此,一开始便是依赖世俗社会中的官方敕造。仅东汉明帝就在洛阳城中建造了7座僧寺和3座尼寺。梁思成等学者认为,官方敕造的佛寺的在布局形态上多仿照当时的宫室、官署,[5]加上前文所述由于供奉高大佛像之需要,佛殿建筑亦采用宫室建筑样式。因此,对宫室官署的模仿成为寺院建筑与世俗建筑趋同的最初因素。除此之外,汉传佛教建筑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舍宅为寺。北魏迁都洛阳后,舍宅为寺的现象开始在上层阶级出现,后逐渐影响民间,至河阴之变(公元528年)后达到高峰,甚至成为一时之风尚。《魏书》有载:“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宅,略为寺矣”,[1]以至洛阳城内“列刹相望,祗洹郁起,宝塔高凌”。[3]舍宅为寺之风历时长久,至明清仍余绪不绝。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皇亲贵胄的府邸还是百姓庶民的宅第,均将原有建筑加以改造。相对简单的做法即将前厅改为佛殿,后堂改做讲室,而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改造亦不鲜见。例如目前完成两次考古发掘的唐代西明寺,⑤曾先后为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初唐万春公主和魏王李泰的宅邸,经多次改造后完全成为寺庙,至晚唐时才逐渐荒废。既然“寺”由“宅”而来,那么“圣”与“俗”之间也自然难以区分。以此方式建造或改建的寺院数量急剧增加,至南北朝时已是伽蓝连路、钟磬相闻,成为佛教建筑本土化和世俗化重要的社会因素。 汉传佛教建筑在其建造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如果说舍宅为寺等现象为一种权宜之策、被动之举,佛教徒基于文化认同和传教弘法的需要,其自行筹建的寺院多倾向于采用世俗建筑的形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佛教作为一种产生于印度的宗教信仰,与中土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经西域传至汉地后,佛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只是作为神仙方术的一种在上层阶层流传,寻常百姓很少接触。其时寺庙数量寥寥,亦鲜有信徒出家为僧,传播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社会民众对佛教的接受和参与,自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佛教在中土的盛衰。因此,在汉魏时期,为了更好地融入汉地社会,佛教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适时地采取了一种迎合与依附的姿态,积极与中土的文化环境相融合,进入后世所谓的“格义”佛学阶段。“格义”佛学简单来说,是以中国儒道等典籍中的概念来比附佛理,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并接受佛教要义。从历史上看,“格义”的方法,确实对佛教在中土的立足和生存具有重要意义。其效用到东汉末年便得以显现,佛教已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以推广,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佛教与汉地文化的贯通与交融。在这一背景之下,寺庙建筑采用世俗建筑的形态亦成为一种折衷致用之道。世俗建筑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沿用其形态作为传教弘法的场所,无形间便增进了人们对佛教的认同感,自然也更有利于佛教的推广。因此,有些佛教寺院甚至开始以园林样式进行建造,如北魏时期的景乐寺“堂庞周环,曲房连接,轻条佛户,花蕊被庭”;[3]正始寺则是“众僧房前,高林对牖,青松绿柽,连枝交映”。[3]这些佛寺景色清幽、林木相间,社会各阶层香客游人纷至沓来,参禅访道、听讲经法、观花品茗,成为广结佛缘之处。可以想见,这样的寺院建筑环境确实更有利于佛教在汉地的融入与弘传。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稳步发展,佛教徒也希望寺院建筑能够体现出佛教的文化特征。这种意愿从一些石窟的经变画中可管窥一二。在敦煌莫高窟第八五窟南壁的“西方净土变”和第九窟南壁上的“王舍城”等大型经变画中,佛教寺院无不华光流溢、庄严殊胜,体现出一种对佛国圣地的追慕与向往。当然,经变画中的建筑毕竟不同于真正的建造实践,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也有僧人试图实现这种愿望。如目前已经消失了的明州延庆寺十六观堂。据宋人陈瓘的《延庆寺净土院记》、清哲的《延庆重修净土院记》等文献记载,十六观堂于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建成,历时七年,至泰定甲子(公元1324年)遭遇火灾后废弃。十六观堂乃依比丘介然之构想所建,“构屋六十余间,中建宝阁,立丈六弥陀之身,夹以观音、势至。环为十有六室,室各两间:外列三圣之像,内为禅观之所。殿临池水,水生莲华。不离染尘之中,豁开世外之境。念处狙寂,了无异缘,以坚决定之心,以显安乐之土”。[7]即延庆寺十六观堂共有十六间房,每间分内外两室,围合成一个圆形院落,院落中央设有宝阁,阁内供奉有三尊佛像。院落外围设水池,池内遍布莲花。这一寺庙建筑的布局与形态较为特殊,却清晰地反映出建造者试图对《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中十六种观门加以表现的意图。从经变画和到十六观堂可以看出,汉地佛教徒无论从理想到现实层面,对能够体现佛教文化内涵的寺庙建筑始终不乏期待。但从实施的角度看,却始终未能推广开来——无论是典籍记载,还是现存实物,都极少发现类似十六观堂的汉地佛教建筑。这一现象与佛教长期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佛教自东传汉地之初,一开始便处于政治上依附于权力阶层,在经济上则依赖信徒供养。在其后一千余年的中土传播历史中,佛教虽几经兴衰,但并未摆脱这种从属和依附的状态,其枯荣盛衰始终取决于世俗社会的权力阶层和供养者。从经济上看,建造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社会资源的分配结果;从政治上看,在中国传统社会,建筑一直是高度反映统治者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佛教徒看似寺院建筑的拥有者,但事实上,隐藏于其后的权力阶层和供养者才具有真正的主导权。建筑空间的形态及其意义无疑取决于其拥有者的观念,并在空间实践中加以体现。因此,在寺院建筑的建造上,僧众在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太多自主权。正是这些世俗社会的隐形拥有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佛教建筑的建造结果。这是导致汉传佛教建筑难以形成独特建筑形态的又一重要社会因素。 在汉传佛教建筑本土化的复杂内因中,建筑的材料技术因素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考察环节。从“上古穴居”到“构木为巢”,中国传统建筑逐渐完成了自身在材料、技术等方面的选择和积累,形成独特的木构建筑体系。正如梁思成所言,这一建筑体系“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条件……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式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8]它是与中国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断磨合并最终与之高度契合的结果,因此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合理性。当印度佛教传入汉地之时,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体系已日趋完善,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种主要结构系统已经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9]在空间的灵活性、防风抗震以及拆建便利等方面均具备卓越之优点。而印度伽蓝主要采用南亚次大陆上所衍生的石构及砖石构造体系,其产生的地理及环境条件与中国相差甚大。佛教进入中土后,这一体系既存在适应性问题,亦无优势可言,自然难有沿用甚至推广的可能性。因此,寺庙建造很快便采用了汉地建筑的材料、技艺和构造体系。在这一情形下,汉传佛教建筑固然已失去其印度伽蓝原型在营建上的土壤和条件,自然也难以创造出迥异于汉地世俗建筑的独特类型。 ①竹林精舍,梵语Kalandaka,又译迦兰陀竹园,位于古代中印度摩伽陀国迦兰陀村。关于竹林精舍的建造者有两种观点。一是由摩伽陀国频婆沙罗国王所建,见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50)//大正藏(第22册),第936页下;二是由长者迦兰陀所建。见[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M].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734。本文采用第一种观点。 ②佛教寺庙在印度称为“僧伽蓝摩”,梵语Sangharama,意为僧众居住的园林,至中国后简译为“伽蓝”。参考丁福宝.佛学大辞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472 ③麦积山石窟第4窟为北周时期所建,是现存最大的仿建筑样式洞窟,再现了南北朝后期佛殿的形貌。参见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考古研究室.麦积山石窟第4窟庑殿顶上方悬崖建筑遗迹新发现[J].文物,2008(9) ④天龙山石窟第16窟为东魏时期首次开凿,北齐时窟前增建仿木结构前廊,是北齐遗留至今的唯一建筑实例。参见李裕群.天龙山石窟调查报告[J].文物,1991(1) ⑤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0(1);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J].唐研究,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