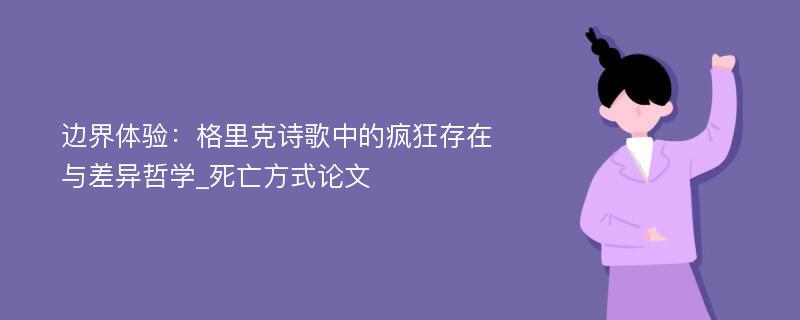
界限经验:格里克诗歌的疯癫在场与差异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界限论文,诗歌论文,差异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你想到这墙,你不会想到监狱。/更相反——你会想到所逃避的一切,存在于斯”(Glück 55),①这是美国当代诗人路易斯·格里克“橄榄树”(“Olive Trees”)中的诗句,她对“墙”的反思诗化了界限存在的场域、僭越界限的可能以及界限经验的生存论意义。在“存在于斯”的界限经验里,格里克采纳了福柯式的哲学姿态——“思考其所不思考的东西”(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 323)。界限之于格里克,与其说是实存毋宁说是阙如,它的显现倚赖越界行为的发生并因后者的强度差异而可能出现边界的移动。越界具有事件质地,其意义如福柯所描述的,“质疑缺乏实证的源头和冷落否定的开局。它不寻求以一事物对立于另一事物,也不通过揶揄、歪曲或掀翻基础而成就自身。它不对界限实施伦理的暴力也不对界限进行革命的征服”(Foulcault,Language 35)。 越界是以与主体自由相关的特殊方式对知识形式的界限所进行的批判实践,是以模糊的方式确认自由与无限的事件(Wolfreys 99)。福柯在“何谓启蒙?”中指出,对界限批判的重点“要从有必要限制的形式转化成有可能越界的形式”(Foulcault,Ethics 315),这就需要关注界限的裂隙、断面和门槛以及处于其间的理性的另一面——疯癫之于诗歌审美和生存哲学的意义。在福柯理论的烛照下,格里克的界限区域成为逃遁同一与戳记差异的经验场所,而其界限经验是抵抗理性宰制、化解存在焦虑的美学反应。通过利用他者之镜反观人类并借助“黑暗”和“泥土”等否定路径“生成动物”,格里克追求着理性与疯癫、同一与差异的混沌存在。本文基于福柯的界限理论,以生存论视角观察格里克的晚近诗集《乡村生活》(A Village Life),研究其界限经验中的疯癫在场与差异哲学,并借以洞见福柯式的疯癫生存美学。 一、界限经验的疯癫在场 格里克的界限经验发生于福柯最为关切的“A”与“B”对子(the Double)间的场域。福柯认为,在撤离和回返、思考与未思、经验与超验以及属于实在秩序之物和属于基础秩序之物等对子之间,可以发现它们辩证的相互作用和没有形而上学的本体意义,因为现代思想不再趋向“从未完成的”(never-completed)差异的形成,而是趋于“就要实现的”(ever-to-be-accomplished)同一的揭露,并且这种揭露只有在对子和裂隙同时显现时才能完成。裂隙居于对子之间,虽微小却不屈不挠(Foulcault,The Order of Things 340)。同样,格里克认为中间地带“不是对极端的妥协,它是变化不居的”(Longenbach 136),因此潜藏着无限的审美可能。界限区域是格里克消弭理性与疯癫断裂的场所,在那里,她可以为劳作者的诗意栖居抒情,为弱势者的轻贱存在正名,为卑微者的消极抵抗言说。通过诗化界限经验中疯癫在场的生存论意义,格里克构建出福柯式的当代疯癫生存美学。 诗集《乡村生活》的开篇之作“暮色”(“Twilight”),书写了“他”在一天的劳作后静坐于窗前,体味暮色中的世界所带来的欢愉。“他”看到“季节变换,……/绿色的东西后面跟着金黄的又跟着白色的——/强烈的愉悦来自抽象的概念,/像来自桌上的无花果”(3)。诗歌以“暮色”题名,将诗歌经验的场地置于界限。以审美发生学观之,暮色是人的知觉进行调节的时段(以听觉的敏锐取代视觉的式微,而后进入幻觉或内省),是人对景物的直观感觉和理性沉思的约合之所(Miller 9)。因此,暮色这一昼夜交汇的模糊时域能够恰切地表征理性主义的基础——理性与感官截然对立的消解(Nesme 206)。在暮色界域内,格里克首先将视觉发现(颜色变化)转换为理性思考(季节变换),但随即搭建起抽象(作为概念的颜色)与具象(无花果)之间的心理连续性,即理性与感官的审美交融,这似乎暗合了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中的“我们”,在同样的暮色下“欣喜于非理性的东西是理性的”(Stevens 351)。然而,“暮色”中感官的愉悦并未滞留,诗歌戛然止于“我放走一切,而后燃起蜡烛”(3)。燃烛何为?史蒂文斯在《内心情人的最后独自》中曾写道:“点燃暮色里的第一束光,就像在一处居室/在那里我们歇息,以微末的理性,认为/被想象的世界是终极的善”(Stevens 444)。诗人通过非理性的想象实现着对世界至善的可能性的揭示,而这种审美意趣似乎也在指引着格里克,令其以“暮色”开启了对理性与感觉断裂问题的思索与修补。 如果说“暮色”所关注的是界限经验中感性与理性同时在场的审美反应,那么“拂晓”(“Dawn”)则指向界限经验中的词与物——书写与实在对应缺席的生存论意义。在《事物的秩序》中,福柯分析了话语与现代人之存在的关联:在经验层上,任何在事物与语词关系维度中发挥作用的东西都已经被拽回到语言内部并被赋予向语言提供其内部合法性的任务。在基础层里,话语分析要从其深陷的符号域中解放出来并在外域中发挥作用,因为人在那里显现为一种有限的和被确定了的存在,受限于其未曾思考的事物里并在其真实的存在中受制于时间的离散(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 337-8)。以此观照“拂晓”的第一节,可窥见格里克之福柯式的语言哲学: 孩子在漆黑的房间里醒来 叫喊着我要我的鸭子回来,我要我的鸭子回来 叫喊的语言没人懂得分毫—— 根本没有鸭子。 但是这狗,通体长着白白的长毛绒—— 就在挨着他的畜栏中。(17) 梦境中的鸭子在与境域分离后便失去了所指,其针对的是理性主义之现象与本质分离的理性主义语言观。漆黑房间里的孩子是康德意义上的“未成年人”,其所叫喊的鸭子因为没有实在对应物而可被判定为不可理解(非理性)的谵语。然而,孩子谵语中的“理性”可以通过福柯的话语理论断出:尽管能指鸭子没有经验所指,但因为狗的存在及其与人的关系,鸭子与“他”便以狗为介质而发生关联。狗所提供给诗歌话语的合法性在于,它因“通体长着白白的长毛绒”而与鸭子相似,又因被关进畜栏而获得与“他”的“社会”秩序伦理意义。福柯话语理论所指的“外域”就是语言境遇,它制约了人的知(某事在发生)与不知(什么在发生以及它如何发生)。失去了语境的能指,其所指(意义)便有了无限开放的可能,“一切都在梦中。但是这鸭子——/没人知道那都发生了什么”(17)。 “拂晓”的第二节描写了光线对(发生了性爱行为的)“他们”的介入:“或是为了叫醒他们,要确保他们知道/记忆中夜里发生的确有其事,/现在光线需要进入房间”(17)。在格里克的诗歌里,光线(太阳)等同于理性,譬如《田园牧歌》(“Pastoral”)中的“太阳喷薄而出,/像理性击溃蠢念”(4)。通过略去谓词而只保留分词,格里克有效地将性爱行为的事件叙述转换成它的语境描述:“也为了让他们看看这事发生的境遇:/袜子半掖在肮脏的床垫下,/被子装饰着绿叶——”(17)。以描述语境而切近事件本身,这是福柯新历史主义的基要之一,也是格里克在夜与昼交汇的“拂晓”界域构造性爱话语的策略: 光线明示了 这些东西而不是其他。 设定了边界,确切而不含糊, 之后便逗留起来,描写 每一样东西,不放过细节, 挑剔地,像用英语写文章, 甚至包括床单上小小的血渍——(17-18) 光线作为符号,其作用首先是分界,它“指示、标注,像箭头一样指引着凝视的目光”(Bal 67)。就“拂晓”而言,光线划定了某些东西的确切边界,如同理性设定了明晰的概念范畴并且强制其界限内的每个细节都按步就里。格里克以英语书写为隐喻,以其要求具备一个统摄性的主题以及紧密支持主题的细节来完成书写的规约,喻指理性要求核心以及维护核心的法度。然而,就像书写的撒播会延宕主旨的实现并会使文本的疆界发生移动,光线也会在逗留中消耗强度而失去对核心的坚守。小小的血渍可以直面光线的凝视,而“浆果在最外层的下面发了霉”则暗示小小的霉菌可以使整个浆果溃不成体。不仅如此,《拂晓》以“仿佛太阳一时蒙蔽了你”(18)作结,意在揭露(如太阳般的)理性也是事物之间所谓的荒谬、无根基和怪诞联系(“蒙蔽了你”)的始作俑者。 “燃烧树叶”(“Burning Leaves”)通过对枯叶燃烧之烈火和余火的描写,诗性地诠释了理性对欲望的决然镇压以及欲望通过越界行为绽放生命活力和追求特异存在的过程。在康德那里,越界意味着破坏,是违反法律或践踏、僭越那些由社会、机构或习俗规定的边界的行为。康德意下的界限是僵死的,将理性拘谨地圈定在界限之内并拒绝非理性的介入(杨凯麟73)。但福柯认为,没有界限不可越出,越界缘起于问题情境并且具有“使动”的事件特性,界限经验引起变化的发生,其中非理性参与了问题的解决。格里克如此描写枯叶燃烧的形态和性态:之于烈火,石围已不成其为界限,因为“火燃烧着升入晴空,/急切而暴戾/……/——火是/渴求的、贪婪的,/拒绝被控制、接受限制”。相反,残余的火花在垒石内明暗闪烁,成为特异而隐晦的存在:“石头垒起的同心圆和灰色的泥土/圈住星星火花:/农夫穿着靴子在上面踩踏。/……那些残余的火花/仍在抵抗,仍未燃尽,/……/因为它们显然未被击败,/只是蛰伏或稍息,尽管没人知道/它们表征的是生还是死”(35)。如果将石围当作死亡的界限,“燃烧树叶”中的烈火和余火则分别隐喻人在少壮期和暮年时的欲望。这里,格里克或许想起了希腊古典时代的情歌诗人,他们渐渐老去,却选择作为火焰而生活在诗句里:“在我饥饿的心中,余烬仍在燃烧”、“如果我们一定得死,那就让我们跳着舞死去”(伯特曼69-70)。野性之火在老之将近时变为星星火花,尽管被垒石控制(同心圆意指向理性靠拢的绝对秩序)、被农夫(衰老或死亡的意识)踩踏,它们却“向上、向侧面”(35),在石围的界限内竭力舞动。余火的疯癫存在及其后果——“只是蛰伏或稍息”,构成了格里克“燃烧树叶”诗歌抒情的核心。 不仅仅是从界限内部思考疯癫的特异功能,格里克还刻意以“生成他者”的构思恢复疯癫之于生存的地位,并借以他者之镜反照理性之缺而不是通过理性之镜挑剔他者之短。“蚯蚓”(“Earthworm”)中的蚯蚓对凡俗说:“面对死亡,/你们却不愿深入掘土/……/我们可以断成两截,但你们却/在核心处毁损,你们的理性/与感觉脱离——/约束不会蒙蔽/像我们这样的有机体”(20)。康德的理性主义将人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理性,它是人类共有的东西,是人的核心能力、核心的自我,而另一部分是感官经验和欲望,它是盲目的、偶然的和特异的印象,是理性所极力排斥的东西。然而,理性与感觉截然对立的后果是对中间力量的忽视,因为它强调了冲突而忽视了团结(Rorty 32-33)。作为有机体,蚯蚓以身体与环境间的互动为存在之本,这反照出人类在理性钳制下的那种对“时过境迁”的恐惧。理性主义与当下语境相分离,因此当它遭遇历史条件的转变时就会在基础处被打断,而对致命的断裂能进行的补救只有折回当下场所,完全浸入此地此时: 一旦你进入土里,你就不会害怕土; 一旦你居住在恐惧里, 死亡似乎就成了渠道抑或隧道之网,像/ 海绵的或蜂箱的,这些,作为我们当中的一分子, 你们将会自由地探索。或许 你们将会在穿越中发现 一种曾经逃离你们的完整性——作为男人和女人 你们不曾自由地 注意到你们的身体中任何曾经 在你们的灵魂上留下印迹的东西。(20) 面对理性主义制造的死亡恐慌,蚯蚓诱使人类越界,进入渠道或隧道之网——那些像海绵或蜂箱的界域。网状区域类似迷宫路径,而迷宫是一个连接生与死的中间地带,它有能力化解向死而生的单向性,成为死亡和重生的链条,因此,迷宫作为概念含有安慰性和实用性的生死观(佩尔尼奥拉68)。在格里克看来,恐惧会促成疯癫的行为——类似穿越迷宫的晕眩运作。晕眩是一种暂时毁坏辨识力的努力,它会给平时清醒的头脑造成极度的恐慌。在眩晕过程中,主体会感觉到其与自身和与世界关系的改变,故晕眩具有使形式模糊和反偶像崇拜的意味(佩尔尼奥拉2l0)。理性主义将灵魂与身体对立,将身体视为灵魂的他者而追求消除一切感觉以及男女身体差异的理性同一。然而,在迷宫这个模糊界域所发生的晕眩运作,会使眩晕主体暂时甩掉理性的桎梏,重新获得自身感觉与知觉合一的完整,并通过身体感觉进而发现自身与他者的差异联系。 二、界限经验的差异哲学 理性主义赖以维系的“二元论”设定了内场与外域、单数与复数、积极与消极和相同与差异等对立项及其秩序,其中的前项被赋予了核心地位,而后项总是被视为需要肃清的东西。格里克却不以为然——她的诗歌给予遭受传统哲学贬损的东西以特别关注,并通过界限经验将它们带入与人的存在模式的关联之中,在生存论意义上呼应了福柯的差异哲学。福柯将人的存在模式定义为“实在之物与有限性的联系、经验与超验的重叠、知识与未知的永恒关系以及对本原的撤离与回归”(Foulcault,Language 36)等。他指出,越界是对知识和其本原界限区分的确认而这种区分指示着差异的存在。“差异不蛰居于任何中心,而是存活于边界,是对既有疆界的不断跨越”(杨凯麟77)。之于格里克,越界是对知识之为自由意志以及身体之为历史隐喻的注记,而渗入其间的是关于记忆逃遁、死亡模拟与自我褶曲等的生存美学。 与诗集同名的诗歌“乡村生活”(“A Village Life”)的首节道:“死亡与无常等候我/像等候所有人一样,幽灵估量着我/它可以慢悠悠地毁掉一个人,/悬念要素/需要被保守——”(69)。面对死亡与无常的危机,“她(村民)相信圣母的方式与我相信大山的方式一样,/……/每个人都将希望贮藏于不同的地方”(70)。格里克对“山”的崇高感有反康德理性和反宗教的双重意涵。格里克凭直觉和情感在“山”上捕获到了一种信念,就像人们相信月亮:“月亮悬挂于大地之上,/……/它是死物,从来都是,/可却装作是别的什么,/燃烧如星辰,那样令人信服,以致你有时会感到/它可能真的让东西在大地上生长起来”(70-71)。这种信念是福柯所说的知识的意志,因为“知识是一种‘虚构’,一种直觉、冲动、恐惧、欲望以及占用的意志之间的相互作用”(Foucault,Ethics 14);它也是济慈所言的“否定感知力”,因为月亮燃烧如星辰的幻象以及月亮使大地作物生长的非理性直觉被纳入到认识论的范畴——“如果灵魂有意象,我想那就是这个样子”(71)。 在《通向无限的语言》中,福柯论述了“为不会死去而言说”的命题:“死亡将至——它颐指气使的姿态和在记忆中的凸起——在在场和存在中掘出裂隙,而我们的言说就从那里开始并返回到那里”(Foucault,Language 53)。对格里克而言,这个裂隙存在于身体在场与死亡意识之间,且由“漫步”提供其发生的场域。在《乡村生活》中,“每次漫步回来我都记着些形象:/香蜂花开在路旁;早春,狗追逐着灰突突的小老鼠,/于是就有那么一刻似乎可能/不再去想对身体的把控在衰萎,/身体与空间的比例在变动”(69)。作为界限经验的“漫步仪式”使“我”获得“齐物”的立场,不再受制于生死的线性暴戾而能够领受并超然于黑暗:“我在黑暗中穿行宛若它是自然的事情,/宛若我已成为黑暗的要素。/静谧无风,天已破晓”(71)。不仅如此,格里克的“漫步仪式”也使处于时间凝视下的身体成为记录历史的文本。“深夜漫步”(“Walking at Night”)中的女人说,“当你看见某个身体你就看见了某段历史。/一旦那个身体不再可见,/它努力讲述的故事便陷入空茫——”(28),女人的身体成为福柯所指的“被刻写的事件的表面(它因语言留痕而被概念消解)、容纳分裂的自我的场所(尽管采纳了实在统一的幻象)以及一个连续解体的书卷”(Foucault,Language 148)。 如同《乡村生活》中的“漫步仪式”,“三月”(“March”)中的“海浪仪式”也提供了应对生命中记忆凸起的可能。“三月”中的差异哲学可被纳入福柯谱系学的历史观内进行考察。谱系学的历史观就柏拉图所指的将历史作为回忆或确认的主题、将历史作为连续性和传统的代理人以及将历史作为知识等三种历史形态做出反应,提出了对实在进行讽拟、对同一进行分解以及对真理进行亏蚀方式的使用等策略(Foucault,Language 160)。“三月”中的大地和大海分别成为传统史学和谱系史学的隐喻。“太阳照射大地,大地繁荣兴旺。/每个冬天,岩石都好像在地下长得/越来越高而大地变得坚硬,冷漠和排他”(36)。褪去繁华后的大地拒绝他者的加入,维护着同一的尊严。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假象,因为明喻修辞“好像”内含“像而不是”的差异。相反,作为大地的解构者,大海不提供连续的同一,亦不固执于过往的记忆,海浪在重复中抹去历史: ……海水拍岸,每次海浪留下的痕迹 都被下一次的抹去。 从不累积,没有一次海浪设法叠加在另一个之上, 从不许诺庇护—— 大海不像大地那样变化; 它不制造假象。 若你问大海能答应你什么 它会说出真相;它说抹去。(37) “重复从来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历史条件,在它之下新事物被有效地制造”(Deleuze 90),德勒兹曾如是说。海浪的重复是认识历史真相的条件,大海不像大地那样会制造持续增高的假象,而是处在永不停歇的差异运动中。“运动,就其各个部分而言,暗示中心的多元、视角的叠加、视点的纠缠,是在本质上扭曲符号表征的诸时刻的同时存在”(56),因而在运动中捕捉任何稳定的中心(同一的本原)都是不可能的。在重复的条件下,抹去记忆成为大海的许诺,其结果是在貌似相同的运动中自由感受生命的能力被有效地唤出。“三月”的末节说:“没有什么可以被强迫生存。/大地现在就像致幻剂,像来自遥远的声音,/一个恋人或主人。最后,你做那声音告诉你做的事情。/它说忘记,你就忘记。/它说再次开始,你就再次开始”(38)。格里克将大海的差异哲学最终转化为人在大地的生存美学:大地成为包容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爱”的创造力(恋人)或可能实施规训与惩罚的等级压迫力(主人)之差异力量的存在。大地作为致幻剂使“你”产生“离身”体验,它通过言说的方式成为“你”的上帝,赋予“你”生命的自由——忘记“前世”或再次开始“今生”的自由。 不仅仅关乎个人历史,“三月”还暗指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一书结尾处对人之有限性的深刻洞见:“人将会被抹去,就像画在海滩上的那张脸”(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 387)。在福柯看来,“人的显现只是在人文知识内部的新近发明,是知识在基础性布置中发生变化的结果”(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 386-87)。现代知识在冷落了统一性、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同时,也就抛弃了历史进化的必然性,历史并不是命定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必然进化,历史本身是具体的,它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张法119)。历史如海浪拍岸的重复事件,海浪运动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事件的情节无法以因果论而只能以概率论预测其结局。将历史作可能性和偶然性的理解是对柏拉图之同一律和真理观的叛离,但这种理解却向人之存在的有限性更逼近了一步。 格里克的差异哲学在“三月”中关乎到历史的谱系性,而她的两首“蝙蝠”(“Bats”)切中了人类以视觉理性排斥疯癫的问题。阿奎那认为,“人通过感官,主要是通过更为敏锐、更能洞烛事物差别的视觉,自由地环顾天上地下他周围的感觉对象,而从万物之中获取理性知识”(转引自陆扬,《死亡美学》3)。但人“囚禁在眼睛中,/……/为了给光线让位/人的眼睛将神秘的东西关闭在外——”(63)。然而,蝙蝠却在被哲学家们称为否定路径的黑暗世界里“培养出/强烈的意识”(34),它对人类说道: ……仰望夜空: 如果经由感官的精神错乱是生命的本质 现在你们所见的看起来就是对死亡的模拟,蝙蝠 在黑暗中盘旋——但人类所知的 根本不是死亡。如果我们的行为方式是你的感觉方式, 这不是死的样子,这是生的样子。(63) 蝙蝠在黑暗中的盘旋是在完成生命中创造性的模拟。死亡是不可见的真实,但蝙蝠却凭借黑暗中疯癫式的盘旋令其秘密变得可见,并使死亡成为对生命的抒情。生命与死亡的辩证是福柯死亡概念的核心。透过对死亡的凝视,生命被赋予“真理”的风格并如同一件作品,但这件由无数微小死亡所铭刻的作品却同时必然是作品的阙如,因为死亡的实现永远在生命之外(杨凯麟166)。死亡应如福柯所描述的,不再是生命的对立和破坏,而是构成生命最独特也最殊异的核心(杨凯麟163)。蝙蝠的每次盘旋都是对充满差异的微小死亡的重复,而生存的意义与特权恰偶居在那里。秉承福柯,德勒兹认为生命本身就是幻象,没有原初只有变化或复制的不同版本。幻象以行动生产新的自我和原初,使生命呈现出不同于其所是的形式、想象或投射自己尚不是的样子。幻象的伦理意义在于对没有根基的变异的确认,对没有标地或外部因由的差异重复的确认(Colebrook 97-102)。如果生命即幻象,那么格里克的《蝙蝠》实际上就是人类得以诗意生存的生命寓言。 蝙蝠通过暗夜盘旋的界限经验释放出超越同一的生命,“在咖啡馆”(“In the Café”)的“他”通过自我褶曲昭告了特立独行的存在。福柯在谈到尼采对哲学的态度时说,“他好就好在能够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由此使哲学和非哲学话语之间的边界可以互相渗透,并终而变得滑稽可笑”(转引自陆扬,《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230)。如出一辙,《在咖啡馆》中的“他”以尼采对待哲学的方式,将自我知识布置在与不同女人交往的游戏中:“与每个女人同居时,他都进入每个自己表演的角色,/充分地,因为它不受常规的羞耻和焦虑所折损”(13)。然而,为了趋向自我知识的完备,“他”需要跳出,“……他想面对面,/与他长久了解的人倾谈”(14)。如此,“他已在新生的边缘。/……/即便是日落时分,对他而言/太阳正重新升起,大地蒙黎明之光照耀/泛着不持固的玫瑰红”(15)。“他”的自我新知发生在对自我的外部寻觅又向自我折返的褶曲里,诗意地隐含在“日落”(昼夜交替)和“黎明”(夜昼更迭)的界限经验中: 在这些时刻他成为自己而不是 与之同床的女人的片断。他进入她们的生活就像你进入梦境, 不由自主,他活在那里如同你活在梦中, 不管持续多久。到了早上,你根本 不记得所梦,一点儿都不。(15) 这里,同一与差异的关系可见一斑。“他”的同一由复数的差异(各种奇遇和发现)所构成,而“他”的完整由复数的断片所拼凑。因为“他”那“站在他的生命之外,仔细观之”(14)的生存方式殊异于众,所以“我们变得酸朽而他依然如故,/充满奇遇,总是制造新的发现”(13)。但这一切都在意识(醒来)与无意识(梦去)的边界处归于荒诞和虚无——“到了早上,你根本/不记得所梦,一点儿都不”(15)。 《乡村生活》是格里克以界限存在为本体并以界限经验为基础,诠释理性与疯癫、同一与差异关系的哲理诗集。诗集撷取了暮色、正午、日落、黎明、日出、三月、仲夏等时间界限意象,以及牧场、树林、河岸、桥头、麦地、海岸、十字路口、道路、围墙、咖啡馆、广场等自然和社会空间界限意象,这些具有本体意义的时空意象为格里克提供了诗歌审美的种种可能。疯癫和差异所应该获得的哲学合法性,允许格里克像福柯那样“找到一个比人类自身更伟大的存在方式,回到理性与非理性都浑然一体的状态”(博伊恩50),抑或索性以“生成他者”(蚯蚓和蝙蝠等动物)的方式,在否定路径上寻觅人之存在的依据、形式和内容。 注释: ①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Louise Glück,A Village Lif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