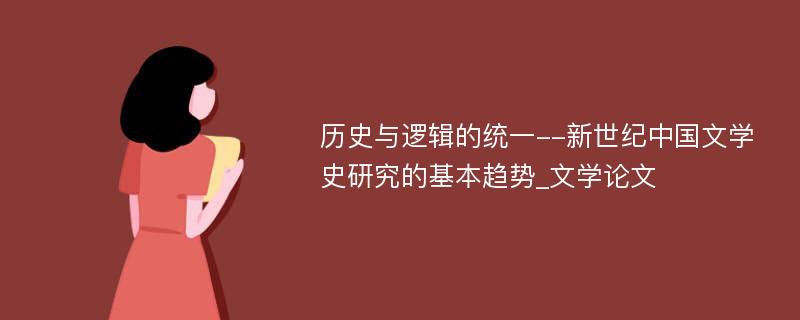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逻辑论文,走向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三种倾向:文化心理、历史逻辑和语言意象。就性质而言,文化心理和语言意象两种研究倾向主要属于研究内容方面的拓宽与深化,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文学为中心指向“外部”世界的研究,后者是从“外部”世界指向文学“内部”的研究。而历史逻辑的研究倾向则主要属于研究方法方面的转换。笔者以为,文学史研究革新质的突破点在于历史观、哲学观的更新,亦即思维方式的更新;未来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在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新思路。
关键词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文学史研究 基本走向 倾向
从1904年林传甲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问世迄今,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历程已沿续了近一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思想意识闸门的开启、“重写文学史”热潮的涌动,中国文学史研究革新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于是,这种革新的未来走向问题,便成了本世纪末文学界,特别是古代文学界,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我们看来,文学史研究革新质的突破点在于历史观、哲学观的更新,亦即思维方式的更新;未来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在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新思路。
一
有论者认为,本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三种倾向:文化心理、历史逻辑和语言意象。〔1〕就性质而言, 文化心理和语言意象两种研究倾向主要属于研究内容方面的拓宽与深化,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文学为中心指向“外部”世界的研究,后者从“外部”世界指向文学“内部”的研究。而历史逻辑(即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倾向则主要属于研究方法方面的转换。在中国当前古代文学史研究的状况下,方法的转换更具有深远的历史革新意义。
从文化或心理角度切入文学史的做法,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2〕前一句话强调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后一句话的意思可以用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的说法解喻:“文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3〕至于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怨”说(王化政教),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以及由荀子开启的“文以载道”说,亦可以视为广义的文化批评。不过中国古代文人“陋于知人心”罢了。
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文化”一词的涵义是十分丰富的,它涉及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说文学史是文化史,实际上已经包括了通常所说的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各种文学史研究方法。我国学术界用“文化心理”一词来概括某种研究倾向,其用意是可以理解的:一是为了区别于单纯的社会学、心理学或历史学研究方法,二是为了强调文化学总体研究方法中的心理学分枝。这种研究倾向的实质,是为了丰富文学史研究的内容,把文学史研究从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这一点作为文学史研究内容方面的发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仅仅如此,则意义也就不大了。值得说明的是,王钟陵教授在《文学史新方法论》中所阐述的文化心理路径同勃兰兑斯的理论有深刻而重要的区别,同时下流行的做法也有显见的不同。例如从民族思维发展的角度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演变,就敏锐地抓住了文化——心理与文学史之间根本性的内在联系。
语言意象的文学史研究倾向实亦有其“本源”。中国古代的章句之学,是由字到句再到章以至篇的文本细读,它包含着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意象批评方法,只是在外在理论形态上有所不同。语言意象文学批评的近源应当是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文本细读原则而来的,其着眼点在文学的“内部研究”。用这种方法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是其长,而将之用于文学史的剖析则是其短。因此,用语言意象批评建构的文学史模式是不完整的,它只能揭示一些共时性的文学现象的意义,而无力于揭示一些历史性的文学史现象的本质。在实践中,这种批评方法并没能树立起成功的文学史典范著作。严格说来,语言意象批评只是与文学作品密切相关的理论,而不是与文学史相关的理论。要注意区别的是,新批评的语言意象分析方法与欧洲大陆所谓的“语言诗学”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探讨语言结构、功能、意义等的文论,后者是将语言视为“存在的家园”的文论,二者不相侔。
因此,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心理研究倾向虽然在文学史内容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并不具备革新的意义。语言意象研究倾向由于过份地关注文学的“内部”关系,因而成了一种封闭式的研究方法,从而失去了建构文学史模式的品格。当韦勒克、沃伦提出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性的“透视主义”文学史观时,他们其实已经超脱出新批评理论原则的樊篱(参见《文学理论》第十九章)。文化心理研究方法所建立的文学史与文化的关系是岛屿与海洋式的相互显隐关系:岛屿既突出于浩瀚的大海之上,又植根于深邃的大海之底;语言意象研究倾向所建立的则是冰山与海洋式的相互映衬关系:冰山漂浮于海面,却没有根基。比较起来,岛屿的前景显然是乐观于冰山。尽管如此,在实质上,两种倾向都是在进化论文学史观和实证方法基础上(如丹纳、勃兰兑斯那样),对文学史研究内容、范围方面进行加宽拓深的的一种“改良”,其路径在中外都是传统的,了无新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评价,这类文学史著作的增加是数量的增多,而不是质量的改变。关于此点,无须在此费舌去从我国近十年来涌现的一批文学史新著中一一指认了,相信有识者自能领会。
于是,在中国文学史学未来前景中,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倾向便格外令人瞩目了。
在这方面,王钟陵教授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先锋代表。他以其震憾整个文学界的《中国中古诗歌史》巨著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革新的道路上树起了一座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正如傅璇琮、钟元凯所评:“从学术上说,王钟陵的这本书表现了重建科学的文学史观的严肃企向和尝试。”“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一旦问世,一个新的参照座标就出现了,以往所有的成果都会在这个座标上或升或降地变换原先的位置。”〔4〕
科学的进步往往依赖于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崭新理论的产生。王钟陵先生关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文学史观,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揭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未来基本走向的(本文重心不是谈其实践成就)。
二
文学史是具有历史品格的学科,它既要求撰写者具备“观千剑而晓器”的卓越的文学审美能力,又要求拥有“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闳大的历史眼光。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王钟陵先生正是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上来创立其云外高瞩的文学史观的。
“历史真实的两重存在性”原理,是王钟陵教授贯彻其“(文学)史的研究就是理论的创造”之原则的重要支撑点之一。〔5〕在他看来,历史首先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之中,这是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是它的客观的、原初的存在。这种存在已经消失在历史那日益增厚的层累之中了。然而,书籍、文物以及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仍然留存着过去的印迹。真实的历史往往依赖于人们对这些存留的理解来复现,因此历史便又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它存在于人们的理解之中。
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两重存在不是指哲学最高范畴“存在与思维”的存在,而是作为一般“有”意义上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在使用“存在”概念时,在不同场合就具有着这两种用法。列宁说:“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但谈到意识时列宁又说:“说不论思想或物质都是‘现实的’,即存在着的,这是对的。”同时他也赞同狄慈根的一个观点:“精神和物质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是存在着的。”〔6〕如果从列宁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存在”含义去理解“两重存在性”,就不会产生“历史真实怎么会存在于人们理解之中”的疑问了,就不会执著于“存在就是物质”的片面提法了。
区分历史真实性具有两重存在性的意义在于端正对历史认识的态度。在认识过程中,客观的、原初的第一重存在是目标,主观的第二重存在是途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界只看到并执著于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没有认识到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是必须通过历史的第二重存在而被认识的,于是在研究工作中虚想出一个与任何认识主体都毫无关系的绝对客观的历史真实来,并极力排斥研究者的主观创造性。这是对历史真实的极大误解。另一方面,由于现象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解释学等西方思潮的东渐,我国一些学者又片面地强调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性,从而导致了另一种极端倾向的抬头。在主、客观,主、客体之间,仿佛悬着一根极其难走的钢丝绳。
历史真实的两重性存在原理,是一种消除主客观、主客体对立的历史哲学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历史的第一重存在要求对文学史作“原生态式的把握”,历史的第二重存在则要求对文学史作“逻辑”的把握。在研究阶段中,二者可以有所侧重,但在整个过程中,二者是不可偏废的,即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客观性是通过逐步接近而困难地达到的”。〔7〕所谓“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是一种从时、空、质上逼近历史第一重存在的具体方法。其主要内涵有三:(一)作为一种致知取向方式,它意在尽量浑泯主、客体之间的畛域。换句话说,它要求文学史家在撰述过程中,主体的心灵与客体的对象相互生成、相互浑融,达到“神与物游”的境界,而非“纯客观”的自我。(二)要求从复杂的时间,空间变化上去把握文学史巨系统运动发展的多样性、曲折性、无序性和随机性等等。(三)要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去把握文学史运动的具体环节和总体进程,即一方面要对材料作精细的爬梳、整理,作考古式、乾嘉朴学的发掘和复原,一方面把具体的材料进一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中归纳、提炼出逻辑的概念、范畴,进行辩证地批评。〔8〕
所谓逻辑的把握,是指侧重于历史存在的第二重的把握,是用“科学的逻辑结构”叙述文学史运动的方法。这一新思路旨在将原生态式的把握与科学的逻辑叙述结构结合起来,以臻历史感性与逻辑理性有机统一的高境。
这种统一性在于:一方面运用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命题对对象所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形式、发展进行辩证地叙述、整体性地考察;另一方面这些概念、范畴和命题的形成,是来自于对大量历史事实进行逐级抽象、高度概括的结果,而不是仅仅靠大脑作纯思辨推演的结果。换句话讲,统一是在“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以至“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9〕的两个过程中实现的。因此,这样的统一是由高度抽象而达到的云外高瞻的理论视点与丰富的流露着活泼泼生机的原生态感性具象有机结合的统一。
概念、范畴抽象、规定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然而也是易于理解的。关于此点,《中国中古诗歌史》已作了十分成功的演示,在此不用冗言。而抽象规定的具体再现的过程,则是更为艰难的,故极易遭人误解。这里试根据《文学新方法论》第四、第五章有关论述作些个人的理解说明。
王钟陵教授所主张的“新逻辑学”思路的建立,首先是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批判和吸取。肯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用辩证逻辑方法叙述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是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两大贡献。但是,由于黑格尔的整个学说是建立在“绝对理念”这一最高范畴基础上的,因而他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缺陷以至于致命的错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上,黑格尔视历史的发展为逻辑理念的显现,因而常常用先验的逻辑次序去剪裁历史;黑格尔的逻辑次序,是由一组矛盾沿着正、反、合一个单线方向,有着绝对目的地展开的,所以他的历史发展观具有螺旋式上升性、目的性、单线性的死板特征,忽视了历史发展的非永恒向上性,非绝对目的性、非单线性等特殊、偶然、随机的方面。王教授的新逻辑学则在充分肯定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又强调了历史矛盾的多组存在(而非一组),从而对黑格尔的逻辑次序作出了改造,得出了历史矛盾的辩证发展同时具有偶然性、随机性、无序性等特征,使逻辑符合于历史而不是象黑格尔的那种头足倒置。
其次,“新逻辑学”思路亦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方法中汲取了更多的营养,同时也注意将之发展成适应于历史领域研究的逻辑学方法。
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恩格斯曾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作过较为集中的阐述。他说:“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逻辑方法,不是单纯的历史、逻辑方法,而是指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两种方法:前者指从历史出发的统一,后者指从逻辑出发的统一。
然而,许多论者只看到了这段话里的从逻辑出发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却忽视了隐含在其中的从历史出发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更没有看到这两种方法的差别。从逻辑出发的统一,是共时性的统一,是将历史考察纳入共时性的逻辑分析模式中的统一。这种统一的重心所在正如恩格斯所说:“采用这种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象。”〔11〕这种统一的共时性在于,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12〕这是说范畴的安排是从逻辑结构出发的,而不是从历史顺序出发的。因此,列宁在谈“哲学上的‘圆圈’”时说:“人物的年表是否一定需要呢?不!”(《谈谈辩证法问题》)
从历史出发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一种历史性的统一,是按照历史历时性的先后顺序来展开逻辑结构的统一。上文说过,逻辑学的研究方法有两个过程:从完整的表象中蒸发出抽象的规定的过程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前者适用于任何一个研究对象。而后者作为叙述方法,则应该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比如探讨文学史中的某一现象,不妨采用将历时性考察化入共时性逻辑分析的研究方式;而要写一部纵向性的文学史著作,则应当采用从历史的先后次序来展开逻辑的研究方式。
从历史出发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研究方式,是王钟陵先生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过程中,受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启发而创立的新逻辑学思路。根据这一思路,不是逻辑显现为历史(如黑格尔所说),或历史验证了逻辑(如恩格斯所说),而是逻辑说明了历史,历史展现了逻辑。这一思路是以“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中所说的新历史发展观为基础的。它承认历史中具有逻辑结构,但否认这种逻辑结构的预成性、目的性、单线性;它要求从历史事物的内在矛盾性中寻求辩证逻辑的发展进程,但不是片面地强调矛盾的某一方面,因而它具有着时空并包并相互转化、必然与偶然相统一、多线性与随机性相交融的特征,具有着活泼泼的历史感性与睿智的逻辑理性交相辉映的光彩!
在西方学术史上,发源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康德、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开始接触到感性的内容。然而真正将逻辑形式与感性内容相结合的,当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现代逻辑实证主义虽以反对形而上学为鹄的,却走上了愈来愈纯思辨的道路,逻辑形式分析的对象萎缩得只剩下语言了。在传统形式逻辑中发展而来的数理逻辑、关系逻辑等,亦只剩下形式的空壳。从西方逻辑学发展的基本背景中,我们不难悟出王钟陵先生为什么要从“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学思路出发,来建立其“文学史新方法论”的原因了。
三
我们之所以认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式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基本方向,主要原因有二:它切合了中国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发展需要,切合了中华民族思维完善的发展需要。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
新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总体情况而言,目前一些文学史著作所采用的方法是历史的、艺术的分析方法。在中国悠久的史官文化和朴实的乾嘉治学传统的影响下,文学史著作会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史”。姜书阁先生《骈文史论》著述大意在于:“述二千年骈体文学之起源、发展与夫演变、衰亡之迹,并于历代各家各派之观点、主张及其创实绩,略以已意有所评论”(自《序》)、郭预衡先生说他在《中国散文史》一书中意在避开作品评论、赏析的角度,“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序言》)。这类文学史著作都高度重视材料的整理,注重对文体、流派、主题等史迹的勾勒,带有中国史书“实录”的传统色彩。近几年来,由于对庸俗社会学方法的厌弃,文学史著作开始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努力运用艺术审美的方法。曹道衡、沈玉成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亦意在将南北朝文学作为特定文化背景中一个组成部分看待,加强对作品审美价值的估价(《前言》)。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则想从士人心态的角度来揭示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但这类史著中的多数常常只是就作品而谈作品,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因而还不具备审美的品格。
历史与艺术分析(个别达到审美)的方法主要属于感性的叙述、判断、实证,在文学史学科发展上没有根本性的前进意义(如前文所说)。而与历史、审美相结合的逻辑学方式,在中外文学史研究领域甚至人文不科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先进性。
西方文学史著述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法国是中心”。20世纪迄今,“文学史研究在各国伴随着理论的活泼而发展”。〔14〕以丹纳、朗松、勃兰兑斯为代表的文学史及其著作,主要特征是把文学史作为文化史的一个部分或作为民族精神史来写,方法上与进化论、实证主义、心理学联系紧密。进入本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逐步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由民族文学史转向比较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出现向文学史内部掘深和向文学史外部范围拓宽的两大趋势。韦勒克、沃伦的“透视主义”文学史观认为要综合历史地把握文学史、要整体地考察变化中的文学历程,代表了“文学内部研究”的倾向。自50年代起苏联伊瓦肖娃著的多卷本《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鲍戈斯洛夫斯基的三卷本《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和80年代苏联集体编写的六卷本《苏联多民族文学史》和多卷本《世界文学史》等,都反映出总体史、比较史、世界史的“文学外部研究”(横向的)倾向。另外,被称为“文学史革命性文献”的尧斯的读者文学史观(文载《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中译本),则独树一帜。上述诸文学史观的发展其实都不出历史与艺术分析(或审美)两大范围,所不同的是研究方向、重心有所变化而已,虽然它们所依据的哲学观、美学各有不同。黑格尔天才地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引入了西方艺术史研究的领域,但遗憾的是,这种新的思路并没有引起西方文学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与西方现代哲学、文论(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走向分析、非理性的大趋势应有关。
中国文学史研究在经历了历史与艺术分析两大阶段的长期徘徊之后,终于由《中国中古诗歌史》开启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新方向。此后,陶尔夫、刘敬圻合著的《南宋文学史》也尝试运用逻辑的方法分析南宋词史的矛盾发展、变化。钱志熙认为文学史研究在审美、历史之上运有逻辑方法,作出“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还处于前逻辑方法”的阶段的结论。〔15〕不过他所说的逻辑方法是文学实现其自身本质过程的研究方法,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思路无缘。韩经太认为“没有新历史观与哲学观的自觉,就很难在文学史建构的思路上取得质的飞跃”〔16〕这种感悟是对的,但过于笼统了。在哲学界,我们有幸看到了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发展史》,不过冯先生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共时性的统一。客观地说,我们难以再例举出其他运用或要求运用逻辑学方法的论著、论文了。但是,学科前进的方向不是由数量决定的,而是由质量决定的。人人都习惯、熟悉的方法,决不是有发展前途的新方法。在中国,逻辑的运用是具有改变人文学科方法论意义的方法革命,而不是内容的“改良”(这不是不要内容)。
或许科学哲学的一些观点能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史学科需要逻辑学方法问题作深入思考。在一些科学哲学家看来,科学进步、知识增长的模式主要有三:一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赖欣巴哈的“静态积累”模式(参观《科学哲学的兴起》),二是批判理论主义者波普尔的“动态不断革命”模式(参见《科学发现的逻辑》),三是历史主义者库恩的“阶段革命和不断革命相结合”模式(也称“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交替”模式,参见《科学革命的结构》)。至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与退化竞争模式,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模式,夏皮尔的科学实在模式等等,都是前种图式的演变而已。比较而言,赖欣巴哈和波普尔注意到了科学发展的量变与质变、静态与动态的问题,但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还是库恩。库恩用“范式”的有、无和变化为标准来划分学科为“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是极富启发意义的。在我们看来,王钟陵教授用“历史真实的两重性存在”原理、“整体性”原则、“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和“历史性的历史与逻辑统一”思路等创立的“文学史新方法论”,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研究科学“范式”的诞生,预示着中国文学史学一场“革命”的到来。
虽然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多元的,但能在实践与理论上建立“范式”的,毕竟因为时代的限制而寥若晨星。某一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自然以有“范式”的研究方法为其前景,但它并不排斥多样化的尝试。中国文化目前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文学史学科是需要“阶段革命”还是“不断革命”(量变与质变),确是发人深省的。
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学史研究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为其未来的基本方向,决定于中西方民族思维特点和其发展趋势上的差异性、互补性。东、西方思维的特点一般被认为:西方属于抽象的、逻辑的、理性的类型,东方(以中、印为主)属于整体的、直觉的、经验的类型。这在前几年文化热的大讨论中已达成共识。但在考察东、西方以思维方式完善为基础的文化发展趋向时,人们常常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无逻辑、无语法这些基本特点当作我们的最大弱点和不足而力图加以克服的(文言文改造为白话,主要即是加强了汉语的逻辑功能),而与此同时,欧陆人文科学、哲学却恰恰在反向而行,把西方文化重逻辑、重语法的特点看作他们的最大束缚和弊端力图加以克服”的。〔17〕西方所谓“语言哲学”是一种弱化、消除语言逻辑功能的非形而上学、非逻辑的哲学,是一种以语言为其家园的哲学。这是本世纪以来席卷西方人文各学科的普遍思潮。其实思维方式的优劣、利弊都是相对而言的,西方的逻辑、抽象并非一定是理性主义的痼疾,东方的非理性的直觉亦不必是保护自己以至拯救西方文化的万应良药。透过东西文化反向而行的表象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向对方逆向转变的实质是思维方式自觉或不自觉的融合。思想的交流是一个重新理解的过程,具有增殖性,不象货币那样等值交换。换句话说,思想及思维方式一经交流就不再是自己的原来了,而往往是交流双方原来底色的调合、融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东西方思维具有互补性,双方通力合作将可以产生一种崭新的、更加广阔而同时又意识到自己局限性的理论,以及一种崭新的、建立在更牢靠基础上的直觉。从这样的背景来展望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便可以看到它在世界文化相互“整合”中朝逻辑、理性迈进的必然性了。
注释:
〔1〕《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漳州文学史观讨论纪要”
〔2〕《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3〕昂利·拜尔编《方法·批评及文学史》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4〕《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
〔5〕《中国中古诗歌史·前言》,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6〕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
〔7〕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8〕参见《文学史新方法论》第78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
〔9〕〔10〕〔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122、15、110页
〔13〕同上第1卷第10页
〔14〕杨洪承《文学史的沉思》第30—32页,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
〔15〕《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审美·历史·逻辑》
〔16〕《江海学刊》1994年第6期, 《关于文学史学问题的几点感言》
〔17〕甘阳《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中译本代序,三联书店1988年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艺术论文; 逻辑学论文; 文学遗产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