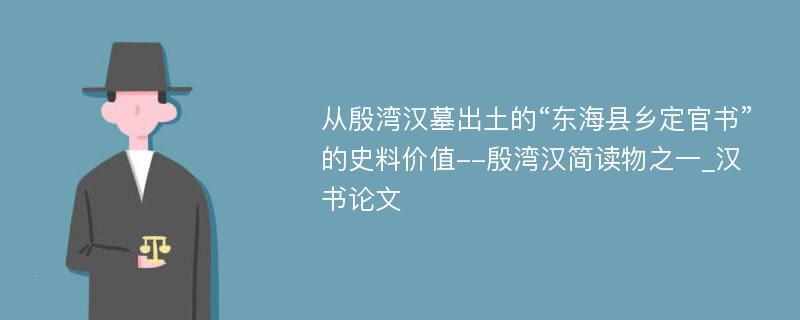
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海论文,汉墓论文,札记论文,史料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1993年出土于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汉墓中的简牍,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其中尤以“吏员定簿”简的史料价值最为突出。它不仅可以印证、补充和订正《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百官志》的有关记载,而且有助于认识汉代“亭”级机构的性质、“有秩”的“官”“乡”之分、县尉的左右之别以及汉代有无“官啬夫”等重要的官制问题,值得史学界重视。
关键词 尹湾汉简 吏员定簿 汉墓
1993年2—4月,在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掘了六座汉墓,其中六号墓与二号墓发现了汉简。六号墓出土木牍23枚、竹简133枚;二号墓出土木牍遣策1枚。仅六号墓出土的木牍与竹简,就有文字近四万个。其发掘情况,详见《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96年第8期。这批出土简牍,经连云港博物馆整理、缀合、释读并定名为《集簿》简(木牍1号)、《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简(木牍2号)、《长吏迁除簿》简(木牍3—4号)、《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简(木牍5号)、《六甲阴阳书》简(木牍9号)及《神鸟傅(赋)》简(竹简21枚),其释文已刊布于《文物》1996年第8期,题为《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尚有《永始四年武库兵器集簿》简(木牍6号)、《礼钱簿》简(木牍7—8号)、《历谱》简(木牍10—11号)、《遣策》简(木牍12、13、24号)、《谒》简(木牍11—23号,凡10枚)、《元延二年起居记》简(竹简56枚)、《行道吉凶》简(竹简18枚)、《刑德行时》简(竹简11枚)的释文未刊布。由于六号墓出土的木牍上有“永始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永始四年”及“元延元年三月十六日”等明确纪年,可以确认尹湾汉墓的建造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到王莽时期,因而这批出土简牍就成了研究这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等等的绝好材料。何况这批出土简牍的完整程度,实为简牍出土史上所罕见,从而更增加了它的史料价值。兹仅就阅读《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以下简称《定簿》)简牍后的感受,试论其史料价值,以求教于方家!
第一,《定簿》所列东海郡县名,可以印证、补充和纠正《汉书·地理志》关于东海郡的记载:
《定簿》列举了汉代东海郡的诸县名称,依次为海西、下邳、郯、兰陵、朐、襄贲、戚、费、即丘、厚丘、利成、况其、开阳、缯、司吾、平曲、临沂、曲阳、合乡、承、昌虑、兰旗、容丘、良成、南城、阴平、新阳、东安、平曲侯国、建陵、山乡、武阳、都平、郚乡、建乡、□□、建阳、都阳、伊吾盐官、北蒲盐官、郁州盐官、下邳铁官、朐铁官。共计43个县级建制的机构名称。其中县分大、小,按照汉制万户以上为大县设县令,万户以下为小县设县长的原则,海西、下邳、郯、兰陵、朐、襄贲、戚均设县令一人,尽管令有秩千石与秩六百石的区分,表明这些县均为万户以上的大县。自费县以下至昌虑县以前的诸县,均设县长一人,秩四百石至三百石,表明这些县为万户以下的小县。昌虑以下至都阳,均不设令或长,而设相一人代替令、长,秩四百石至三百石不等,表明这些县属于侯国。分别为大县7、小县13、侯国18、盐官3和铁官2,共计43个县级建制机构。由于朐县与况其为皇后、公主所食地,故曰邑,在同墓出土的《考绩簿》中有朐邑况其邑之名,故20个县亦可作县18、邑2,加上侯国18与盐铁官五,亦为43。以此同《汉书》卷28上《地理志》所载东海郡的情况比照,就不难发现其同与异。《地理志》谓东海郡辖“县三十八”,而盐官、铁官不在其内,《定簿》所列县级机构名称除去盐官3和铁官2,恰为38,可见《定簿》所载县数可以印证《汉书·地理志》所载东海郡的辖县数量。再以《地理志》所载东海郡的县名来说,除《定簿》之“南城”作“南成”、“况其”作“祝其”外,《定簿》多一“海西”和空缺一县名,《地理志》多“于乡”与“海曲”二县名,余悉同。这表明在县名方面,《定簿》与《地理志》绝大部分相同,只有极小的差异。我以为上述极小的差异,都应以《定簿》所载为正,理由如下:以《定簿》之“况其”县与“南城”县二名称来说,在同墓出土的《东海郡吏员考绩簿》中(以下简称《考绩簿》),也同样出现过,而且也分别作“况其”与“南城”,而不作“祝其”与“南成”,如果说《定簿》的书写者有误的话,不可能在《考绩簿》中也同样误抄此二字。因此,我疑如果不是《定簿》的释文有误,就是《汉书·地理志》的“祝其”与“南成”有误,二者必居其一。至于《定簿》之“海西”,在同墓出土的《考绩簿》中也作“海西”,不可能二处均误;且“海西”与“海曲”的“西”字与“曲”字,字型相似,因疑《汉书·地理志》实误“海西”为“海曲”。《定簿》之空缺县名,我想应为《汉书·地理志》中的“于乡”,且《考绩簿》中有“干乡丞吕迁九月十二日输钱都内”之语,“干乡”实为县名,其“干”字字形与“于”极似,无疑此“干乡”亦为“于乡”。如此,则《定簿》空缺的县名恰可补为“于乡”。最后,以《定簿》所载东海郡的三盐官与二铁官来说,《汉书·地理志》中只载下邳、朐二县有铁官,与《定簿》合,而缺载伊吾、北蒲与郁州三盐官,据滕昭宗同志在其《尹湾汉墓简牍概述》一文中(刊《文物》1996年第8期)的考证,郁州本为《水经注》中的“郁洲”,在海中,其盛产盐可以想见,故此三盐官为《地理志》所漏载。
第二,《定簿》所载东海郡辖县吏员的类别、名称与秩禄,可以印证、补充《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及《续汉书·百官志》的有关记载:
《定簿》载东海郡太守府的吏员时,谓郡设“太守一人,秩□二千石;太守丞一人,秩六百石;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九人,门兵佐一人,小府啬夫一人,凡二十七人。”又郡设“都尉一人,秩真二千石;都尉丞一人,秩六百石;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四人,门兵佐一人,凡十二人。”以此同《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及《续汉书·百官志》所载比较,则详略立现。《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续汉书·百官志》所载大体同此。观《定簿》所载郡设太守、太守丞及都尉、都尉丞的名称、数量与秩禄,均完全一致,可以印证《汉书》及《续汉书》所载不误。但太守、丞及都尉、丞之下的佐吏名称及数量,《汉书》及《续汉书》均不载,而《定簿》有卒史、属、书佐、门兵佐及小府啬夫之设置,且各有定数,明显可补二书之缺。
又《定簿》载东海郡所辖县之吏员,尽管每县吏员总数因县的大小不同而不同,但类皆有令或长一人、丞一人、尉二人或一人,其秩禄令秩千石至六百石,长秩四百石至三百石不等,丞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不等,尉秩四百石、二百石,这些情况同《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为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及《续汉书·百官志》“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等语,除县长秩禄略有差别外,其余悉同,可证《汉书》与《百官志》均不误。然而不同之处也不少:其一,《汉书》及《续汉书》均不载县之县尉有左、右之分,《定簿》载大县类皆设县尉二人,如兰陵县、郯县便是如此;在同墓出土的《东海郡吏员考绩簿》中,谓“兰陵右尉梁攀九月十二日输钱都内”和“郯右尉郑延年九月十三日输钱都内”及“郯左尉孙严九月廿一日送罚戍上谷”,表明郯县二尉中有左、右之分,兰陵县二尉中既有右尉,自然有左尉。可见汉代县尉之设,凡二人者必分左、右尉。其二,《汉书》与《续汉书》均不载县有不设县尉者,而《定簿》中却有不设县尉之县,如合乡、承、新阳、东安、建陵、山乡、武阳、都平、都乡、建乡、建阳、都阳及空缺之于乡诸县,均无县尉之设置。如谓是一时空缺未置,又不可能同时空缺 这么多县的县尉不置。其三,《续汉书·百官志》明言关于县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而《定簿》所载设县尉二人者虽然大部分为大县,但也有小县设县尉二人者。如临沂县、缯县、开阳县、司吾县、利成县、厚丘县、即丘县与费县等,均设县长而不设县令,知为小县,而这些小县均设县尉二人,与《后汉书》不合。所有这些相异之处,无疑也可补二书之漏载。
至于《定薄》所载县令、长、丞、尉之下的佐吏名称与数量,更可补《汉书》及《续汉书》之缺漏。关于县令、长、丞、尉之下的佐吏,《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只有“百石以下为斗食、佐吏之秩,是为少吏”一句,《续汉书·百官志》则连此句也没有。而《定簿》则载东海郡所属诸县令长之下的吏员甚详,计有“官有秩”、“乡有秩”、“令史”、“狱史”、“官啬夫”、“游徼”、“牢监”、“尉史”、“官佐”、“乡佐”、“亭长”、“邮佐”等名目。尽管按县的大小不同在各类吏员数量上有差异,有的县虽缺少“邮佐”、“官啬夫”及“官有秩”,但大体上各大小县包括侯国在内均有上述诸类佐吏。这无疑可补“百石以下斗食、佐史之秩”的诸少吏名目之漏。
又《定簿》所载东海郡所属各侯国,除均设有相、丞、尉各一人外,同样有“令史”、“狱史”、“乡啬夫”、“游徼”、“官啬夫”、“牢监”、“亭长”、“尉史”、“官佐”、“乡佐”之设置,更有“侯家丞一人,秩比三百石”,“仆”、“行人”、“大夫”各一人,“先马中庶子十四人”等侯国家臣。而《汉书·百官公卿表序》缺载侯国家臣之名目,《续汉书·百官志》只说:“每国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县。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也。但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候,使理家事。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凡五官。”以《定簿》核之,知侯国之家臣,除设家丞、行人、门大夫、洗马、庶子五官外,还设“仆”一人;且“洗马”作“先马”,“庶子”作“中庶子”,“先马”与“中庶子”合计为14人。如此,则《续汉书·百官志》关于侯国之家臣误“先马”为“洗马”与“中庶子”为“庶子”,漏载“仆”及先马、中庶子之定员数十四人。
第三,《定簿》所载东海郡诸属县吏员中的“官啬夫”一官,可补汉代史籍之缺漏: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云“县令长”下之吏员名称,只有“乡啬夫”一官,其职掌为“听讼、收赋税”;县级无“啬夫”之设置。《续汉书·百官志》亦云:“乡有秩、三老、游徼……”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意即小乡只设乡啬夫一人,而不设其他。可见县也无“啬夫”一官。散见于汉代其他史籍及《居延汉简》中的“啬夫”,也仅见“虎圈啬夫”(见《汉书·张释之传》)、“市啬夫”(见《汉书·何武传》)、“厩啬夫”(见《汉书·田广明传》)、“暴室啬夫”(见《汉书·外戚传上·孝宣许皇后传》)、“候门啬夫”(见《居延汉简释文》卷1)、“传食啬夫”(同上卷3)、“关啬夫”(见《居延汉简》甲乙编10、6)、“库啬夫”(同前90、41)等名目,却不见有“官啬夫”的名称。另外,散见于汉代的灯铭及其他器物铭文中的“啬夫”一名,也不能断定是否为“官啬夫”之省称。可是,在云梦出土的秦简中,却屡见“官啬夫”之名,而且可以判断秦之“官啬夫”为各类专业啬夫如“苑啬夫”、“库啬夫”、“仓啬夫”、“皂啬夫”、“田啬夫”、“厩啬夫”、“司空啬夫”、“发弩啬夫”、“采秩啬夫”等之总称,详见拙著《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中的《论〈秦律〉中的“啬夫”一官》一文。秦的这种以“官啬夫”主管各类生产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制度,在汉代史籍中却无系统反映,特别是汉代现存史籍中无“官啬夫”的名称令人注目。因此,就引发了不少疑问,或以为汉代已无秦的“官啬夫”制度,或认为由于汉代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而使秦的啬夫一官失去了作用。今观《定簿》所载东海郡属县吏员的设置情况,可知“官啬夫”制度在汉代并未绝迹;“啬夫”一官在汉代仍有其重要性。
《定簿》在统计东海郡郡太守府的吏员设置时,明确提到东海郡郡级吏员二十七中,有“小府啬夫”一官,数量为一人;在提到东海郡所属诸县吏员设置时,大县均有“官啬夫”之设置,如海西县的107名吏员中有“官啬夫三人,乡啬夫十人”;下邳县的107名吏员中有“官啬夫三人,乡啬夫十二人”;郯县的95名吏员中,有“官啬夫三人,乡啬夫六人”;兰陵、朐邑各有“官啬夫4人”;襄贲、戚县各有“官啬夫三人”;即使是小县,也有官啬夫二人或一人,如费县、即丘、厚丘、利成、况其、开阳、缯县、司吾、平曲等也各设“官啬夫二人”,昌虑、兰旗、良成、阴平也设“官啬夫”二人或一人;伊吾、北蒲和郁州三盐官及下邳、朐二铁官,也各设官啬夫,少者一人,多者五人;不设官啬夫的县只有临沂、曲阳、合乡、承、容丘、南城、新阳、东安、建陵、山乡、武阳、都平、郚乡、建乡、建阳、都阳等,而且大部分为侯国。从上述情况看,汉代东海郡所属县“官啬夫”的设置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具有普遍性,东海郡的43个县级建制机构中,有18县、2邑与5个盐、铁官处设置了“官啬夫”;二是官啬夫与乡啬夫并设,表明“官啬夫”决非“乡啬夫”之异名;三是5个盐、铁官处均有“官啬夫”,而且下邳铁官处多达5人,朐铁官处全部吏员只有5人而“官啬夫”占1人,这表明东海郡的“官啬夫”仍为主管煮盐、冶铁业等国有经济部门的官吏。东海郡如此,其他郡想也不会例外。以此言之,则汉代均应有郡级“小府啬夫”及县级“官啬夫”之设置,这同秦代普遍设置“官啬夫”以主管国有经济部门之制如出一辙,这是汉承秦制的又一反映,可补汉代史籍的严重缺漏。
第四,《定簿》中关于东海郡诸县设置“亭长”数量的记载,亦可证“亭”并非乡以下地方行政机构名称:
关于汉代的“亭”是否为乡以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问题,一贯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汉代的“亭”是郡、县、乡、亭、里的地方行政机构中一级机构,其说始于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论的“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另一种看法认为“亭”不是乡以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其说始于应劭《风俗通》所说:“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后之学者,或主前说,或主后者。自居延汉简与云梦秦简出土之后,似乎为后一种说法增添了砝码,我个人就曾写过《论秦、汉时期的亭——读〈云梦秦简〉札记》一文,首刊中华书局出版之《云梦秦简研究》一书,后收入《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一书,力主后一说法。然而,现在仍不免有人怀疑此说。今尹湾汉墓出土的《定簿》,又为此说增添了新证。
《定簿》载东海郡海西县有亭长54人、下邳有亭长46人、郯县41人、兰陵县35人、朐邑47人、襄贲县21人、戚县27人、费县43人、即丘县32人、厚丘县36人、利成县32人、况其邑23人、开阳县19人、缯县23人、司吾县12人、平曲县4人、临沂县36人、曲阳县5人、合乡县7人、承县6人、兰旗县12人、昌虑县7人、容丘县11人、良成县7人、南城县18人、阴平县11人、新阳县12人、东安县9人、平曲侯国5人、建陵县6人、山乡县4人、武阳县3人、都平县3人、郚乡县5人、建乡县4人、□□(疑为“于乡”)县2人、建阳县5人、都阳县3人。另外,下邳铁官吏员中有亭长一人,朐铁官及伊吾、北蒲、郁州三盐官处均无亭长之设置。基于上述情况,表明亭和亭长的设置有如下特征:其一,东海郡所属诸县的亭和亭长的设置,是全县统一计算的,足见亭及亭长是直接受县统辖的,而不为乡级机构所统辖。其二,亭及亭长设置的多少,是以县的大小为依据的,故大县往往为数十人,而小县往往为十余人或几人。其三,下邳铁官是主管冶铁业的机构,并不治民,却设亭长一人,可见下邳铁官的亭长是维持治安的官吏。其四,诸县亭与亭长设置的数量,同《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说“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之制不合。因为“一里百户”是定制,如此则一亭当有千户,一乡当有万户。而秦、汉之制均为万户以上设县,且为大县,决不可能有万户之乡;如果一亭有千户,以海西县来说,有54个亭长,则其户必在5万以上,以每户五口计算,仅海西一县就有口25万之多,而同墓出土的东海郡《集簿》载全东海郡只有139万多人口数量不合。因此,“十里一亭”与“十亭一乡”之说是根本站不住的。其五,再以一些小县来说,全县仅有十余个亭或两个亭不等,按此“十亭一乡”的原则去建乡,试问将如何进行!难道有无乡之县吗?因此,综观“亭”的上述特征,表明它不可能是乡以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而应是全县性的维持社会治安和兼顾邮传的机构。
第五,《定簿》关于东海郡县级吏员中有“官有秩”一官名的记载,可补汉代史籍之缺!
关于“有秩”一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有“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的说法,《续汉书·百官志》有“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等记载,二者都提到乡设“有秩”一官;《汉书·张敞传》有“敞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之语。由此可见,史籍中提到的“有秩”,本来均为“乡有秩”,并无“官有秩”之官名。但是,在《定簿》中却第一次见到了“官有秩”之名。《定簿》谓海西县的吏员中有“官有秩一人,乡有秩四人”;下邳县吏员中,有“官有秩二人,乡有秩四人”;襄贲县吏员中,有“官有秩一人,乡有秩二人”;兰陵县吏员中,有“官有秩一人”;而且所有这些设置“官有秩”与“乡有秩”的县,往往“官啬夫”与“乡啬夫”同时并设。这些情况表明:“官有秩”与“乡有秩”是不同的两个官名,“官有秩”与“乡有秩”同“官啬夫”与“乡啬夫”也不相同,否则不会同时并设。因此,《定簿》关于“官有秩”一官的记载,可补《汉书》及《续汉书》之缺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