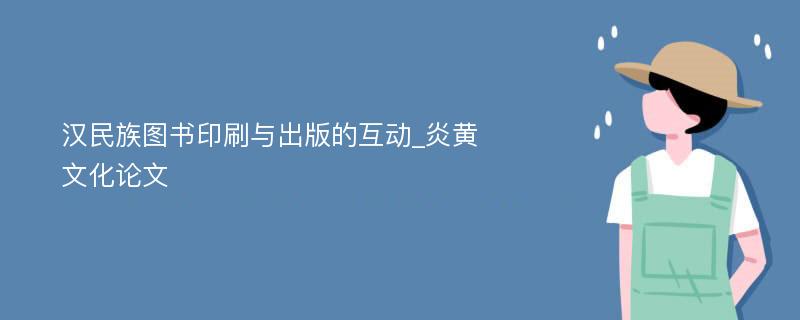
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字书籍印刷出版之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族论文,互动论文,少数民族论文,文字论文,书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不断互相接触、交流、融会,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丰富、发展了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文字书籍印刷出版方面,各民族的互动有生动的反映。由于汉族文化的先进和强势地位,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更为突出。
一、中国汉字对少数民族文字的影响
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制并使用了本民族文字,这不仅在民族文化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重要内容。
早期的少数民族文字多出现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这些文字由西部传入。由阿拉美文字转变而来的佉卢字母,在公元前就已经传入中国;焉耆-龟兹文来源于印度婆罗米文中亚斜体,有5世纪时的文献;粟特文也属于阿拉美字母系统,有2至3世纪的铭文;于阗文是印度婆罗米文的笈多王朝变体,存世的文献多为7-10世纪的遗物;突厥文由阿拉美文的粟特文字发展而来,存有8-10世纪的文献;回鹘人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创制了回鹘文,从8世纪就开始使用这种文字。7世纪吐蕃参照印度的梵文创制出藏文,一直使用到今天。这些文字都不是汉字系统,但在书籍的编纂方面也都受到汉文化的强大影响。10世纪后,中国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一些强大的少数民族建立了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王朝,并大力发展文化,创制文字,而这些文字的创制往往受到汉字的强烈影响。
1.文字创制的影响
宋朝前期是北宋、辽朝、西夏三足鼎立,后期是南宋、金朝、西夏互相对峙,此外还有回鹘、吐蕃、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影响加强,契丹、党项、女真族先后建立起强大的辽国、夏国和金国,不仅发展了社会生产,也创造了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辽、夏、金建国前后,政府和社会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文字的创制都有迫切需求,作为强大民族政权的主体民族,创制民族文字也是民族自尊、自信表现。三个王朝都在皇帝的倡导下分别创制了民族文字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使用,在中国北方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少数民族文字使用热潮。
契丹、党项、女真族创制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时,都以突出民族文化相标榜,然而在创造民族文字时,则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强大影响。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后,于神册五年(920)制契丹大字,“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①契丹人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参与创制契丹文字②。契丹大字的创制受到了汉族文人的影响,汉族文人参与了创制契丹大字,创制时参照了汉字。最早记载契丹字的汉文史书《五代会要》载:“契丹本无文字,惟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撰为胡书。”③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辽太祖多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契木之约”。④从存世的契丹文字文献看,这种文字受汉字影响很大,沿用了汉字的横平竖直、拐直弯的书写特点,还直接借用了一些笔画简单的汉字。契丹大字中有的像汉字一样,一字一个音节者;有的则是数字一个音节,每字代表一个音素,应是一种音节-音素混合文字。后来又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小字也借鉴了汉字的笔画,并从同是黏着语的回鹘语中学习拼音法规则,基本上是音素文字。契丹文的书写规则也与汉文一样,自上而下成行,自右而左成篇。
西夏文的创制也受到汉字的直接影响。《宋史》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⑤“八分”是汉字的一种书体。西夏文和汉字一样,属于表意性质的方块字,文字形式和汉字相近,由横、竖、撇、捺、点、拐等笔画构成。其文字构成也受汉字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的影响。西夏文书写也同汉文,自上而下书写,自右而左移行。西夏文也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一篇西夏文文献,乍看就像一篇汉文。从这些都能看到汉字、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强烈影响。因西夏语和汉语同属单音节词根语,与汉字性质相同、形体相近的西夏文可以顺利使用。
女真族原来只有本族语言,而无文字。在与辽、宋交战过程中一些人学会了契丹文和汉文。当时随着交往的增加,文化的交流自然加强,各民族中都有一些掌握双语的人才。对汉文化的仰慕与追求自王室至百姓都成为风尚。女真统治者拜俘虏中的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为师,聘为高官,请其为金朝制定法令制度,甚至扣留宋朝使臣,请其授以汉族文化。《宋人佚事汇编》载洪皓出使金国被扣十余年,辞不就官,为金人所敬。他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默写于桦树皮上,教当地女真人读书,被称为“桦皮四书”。⑥
当时女真与契丹为邻,受契丹文化的影响很大,汉文化对其也有深远影响。女真文字是在契丹文字的直接影响下,在汉文字的间接影响下创制而成的。据史载,完颜希尹“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⑦当时规定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所以女真字制成后与契丹字、汉字在金朝境内同时流通,金章宗二年(1191)“诏罢契丹字”,只准用女真字和汉字。
当时在三个王朝中都是多种语言、文字同时流行。这种文化的互动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是促成这三个民族很快与其他民族融合。当这些王朝灭亡后,这三个民族逐渐消亡,其中文化的互动、融合,是促使民族消亡的重要因素。
除北方外,南方少数民族也陆续创制使用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其中借鉴汉字的有多种。
有方块白文。白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由于汉族和白族的交往密切,白族人长期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白语含有大量汉语词,是汉语、藏缅语混合语言类型。白族从唐代开始曾经使用过以汉字为基础的方块白文,记录白语。白文流行于云南大理一带,是白族使用的一种土俗文字。方块白文一部分是借用汉字的形和音,不取义;一部分是借用汉字的形和义,不取音。这些类似形声字或会意字。还有一部分是取汉字的某些部件按汉字的造字法而创造的新字。有时全用汉字的形、义,实际是汉字白读⑧。
另有方块壮字。壮族民间曾经模仿汉字创制过壮族文字,俗称“土字”或“土俗字”,现一般称“方块壮字”或“古壮字”。在与汉族密切接触、交往,广泛深入地学习吸收汉字文化的过程中,壮族人借用汉字造字创造了方块壮字。其中有的直接借用汉字,有的利用汉字重新组合,或对汉字加以改造,也有类似象形、会意、形声等字类。
最近在土家族地区又发现一批文献,其中皆是改制汉字而形成的一种文字,可能是土家族过去使用的文字。由于汉文化的广泛传播,还有不少少数民族曾尝试着利用汉字或汉字的变体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其文字形式类似方块壮字,而比方块壮字更为简约,甚至没有形成体系,这些字仅用于民间,如布依族、侗族、苗族、瑶族、哈尼族等都有借用汉字而创造的文字。
2.文字使用的影响
辽朝创制契丹文后即用来修纂本国历史,这也是受到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传统的影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和中原王朝皇帝一样,十分重视本朝历史的修纂。《辽史》载:“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⑨后仿照宋朝成立国史院,设国史监修官。所修国史包括起居注、日历、实录等。创制契丹文另一个目的是用契丹文翻译汉文书籍,所译书籍包括汉文的史书和医书。据《辽史》记载,萧韩家奴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耶律倍译《阴符经》,耶律庶成译《方脉书》等。⑩他文献中也有以契丹文翻译汉文典籍的记载,如曾译《辨鴂录》(11)。甚至辽朝皇帝也参加译书,辽圣宗耶律隆绪曾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12)。这种译书活动使契丹族更直接地受到汉族的文化影响。
西夏文创制后,首先用来翻译汉文著作,“教国人记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13)“蕃书”、“蕃语”皆指西夏文。《孝经》、《尔雅》、《四言杂字》应是最早的西夏文书籍。夏毅宗谅祚曾于宋嘉祐七年(1062)向宋朝求赐字画和经史书籍:“夏国主谅祚上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欲建书阁宝藏之。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本朝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其马。”(14)可见宋朝在西夏前期曾应西夏之求,赐给其《九经》。西夏是否将《九经》全部翻译成西夏文,不得而知。但在现存的西夏文文献中已经发现了刻本《论语》,写本《孟子》和《孝经》。从已经发现的西夏文献可知,西夏翻译或编译了很多中原地区的书籍。如史书《贞观政要》,类书《类林》(15),兵书《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等(16)。
西夏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始终是西夏的第一宗教。西夏在11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曾先后六次向宋朝赎取《大藏经》。西夏建国初期用了50多年的时间将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称作“蕃大藏经”。这部大藏经共有820部,3579卷。它是西夏王朝数量最大的翻译著作,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大藏经中最早的一种,在西夏书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有特殊的地位(17)。后来,西夏又补译了不少佛经,其中也包括从藏文翻译的藏传佛教经典。西夏还将一些藏传佛教经典译成汉文,形成了党项、汉族、藏族三角的互动影响。
金代对汉族文化典籍十分重视,早在金太祖天辅五年(1121),完颜阿骨打便下令“若克中原,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18)天会五年(1128)十二月攻下北宋首都开封,将北宋国子监所藏图书、书版尽数劫去。金朝立国后中央政府直接刻印出版图书,金天德三年(1151)设国子监,除了培养士子外,还负责出版教学用的儒家经典,如九经、十四史,还有《老子》、《荀子》、《扬子》等书。
由于文化教育的需要,女真文字的翻译出版也十分兴盛,从编译的女真文图书内容来看,大多为儒家经典,这与金代对女真人进行儒学教育是分不开的。为了使不懂汉文的女真人学习儒家经典,特地建立了译经所。弘文院也是负责译书的机构,《金史》载:“弘文院,知院,从五品,同知弘文院事,从六品,校理,正八品,掌校译经史。”(19)当时女真文译本有《易经》、《书经》、《孝经》、《论语》、《孟子》、《老子》、《刘子》、《扬子》、《列子》、《文中子》等典籍(20),还有史子类图书《贞观政要》、《新唐书》、《史记》、《汉书》、《盘古书》、《孔子家语》、《太公书》、《伍子胥书》、《孙膑书》、《黄氏女书》等。显然汉文化对金国书籍影响之大。
在少数民族出版物中,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一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另一种少数民族文字对照的文献,或多种文字合璧的文献十分丰富,在世界上堪称典范,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文化互动的真实体现。
二、中国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印刷术的互动
中国在隋唐之际发明了雕版印刷,北宋时期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汉族地区发明印刷术以后,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更为强劲。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和带动下,少数民族也形成和发展了印刷出版事业,出版了大量的图书,少数民族文字的印刷出版也从这时走向繁荣。各民族还在印刷事业中互相影响,有很多重要创举,推动了中国出版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辽朝统治者仰慕汉族文化,提倡儒学,修建孔庙,设立太学,实行科举,从宋朝输入大量汉文印刷典籍。同时,辽朝在境内也发展汉文印刷,刊印汉文五经,又出版《史记》、《汉书》等。此外,还印刷有蒙书、医书。
辽朝大力提倡佛教,继宋朝出版汉文大藏经后,也刊印了汉文大藏经《辽藏》,或称《契丹藏》。辽朝的南京(今北京)设有印经院,是当时印刷的中心。由于印刷业的发达,民间也有私刻、私印书籍者。但因辽代书禁甚严,辽朝文书典籍传入中原绝少,加以金灭辽时破坏惨重,文化典籍毁灭殆尽。辽朝曾用契丹文翻译了很多书籍,这些书籍是否刻版印刷,史无明载。根据当时辽文化发达的程度和汉文书籍刻印水平,有能力印刷契丹文字书籍。但至今未见刻印的契丹文书籍。这可能与辽朝严禁契丹文字书籍出境有关(21)。
西夏刻印书籍从技术到内容都受到汉族的直接影响。西夏出版了很多译自中原的著作,存世的有《论语》、《十二国》、《经史杂抄》、《德事要文》、《德行集》、《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类林》等。西夏编著出版的世俗著作如语言文字类的韵书《文海宝韵》、字书《音同》,法律类有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官阶封号表,识字蒙书《番汉合时掌中珠》(见封三上图)、《三才杂字》,志书《圣立义海》,谚语《新集锦合词》,诗歌集,劝世文《贤智集》等(22)。刻印的佛教著作更是种类繁多。西夏书籍的刻印量不等,以佛经印刷量最大,如在一次法会上便“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共25万卷,可见当时印刷规模之大。
西夏人在汉族的影响下发展了活字印刷出版。在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就开始使用。目前已发现西夏活字印刷书籍十多种。其中有泥活字印本如《维摩诘所说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见封三下图)等。西夏开创了木活字印刷。毕昇曾实验过木活字印刷,但没有完全成功(23)。从西夏木活字印刷品来看,当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印刷质量也大大超过泥活字印刷,比元代王桢的木活字印刷要早一百多年。如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德行集》、《大乘百法明镜集》、《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等(24);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九卷(25);敦煌北区洞窟发现的西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诸密咒要语》等。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历书《西夏光定元年(1211)辛未岁具注历》残页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文活字印刷品(26)。西夏的活字印刷品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表明西夏在活字印刷出版方面,与中原地区衣钵相传,互相影响,作出了突出贡献。
西夏还刻印多种汉文典籍,多为佛经,其中不少印制精美(27)。有年代可考的西夏汉文刻本世俗书籍发现很少,已知刻本有《西夏乾祐十三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28)。
西夏灭亡后,在蒙、元时期党项人为色目人,民族地位较高。当时仍出版西夏文文献,全是佛经。国家图书馆藏有刻本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雕刊完毕时间是定宗贵由丁未二年(1247)(29)。元代最重要的西夏文文献印刷是由政府雕印西夏文大藏经。元世祖时就着手刻印西夏文大藏经,元成宗即位后曾一度“罢宣政院所刻河西大藏经板”(30)。不久又恢复刻印(31)。元代西夏文大藏经的刻印先后经过30年的时间,才在杭州万寿寺中完成。当时印行西夏文大藏经至少4次(32)。除刻印西夏文大藏经外,还刻印西夏文单部佛经。包括整藏的西夏文大藏经和单部西夏文佛经印刷后“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看来主要是散施到西夏故地宁夏、甘肃等地。
金代在山西平阳(今临汾)设有刻书机构,平阳在金代成为中国北方的出版中心。除了官家刻印图书外,有很多私人书铺也刻印了不少图书。金国不仅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还刻印了很多书籍,有的女真文译著发行量还较大,如大定二十三年(1183)翻译的《孝经》一次就印刷了上千部付点检司,分赐给护卫亲军。当时除了国家刻印图书外,私人也刻印了不少书籍。
吐蕃文化发达,对书籍的大量需求,20世纪初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量唐代藏文佛教和世俗写卷。然而过去一直未能发现15世纪以前的藏文印刷品。
西夏与藏族来往密切,并接受了藏传佛教,西夏境内有很多藏族居住,也流行藏文。西夏发达的印刷事业为藏文佛经的刻印创造了条件。在西夏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发现了多种藏文刻本,如《顶髻尊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等,佛经中很多处出现反i字,证明其为古藏文(33),是12-13世纪初的藏文印刷品,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藏文印刷品(34)。这些刻本雕刊精细,是很成熟的印刷品,证明印刷出版从中原、西夏到藏族地区的辐射路线。
元朝的大一统局势,有力地推动了藏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当时西藏能从元大都获得大量纸、墨,使藏文书籍的刻印和流通在西藏地区兴盛起来。
元世祖命达玛巴拉等高僧在大都勘校藏汉文佛教典籍,编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当时由藏、汉、畏兀儿等民族的学者一道,对藏、汉两种文字的佛经认真核对,校勘异同。校出佛经5386卷,至大德十年(1306)才刻板流行(35)。元朝僧录管主八于大德六年(1302)曾印装西番字(藏文)《乾陀般若白伞》30余件,经咒十余部,散施西藏等处。这是元代较早地刻印藏文书籍的记录,但这些印刷品也没有保留下来。当时除佛经外,也刻印藏文世俗著作。如八思巴的弟子汉僧胡将祖将《新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纪》译成藏文,由仁钦扎国师于泰定二年(1325)在临洮刻版印行,印本也未传世。
回鹘王国地处中西交通要冲,文化发达,原信仰摩尼教,后信仰佛教。早期曾使用突厥文,后被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鹘文所代替。11-12世纪回鹘民族已经使用回鹘文进行雕版印刷。回鹘人还创制了回鹘文活字印刷。1908年法国伯希和在莫高窟北区181窟发现了960多枚回鹘文木活字,收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后敦煌研究院又先后发现54枚,藏于敦煌研究院。由于回鹘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类型的两种语言,汉地活字印刷术不能简单地应用到回鹘文的印刷上。回鹘人在设计活字时,考虑到回鹘文是拼音文字和回鹘语是黏着型语言的性质。更为重要的是,回鹘文活字中有大量的以语音为单位的活字,这些回鹘文活字是包含字母活字在内的混合类型活字,开创了字母活字的先河(36)。回鹘文活字印刷在印刷史上开创了新的里程碑,为世界印刷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37)。
元世祖忽必烈使国师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蒙古文字,又称八思巴字,至元六年(1269)作为官方文字正式颁行,用来“译写一切文字”,除拼写蒙古语外,也拼写汉、藏、畏兀等语。现存八思巴字拼写蒙语和汉语的碑铭各有20余通,拼写藏、畏兀语只有少量佛教文献。保存至今的八思巴字刻本不多。传世抄本《蒙古字韵》是八思巴字与汉字的对照字典,原来是否有刻本问世,尚难断定。《事林广记》所收《蒙古字百家姓》为八思巴字、汉字对照。因《事林广记》多次刻印,《蒙古字百家姓》也就有多种版本,比较常见的有元至顺间(1330-1332)、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明永乐十六年(1418)、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等多种刊本(38)。20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发现刻本八思巴字《萨迦格言》,共4叶,3叶藏于德国,1叶藏于芬兰。近些年在敦煌北区洞窟中也发现一纸残叶。刻本《书史会要》中有八思巴字字母,也应是八思巴字刻本的一种。西夏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也有八思巴字刻本残叶。还有一种蒙古文—八思巴字合璧的刻本佛经《五守护神大乘经·守护大千国土经》,为元代刊本(39)。
在成吉思汗时,就开始在蒙古贵族中传授以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系大臣塔塔统阿首倡,称为回鹘式蒙古文(40)。天历二年(1329)创立艺文监(后改为崇文监),专门主持蒙文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孝经》(见封二上图)、《尚书》、《贞观政要》、《百家姓》、《千字文》、《大学衍义节文》、《帝苑》、《忠经》等书籍。此外元朝至元六年十二月(1270)还定制命诸路府官子弟入学,“以蒙古字译写《通鉴节要》,颁行各路,俾肄学之”。(41)
至元元年(1264)“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至正五年(1268)“敕从臣秃忽思等录《毛诗》、《孟子》、《论语》”。十九年(1282)“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42)汉文经书的蒙译本主要用来教学(43),也用来颁赐王公大臣。用回鹘式蒙古文印刷的典籍多已不存,传世的仅有汉文、蒙古文合璧的《孝经》残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据史书记载,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孝经》进呈武宗,武宗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44)可见当时曾刻印广泛流传。
元代随着蒙藏关系的发展,在西藏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吐蕃、回鹘、蒙古、汉族僧人参与,将大藏经译成蒙古文,并于大德年间(1297-1307)在西藏开雕,印刷流行(45)。
满族早期曾利用蒙古文记录满族语言,但使用很不方便。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古字母为基础,结合女真语,创制了满文(46)。后又有所改进(47)。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
在关外时期,满文译作汉籍很多,皇太极时期翻译规模更大,并成立了专门机构,初名为“笔帖赫包”,意为书房,后改名为“笔帖赫衙门”,乾隆年间又改为“文馆”。译成满文的书籍有《素书》、《刑部会典》、《三略》、《万宝全书》、《通览》、《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等。还有选择地翻译了《四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等书。这样在满族人中间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这些早期满文书籍是否刻印,史无明载。但传世的刻本中有汉文《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约刻于天命三四年(1618-1619)。又有崇德三年(1638)蒙文《军律》刻本。当时作为本民族文字的一些满文书籍很有可能会刻印。史载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政体,乃命文成公达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48)颁赐”的书或有印本。
随着满族民族文化的发展,官刻本和民间坊刻本都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清朝自嘉庆、道光时期,国力开始下降,满族文化出现逐步弱化的趋势,满文的印刷也随之式微。除继续按惯例刊印前代皇帝的满文《圣训》外,还刻印了满文《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不多的几种书。一些地方官衙也刊印了满文图书,如《清文指要》、《清文总汇》、《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等。在东北满族集中的地区满语、满文有较多的使用(49)。
清初就已出现了少数坊刻本,如南京听松楼刻印的《诗经》。康熙朝坊刻本开始繁荣,仅北京就有10家刊印满文的书坊,刊印了《大清全书》等书。后雍正、乾隆时期刊印满文的书坊增多。当时的二酉堂、天绘阁、尊古堂、三槐堂、聚珍堂都是刻印满文书籍的老字号,印过不少实用的书籍。当时书肆出版已有明确的版权意识,在书籍的牌记上标明“翻印必究”的字样,维护自己的版权(50)。
彝族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彝族很早就创制了民族文字一彝文。彝文文献十分丰富。用彝文书写的古籍多达几千卷,保存了古代彝族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各历史时期有关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地理、语言、文字、医学、农技、工艺、礼俗、宗教等内容。彝族刻印书籍起于何时,难以遽定。在《水西大渡河建桥记》碑中记载:“木刻竹简,多如柴堆。”这里所指是否指彝族早有雕刊木版印刷书籍还难以断定,但彝族至少在明代已经有木版印刷。在所见到的文献中,彝文的刻本《劝善经》可谓凤毛麟角。
彝文《劝善经》,彝语称“尼木苏”,内容为汉文《太上感应篇》的译文。刻本彝文《劝善经》是彝文古籍中内容丰富、字数较多的最早彝文木刻本。据马学良先生考证,成书年代大约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刊印时间为万历三年(1575)(51)。此书20世纪中叶发现于云南省禄劝、武定等县。据说当年收集包括《劝善经》在内的译文经典时,还有若干块刻板,但至今未能查到。另一部重要彝文书籍《玛牧特依》,可译为《教育经典》,为彝文教科书。此书有雕版印刷本,上半部书刻于清代,下半部刻于民国时期,先后两次才完成全书的雕刻。这是继明代雕印《劝善经》后的又一次雕版印刷彝文书籍。
纳西族有悠久的历史,有辉煌的文化。纳西族很早创制、使用的东巴文,是图画记事和表意文字中间发展阶段的象形文字符号系统,至近代仍在使用。用东巴文书写了大量的典籍。纳西文还有一种音节文字是哥巴文,其产生年代晚于东巴文,其经书的数量也远不及东巴文(52)。可喜的是,1973年于云南中甸县白地乡发现东巴文木刻版,无刻写年代和制作人名。板长约33厘米,宽12厘米,厚1厘米。木刻内容为“阮可超荐经是也”,是目前仅有的东巴文经卷夹板木刻。另有东巴文和哥巴文对照字汇刻板(见封二下图)。此板制作于20世纪初,系云南省丽江长水乡东巴和泗泉制作。今仅存两块雕版,梨木制成。一块两面,为序言;另一块板内容系关于人类、人体的字词。该版具有重要价值,今存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博物馆。
中国汉族发明的印刷术,很快影响、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少数民族刻本的刻工既有少数民族,又有汉族;版心的书名、表卷次和板次的数字以及页码有的用少数有民族文字,也有的用汉字。可能雕刊这些民族文字的刻工有少数民族,也有汉族。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发扬光大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成为当时的先进文化,不仅传播到邻国,还远播至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书籍装帧形式上的互动
书籍的装帧形式很引人注目,是书籍出版的一部分。中国的中原地区自纸张发明后,先后出现了卷装、蝴蝶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绩装、梵夹装、线装等形式。中国的少数民族书籍也有自己的装帧形式。比如于阗文书籍装帧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梵夹装,纸叶左侧中间有一圆孔,以便用绳相连;另一种是卷轴装,纸的宽幅不等,这种图书往往是汉文与于阗文合璧。这两种不同的装帧形式反映出汉文化与印度文化在于阗地区的影响与结合。
印刷出版很发达的西夏,从其书籍的装帧形式看,基本上借鉴了中原地区的装帧方法,几乎囊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出版图书的各种形式,如卷装、蝴蝶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缋装、梵夹装、线装等。西夏书籍是研究中国古代印刷、装帧、出版不可多得的资料。蝴蝶装是宋朝才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装订方法,是册页装订的最早形式,它比卷装翻阅方便,流行于宋、元时期,是书籍装帧史上的一大进步。西夏的世俗刻本书籍多是蝴蝶装,而刻本佛经多是经折装,一些写本佛经则采用卷装、梵夹装或缝缋装。
黑水城出土的藏文刻本有梵夹装和蝴蝶装。蝴蝶装式是一种较古老的书籍装帧方式,从装帧的角度证明这种藏文刻本是很早的刻本。
藏文是自左向右横写,自上而下移行。藏族原来采用从印度传来的方法,把佛经文字纪录在贝叶上,简称为“贝叶经”。直到中原地区的造纸术传入藏区后,才开始把藏文写在纸上。吐蕃时期的写本多是卷子式,在一张纸上横写,一纸写完再续粘一纸,有的长达几米。后来为了书写和保存的方便,出现了藏族特有的长条书式。长条书由很多规格相等的长方形纸页组成。这种装式大约起源于印度的贝叶书。
黑水城出土的藏文蝴蝶装刻本,其装帧形式直接借鉴于西夏,间接受惠于汉族。如藏文《顶髻尊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形式是典型的蝴蝶装,版心有汉文页码。只是这种蝴蝶装被改造了,它适应了藏文的书写方式,与汉文、西夏文蝴蝶装自右而左成行、自上而下书写、先书写右半面、后书写左半面不同,而是自左而右书写、自上而下成行,更为特殊的是每行写到版心时,不是移到下一行书写,而是越过版心继续书写,也即同一页左右两面的同一行是通读的。这是蝴蝶装在横写的少数民族文字中的灵活运用,是蝴蝶装的新发展,也是一种创新,表现出民族间文化的交融和吸收(53)。目前这种书籍在世上是绝无仅有的。另一种是仿贝叶装式的梵夹装,如写本《圣般若波罗蜜经》,有的叶中还有仿贝叶经用于穿绳线的圆孔(54)。
而源于印度的梵夹装又影响到西夏,使西夏文文献出现了梵夹装,这种装帧形式可能是西夏人向藏族学习的。西夏文书籍的梵夹装又不同于藏文的长条书。藏文的长条书是自左向右横写、自上而下排行的。西夏文的梵夹装是自右向左排行,自上而下竖写,这是由于两种文字书写方式不同的缘故。这种书纸质较厚,皆为两面书写。一种是写完第一面后,向上旋翻,在背面继续书写;另一种是写完第一面后,向右旋翻,在背面继续书写。目前这种装式只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保存。如《慈悲道场忏法》,向上旋翻;《大方广佛华严经》,向上旋翻;《圣大悟阴王随求皆得经》,向右旋翻。此外还有《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圣摩利天母总持》等。这种把用来书写横行拼音文字的长条书式改进成书写竖行方块字书籍的装帧形式,是西夏人的一种创造,它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回鹘文也有多种装帧形式,以卷轴装和梵夹装为主。不同的装帧形式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据此,可以帮助我们断代。卷轴装的回鹘文献多属早期,梵夹装和经折装则在其后。如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即为卷轴装,被斯坦因携至英国,现藏英国图书馆。《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则为梵夹装,这种装帧的书页在左侧都有一个红色的圆圈,圈的中间则是一个洞,以便用绳子穿过扎紧。也有个别是每叶双圈双洞的(55)。除了这两种常见的装帧形式外,还有册页装。如《阿毗达摩俱舍论实义疏》,原藏于敦煌藏经洞,现存英国图书馆,此书分装两册,第一册67叶,第二册82叶。此外亦有经折装,这种装帧形式多为刻本佛经,大多数回鹘文印刷品是元刻本。
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中,卷装、蝴蝶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缋装、线装等是从中原地区形成和发展的,后陆续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多数民族地区书籍装帧的主流。而梵夹装则是由印度的贝叶书传入西域、西藏,演变为纸质的梵夹装书籍,再继续东传到河西一带,成为主要流行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一种特殊的书籍装帧形式。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书籍的装帧形式上的互动,使一些装帧形式嬗变成新的亚种。
本文曾在法国远东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其他法国机构联合举办的“中国和欧洲:印刷史和书籍史”国际研讨会(10月15-16日在京举办)上宣读。
注释:
①《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第16页。
②《辽史》卷七五《耶律突吕不传》,卷七六《耶律鲁不古传》。
③(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九。
④(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八。
⑤《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⑥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中华书局,1981年。
⑦《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希尹传》。
⑧徐琳、赵衍荪:《白文〈山花碑〉释读》,载《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
⑨《辽史》卷七十六《耶律鲁不古传》。
⑩《辽史》卷一○三《萧韩家奴传》,《辽史》卷七二《宗室传》,《辽史》卷九八《耶律庶成传》。
(11)(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五。
(12)《契丹国志》卷七。
(13)《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1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嘉祐七年(1062)四月己丑条。
(15)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第156-221页。
(17)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1期。
(18)《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19)《金史》卷五十六《百官志》。
(20)《金史》卷八《世宗传八》。
(21)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89年,第111-131页。
(22)史金波:《西夏古籍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3期。
(23)(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板印书籍”条。
(24)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1期。
(25)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文物》1994年9期。
(26)史金波:《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文物》2001年10期。
(27)《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6册。
(28)邓文宽:《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华学》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29)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期。
(30)《元史》卷十八《成宗纪》。
(31)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1期。
(3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7页。
(33)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丝路上消失的王国》(台湾中文版),1996年,第274-278页。
(34)史金波:《早期藏文雕版印刷考》,2004年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年会报告论文。
(35)该书序:元世祖“皇帝……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帝师拔合思八、叶琏国师……汉土义学亢理二进主庆吉祥及畏兀儿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藏等,集于大都,自至元二十二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各秉方言,精加辩质,顶踵三龄,铨雠乃毕。”
(36)雅森·吾守尔:《敦煌出土回鹘文活字及其在活字印刷术西传中的意义》,《出版史研究》第3集,1998年。
(37)史金波、雅森·吾守尔:《西夏和回鹘对活字印刷的重要贡献》,《光明日报》1997年8月5日。
(38)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年。
(39)照那斯图、牛汝极:《蒙古文—八思巴字〈五守护神大乘经·守护大千国土经〉元代印本残片考释》,《民族语文》2000年1期。
(40)《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
(41)(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五○。
(42)《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九》。
(43)《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44)《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45)道布:《回鹘式蒙古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2年。
(4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卷三。
(47)《清史稿》卷二二八《额尔德尼、噶盖、达海等传》。
(48)(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
(49)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四、卷五、卷六。
(50)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51)马学良、张兴等:《彝文〈劝善经〉泽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
(52)和志武:《东巴文和哥巴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52)俄国藏黑水城出土文献,XT.67。
(54)俄国藏黑水城出土文献,TK.24。
(55)冯家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一号,1953年第6期。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契丹文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印刷工艺论文; 活字印刷术论文; 论语论文; 孟子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西夏论文; 契丹论文; 辽史论文; 贞观政要论文; 八思巴论文; 六韬论文; 藏文论文; 大藏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