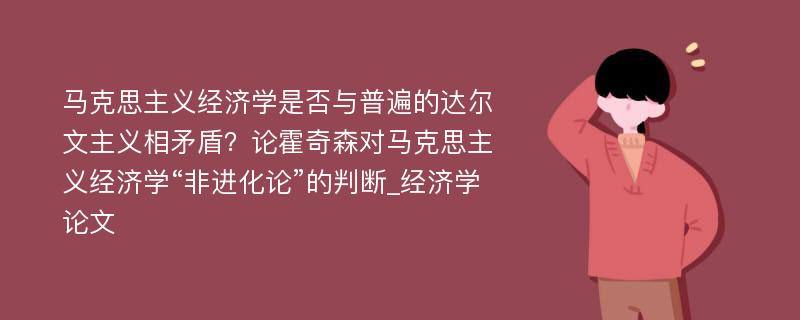
马克思经济学与普遍达尔文主义相矛盾吗?——兼评霍奇逊对马克思经济学“非演化”的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学论文,达尔文主义论文,矛盾论文,霍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1999年以NEAR标准对马克思经济学给出“本体论上不承认新奇”的判断之后,霍奇逊继而又发展出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达尔文主义原则,该原则包含了与现代演化哲学相关的许多理念,如新奇、涌现、不确定性、反还原论等,就这些问题,霍奇逊在多部著作和论文中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和判断。
一、普遍达尔文主义与NEAR标准
尽管众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承认马克思经济思想对当代演化经济分析有着开创性的意义①,但当代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霍奇逊却坚持认为,马克思不属于演化经济学家。在他的1999年的《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一书中,霍奇逊按照本体论、方法论和隐喻提出了划分演化经济学的三个标准:一是新奇性(novelty),新奇性是本体论标准,意指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二是方法论上的反还原论(anti-reductionism);三是隐喻标准,即是否承认和采用生物学隐喻。霍奇逊将其中的前两项概括为NEAR经济学(即接纳新事象Novelty embracing、反对还原论anti-reductionism)。②霍奇逊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尤其是就包容新奇、反还原论两点上,演化经济学家形成共识,如斯坦利·梅特卡夫(Stanley Metcalfe)、福斯(Nicolai Foss)、魏特(Ulrich Witt)等。福斯就指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魏特等人所发展的这一类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涌现及其可能的扩散”,这正是新古典和演化范式区分开来的原因。③按照这一标准,马克思被排除在演化经济学阵营之外。霍奇逊的判断是,马克思仅符合反还原主义这一条,但马克思不接纳新事项(不满足第二条),马克思是非生物学的(不满足第三条)。符合这一标准,与马克思同列的还包括旧制度经济学家艾尔斯和米契尔。
孟捷援引卢卡奇的一系列论述对霍奇逊“马克思在本体论上不承认新奇”这一判断进行了批驳,认为马克思在本体论上是承认新奇的。④就霍奇逊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缺乏对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这一判断,孟捷⑤和刘凤义⑥也进行了评述。本文认为,评价霍奇逊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判断,更适合的切入点是他后来所提出的普遍达尔文主义原则。霍奇逊1999年提出的NEAR标准与其后来所提出的普遍达尔文主义原则⑦是一致的,在这一标准下,霍奇逊对马克思做出了属于决定论、预设论的判断,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倡导的演化无方向、无目的、多样性等原则相背离。
如前所述,霍奇逊不仅给马克思冠以“本体论上不承认新奇”的判断,还给了一个非生物学的判断。从霍奇逊后期的思想发展看,“非生物学”这一判断具有更为深刻的意蕴。在多篇论文和著作中,霍奇逊都反复强调生物隐喻的重要性:“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都是极其复杂的系统,都带有繁杂的结构和因果关系,既包含了连续的变化,又包含了极大的多样性。”在霍奇逊看来,生物学隐喻虽然是有局限性,这种做法有危险,不过他仍然坚持认为:“所有隐喻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困难,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除非有另一个替代之物,否则我们不可能放弃隐喻。”在霍奇逊那里,生物学隐喻并非等同于生物学术语,它具有方法论的含义。他还专门讨论了与生物学隐喻有关的三个关键哲学问题,即本体论、方法论还原主义和数学形式主义。在提出NEAR标准时他也曾强调:“隐喻标准作为分类尺度被列为最后一个的首要原因在于,对具有本质意义的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⑧
2002年以来,霍奇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从本体论、方法论、思想史多个角度讨论了进化论与经济学的关系。这些论著表明,霍奇逊所倡导的普遍达尔文主义,是想将进化思想视为一种哲学理念,并试图超越单纯生物领域,将其应用于经济分析。“普遍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则,加上一些特定的辅助性说明,就可以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能用于现象解释。”⑨“在社会进化理论中,达尔文理论更是一种哲学原则而非生物学简化主义。”⑩在数篇论文中,霍奇逊不厌其烦地强调进化论的哲学意义,试图厘清生物术语套用和比喻的误解:“进化论与种族主义、性、民族主义无关,也没有为‘适者生存’提供任何道德支持,也不证明人在权力和财富上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说明演化总是进步的或者最优的。”(11)“进化论意味着因果解释,适用于所有包含了变异、遗传和选择机制的组织和复杂系统,支持任何一个有原因的事件或现象……进化论提供了一个关于结构化规则和规则系统的本体论。”(12)
在提出NEAR标准时,霍奇逊在“本体论上承认新奇”这一点后还有两点补充:第一,新奇不仅仅是新事项,同时也是多样性的源泉;第二,仅仅承认新奇还不够,还需要对新奇产生的方式体现出涌现观。“新事象的引入和对还原论的抛弃都必须依赖涌现(emergence)的概念,涌现是社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的中心特征。”(13)这种说明,与演化哲学是一致的,演化哲学中,同样包含了如下含义:涌现是系统新特质表现的形式,而多样性构成了系统运动和系统变化的动力,而且,涌现是不确定的,哪怕它可以以确定性的方式展开。新奇、反还原论、生物隐喻围绕着新事象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理论标准,其中,涌现和不确定性是霍奇逊尤为重视的观点。这样,霍奇逊赋予了普遍达尔文主义原则因果解释、新奇、选择、多层级、涌现、非决定论等丰富的含义,构成了一种经济学思想是否属于“演化”的终极衡量标准。
二、普遍达尔文主义原则下的马克思经济学
按照这种标准,霍奇逊对马克思经济学做出了“非演化”的判断,其理由主要是以下三点。
1.马克思预设了演化的方向和目的
霍奇逊认为,马克思预设了历史演化的方向和目的,与演化观是不相容的,因为演化没有最优,没有预设,也没有终结,这成为他认定马克思“非演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设想是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revolutionary,than evolutionary)”(14)。在将凡勃伦思想与马克思思想进行比较时,霍奇逊反复指出:“不同于马克思的地方在于,凡勃伦认为多重特征(multiple futures)是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和累积因果意味着历史没有终极,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这种终极是共产主义或者无阶级的社会,但凡勃伦拒绝这种终极观点。”(15)“凡勃伦式的进化论与马克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凡勃伦那里,演化意味着累积因果,没有终极,没有结束。而马克思却描述了一个终极社会。”(16)在霍奇逊看来,虽然马克思强调变化和发展,也注意到了经济过程中的发明和创新,但是,由于马克思“着重于技术的视角而将历史视为朝着给定方向的进步过程”(17),他不能归于演化经济学家之列。为强化这一观点,霍奇逊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将自动终止演化的动力。因为按照系统演化的原理,只有多样性才能导致新奇,导致涌现,导致演化动力。“导致系统演化的动力来自差异性,因而不纯原则(the principle of impurity)是重要的。”(18)而马克思设想的单一性社会(共产主义)不会再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就消弭了演化的动力。(19)
2.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微观演化机制
霍奇逊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没有微观演化机制。“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是一个只有宏观层次的结构和力量,而对微观机制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20)霍奇逊的理由是,马克思没有考虑个体差异,也没有考虑个体能动性(21),只简单地用阶级和阶级的利益冲突来解释动力,主体只有简单的刺激—反应活动。(22)马克思“在如何变化这一问题上处理的过于含糊简单,只是找出了一个生产力的因素……马克思将阶级行动理解得过分简单,工人为了少的劳动时间和高工资待遇而斗争,资本家为了利益而压制”(23)。通过这一点,霍奇逊进而否定了马克思在本体论上是包容新奇的。因为“异质的、相互作用的个体才能导致新奇的涌现”(24)。他认为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异质性、创造性和能动性。“虽然马克思意识到了个人的存在,但是他相信人们是在系统的制约下行动的,这个理论缺少了对个体的分析,而是用系统的制约来解决全部问题,人们的确行动,但是他们行动的范围极大地受到既定系统的限制,这个限制被看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分析中,人类行为的心理和文化源泉都被低估了。”(25)简言之,就是缺乏能动性。
3.马克思理论与达尔文理论不相容
为了更全面、更有力地证明马克思经济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与演化哲学不相容,霍奇逊还直接用马克思对进化论思想的一些评述作为依据,认为马克思是“非演化”的。“尽管马克思在多处表示了对达尔文理论的欣赏,但这种欣赏和借鉴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达尔文的唯物主义、反上帝、反神创论的倾向,而不是和达尔文一样有着进化哲学观。”(26)在这里,霍奇逊使用了一个侧面例子,那就是,马克思极其厌恶马尔萨斯(例如,马克思曾经评价马尔萨斯是“一个被他们的敌人收买的统治阶级的辩护士,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而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正是马尔萨斯的个体竞争思想,使达尔文将竞争从种间竞争转移到种内竞争,从而解决了演化动力与种内多样性的选择问题,因而在演化思想史上,马尔萨斯具有重要地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如果没有马尔萨斯的内容,达尔文的学说将更加科学。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抛弃马尔萨斯脏水的同时也泼掉了达尔文的孩子”(27)。在《马克思和达尔文影响下的经济学》中,霍奇逊把马克思和达尔文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尽管都强调变化和发展,但马克思和达尔文在演化问题上的观念差异明显。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冲击或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而在达尔文理论中,无论个体还是物种甚至生态系统都不可能实现内在转换,进化必须发生在环境和个体的互动之中。“达尔文强调的是环境外部因素和内部变化因素的综合作用,这是关于多样性本体论的创新。”(28)霍奇逊列出了一系列历史证据来表明外生因素对于系统演化的影响,如,古希腊斯巴达和波斯的冲突影响了希腊的进程等。在霍奇逊看来,马克思是在研究封闭的、只有内因起作用的系统,而达尔文针对的则是开放的系统。
三、霍奇逊的三个判断是否成立
1.马克思是否预设了演化的方向和目的
马克思是否预设了人类社会的演化历程?对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已有过很多讨论。汤再新教授曾撰文指出,以马克思未来社会的描述攻击马克思本身就是一种误读。因为,(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未详细论述过未来社会。(2)他们之所以从未详细论述未来社会,是出于他们所坚持的唯物史观。(3)他们也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提出过一些预测性的见解。这种预测是因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看作是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4)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持的这种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决定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观点具有抽象的一般的性质,这些观点不会顾及实际发展过程中必将出现的具有不同特点和性质的过渡阶段(29)。
马克思是否终结了演化呢?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霍华德·谢尔曼和威廉·杜格对此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民主社会主义建立之后,进化还会继续下去吗?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就一般的答案而言,进化永远都不会有终点……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史前社会,因此,社会主义也就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进化时期的开始,事实上,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开始,都是将社会主义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事物。”(30)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运动是普遍的、永恒的和无条件的,马克思就是“借用了生物系统的发展规律,宣布资本主义社会的短暂性”(31)。
2.马克思是不是没有微观演化机制
霍奇逊判断马克思无微观演化机制的理由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阶级划分及经济利益冲突的处理方法;二是没有考虑主体能动性。这种判断是无法成立的, 《资本论》的主要任务在于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将重点集中在经济利益的选择和冲突上是必然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分类是一种分析抽象的必要,而不是说马克思认为不存在其他因素或者其他因素无关紧要。霍华德·谢尔曼和威廉·杜格指出:“只有在一个抽象的模型中我们才能发现纯粹的阶级关系……虽然马克思在他的基本经济模型的某些部分使用了一种简化的两阶级模式,在这些地方,没有必要引入许多阶级将论述复杂化,但马克思完全清楚,这是对现实的简化。”(32)至于马克思只描述了纯粹经济利益冲突这一点,霍华德·谢尔曼和威廉·杜格指出:“只有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常常将阶级冲突仅仅视为经济层面上的冲突,与此相反,现在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过去简单的教条持有批判态度,所关心的不仅仅是经济冲突,而且还有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阶级冲突。”(33)
认为马克思笔下的主体没有能动性,认为马克思把“人类被当成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囚犯,故而监狱的墙壁决定了结果”(34),更是有悖于马克思理论。马克思认为人既有能动性,也有受动性,现实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现实的人的活动既受既定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的制约,又能够选择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35)“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6)
3.马克思是否与达尔文理论不相容
马克思对于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性的判断和赞扬是有目共睹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在两个脚注中提到进化论,一个引证了达尔文在比较动植物的自然器官和劳动工具时的观点,另一个提出了应当从一种进化的观点写工艺史的观点。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的确写过: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但同样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也强调了达尔文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的重要性。
马克思之所以厌恶马尔萨斯,是因为马克思反对马尔萨斯把人口和其他社会因素割裂开来,将人口问题当作自然过程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根本不存在独立于社会生产条件以外的人口问题,如果说人口需要有一个数量限制,那也是对于一定的社会条件来说的。马克思说:“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37)这里,丝毫与自然选择等演化机制的判断无关。
至于马克思忽视外部因素的判断,更是难以成立。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一直坚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观点,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而且,马克思也没有排除霍奇逊所说的外在干扰与冲击,哪怕是偶然的。熊彼特曾写道:“马克思的综合的理论体系包括了所有那些历史事件,比如战争、革命、法律的变化以及那些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特征之一就是把这些历史时间和社会制度本身纳入经济分析过程,或者说,就是不仅把他们作为数据,而且把他们作为变量。这样,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国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英国的自由贸易、劳工运动以及其他任何特殊现象,殖民扩张,社会制度的变化,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民族和政治党派,所有这些都可以进入马克思经济学的领域内。”(38)马克思著作中不乏对随机因素冲击的描述: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39)
四、在生物学和哲学之间的普遍达尔文主义
——霍奇逊的主要疏漏所在
乔治斯库·罗根曾指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物理学范式和生物学范式。在经济学历史上,这两种范式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从马歇尔的“经济学的麦加在生物学”,到纳尔逊和温特的“我们是坚定的拉马克主义者”,生物学的影响一直存在于经济学领域中。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在经济学领域中获得支配性地位的是物理学范式。整个新古典体系,基本上就是牛顿——拉普拉斯体系的社会理论翻版。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理学范式的缺陷日益突出,而与此同时生物学范式的价值也日益彰显。“力学方法拒绝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知识数量变化和不可逆性,它使经济学陷于没有系统误差,没有累积发展的均衡图式之中,而生物学方法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它克服了这些缺陷,特别是,使用生物学方法的结果使得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归纳主义有了取代方法”(40)。
生物学之所以对经济学具有借鉴价值,主要在于生物系统和经济系统两者都是高度复杂的巨系统,但前者是生物演化,后者是文化演化,在动力、速度、能动性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经济思想史表明,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到两者的差异性,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具体理论和研究方法这两者的关系,就很难体现生物学范式在方法论上的借鉴价值,甚至会对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负面影响,典型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生物学内部也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也存在还原论和反还原论的争论。“生物科学本身就不是没有力学方法和归纳主义方法,很多生物学家就在尝试用物理学或化学术语解释生物学现象,”(41)例如,双螺旋的发现者沃森就认为生物学最终将建立在物理学和化学的基础之上。生物学理论不仅能为演化经济学提供启示,也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支持。在理性经济人这一问题上,正统经济学就是“凭借基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好像原理’的工具主义立场,他们可以方便地为其辩护并使理论免受假设非现实性的伤害”(42)。
霍奇逊显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避免单一的术语模仿,达到为演化经济学提供方法论基础这一目的,他才一再强调普遍达尔文主义的哲学意义。但是,他显然又有些游移不定。一方面,他不断强调普遍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关于方法论的解释,为此他不断阐明普遍达尔文主义与恩斯特·迈尔的演化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间的内在关联,以强化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时不忘生物演化,并不断回到生物学领地之中进行佐证。有意无意地,霍奇逊又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选择和动物的选择等量齐观,他写道,“正在选择的人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可以赋予人的特权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别的动物也在选择,蚂蚁收集并保存活的蚜虫,一头牛先吃最嫩的草。”(43)
正是由于在生物学和哲学之间的摇摆态度,霍奇逊在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时才过分地纠缠于自然科学的相似性,反而忽视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人的确具有生物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的演化也从属于生物演化法则。霍奇逊极度推崇的达尔文理论,也“并不是严格的公理,它是具有一个严格的演绎核心,但它独自是证明不了什么的,因而也就被置于大量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了”(44)。马克思并不否定生物分析方法的借鉴价值,“经济生活呈现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45)但他同样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是不同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文化进化的主要动因,文化系统内部或文化系统之间的斗争或竞争例如阶级斗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也是文化进化的重要动因。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朝着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的方向发展的,可以认为文化进化是由社会物质生产为导向的。”(46)
如果说霍奇逊始终坚持普遍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系统分析方法,那么他更不应忽视马克思在系统方法应用上的独创性贡献。因为“马克思使用系统、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动态、平衡、有序、随机等现代系统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巨大系统……《资本论》中的一整套科学范畴的联系发展和运动就是以系统思想为基本原则的”(47)。事实上,是马克思最先开创了一条能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法论路径,诸如新事象、选择、多样性等,都应该作为社会存在的特有范畴来加以解释,而无需特别求助于生物学。基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马克思清晰地完成了历史的宏大叙事,熊彼特曾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含义……在试图用马克思的论证方法来解释历史变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其他的困难,但只要承认生产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基本真理的魅力正存在于这种真理所具有的单一关系的严谨和简明之中。”(48)
马克思是否符合霍奇逊的普遍达尔文主义原则,或者说马克思是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这样的问题并无将马克思进行归类处理的含义。事实上,马克思不会因没有贴上演化经济学或某一其他流派的标签而失其光辉,也不会因为贴上了某类标签而从中增其伟大。剖析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理论的评价,一方面可以理解在西方社会科学语境下的马克思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我们发展马克思经济学提供思路。
注释:
①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载《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
②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③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4页。
④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载《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
⑤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载《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
⑥刘凤义:《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方法论探讨——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比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1期。
⑦参见霍奇逊2004,2006的论文:"Why We Need a Generalized Darwinism and Why a Generalized Darwinism is Not Enough",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61(1),September 2006,pp.1-19,"Darwinism,Causalit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11(2),June 2004,pp.175-94。
⑧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73、133页。
⑨Geoffrey M.Hodgson,"Generalizing Darwinism to Social Evolution:Some Early Attempt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39,No.4,December,2005,pp.899-913.
⑩Geoffrey M.Hodgson ,"Darwinism,Causalit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Vol.11:2,June,2004,pp.175-194.
(11)Geoffrey M.Hodgson,"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37,No.I,March,2003,pp.85-86.
(12)Geoffrey M.Hodgson,Economics in the Shadows of Darwin and Marx:Essays o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Themes,Edward Elgar,Cheltenham,2006,p.29.
(13)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
(14)Geoffrey M.Hodgson,"Marx,Engels and Economic Evolution",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Vol.19,7/8/9,1992,pp.121-128.
(15)Geoffrey M.Hodgson,"Varieties of Capit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eblen and Marx",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29,No.2,1995,pp.575-583.
(16)Geoffrey M.Hodgson,"Generalizing Darwinism to Social Evolution:Some Early Attempt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39,No.4.December,2005,pp.899-913.
(17)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
(18)Geoffrey M.Hodgson,"Economics and Systems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Vol.14,4,1991,pp.65-86.
(19)Geoffrey M.Hodgson,"Marx,Engels and Economic Evolution",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Vol.19,7/8/9,1992,pp.121-128.
(20)Geoffrey M.Hodgson,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gency,Structure and Darwinis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ism,Routledge,London,2004,p.188.
(21)霍奇逊的这一观点直接受凡勃伦的影响,参见 Geoffrey M.Hodgson,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gency,Structure and Darwinis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ism,Routledge,London,2004,p.239.
(22)正是基于这一点,霍奇逊对马克思和凯恩斯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在评价凯恩斯时霍奇逊指出,“鉴于凯恩斯受到了关于人类意志和血气冲动的不确定性,以及创造性和新事象的能力等思想的影响,他达到了NEAR演化经济学范式的一个标准。”见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23)Geoffrey M.Hodgso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eblen and Marx",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29,No.2,1995,pp.575-583.
(24)Geoffrey M.Hodgson,"Economics and Systems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Vol.14(4),1991,pp.65-86.
(25)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如何忘记了历史——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定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26)Geoffrey M.Hodgson,"Marx,Engels and Economic Evolution",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Vol.19,7/8/9,1992,pp.121-128.
(27)Geoffrey M.Hodgson,"Marx,Engels and Economic Evolution",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Vol.19,7/8/9,1992,pp.121-128.
(28)Geoffrey M.Hodgson,Economics in the Shadows of Darwin and Marx:Essays o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Themes,Edward Elgar,Cheltenham,2006,p.32.
(29)汤在新:《澄清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载《南方经济》2005年第2期。
(30)霍华德·谢尔曼,威廉·杜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2-183页。
(31)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和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79页。
(32)霍华德·谢尔曼,威廉·杜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33)霍华德·谢尔曼,威廉·杜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34)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如何忘记了历史——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定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3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5页。
(38)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3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页。
(40)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和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9页。
(41)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和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69页。
(42)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和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8页。
(43)转引自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载《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
(44)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和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70页。
(4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页。
(46)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和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61页。
(47)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和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5页。
(48)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标签:经济学论文; 达尔文论文; 社会达尔文主义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本体论论文; 进化论论文; 系统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