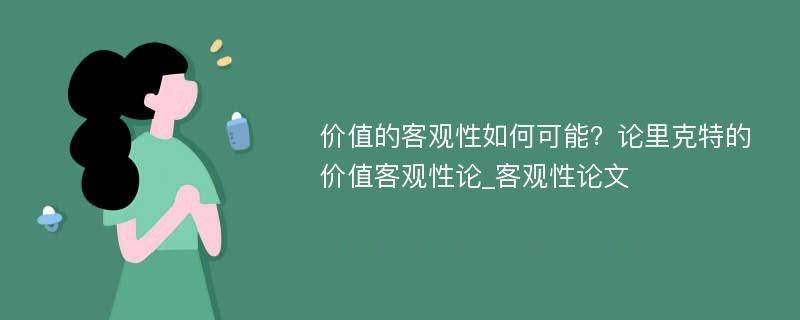
价值的客观性何以可能?——论李凯尔特的价值客观性论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观性论文,价值论文,尔特论文,李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1 一、问题的提出 就国内价值哲学的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一股价值研究热,但在处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时,很多学者意识到了传统认识论运用于价值论研究的不足,却无法从思维方式上确立价值论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特殊性,因而也无法从认识论中“伸展”出价值论研究的方法论,最后还是不得已继续借用传统认识论的术语,如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事实、价值真理与价值的主体客观性问题等等②。正是由于缺失对价值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自觉提炼,国内价值论研究陷入了某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当中。 事实上,自休谟以来,“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罗素甚至认为两者的关系构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一直是由两个不调和地混杂在一起的部分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这两部分未能充分划分清楚,自来是大量混乱想法的一个根源”②。与之相似,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科尔斯戈德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视角,也揭示了“价值”的特殊性:“价值是一个难解之谜,自从哲学诞生之后,哲学家们就一直想揭开谜底。”③因此,与价值相关的“规范性问题”,“不仅产生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之中,也产生于任何哲学领域”,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本身可能是普遍的人类问题或者普遍的人类处境”④。 作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简单化约的两重性的存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而如何正视并在何种意义上保持两者的张力则是问题的难点。具体来说,首先需要基于更大的参照系,以能够将两者纳入到一个可以比较的平台之上,然后再确立两者的有机关联与沟通枢纽,进而论证价值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准此,对价值论问题的探讨才能真正有枝可依、有章可循。正是在这里,新康德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作为文德尔班的学生,李凯尔特在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中似无多少创建,一般认为他最多也不过是发展了其老师关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区分而已。但在《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的英译者欧克斯(Guy Oakes)看来,如果说文德尔班确立了历史科学概念所关注的个别性与方法论的特殊性,而拉斯克在概念与实在之间设置的“非理性裂缝”(hiatus irrationalis)为历史科学概念的构成提供了脚手架,那么,李凯尔特则通过回应这个“裂缝”所导致的问题确立了把握历史个别性的方法论基础。⑤本文尝试以李凯尔特历史科学的奠基路径为视角,对其作一个批判性的考察,以推进价值论问题的研究。 二、历史科学概念的价值担当 李凯尔特认为,历史科学所把握的现实的个别性只有与文化价值相关联时,才能真正取得自己的科学性:“在无限众多的、个别的即异质的对象中,历史学家首先研究的,只是那些在其个别特征中或者体现出文化价值本身或者与文化价值有联系的对象。”正是通过文化所固有的价值以及通过与价值的联系,“可叙述的、历史的个别性概念才得以形成。”⑥ 由此可见,李凯尔特在这里引入了文化价值这一新的元素,其目的是“借助于这个概念来形成个别化的概念形成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从那纯粹的、不能加以科学表述的异质性中把可表述的个别性提取出来”⑦。于是,历史科学能否把握“个别性”的问题,便转变为文化的“普遍价值”与历史的“个别性”之间的结合可能性问题。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对“个别性”的抽象,文化事件的意义却完全依据于它的个别特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用个别化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科学;同时,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某种普遍化的方法,历史科学的普遍化就是文化价值的普遍化。但文化价值的“普遍性”能否与“个别性”结合起来?李凯尔特的回答是肯定的,他首先分别对“个别性”与“价值”作了规定。 就“个别性”而言,李凯尔特在“概念”与“现实”的二元关系中,区分了两种“个别性”:一种是完全不能被任何概念理解的、纯粹的异质的“个别性”;另一种是对于现实的一定理解,是可以被纳入概念之中的“个别性”。前一种个别性始终大于、高于、多于后一种个别性。而后者根据所纳入概念的类型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自然科学概念由以抽象出来的“数量个别性”,与历史科学概念中所包含的通过价值联系所形成的“个别性”。⑧ 就“文化价值”而言,在李凯尔特看来,一方面,价值不同于现实,具有某种独立性;另一方面,价值又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概念的普遍性。就前者来说,“价值不是现实,既不是物理的现实,也不是心理的现实。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而不在于它的实际的事实性”⑨。即价值是某种相对独立的东西,如果它附着于对象,则使得对象变为财富;附着于主体的活动,则可以使得主体的活动变成评价。就普遍性来说,“文化价值或者事实上被普遍地、即被所有的人评价为有效的,或者至少被文化集团的全体成员期望为有效的”⑩。正是这种普遍性,使得历史概念的形成排除了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因而是历史概念形成的“客观性”依据。从这个意义说,文化价值的普遍性显然不同于自然科学意义的普遍性。因为价值的普遍性与现实的个别性之间不仅没有龃龉,而且能够相得益彰,“虽然我把个别现实和普遍价值联系起来,但是个别现实并没有由于这个缘故而变成普遍概念的类的事例,反之,它始终是由于其个别性而具有意义”(11)。 如果李凯尔特所谓的历史科学概念构成中的“普遍的个别性”是可能的,那么,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及其普遍化方法,历史科学便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作为文化科学,它研究的是与普遍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而作为历史的科学来说,它们则从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方面叙述对象的一次性发展。(12)从这个意义说,“普遍价值”与“个别性”便是历史科学概念“一体两面”的特征。而同时,这种双重意义又没有否认并消解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只要历史所研究的是那些一次性的、个别的现实事物本身,而它们又是独特的现实事物,我们对它们确有所知,那么历史就是“现实”科学;只要它所采取的对众人均为有效的纯观察立场,只要它仅仅把那些因为和某种一般价值相联系才成为重要的或本质性个别现实事物或历史的不可分个体作为自己表述的对象,那么历史科学就是现实“科学”。(13) 正是坚信“普遍价值”与“个别性”之内在结合的可能性,李凯尔特特别反对将“历史学”当作“经济史”或者“自然科学”的做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种做法是建立在一条完全随心所欲地选择出的原则之上的。”(14)他将孔多塞与唯物史观都归于这种做法当中。他认为,后者将“历史”视为“唯物主义”,“根本就不是一种经验的、与价值相联系的历史科学,而是一种以粗暴的和非批判的方式臆造出来的历史哲学”。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哲学把价值实体化为一种事实的存在,并将经济文化之外的一切都变成了纯粹的“反映”,“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一种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从形式方面表现出柏拉图唯心主义或者概念实在论的结构”(15)。如果结合李凯尔特所处时代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背景,他的批判无疑表现出时代的特性。 三、历史科学价值的客观性论证 如此说来,如何论证文化价值的普遍性沟通历史的个别性的合法性,并避免主观随意性的质疑,进而论证这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普遍的个别性”的客观性,便是历史科学能否奠基的关键。这里的难点在于,由于价值始终是针对一定范围的人有效,因此总是有“主观随意性”之嫌,因而历史科学的客观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客观性”(16)。李凯尔特通过分别批驳自然主义的客观性、经验论的客观性与形而上学的客观性,以逼问出价值的客观性。 自然主义对价值客观性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们看来,只有一门科学,即自然科学,与价值相关的历史科学由于其主观随意性,根本不配称为科学,如果一定要称历史科学的话,也“只有当赋予历史学以自然科学的或者至少是与价值无关的基础时,才可能使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17)。李凯尔特指出,这种从自然主义出发构造历史科学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原因在于,“普遍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不仅从概念上说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前者表述的是普遍之物,后者表述的是个别之物,而且也因为前者忽视一切附着于实际材料之上的价值差别,反之,后者却在把对它而言的本质之物与非本质之物区分开时不可能不考虑价值”(18)。因此,自然主义无法理解客观价值与历史科学的客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便没有有效性。如果将自然科学视为“一阶的”,那么,历史科学则是“二阶的”,“关于一种方法的科学性或非科学性的判断是一些价值判断,因此它们本身已经预先假定一个价值标准,科学的客观性正是按照这个标准加以测定的”(19)。 经验的客观性是指以经验的有效性作为判断客观性的标准。但是根据李凯尔特对概念唯名论的批判,概念并不通过经验事实的反映便可实现,而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同是对经验事实的加工与改造,且都包含着超越经验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够说历史科学就其客观性而言比自然科学有任何逊色之处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原因在于,相对于经验来说,历史科学概念所应当具有的绝对的普遍有效性与自然科学概念所具有的普遍规律的有效性,都是概念的客观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种是在经验上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这种价值以如此方式与对象相联系,使得对象被结合为历史个体),另一种是“在经验上得到普遍认可的比较观点(这种比较观点把本质之物与非本质之物区别开)”(20)。因此,就概念的形成来说,“与价值相联系的历史概念形成中起指导作用的价值,在经验方面并不比自然科学为了从经验方面对各种对象进行比较所采用的那种观点,具有较少的有效性”(21)。 与经验的客观性相比,形而上学客观性假定有一种绝对的、超越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实在,后者作为本质处于现象世界之后,这就以一种不同于经验客观性的方式提出了客观性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李凯尔特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形而上学恰恰是反历史的。原因在于,“在那种情况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以相同的方式或者是历史的,或者是非历史的,一切个别之物都失去了它的独特意义。它变成了类概念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事例,类概念所表现出的是世界精神的合乎规律的发展中某一阶段的普遍本质”(22)。 如果承认这些价值的存在及其有效性,那么,参考这些价值形成的概念便具有科学的客观性,甚至是人们能够期望的那种最高的客观性。“相反,如果这些价值不是有效的。那就根本再也不能谈论什么科学的客观性。”(23)正是在这个意义可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的客观性,都只能建立在理论价值的有效性之上,而绝不能建立在纯粹现实的存在之上。(24)这样一种客观性摧毁了自然主义的神话。如果基于价值的有效性来考察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话,就不难发现,自然科学其实也是历史的文化产物:“不仅自然科学是文化人的历史产物,甚至‘自然’本身从逻辑的或者形式的意义而言也不外是理论的文化财富,是一种借助于人的智慧而对现实所作的有效的、即客观的有价值的理解。自然科学恰恰始终必然以附着于其上的绝对有效性为前提的。”(25) 四、李凯尔特对价值客观性的先验论证 综上所述,李凯尔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康德的问题:“普遍的个别性”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又是如何可能的?正如康德从“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引出“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自由的实在性进行论证一样,李凯尔特是通过对自然科学概念中对普遍性与个别性关系的处理及其界限的考察,来论证价值客观性的。 但是,“康德的自由理论是他的哲学中最难以解释,不用说也是最难以为之辩护的一部分”(26)。原因在于,康德所论证的自由的核心是先验自由的观念,这种自由的因果性不同于自然的因果性。然而,“自由概念对于一切经验主义者都是一块绊脚石,但是批判的道德哲学家理解最崇高的实践原则的关键”(27)。而后来者对于康德自由理论的先验方法充满质疑,甚至认为他最终放弃了对先天概念提供先验演绎的批判要求,从而“陷入了一种实践理性的独断论”(28)。同样的批评也存在于对李凯尔特的历史科学的评价上,很多学者认为李凯尔特所谓的价值“是某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神秘离奇的东西,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虚构”(29)。这也是长久以来,李凯尔特历史科学的奠基路径以及他对价值客观性的论证始终没有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 但康德哲学的原创意义,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所开创的先验方法。这种方法表现出某种调和、超越的姿态,或者借用柄谷行人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跨越性的批判”。具体而言,康德在知识论中“调和”的是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分歧,以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奠基;在伦理学中,康德面对的则是中世纪后期以来的理性主义(intellectualism)与意志论(voluntarism)之间的争论。对康德来说,理性主义传统没有充分考虑到人类理性本身的有限性,将某些无法认知的超越原则作为我们自身的原则,从而陷入了独断论,且导致他律,使得自由不可能;意志论则无法提供一种普遍有效的标准。基于此,康德伦理学的任务就要“超越”两者,为政治法律提供一个规范性的基础,使得“这一基础既能够体现人的意志活动中的自主性,又能够体现人类理性活动中的普遍必然性”(30)。而通过实践理性的运用,特别是对“自由因果性”与“自然因果性”的区分,康德使得意志论与理性论也得以综合。这种综合正是实践理性中的“先验方法”。正如墨菲所言,“康德既没有以一种功利主义的方式通过记录特定类型的偏好的频率以期发现某些基本的道德价值,也没有像古典的道德形而上学那样,试图通过表明那些价值是从不可靠的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前设中获得的,从而发现那些价值。他的方法既不是归纳的,也不是演绎的,相反,如同一个熟悉《纯粹理性批判》的人所预料的,康德是通过一种先验论证来论证这些价值的”(31)。如果说,在思辨理性的语境中,自由因果性是一个否定性的、无法加以贯彻的概念,那么,通过实践理性语境中的先验论证,自由因果性的客观实在性才第一次得到了证实。(32) 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显然处在“回到康德”的强大“气场”之中。相对于朗格等对康德的另一种阐发方式,西南学派更重视康德伦理学与价值论。文德尔班曾说:“哲学虽然走过一条极其崎岖不平的弯路,但终于能够回到康德关于普遍有效的价值的基本问题上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33)正如欧克斯所言,在西南学派中,李凯尔特的贡献在于为价值的客观性提供了一个方法论论证。(34)他以自然科学的概念形成及其界限作为参照,逐渐引申出价值的普遍性与历史科学之个别性的关联方式。这种“普遍的个别性”迥异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与“个别性”,原因正是在于“价值”的关联。但是这种价值的客观性既不是自然主义的客观性,也不是经验的客观性,更不是形而上学的客观性。如上所论,李凯尔特对这种价值客观性的论证过程正是康德先验方法的运用。但是李凯尔特对先验的方法的运用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坚定的现实根据与充足的理论逻辑:就前者而言,正如康德将“道德律”视为一种“理性的事实”,因而能够作为“自由”演绎的基础一样,现实生活中也广泛存在着“价值”这种“理性的事实”,因为“文化价值或者事实上被普遍地、即被所有的人评价为有效的,或者至少被文化集团的全体成员期望为有效的”。(35)人们在阅读历史科学的著作时,“肯定把宗教、教会、法律、国家、科学、语言、文学、艺术和经济组织等等所固有的文化价值理解为价值,因而不把它看作主观随意的”(36)。就后者而言,李凯尔特对价值的客观性论证始终是在“概念”与“现实”的“非理性裂缝”中,以自然科学作为参照,逐层展开的。这种展开过程也是以一种反证的方式对价值之客观性的逼问过程。而一旦成功,那么,价值的客观性便不仅是事实真理性的根据,也是世界之客观实在性的根据,从这个意义说,“休谟问题”便由此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解决。 ①李德顺:《价值论—— 一种主体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33页。 ②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395页。 ③④科尔斯戈德:《规范性的起源》,杨顺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2页;第303页。 ⑤(34)Guy Oaks,Introduction:Rickert's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The Limit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Natural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viii,p.ix. ⑥⑦⑧⑨⑩(11)(12)(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9)(35)(36)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涂纪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79页;第78页;第79页;第83页;第91页;第90页;第91页;第103页;第104页;第122页;第137页;第151页;第154页;第161页;第159页;第176页;第189页;第190页;第128页;“译者前言”;第80页;第123页。 (13)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37页。 (26)(28)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导言”,第1页;“导言”,第4页。 (27)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6页。 (30)(31)杰弗里·墨菲:《康德:权利哲学》,吴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代译序”;第42页。 (32)俞吾金:《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3)冯平主编:《先验主义路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