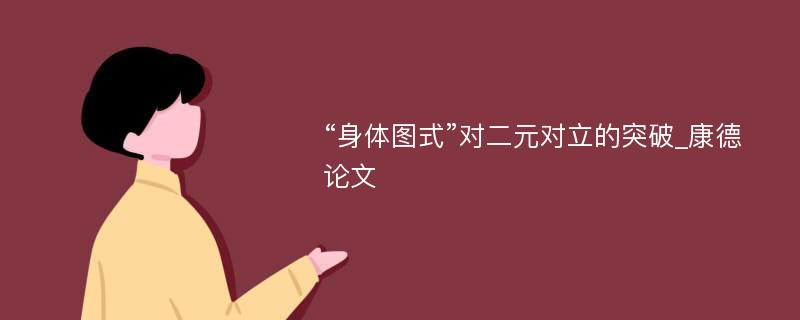
“身体图式”对于二元对立的突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式论文,对立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7-0079-04
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对于“身体”的阐发,使其从现代科学所设定的“客观身体”——这一机械形象中解脱出来,成为充满“灵气”的处世基点,这一分析对于我们去伪存真、认清“身体”之本色有着积极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庞蒂依循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哲学家的思路,以“身体”为据点展开了对于笛卡尔“我思”哲学的批判,这有助于我们跋涉出以“我思”原则为立论基础的认识论美学带来的局限。“身体”由此成为我们建构美学现代形态的理想支点。
一、身体:我们处世的真实基点
借助现象学还原,梅洛-庞蒂指出,我们与事物最为真实、最为致命的接触并不是“我思”,而是“我看”,因为我们与事物最为源初的接触是通过我们的眼睛及其它器官发生的,“我们看事物”、“我们知觉事物”因而是一种确凿的达到事物的方式,“看”与“思”同样毋庸置疑,而且是对于“思”的一种挑战。“看”就是进入一个自身显现的存在之宇宙,因为,“看”一个对象就是居住到对象之中,根据事物面向它的那一面来把握它,在其中,“看”与存在是互相遮掩的,例如,我们只是也只能看到箱子的一个或几个面,而非全部,但我们却说看到了一个箱子。“看”就这样“遮掩”了事物,事物也就这样“遮掩”了“看”。这就是我们的眼睛、身体通过“看”、“知觉”与事物形成的交流,其中孕育着我们通过身体与事物相互开放形成的共有关系。
与事物的接触勾勒出我们的生存真实:我们必然“在世界之中”(l'etre-au-mondu),在我们的身体通过行动开拓的意向空间中与世界彼此开放。身体决定了我与这个世界必然的联系,因而成为我们处身于世的基点[1]。
“我们的身体”,即“己身”(le corps propre),是知觉主体,是“有所体验的身体”(le corps vecu)。这是一种有意向的身体,绝非机械的、呆板的肉体,因此也可称为“身体-主体”:作为“两层存在”,“身体-主体”既可主动感知,又可被感知,这即是内蕴的“可逆性”。庞蒂通过扬弃“身体图式”这一生理学术语来分析、阐明这一“身体-主体”。
简而言之,生理学往往将“身体图式”理解为一个表象中心,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体验的概括,梅氏认为,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将“身体图式”理解为在我们感觉时对于我们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这其实已经趋近于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完形”。不过,仅仅认为“我的身体是整体优先于部分的一个现象”[2],还不足以解释“身体图式”如何作为“一种新存在”:身体图式不是存在着的身体各部分的简单联合,也不是对存在着的身体各个部分的整体意识,而是根据整体计划的价值,主动地把存在着的身体各部分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是“动力的”,它表明我们的身体为了某个实际的或可能的任务而向我们呈现的姿态。
通过分析运动机能障碍等病例,梅氏进一步证明“身体图式”对于人类活动所起的支撑作用①。梅氏指出,病人能够完成具体运动,说明病人并不缺乏运动机能,也不缺乏思维,之所以不能完成抽象的活动,就在于病人缺乏正常人的运动和运动表象(思维)之间的有效黏合,换言之,在正常人的运动中,运动与思维被某种强大的能力所把握,这种能力可以使我们轻而易举地完成抽象运动,这就是身体对于运动与思维的整合,即身体的“运动计划”,或曰“运动意向性”的有效展开。运动进而实现了与其背景的合二为一:运动背景内在于运动并激起运动,且在每时每刻支撑着运动的展开。
身体的“运动计划”可以使世界集中在一个点上,这使抽象运动得以可能:因为在紧急、必需等等的具体活动之外,我们依然拥有我们的身体,这确保了我们可以接受抽象活动的背景,进而完成它。因此,我们发现所谓的“意识生活”(包括认识、知觉、欲望等)是由某种力量主导的,这一力量正是身体图式在支撑我们行动时的“意向性”结构,梅氏将之称为“意向弧”。
在疾病中,患者的意向弧“变得松弛”,这一症状的表现就是身体失去这种主导性:患者因此受到现实的束缚,他缺乏自由,特别是缺少适应环境的一般能力和一种具体自由,于是产生所谓的“运动障碍”。进一步而言,正是“意向弧”的松弛导致了意识的错乱,而意识一旦继续错乱下去,就形成病变。这种疾病形成之后,在侵袭患者的视觉、语言等领域时,不但破坏视觉表象或“本义的视觉”,而且还会损害“俯瞰”同时出现的众多事件的能力,并且改变确认物体或意识到物体的方式,于此疾病也就完成了对于内容的分解。
患者能够完成自己曾经的工作、能触摸被蚊子叮咬的鼻子,就是因为在这些“习惯”中,“身体”理解了运动,把握住了运动的意义;患者之所以无法按医生的要求去触摸鼻子,也是因为身体不再能“理解”这一抽象运动的意义,意识因而不再能凭直觉实现这些运动。疾病于此也就完成了对于“意识”的还原,意识并不是“我思”,而是“我能”(Je puex)[3],换言之,意识对于身体有着绝对的依赖,身体就是梅氏所说的“意识的能动超验性”所在[4]。最终说来,疾病在损害这种结构的同时,又用经过特殊缺陷改造的新结构替换原有结构,疾病因此不仅仅是我们可见的种种障碍,而且还是患者的存在方式。这正是身体决定的“处身于世”这种存在方式的脆弱性的体现。
二、“身体”作为源初意向性的所在
在康德的思考中,人在认识外界时必须通过知性范畴来把握“感性直观”所得之物,但是,这分属“感性”与“知性”的两者如何沟通?康德提出了“图式”概念,并视其为范畴与现象之间的中介:“它一方面和范畴同质,另一方面和现象同质,并且这样就使得前者在后者上的运用成为可能。这种中介性表象必须是纯粹的,即,抽离了所有的经验的内容,然而它必须在一方面是理智的,在另一方面是感性的”[5]。
在“整体统合性”、“先在性”等方面,“图式”与“身体图式”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甚至相通性,但是,“图式”固守于思维认识层面,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则是人之身体所有的一种结构能力,该理论的基础是梅氏对于现代心理学、生理学的批判性解读。两者本质上的差异决定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康德在认识论领域的哥白尼革命虽然使得认识论放弃探讨主体的知识是否能与对象相符合,转而探寻对象如何为主体的先验认识机能所统摄,也就是说,“图式”于此所解决的正是对象与认识如何衔接这一关键难点,但是,这决定了我与世界还是一种彼此外在对立的认识关系;“身体图式”则意味着我走进世界,世界因此向我开放,我也向世界开放,所以,我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嵌入”,身体决定了我对世界是一种“体认”。这种生发于我与世界彼此“嵌入关系”中的体认,注定了要放弃认识论所追求的明晰,也就是说它无法避免我们通过身体理解世界带来的模糊性,而且这一体认处于不断开放的状态中。
两者的差异恰恰源于一个相同点:即康德也关注过的“意向性”。康德在《对唯心主义的驳斥》中已经指出,内部知觉如果没有外部知觉则是不可能的,诸多现象联结而成的世界已在我的统一性的意识中被预料到,这是我实现自己作为意识的手段,其实这就是要说明“一切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也是庞蒂同时代的哲学家萨特展开自己思想的支点。在梅氏看来这种思考最大的问题在于设立了“我”(意识)与世界的二分,而且世界在其中是被预设好的,所以,这是一种给“意识”规定了目的的绝对思维,康德的做法就是将其加在人的意识之上来说明人的意识如何关照世界,这其实是一种隐在的目的论。
胡塞尔认为,首先应该走出这种预设,将意识理解为世界的计划,也就是说,意识并不包含、拥有世界,但是意识是不断走向世界的。世界显然溢出了意识的预料,它是一个前客观的个体。因此胡塞尔区别了“行为的意向性”和“生产性的意向性”(fungierende intentionalitat),前者是康德已经谈到的我们的判断和我们有意识选择立场时的意向性,而后者在我们的愿望、评价、我们所看到的风景等等中表现得要比在我们的客观认识中更为明显,显然,这种“生产性的意向性”更具本源性,正是它形成了世界、我们的生活本身所有的自然而然的统一性,因此,通过“生产性的意向性”所获得的对于世界、生活等等的理解倘若可以算作一种原文的话,那么我们的认识(包括科学认识)只是由这一原文翻译而成的译本,它需要前者为基础。根据“生产性的意向性”,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也最终回到其模糊状态,任何分析也都不可能使之变得清晰。
胡塞尔的分析虽然最终也逼近了“有意向的身体”,但是胡塞尔却让其服从于先验意识,梅洛-庞蒂认为这种做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意识与对象的关系问题,因此,在胡塞尔的论述中,“自然”时而作为绝对精神的相关物而显现,时而又作为原初的、已经精神化的层面而出现[6]。换言之,我们与对象的关系依然让人困惑。梅洛-庞蒂的研究工作则是要证明身体才是这种源始意向性(即胡塞尔所谓的“生产性的意向性”)所在,这就为康德、胡塞尔在意识层面探究的行为意向性找到了一个更为原始、真实的始基——“身体”或曰“身体图式”。换言之,康德思考的是我们对现象所拥有的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而梅洛-庞蒂探究的正是我们在与世界的相互开放中一切行动之所以可能的先在界域,这显然是更为源初的。
三、“身体”与美学中的二元对立
鲍姆嘉通在用“Aesthetica”命名“美学”或曰“感性学”时,明确指出“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7],“根据由它的基本意义而得出的名称,感性认识是指,在严格的逻辑分辨界限以下的,表象的总和”[8]。这种对人类的认识活动的设想,秉承着理性主义传统:“我们就把一般感性规则的科学,即感性论,和一般知性规则的科学,即逻辑,区分开来”[9]。
依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明白:“认识”都有其感性基质,“逻辑学”所代表的知性科学的感性基质只是隐而不显而已。因此,“只有知性才提供规律”[10]这一说法显然是一种并不可靠的夸大其词。深入来看,这种对于知性的迷信正是认识论美学的根本局限: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知性”,在主体层面解读审美,这恰恰忽视了“审美对象”在审美活动这一现象场中的作用,即没有充分理解到对象作为“一种向我的认识开放的超越”[11],是这一场域中限定我们,并促使我们不断超越的交流者。
对于认识的还原有助于我们深入审美活动如何实现感性与理性的融汇这一难题,即“美学的中介性”[12],对于这一问题,美学家们虽然有着深刻的探究,但还是遗留下了诸多困难。康德的解读应该说是其中最具权威也最为深刻的②。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有两种“判断力”:“规定性的”和“反思性的”[13],“规定性的判断力”是指知性将表象归属于明确概念的判断作用,而审美活动所涉及的反思判断力,却能使“特殊”不再停留于自身,而是力求“普遍内涵”,也即康德所谓的“寻找普遍”。康德进一步指出,在审美活动中,想象力得以在反思判断力的运用中展开,此时,想象力不是“再生的”,而是“被看作生产性的和自身主动性的(即作为可能直观的任意形式的创造者)”[14],也就是说,想象力作为主动的创造者,在经验层面杂多的特殊之中建立一种“秩序”和“形式”,使纷呈的特殊具有了一种普遍性,这也就是所谓“无规律的合规律性”,当然,这其中的“规律”绝非知性所探求的“客观规律”,因为此时,“知性是为想象力服务的”[15]。
这样,基于个人的鉴赏判断就可以要求一种普遍赞同。这里的基础正是康德美学中的重要概念——“共通感”,但是“共通感这一不确定的基准实际上是被我们预设了的……至于事实上是否有这样一个作为经验可能性之构成性原则的共通感,还是有一个更高的理性原则使它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调节性原则,即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才在我们心中产生出一个共通感来……我们还不想也不能在这里研究”[16]。于此,无法论证只能预设的共通感成为不可逾越的极点。
康德认为在审美活动中,“对象恰好把这样一种形式交到想象力手中,这形式包含有一种多样的复合,就如同是想象力当其自由地放任自己时,与一般的知性合规律性相协调地设计了这一形式似地”[17]。但是,康德的思考却不得不停止于“想象力”与“知性”之间的矛盾:“说想象力是自由的,却又是自发地合规律性的,亦即它带有某种自律性,这是一个矛盾”,因为,“只有知性才提供规律”[18]。
身体图式揭穿了“只有知性才提供规律”这一谎言,祛除了康德语气中的不确定成分,进而为“想象力”找到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想象力并不仅仅是内在的精神官能运用的一种主观性条件,而是身体自身行动的一种能力,换言之,可以沟通不同官能作用的“想象力”,正是身体所特有的整合能力,在审美活动中,与对象交流时,最为积极、充分的展现。
因此,“共通感”并不能依靠“一个更高的理性原则”来假定,而是应该从身体与对象交流及身体间的同构性,即“身体间性”(intercorporeité)来寻求依据。身体、对象都是审美活动“这一独特力场的不同区域”[19],进一步而言,在审美活动中,对象作为“一种开放的超越”,在与我们的身体不断交流的同时,刺激并诱使着我们身体的整合能力(即想象力)不断趋向更高层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审美活动中,会出现官能的挪移,即“通感”这一奇妙的体验:“我们看见了物品的深度、滑腻、柔软、坚硬——塞尚甚至说味道”[20]。也就是说,审美活动恰恰摆脱了所谓“知性”的束缚,使我们与对象的交流回到最为真实的“物我交融”的原初状态。进一步而言,审美活动正是身体整合各个部分参与其中,与对象由意向性牵连,形成一个“力场”的过程:于其中两者相互开放,在不断超越最初交流的同时,使得交流继续深化。
审美活动之所以能够使得我们进入原初知觉,进而与对象进行深入交流,正是因为身体作为一个“两层存在”对于审美活动起到了支撑作用:“一层是众事物中的一个事物,另一层是看见和触摸事物者”[21],身体使得我们既是可见者、可触者,同时又是被见者、被触摸者,而且这种转化永不停止。身体这一“可逆性”使得我们可以进入物的世界,进而使得对象绽现自身,审美正是这种交流得以深化的表现。身体与其他身体、事物的这种“可逆性”交流,在庞蒂看来正是——“肉”(chair)——“这一存在的原型”[22],作为一切存在者的源泉、要素、模子的具体化表现,这种“可逆性”也就使得我们成为拥有“普遍”的“特殊”,因为“肉的这种源初特性通过处在此时此地而向所有的地方永恒地播散,通过作为个体而成为既是具体的,又是普遍的”[23]。最终说来,“共通感”根源于审美活动使得我们冲破重重阻挠,所回到的“我-他”、“人-物”相融为一的源初状态。
注释:
① 例如枕叶受伤的施奈德,出现了被精神病学称为精神性盲的病证,该病患者可以顺利完成许多习惯活动,例如他可以取出火柴点灯、掏手绢擦鼻涕等等,甚至可以从事自己原来的工作——制作皮包。但是,他却无法按医生要求去完成运动。
② 席勒在“第二十七封信”(《审美教育书简》)中,虽然竭力论述“审美王国”是从“暴力王国”过渡到“道德法律王国”的必经之途,但是却流于空泛,难以服众,这正是其游戏说的缺憾;黑格尔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来定义美的本质时,也注重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但是,在对于审美活动中如何实现这一问题,却没有展开,原因在于其对于“人是心灵”的完满论述:“人作为心灵,却复现他自己,因为他首先作为自然物而存在,其次,他还为自己而存在,关照自己、认识自己、思考自己,只有通过这种自为的存在,人才是心灵”(《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8-39页)。
标签:康德论文; 美学论文; 想象力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心理学论文; 图式理论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