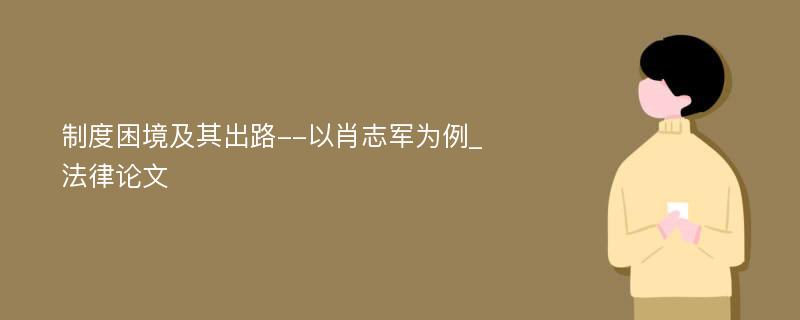
制度的困境及其出路——从肖志军案切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困境论文,制度论文,肖志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11月21日下午4时左右,怀孕41周的22岁女子李丽云因呼吸困难被以夫妻名义与其长期(三年)同居的肖志军送到北京某医院进行治疗。医生检查后发现孕妇及其体内胎儿均面临生命垂危,建议进行剖腹产手术。虽经各方多次劝说,肖志军始终拒绝手术,并在手术通知单上写下“拒绝进行剖腹产手术”的字样。在医院常规抢救3小时过程中,医院紧急请该院神经科医生确认肖志军精神正常,并紧急上报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得到的指示为: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最终,孕妇及体内胎儿不治身亡。2008年1月24日,死者父母和代理律师一起向朝阳法院立案庭递交了诉状。死者李丽云的父母正式提起民事诉讼,将朝阳医院和肖志军一并告上法院,要求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停尸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1000元。1月3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此案。①
肖志军事件经过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后,争论文章迅速涌现、络绎不绝且相互转载。一时间,公众舆论汹涌如潮。有人谴责肖志军愚不可及、荒唐之至,有人责备医院道德沦丧、见死不救,有人认为肖志军“可恨”之外尚有“可怜”之处,有人责怪“官僚主义”滋生“袖手旁观”……在讨论之中,法律、权利、道德、人情、责任、制度等话题无所不及,大大拓展了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通过在中国宪政网上对2007年度全国发生的、具有影响的21个宪法事例进行在线投票,并结合专家评议意见评选出了“07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肖志军事件“榜上有名”。②那么,这个事件为什么能引发这场集体性的大讨论呢?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主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如果根据该法条的规定,医院在对患者进行手术之前,要区分四种情况:(1)患者同意+患者家属或关系人同意并签字;(2)无法征求患者意见时,只需取得患者家属或关系人同意并签字;(3)无法征求患者意见+家属或关系人不在场时,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并在取得上级领导批准后进行手术;(4)在(1)(2)(3)情况之外的其他特殊情况下,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并在取得上级领导批准后进行手术。
在当时患者李丽云已经昏迷的情况下,该医院需要对她进行剖腹产手术,便首先将这种情形归纳到了以上的第(2)种情况,即必须经过患者的“家属或者关系人”肖志军的同意并且签字。然而,事与愿违。尽管经过了院方的苦口婆心地劝说,肖志军仍然固执地拒绝进行手术,并且在手术通知单上写下“拒绝进行剖腹产手术”的字样。如果医院严格遵守法律,无疑合乎了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但是,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尸两命”的结局,这就与医疗机构的天职——救死扶伤——相违背,也与法律所追求的实质合理性不相符合。医院的这种“墨守成规”行为的形式合理性,与“救死扶伤”的实质合理性之间的严重对立冲撞,刺激了人们的道德直觉,引发了集体性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有的律师从法律专业角度提出对法律的见解,有的学者从伦理学角度对医生进行指责,有的政协委员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为国家献计献策……在本文中,笔者将论证,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在解决此类案件中陷入了困境,其表现为:我们只能在法律文本中对一些令人神往的制度垂涎三尺,却在现实中寻觅不到它的踪迹。而通过制度革新走出制度的困境仍然不是一条一劳永逸的良策。只要权利保护的外部成本仍然存在,制度就有再次被架空的可能。因而,既然是权利保护的外部成本使得制度的运行陷入了困境,那么探究这种成本的源起便有助于我们走出这一困境,从而在根本上避免悲剧的“昨日重现”。
一、制度的困境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们先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角度审视一下该事件。在北京某媒体组织的一次讨论中,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青松律师从法律专业的角度认为,并非只有家属签字之后才能给生命垂危的患者动手术。不签字就不能动手术,是对法律的一个误解。他认为,当医生确定不实施手术就可能导致患者丧失生命的时候,就是一种特殊情况,医生及医疗机构就要实施自己的特殊干预权。③
张律师所说的“特殊情况”来源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对于医疗机构在实施手术之前是否需要征求患者家属的同意并签字,该条例规定了四种情况。其中前三种情况都非常明确和清晰,而第四种关于“其他特殊情况”的兜底条款则非常模糊。然而这个兜底条款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特殊情况”之前有一个“其他”来修饰。而按照法律解释的同类规则(ejusdem generis),当一法条列举若干情况之后跟随“以及其他”的字样时,这一“其他”只能包括未列举的同类情形。④这就意味着,当时立法者在制定这一条款时曾意识到,我们的刻版僵硬的法条根本无法囊括进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复杂性的现实生活,因而在明确了前三种发生概率较高的情形的处理情况的前提下,针对该三种情形之外的发生概率较小的情况则“模糊化处理”。而在该事件中,肖志军作为患者亲属或者关系人,其拒绝签字行为首先可以清晰地划归到第二种情形,而不是“其他”特殊情况。难能可贵的是,医院的工作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抱着该事件可能会属于第四种情况的怀疑态度,按照法律规定向上级领导请示。而领导的批示与院方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院方更不敢“越俎代庖”了,否则医院将面临很高的事故风险和巨大的法律责任,这将在后文予以分析。
上面的分析得到了卫生法学专家、曾经参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起草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卓小勤教授的支持。他认为,患者的同意是医疗行为合法性的基础,是一个逻辑起点。医患关系是一个合同关系,而合同的成立必须是以对方承诺作为前提,如果患者不同意的话,这个医疗服务合同就不成立。在医院已将拒绝做剖腹产手术会导致母子双亡的风险以书面形式及时告知患者的前提下,家属一方仍然做出这样不理智的选择,产生的后果应由患者一方承担。⑤但是,张律师主张医疗机构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干预权”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1999年开始施行的《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第26条规定,“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第37条规定,“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医师,应当承担警告、责令暂停执业活动、吊销执业证书以及追究刑事责任等法律责任。根据该法的以上规定,医师只有在实验性临床医疗时才应当征得患者或者其家属同意;除此之外,医师应当对于危急患者予以抢救和诊治;否则,如果由此造成严重后果,医师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就与1994年开始施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发生了冲突。但由于《执业医师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规范,其效力等级明显高于作为行政法规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二者发生冲突时,当然应当遵守《执业医师法》的规定。“而且《执业医师法》第24条是直接源于《执业医师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医生的执业宗旨而产生的,不允许其他具体的操作性规定与其相抵触,发生抵触时应当优先遵守《执业医师法》第24条的规定,即医生应当优先履行救治危急患者的义务。”⑥也就是说,依据中国现行的法律,在肖志军一案中,即使肖志军在手术通知单上拒绝签字同意手术,医院也应当先行救治李丽云。
在这里,法律的规定与伦理学的态度是暗合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裴晓梅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救治生命都是第一位的,这要求医疗机构不能机械地执行法律。中国医学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伦理学会会长、东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慕义表示,在生命伦理学的理论中,对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有一个制约和控制的原则,就是医生的干预权。不能机械地理解知情同意权。病人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危及生命时,医生要根据病人病状与生命保全的最高利益果断行使干预权,并排除所有可能对挽救生命造成的干扰,全力保全病人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医院方认为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是由于其亲属拒绝签字,自己没有责任的想法是错误的。”并且,孙慕义给记者讲了一件发生在武汉的个性病例:一名幼儿在吃荔枝的时候被果核卡住了气管,被送到医院后经诊断面临生命危险,紧急救治的唯一办法是切开气管取出异物。孩子的父亲坚决反对,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当事医生在向家长当面告知患儿病情而得不到签字的情况下,强行为孩子实施了气管切开手术,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事后,家长怀着感激的心情向医院及当事医生表示了歉意。⑦甚至有人撰文指出,我国的医疗手术签字法规缺乏危及生命安全特殊情况下相关的补充条款,并且“一旦患者昏迷神志不清,亲属又拒不签字,甚至根本找不到亲属的情况下,医院方必须先行抢救,把公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这种施救也必当对过错承担责任。”⑧
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肖志军拒签案中,甚至不仅仅在该案中,颁布时间更晚、效力等级更高,更重要的是,更赋有人性化色彩的《执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为什么在实践中被《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架空了?为什么医疗机构普遍“有法不依”或者说是“集体性违法”?我们需要从后果主义——《执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所可能引致的一系列后果——来寻求答案。显而易见,《执业医师法》第24条是一项道德色彩很浓的规定,可以说是“权利话语”在法律文本上的具体体现。然而权利话语的大行其道,会有可能蒙蔽人们的双眼,使我们过度关注某个事件当中的当事人,而忽略的是,还有很多事件背后的那些看不见的当事人同样也需要我们的救助,从而把更多的患者推向更不利的境地。
根据《执业医师法》第24条的规定,对于危急患者(大概类似于李丽云这样的患者),医师就必须义不容辞地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能擅自拒绝采取急救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院先行进行抢救,那么即使医院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手术,患者家属也可能以自己不同意签字为由拒绝交纳医疗费。这是因为,医患关系是一个合同关系,而合同的成立必须是以对方承诺作为前提,如果患者拒绝进行手术前的签字,则意味着这个医疗服务合同就不成立,从而医院无权要求患者家属支付医疗费。这就存在着一个很不妙的社会激励,一些心怀叵测的患者家属会利用这条法律,通过“恶意拒签”来规避自己缴纳医疗费的义务。即使医院以“无因管理”的理由将患者家属诉诸法庭,而且最终可能也赢得诉讼,但是医院在这上边所耗费的成本(协商、谈判、聘请律师、出庭以及执行)无疑是巨大的,这些都要计入医院的经营成本的。要知道,医院的社会属性不仅体现在公益性上,同时也体现在经营性上。因为医疗活动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必须讲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医疗服务活动中也存在着社会供求的关系,从而医院是具有经济性质的经营单位,受着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制约,存在着医疗服务市场的一些规律与特点。⑨这就意味着,因“恶意拒签”耗费的额外的经营成本都要分摊到医疗服务的过程中,那时候,药品的价格、医疗器械的使用费、手术费等等都要面临上涨的趋势。而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在此过程中会因为支付不起高昂的医疗费而受到利益上的实质性损害。
我们的分析仅仅考虑了手术成功的场合。假如很不幸,医院的手术失败,那么,患者家属不但不会交纳医疗费,还很有可能会非常气愤地将医院推向被告席进行侵权索赔。这时候,医院所面临的尴尬境地会使人们对典故——“赔了夫人又折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时候,医院的经营成本同样会像上文所论述的那样极度攀升。因此,如果法律规定了医院的“强制医疗”义务,那么无论医院进行的手术是否成功,都会导致一致的结果,即医院经营成本以及患者医疗成本的极度攀升。在此意义上,医院与患者产生了“共荣利益”。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结果。作为一种经营性事业单位的医院,处于自身发展的考虑来讲,在面对这种紧急情况下的最优的策略选择可能就是,谎称病人已经严重病危,并且宣称没有抢救的必要和可能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和患者家属产生纠纷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医院掌握了医学的专业技术及其相关信息,如果医院方面将这些信息隐瞒,作为外行的患者及其家属是不清楚相关的医疗信息的。这会使得更多的相似处境的患者可能根本就丧失医疗机会,从而处于更不利的境地。
《执业医师法》第24条的规定只是静态地关注单个权利的保护问题,并没有关心因为这一个权利的保护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更重要的是,这些连锁反应会使得单个权利保护的初衷大打折扣,甚至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些都是权利保护的成本。这种效应类似于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即“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权利保护的外部成本的存在使得充满正义感的《执业医师法》第24条在实践操作中无情地被放逐。我们只能在法律文本中对这种令人神往的制度垂涎三尺,却在现实中寻觅不到它的踪迹。这便是制度的困境。如何从根本上走出这一困境,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二、制度革新是不能一劳永逸的
面对这一困境,一些学者很自然地将反思的大棒挥向了术前签字制度,试图通过制度的革新破解这一困局。有人在《南方周末》上很尖锐地提出,“签字制度的荒谬在于它为推脱责任提供了方便。不妨问问有过这种签字经历的人,他们认不认为此举是在强迫家属承担风险?‘手术同意书’是法律设定的医院满足患者知情权的义务。显然,它不能免除医院的法定义务,更不能免除出现过失后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若不改变,类似的悲剧怎能不再上演呢?今年上半年,在北京某大医院,一个患阑尾炎的17岁少年,也因为陪同的朋友不敢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死在急诊室门口。另外,签字制度未必就能防止医疗机构草菅人命。”⑩全国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刘红宇律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提出议案指出,“手术签字制度”的缺陷已经活生生地导致本案产妇母子双亡悲剧的发生。虽然《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也规定“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赋予医疗机构独自决定手术的权利,但是由于其为兜底条款,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模糊不清,不具有操作性。因此刘红宇律师提出两点建议,即建议加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对生命权的保护;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障医疗机构为抢救急诊病人后产生的医疗费能得到有效支付。(11)“尽管这确实只是一个较为极端的个案,我们也不能由此就肯定一定要通过立法单方面确定医生的‘强制救护’。但这其中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有关方面应该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逐渐建立健全一种相对更为合理、人性、科学且严格有序的规章制度,既保证患者享有基本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同时又能让医院在危急情况下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从根本上打消医院方面的顾虑,从制度上保证类似的悲剧不再出现。”(12)尽管这是一种非常顺理成章的思路,但是这一思路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需要我们怀疑的。
我们知道,设立手术签字制度的初衷是保障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也是为了有效地防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滥用权力。然而,医院在严格按照制度安排自己的医疗行为时,却发现,尽管实现了该制度设置时的初衷,却也产生了一些严重冲撞我们道德神经的后果,肖志军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在“一尸两命”的后果面前,人们很自然地就会首先联想到我们的制度存在问题,如果没有这项制度,或者,如果医院正确地执行《执业医师法》第24条,或许李丽云会苏醒过来。人们对制度的指责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在肖志军事件中,似乎是制度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人们总是在谩骂、在指责、在建议、在畅想,总是希望我们的专家能够设计出一种万能的制度,一种不会产生悲剧的制度。殊不知,制度意味着“一刀切”,而不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助于实质正义能够得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柏拉图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在他的理想国里,能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贤人之治要比“一刀切”的生硬的制度(法律)之治更加令人神往。然而,制度的“一刀切”的智慧却为司法者、执法者以及守法者降低了司法、执法和守法的信息成本,也锤炼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一刀切”的制度为人们行为提供了一种预期,可以使得人们很好地根据制度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行为,这样,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大大提升。与此同时,“一刀切”的制度也严格阻止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泛滥,徇私舞弊和恣意裁判也被驱逐在正义大门之外。“一刀切”的制度还会使对判决结果的预测成本降低,因而诉讼数量以及整个社会诉讼资源的支出也会大大降低。“法律形式主义尽管看起来不通情理,但它的确代表一种深刻的司法智慧。”(13)
当然,“一刀切”的制度并不是没有缺陷的。“任何制度针对的都是常规问题,有常规就有例外,而制度恰恰无法处理那些常规之外的问题。”(14)因此,制度的“一刀切”并不总是给人们带来欢乐,相反,有时候它也会使人们陷入深深的忧郁和悲伤之中。肖志军事件的悲剧结果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术前签字”制度的本意是保证患者方面对手术和疾病的知情权,然而它在面对“常规之外的”特殊情况时,却沮丧地陷入了尴尬境地。在笔者看来,这一事件的悲剧性在于,它以“一尸两命”的方式展现了“一刀切”的制度与现实生活中特殊问题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法理学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至少到目前还没有解,也许永远不可能有解的法理学问题。也正因如此,肖志军事件的悲剧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一个悲剧的发生是否足以推翻一项制度?结论不能草率地得出。因为,衡量一项制度是否是可以被我们接受或者是继续接受的,要看这项制度是否从整体上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我们假设,在既有制度下的某类悲剧发生的概率是P,悲剧发生的实际社会损失是L,而我们追求一种新的制度设计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的社会成本是B,如果B<PL,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我们进行制度的革新就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相反,如果B>PL,这就意味着,在既有制度下忍受或者说是放任悲剧的发生,就能够从整体上使整个社会保持一种较高的福利水平。这主要是因为,“确立制度的最终目的恰恰是要能满足人类的福利,如果尊重一个制度仅仅因为其是制度,完全不考虑其是否满足了社会的福利,那么这个制度最终必定会失去其作为制度的正当性和活力,并且会压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产生的新的制度需求。”(15)我们必须明确,即使是一项有效的制度也不可能阻止所有悲剧的发生,而我们之所以称它为“有效”,我们之所以“尊重”它,是因为它能以合理成本阻止大多数悲剧的发生。而我们“不尊重”一项制度之前,应当首先对该项制度的社会效果做出定量分析,(16)然后再做出定性的判断。
尽管一个悲剧的发生并不能简单地否定一项制度,但是它也并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悲剧发生之前,相信很少有人会意识到我们的制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说明,悲剧的发生至少可以为我们敲响警钟,敦促我们去关注是否应当进行制度革新这一问题。事实上,制度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恰恰是在既有制度框架下的悲剧中展现出来甚或实现的。如果没有肖志军案的悲剧,人们就不会那么强烈地认识到术前签字制度的弱点和局限,也就无法看到其他可替代性制度方案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李志军”、“张志军”的“前赴后继”,传统的术前签字制度就将继续保持原样。“社会必须支付这个代价之后,才能使人们逐步有所体悟。这也是人类的悲剧。人必须吃一堑才能长一智。这一点是法律制度与其他自然学科很不相同的地方。制度从根本上看是无法事先安排的,仅仅是人们行动的产物。”(17)
虽然悲剧的发生可以提醒我们对于一项制度需要保持警惕,虽然制度革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悲剧的发生,但是通过制度革新走出制度的困境仍然不是一条一劳永逸的良策。只要权利保护的外部成本仍然存在,制度就有再次被架空的可能。因而,既然是权利保护的外部成本使得制度的运行陷入了困境,那么探究这种成本的源起便有助于我们走出这一困境。
三、能够破解困局的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也存在类似于《执业医师法》第24条的规定,而且有人在质疑目前的术前签字制度的时候,在大力地宣扬要借鉴国外的制度,其言外之意是,“外国的月亮确实圆”。(18)那么我们就首先考察一下“外国的月亮”。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有一项公法即《紧急灾难施救法》,要求所有人在发生危及生命的灾难时伸出援手,包括医疗界人士。比如,美国《医疗法:紧急施救手术法规》规定:“医生有权在病人面临生命威胁,或有导致身体残疾的危险时,在未得到病人同意以及未得到任何其他人准许的情况下,对病人实施救治。”当遇到突发灾难时,病人有可能失去行为能力,此时,医生有权援引《紧急施救手术法规》中的规定,自主决定最佳救护手段。而在采取紧急措施时,医生也会留下详细的治疗纪录,以备日后查验。(19)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医学中心博士刘大海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美国,生命权至高无上,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危急关头医生见死不救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而且当事医生要负法律责任。据刘大海介绍,在美国,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人诊所,只要有病人送来,都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救治,哪怕病人没有医疗保险,甚至付不起医疗费。如果医生需要对病人进行手术,而病人头脑清楚时,只要病人签字就能手术,家属的签字只能起辅助作用。刘大海说,手术前,医生会向病人详细地解释病情,把手术的利弊关系和可能发生的情况明确告诉病人及其家属,必要时还要求病人复述这些解释。对于某些复述不详细的病人,医生还会对其进行提问,以确保病人真正理解。在治病过程中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比如病人出现大出血、休克以及神志不清,病人的手术决定权在医院,而不是家属或其他人。医生首先会马上对病人的病情进行会诊,只要有2名以上的主治医生商讨并签字,就能决定病人是否需要手术。然后医生会把会诊结果和病人的病情以及急救措施告知家属。如果遭到家属的反对,不同意手术,便由医院设立的“道德办公室”做出最后决定,一般该办公室都会采纳医生的意见。(20)由此可见,我国的《执业医师法》第24条在一些西方国家,或者至少在美国,已经顺利地开花结果。耐人寻味的是,在美国运行良好的一项制度,在我们国家却只能令人神往,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在“中国特色”已经成为强大的政治话语这一背景下,有人可能会坦然的认为是“国情使然”。那么我们继续追问,在这里,有差别的“国情”又具体指的是什么?
我国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心胸外科的一位医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写下下面的话:
临床上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患者拒绝接受或不配合手术或治疗,而此时,从治疗角度来看,患者又必须接受治疗或手术,此时,医方应做好详细的记录,在履行了完全的告知义务后,患者仍不予配合的,一定不要忘记让患者明确签字“拒绝手术(治疗),后果自负”,尽可能做到没有法律上的漏洞,因为即使是患者不接受手术或治疗,可一旦发生意外,此时患方往往会以他们对疾病的后果没有预见或其他理由起诉,医方又没有充分证据,在诉讼中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而处于劣势。(21)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医生对于病人的照顾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并且对患者信任有加。而我国的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提防患者的“倒打一耙”,并且将这种“经验”作为可传授的“知识”。这种医生对患者的不信任,从侧面反映出,在医患关系方面,中国要比美国紧张得多,换句话讲,中国医患之间的信任度要比美国低得多。而且,郑也夫在一次题为“中国的信任危机”的讲演中提出,中国社会在“人格信任”、“货币系统信任”、“专家系统信任”这三种信任结构中都出现了危机,而且他对中国信任的重建似乎并不乐观。(22)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分析指出,华人本身强烈地倾向于只信任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庭和家属以外的人。家族以外或者说“圈子”以外缺乏信任使得在中国,无关系的人很难组成社团或者组织,因而组织形态的交易只能落在存在于家族里或者是“圈子”里,从而形成不了大企业。并且福山将中国社会信任度低的原因归结于中国自身的文化。(23)福山在该书中分析指出,美国、日本、德国的社会信任度要远远高于华人社会。尽管张维迎不同意福山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但是他自己不得不承认中国现阶段存在很大的信任危机。(24)
而反过来,从上边的中国与美国的医生对患者的不同态度以及肖志军事件,也可以反映出,同样是为了保证患者知情权以及生命权的法律制度,却因为社会信任度的不同,导致了实质正义的实现效果产生了很大差别。高信任度有助于制度的实施和操作,也有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这是因为,信任是所有交易的前提,如果买方对卖方提供的产品的品质、质量没有信任,或者卖方对买方的支付手段和支付方式没有信任的话,交易就没有办法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任促成了交易。不仅如此,信任还降低了交易成本。比如,我们在饭店退房结账时,柜台小姐总是让你先等一下,然后她拿起电话通知楼上的服务员去检查一下房间有没有丢东西。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使交易成本大大增加(浪费的时间总量很大)。
此外,法律制度的运行本身离不开信誉基础。在一个人们普遍不讲信誉的社会里,法律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在一个人们比较重视信誉的社会里,法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25)对于法治状况而言,信任危机导致了:原本可以协商解决的纠纷,现在必须要打官司了;原本无须上诉的案件,现在必须要上诉了;原本可以调解或和解的案件,现在必须要判决了;原本判决就可以结束的案件,现在必须要强制执行了;原本可以顺利执行的案件,现在执行也不解决问题了;原本通过司法途径可以解决的案件,现在还要上访了。以上每一种情况都会大大增加法律实施的成本和难度,(26)更重要的是,也增加了权利保护的外部成本。在李丽云刚开始生病时,肖志军对她说,“能撑就撑着,进了医院,医生总会想着方法骗病人钱,报纸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甚至于,李丽云被送往医院后在血氧持续下降的情况下,肖志军对劝他签字的医生说,“我想得很清楚,她只是感冒,不用手术,这个字我不会签的。”(27)如果肖志军信任医院,李丽云或许会重新走下手术台;而如果医院信任肖志军,从而将上文我们分析过的无论手术成功与否都可能会发生的对医院不利的风险、责任与成本抛到九霄云外,那么李丽云及其胎儿就可能会被医院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由此可见,提高社会信任度能够降低权利保护的成本,从而打开走出制度困境的通道。
郑也夫也表示,对于李丽云的悲剧,医生和患者(家属)之间相互丧失信任,也是重要的因素。他分析,患者(家属)不信任医院,不愿听从手术建议,医院如果自作主张实施手术,可能被患方以“未同意手术”为由不交费,甚至在手术失败后面临法律问题。(28)实际上,如果我们的社会信任度足够高,即使不去重新设计我们的“术前签字制度”,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悲剧的发生。相反,如果我们的社会信任度一如既往地持续走低、没有改观,即使引进了“装备精良”的“华丽”的制度,也会因为缺乏支撑它运行的社会资源——信任——而被荒芜。所以,我们看到外国的“先进”制度不能盲目的“垂涎三尺”,还要考察一下我们是否拥有充足的社会资源能够“消费”得起该项制度,而盲目地效仿只能会导致制度由于运行费用过高而形同虚设。防止悲剧发生的根源不在于制度,而是提高整个社会的信任度。“肖志军事件中,我们需要检讨的绝非仅仅是‘签字制度’这样的‘补漏’问题,而应着手于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公共信任感的重建。而这,无疑是一个更艰巨和庞杂的系统工程。”(29)
要想提高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信任度,就必须要先了解“信任”具有什么样的品质。物质资源一旦面临稀缺的状况,其市场价格就会大幅度提升,市场经济很容易缓解稀缺资源的供给不足。而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却对市场机制的反应并不敏感,“社会资源”的稀缺不仅不会提升其自身的市场价格,还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继续贬值,换言之,信任危机一旦发生,就很容易出现恶性循环,在一个普遍不信任的社会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就会出现关于“社会资源”的“柠檬市场”。(30)假设在肖志军看来,如果社会上所有医生行业的平均信用度不高,并且如果肖志军要搞清楚某个具体的医生的信用度是否高于平均值需要花费高昂的信息费用,那么肖志军就会对所有医生统一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反过来,当医生知道肖志军的这一态度时,他们对患者的医疗建议难免不会仅仅是“点到为止”,甚至“破罐子破摔”,因为他们缺乏一种改善自身信用度的激励。在肖志军事件之后,腾讯网做了一个网络投票调查,有一个问题是,“对于医生的建议或处方,你是否用过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在该问题下的总票数是24483,而该问题的其中一个选项——“完全信任医生,谨遵医嘱”——下的票数是4163,所占比例仅为17.00%。(31)
我不敢果断地下结论说,17%就是目前我国医生行业的社会信用度,但是这个数字至少也能反映一些问题。这些年,从各地陆续发生的“天价医药费”事件,到屡见不鲜的“见死不救”事件,再到治病过程中随处可见的“霸王条款”,直至半公开的“小病大看”、“无病乱看”现象,医院作为一个盈利性的“市场主体”,在公众中的形象早已离昔日妙手仁心的白衣天使形象渐行渐远。伴随着这种公众形象的滑坡,在人们心中,医生不再是“父母心”,医嘱也不再是必须言听计从的“最高指示”——处于信息不对称和绝对弱势中的患者,被迫学会用“消费者”的精明和洞悉力来提防医生,从进医院的那天起,就以敌对的立场来怀疑诊断结果、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于,在医疗事故发生后,“医闹”竟然逐渐演变成了患者家属“维权”最有效的主渠道。而另一方面,由于患者信任感缺失、医疗纠纷激增,医院也越来越小心谨慎,对患者缺乏信任,处处留心“免责”,不签“生死状”就绝不动手术。进而形成医患之间越来越不信任的恶性循环。(32)
医疗卫生系统的信任度的提高问题如果不能说是迫在眉睫,也可以说是亟待解决。前文提到,医生普遍缺少一种提高自身信任度的激励。那么应当如何给医生创设这种激励呢?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参考移动公司的做法。笔者所在大学的移动营业厅里有一个纸箱子,箱子上有三个投信口,每一个投信口下边分别标注着“非常满意”、“较为满意”、“不满意”。我们去办理完业务之后,业务员总会递给你一个印着该业务员的编号的卡片,并请求你将该卡片投进那个纸箱子。据我了解,顾客对业务员的满意程度总是要和她们的奖金直接挂钩的。而移动公司通过这种做法既搜集了顾客对业务员满意程度的信息(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以奖金的形式对那些满意度较低的业务员进行惩罚(给予顾客惩罚业务员的机会),从而为业务员改善自己的服务质量创设了一种激励。
因而,要给医生创设一种提高自身信任度的激励,就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信息问题;二是惩罚问题。前面提到,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患者对整个医疗服务行业普遍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从而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所以我们首先要改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患者知道,哪些医生是信任度高的,然后将这些信息向患者披露。医院可以像移动公司那样赋予患者一项投票权(也是一种惩罚权),然后医院将搜集来的信息可以以宣传栏的形式公布给患者,这样患者就会选择那些满意度高的医生就诊,并且如果医生的收入与接待患者的数量呈正相关,那么这样一来,“良币”就会驱逐“劣币”了。当然,为照顾到“劣币”的“隐私”,我们向患者披露信息时可以只披露那些“良币”的信息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同样的原理,如果把上文中的“医生”替换成“医院”,并将上文中的“医院”替换成“卫生局或者自律性的行业组织”,那么在医院之间,同样也会产生“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如果将这一原理运用到社会上的更多的公共服务机构,那么社会整体信任度的提高就会为期不远。到那时,制度的困局就会不攻自破了。
注释:
①这一概括主要参考了《京华时报》、《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等几家报纸的连续报道。
②http://news.qq.com/a/20080104/000972.htm,2008年3月15日。
③董城:《“拒签事件”:生命遇险,强制治疗权能否适用》,载http://news.qq.Com/a/20071128/001652.htm,2008年3月15日。
④《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2页。
⑤董城:《“拒签事件”:生命遇险,强制治疗权能否适用》,载http://news.qq.com/a/20071128/001652.htm,2008年3月15日。
⑥吕英杰:《“肖志军拒签案”医生的刑事责任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4期。
⑦董城:《“拒签事件”:生命遇险,强制治疗权能否适用》,载http://news.qq.Com/a/20071128/001652htm,2008年3月15日。
⑧刘效仁:《医患合同引悲剧呼唤急诊立法》,载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14896,2008年3月16日。
⑨“医院管理理论和技术”,载http://www.37c.com.cn/literature/literature06/manage03.asp?filename=003/01/0030101.htm,2008年3月16日。
⑩http://www.infzm.com/enews/20071129/ed/pzp/200711/t20071128_31430.htm,2008年3月17日。
(11)http://www.chineselawyer.com.cn/pages/2008-3-13/s43334.html,2008年3月17日。
(12)阮占江:《勿让制度之弊遮蔽良心之善》,载http://news.qq.com/a/20071130/001780.htm,2008年3月16日。
(13)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4)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悲剧说起》,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第12页。
(15)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悲剧说起》,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第12页。
(16)最近几年兴起的对于“立法后评估”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17)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悲剧说起》,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第15页。
(18)http://www.chineselawyer.com.cn/pages/2008-3-13/s43334.html,2008年3月17日。
(19)《国外手术签字:危机时刻生命至上行规让路》,载http://news.163.com/07/1202/17/3UNOK336000120GU.html,2008年3月17日。
(20)《家属没签字,国外医院的医生怎么办?》,载http://bbs.sxws.gov.cn/dv_rss.asp?s=xhtml&boardid=45&id=243&page=1,2008年3月17日。
(21)黄戈:《对手术签字的法律思考》,载《医学与哲学》2004年第2期。
(22)参见郑也夫:《中国的信任危机》,载《信任的危机——中国当代社会热点问题十三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5页。
(23)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95页。
(24)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5)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29、34页。
(26)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个经济学的进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
(27)刘延迅:《“狂人肖志军”》,载《新世纪周刊》2007年第30期。
(28)http://news.sina.com.cn/c/2007-11-27/013512972750s.shtml,2008年3月17日。
(29)徐锋:《丈夫拒签悲剧中的信任危机》,载http://news.qq.com/a/20071125/000433.htm,2008年3月18日。
(30)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个经济学的进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31)http://vote.qq.com/cgi-bin/survey_project_stat?pjtId=9668&rq=yes,2008年3月18日。
(32)徐锋:《丈夫拒签悲剧中的信任危机》,载http://news.qq.com/a/20071125/000433.htm,2008年3月18日。
标签:法律论文;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论文; 肖志军论文; 医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