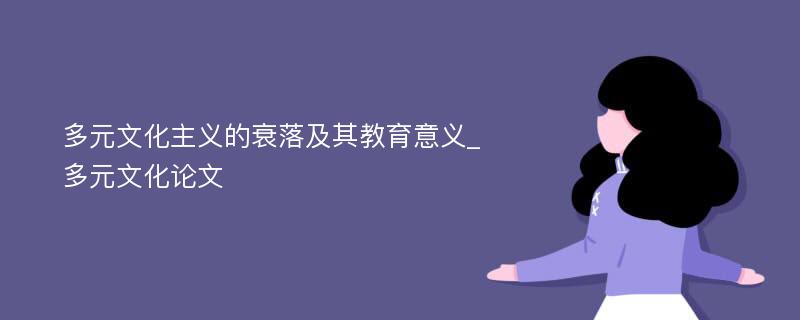
论多元文化主义的衰退及其教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5)05-0026-05 “二战”之后的全球化浪潮,给西方很多国家带来了族群构成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随之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其核心在于怎样整合少数族群,同时给予少数族群以公平的机会和待遇。20世纪60年代,针对文化多样性问题的多元文化主义兴起,并一度成为很多国家整合少数族群的政策取向,甚而具备意识形态特征。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无论作为理论还是政策取向都受到了广泛批评,尤其在欧洲国家遭遇的批评更为强烈。直到近期,欧洲各国政府首脑不得不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之时对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实施证明了这一点。当前,多元文化主义思潮陷入衰退,必然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共存共荣:多元文化主义的幻象 (一)少数族群权利的声张——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 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民权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尊重和认可文化差异,让少数族群能够享受与主流群体同等的权利;同时,鉴于少数族群的弱势地位,强调应对少数群体的权利给予特别保护;最终实现少数族群与主流群体在多元文化下的共存共荣。 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于对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的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黑人政治、后现代思潮以及批判理论的影响,本身不是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而且也因学术视角及政治立场的不同分为不同的流派。例如,以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a)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以玛丽恩·杨(Marine Young)和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为代表的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以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为代表的社群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1]但是,不同流派的多元文化主义有共同的逻辑起点——文化差异,也诉求共同的现实目标——文化平等;它们都描绘出一幅相同的幻象,即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尊重和认可少数族群对所属群体的文化认同,因此达到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各种流派之间的差异在于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这一目标。[2] (二)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整合模式 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兴起之前,主要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整合政策是同化少数族群,典型如美国的“大熔炉”。同化论认为,为了融入社会,少数族群成员应该放弃原有的文化认同而融入主流社会,接受所在国主流群体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多元文化主义是在批评同化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因各国国情的不同,多元文化主义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以及荷兰,这些国家的族群结构以及少数族群的来源都有差异,本国主流群体对文化多样性的观念也大不相同,因此整合模式也不一致。但各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都是基于这一共识:在反对同化论的基础上,倡导尊重少数族群保持其特有文化认同的权利,提倡对“差异”的尊重和补偿。 (三)多元文化主义的扩张及其问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所含涉的对象不仅包括移民或有色种族,而且还包括了不同阶级、女性、同性恋、残疾人等各种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高举“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要求主流群体尊重和认可基于群体的“文化”差异,获得与主流群体成员平等的权利和待遇。台湾学者张建成称此现象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巨伞论”。 诚然,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要求得到主流群体的尊重和认可、声张自身权利的诉求应当得到拥护。但是,这样的诉求以“文化”为名,却“没有认识到‘文化之外’的社会机制、经济差异等因素的影响”,[3]而实际上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是由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所致。此外,每一种文化群体中成员的文化认同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比如作为弱势群体的白人女性同时是主流群体成员,而强调群体权利的多元文化主义无法应对这样的内部多样性。因此,文化群体成员身份的合理认同就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死结。 二、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领域的衍生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假设 多元文化教育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教育领域的衍生,不过其基本理念超越了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教育使儿童学会容忍和尊重差异,进而促进社会平等。如同多元文化主义一样,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也因为关注重点不同而存在差异,如克里斯汀·贝内特(Christine Bennett)在《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与实践流派》一文中,将多元文化教育分为课程改革、社会公平、多元文化能力和公平教育四大流派。[4] 这些不同流派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基于下述假设:(1)当前课程反映的是主流群体的文化,少数族群文化被压制,另外,儿童的学习风格也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却没有反映到学校教育中,成为造成少数族群儿童学业失败的主要原因;(2)少数族群文化不受尊重,少数族群儿童的文化认同不被学校教育所认可,因而造成少数族群儿童在教育过程中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3)少数族群的历史贡献没有反映到课程内容中,因此少数族群儿童没有从教育中获得自我价值和自尊;(4)教育机会公平、参与公平和学业成就公平是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主体内容 基于以上假设,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者提出了各种教育改革方案。其先驱詹姆斯·班克斯(James Banks)从学生发展和社会正义两个角度建构多元文化教育目标,在此领域具有代表性。班克斯所建构的多元文化教育目标包括:[5](1)增加来自弱势族群学生的教育机会;(2)重新建构学校教育目标,以使多元文化教育成为实质行动,让学生拥有公平学习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学校教育的主要假设、观念和结构;(3)培养所有学生(包括主流文化学生)的多元文化态度、知识和技能,对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4)培养学生跨文化的知识与信念,以跨越国家界限。班克斯的多元文化课程建构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也成为很多国家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基本取向。班克斯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局限,如注重对教育的改造,强调发展跨文化的知识与信念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从多元共存到公民整合:多元文化主义的衰退 (一)转向公民整合与增强国家凝聚力: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政策取向的衰退 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衰退,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认同再次成为少数族群特别是移民整合政策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政策取向受到了批评或质疑,渐次退出官方政策文本。直到最近,仍有很多学者和政治家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失败的。 荷兰一直被看作是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典范——是唯一全额资助少数族群以“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实施教育的国家。荷兰允许在公立学校中建立少数族群班级,也允许各族群建立自己的初等和中等学校。但从美国“911”事件以后,荷兰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受到质疑,荷兰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发生了急速转向。[6]更让人诧异的是,澳大利亚作为最早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之一,国内的右翼政治势力自20世纪90年代一直在强调国家认同,呼吁在社会各领域剔除少数族群的认同,进而将多元文化整合为澳大利亚白人移民传统的认同,这种政治倾向特别以来自亚洲的移民为重点。[7]进入21世纪后,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因恐怖事件的增多而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 进入新世纪后,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批评,作为政府政策取向的多元文化主义开始在批判声中渐渐消退。2008年是欧盟的“跨文化对话年”(Intercultural Dialogue Year),欧洲委员会颁布的《跨文化对话白皮书:平等尊重友好相处》(White Paper on Intercultural Dialogue:Living Together as Equals in Dignity)在倡导跨文化主义的同时,也宣告了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失败。白皮书指出:“……虽然有着良好的初衷,但是现在一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导致了社会分离和群体之间的误解,同时也对少数族群中的个人权利造成了损害,对女性权利的损害尤甚,因为多元文化主义仅仅将个体看作是单个的集体行动者。当前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然而经过反复讨论,咨询委员会成员大都感到多元文化主义不再是一个适合的政策取向。”[8] 在国家层面上,2010年,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了,完全失败了”;在2011年2月4日至5日召开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David Kameron)也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了”,[9]并呼吁寻求新的整合政策;随后,在2011年2月10日,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宣布了法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紧接着在2月14日,荷兰副首相马克西姆-费尔巴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在荷兰失败。不言而喻,各国政府首脑接连宣布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一方面反映了欧洲移民国家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右倾化政治氛围和倾向,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在所谓“老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的公众对移民整合现状的失望。 (二)文化本质主义及族群分离的肇因:多元文化主义理论面临的批评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衰退不仅表现在政策取向上,在理论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在近20多年来也受到广泛的质疑。在本世纪初,克里斯蒂安·乔普克(Christian Joppke)就指出,多元文化主义衰退的原因与自由主义者对其批评相关:[10]首先,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缺乏公众的支持;其次,这些政策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层面将移民及其子女隔离在边缘;再次,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重新抬头,认为普遍自由主义权利是保护少数族群的基点。多元文化主义所面临的批评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静态、本质主义的文化观。多元文化主义立场的基本前提是每个族群都有其成员所共享的、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独特文化,作为这个群体的成员必有固定不变的群体文化认同,应为他们提供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由于这种文化观与19世纪的人类学鼻祖爱德华·泰勒(Edward Bumett Tylor)的文化定义相近,因而一直受到批评。并且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多元文化主义过分强调少数族群作为一个整体,往往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我族中心主义”,即主张某一特定少数族群文化优于其他族群的知识和生活方式,因此陷入对本族文化的孤芳自赏之中而难以自拔。如美国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论者在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心”的时候却倡导“黑人中心”,对黑人的历史竟远溯及古埃及,没有顾及非洲大陆黑人文化的内部差异以及古埃及文明的断裂。事实上,在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早就摈弃了这种本质主义的文化观——个体并不必然被嵌入所在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也不必然保持对该群体文化认同。 (2)人为地构筑了族群之间的边界,导致了社会分化和族群分离。批评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本质化的文化观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人为地构筑了边界,忽视了日常生活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以及随着交互而产生的文化生成和文化变迁。如前所述,乔普克等学者也指出了多元文化主义因其僵化的族群边界观念而遭受广泛批评。很多学者也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所提倡的“欣赏”差异或提升文化意识并没有让所有的文化得到平等的宽容或尊重。 (3)忽视个体的文化权利。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视野中,少数群体的权利和个体的权利通常是统一的,既会相互促进,又会相互冲突。威尔·金里卡对此作了内部限制和外部保护的区分。在此基础上,鲁德·库普曼斯(Ruud Koopmans)对移民的权利也作了两种区分:移民作为个体的权利保护和作为群体成员的权利保护。对于前者,国别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多年来的政策促进了个体权利平等,特别是在荷兰、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因此,作为个体的移民在这些国家能够和本土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对于后者,在对入籍的文化条件、宗教活动、公共机构中的文化权利、劳动力市场平等和政治代表权利等五个指标做了对比研究后表明,群体权利保护所造成的族群隔离远甚于其权利的获得。[11] 四、从群体间文化差异到个体间跨文化交互:多元文化主义衰退的教育意义 多元文化主义的衰退在理论上基于反对本质主义文化观念,在实践上则在于倡导国家的凝聚力,此种变化对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教育政策中就出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衰退迹象——在官方政策中“多元文化”一词开始消失。而最早实行多元文化教育的加拿大,甚至有学者直接宣告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死亡。[12]概括而言,多元文化主义衰退的教育意义有如下几点: (1)文化多样性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整合少数族群,更在于培养适应文化多样性社会的公民。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和人口流动的普遍性,同质的族群或民族文化已不复存在,文化异质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多元文化教育试图通过在教育中纳入某些族群的历史及其贡献而实现对差异的认可,让学生形成文化认同,实属人为构筑文化边界。毋庸置疑,多元文化教育所强调的多元文化平等仍具有其意义,但必须摈弃其文化本质主义倾向,在课程中应倡导容纳所有族群的历史贡献,且其目标在于文化多样性的正常呈现和文化意识的培养,而非仅仅针对某一少数族群的儿童。 (2)有关族群文化的教育削弱,公民教育得以加强。反映在课程内容上,对于某一特定族群文化的表征削减,同时增加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相关内容的呈现,以此让儿童形成多元文化社会的观念,即尊重和容忍差异。但这种差异一定是建立在个体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群体文化的差异。有关国家认同的表征,如该国的历史、语言以及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教育内容有所增加。如在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正尝试在英语、数学、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艺术、语言、医疗和保健教育以及技术等八个学科门类中,以跨文化主义为基本取向构建公民教育的课程内容。[13] (3)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的培养成为文化多样性教育的核心内容。跨文化能力是指个体在跨文化情境中实现有效、恰切的交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技能及态度和价值观。跨文化能力是一个缺乏明确界定的概念,相关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给出不同的定义、建构不同的基本内容。[14]因而,跨文化能力在学校教育领域也缺乏广泛认可的界定。最近,欧盟颁布的文件《通过学校教育培养跨文化能力》(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rough Education),从态度、知识、技能和行动四个方面对跨文化能力的内容进行了描述。[15]概言之,跨文化能力是当今文化多样性社会中的必备能力。如前文所言,虽然詹姆斯·班克斯论及多元文化课程的建构中没有明确提出跨文化能力,但其“培养学生跨文化知识”的观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培养跨文化能力的设想。 毫无疑问,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在反对族群歧视、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待遇等方面功不可没,而且在批评西方白人文化霸权时所揭露的诸多问题,在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同时,使人们逐渐接受了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各国盛行很多年,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政府少数族群整合政策的主要取向。 虽然多元文化主义的坚强捍卫者如威尔·金里卡、纳萨尔·米尔(Nasar Meer)和塔里克·莫多德(Tariq Modood)等在为这一思想竭力辩护,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加入辩护阵营,[16]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存在固有的理论缺陷,既导致在理论上陷入困境,也必然在实践中招致摒弃。这是因为,限于文化政治的多元文化主义虽然以“文化”为旗帜,却没有注意到其他学科,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进展——“文化”不再被看做是一种某一群体所必定共享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群体成员也不会必然形成本群体的文化认同,且文化之间不存在边界,特别是在当今交通和信息技术非常发达的时代,文化时时处于相互交流和渗透之中。此外,多元文化主义所谋求的消除歧视、尊重差异是基于群体文化,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要反对的偏见、歧视和刻板印象正是基于群体的、类型化的简单认识。“二战”以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明确地阐述了群体刻板印象正是歧视产生的根源。因此,在强调族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谋求获得对差异的认可和尊重,无疑是缘木求鱼。 总而言之,反映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多元文化教育必然会被扬弃,其追求教育公平的目的依然会通过其他各种思潮和政策推动,如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等,但其目标是培养适应于多元文化环境中共存共荣的公民,对象包括所有儿童。与此同时,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和认可,将从群体文化差异转向个体的文化背景差异,其重点也就从谋求少数族群教育权利的平等逐渐升华至所有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平等,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必然成为文化多样性教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