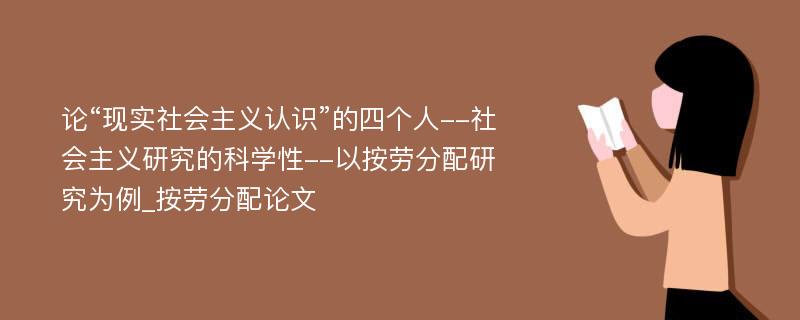
“现实社会主义认识”四人谈——社会主义研究的科学性有待加强——以按劳分配理论的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按劳分配论文,科学性论文,四人论文,为例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研究一直存在一些弊病。改革开放前,本本主义盛行,带有苏联模式印记的社会主义理论被奉为信条,人们只能“学习”和“理解”,不得献疑;改革开放以来,与注重实际的良好学风伴生的是,对流行口号、现实政策等,总是随风起伏。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治学态度都患有科学精神欠缺的通病:对于成说,常常怯于审视,有时却又轻率地“发展”;出于“势利”的计较而回避结论;无意追求概念的明晰、逻辑的严谨、证据的充分,等等。这种情形是造成社会主义研究的学科声誉欠佳、研究水平难以言说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例子,这里简单回顾一下我国学界对按劳分配理论的研究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行按劳分配,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大前提,还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第一,消灭商品货币,使“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即个人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第二,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的耗费,不存在计量和比较的困难。关于第一个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十分清楚。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都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但两者有根本差别。前者的等劳交换只是作为支配商品价格运动的规律存在着,用《哥达纲领批判》的话说,“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这里,真正的等价交换只是偶然现象。等劳交换原则在按劳分配中的情形正相反,它应该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交换尺度是社会事先确定的生产各类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这在商品经济中是不可能的。论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正面阐述了按劳分配要以个人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为前提,而且从反面谈到了商品经济与按劳分配的对立,这一点,从他们对普鲁东“劳动货币”的批判以及对欧文的“劳动公平交换市场”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价值规律从而商品经济本身被破坏,或者是按劳分配丧失其本义。依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者获取一定量的消费品,须向社会提供等量社会必要劳动。在商品经济中,劳动者的劳动是否是社会必要劳动,要受价值规律裁判:可能,他提供的是完全没有市场需求的无效劳动;可能,其劳动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则他实际耗费的劳动只能部分地得到社会承认;可能,其劳动生产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则他实现的价值将高于他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这样,我们面对的是两个意义上的劳动:社会必要劳动和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在这种情形下实行按劳分配,按哪个“劳”为尺度呢?若以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为尺度,则那些没有向市场提供有效劳动的劳动者也将参与分配,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劳动者的所得也会超出他向社会提供的有效劳动,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劳动者的收入将低于他向社会提供的有效劳动。这是对价值规律的破坏。这将导致落后者不思进取,先进者失去动力。生产者失去积极性的最终结局是整个经济的破产。若依社会必要劳动为尺度进行分配,首先,其商品价值完全没有实现的劳动者或企业将破产;其次,对那些成功售出其商品的劳动者或企业来说,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将使他们的个别价值实现为不同的社会价值,从而造成收入差距。这里,价值规律保全了,但结果将是劳动者的分化,最终是按劳分配与公有制一道瓦解。不仅如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以社会必要劳动为尺度进行分配,从一开始就牺牲了更为根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劳动生产率的差别首先是由社会提供的不同水平的生产资料造成的,而由此造成的收入差距却要由劳动者承担,这表明了劳动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方面的不平等。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都不兼容。
如果说上述经典作家关于按劳分配的第一个条件的论述在学理上是成立的,那么,他们关于按劳分配的第二个条件——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进行计量的论述,从最初就不十分清楚。恩格斯曾设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下,“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取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1](P660)。这里谈的是调节社会总劳动的原则,但它同时也是调节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原则,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这里“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2](P96)。
这里有许多问题不清楚。第一,简单劳动的计量也许不难,但对于复杂劳动,如生产蒸汽机,要确定从图纸设计到产出成品需要多少劳动小时,绝非易事,估计到科技的飞速发展,事情更加复杂。第二,退一步说,即使生产各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可以事先确定,最困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劳动复杂程度各异,相同的劳动时间包含着不同的劳动量,它们的比例如何折算?面对这个困难,经典作家想到了消灭固定分工。恩格斯设想在“建筑师”与“推车人”之间互换工作,可以使他们的劳动量相比较。确实,建筑设计劳动与推车劳动没有可比性,但如果约翰和彼得既是建筑师也是推车工,则可以把他们的同类工作分别进行比较。但是,固定分工的消灭有赖于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这绝非一日之功,而且《哥达纲领批判》有言,固定分工要到共产主义方能消除,因此,社会主义阶段仍旧存在的由固定的、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分工引起的分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第三,还有一个设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重复了约·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1839年)一书中的一个意见:复杂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是由社会承担费用的,因而他们不应要求较高的报酬。这个设想至少忽视了下述事实:复杂劳动能力绝不仅仅是支付学费的结果,有天赋因素,更重要的还有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努力。实在说,这第三个设想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问题。
原始设计本来有欠缺,后人的实践也难完善之。在纯粹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一旦按劳分配无法实施,又不能实行其他所有制结构中才会有的分配方式,余者只有平均主义一途。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消费品分配中广泛存在的平均主义,是当时的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那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按劳分配的研讨,总的说来是怎样的情形呢?很难说在学理上很严谨。经典作家设计的按劳分配以商品货币的消灭为前提,这一点人人清楚。但是,人们虔敬地谈论着经典作家的正确性,同时又认真地探讨着如何在商品货币关系下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人认识到这里的两难,试图借助“不完善的按劳分配”、“基本上是按劳分配”等说辞以走出困境,此类努力最终归于无效。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知道商品经济无法摆脱,同时又对按劳分配坚信不移,便不顾学理,言矛,便置盾于不顾,说盾,又弃矛于身后,坦然地调和着无法兼容的东西。
劳动计量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商品经济中,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可以进行量的比较,但那是自发的,“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2](P58)。现在的困难在于要进行自觉的计算。要比较熟练与生疏、脑力与体力、复杂与简单等等劳动的耗费,许多人谈到过其中的困难,做了若干克服困难的尝试。然而,比如一个技师的2小时劳动被认定等量为一个粗工的4小时劳动,迄今为止尚无令人信服的说明,为什么不是更少些或更多些。曾有学者指出:“从理论上说,只有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算单位的简单劳动,才能准确测定各种劳动者各自提供的劳动量。但在实际运用上,各种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的比例,却是难于准确确定的。”[3](P143)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准确实行按劳分配,是困难的。论者没有得出这一结论。
四十多年前蒋学模先生就曾说过:在按劳分配中进行劳动计量,“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是劳动核算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4](P386)。问题至今仍不清楚,症结何在?我们看到,讨论总是绕着技术问题即计算方法兜圈子。但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原本不是技术领域的问题,因此,困难不会在技术领域求得解决。在商品交换中作为媒介的货币,绝非本·富兰克林、托·霍吉斯金等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为便利交易而发明的工具①;它首先是社会关系的化身,其次才是劳动计量的工具。在以按劳分配形式存在的等劳交换关系中,产生了自觉计量劳动的要求,从学理上说,其计量手段亦首先必须是社会关系的体现——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憧憬过的自由变换工作的自由人的关系中,劳动时间才直接体现着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劳动量的直接表现。
近年来的一些新话语,使本来不清楚的问题变得更含混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的提出,适应着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非常合理。但其中的劳动被说成是按劳分配的劳动,这就完全不讲学理了。这里的劳动绝不是按劳分配中的劳动,而只能是劳动力价值。不讲学理的一个后果是,理论上不清楚,实践上没有贯彻的可能。公众的感觉是,说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理论的严肃性受到损害。
顺便说,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能否兼容,是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能否兼容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如果说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是相斥的,那么,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能否兼容呢?能否兼容,要看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如果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它们是不兼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了两者的兼容,使得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走出困境,但出路是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中找到的。商品货币关系是自发形成的,其基本运行规律绝不因人的干预而改变,遇到障碍,它就以经济破坏来显示其力量。社会主义则不同,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作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设计。当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相斥而两者都不能放弃,同时,商品经济自有其不可移易之规定,唯一的出路是重新解释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商品经济因素冲突的逻辑结果。回到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的话题。在选择了市场经济以后,如果不能像重新解释社会主义那样去重新解释按劳分配,还不如暂束之科学殿堂,以保持其作为尚待验证的科学命题的尊严。
注释:
①参见《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页;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