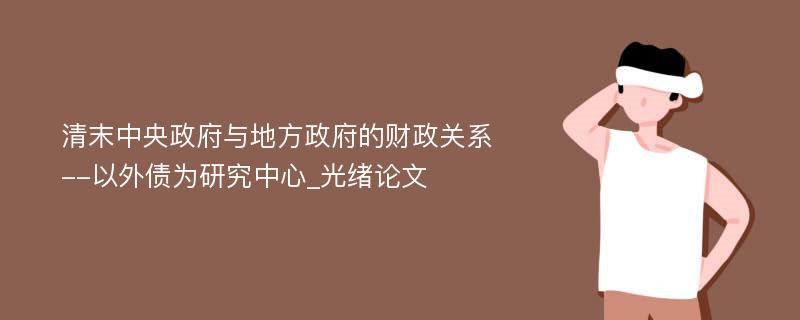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债论文,晚清论文,研究中心论文,财政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587(2004)-01-0094-08
晚清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的逐渐崩溃,中央政府监管的日趋失控,财权的不断下移,构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并引发了中央与地方围绕财权分割的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这期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一直伴随着中央与地方的实力消长过程中。由于外债的介入,使得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更为复杂和特殊。本文试图以外债为中心,阐述这一关系形成和演化的曲折历程,展示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中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就地筹款——外债介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肇端
统一的财政权是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鸦片战争前,全国财政机构在内由户部统理,在外为布政使司。各省的布政使司只是中央财政机构的分支,不是独立的一级财政,更不是地方督抚的下属。地方的各科常例开支,须经户部核准核销,项有定制,数有常额,中央拥有对地方财政的控制权和全国财力的统一调配权。但自太平天国后,这种控制权被打破了。太平天国起义耗费了清政府大量库银,清廷不得不谕令地方就地筹饷拨解,“无论何款,赶紧设法筹备”(注:《清文宗实录》卷67,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第40册第876页。),就地筹饷权的下放是督抚权力扩展的契机。各省督抚打着“就地筹饷”的旗号,不仅采取盐斤加价、开辟厘金的办法筹款,沿海省份还首开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向外商举借外债,打破原来各省不得指拨关税的定制。咸丰三年(1853),苏淞太道吴健彰为雇募外国船炮攻打上海小刀会起义,向上海洋商借款十二万余两库平银,是为中国外债史之滥觞。咸丰四年(1854),两广总督叶名琛为镇压天地会起义,向美商旗昌洋行借款26万两;咸丰七年(1857),闽浙总督王懿德为镇压福建小刀会起义,以“本埠及其他贸易港口的关税为担保”(注:许毅:《清代外债史资料》(上),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向福州英商借款50万两。在咸丰十一年(1861)到同治四年(1865)间,江苏、福建、广东等省,先后至少向英、美各国洋商举借十二笔外债(包括江苏借款四笔,苏淞太道借款四笔,福建借款三笔,广东借款一笔)。借款总额达1,878,620两,利息率低者年息八厘,高者达一分五厘,绝大多数以关税抵押或摊还。对于各省举借外债的举动,清政府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因为清政府要依靠地方大员来镇压农民起义,若严禁地方借债只会导致农民起义更加风起云涌,威胁到清政权的统治,而且各省自借自还,并不牵扯中央财政,所以并不在意对地方借债的管理。在财政体制中外债也未列入经常奏销的岁入项目,仅仅看作地方的临时性支出,“即令事出万紧,仍令该省自行设法归楚”(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地方官员也认为借债是“权宜暂借济用”,因此地方政府举债大多不上报。如同治元年(1862)的苏淞太道吴煦向上海英商银行的借款,咸丰十一年(1861)底至同治元年(1862)初福建巡抚瑞瑸向英法等国银行的两次借款,都没有上报。受战争局势的影响,这时的债务期限短,利息高,数额小,总数不过250万两左右,而且偿还及时,几乎没有造成坏的影响。
太平天国后,“就地筹饷”逐步向“就地筹款”演变,进一步扩大到各省筹划海防、举办洋务的过程中。从光绪九年(1883)至十年(1884),为筹办广东海防,经两广总督张树声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手,先后借洋款五笔,共700余万两,均“粤借粤还”,被纳入“就地筹饷”的范围。(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第71-78页。)自80年代起洋务派举办的民用工业也不得不依靠外债和高利贷。从光绪三年(1877)到光绪十一年(1885)轮船招商局先后三次向外商借款,平度金矿、湖北织布局、湖北铁政局都向汇丰银行借过款,光绪十七年(1891)开平矿务局向德华银行借款20万银两等等,直到甲午战前,洋务派借债多是在“由我自主”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时期外债数额在清政府财政收入并不占十分重要地位,即使加上其他用途的外债,也在清政府收入总额中年均仅占5%以下。不过太平天国后借债的地方官员不再是一般道台级的官员,而是封疆大吏,诸如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等。且每笔数额较大,有的达230万两,期限也较长,均在1年以上,最长的有30年。据不完全统计,太平天国时期到甲午战争前,由各省自借、自还、自用的纯地方性外债银达1440余万两。(注:《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6年5期。)在各省看来,这不过是“将本省自有之财提前应用”(注:《张文襄公奏稿》,卷24,“筹办江西善后事宜折”。),而且“转瞬即行归还,又实不便多借”(注:许毅:《清代外债史资料》(上),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因此这些外债完全脱离中央集权财政系统的控制,成为地方的临时收入。正如梁启超所说:当时世界各国之地方行政区,“未有能直接为国际交涉以借外债者,有之则从中国始”(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24,“中国国债史”。)。
“就地筹饷”向“就地筹款”的演变,使得地方拥有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各省不仅自掌厘金、自借外债,还拖欠京饷、截留税款。不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原以“起运”、“存留”方式加以分配的“春秋拨”体制逐渐被打破,而且仅仅依靠中央权威来掌控省区之间资金调拨的解协饷制度也变得苍白无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西征借款。光绪元年(1875)底,各省关积欠协饷已达2740万两(注:《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76页。),相当于3年的应协款额,直接影响了西征战事的顺利进行。为保证所需军饷的足额到位,左宗棠使出了变协饷为各省所欠外债的杀手锏,使协拨省份加盖关防的海关印票代替了难具约束力的中央催解,先后六次委托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向外商借款合计达1595万两,为保证西征战事的顺利进行扫清了资金障碍。因为中央对协饷转化为外债的应急之策均以谕旨的形式表示赞同和支持,所以西征借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左宗棠受中央之命与协拨省份争夺饷源的一种工具。不仅如此,“因为受协省份运用外债的国债性质迫使协拨省份从协饷中如期偿还本息,使中央在协饷资金运转中被逐渐架空,地方也无疑从协饷转化为外债的过程中增强了自己的财政独立性”(注:马陵合:《试析左宗棠西征借款与协饷的关系》,《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所以,西征胜利并不能挽回清朝统治机制内部崩溃的总趋势,反而各省违抗解协饷的定制,使地方与中央的经济矛盾发展到新的阶段。户部奏折也坦称:“近一二年各省因筹办海防,购买船炮,匀还洋款,往往截留京饷,每年解部者不过十之六七。”(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2433页。)为改变这一状况,清政府试图变通解协饷制度的运行方式,采取中央专项经费的办法,以限制地方截留税款。即中央根据户部已掌握的各省关的“的款”(确有款项)来规定一项专项经费的总额,然后分摊到各省关。同治十三年(1874)的“抵闽京饷”和光绪十一年(1885)的“加放俸饷”即是这一政策的体现。但这种枝节的修补对于改变僵化衰微的清朝财政体制早已无济于事。光绪八年(1882)清廷下谕;“以前各省未经报销之案,著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70,考8266。)如此整饬财政无疑乃是中央对地方的公开让步,是对既成事实无可奈何的承认。
西征借款后,近代外债的举借方式有所转变。同治四年(1865)前地方借债多是“先斩后奏”或干脆“不奏”,本身即是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下令各地“就地筹饷”的产物。但西征借款均得到清政府的批准或确认,成为第一批由中央政府正式对外举借的外债。而且西征借款受到海关税务司的正式干涉,赫德掌握了清政府对外借债的决定权。使得以后的借款都要经过这样的程序:借款要经谕旨批准,总理衙门遵旨让海关总税务司饬令各省关税务司,对发行之债票盖印签署。西征借款就成为中国近代外债主权沦落的起点。(注:许毅:《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这使得清政府不能也不可以再对外债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了,于是令总理衙门掌管外债事务,规定地方大员借用外债,必须上奏朝廷批准,并且事后要上报,赋予了外债的官方性质。例如福建台防借款、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经手的汇丰借款都事先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在光绪三年(1877)豫晋旱灾款的申请中,李鸿章点明了借款需要批准的程序:“听至洋款,若蒙奏准,只要认还确有把握,彼族以多多为善,不在一二百万计较多少,各国借款,均须国家应允,必奉旨乃可相商,必总署与户部复奏转行驻京公使,必各关分年扣还,再由借款省分缴还各关。非此则断不能办。利息低昂,鸿章或可从旁商量,准借与否,实无此权力耳。”(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8卷,第2页。转引自张佩:《中国近代外债制度的演变》。)中央政府开始对外债负有完全的偿还责任,不再是省借省还了。光绪十年(1884),清政府对财政会计科目做了较大调整,开始设立有关外债的科目,“以营勇饷需、关局、洋款、还借息款等四项为新增开支”(注:《清史稿·食货志》。)。这种设置虽颇有争议之处,因为洋款(外债)应为收入类科目,“还借息款”才是支出类科目,但毕竟说明了户部已经认识到外债对国家财政的重要影响,开始着手管理外债了。
但这一时期,源于对传统财政体制的维护及考虑到外债的偿还能力,中央政府对借债还是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如同治元年(1862)五月福建巡抚徐宗干继年初向福州、厦门英法商人借款40万两后,又续借10万两时,清政府立刻指出:“所奏各情,自系为各军粮饷易于应手起见……若概行汇借,将来各省效尤,难保不生纠葛。所称洋商向义凑借之语,洋人视利最重,亦难保不致纠缠……不得仅顾目前,率行汇借,致启弊混之渐。(注:许毅:《清代外债史资料》(上),第16页。)这是清廷对地方自行借债的首次正式表态。针对地方督抚大借外债的现实,清政府多次通令,“借用外债,事同挖肉补疮,尤恐将来挖无可挖,补不可补。嗣后各省无论应用何项,均不准持有四成洋税,动辄向洋人筹措,致令中外各事,诸多掣肘”(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第79页。),“嗣后无论如何为难,不得轻议借用洋款。”(注:许毅:《清代外债史资料》(上),第113页。)所以当光绪二年(1876)元月,左宗棠上奏朝廷“饷源涸竭,拟继借大批洋款权济急需折”,中央政府的批示为:“借用洋款,本非善策,前经该衙门奏明,嗣后无论何省,不得辄向洋人筹借。惟左宗棠因出关饷需紧迫,拟借洋款一千万两,事非得已,若不准如所请,诚恐该大臣无所措手,于西陲大局殊有关系。”(注:《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65页。)光绪十一年(1885)两江总督曾国荃两次上奏借债练水师、购军械等海防事宜,并着手议借外债购船时,遭到清政府的反对:“该督未候谕旨,辄向洋商议借巨款,并录稿知会各省,未免轻率,著传旨申饬。拟借洋款,如未订准,即著毋庸议借。倘已经借定,即将此款存储,不准擅行动用。”(注:《清德宗实录》卷3,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第54册第959页。)这正如贾士毅所指出的:“中国在清末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为了解决举办新政的缺款问题,李鸿章等各省督抚即常常以省内之矿和铁路修建等为条件,对外实行借款。到后来清廷发现此一缺漏之后,便借口恐疆吏滥借外债,引起外国利权交涉,而通令各省非经朝廷核准,不得借用外债。”(注:贾士毅:《民国财政史》,正编,下册,第108页。)
总起来说,甲午战前,外债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中还不占关键性因素。此时地方举债的目的是应付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带有代借性质,替中央政府出面进行财政资金的筹措。洋务运动时期,借债基本上用于地方事务,多属于赢利性的生产费用。清政府财政工作的重点仍是试图恢复原有的拨款奏销制度,将财权(包括外债的管理控制权)统一中央,所以对外债采取谨慎举借和加强监管的态度。因此,这一时期的外债还构不成对中央财政收支结构的威胁。
二、外债摊还——晚清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妥协
甲午战争是晚清财政的转折点。2万万两的战后赔款,最终把清政府推向了借债活动的前台,不但总理衙门与户部代表中央政府直接成为债务主体,中央部门的单独债务活动也时有发生。而且借款数目极大,超过以往所有债务,使得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的借款活动一度受到限制。并且外债摊还实行由中央向地方硬性摊派的办法,直接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恶化,清廷的统治摇摇欲坠。
《马关条约》换约后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就下令组建筹措借款的“委员会”。赔款委员会的设立,表明清政府已放弃先前谨慎借债的立场,举借外债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事务,从此清政府走上了依靠外债的道路。整个甲午战争开始因战费无着,以“汇丰银款”、“汇丰镑款”、“克萨镑款”、“瑞记洋款”军费外债始,到后来因赔款无法偿付,以“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三大赔款借款终,仅在光绪廿年(1894)至光绪廿四年(1898)这五年内,清政府所借的甲午战费和赔款借款,合计即达库平银3亿5千余万两,比甲午战前所借总额,超过6.6倍。(注: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页。)“至1900年,这七笔外债每年本息偿付额达2,490万余两,以后成为常年的财政负担。”(注:《辛亥革命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随后的庚子赔款4.5亿两,加上年息四厘,计9.82亿两,清政府无力筹付巨额赔款,当即转化为39年期的外债,平均每年需摊付2,500余万两(注:宓汝成:《近代中国外债》,孙健:《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第443页。),这使得早已捉襟见肘的清朝财政更加入不敷出,陷入“司农仰屋”的窘境。从此中国背上了巨额外债的沉重包袱。
战事一过,筹款偿还外债成为清政府的财政焦点。起初,户部试图仍按传统的开源节流措施来筹款,大体不过仍是盐斤加价、裁减局员薪费之类的措施,结果遭到各省的反对。无奈之际,清廷又令各省督抚将军各抒所见、通盘筹划,其结果多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即便在光绪廿四年(1898)清廷推出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筹款方式——昭信股票,但实施过程中因苛派骚扰导致流弊丛生,半途而废。为此,光绪廿五年(1899)清政府试图以关税、厘金、盐课为重点进行整顿财政,其方针是“裁汰陋规,剔除中饱,事事涓滴归公”(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370页。)。实质是企图收回部分地方财权,最终因地方督抚及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或搪塞、敷衍,毫无实效可言。然而,甲午外债的偿还,急不可待,按照过去户部和督抚之间互相推诿的方式,万难凑足款额,只有采取请旨向各省硬性摊派的办法了。光绪廿二年(1896),户部为向各省摊派偿还俄法及英德两款,向朝廷奏报:“查近来新增岁出之款,首以俄法、英德两项借款为大宗……应还本息,二者岁共需银12,000,000两上下……国家财赋,出入皆有常经,欲开源而源不开,欲节流而流不能骤节,其将何以应之?此非各省关与臣部分任其难不可……请分饬下各省将军、督抚查照臣部单开,分认数目,于各省所收地丁、盐课、盐厘、杂税及各海关所收洋税、洋药、税厘项下,除常年应解京饷、东北边防经费、甘肃新饷、筹备饷需、加放俸饷、旗兵加饷、固本京饷、备荒经费、内务府经费、税务司经费、本关经费、出使经费等项,仍照常分别批解留支外,其余无论何款,俱准酌量提划。各照分认数目,按期解交江海关道汇总,付还俄法、英德两款本息。”(注:沈桐生:《光绪政要》,第22卷,第16-18页。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紧接着,光绪廿七年(1901)9.82亿两的庚子赔款,清政府每年需筹款约2,200余万两,于是决定300余万两由解部款改拨之外,余1800万两“按省份大小、财力多寡为断”向各省摊派,全国除东北三省以外,19个省无一例外。并严令各省务须“竭力筹措,源源拨解,按期交付,不准丝毫短欠,致生枝节,倘若因循迟误,定惟该将军督抚是问”(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5,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页。)。以前,朝廷要求各省交纳款项多是采取商议的态度,地方当局也能抵制,并取得一些成功,而这一回,受外国干涉威胁的中央政府只能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各省的交款必须按月储存于上海,并没有商讨款额之余地。(注: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这样,光绪廿年(1894)至光绪廿七年(1901)间8项借款(铁路借款尚不在内)的各省摊解额,光绪廿一年(1895)为库平银9,219,000两,光绪廿八年(1902)增至47,724,000两,比清政府交与外国银行的本息银数还多收库平银250余万两。这8项借款所付本息银数,在光绪廿五年(1899),约占清政府财政总岁入额的25.9%和岁出额的22.8%,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约占总岁入额的41%和岁出额的31%。(注: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25页。)外债摊还的结果,使中央财政暂时逃过一大难关,但并非解决了财政的全部问题,反而使筹款重心由中央移向地方,进一步加剧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上的矛盾,加速了中央财权的下移和财力的外倾。这必然带来整个财政体制的变迁。
首先,沉重的战争赔款和外债,迫使清政府将地方大量“的款”用于抵押和指拨偿还外债。因担保外债而挪移的地方财源必须另行解决,而中央对此一筹莫展,这无疑更使各省有理由拒绝筹解京饷,加速了京协饷制度的瓦解。如英德续借款以长江各省厘金作抵,加剧了长江各省与中央在财政上的矛盾。此前,户部拟定七处厘金作抵,就遭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反对,因七处厘金改征抵借,江南骤短军饷洋款至一百八九十万两之多,他要求“将应解京协各饷捐款截留备抵”,并振振有辞地讲:“以本省之款,供本省之用,理势宜然。”(注:千家驹:《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页。)江苏厘金归税务司代征后,“水陆各军饷源顿竭”,要求户部“迅速接济”(注:《光绪朝朱批奏折》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奎俊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奏。)。户部无能为力。于是各省无视中央,截留中央之款的事屡屡发生。户部在一份奏折中抱怨说:“臣部总揽天下财赋,凡有大军大役,用款向由部拨……近年库款支绌,(各省)知臣部筹措之难,动辄自行电檄各省,求为协济……各省亦不尽能另筹的款,遂将例支正项及报部候拨者,挪移擅动以应之。迨臣部查知,而款已动用,往返驳诘,迄难就绪。”(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474页。)庚子后,情况更加严重。光绪廿九年(1903),各省关应向中央解款的专项经费数为2,500万两左右,当年户部银库实收数额包括其他各项收入在内,不过1,422万两。(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其次,外债摊还,使地方向中央的解款制由拨改为摊,同时也赋予地方以开征新捐税的权限,地方财政收支独立成为现实。中央在原有田赋税收之外责成地方筹款上解,无疑承认了地方在完成解京款项的前提下自收自支的地丁、盐课、厘金、杂税、关税等款项的合法性,各省自行摊派,自开捐费,名目繁多的“外销”款愈来愈多,中央逐步丧失对地方的考核、稽查、督察之权。20世纪初,直隶、江苏、湖北、广东等实力较强的省份,年度财政收入达到2000万两以上。(注:据刘岳云《光绪会计表》、哲美森《中国度支考》等估算。)与日益膨胀的地方财政相比,中央财政收支状况则急剧恶化,建立在借款基础上的财政总额日益庞大,赤字也越来越大。光绪廿年(1894)尚盈余75万余两,到光绪廿五年(1899)赤字达1,292万两,宣统三年(1911)赤字已上升到7,939万两。据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中央财政总收入已突破2亿两,而户部银库当年从各省所得到的直接款项仅为1,650万两,加上各省临时上缴的练兵费730万两,也不过2,400万两(注:度支部清理财政处,光绪三十四年部库出入款目表,北京图书馆藏。),仅占中央年财政收入的12%(注: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中央虽握财政机关,不过拥稽核虚名,无论田赋、盐茶,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内而各局院,外而各行省,乃至江北提督、热河都统,莫不各拥财权”,户部“仅有稽核之虚名”(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8,《国用六》,考8224。)。难怪时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北京政府之收入,不及海军衙门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两个衙门之多。”(注: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56页。)财权下移已成定局。
最后,“就地筹款”正式代替“就地筹饷”。甲午战争后,巨大的外债和赔款压力使得清政府已无力进行财政整顿,只得沿着“就地筹款”的道路继续推进。光绪廿三年(1897)闰三月,户部奏折称:“迭经钦奉谕旨,饬令各省考核钱粮,稽核荒田,开办蚕桑,振兴商务,并行令各省督抚就地筹款。”(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第235页。)光绪廿七年(1901)八月,户部又提出“各该督抚均有理财之责,自可因时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措”(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第957页。)。就地筹款名正言顺的成为地方扩大收入的途径,直接影响了晚清地方新政的举行,“各省之办新政,率就地自筹”(注:吴廷燮:《清财政考略》,《光绪时之财政》。)。地方大兴编练新兵、兴办实业,所需军政费用浩繁。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得一度沉寂的地方外债又逐渐增多,大约有50多项。各省除为补充地方财政亏空和维持地方金融、挽救市面而借款外,还通过地方官银号进行借款,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和宣统三年(1911)湖北两次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借款,1908年南京向汉口日本正金银行的借款,宣统三年(1911)湖北向德商礼和洋行的借款都是由官银号出面举借的。可见,新政无疑又增加了地方督抚的实力,中央控制调度全国财力的权力更加衰微。
清末财政格局的变化直接反映权力格局的变化。地方督抚帮助中央筹款还债,必然也要从中央分得相应的实际权益。因此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官制改革中,即使可以通过对地方督抚的任免、调职来加以控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由经济运作和经济利益分配所形成的地方自主的局面。(注:汤可可、周力:《甲午战后的清朝财政问题》,见《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汝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武昌起义一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各自为政,清政府陷入方州无主、众叛亲离的境地,灭亡在所难免。
三、清理财政——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终结
庚子以后,尤其清末最后几年间,由于先前外债摊还和争夺税款,使原本不明晰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更加混乱,中央对地方的收支情况更加无从了解,中央对地方近于失控。形势迫使清政府开始清理财政,但为时已晚,清理财政的结果未能从根本上遏止清廷中央集权的衰微,反而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光宣之际,中央财政严重入不敷出,地方财政也全面亏空。光绪廿九年(1903)中央财政收入10,492万两,支出13,492万两(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8,考8249。),赤字比庚子前增加一倍以上,宣统二年(1910)赤字为庚子前的三倍以上。财政收支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鸦片战争前,财政收支总额稳定少变,略有节余。鸦片战争后,关税、厘金和官业收入几占岁入的一半;支出主要是军饷、洋务和息债,辛亥年间三项支出共占岁出的70%,而行政经费不及岁出的9%。(注:《清史稿·志一百·食货六》。)清廷的财政经济实力的严重消耗,明显地反映其财政支出的半殖民地性质。
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对全国财政收支进行清理,财政管理制度及预决算方式的整顿与改革提上了日程。
财政清理作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重要措施之一,目标是以度支部为财政中枢,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办成财政预决算,加强对全国财政的监督控制,改变传统的“量入为出”为“量出制入”的度支原则,集财权于中央。为此,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577-5580页。)。光绪三十四年(1908)底,度支部、会议政务处重新议定清厘整顿章程,度支部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调查光绪三十四年出入款项,编制财政说明书。宣统元年(1909),提出清理财政的六项措施,首条即是“外债之借还,宜归臣部(度支部)经理”(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18页。),即“各省各部借外债,经度支部同意,由部借入转交各省、部,偿还借款由度支部负责”(注:转引梁义群:《清末新政与财政》,《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宣统二年(1910)起,清廷仿效西方国家制定预决算的新型财政体制,开始编制宣统三年和宣统四年全国预决算案。但甲午后,外债摊还和争夺税款已使得中央难以明了地方财政情况,所以在实际运作中度支部只好上奏请饬各省督抚将“何项应入国税,何项应入地方税,详拟办法,咨明度支部分别核定”(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956页。)。这样,就把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的标准下放给地方,出现各省编制地方财政预算计划时,自行其是,任意增减,弄虚作假的现象。另外,各省预算,经地方督抚核准后一面上报度支部,一面交各省咨议局讨论。但实际上度支部在编制全国总预算时,并没有将各省咨议局要求修正的收支补入。这样,财政预算收支出现了不平衡,如有赤字,应明确弥补之方法。但无论是各省还是全国的预算,都是以赤字预算交议。因此,在以后清政府和各省督抚通过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后,又与资政院和咨议局发生了种种冲突,后者无法制约行政部门的借债权限。(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页。)预算案成立后,各省督抚视度支部形同虚设,“纷纷请变异”,最后不得不取折衷方案,各官公费,“暂照部定数目办理”,其余各款,照“认定数目”(即部定院核准后督抚承认的数目)办理。可见,宣统二年(1910)的国家财政预决算试图从管理体制上改变传统的国家与地方财权不明的弊端,解决征收权与管理权矛盾的症结。结果却是地方的加收摊派反成“合法”,而中央预算徒具形式。分税制未及实行,财权仍然涣散。
一息尚存的清政府为维持苟延残喘,对外债仍是百般罗掘,以求“按期照付以维信用”(注:一档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外务部致驻日、美、俄等各使臣电》。),但这时中国的关税、厘金、盐课甚至田赋都被指作外债的担保,现已无可抵押;加之国内人民反对借债的呼声日益增强和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均衡,出现了清政府告贷无门的尴尬境地。自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清政府与“各种可能贷款给清政府的外国关系都曾予以洽商”(注:[美]欧弗来区:《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5页。),虽有某些国家政府或私人给以某些财政支持,但数额与作用并不太大。无奈之际,清政府电告各省督抚“现在时局危迫,库款告罄;筹措外债,又成画饼;累蒙慈圣颁发内帑,藉资挹注,刻已无可再发”,“倘不速筹的款,则哗溃即在目前”(注:一档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内阁、度支部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被迫公开承认财政已经崩溃。并“求各省分筹接济,稍救眉急”,“明知外省同一艰窘,惟势逼处此,万不能坐以待毙……务希分任其难以顾大局”(注:一档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内阁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然而,各省督抚或自顾不暇,或另怀它图,对清廷的“求援”应者寥寥。不仅如此,各省督抚拥军事、财政实力自重,还千方百计攫取清廷财权。有的地方督抚要求省借外债,“毋庸交咨议局议决”(注:一档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闽浙总督松寿致内阁电》。)。有的督抚竟然要求中央出面借款归地方使用,地方不负责偿还。山东巡抚孙宝琦于宣统三年(1911)首先明确提出“由政府出面商借外债”,然后“分配各省”以救危急。(注:一档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二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致内阁电》。)还有些地方督抚要求清政府为地方代筹代偿赔款及外债本息,或者干脆把外债负担推给中央政府。如两江总督张人骏要求清政府“向各国公使声明,江宁先后借款共700万两,统由国家担保”(注:一档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五日两江总督张人骏致内阁电》。)。还有的地方督抚直接向清政府伸手要款。宣统三年(1911)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请求朝廷“暂发内帑100万两以重根本”(注:一档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内阁电》。)。所有这一切表明财力的丧失意味着统治权的丧失,清政府濒临崩溃与灭亡的边缘。
清朝财政的半殖民地化,从根本上遏止了其摆脱财政危机的活力机制;晚清以来,传统的财政体系已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当财政危机爆发时,财政体制的变革就与整个社会的变革结合在一起,以挽回利权的革命方式推进清王朝的崩溃。但清末财政所遗留下来的巨额外债的包袱,以及国家的衰竭,人民的灾难,地方的割据,则长久地影响民国时期。
晚清中国,外债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中央政府对地方外债监管的失控折射着中央财权的衰微和中央集权体制的衰落。尽管不能说是外债灭亡了清王朝,但是外债却是影响晚清政局的一个制约因素,它是地方财权扩大的催化剂,又是间接导致清王朝衰弱的重要历史缘由。如果说监管失控在太平天国的特殊战争时期,还情有可原。那么,甲午战后,清政府面临外国强权、失去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不是从调整和改革中央体制做起,不是从规范和控制地方财权做起,反而为维护统治,将改革措施直接下放使之成为地方督抚的事,致使地方实力再次膨胀。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只是在各项政策推行并与中央体制发生矛盾后,才深切地感受到中央财政制度调整的必要性,并力图通过清理财政来削弱地方、集权中央,但外重内轻、积重难返的局面已成定局,制度的变革早已落在了政策变革的后面。
标签:光绪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代论文; 晚清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续文献通考论文; 光绪朝东华录论文; 地方财政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