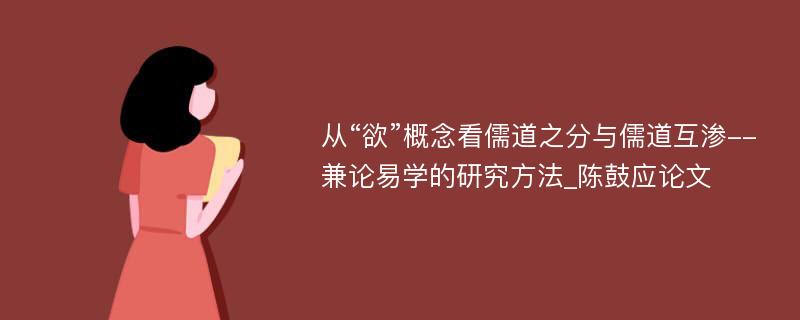
从“要”这个概念看儒道分野及儒道互渗——兼论易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道论文,分野论文,易学论文,这个概念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0)04-0027-08
马王堆汉墓帛书《六十四卦》和帛书《易传》陆续公布后,大大深化了对早期易学史的认识,激发了当代学者的研究热情和研究灵感。新作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新见层出不穷,令人振奋不已。特别是,陈鼓应先生一反传统观点,提出《易传》的哲学观点属于道家而非儒家的新观点[1],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在讨论和争鸣中,有些学者赞成和发挥了陈鼓应先生的基本观点,如胡家聪、王葆玹等先生(参见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1]附录二);有些学者反对陈鼓应先生的基本观点,如陈来[2]、吕绍纲[3]、廖名春[4]等先生;亦有一些学者另立新说,如余敦康[5]先生。目前,这场讨论正在深化进行之中。
这场讨论和争鸣不但涉及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许多具体问题、特殊问题,而且涉及了许多一般问题、方法论问题。为了使这场讨论和争鸣达到一个新水平,进入一个新阶段,避免争论中“各说各的话”、“交锋错位”的现象,实有必要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加强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可以预期,在这两个方面(或曰两个方向)研究的良性互动中,不但可以大大深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而且可以有力地深化对若干一般性问题和方法论问题的认识。
本文以下将分两个部分分别谈谈作者对易学研究中若干方法论问题和若干具体问题的粗浅看法。
一
在中国,历史学有很悠久的传统。唐代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云:“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赵鞅,晋之一大夫尔,犹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耳,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令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20世纪甲骨文的发现及其研究已证明中国古史所记录的商代世系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但以上所述的“重视真实地记录历史”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王朝和世系或如今日所说的“政治史”的范围;如果谈到思想史和学术史,那就另当别论,情况大有不同了。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云:“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去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章学诚认为,正是在“言公”思想的指导下,师徒相传,“推衍变化,著于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
这种无法分辨(甚至是有意或无意混淆)“孰为师说,孰为徒说”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给当代学者研究古代思想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当代学者在研究古代易学史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同样的困难。
然而,最大的困难——更确切地说是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言公”的困难和问题。
在这里,最大的问题——说得严重一些——是某种程度的歪曲历史、抹煞历史甚至篡改历史和伪造历史的问题。
在学术和思想领域,往往是存在着不同派别的争鸣和斗争的。争鸣和斗争的结果又往往是一派的胜利和其他派别的失败,而胜利者为了一己之私又常常歪曲甚至伪造有关的历史。齐思和先生在《黄帝制器的故事》一文中曾考证了许多制器发明(属于“技术”)传说的“演变之迹”。在中医史上,战国和秦汉时期,扁鹊学派是影响最大、享誉最高的学派,可是,在黄帝学派取得胜利后,中医史被编造为黄帝学派和《黄帝内经》的一元传承史,扁鹊学派的历史存在被抹煞了。[6]
在易学史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在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初黄老之治之后,是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终结的。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之中,早期的易学史也被编写为儒学史,特别是经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汉书·儒林传》中记载了一个传《易》的系统:“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这是一个为儒家所垄断的一家和一元的传《易》历史系统,它完全抹煞和否认了战国时期其他学派同易学发展的联系。
自汉代至清代,儒家的独尊地位从根本上说未曾动摇,相应地,把早期的易学史唯一地归属于儒学史这个基本的“历史认识”也没有什么变化。自80年代末以来,陈鼓应先生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出和论证“《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属于道家”,这确实是对传统的易学史观点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认为,陈鼓应这一系列论文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突破了——甚至可以说“摧毁”了——把战国和秦汉的易学史“定性”为儒家一派和一元发展史的传统历史观点。对于陈鼓应先生在《易传》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和其观点的重大启发意义,我们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虽然陈鼓应本人在其《易传》研究中,强调的重点是《易传》的道家性质,而不是战国和秦汉时期易学的多元性;但以传统的易学史观为背景,应该承认以陈先生的观点为基础,战国和秦汉时期易学史的多元性和多元观已经是呼之欲出和水到渠成了。
目前,已有多位学者明确提出和主张多元的易学史观。例如,张立文先生说:“汉代司马迁和班固所记载的易学传承谱系,可能只是指儒家一系而言。”张先生又说,战国时期,“儒、道、墨、法、阴阳五行、兵各家,都有可能对《周易》作出自己的理解或解释。这种理解或解释又与当时地域文化传统相关联,如邹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等,带有地域文化特征。”[7]邓球柏先生也说:“我们初步认为,秦汉已出现了阴阳易、儒易、墨易、兵易、法易、名易、道易等易学流派。帛书《系辞传》很可能是各家易学流派的总汇。而《二三子》显然是儒易,《易之义》是为阴阳易。”[8]
容易看出,在承认学术上存在着百家争鸣的前提下,承认在易学领域中也存在着不同学派和不同流派的易学实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相反,如果肯定社会上大的学术环境是百家争鸣,同时又单独认定易学领域中却是儒家的“一家独鸣”,这是有些难以想象和不大合乎逻辑的。
作为一个一般性的论断,肯定在战国和秦汉时期存在着若干不同学派的易学,即肯定这个时期的易学史的多元性,在目前似乎已不是一件难事。目前易学研究中,不同意见分歧的焦点常常集中表现在如何叛定具体作品的学派归属和如何确定一个易学学派之能够成立的标准的问题上。
这就是说,对于从春秋末年到汉初的早期易学史有两个大问题的。
第一个大问题是:这个时期的易学史是一元史还是多元史?
第二个大问题是:划分和判定一个易学学派与判定一篇作品的学派性质的标准是什么?
很显然,这两个问题是有密切联系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我们可以回答说:种种迹象和证据表明这数百年的易学史既不是儒家易学的一元传承史,也不是道家易学的一元传承史,而是多学派的多元发展史;它甚至也不是儒道两条互不交错的“平行线”“平行前进”的历史,而是更多学派(究竟有几个学派可以成立则仍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及“亚学派”(例如有人指出的道家易学中的“黄老易”和“庄老易”)互斥又互渗、多条线索交织、呈现某种“网络化”图景的历史;它既不是单纯的“残途同归”史,也不是单纯的“同途殊归”史,而是“殊途同归”和“同途殊归”的“双相”历史。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判定一个学派及一篇作品的学派性质的标准和方法的问题,当代的许多学者实际上是持有某种“本质论”的观点和采取某种“样板匹配”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自己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而认定(或设定)某一学派的“本质特性”作为标准,如果认定某一作品可以与此“样板”有较好的“匹配”,则认定该作品属于这个学派,反之,则认定该作品不属于这个学派。
由于不同的学者在设定某一学派的“本质特性”时往往有不同的观点和设定,再加上在进行“样板匹配”时不同学者往往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操作”,于是就常常出现同一篇作品被不同学者划不同学派的现象。
应该承认,要具体地确定一篇作品的学派性质,有时可能是一个很困难、很复杂的问题。
在本文的这个部分里,我们关注的焦点不是划分学派性质的具体问题,而是划分和认定学派的一般性的“准则”和方法论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研究中提出了“家族相似”(familyresemblances)这个重要的哲学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维特根斯坦说:“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似性: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禀性,等等,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9]“这种亲缘关系并不是什么性质的相同或者构成成份的相同。它能像链条一样将它的诸成员联系起来,使得其中的每一个都与另一个通过中间环节而互有联系;两个彼此邻近的成员可以有共同的特征,彼此相似,而彼此相距遥远的成员间则不再互有共同之处但还是属于同一个家族的。而且即使存在着为一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所共同具有的特征,它也不必就是这个概念的定义特征。一个概念的诸成员间的亲缘关系可以通过它们之内的特征的相同与否加以确定,而这种共同性在该概念家族中是以极为复杂的方式交错出现的。”[10]
我认为,对于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包括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学术史在内)来说,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方法。
虽然我们大家在生活经验中都很熟悉家族相似现象,可是,许多学者在研究思想史、学术史时却很少想到应该运用“家族相似”的分析方法,而宁愿采纳“本质论”和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共相问题时的“实在论”观点和方法。由于可以看到当代学者在应用“本质论”和“实在论”观点和方法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出现了许多问题,现在确实已是需要我们更深入、更认真地考虑“家族相似”论和“家族相似”分析方法的时候了。
我认为,为了更好地应用“家族相似”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有必要再补充“家族差异”和“跨家族相似”这两个概念。
如果说,“家族相似”强调的是同一家族内部不同成员间的相似性;那么,“家族差异”强调的就是不同的家族的成员(例如儒家的成员和道家的成员)之间的差异性,而“跨家族相似性”则又承认不但同一家族内部的不同成员间可以有相似性,而且不同的家族的成员间也可以存在某种相似性,当然,“跨家族相似性”是一种与“家族相似性”很不相同的相似性。
可以认为,家族相似鉴定和分析,家族差异鉴定和分析、跨家族相似鉴定和分析,这三者就是家族相似理论和方法的最主要的内容和方法。
在进行家族相似研究和分析时,我们不但需要研究和分析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成员的相互关系,而且需要研究和分析处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成员间的相互关系,用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话来说,我们需要把同时性分析(synchrony)和历时性分析(diachrony)结合起来。
二
一般地说,对于以下几个观点,不同学者是容易达成共识的:(1)儒家著作(或儒家学者)组成了一个相似的“家族”;(2)道家著作(或道家学者)组成了另一个相似的“家族”;(3)儒、道之间存在着“家族”差异性,即存在着儒、道分野;(4)儒道之间也还存在着相互渗透的成份,即存在着某种儒道之间的“跨家族相似性”。
这几个命题不但适用于认识和分析儒道两家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而且适用于认识和分析儒道两家的易学思想和易学著作。与此同时,我们又要承认把这几个观点应用到分析儒道两家的易学著作和易学思想时,是一件比分析儒道两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更加复杂和更加困难的工作。
在研究和分析从春秋末年到西汉时期的易学史,研究这个历史时期中儒道两家的易学著作和易学思想的相互关系时,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可以肯定地说,有许多著作都失传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历史链条”或“历史网络”只是片断的、残缺不全的,有许多历史环节已经缺失了。
诚然,也有一些著作流传到了今天。但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许多古书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颇长的历程,而不是成书于一时和成书于一人的。有人说,古书的形成,“是一个长过程。它是在学派内部的传心过程中经众人之手陆续完成,往往因所闻所录各异,加以整理方式不同,形成各种传本。有时还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老师的东西和学生的东西并不能分得那么清楚。”[2]实际上,问题大概还要更加复杂,因为我们可以肯定古人所能读到的古人的“当代”和古人的“古代著作”中有许多是后人所不知道的,我们万万不可认为今人所掌握的著作就是古人所能看到的全部材料;由此,我们也便有理由推测,在古书流传中,徒弟在整理本学派的著作时,不但有可能附益老师的“口述观点”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且有可能汲取和附益其他学派的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和材料。可惜的是,后面这种情况,我们常常是无法拿出确切证据的。这就使得后代学者在研究这类问题时陷入了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两难困境:如果大胆推测,就难以避免犯言而无据的错误;拒绝进行推测,又要犯把“最终结果”当成“历史网络”,把个别历史环节看作整个历史链条的错误。面对这种两难困境,不同的学者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态度,而这种不同态度又往往是造成学术研究中意见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以下将采取不拒绝进行推测的态度,当然,在进行推测时也要尽可能的持慎重的态度。
本文以下分析的重点是帛书《要》和《易之义》的若干问题。
在帛书《要》和《易之义》两文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对“要”这个概念和方法的格外重视。
《要》云:“子曰:吾好学而免闻要……”。《易之义》云:“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要》云:“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要》还直接以“要”作为篇名。由此可见,《要》和《易之义》的作者是有意识地和十分明确地把“要”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来理解和运用的。
这向我们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黄帝四经》中《经·成法》(原名《十大经》,今从李学勤先生说改名为《经》云:“百言有本,千言有要,万言有葱(总)。”《道原》云:“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得事之要,操正以政(正)畸(奇)。”但就《黄帝四经》全文来看,“要”只能算是一个重要概念,还不能说是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
再看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其论道家则曰:“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又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主劳而臣逸。”然后又用“在道之要”总结道家思想。文中还批评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再加上“论六家要指”这个实际上的“篇名”,可证司马谈理解的道家思想体系中,“要”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
《鹖冠子》一书中,不但“著希第二”和“天则第四”两篇中谈到了“要”这个概念,更值得注意的是“度万第八”开头的一段话:“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与神谋,道与人成,愿闻度神虑成之要,奈何?鹖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湿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猛刑颇则神显,神湿则天不生水,音声倒则形燥,形燥则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则阴阳无以成气,度量无以成制,五胜无以成执,万物无以成类,百业俱绝,万生皆困。”又曰:“凡问之要,欲近知而远见,以一度万也。”这个“以一度万”的观点同《要》所云“能者由一求之,所谓得一而君(群)毕者”也是如出一辙的。
值得注意的是,申不害和荀子也很注意“要”这个概念和方法。
《申子·大体》云:“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荀子·王霸》云:“治国有道,人主有职”,“人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明主好要,而阇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
对比分析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在“要”这个“结合点”上,儒、道、法三家之间是存在着“跨家族相似性”的。而这种“跨家族相似性”又是学派内部的历史继承性和跨学派的思想渗透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认为,“要”这个概念和方法首先是由《黄帝四经》提出来的。在《黄帝四经》中,“要”是一个重要概念,但还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到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中,“要”的重要性就大大提高了,简直可以说已成为一个带有纲领性的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方法了。而在《鹖冠子》一书中,“要”的重要性又介于《黄帝四经》和《论六家要旨》之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家族相似性。
许多人认为申不害是法家,但《史记》又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从“君要臣详”论来看,申子之学确实有本于黄老之处。但《黄帝四经》中作为“千言有要”之“要”是一般的思想方法论原则,而申不害的“君要臣详”之“要”却是政治学——特别是君臣关系论——原则,在某种思想继承性之外,我们又看到了某种差异性。如果没有韩非对申不害的发挥,如果没有形成以申不害、韩非为法家人物的思想定势,单纯就申不害本人的思想,也许未尝不可把《黄帝四经》同申不害思想的相似性看作家族相似性;可是,一旦形成了那种思想定势,人们大概就更愿意或更倾向于把这种相似性看成跨家族相似性了。
对于《荀子》一书中的“君要”论,大概许多学者都会认为这是其与黄老学派之间的跨家族相似性的表现。但就这个具体观点而言,荀子的思想同申子的思想有更直接和更明确的继承性,是申子思想在荀子思想中渗透的表现。
帛书《要》和《易之义》的重见天日,一方面使我们重新得到了一个曾经“遗失”的历史的环节,使我们在分析和确认家族相似性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新成员,一张重要的“新照片”,一个新的“参照物”;另一方面,它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从前引文句中可以看出,从对“要”这个概念的整体理解和把握来看,《要》和《易之义》同《论六家要指》有最大的相似性。
对于《要》和《鹖冠子》,已有学者指出:“《鹖冠子》与帛书《要》篇有着深刻的可比性”,“《鹖冠子》的思想倾向与用词多与《要》篇相近”,[11]也就是肯定了二者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文中对“要”这个概念的分析是支持这个结论的。
在《黄帝四经》中,“要”主要具有方法论含义;而在《申子》和《荀子》中,“要”主要是政治学和君臣关系论方面的含义。在《要》和《易之义》中,也首先是在方法论的含义上理解“要”的,帛书《要》讨论的政治学重点是“君道”,而不是“君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要》、《易之义》和《荀子》、《申子》的某种差异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易之义》和通行本《系辞下传》第五章一段文句的异同。《易之义》云:“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以矣。键、川(乾、坤)也者,易之门户也……”;而《系辞下传》则曰:“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两相比较,《易之义》多出“易之要,可得而知矣”一句,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一句话又是有生要意义的一句话,而不是无足轻重的一句话。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乾、坤,其易之门邪”及其以下数句话只于通行本《系辞》而不见于帛书本《系辞》。
出现这个差异的原因,大概有四种可能。第一种可能:通行本出现在先,帛书本出现在后,帛书作者增添了“易之要”这句话;第二种可能:帛书本在先,通行本在后,通行本作者删去了“易之要”这句话;第三种可能;有一共同祖本,通行本沿袭祖本,而帛书作者增添了“易之要”这句话;第四可能:有一共同祖本,帛书本沿袭祖本,而通行本作者删去了“易之要”这句话。
总而言之,“易之要”一句不可能是无意的漏抄,而只可能是特意的增添或特意的删除;而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其共同的结论都是一个: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重要的差异性。
如果说,“博而寡要”和“秉本执要”是儒道两家的一种“一般性”的家族差异性;那么,是否强调“易之要”就成为了儒道两家易学思想方面的一种家族差异性了。
蒙文通先生早就指出,道家中既有排斥仁义的流派,又有不排斥仁义的流派。《吕氏春秋》、《淮南子》和《论六家要指》都有兼综儒墨的特点,可以从中找到许多儒家思想渗透的成份或因素。《要》和《易之义》中也都有许多儒家思想的成份,即便是力主《易传》道家归属说的陈鼓应先生也承认“《二三子问》、《易之义》、《要》这几篇古佚易说,若从学派性质来看,形式上是属于儒家的作品,然其中却渗透着不少黄老思想”。[1]陈来先生持论与陈鼓应先生不同,但陈来也说:“帛书《易传》与今传《十翼》应有关系,它们应同属孔门易学的不同传授系统,且互有影响。”[2]
就吸收儒家思想而言,《要》和《易之义》同《吕氏春秋》、《论六家要指》、《淮南子》之间是存在着某种相似性的。若依上引陈鼓应的观点,这是一种跨学派的相似性。但也有学者认为帛书《易传》是一组同一学派的文献,依此观点,则在承认帛书《易传》是道家文献的前提下,必然得出《要》、《易之义》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与方法同司马谈等人的相似性是某种家族内的相似性。
许多学者在帛书《易传》同今传《十翼》之间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这一点上是没有争论的,目前的争论焦点是:这种相似性是学派内的家族相似性还是跨家族的相似性?这种差异性是学派内的差异性还是不同学派家族之间的差异性。
应该承认,这是目前尚未完全解决和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从《要》和《易之义》这两个新发现的易学历史“环节”来看,许多迹象表明:儒道两家的易学思想在战国至汉初的数百年间是经历了一个多次和多重的既有相互渗透、交叉,又有相互排斥、背反的过程的;既使用了“拿来主义”的方法,使自己的著作中出现了对于“对方思想成分”的新组合、新解释,又使用了“剔除主义”的方法,从而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了某些“剔除操作”的痕迹或留下了许多进行批判和“大唱反调”的成分。在今传本《易传》和帛书《易传》中,这两种不同的历时性运动轨迹和学术方法运用的痕迹都是可以发现的。《黄帝内经·素问·征四失论》批评了当时医学界存在的“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的现象,可以推测这种现象在易学中也是存在的,只是在个人的眼中看来,这种“受师不卒”“更名自功”的现象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本文中谈了作者对若干具体问题的看法,但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强调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家族相似的观点和方法是一种比“本质论”观点和方法更适用、更恰当的观点和方法。
最后还需顺便指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帛书《易传》和今本《十翼》各自的内部都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对待“要”这个概念的看法中的矛盾就是一例),似在提示我们:某些文献在传授和写定过程中有可能经历了跨学派的过程。正是基于这个估计,本文第一部分说从春秋末到西汉初的易学史不但是多元化的历史,而且是多条线索互相交叉和交织、呈现某种网络化图景的历史。
收稿日期:2000-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