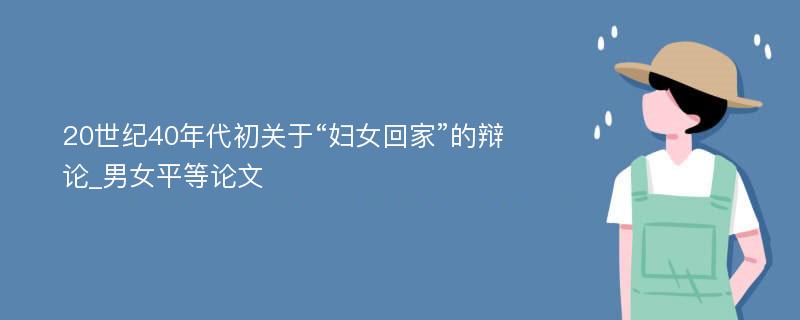
20世纪40年代初关于“妇女回家”问题的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年代初论文,妇女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6)03—0138—07
抗战爆发后,已经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中国职业妇女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从而扩大了抗战初期妇女职业活动范围。然而不久,国统区出现了一股提倡“妇女回家”的逆流,公开宣扬妇女不应该从事职业活动,而应该回到家庭做贤妻良母。为了捍卫妇女职业权,一批先进妇女和进步男性纷纷发表文章进行反击,于是在1940—1942年间形成了一场关于“妇女要否回家”的论战,对妇女职业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场论战中,一批进步人士尤其是女性开始对生理决定论进行批判,并对妇女解放途径进行追寻,为我们今天构建公正的社会性别制度,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材料。
一 “妇女回家论”的提出
随着民初女权运动的兴起和五四思想的解放,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妇女在经济、教育、婚姻、参政和法律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权利,妇女进入社会、参与社会开始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却存在很多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妇女回家”的反动言论。
抗日战争初期,为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需要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对抗战活动积极支持与参与。1938年5月, 国民党改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职业的发展,一时阻塞了“妇女回家论”者的舆论渠道。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把打击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力图将妇女运动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 以限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1940年,国民党浙江执行委员会制订了《非法妇运防止办法》,严密考查和防范所谓“某党非法妇运活动”。此办法推广到国统区各地,致使许多职业妇女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庭,这为“妇女回家论”的活跃提供了市场。1941年1月,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妇女运动干部会议,再次将三民主义确定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最高指导方针,提出了“妇女回家”的主张,要妇女“加入国民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还制定了“奖励生育”等四条要旨[1](16页)。 国民党的妇女政策不仅鼓励了社会上歧视和裁撤女职员的风气,而且成为了“妇女回家论”的官方依据。
就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大约在1939年初,报刊上就出现了宣扬反动政治的主张。1939年5月30日,叶青在《时代思潮》第1期上发表《三民主义底创造性》一文,以研究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为名,否定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说:“三民主义所以要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合而为一个主义,在于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合而为一次革命了”,“至于一次革命底进行,……换一句话,就是以民生主义代替布尔塞维主义”[2](458—464页), 从而达到鼓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目的。1940年4月以后, 随昆明《战国策》半月刊的创办而产生的“战国策派”,以陈铨《论英雄崇拜》和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为代表,公开宣扬意志哲学、英雄史观和法西斯战争观,认为:“人类意志是历史演化的中心,英雄是人类意志的中心”,拿破仑、俾斯麦和蒋介石等人就是这样的英雄,对他们要“忘记自我”地去崇拜[3],而此时“是又一个‘战国时代’的来临”,因此中国需要“纯武力”的统治[4]。 反动专制政治的权威必然需要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维护,结果封建思想与封建礼教同反动专制政治相伴出现。
1939年9月,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讲话中,蒋介石公开要求,“伦理建设就是国民道德建设,要以总理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精神,以昌明我国固有的人伦关系,即所谓五伦”;“五伦中君臣关系,表面上看,现在似乎已过去不适用,但实际在解释上不可泥于一义”[5](12—13页), 实质是要人们忠于蒋介石本人。受其影响,一些学者纷纷倡导中国传统礼教。钱穆在《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文中说,中国文化已到了“应该鞭策向前”的时期,怎样鞭策呢?“第一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观念”[6](23页),在这里, 钱穆暗示中国要采用封建社会的精神才能求得发展。钱穆《孔子与心教》一文在阐述孔子的心教后指出:“只因有孔子的心教存于中国,所以中国能无需法律宗教的维系,而社会可以屹立不摇。此后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实有盛唱孔子心教之必要。”[7](23页) 此外,林语堂《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梁漱溟《中国以什么贡献给全世界》、陶希圣《论道集》等都对封建传统礼教思想进行了宣扬。封建礼教隐含“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歧视和性别分工观念,自然容易引发“妇女回家”的言论。事实上,这些封建礼教持有者正是“妇女回家论”的倡导者。
同时,战时国民经济的衰退也造成了“妇女回家论”的客观条件。1938年,武汉失守,国民党迁都重庆,政府机关、工商企业、医院学校以及大量人口纷纷内迁,这必然增加经济发展极为落后的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负担。尤其是1942年以后,由于战争影响,许多工厂企业倒闭或停工减产。1944年,受河南战役和湘桂战役影响,国统区工厂损失21%左右[8](197页)。国统区经济凋敝,导致各部门紧缩规模,缩减编制,裁减职员,职业妇女首当其冲,“妇女回家论”更成为裁撤和拒用女职员的借口。
1939年7月,福建省主席陈仪公开宣称:“在二十年之内, 一般的妇女不可能享受平等的社会地位。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妇女,她一出嫁,丈夫和孩子就剥夺了她社会服务的机会,对社会贡献最大的就是管理好一个家庭。”[9] 12月,陈仪又在《我们的理想国》演讲中进一步指出: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将来妇女生活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家庭中”,“妇女们在家庭中第一件事,就是教养儿女”,“其他家事的管理及煮饭、烧菜、做衣服等等,都是女子应做的事”[10]。到1940年,鼓吹“妇女回家”的言论日渐增多。1940年7月6日,端木露西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蔚蓝中一点黯澹》一文,指出:“从五四到民国二十三年,妇女运动所得到的成就,除了男女同学,机关里有了少数的女职员、女官吏以外,我们实在看不出这一运动对于一般妇女的心灵修养上给了什么解放的效果”,“过去妇女运动太注重解放的形式,而忽略了妇女跑进社会以后一种更重要更基本的做人的态度和知识”,由此得出,“在现代的社会制度组织之下,我们不能否认在二万万多的女同胞中,无论她的阶级如何,十分之九的妇女归根到底还是在家庭里做主妇,做母亲的。在这种社会制度没有彻底改革以前,一个女子为了她自身的幸福,似乎也有权要求享受一个幸福的家庭吧,而这一种家庭最主要的是必须她自己先做一个好主妇,一个好母亲”,故而主张妇女应该“在小我的家庭中,安于治理一个家庭”。
同时,尹及、沈从文等人也在《战国策》上发表文章,鼓吹妇女回家,将“妇女回家论”推向高潮。尹及《谈妇女》一文,通过所谓生物平等和政治意义来证明妇女应该回到家庭。他说,男女双方是生物界的一员,平等分担延续生命的责任,女人的真正位置是在家里,“因为只有在家里才能得到真正的、生物的、长久的平等,在家外——譬如说,参政会——得到的平等是假的”;从大政治观点看来,女人的真正地位也是在家里,因国力取决于人力,“人力之创造只有女人可担任”,所以妇女须回到家庭,“她们的真正自由是在丈夫的自由里,真正的个人职业是在婚姻里”[11](9、10、12页)。 沈从文《谈家庭》一文论述了家庭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他指出,妇女之所以求解放争平等,是由于“她们之中大多数就并不明白自己本性上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因而他认为,要使妇女回到家庭,“对家多发生一点兴趣,多负一分责任”,“努力来安排一个家”[11](14、18、19页)。沈从文还在《男女平等》一文中指出:“事实上许多方面既不相同,求平等自必相当困难。不平等永无‘高下’,无‘是非’,只是有一点‘差别’。”“中国古代政治家,早看出了这种差别可能发生许多问题,想用人为的方式求其平等,礼教由此产生,礼教中谈及男女问题虽云‘男尊女卑’,其实在家庭制度中给了女子一种绝对平等观。”“到近代,平等观重新被提出,妇女问题也因此而起……也可以说起因于男女两方面的知识不够,……在‘男女平等’的名词上各执一端,纠缠不清。”其实,“女性若明白一个家对于母性本能发展的重要性”,回到家庭,建设一个幸福而又不丧失现代女子所需要的自尊心的家,妇女问题就简单多了[11](21—23页)。尹及、沈从文二人的文章从理论上提出和完善了“妇女回家论”。
二 围绕“妇女回家”问题的论战
“妇女回家论”一出现,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遭到妇女界和进步人士的反击,国统区各大妇女刊物和主要报刊都成了论战的战场,论战主要集中在福建、重庆和桂林三地,其中重庆和桂林又是这场论战的中心。
在福建,除了广大女同学通过标语、传单等与陈仪的观点进行辩论外,更多的进步妇女则在妇女刊物上发表文章,如《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发表《六百万人的职业潮》、《妇女共鸣》发表《回厨房去口号下的福建妇女》、《浙江妇女》发表《为福建职业妇女呼吁》等数十篇文章,批驳陈仪的“妇女回家”论,其中《六百万人的职业潮》一文最具代表性。文章指出:“抗战前的福建妇女过着的是枯寂平静的生活”,然而,“伟大的抗战在她们止水般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许多妇女走出了家庭,或者分出了一部分的时间献身抗战工作”,在福建妇女正积极争取工作机会的当时,陈仪却要剥夺妇女服务社会的机会,“这不单只是个人的苦闷,实在更是国家的损失”[12]。
在重庆,女界及进步人士主要在《大公报》、《妇女新运》、《妇女生活》、《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江西妇女》、《浙江妇女》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从各种角度回击端木路西的“妇女回家论”。1940年7月22日, 喻培厚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蔚蓝中的一点黯澹”之商榷》一文,从人类负有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保护两种责任,说明妇女除生育责任之外还有社会责任,“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母亲要有职业,每一个职业女性都是贤良的母亲”。7月27—28日,夏英喆发表《怎样认识现阶段的中国妇女运动——“蔚蓝中一点黯澹”读后感》一文,从消除男女不平等的经济根源上驳斥端木的言论。他说:“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就是因为妇女脱离社会劳动,经济上仰赖男子,所以才被叫做寄生虫。妇女要求与男子平等,当然应当从参加工作、求经济独立入手,可是端木先生叫妇女做主妇,回到家庭去,这不是根本违反了男女平等应从经济入手的原则吗?”[13] 中共南方局妇女委员会领导人邓颖超撰写《关于“蔚蓝中一点黯澹”的批判》一文,指出:端木露西的言论“正代表着大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悲观失望的没落反动情绪”,“正是这一年来复古倒退逆流在妇女问题上的反映”,其目的是“将妇女解放和国家社会解放分开来,在抗战的伟大时代,幻想着‘小我家庭’,个人主义的自私的‘新’贤妻良母”,“以此去反对和阻碍妇女做人”,“在客观上亦正和敌奸玩弄奴役妇女的办法,起了应声”[14]。此外,沈兹九《关于女子的天职问题》、胡子婴《怎样扫除“蔚蓝中一点黯澹”》等文章也有力地反击了端木的“妇女回家论”。
值得指出的是,在重庆和福建,端木露西和陈仪并没有回应女界与进步人士对他们的驳斥,也没有其他支持这二人的观点出现,因此事实上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舆论交锋。然而,在桂林则完全不同。1941年,当一批先进妇女和进步男性起来驳斥尹及和沈从文的言论时,虽然沈、尹二人并未回应,但却有一批封建文人站出来捍卫他们,于是演成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主要是以桂林的《力报》副刊《新垦地》为中心,交锋双方共发表了40多篇文章。论者针对的对象各不相同,而争论的主题却是一致的。综观这些文章,论战的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何为男女平等,二是形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三是怎样实现男女平等。
关于何为男女平等的问题,“回家论”者有几种论点。一种论点认为,“男女平等已经是一件生物界的事实”。因为“性的作用,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尽致,性的行为上,男女相遇,绝对是平等者的相遇”,所以,“男女的平等应建筑在生物的平等之上,因为只有这种平等才是相容、相成、相辅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相拒、相争、相消的平等”[11](8—9页)。另一种论点认为,男女不平等属于男女双方在名词上的纠缠不清,其实并无高下,“只是有一点‘差别’”[11](21—23页)。还有一种论点认为,“所谓真的平等, 就是大家的立脚点站在一条平线……因为大家的使命不同,所以各有各的任务。男人治外,创造经营,女人治内,继往开来,这是生存赋予的使命,天经地义的平等。妇女要自己的地位、工作,达到和男子一样,这是假平等”,“我们不应说把平等看成机械的东西,以为男子能做的工作,女子一定也要会做,才算平等,如果真正为国家利益为人类进行打算,无论男女都应该选择与他(她)最适合的工作做”[11](123、154页)。甚至还有人认为,妇女参加生产,获得劳动机会,就是男女平等。“看看广西乡村的妇女,湖南湘西的妇女罢,他们不用你去喊家庭解放,也会走出厨房,不用你宣说平等,他们已经和男性平等了,有时男性反蹲在家里煮饭,待孩子,女人却出外面参加社会活动”[11](166页)。显然,在“回家论”者看来, 男女平等就是纯粹的生物性的平等,或者是一种基于生物性别差异上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制度。对此,反“回家论”者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的动物,而不是与一般的生物一样只具有本能的动物”[11](66页)。男女平等是社会的平等而不是生物的平等,“真正的平等是基于男女的经济平等,经济平等以后,才能谈得到国家,文化,及社会,政治,生活一切方面的平等”[11](79页)。经济的平等并不是劳动机会的平等,“湖南、湘西、广西乡村妇女确实都在劳动,但是湖南、湘西、广西的男子都还是在买卖老婆,还是在虐待老婆,还在娶童养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女人还少一样东西,就是政治经济上的独立人格,所以她们虽然也在劳动,实际上和农民家里一条牛在劳动,意义是差不多的”[11](182页)。同样,“真正的平等,并不是‘同样化’,妇女所要求的平等也不是要把自己‘男性化’,真正的平等应该是基本上的平等,一切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去发展,自由去为社会服务”[11](72页)。
显而易见,如果按照“回家论”者的男女平等观来看,中国早已不存在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因为妇女一直在从事生产劳动,而且男女之间在单纯的性关系上已经平等。但是,为何在事实上却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呢?“回家论”者认为,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是自然的,是由于生理的限制导致的。“不管社会上对于妇女们如何看待,不管社会上的环境如何于妇女们不便,这都是由于妇女们自己引起来的。妇女们的生理与男子们不同,是引着妇女在社会上向她们自称为不利方面去的关键”[11](131页),这种“差别既是根本上的”, 妇女“要求的又疏忽了这个根本上的‘不同’”[11](22页),结果就出现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换言之,男女本无不平等,都是因为妇女自己不顾生理差异,提出不合性别特征的要求而出现的。对于这种说法,反“回家论”者明确指出:“我们要认清楚,男女的不平等并不是由于性的关系的不平等,而是由于彼此在社会上的经济关系不平等而来的。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等方面的不平等”[11](71页)。“上古时代的男女不仅在生产上,甚至在战斗上都是绝对平等的,所以并不因性的特质产生高下。但后来因为经济条件的变化——主要是劳动农业的发达,妇女地位便由基本劳动降到辅助的地位。到私有制度以后,集体的共同经济被破坏了,个别的经济单位出现。妇女更被逐渐从生产地位排挤到更次要的,如织布,缝纫或非生产性的工作上——如管理厨房,哺育孩子等等”,妇女“便愈丧失其独立人格”[11](192页),结果就形成了男女不平等。在这里, 反“回家论”者从社会关系和历史生成上寻找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以此证明男女不平等不是与生俱来的生理因素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由于论战双方在追寻形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时得出的结论不同,因而在关于怎样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上也完全对立。“回家论”者认为,妇女要想得到平等,只有回到家里,“因为在家里,女人的地位是为妻为母,为妻为母而做到贤与良,则女人的真正平等就得到了。当她为妻为母时,她不怕丈夫以不平等待她,因为她当具特有‘性’的武器,可用以强迫男子就范,他就范时,平等——生物的,真正平等——就得到了”[11](9页)。此外,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将男女关系重新给予一种解释,在分工合作情形上各自产生一种尊严感,这尊严感中实包括了权利和义务两种成分。义务不能相同,权利也容许有不尽同处,到那时女子‘得到一切’的幻想或者自然会承认事实,改为‘得到所能得到的’”[11](22—23页),这样也就没有什么不平等。这种观点实际上暗含了不存在真正的男女平等。对此,反“回家论”者严正指出:“妇女问题的具体内容,主要的是妇女职业问题,妇女劳动问题,妇女参政问题,妇女教育问题及婚姻问题等。所有这一切问题,都属于社会问题的范畴,而绝不是什么生物问题,也不能用生物的平等去解决。”“我们的路是发动全国妇女力量,一方面是和男子共同参加抗战建国,一方面是争取妇女政治经济的平等地位,从而获得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与新的经济生活的获得,即在这样的途径上,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11](66—67、193页)
三 论战的意义
围绕“妇女回家”问题进行的论战,既揭示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生理决定论和传统性别分工制度,也表现出当时进步人士(包括妇女)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社会性别观念的先进性。
就“妇女回家论”者来说,他们所依据的理论就是长期以来影响巨大的生理决定论,即男女差异是由生物性别差异决定的。这种生理的差异就是男性性别优于女性性别。由于性别差异是天生的,所以男性优于女性也是无法改变的,从而导致了男性统治地位的建立。这样,由性别差异而形成的性别歧视观念便铸成了生理决定论。为了证明男女生物性差异的合理性,他们从神话和科学上去寻找依据。“从最古神话到最近科学家意见,都说男女生来好像是‘不平等’的,神话说男子用黄土做成,女子用水做成。科学家说从生理组织方面观察,男女生来就不一样,在适应组织表里到行为活动或情绪发展时,男女更不一样”[11](21页)。有了男女的生理差异便有男女能力的差距,“老天爷已经为她们安排好了的生理问题,要怀孕、育婴、哺乳,这难关不能打破,在这时期,非有男人保障不可”,同时妇女“聪明才智实在不及男人”,而且“意志薄弱,拿不定主意,天然的温柔,女性易为男性引诱。男人拿着女人这些弱点无往而不胜,于是乎成为男人的世界”。他们还找出了例证,“女人的专科,如缝纫,烹饪,接生,音乐,这四样本行,请问女人有哪一样及得男子”,并且妇女自己也承认“天然生理上的限制,因此屈服下来,只好得计就计,徒慕逸怠,于是女人遂以结婚为她唯一的谋生的武器,唯一的免费投资”[11](156、158—159页)。
基于男女根本差异在于它的生理性的认识,“回家论”者自然要维护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制度。这种性别分工制度要求女性的行为举止要符合其生理性别特征,女性只能从事符合其性别身份的事务,于是,男外女内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得以确立。不过,他们非常清楚五四以来妇女解放的状况,所以,他们决不谈“男尊女卑”,反而站在维护男女平等的立场去谈分工合作的意义,“男女的分工合作并不是压迫女性,只是工作能力的问题而已”[11](153—154页),“男女不妨分工合作,男子在社会上服务,女子在家庭中服务,只要能各尽其责,对于国家,对于人类的贡献,即是同等的重要”[10](175页)。他们由此提出, “三从四德虽是封建时代的礼教,但它并不是要妇女做牛马,当奴隶,而是要妇女们做贤妻良母的训条”[11](113—114页)。在他们看来,如果妇女的行为方式、角色分工等不符合她们的性别身份,也就是跨越了家内私人领域,进入了社会公共领域,那么,她就是一个男性化的女性,或者是一个非正常的女性。“男性十足的女子,在生理上有点变态,在行为上只图摹仿男子”,“或者是身心不大健康,体貌上又有缺点”,“要家而得不到家的”[11](18页)。男性化的女性不仅破坏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制度,而且危害了男性权威。为此,他们警告妇女:“达到和男子一样,这是假平等。假平等之争取,不只无益,而且足以扰乱社会的秩序,扰乱的份子会受到任何的制裁。”[11](123页)
对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制度和“回家论”者的生理决定论的驳斥,反“回家论”者运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方法论和社会性别的一些理念,尽管当时还没有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言,它强调的是两性的社会差异,“通常用来指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社会含意,即由特定文化规定的,被认为是适合其性别身份的性格特征及行为举止”[15](217页)。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性别差异和性别不平等不是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因此,男女两性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反回家论者”充分意识到了性别差异的社会意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是具有文化的万物之灵,将性别关系简单归结为生物性的关系是对人类的侮辱。所以,在追问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之时,他们也从社会历史生成上去寻找原因。女子受男子的压迫,并不是自有人类以来便如此的,在原始共营共享的社会中,男子和女子在生产中起着同样的作用,所以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到了生产技术更加向前进步而进入了私有社会后,男子掌握了生产技术和占有了生产手段,由于妇女在劳动中的作用减低”,便“没有了男女地位的平等”,“到封建社会,男子更把这种关系用法律道德规定起来,于是女子便完全丧失其政治经济的地位”[11](66、192页),这完全符合社会性别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性别理论认为,性别分工、性别行为的差异是由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只有从整个社会机体中才能寻得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产物,其中经济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寻求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途径上,反“回家论”者的观点更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蕴含了社会性别理论的意蕴。马克思主义认为,性别压迫是与私有制、阶级一同出现的,“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16](63页)。因此,要实现男女平等,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力,同时还要进行制度变革和文化观念的革命。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政治文化构建的,因而它是可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反“回家论”者认为:“妇女所要争取的平等和解放是社会的平等和解放,只有经过社会的变革才能把妇女问题真正解决;妇女的完全的彻底的解放,只有在全人类得到解放之时;妇女之不被压迫、剥削与奴役,也只有在世界上消灭了人吃人的现象之时。”[11](66页)
可以说,反“回家论”者的妇女解放思想和男女平等观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再加上五四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因而他们在当时的舆论上占据了优势。除了在桂林有一批封建文人叫嚣外,在重庆和福建,几乎没有顽固派的声音。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妇女回家论”却影响很大,加剧了国统区裁减、拒用女职员的逆流,以致形成抗战时期空前规模的妇女失业现象。这说明,传统性别分工制度和生理决定论在当时依然存在,它并没有被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完全摧毁。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它又表现出很大的破坏力,足以引起妇女解放运动者的高度关注,所以直到1942年,他们都还在对此进行舆论批判。但是,这场清算性别歧视观念和传统性别分工制度的斗争并没有坚持下去。因为正如社会性别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所主张的,妇女的解放是与阶级、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单纯任何一方面不解放,都无法使妇女获得解放。而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解放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田园、家舍、学校、工厂……一切都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轰毁了”[11](69页),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现实,妇女们十分清楚,必须牺牲个人利益,“献身大我国家”,参加抗战救国,“去获得民族的解放,才能求得本身的解放,才能享受‘做人’的真正幸福”[14]。于是,妇女暂时中止了对性别歧视观念和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斗争,转而争取的是民族的解放和作独立的人的权利。应该说,这的确是当时中国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
当今,中华民族的独立早已实现,阶级剥削制度早已推翻,但是现实社会中的性别歧视观念和男女不平等的事实却依然存在,原因在于我们对经济和观念的解放还很不够。因为经济的解放并不完全是劳动权利、职业平等权利的获得,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发展现代大工业,实现高度的物质文明,并同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熔化在公共的事业中”[16](162页),妇女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 文化观念的解放更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巨的过程。由于历史上中华民族危机深重,每一次性别文化观念的变革都要受到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制约,如前所述的抗战时期就是如此,因而它在客观上影响了对旧文化、旧思想、旧观念的深入批判,以致在思想观念上留下了一些封建残余,即父权制观念和父权制家庭的根基未能破除,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依然存在。由此可见,目前我们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需要坚持对性别不平等的思想文化进行斗争,最终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这种平等,既不是简单的“同样化”、“向男看齐”,也不是完全否认生理性别而建立一种“中性关系”,而是在承认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女性和男性的共同解放。
收稿日期:2005—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