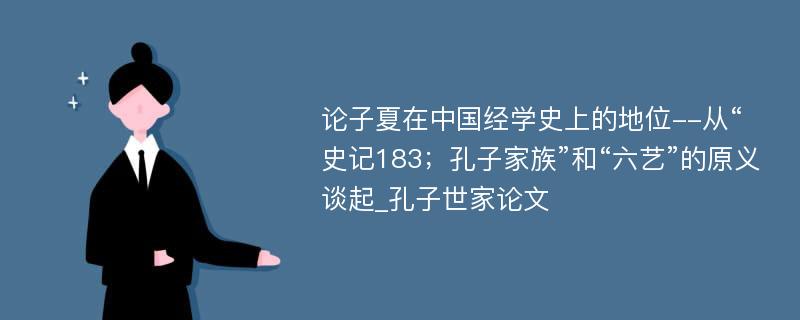
论子夏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从《史记#183;孔子世家》“六艺”的本义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孔子论文,经学论文,本义论文,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子夏是孔子门下三千弟子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素有“孔门七十二贤”之说,子夏是其中之一;又有孔门“四科十哲”之说,子夏仍赫然在列。不仅如此,“四科十哲”当中,“文学”一科共有两人,其中就包括了子夏,由此可见,子夏毫无疑问是孔门“文学”弟子中的佼佼者。“文学”这个概念首见于《论语》,其含义大体上就是今天所说的文献学。因为孔子的时代,“文学”的主体部分不外乎孔子设坛授徒所使用的教材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学”也就是“六经”之学,就是经学。如果说孔子以删定“六经”为中国经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那么可以说子夏是在中国经学的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第一人。为了便于分析说明子夏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先对《史记·孔子世家》“身通六艺”中“六艺”的本义作一番探究。
一、“身通六艺”中的“六艺”不是指“六经”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六艺”含义有二,一是指国子受教的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再是指“六经”。那么司马迁这里所说的“六艺”指的是什么?现当代一些颇有影响的学者认为就是指“六经”,比如吕思勉先生在专论《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六艺”概念的一篇札记中写道:“此七十有二人者,盖于《诗》、《书》、《礼》、《乐》之外,又兼通《易》与《春秋》者也。”(注:《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第4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王利器先生在《新语校注》一书中,在注解《道基》篇“定五经,明六艺”时亦以上述《孔子世家》中的文字等为根据,指出:“是‘六艺’即‘六经’也。自秦火后,《乐》失其传,故‘六艺’遂为‘五经’,此‘六经’衍变之迹之可得而言者。”(注:《新语校注》,第19页,中华书局,1986年。)金景芳先生在《孔子与六经》一文中指出:“《诗》、《书》、《礼》、《乐》是普通科,人人共习。六艺则不然,其中有《易》和《春秋》二书,是具有高深理论的著作,非高材生不能通。故在孔子弟子中身通六艺者只有七十二人。”(注:金景芳:《孔子与六经》,《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匡亚明先生也在所著《孔子评传》中写道:“在孔子当时及其以前,未闻有‘经’,到了司马迁著《史记》时,仍称‘六艺’,如《孔子世家》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滑稽列传》说‘六艺于治一也’,说明那时‘六艺’和‘六经’还是并称的。”(注:匡亚明:《孔子评传》,第33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如果按照以上学者的观点来对照理解司马迁的记述,那就意味着,在孔门三千弟子当中,有七十二个人每人都对《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过相当系统的学习并且学有所成。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孔子世家》中的“六艺”即“六经”之说,而认为“六艺”乃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集中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编纂而成的《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在“六艺”条下均把《孔子世家》的那番记述作为此种含义的书证,便是明证。
那么,“身通六艺”中的“六艺”究竟是指“六经”还是指六种科目?笔者认为,综合各种文献资料来看,“六艺”应当是指六种科目而非“六经”。
首先,孔子自己曾经说过:“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显然是《孔子世家》“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一句话之所本。贤弟子的数目到底是“七十有二”还是“七十有七”,这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故此存而不论,这里拟着重就“受业身通”和“身通六艺”意义上的关联略作分析。“受业身通”云云是司马迁引述的孔子语,“受业身通”四个字,“受”即接受,“业”指学习的内容,“身”指学习者自身,“通”即通晓。合起来说,所谓“受业身通”,就是学习者通过接受教育而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显然,孔子在此并未涉及弟子们的具体学习内容。不过,司马迁在记述孔子的教育成就时,将“受业身通”确指为“身通六艺”,也不是毫无凭据的,其凭据就是《论语》中的有关记载。检诸《论语》,虽无“六艺”的提法,但《述而》篇却有“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文。对“游于艺”中的“艺”字,历代众多的注家均明确解释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如朱熹说:“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也将“游于艺”翻译为“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注: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7页,中华书局,1980年。)。可见,“身通六艺”中的“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而非“六经”无可置疑。
其次,孔子整理《诗》、《书》、《礼》、《乐》虽然始于鲁定公五年(前505年),然而他删定“六经”却是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结束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后的事情,尤其是“六经”中的《春秋》的成书情况,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明确写道:“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这就是说,《春秋》的成书时间,不早于鲁哀公十四年。此时孔子已经71岁,两年过后,孔子便辞别人世。孔子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用新修成的《春秋》教授弟子,使至少七十二人达到“受业身通”的程度,以当时的办学条件,谈何容易!这就意味着,孔门七十二贤人所“身通”的,不会是“六经”而应当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再次,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原则。孔子认为人的智力是有差异的,主张教育内容必须要有层次性,用他的话说就是:“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同时,孔子还认为人的兴趣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他强调教育内容必须要有针对性,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同上)的论断就反映了这种观点。孔子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是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天赋和兴趣对于古文献学习的重要性。因材施教也就是根据智力状况和兴趣特点而实行的差异化教学,这种差异化教学,典型地表现在《易》和《春秋》之教学对象的选择上。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对于子贡的这番话,历代注家有着较为一致的解释,如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夫子文章,谓《诗》、《书》、《礼》、《乐》也。……群弟子所以得闻也。……孔子五十学《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传是学。然则子贡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易》是也。”程树德《论语集释》进一步断言:“以《诗》、《书》、《礼》、《乐》为文章,以《易》、《春秋》为言性与天道,其论精确不磨。”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尚且不曾得闻孔子的《易》和《春秋》之教,由此可知,七十二贤人不是人人“身通六经”,便是逻辑的必然了。现当代许多学者也都认为,《诗》、《书》、《礼》、《乐》是普通教材,《易》和《春秋》是更高深的著作,只有高材生才会得到孔子的传授(前引金景芳先生的言论即含有此意),此在客观上也间接地旁证了我们的判断。另外还有一些简单的事实,这就是除了子贡之外,“好长剑”而几次要求终止学业的鲁莽弟子子路、“昼寝”而被孔子斥为“朽木不可雕也”(《论语·公冶长》)的宰我、自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而被孔子一针见血地以“今女画”(如今你还没有开步走)(《论语·雍也》)相抨击的冉求等等,他们皆在七十二贤人甚至十哲之列,但都对学习古代文献兴致不高,其不曾从孔子那里得到《易》和《春秋》之教,是不证自明的。既然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若干人不曾接受“六经”的全面教育,那么他们全体所“身通”的,当然只能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了。
二、子夏是孔门弟子中于“六经”皆有深厚学养的惟一一人
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孔门弟子当中有不少人在“文学”科目的学习上均有所成就,除子夏外,突出者还有子游、子张、曾参、澹台灭明、商瞿、漆雕开等等。这些人大都在经学的某个领域学养颇深,如子游的礼学、商瞿的易学、漆雕开的尚书学等;这些人也都曾设坛授徒,在一个时期、一定地域内形成了较大的影响。不过,与其中的大多数人“术业有专攻”的情况相比,子夏却是以对“六经”均有系统研习而成为孔门弟子当中惟一的一个。孔子曾经向子夏系统地讲述了自己对于古代文献的研究心得,并同他就有关文献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经常展开切磋,这方面的有关记载,堪称孔子和子夏师徒二人教学相长的生动反映和体现。
其一,子夏对《诗》的研习。《韩诗外传》卷五记载说:子夏在研习《诗经》过程中,对《关雎》为什么被列为《国风》的首篇疑惑不解,并就此请教孔子,孔子为他作了细致的讲解。孔子从《关雎》之人讲到《关雎》之道,又从《关雎》之道讲到《关雎》之事,最后又把“六经”与《关雎》相联系,指出:“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一席话使得子夏豁然开朗。《札记·孔子闲居》记载:子夏诵读《诗经》,当读到《大雅》部分《泂酌》篇中的“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一句诗后,请教孔子道:“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孔子回答说:“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并进而解释了什么是“五至”、什么是“三无”,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概念。子夏听罢,诚恳地说:“弟子敢不承乎!”如果说以上两段记载反映了子夏的好学和孔子的善教,那么下面这段记载则分明反映了子夏的举一反三和孔子的循循善诱。《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请教《诗经》中的几句诗的诗意,孔子用一句话作了答复:“绘事后素。”启发子夏进一步深入思考;子夏根据孔子的提示,不仅领悟了“素以为绚兮”的意蕴,而且明白了“礼”后于“素”(仁义)的道理,以致孔子情不自禁地称赞说:能给我启发的就是你卜商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诗经》了。《韩诗外传》卷三也引述了孔子对子夏的这句赞语,并评论说:“子夏问《诗》,学一以知二。”
其二,子夏对《书》的研习。《韩诗外传》卷二记载:“子夏读《书》已毕。夫子问曰:‘尔亦可言于《书》矣?’子夏对曰:‘《书》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代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弟子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虽居蓬户之中,弹琴以咏先生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亦可发愤忘食矣。’”孔子让子夏谈自己学习《尚书》的感想,子夏明确表示“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这显然表明,子夏师从孔子,对于《尚书》的学习是非常系统的。《尚书大传》卷五也记载了子夏向孔子汇报学习《尚书》心得体会的事情。子夏说,通过学习《尚书》,对尧、舜、禹、汤、文王的治世之道已经了然于胸,而个人的得失和生死已经置之度外。孔子对他的回答从总体上给予了肯定,然后指出,你这只是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未入其中,教育子夏要善于把握《尚书》每一篇当中的深刻意蕴,汲取临民治政的智慧。可见,子夏对于《尚书》的学习,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其三,子夏对《礼》、《乐》的研习。孔子有句名言,叫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他很注意向自己的学生传授《礼》、《乐》,而子夏也每每能够做到认真学习、有疑必问。《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几乎一半的篇幅记载的都是子夏向孔子请教有关礼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比如他曾就上古典籍中“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礼”的记述向孔子求证其真实性,孔子不仅耐心地讲述了西周初年的那段历史事实,而且郑重地指出了依礼行事的重大意义,这就是:“夫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焉。”使子夏既弄清了历史真相,又深刻领会了依礼行事的必要性。孔子向子夏传授《乐经》的情况,现有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孔子重视和实行乐教是世所公认的,而子夏具有较好的音乐造诣也是确凿无疑的。据《史记·乐书》,魏文侯曾坦诚地对于夏说:我穿着礼服端坐着听乐师们演奏古乐,唯恐打瞌睡,而听郑卫之音却不知疲倦,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子夏于是从古乐和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乐的起源说起,对它们的特征和功用作了分析,劝说魏文侯“谨其所好恶”。子夏的基本观点与孔子的一贯思想毫无二致,甚至不少语言也都是非常相似的,由此不难推断,子夏的确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学得了丰富的音乐知识。
其四,子夏对《易》的研习。《说苑·敬慎》记载:孔子读《易》,至于《损》、《益》二卦,喟然而叹。子夏起而问道:老师为什么叹气?孔子回答说:“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听罢,表示说:太好了!我一定铭记在心,并终身奉行它。如果说上述记载只是反映了子夏接受孔子“易教”的情况,那么《孔子家语·执辔》篇中的这段记载,则显然证明了子夏对于《易经》是颇有研究的:“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耦,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昼生者类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阴主牝,至阳主牡。敢问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
其五,子夏对《春秋》的研习。子夏向孔子学习《春秋》,史有明载。《史记·孔子世家》指出:“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司马迁明言“弟子受《春秋》”,而于众弟子中单单标举子夏一个人的名字,可知子夏在《春秋》的学习上是得到了孔子的悉心指教的。《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春秋繁露·俞序》也载有子夏谈论《春秋》的言论:“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正是基于以上史料,清代学者朱彝尊在《孔子门人考》中断言:“孔子授《春秋》于卜商。”
三、子夏的经学传播之功
深厚而又系统的“六经”学养,为子夏在经学传播方面卓有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学者李启谦先生指出:“子夏是孔子的高才弟子之一,他的学业成就是突出的,特长是明显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他对后世的实际思想影响,超过了孔门弟子中任何人,就是颜回、子贡等人也要比他差一等。”(注: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第120、121页,齐鲁书社,1987年。)这是一个很高同时也很符合客观事实的评价。当代学者姜广辉先生在《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儒学传统重新诠释论纲》一文中写道:“韩非子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说语焉不详。以今考之,七十子之徒学问成就最高,从而成为大宗师者有三人:一为子游;一为子夏;一为曾子。”他认为“子游一系,可称为‘弘道派’”,“曾子一系,可称为‘践履派’”,“子夏一系,可称为‘传经派’”,并断言:“子夏一派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原典的全面研习有很大贡献。……汉以后经学的发展,主要是这一派的推动。”(注:姜广辉:《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儒学传统重新诠释论纲》,《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这无疑是深中肯綮之论。
子夏的经学传播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六经”无所不传;二是弟子众多,且其中的一些人名声显赫,
先说前者。与自己“身通六经”的学养相适应,子夏在经学传播上也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无所不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司马贞《索隐》:“子夏文学著于四科,……传《易》,……又传《礼》。”这是子夏向众弟子传授《易》、《礼》二经的明证。《史记·魏世家》谓“文侯受子夏经艺”,《仲尼弟子列传》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乐书》则详述了子夏与魏文侯师徒二人围绕古乐、新乐所进行的讨论,这表明,子夏传《乐》,无可置疑。另外,作为一部解释《尚书》经义的著作,《尚书大传》先后五次明确提及了子夏,其中一次称“魏文侯问子夏”,魏文侯所问,毫无疑问是关乎《尚书》经义的内容;再者,书中还记载有子夏解释《尚书·康诰》慎罚原则的一番话:“昔者三王悫然欲错刑遂罚,平心而应之,和然后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虑之乎,吾意者以不和虑之乎,如此者三,然后行之,此之谓慎罚。”从语言风格上分析,它很像是随问而答,就内容而言,它阐发的是治国策略。鉴于子夏和魏文侯的师徒关系,笔者推测,这或许就是二人之间的问对。可见,子夏传《书》,也是“信而有征”的。
子夏传经,用力最多、也最有成就的,当数《诗》和《春秋》。对于子夏传《诗》,《汉书·艺文志》记载说:“(《诗》)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三国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传授脉络相当明晰。唐代陆德明在所著《经典释文序录》中引用与陆玑同一时代的徐整的话说:“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徐整与陆玑两人所列《毛诗》的承传情况颇不相同,说明早在三国时期,有关问题已不甚明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传《诗》的源头,一定要追溯到子夏。
子夏传《春秋》,也是古往今来学人公认的事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就有子夏“说《春秋》”的明确记载。在汉代,讲授《春秋》经义有三种主要传本,即《公羊春秋》、《谷粱春秋》和《左氏春秋》。关于《左氏春秋》的作者,历来聚讼不已,且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将其著作权归到子夏名下的学者不断增加,这一点暂且不论,仅就《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而言,它们与子夏的联系也是相当密切的。唐代徐彦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引戴宏《春秋说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戴宏的这番话,把公羊学从子夏到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毋子都的传承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谷梁春秋》的源头同样在子夏那里。陆德明在《春秋谷梁传注疏》中写道:“谷梁子……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对于《谷梁春秋》的传承过程,有的学者提出质疑,但是对谷梁赤师从并受《春秋》于子夏,则是完全接受和认可的。
再说后者。孔门弟子中设坛授徒者并不少,有些甚至也形成了不小的规模,如澹台灭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李启谦先生据此得出结论:“他(指澹台灭明——引者)和他的弟子已经形成了个势力不小的学派。如果说在北方是子夏的势力最大的话,那么在南方就数到澹台灭明了。”(注: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第152页。)不过,澹台灭明虽然弟子众多,但是知名者寡;子夏不然,其弟子不但人数多,而且彪炳史册者也有十数位,其中既有魏文侯这样的侯王,又有段干木、吴起、李克(即李悝)、商鞅这样的出将入相的人物,还有慎到、禽滑厘、公羊高、谷梁赤等思想名流,而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等也是其隔了几代的再传弟子。可见,子夏真正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其经学传播之功在孔门弟子中无人能出其右。
四、子夏的经学研究成就
子夏“身通六经”,是一位博学者;他设坛授徒,是一位传播者;与此同时他还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对“六经”的研究当中,是一位硕果累累的研究者。正是因为有深入扎实的研究作基础,子夏的经学传播才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子夏的经学研究成就,从文献学的视角来看,既有训释元典的具体成果,更有研究方法上的发凡起例。其具体成果固然对后人正确地理解元典有着积极的作用,值得充分肯定;而其研究方法上的发凡起例,则对推进整个经学研究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更为关键的方法论指导,因而应当给予更加足够的重视和更加崇高的评价。
对于子夏训释元典的具体成果,南宋学者洪迈在所著《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题下有比较集中的记述:“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不过,对洪迈的这番记载,古往今来一直存有争议,这里笔者不可能逐一详加考证,只能扼要予以分析说明。
其一,关于《子夏易传》。对《子夏易传》一书,历代不少学者都认为其不出于子夏之手而系后人的伪托,他们的一个主要根据就是《汉书·艺文志》未予著录。《汉志》的确没有著录《子夏易传》,但是班固编纂《汉志》所依据的《七略》却有“《易传》,子夏、韩氏婴也”的记述文字,而据清代学者考证,《汉志》著录的《易》十三家中的《韩氏易传》与《七略》所说的“《易传》,子夏”云云是同一种书。鉴于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中有相应的记载,子夏习《易》、传《易》又见于多种古代典籍,所以得出子夏作有《子夏易传》的结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至于后世出现的《子夏易传》“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一》)的情况,那只是后人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责任推到子夏身上。
其二,关于《诗序》。洪迈说子夏“于《诗》则有《序》”,这不是他的主观臆断,而是有着充分的文献根据的。前引《汉志》“(《诗》)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这句话中的“毛公之学”,正是指《毛诗》之序。如果说《汉志》的表述尚嫌隐晦,那么以下几种说法就非常直截了当了:一种是东汉郑玄所言:“《序》,子夏所为”(《毛诗正义·小雅·常棣》注引《郑志》);一种是前引三国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所言:“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一种是三国王肃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注文中所言:“子夏所序意,今之《毛诗》序是也”;一种是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言:“《诗》者,……孔子最先删录,……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等等。当然,不同的意见也有并且五花八门,但完全否定子夏作《诗序》者毕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他们也无令人信服的根据。本世纪初,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首批资料正式公之于众,其中的《孔子诗论》非常引人注目,有学者指出:“竹简《诗论》的开头部分为序论,接着按《讼(颂)》、《大夏(雅)》《小夏(雅)》、《邦风》次序进行分论,最后还有总论。将竹简《诗论》与《毛诗》序相比较,我们发现,语句的表达有明显不同,而其内容观点却是基本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竹简《诗论》的下葬年代估计在战国中期,则竹简《诗论》的抄写应当更早,是我们所见战国初期子夏论《诗》的最原始资料,而今本《毛诗》序则是由战国末至汉初的荀卿、毛亨、毛苌等人写定。在这二百多年间的流传过程中,语句出现变化是自然的,但毕竟是师徒相传,所以其基本内容与观点,仍然能保持大致不变。”该学者甚至推断:“竹简《诗论》可能是失传了两千多年的子夏《诗》序”,“竹简《诗论》可能是《毛诗》序的原始祖本”(注:江林昌:《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104—10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如果今后能有更进一步的相关竹书资料整理和公布出来,那么子夏作《诗序》的问题就可以盖棺定论了。这里还有必要赘言几句。《孔子诗论》刊布之后,不少学者纷纷撰文,从不同的角度考证其作者,其中多数人都主张它应当是孔子后学的作品,更有李学勤先生等数位学者进一步将作者确认为子夏。不过,李先生不赞同竹简《诗论》即《诗序》的观点,而主张把《诗论》、《诗序》、《毛传》看成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注:转引自杨春梅:《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2002年第4期。)。如果李先生所言不谬,那么《孔子诗论》就成为不见诸文献著录的子夏的又一部著作。
其三,关于《丧服传》。“六经”中的《礼》实即后世所谓“三礼”中的《仪礼》,《丧服》是《仪礼》十七篇中的一篇。今本《丧服》篇包括经、记、传三部分,而以“传曰”领起的解释性文字便是《丧服传》。子夏习《礼》、传《礼》史有明载,而子夏向孔子请教丧礼的师徒问答以及子夏答复他人有关丧服事宜的言论也屡见于《礼记》之《檀弓上》、《曾子问》等篇,由此看来,子夏作《丧服传》,在情理上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丧服传》出于子夏之手的记载首见于《隋书·经籍志》,唐宋时期的学者基本上都对此深信不疑,元以后始有学者提出异说,迄今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今本《仪礼》中的《丧服传》未必是子夏原作,子夏原作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肯定会有被弟子或弟子的弟子加工、改造的情况发生,但其基本内容不会有大的改变,所以,将《丧服传》的著作权归到子夏名下,并无不当。子夏经学研究的具体成果并不限于以上几种著述,先秦两汉许多经史典籍和子书中记录的子夏有关诸经疑难的训解,同样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这一类的内容,笔者拟结合对于夏经学研究的发凡起例之功的分析评判略作阐述。
对于子夏在经学研究上的发凡起例之功,东汉徐防在一篇奏疏中作了十分精炼的概括,这就是:“《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所谓“发明章句”,就是划分章节、判明句读、揭示篇章的宗旨以及字句的意蕴。“发明章句”在我们的整个古代经学史上,始终是学者们惯用的基本治学方法,此法创始于子夏,仅此便可奠定子夏在经学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子夏在学习、研究和传授“六经”过程中,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而这些疑难问题的解决过程,也就是“发明章句”的过程。“发明章句”,划分章节、判明句读是初始性的工作,揭示篇章的宗旨和字句的意蕴才是关键所在,而揭示篇章的宗旨和字句的意蕴,也就是训诂,因为训诂“作为一个词语看,概指各种有关的注解工作”(注:冯浩菲:《中国训诂学》,第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综合考察各种相关文献资料,可知子夏所涉及的训诂方面主要有释词、解句、作序、校勘等(这些工作都是以正音、断句为前提的)。这里略举数例以分别说明。
其一,释词。《札记·乐记》记载:魏文侯向子夏请教音乐方面的问题,子夏前后三次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加以说明,其中的一次,在引用了“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这句诗以后,他接着说道:“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其中的“肃肃,敬也;雍雍,和也”,便属于训诂方面中的释词范畴。《尚书·康诰》有言:“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尚书大传》卷四记有子夏语:“昔者三王悫然欲错刑遂罚,平心而应之,和然后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虑之乎,吾意者以不和虑之乎,如此者三,然后行之。此之谓慎罚。”子夏这番话显然是对经文词汇的诠释,属于释词。此外,《丧服传》中释词方面的例证俯拾即是,不再一一列举。
其二,解句。《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其中子夏的言论,便是对孔子“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一句话内在意蕴的阐释,属于训诂方面中的解句范畴。《礼记·乐记》记载有子夏这么一番话:“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这番话,可视为说明性解句法的一个例证,具体些说,子夏“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数语乃是对《诗》中“诱民孔易”句意的举例式说明。
其三,作序。前已述及,《诗序》的作者应当就是子夏。《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大序概论全经,小序具体揭示各篇诗的创作背景或主旨。子夏的《诗序》是一部重要的训诂著作,同时也标志着训诂学的一个重要训诂方面——作序的诞生。其实,在概论全经的意义上说,《诗序》并不是子夏的惟一一篇序类文字,他还曾序论过《尚书》和《春秋》两经,前者见载于《韩诗外传》卷二,即“《书》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代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几句话,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话还在《孔丛子·论书》中有记述,且在子夏这番话之前,还有他向孔子“问《书》大义”以及孔子择要所作的阐释;后者见载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即“《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数语,另外同篇韩非所记“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的所谓“子夏之说《春秋》”语,也应视为子夏序论《春秋》的文字。
其四,校勘。子夏精于校勘。《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子夏前往晋国,路过卫国时,听到有个读书人抱着一本史书诵读道:“晋师三豕涉河。”子夏当即纠正说:“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这则故事既反映了子夏的博学多识,同时也表明,子夏是中国传统校勘学之理校法的开创者。《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子夏是亲承师教,至于他是否做过“六经”文本的校勘,我们不敢妄断,然而子夏从事过经典的校勘,却是无可置疑的,其证据就在于《论语》的纂辑。《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既然是“弟子各有所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那么在《论语》成书过程中,考订异同、择善而从就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校勘的工作内容。郑玄等历代多位经学大师都曾明确指出子夏是《论语》的主要纂辑者之一,这当然就意味着,子夏参与了《论语》文本的编修工作,亲历亲为了《论语》的文字考订和校勘。
标签:孔子世家论文; 六艺论文; 孔门七十二贤论文; 孔子论文; 史记论文; 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国学论文; 子夏易传论文; 诗论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