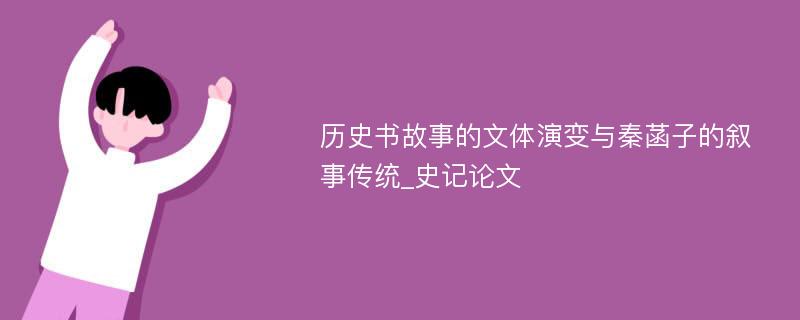
史书“故事”的文体衍化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书论文,秦汉论文,史书论文,文体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4)02-0163-05
中国古代史书有很多与文学有关的范畴,详细研究它们,对于考察古代文学发生、衍化的轨迹,很有意义。例如“故事”一词,多见于《史记》、《汉书》记载,主要与政治制度有关系。子书中很多“故事”,则是借用以往“旧事”来说理,也具有“故事”的规范意义。再深入考察,这种“故事”还与汉代很多文体的产生有关,尤其是能够体现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孔丛子》的叙事体例一窥全貌。从《孔丛子》的叙事体例看,主要“记言”,而“记言”又以“人”为经,以“事”为纬,从而使得全书近似于《晏子春秋》的风格,故事性非常强,具有“小说”的某种特征。例如“陈惠公大城因起凌阳之台”,记事与问答风格与《晏子春秋》十分相似。今本最后一节“宰我问君子尚辞乎”,孔子答毕宰我之问,又有“孔子曰”,《礼记》则多有此叙事方式[1]。
为了说理的需要,《孔丛子》多引前朝“故事”。这种来源于前朝的“旧事”,具有历史借鉴意义,不仅能够增强说话者的说服力,而且能够增强故事性,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这种由“记言”生发出来的“叙事”体式,是先秦诸子的一种学术惯例。例如《墨子》、《庄子》、《孟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汉代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新序》等文献中,都有大量故事性很强的叙事材料。从诸子撰述的“叙事”角度考虑,先秦两汉的“故事”传统,是诸子撰述时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虽然,“故事”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其社会功能的扩大,必然影响到处于其中的诸子著作,进而产生特定的“故事”体例。发展到后世,古典文学诗文中“典故”的产生与流行,就与此有关。
一、“故事”本义及其与后世“小说”之关联
先秦两汉子书中的“故事”,与后世文学体裁意义上的“故事”有所差异,与后来的“典故”也不完全一样。按照汉代史书记载,当时之“故事”,主要解释为“旧事”、“旧业”、“先例”。具体说来,《史记》、《汉书》记载“故事”颇多,然其义有别。总略说来,“故事”之义有三,具体如下。
1.旧事,旧业。先秦时期,“故事”主要含义为“旧事”、“旧业”,如《商君书·垦令》:“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故事。”此“故事”皆为“旧业”义。
汉初,“故事”逐渐演变为“旧事”。《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述故事”、“长老好故事者”,主要指的是“旧事”,但其中也隐含了“典章制度”的意义,指的是具有真实性的“历史”。从文献保存看,此类“故事”,与后世文体意义上的“故事”,相距尚远。
2.先例,旧日的典章制度。入汉以后,除了“旧事”之义,“故事”主要的意思是“先例”、“典章制度”等,有时候与“旧事”意思极为接近。或指汉代因循已久的定例,如《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锺离生。”或指前代法例,如《史记·三王世家》:“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或指前朝延续下来的优良传统,如《汉书·刘向传》:“宣帝循武帝故事,招名儒俊材置左右。”为了一定的社会与政治目的,当朝者也会“自创故事”,以成后世之“法”,如《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先拜相后封侯”。始于公孙弘,后逐渐成为“定例”,故此处云“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汉代“先例”、“典章制度”之义较多,可知当时此类“故事”,主要具有社会、政治功能。从文献保存看,此类“故事”,多与先秦政治、文化传统有关,并且主要作为当时人处理政治、文化问题的借鉴而出现的。这些本来不具有“叙事”意义的“故事”,一般指的是一种“传统”、“精神”、“思想”。后来作为“典故”,出现在叙事文学中,方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资料。据汉代史书记载,王莽之前,汉人多遵循汉家“故事”。王莽复古,即多遵循周公或其前“故事”,如《汉书·王莽传》多处记载:“太后临前殿,亲封拜。安汉公拜前,二子拜后,如周公故事。”“夫有法成易,非圣人者亡法。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时子寻为侍中京兆大君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从之,拜丰为右伯。”
可见,两汉之际,“故事”多被用来指先朝“典章制度”,并且被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这种“制度”、“惯例”,不仅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而且在汉代社会风俗中也成为人所共知的“条令”或“规范”。这为它们在汉代的接受与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为它们在文学文本中转换成“典故”创造了条件。
3.具有后世叙事意义上的“故事”。在“旧事”、“先例”意义基础之上,后世文学体裁之义的“故事”,也开始出现,如《史记·滑稽列传》:“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此“故事”已经具有后世“小说”意义上的“故事”含义。证据是据“褚先生”之语,可以推断,这种与后世文体有关的“故事”,体例与题材主要来源于“外家传语”。并且,此“故事”与“滑稽”并列,称为“故事滑稽之语”,证明此时的“故事”有娱乐功能,故“褚先生”方有“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之说。从这里看,汉代的“故事”,除了严肃意义上的“先例”,还有“滑稽”意义上的“旧事”。前者是“成例”,是文学题材中被引用之“典故”。后者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有情节,开端,有发展,也有高潮。这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从“小说”的性质与特征看,此类“故事”亦属“小说”范畴[2]。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小说”基础上,逐渐出现了六朝、唐代“传奇”小说的元素。例如《史记·龟策列传》:
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与人议,欲遣去。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龟见梦曰:“送我水中,无杀吾也。”其家终杀之。杀之后,身死,家不利。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
此“故事”显然是由旧事、典章制度生发出来,具有“小说”意义的“故事”。其“传奇”色彩又使得此类“故事”具有进一步“衍化”、“发展”的趋势。“龟能行气导引”,说明此“故事”与当时的神仙、导引联系起来了。“龟见梦曰”,显然是后世“传奇”小说写法的渊薮。“杀之后,身死,家不利”,这种“报应”说,可能来自于民间信仰或道家思想。诸如此类,融合了多种元素、多种思想的“故事”,已经与此前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旧事”,或具有“传统”性质的“先例”,产生了很大差异,而与后世具有“小说”性质的“故事”意义非常接近。也就是说,汉代此类“故事”,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叙事”色彩。这是“故事”在汉代的一大变化。
二、“故事”本义在汉代的文体衍化
作为“旧事”之义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为与“小说”关系密切的文体,而作为“旧例”、“典章制度”之义的“故事”,又有何发展呢?事实上,它们也没有消亡,而是逐渐与汉代应用文体发生了联系。
《汉书·魏相传》:“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此处有三个“故事”,一般皆可解作“旧事”,但最后一个“故事诏书”,“故事”与“诏书”并列,有人解作“皇帝处理旧事的诏书”。但笔者认为,将其理解为“与旧事有关的诏书”,更为可靠。也可以理解为,当初很多“诏书”有解释、说明汉代“旧事”规则的作用,因为当初很多“诏书”的撰写与发布,也是根据“旧事”规则进行操作的。这里有两个证据:第一,皇室行为规范与礼仪,皆有“旧事”可循,如蔡邕《独断》称:“幸者宜幸也。世俗谓幸为侥幸。车驾所至,民臣被其德泽以侥幸,故曰幸也。先帝故事,所至见长吏三老官属亲临轩作乐,赐食皂帛越巾刀佩带。民爵有级数,或赐田租之半,是故谓之幸,皆非其所当必而得之。王仲任曰:‘君子无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春秋传》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当得,故谓之幸。然则人主必慎所幸也。御者进也,凡衣服加于身,饮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寝,皆曰御。亲爱者皆曰幸。”“先帝故事”以下,又引王充、《春秋传》等语,显然说明“幸”这一行为,是受“先帝故事”、先贤或古代典籍流传下来的道德规范所约束的,是有“旧规”可循的。第二,皇帝与大臣“诏书”,皆依“旧事”而为之,如蔡邕《独断》称:“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官如故事,是为诏书”,可知诏告之制作,皆因循“一定之规”。这种因循“旧事”之作,虽然本来属于官场惯例、制度规定,但长期沿用,亦逐渐成为约定俗成之文。其名称不一,但总属文学范畴,故蔡邕总结云:“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总之,由蔡邕所言“官如故事”之“制”、“奏”、“策”等分析,汉代很多文体,尤其是应用文体,都有“模范旧事”之事。刘勰《文心雕龙·章表》在蔡邕基础上,又有深入阐发:“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3]
由其中“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分析,这些应用文体,各有“故事”,而“旧例”、“典章制度”,亦融入汉代应用文体中,成为其应用中不可割裂的元素。这种或隐或现的文化元素,融进汉代文学书写的体例之中,就成为汉代文学书写的“传统”和“旧例”。再进一步,就以“典故”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文学体式中。
诸子文学的书写也是如此。例如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等,皆多采前代与本朝“故事”,用以提出适应于汉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文化标准。刘向撰写过程中,择取“故事”,必然是“胸有丘壑”,他所遵循的“去取原则”,实际上就是符合“故事”的叙事原则。这也是诸子叙事的一种“传统”与“成例”。推而广之,汉代其他诸子讲论六经与《楚辞》等文学作品,也是遵循“故事”传统。如《汉书》卷六十四:“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侍诏金马门。”其中未必皆属于“叙事”传统,但他们讲论六经,诵读文学,遵循汉代“故事”,没有问题。
汉代诸子与整个汉代文人叙事的这种“故事”传统,起源于先秦,但主要倡导者则是汉武帝。《史记》、《汉书》多有汉武帝“修故事”记载,汉朝历代君主亦有“修武帝故事”之类的文献记载,这说明汉人的“故事”传统,大多源自汉武帝。汉代文人的“叙事传统”,则亦源自汉武帝。汉代诸子对此多有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桓谭《新论·识通》记载:“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为最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4]
桓谭是两汉之际的大学者,与刘歆、扬雄多有交往,其《新论》称汉武帝“模范前圣故事”,当为可信。从这里说来,汉代诸子对汉武帝“模范前圣故事”特别重视,在撰写过程中,他们潜意识里也有“故事”传统的影响。这是汉代文学叙事传统中非常特殊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的体现。
三、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及其文学价值
秦汉子书重在说理,但有时候为了特殊的说理需要,还会借助大量的“叙事”技巧来说明问题。这就使得秦汉子书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子书与史书、文学文本中相同的叙事,在目的与情节上有异同,但子书“叙事”已经具有了某些文学色彩。
由上文看,从单纯的“旧业”、“旧例”到具有叙事色彩的“传说”、“小说”,“故事”的涵义在史书记载中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与之相适应,与史书并行的子书,对“故事”的接受与理解,应该主要集中在“叙事”角度,即子书之“叙述传统”,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故事”的题材与模式。
汉武帝时期是对汉家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历史阶段,故汉家“故事”多因循汉武帝之旧例。如《汉书·王褒传》记载:“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侍诏金马门。”此处之“故事”,显然是“旧例”之义。需要注意的是,“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楚辞》等楚人作品已经进入汉家“故事”,成为汉人文学交流与撰述的主要参考对象。二是“故事”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说明它与“文学”的距离更为接近了,为“叙事”功能的增强奠定了基础。
秦汉子书具有说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的特征,子书采“故事”,必定是为了满足其“叙事”功能的需要,进而达到“说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故事”之真伪与准确性成为次要的事情,而借“故事”来“说理”则上升为主要目的。
笔者认为,《孔丛子·记义》记载的“公父文伯死”事,多见于《国语·鲁语下》、《战国策·赵策》、《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礼记·檀弓下》、《韩诗外传》、刘向《古列女传》与《新序·善谋》等书,但它们记载的人物的名字、口吻与叙事的详略各有侧重,这显然与各书撰述目的不同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子书对“故事”的转述,往往不如史书翔实,大多简化故事情节,甚至一句话将整个故事引出来,而重在由此出发去阐发义理,在阐发道理过程中,有时候还会再引其他“故事”以佐证。史书或其他以“故事”题名的著作则不然,它们非常关注故事的完整性与情节的曲折性,往往重在叙述一个故事,而不关注说理。例如《孔丛子》和《汉武故事》都有“子杀母”故事。
《孔丛子》以“梁人取后妻,后妻杀夫,其子又杀之”一句话就将整个“故事”的主要内容说清楚了,季彦与梁相的对话,重在说理。其中,季彦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还引用了《左传》“文姜与杀鲁桓”故事,但也是简明扼要,毫不复沓。而《汉武故事》则不同,由于该故事重点在塑造汉武帝聪敏过人,故通过“帝疑之”、“帝命问之”、“太子答曰”等关键词,将整个故事叙述得曲折,具有传奇色彩。前者显然属于子书的撰述体例,后者则具有“小说”的性质。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叙事”技巧。可以说,子书之“叙事”,很大程度上是史书“实录”向文学“虚构”发展的一个关节点。
秦汉子书的“叙事”与史书“故事”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子书之编撰亦与史书“故事”具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以“春秋”题名的子书,更是如此。例如《晏子春秋》中的“故事”与一般的子书相比,更具“小说”性质。《孔丛子·诘墨》“孔子之齐,见景公,公悦之,封之以尼溪”故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同时见于《孔丛子》、《墨子》、《晏子春秋》与《史记》,但亦有小殊:
《孔丛子·诘墨》“墨子曰孔子之齐,见景公,公悦之,封之以尼溪”事,《晏子春秋》叙述字数最多,说明特别重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墨子》与此大同小异,且二书叙事结构与表达方式十分接近。如首句《晏子春秋》为:“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夫儒,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5]《墨子·非儒》为:“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6]除了封孔子的地点不同,其余毫无差别。这说明《墨子》作为子书,虽然主要是为了“非儒”说理的需要,但也不是不重视对“故事”的详细介绍,但毕竟还是为了“说理”,有些情节,《晏子春秋》表述比《墨子》繁富,有的文字为《墨子》所无。这说明《晏子春秋》更重视故事的完整性与曲折性,更强调“叙事”。
《孔丛子·诘墨》中,晏子说儒者“倨法而自顺”、“崇丧遂哀”、“其道不可以治国,其学不可以导家”,与《史记·孔子世家》的表达方式极为接近。由于《诘墨》是转述墨家之语,故《史记》的记载,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儒家的说法。
这个故事中,《墨子》重在“非儒”,《孔丛子》重在“诘墨”,二者对“故事”的叙事不太重视,而是将重点放在说理上。《晏子春秋》重在通过对话塑造孔子与晏子的形象,对故事情节特别重视。《史记》既重视叙事,也重视说理,情节更为完整。
可见,子书虽然重在“说理”,但有时候也非常重视“故事”的叙述技巧,并且为了说理需要,不十分在意故事的真伪。这是后世文学“叙事”进程中“虚构”的先导,也符合文学审美功能的需要。史书虽然重在“实录”,但在“叙事”过程中,为了“说理”需要,有时候会简化不必要的故事情节,这就为子书补充史书的故事“断链”提供了可能。另外,史书中的这种“简化”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为后世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续写、虚构的空间,从而大大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总体上看,这种既不同于史书“实录”,又不完全等同于文学“虚构”,并且主要与史书“故事”有关的撰作特征,基本上算是秦汉子书“叙事”的一个基本传统。
由此,笔者想到一个问题,即古代子书、史书与文学文本中的共同材料,互有同异,与各种文本的撰写目的、叙事需要有很大关系。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的时候,一方面不能将各种文本相同的材料单纯地放在一起进行“一锅烩”式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不能刻意夸大它们之间的差异。简单地以孰是孰非、孰真孰伪来界定不同文本中的相同文献,是研究者的大忌。也就是说,后世虽然以“四部分类法”将中国古书分为四类,但其中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书目的分类,未必完全准确。在学术研究中,除了讲究学术方法上的“打通”、“融通”,尤其要重视从更细致的材料入手,从“异”中找到“同”,进而总结其“异”、“同”产生之原因,为学术研究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总之,秦汉子书中大量的“故事”、“旧事”,与汉代史书记载的“故事”有很大内在联系,也是秦汉子书“叙事传统”的典型表现。子书“叙事”体现的与史书不同的学术特征,是后世文学文本“叙事”产生的关节点。一方面,古代文学创作的某些手法与技巧,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中国古代不同文本之间对相同材料取舍、运用时的不平衡发展。另一个方面,中国古代某种文体的产生,可能来源于不同的文学体式;同一种文学体式,有时候也能衍化出不同的文体形式。通过对某一“范畴”的深入研究,以往未知或较少关注的文学样式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完全可以尽可能得以还原。无限夸大“历史还原”的作用,当然不符合辩证法,但以历史事件发生之后不可能“完全还原”而彻底否定“历史还原”的研究价值,同样是学术僵化的表现。
收稿日期:2013-11-20
标签:史记论文; 秦汉论文; 汉朝论文; 文化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汉武帝论文; 读书论文; 楚辞论文; 文学论文; 晏子春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