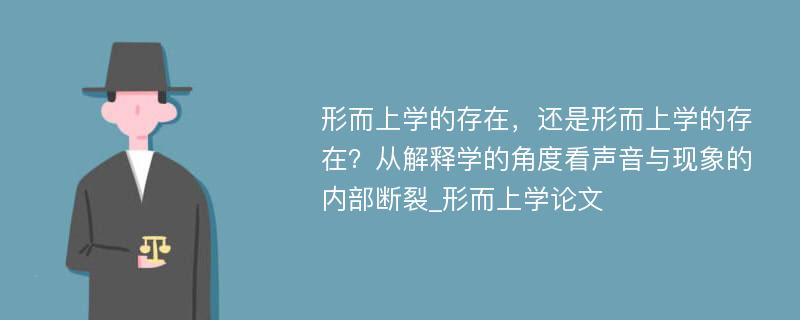
形而上学的在场,还是在场的形而上学?——从解释学的立场看《声音与现象》中的内在断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解释学论文,立场论文,现象论文,声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声音与现象》是解构主义的奠基性著作,德里达在这部书中把他自己独有的解构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善于从对方的体系中发掘细微的断裂然后以之为契机摧毁整个体系的德里达,在该书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断裂和矛盾。本文试图依照该书的解构线索,从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入手,揭示德里达摧毁在场形而上学的内在性统治的独特思路,并借此暴露出它内在方面的断裂乃至矛盾之处,这种断裂和矛盾最终导致德里达将一切在场等同于形而上学的在场,亦即否定了本真在场的可能性。本文的分析是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立场出发的,因而我们在分析中将适当地把德里达与伽达默尔的视角相对照。但我们力图完成一种内在的批判,亦即尝试指出,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自身即包含着瓦解自身的因素。
应该承认,德里达的解构虽然在有些概念上对胡塞尔不无歪曲,但总体是成功的。但我们这里不关注德里达的解构对胡塞尔是否公正,也不细致讨论整个环环相接的解构过程,我们集中关注德里达如何处理他在性,并通过它来取消在场形而上学的统治地位的。
一、指示与表达的交织
德里达的解构建立在对胡塞尔现象学(尤其是符号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而胡塞尔的整个现象学又是建立在彻底的内在性的基础之上的,它集中体现在现象学原则之中的原则——直观明证性之中。以这样的原则为基础,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构建了“理想性、观念性含义——同一可重复的空洞含义意向及含义充实行为(包括确保这种同一的含义载体,即现象学的声音)——理想性对象”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先验内在性链条。
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整个内在性的完美链条中,最初的外在性因素就是指号及指示行为。德里达的解构首先就从这个外在性因素入手。胡塞尔认为,表达和指号的区分在于前者在意识中获得某种含义,后者不具有含义,而仅仅通过指示来引发某种心理动机:“某人现时地知晓一些对象或事态的存在,这些对象或事态在下列意义上为此人指示了另一些对象或事态的存在:他把对一些事物存在的信念体验为一种动机,即信仰或推测另一些事物存在的动机。”①亦即,表达是明确的意义把握行为,而指号是心理上的或然性的动机关联。同一个事实既可以作为指号,也可以作为表达出现,这取决于是否进行含义把握行为。
在德里达看来,指号具有外在性、境域性、不透明性特征,它关联着物理身体侧,是或然性的存在,不能够成为逻各斯的内在部分。境域中指示着的动机,不能与含混的生活本身脱离开来,亦即不具有清晰、先验、绝对的意义。指号的这些特征,归根到底就是内在性所不能消化的他在性。如果能够证明内在性的表达不独立于指号,反倒依赖于指号,也就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胡塞尔为了建立内在性的特权,要求或者将指号驱除出去,或者将指号转化为具有含义的表达。而在德里达这里,恰恰指号构成了打破在场形而上学的内在性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在意识的内在性中首先遭遇的就是这些它无法消化的他在性和非在场特征:他人的手势、表情、整个身体、世界性、空间性、“事实性,世俗的存在,本质上非必然性的东西”②,总之就是逃避纯粹含义意向,逃避精神性。“存在从表达中被驱逐出去的东西,例如面部表情、体态语言,整个身体和世俗标志,简言之,整个如此这般的可见和空间性的东西……可见性和空间性恰恰破坏意识和精神激活的、在话语中开启的自我在场。可见性和空间性是自我在场的死亡”③。然而,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何在整部书中,德里达使用了多达十数种名词来举例或描述这种指号或与指号关联之物,但却始终没有谈及一种不容易被忽略的指号:声调和语气。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德里达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
在德里达那里,指号作为他在性就是作为符号的他在性。因此,在场的内在意识行为,总是受到这种不透明的指示行为的影响。德里达指出,指号和表达的区分,不是语言与非语言的区分,而是明确的语言与不明确的语言之分,明确的语言与不明确的语言总是交织在一起④。内在性在这里如何被打破的?就是作为指号的符号,即不明确的语言,通过自身的不透明性,指示着某个不在场之物。因而不在场之物对在场的内在性起着限制作用。
德里达在消解内在性统治时,根本区别于伽达默尔之处就在于,他把符号作为一个能够进入内在,并在内在之中固守自身的独立者,从而发挥着破除内在性霸权的巨大作用。而伽达默尔没有认识到符号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没有看到符号能够反作用于我们。但德里达在赢得这个优点的同时又抛弃了解释学的洞见。德里达在这里预设了一个没有明说的公式:当下在场=内在性。固然,当下在场意识是在内在性之中的意识,但在内在性之中的意识不等于就是内在性统治一切。德里达一方面反复声称在场与不在场的交织和相互规定,但实际上整个《声音与现象》一书中,他只谈不在场如何规定在场,从未谈在场如何规定不在场。为了瓦解在场的上千年的统治而在一本书中这么做似乎无可厚非,然而不可否认,德里达谈在场的时候,并未将在场看作自身可能是非纯粹在场之物。我们有权力问:难道在场不也恰恰是他在性朝向我们的入口吗?如果德里达有权说,他人的表情预示着他人的不可规定而反抗我的权力,那么我们不也有权说,他人明确指出我的错误,也是对我的一种限制吗?甚至在场显现中的整个自然,都作为一个他在性力量,而反抗着内在性统治。归根到底在于,德里达将一切在场的意识形式,仅仅当作纯粹的内在性的反思意识,而实际情况则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内在意识既是向内反思的,也是向外开放的⑤。
二、符号作为特洛伊木马
接下来我们跟随德里达对独白和孤独心灵生活的分析。孤独心灵生活的分析,对于德里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切交流之所以可能,首先以心灵内在的在场为基础。德里达分析道:“表达是外在化,它在某种外在中传递某种首先在内在中已经建立起来了的意义。”⑥相对而言,表达只是将前表达层次的意向含义转换成明确的意义和表达,是一个非生产性的重复。在胡塞尔那里,生产性的原初在场,和非生产性的表达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结构,从而保证了原初的生产性的纯洁。
德里达追问的是,“难道说在独白中就与自己没有任何交流吗?传诉和对传诉的认知就被悬置了吗?……我从我自己这里学不到任何东西了吗?”⑦为了说明在孤独的心灵中没有指示功能,胡塞尔区分两种指引,一种是作为显示的指引(可以被直接表达),一种是作为指示的指引(指号符号)。在前者那里,语词并不作为符号呈现,我们仿佛是直接经历意义,或者说意义直接向我们显示。语词的想象属于前者,想象的语词属于后者。例如,如果我自言自语:“我错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么就属于想象的语词。胡塞尔认为想象的语词并不重要,因为它只是一种可以驱除的偶然替代:如果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某个事物(显示),我们为什么要通过镜子的折射(指示)来看它呢?胡塞尔的论证与我们的经验相符,似乎具有一种明证的力量。然而恰恰在这里,德里达提出,孤独心灵生活之中,自我也在进行传诉交流。自我从来不是完全透明的,自我之中具有他在性,符号本身作为这种他在性而反作用于我们。德里达区分两种自我影响(Autoaffection,自我触发),一种是胡塞尔所意味的纯粹自我影响,即纯粹的内在性、排除了他在性、物理外在因素等等,从而保证了在场意义的完全呈现,另一种自我影响类型,则是凭借外在世界因素而具有他在性,从而属于指示系统。德里达否认存在纯粹的自我影响,认为任何自我影响都是他在性的影响,都有外在性。
为了在根本上支持这一论证,德里达分析胡塞尔的代现(Reprasentation)与再现(Re-prasentation)的学说。作为显示的语词在意识行为中是以代现的方式呈现的,胡塞尔说:“任何一个具体完整的客体化行为,都包含三个组成元素:质料、质性和代现性内容,而代现性内容或者纯粹作为符号性的被代现者起作用,或者纯粹作为直观性的被代现者起作用。”⑧显示的语词即通过符号性的被代现者而向我们呈现。与之区别的是再现,诸如想象、图像意识和回忆,它的特征是进行再造、使当下化,也就是通过想象行为而让不在场关联为在场。胡塞尔的观点是:代现是作为奠基性的表象,而再现是对奠基性表象的想象变更和再造,它最终落入表象之中。相反,德里达认为,代现和再现之间没有本质区分,根本不存在无想象的代现。“当我实际有效地使用语词时,无论我是否以交流为目的(我们在此考虑先于这个区分的一般符号),我必须从操作的开始时就运用语词符号,在语词的重复结构中去使用这些语词符号,这种重复结构的基本要素只能是代现的(Representative)。如果事件是指一个不可代替和不可反转的经验特殊性的话,那么符号绝不是一个事件”⑨。
简而言之,符号作为符号,必然是自身可重复的同一性之物,而我们在使用这个含义的时候,都必须使之当下化,使那个抽象的能指在当下作为意义向我呈现。那么每一次代现地使用语言语词时,不就是一种再造吗?字典上的任何词语,都不是直接被我们拿来使用的,它必须出现在我们的思维之中,而要使之出现,就必须通过再现的方式。同一性的语词符号就好比钱,而代现的语言、直接向我呈现的意义就好比食物。胡塞尔认为在代现中我们没有想象和再造,就等于试图以吃钱的方式消除饥饿。问题仅仅在于,在我们仿佛直接面向意义的时候,符号已经经过我们的再造作用了。
这个论证击中了胡塞尔的要害,直接摧毁了在场形而上学的内在性统治。德里达证明,在我们的在场意识之中,具有书写和符号的中介。我们不是直接面对意义,而是在已经被反复书写了的、共同性的语词的中介下进行思维的。我们从来不是面对理想性的纯净的意义,而是被前人反复使用和涂抹了的文字。不在场的文字规定着在场意识,它比在场意识更为古老。由此可见,外在性在内在性之中掀起了怎样的动荡!决定性的就是这个作为符号和书写的“特洛伊木马”。当我们说一切被认识和理解都是被内在占有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一切内在性不过是在外在性的书写和符号之中做了新的涂抹。既不是内在性统治,也不是外在性统治,而是内在与外在,在场与不在场的游戏。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话来说,历时性的言语不过是共时性语言的重复。在内在性的言语之底层,有一个外在性的“语言”在规定着我们。很明显,德里达在这里并未“脱离法国结构主义的‘家门’”⑩。
三、内时间意识作为延异和踪迹
在第四章的结尾,德里达写道:“当然这个在场的概念不仅包括在与自我的绝对接近中的存在的呈现之谜,也指明了这个接近的时间性本质。”(11)胡塞尔在场意识的不可还原的绝对优先性,于是体现在时间意识中当下瞬间的奠基性之中。因此对内在性的解构,在时间意识中就是对原印象的基础地位的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恰恰是胡塞尔自己发展的思想,构成了对这个学说的颠覆。根据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在意识的河流之中,存在滞留、原印象和前摄三重结构,一方面原印象自身是虚无,需要在滞留和前摄之中构成,另一方面,滞留和前摄作为对原印象的变样,最终要还原到原印象之中(12)。德里达赞同胡塞尔关于滞留和前摄对原印象的规定的思想,并推论:如果滞留和前摄是一种他在性的非在场,而纯粹在场的原印象恰恰要以非在场为前提,那么不恰恰证明了在场本身并不具有原始地位吗?胡塞尔关于滞留和前摄应该和可以还原为原印象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滞留和前摄实际就是符号的再造。除此以外,胡塞尔认为滞留、前摄和原印象一样,属于感知范围,而回忆(次级回忆)和期待则属于再现范围,两者有本质区别,在时间意识中,表现为前者构成固有的时间意识之相位,“一个点状的相位永远不可能自为地存在”(13),而后者则能够再造一段时间流,自成一个时间世界。但是德里达认为胡塞尔过于夸大了这种区别的重要性,如果滞留和前摄已经是一种再造,而次级回忆也是一种再造,那么它们的区别就只是两种再造方式的不同,因而就不是根本性的区别。胡塞尔这里确实包含着一种理论的窘迫:本来,只有在当下瞬间才是活生生的在场,才是原始的;当发现滞留之后,为了保证原始在场的优先地位,就扩大了原始在场的范围,将本来非在场的滞留变成原始的感知在场。再造着的滞留现在被纳入直观明证的范围,而这与直观明证的绝对被给予性自相矛盾。
德里达由此引申出延异的思想:如果不在场的他在性因素才塑造了一个当下的意义,这个意义始终被他在性所规定,那么意义也就成为踪迹。符号在每次重复中,就产生了一个意义的踪迹,但每一次重复既是意义的闪现,也是意义的消逝,因为它的意义仅在那个当下重复之中。可见,对时间学说的批判,就是将前面的解构在更为深刻的内时间意识层面重演了一遍。在场的原始存在不是真正原始的,原始的书写才在意义的源头活动着,原始在场瞬间应该在踪迹的基础上被思考,而不是相反。德里达自己明确说道:“一旦我们承认空间既是一个‘内在’或‘差异’,也是一个向外在的开放,也就不再有绝对的内在,因为外在已经潜入这个运动,借此非空间的内在(被称为‘时间’)被构造和作为在场;空间‘在’时间中;空间是时间的纯粹离开自身,是作为时间的自我关联的‘外在于自身’……时间不是一个绝对主体性,恰恰是因为它不能在当下和一个当下存在的自身在场的基础上被感知到。”(14)德里达以让人信服的彻底的方式,颠覆了意识哲学内在性的统治。
然而,前面暴露出的不足,在这里再次表现出来:当下瞬间的在场,仍然以胡塞尔的反思意识为范型,而不是以外向性和自身改变着的“前反思”意识为范型,因而这种在场就只是在封闭的理想同一性之中自我重复的在场。这当然是应该反对的形而上学的在场。但是德里达或多或少将形而上学了的在场同在场本身等同起来,而没有顾及在场本身作为积极规定的可能性。如果套用伽达默尔的那句话,“没有形而上学的话语,只有对话语的形而上学的使用”,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形而上学的在场,只有在场的形而上学化。由于没有区分这两者,德里达的理论就处于窘迫和不和谐的境地:Ⅰ.指号本身恰恰是在当下瞬间处境之中才具有生命力的,脱离了当下处境的指号就不再作为指号,因而对指号的引入,暗藏着对在场当下及其处境的肯定;Ⅱ.在符号的延异和踪迹之中,恰恰要求符号摆脱处境,因为只有当书写的作者已经死亡,作为遗嘱起作用时,文字的意义才获得生命。为了解构表达,根据Ⅰ,德里达将指号与外在对象(自然、世界、空间性等)联结起来;为了解构直观在场,根据Ⅱ,德里达又将符号规定为自身延异的能指系统,转而要求意义自治。德里达在解构胡塞尔的时候,被拆解的绳索绊了一跤。
指示之所以具有他在性的力量,其实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指示在在场之中,让他在性和不透明性作为限制而规定着表达的内在性;另一方面,指示作为指号符号,固定为语词,因而他在性潜入了符号和书写,对在场内在意识构成消解。德里达面临的矛盾正是由于他只看到了第二方面,而没有看到第一方面。因此,在场中与外在对象发生关联,并不必然构成内在性的霸权,而是相反,恰恰构成对内在性的限制和消解。德里达的这个矛盾,在关于声音的论述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声音批判的左右为难
声音被德里达看作是在场形而上学的帮凶,原因是声音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透明性,即最大限度地无身体性特征,因而没有不透明的他在性因素的干扰;第二,自身消逝的特性,“能指的现象学‘身体’在他被产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在消逝;声音能指看起来已经是理想性要素。它现象学地消除自身……”(15)第三,与意识活生生的在场具有绝对的接近性。恰恰是通过声音的透明性,使得在场意识仿佛和声音交融在一起,能指绝对地接近所指,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了在场的中介性,保证了在场的理想重复性。“话语是活生生的”(16),在说话时,在场得到完美的保持。相比较而言,文字具有明显的不透明的物理侧;由于具有保存性而将不在场的意义固定下来;最终,文字成为一个他在,一个能够反作用于在场的非在场因素。一个人在书桌前贴上一个写着“加油!”的便条,就是借助文字的上述特性而使之成为一个中介和他在性的力量,对在场构成限制。
声音在胡塞尔那里,被认为帮助了含义的理想同一性的保持,“这种能指与所指的绝对接近,以及直接在场中的消除,就是胡塞尔能够考虑作为‘无生产性’和‘反射性’的表达的中介的条件。吊诡的是,也正是由于这个条件,胡塞尔能够在不损失任何东西的情况下,还原这个中项,并断定存在一个前表达的意义层次”(17)。
但正如方向红所认为的,德里达用声音概念批判胡塞尔只是一种“误置”(18)。胡塞尔确实要求一个非中介,这个非中介就是立义的代现,或者直接来说就是意识行为本身。事实上,德里达的声音概念,在物理声音、想象语词、意识行为本身三者之间摇摆。如果德里达只是声称声音就是意识本身,那么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批判也就落空了,因为如果语音只是意识,那么就没有什么语音中心主义,它其实就是意识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而已。而假如德里达要避免这个困难,转而强调语音作为具有物理侧的语音,以此来落实语音中心主义的指责,那么语音和文字又有何根本性的区别呢?因为它们和文字的差别,只是在透明性的程度上的差别。任何语音作为语音,多少都通过物理侧而抗拒着意义的理想同一性。很明显,德里达在此陷入了两难。
我们认为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概念是一个相当薄弱的概念,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很多时候,也许恰恰是文字充当形而上学帮凶,而语音反倒构成消解的力量。第一,语音具有稍纵即逝的特征,但声音的稍纵即逝,恰恰标志着意义的稍纵即逝。固然,声音在话语中完美地保持了在场的意义,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意义始终处于对话之中,那么意义的不确定性,不就是一种确定的不确定性,或者直接说就是一种延异。而这正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立场。第二,语音与自我在场绝对接近,与境域保持密切关联,恰恰使得语音远离逻辑化,而与原始的生存处境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难道活生生的说话不是最大限度保留着指示的不透明性吗?难道文本不是尽可能地抽象于某个处境,而对最普遍的读者,试图讲一些永恒的话,因而是更为形而上学的吗?恰恰是话语保持着与人的生存处境的原始关系,而当人们懂得书写了,就开始将话语中不透明性的东西(音调、语气、修辞情境、修辞手段、无法言喻的微妙差异、或然性猜测、情绪、习俗等)蒸馏掉,只剩下严谨而又干枯的明确论证(逻各斯)。
五、意义自治与本真在场
对内在性可能造成最根本的冲击的,是意识要向世界保持开放,这种开放胡塞尔称之为充实。但他认为,意识的理想性恰恰在于它独立于直观充实。因此“我”这样的词不在具体处境中被直观时,恰恰是纯粹观念的,没有被经验性的直观充实所污染的。但“我”的含义理想性又不能完全排除具体处境,“本质上机遇性表达能被识别就在于它原则上不能在话语中被一个持久不变的客观概念取代而不改变陈述的意义(Bedeutung)。如果我用客体性概念内容(任何哪个正指向自身的说话者)代替陈述中出现的我这个词,就会是荒谬的。‘我很高兴’就变成‘任何那个正指向自身的说话者很高兴’”(19)。胡塞尔对此难题的解决方案是:尽管在具体意指中,含义具有各种偏差,但这种偏差并不影响含义本身的观念统一性,造成混淆的原因仅仅是有一些语词在含义统一性发生变化时并不通过可见的符号差异体现出来。因此,在一个公共场合说“我”的时候,这个含义不论在场的任何人只要了解这个境域,都能够把握这个含义的观念同一性(20)。
德里达指出胡塞尔这里存在自相矛盾:如果“我”这个词在各种处境中,在我们的个人直接性观念之中都有一个理想性含义(即“我”具有多个理想性含义),那就与之前认为的“我”这个词在孤独话语中才最具有理想性矛盾。机遇性表达(作为含义的多)为了保证理想同一性(作为含义的一),只得将理想同一性自身转变为多,亦即在不同的境域中有不同的理想同一性。但这实际上再次将对境域的直观引入进来了,而千差万别的境域岂不是具有了无限多的理想同一性了吗?当胡塞尔说“此刻的意义只能从鲜活的言说,从包围着他的直观处境才能获得。如果我读一个词而不知道谁写的,它可能不是无意义的而是只是远离了它的通常意义”(21)。德里达完全有理由指责胡塞尔违背了观念含义对充实直观的独立性原则(意义自治原则)。这个意义自治原则,大概源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符号封闭性原理。
德里达认同该原则,并且认为胡塞尔恰恰是贯彻此原则不够彻底才导致了矛盾。“胡塞尔的前提恰恰允许我们引出相反的结论……我们懂得我这个词,不仅当作者未知时,而且当他是虚构的时候。意义的理想性在此借助其结构而具有遗嘱的价值。正如一个感知陈述的引入并不依靠实际乃至可能的感知,‘我’的意指功能也不依赖于说话主体的生命”(22)。
德里达要求将境域性彻底地消除,实现意义的自治,最终实现能指对能指的替代,以及符号和书写的延异(这与之前指号源于境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恰恰是在没有进行个别的直观时,对意义的把握才是最纯粹的,“纯粹意义甚至要求:整个主体和陈述对象的不在场——作者的死亡,以及(或)能被描述的对象的消失——并没有阻止一个文本成为有意义的”(23)。
然而,德里达的这个方案,既包含着锐利的洞见,也包含着比胡塞尔的方案更为根本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德里达通过抵制在场的直观充实,揭示了作为补充、符号、书写和踪迹而给出的东西,亦即作为不在场的他在性,是如何比当下在场的真理更为古老,是如何在内在性之中,进行着书写的游戏。通过搬掉认识的在场形而上学的上千年的重压,暴露出根源处的符号的延异运作。但另一方面,当德里达将直观充实的在场直接判定为封闭的、形而上学的、内在性的,也就根本上否定了在场可能具有的他在性。德里达将表达、理想性、真理、对象、直观直接和在场联系起来,也就否定了它们作为非在场的在场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问:难道对“我”的在场直观必定会构成对“我”的意义的妨碍吗?说作者虚构或作者已死是理解“我”的意义的必要条件,这真是一种奇怪的说法,只是源于德里达对在场的不必要的恐惧。胡塞尔是为了保证意义的理想同一性,才要求悬置作为多的充实的,而我们现在并不需要捍卫意义的理想同一性,因此直观充实也就不再构成对“我”的意义的妨碍。
关于“我”作为机遇性表达的理想性含义,德里达只说出了一半的答案。我们认为,一方面如同德里达所述,“我”的意义在排除语境及其直观之时,其意义就被放入一个符号自身的系统之中,由这个符号自身系统所规定。但另一方面,“我”的意义同时也受在场的规定。在场的直观充实并不必然损害“我”的意义,而是恰恰也补充了“我”的意义。利科就同时看到了这两方面,并把前者称之为“表达的我”,而把后者称之为“定位的我”。作为语言的产物的我,是作为表达的我,而作为主体意识的产物的我,则是定位的我(24)。德里达对在场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在每一个在场充实之中,其意义都在变化,都处于延异之中。亦即,“我”的意义同时受到能指系统和直观在场两方面的补充。孤立的“我”自身并无意义,它只是一种否定性的规定,只有放在能指系统之中和直观在场的境域之中,意义才开始呈现。胡塞尔的那个困境,即“我”的意义的客观同一性与机遇性处境中的多之间的矛盾,也就不存在。因为并不存在客观同一性,意义只是事件,作为事件,它每次都是独特和不可重复的。
综观整个解构,《声音与现象》存在如下方面的断裂:
第一,指号源于境域性或我们的原始生存处境,指号的不透明性源于生存处境的不透明性。但书写的踪迹恰恰要求摆脱这种对象性关系,而进入意义自治。对象性事物在其中扮演着矛盾的角色,在指号分析之中,对象性事物使指号得以可能,在直观充实分析之中,作为生存处境的对象性事物必须加以排除。
第二,声音在整个解构中扮演着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声音本身具有物理侧(特别是在音调和语气中),自身具有不透明性和非在场性,因而必然要起着抵制在场形而上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声音又被当作无身体的声音,被解释为理想同一性的完美中介,从而起着维护在场形而上学的作用。
第三,意义自治是一个矛盾的要求。一方面,在解释指号的时候,德里达认为使指号得以可能的是对象性之不透明,因而肯定指号在逻辑上就预设了对意义自治的否定。另一方面德里达又要求彻底贯彻意义自治,即指号的真正意义只有在意义自治中才完美实现。
第四,德里达的这种断裂,归根到底源于胡塞尔的论证的两个对立侧面之间的断裂。因为事实上有两种相反力量在妨碍着胡塞尔建立理想同一性链条:一方面,不在场才是影响在场可重复的原因,例如自然、物理外在、符号、偶然处境干扰等因素,在场由于不在场的延异而使得在场不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发现,在场本身对在场的可重复性造成威胁,因为直观充实是经验的多样性。因此也就存在两种在场,一种是理想性自身重复的在场,即在场形而上学所维护的在场,另一种是在实际的历史和生存处境之中的,不断限制、否定、构造着主体的面向对象的在场,主体面向对象就是让对象改变自己,这恰恰是本真的在场,是自身延异着的过程。形而上学的在场作为内在性,是完全自身封闭的。而本真直观充实的在场,不是封闭的内在性,而是向经验保持开放,是伽达默尔所说的“痛苦”和“否定”的经验的造就(25)。而胡塞尔的在场,由于预设了含义的先天理想性,因而直观充实就只是一个致力于达到理想对象性的过程,其起点和终点都已被规定好。
胡塞尔的矛盾只是在于:一方面,为了含义的理想同一性在场,要求排除直观充实在场的干扰;但另一方面,知识论的最终目的又使得他不能放弃直观充实在场,而要最终返回直观充实,这样就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德里达就是在拆解这个谜团的时候被绊了一跤:为了维持不在场,他把自身可以是延异的本真在场也一并排除了。而一旦我们承认,本真的在场可以和原始书写一起,作为消解在场形而上学的同盟军,即作为踪迹而起作用,也就等于承认并非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还存在一种确定的不确定,或者说不确定的确定,也就可以一方面承认解构主义的真理性,另一方面又补充其缺失的建设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利科的解释学由于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解释学辩证地结合起来,就同时保存了这两者(26)。
如何既彻底释放他在性的力量,又维护在场和不在场之间的相互规定?对此,伽达默尔和德里达都只说对了一半。不管伽达默尔口头上如何强调语言作为他在性自身,解释学的理解最终都将其纳入了理解的内在性目光之中,哲学解释学很大程度上成了伽达默尔思想的紧身衣(海德格尔抛弃早期的解释学道路,或许就是一种先见之明?)。而当德里达强调文本和符号的原始性的时候,也封闭了它们与内在性自身的交流通道,忽略了不仅是不在场规定着在场,在场也同时规定着不在场。为此哲学必须踏上新的道路。
①⑧(20)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3、95、100页,潘策尔编,倪梁康译,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②③⑥⑦⑨(11)(14)(15)(16)(17)(19)(21)(22)(23)Jacque Derrida,Speech and Phenomena,trans.David B.Allis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S93,S36,S32,S41,S50,S58,S86,S77,S78,S81,S94,S96,S96,S93.
④这让我们想起伽达默尔的内在话语,内在逻各斯,事实上,两者正是关于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在这一点上,德里达并未超出伽达默尔。
⑤萨特则明确地区分了两者,即将意识分为封闭的反思意识和开放的反思前的我思。
⑩叶秀山:《意义世界的埋葬——评隐晦哲学家德里达》,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12)(18)另参见方向红:《误置中的意外——论德里达解构胡塞尔符号理论之得失》,载《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3)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第80页,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4)(26)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第314、32页以下,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Ⅰ》第362页,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