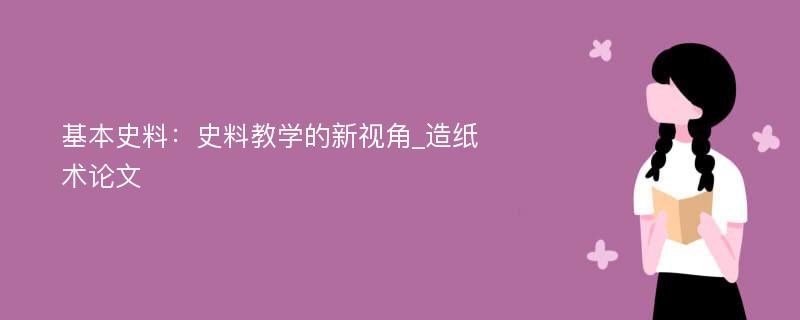
基本史料:思考“史料教学”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料之于历史教学,是不可或缺的。但“史料教学”与历史教学是什么关系?“史料教学”如何操作,才能体现历史教学的特质和价值?对于这些问题,历史教育界是有争议的。笔者试着从基本史料这个角度,对“史料教学”提出一些新的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史料教学”的纷争 “史料教学”这个名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①。进入21世纪以后才开始逐渐传播开来,真正大行其道也不过是近十年的事。史料教学的提出及其探索,对于打破教科书中心,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践行历史教育价值,都不无裨益。 但是,在史料教学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甚至是异化的现象。诸如,史料过多过滥,一节课动辄使用二三十则材料,造成学生目不暇接、无思考的可能;史料不够“原始”,多为史家著述,是二手甚或三手材料,离历史现场太远,历史气息散失殆尽;用“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去使用史料,目的不在于启迪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而是为了佐证教师认同的某个权威观点。 对于以上种种现象,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乃至尖锐的批评。代表人物有李惠军和赵亚夫。李惠军认为,“没有专门的‘史料教学’,只有专门的‘历史教学’”。他论述了课堂教学中非理性的“史料教学”造成的负面影响:“要么是历史课被几则史料割裂得支离破碎;要么是一段清晰的历史,在笨拙的‘史料教学’中,被搞得乱象丛生、面目不清”[1]。 赵亚夫则从理论层面论述了“史料教学”的本质。他认为:“‘史料教学’如果不针对怎样提出问题、怎样解释问题、怎样反思问题,而旨在挖掘史料、堆砌史料,让史料服务于教师的讲授,它就偏离了中学历史教学的本位,行不通的。”要真正理解“史料教学”,必须从历史教学的本质入手,即“围绕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批判的命题来解决如何拥有历史意义、历史意识(或认识)的问题”,也就是说,教学中使用史料,只有与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批判、历史意义、历史意识等结合起来,才有意义。而这些并非是“史料教学”的独有问题,而是历史教学的基本问题。他进而提出:“理解材料或史料、使用材料或史料,并将其贯穿于教学过程,本该就是历史教学的基本特性,无须非要戴顶‘史料教学’的帽子。”[2] 以上论述都不否认真正的史料教学的价值,批判的都是“史料教学”的弊病。从根本上讲,只有历史教学,没有史料教学,因为历史教学肯定要使用史料,这是回归历史学科的特质。但在教学实践层面,滥用史料的历史教学和不用史料的历史教学②是并存的。在许多地区的历史课堂上,部分教师满足于照本宣科,甚至懒得引用史料证实自己的观点,更谈不上指导学生对史料进行理解与批判。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彻底否定“史料教学”的提法,固然有助于一部分人转而思考历史教学的本质而不是盲目追逐一个时髦名词,但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丧失了被唤醒起来重视史料的可能性。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让“史料”与“历史教学”这两个词能直接联结起来,还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为凝聚大家对史料重要性的认识,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该大力倡导“基本史料”的使用。 二、基本史料的特征 与文献材料或口碑资料等相比,基本史料这个概念不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而属于历史教学的范畴,与其相对的概念是延伸史料。对于历史教学而言,学习一段历史时所无法绕过的材料就是基本史料,拓展学生历史认识的有关史料属于延伸史料。笔者在此无意探讨基本史料的定义,只想阐明基本史料的主要特征。具体来说,基本史料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基本史料是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的。学习秦朝的历史,《史记·秦始皇本纪》是师生应该参阅的基本史料;学习太平天国运动,《原道救世歌》和《天朝田亩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习北美独立战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文本是无法回避的史料;学习美国内战,不能不看《解放宣言》。当然,所谓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是一个较为宽泛和模糊的概念,其范围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比如说,对于某些教师和学生而言,在学习北美独立战争时,《联邦党人文集》和《常识》也是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基本史料还受课程设置与课时安排的影响。如果课时相对宽裕,基本史料的范围不妨可放宽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基本史料还是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史料应该与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知识要点和教师所确定的教学重点直接相关。 第二,基本史料应该是原始材料。原始材料是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或不久所创制的。它虽然也是出于记载者的特定视角,可能承载记载者的偏见,但是不管记载者如何掩饰,总还是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珍贵的历史信息。有的时候,对于记载者而言,因为某些情况在当时的语境下不言而喻,所以记载者认为根本就无须交代;而在后人看来,缺少这个“无须交代”的情况,整桩事情就变得难以理解,甚至这个“无须交代”的情况恰恰就是最有价值的地方。以这个“无须交代”的情况为突破口,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历史秘密。总之,原始材料与后世史家著述相比,在帮助学生返回历史现场方面有自己的优长。后世史家的著述当然也很重要,但它的价值主要在于提供理解和解释历史的视角与方法,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和思路,而不是将其著述作为历史的真实来看待。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受条件的限制,有时难以找到原始材料,那就要找最接近原始材料的史料。比如说,学习造纸术,当然要找蔡伦的材料。《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有关蔡伦的内容虽然不属于原始材料,但与原始材料最为接近,所以就属于不能不看的基本史料。 第三,基本史料应该是易得的。中学图书馆条件有限,藏书量不大。很多材料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属于最基本的材料,但对于中学历史教师而言,却难有“一睹芳容”的机会。如张德坚《贼情汇纂》,属于原始文献,史料价值很高,凡是研究者无不备阅,但是现在市面上难以见到,中学图书馆也少有收藏。因此,对于大部分中学历史教师而言,它就难以称得上基本史料。但令人快慰的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快速普及与发展,许多以前难以由个人收藏的资料,现在很容易就能在网络上检索得到。如二十四史,中学历史教师不必耗费巨资成套购置,上网就能轻松查阅到相关的内容。此外,有学者编撰了一些史料汇编性质的书③,汇集了许多珍贵的原始材料,值得拥有。 三、基本史料的教学意义 基本史料这个概念的提出,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期望能够袪除时弊。 前面讲过,目前的一些历史课堂教学中,堆砌史料的现象很严重,史料数量很多,质量却不高,教师也没有引导学生深入挖掘史料的问题、信息与价值。 笔者随机在网上找到一个名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的课件[3],有8则重要材料,分别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对美国法治体系的赞赏,1787年宪法关于国会权力规定的条款,19世纪英国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和“一位中国学者”对美国宪法的肯定,制宪会议上特拉华州代表马丁·路德和革命导师恩格斯对美国宪法的否定,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片断,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节选,其次还有一些综合编辑而成的材料。 这节课的重点是1787年宪法,以上材料大部分也是围绕宪法选择的④。但是,材料的重头戏却是后人如何评价美国宪法,反映的是后人的观点,而非宪法自身。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后人的观点是咀嚼过的甘蔗渣,想让学生真正体验甘蔗的味道,应该让他直接去啃咬甘蔗。可惜的是,在这个课件中,与宪法相关的材料只占极少部分,且这部分史料描述的是立法权,用来说明的是联邦制。而我们知道,美国宪法的精髓之一是三权分立与制衡。通读美国宪法,我们会发现,在宪法文本中,大量条款被用来叙述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如何互相制约,极为琐碎,令人难以卒读,不如《独立宣言》那样掷地有声、朗朗上口。但正是这个“难以卒读”耐人寻味。为什么制宪会议代表耗费127天,唇枪舌剑,面红耳赤,只为斤斤计较于权力的运行与制约,而非使用美妙的言辞去描述一个动人的政治原则?这正是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关键所在。此外,通读美国宪法,我们也不难发现,美国宪法的另一精髓是多元利益的妥协,包括大州和小州的妥协、南方与北方的妥协等,北京大学王希教授关于美国宪法的名著《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的书名也揭示了这一点。 按道理,从弗里德曼到威廉·格莱斯顿、“一位中国学者”、马丁·路德、恩格斯,再到马丁·路德·金和孟德斯鸠,此课件的作者旁征博引,寻找材料所花费的精力应不会少。但是,只要上网稍一检索,就能找到美国宪法的文本。放着更有价值的原始材料不用,却花费更大的精力去搜寻低廉的史料,不由让人徒生舍本逐末之叹。其实,已经有教师尝试以美国宪法文本为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材料,对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4]由此可见,史料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因此,提出基本史料这个概念,首先针对的就是课堂教学中滥用史料的情况。期望这个概念能启发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的原始材料的解读与探究上,这样既能减轻教师备课的负担,又能提高教学的效益,还能对那些不引用史料的教师起到正向的引导作用。后者不喜使用史料,原因可能有多种,或是因为受条件限制寻找史料不便,或是因为望浩如烟海的史料而生畏,或是没有意识到使用史料所带来的教学效益。基本史料是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的,是原始材料,是易得的。这样做,教师备课成本不是很高,而教学效益很好。如果大家把目光聚焦在基本史料上,会对这种现象的改善有所助益。 当教师的精力从泛泛搜索材料中解脱出来之后,将有时间去干更有益的事情,那就是深入地多角度地解读基本史料,设计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改变学生的历史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即“通过对历史材料的识别、区分、质疑、解释等技能,获取证据、探明事实、理解意义”[2]。 那么,该如何深入挖掘一则材料呢?有人建议,分析一则历史资料,可提出以下典型问题[5]: (1)这是原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 (2)它是什么时候制作的? (3)由谁制作出来的(例如目击者/当事人/记录他们所见所闻或研究结果的人)? (4)这一资料是从什么人的角度写成或制作的? (5)它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写成或制作的(个人动机/政治动机/宣传手法等)? (6)它的对象是什么人? (7)这一资料有多可靠?它的报道是公正、客观的,还是带有偏见的? (8)有没有其他资料支持它的论点? (9)它对于研究某一特定历史议题/方面的作用有多大? 上述问题中,容易被忽略的是第6个问题。一则文献的内容,不仅取决于它的作者,也取决于它的读者。因为文献本身就是作者与读者交流的产物,尤其是有些文献,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心中已有特定的读者,所以他在内容取舍、遣词造句等方面煞费苦心,会有意突出或夸大某些内容,缩小或隐瞒另一些内容。 此外,第8个问题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有没有其他资料反对它的论点?这个问题并非可有可无,因为它关涉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品质,即思维的公正性。“公正性要求我们努力平等地对待每一种观点”[6]。而人类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天然倾向于支持自己喜欢的观点,对反对意见或视而不见,或贸然否定。但在另一方面,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能够正视自己本性上的局限,并努力加以改进。拥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总会认真考虑反对意见。对材料的批判性阅读也是如此,不仅要思考有无其他资料支持它的论点(因为孤证不立),同时也要思考有无其他资料反对它的观点(这样才能不封闭思想)。 总的来讲,以上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拷问一则材料的价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分析工具。教师在备课时可以将其用来分析自己搜索到的基本史料,进而决定如何运用史料来设计教学活动;也可将这个分析工具直接交给学生,让学生来完成对基本材料的分析。 四、基本史料的运用 基本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可简单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理解历史;第二,探究历史。下面试举两例予以说明。 “历史方法的特色是以研究的方式进行理解的工作。”[7]10科学家对自然进行的是解释。历史是人类有目的的行为,因此,史学家对历史进行的是理解,要理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历史教学中,许多教师和学生对林肯在《解放宣言》中只解放叛乱地区的黑奴表示不解,甚至简单断定为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局限性的体现。在作出评价之前,我们首先要理解林肯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理解其内心呢?“整个内心只能借着它的言行来理解”[7]11。因此,要理解林肯为什么这么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完整地阅读《解放宣言》这一基本史料。此外,“个别的事物只能在整体中被理解,而整体也只能借着个别的事物来理解”。[7]11如有必要,我们还要将林肯这一举动置于美国的政治体制与观念、南北战争的形势与人们的反应、林肯个人的性格与信念等背景中去思考。在《解放宣言》中,林肯宣布解放黑奴后,特意加上了这么一段话:“And upon this act,sincerely believed to be an act of justice,warranted by the Constitution,upon military necessity,I invoke the considerate judgment of mankind,and the gracious favor of Almighty God.”[6]即,林肯申明,这一举动是正义的,合乎宪法的,是一个军事措施,而他是作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的职权来采取这一军事措施的。为什么会这样?按照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黑奴是私人财产,不能绕过法律的手续贸然予以剥夺,而以立法的形式来废除黑奴制度是国会的权力。作为总统,林肯无权制定法律解放黑奴。因此,林肯就找了一个理由,他认为这是战争时期,而他是军队统帅,出于军事目的而解放叛乱地区的黑奴,相当于没收叛乱者的财产。当然,对于没有叛乱的地区,他自然就无权解放当地的黑奴。这一理解,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而之前的理解(实则是误解),是在没有看到完整的《解放宣言》之前,就用我们惯有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理念去评价林肯的作为,自然离事实相距甚远。 “历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7]36,历史教学同样也应如此。探究的基础是史料,探究的起点是提问,要质问史料,“要在自己的心灵中带着问题阅读他们”,“要从一段话里公然提炼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来构成对他已经决定要询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7]373。《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粗粗一看,这段史料平淡无奇,因此教师在备课时就将其轻易放过了。可是,只要我们认真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里头有不少问题。首先,一个宦官为什么要从事发明创造?其次,他改进造纸术后,为何要马上向皇帝报告?再次,皇帝为何要称赞蔡伦的造纸术?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除对天文、医学、农学、数学等有所扶持外,对一般的科学与技术都不甚重视。那么,汉和帝为何对造纸术的改进如此重视?这些问题,对于范晔来讲,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讲,却是个迷惑不解但值得探究的问题。征诸史籍,这应该和东汉的文化教育有关。《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3万余人在太学读书,经书的传抄是个大问题,竹简、缣帛作为书写材料,难以普及。蔡伦其时,太学有多少人呢?元兴元年是105年,元兴是汉和帝的年号。汉顺帝125—145年在位,在和帝之后。本初元年是146年,本初是汉质帝的年号。因此,汉和帝时期太学人数不会达到3万余人,但应该也不会少。汉和帝本人对文化教育十分重视。《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东观汉记》记载:孝和皇帝“外忧庶绩,内勤经艺,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按,东观是东汉皇宫藏书之府。由此可见,汉和帝对书籍是十分看重的。以此为背景,就很容易理解蔡伦《后汉书·宦者列传》关于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记述,改进造纸术的意义也就迎刃而解。因此,依据这段史料,可以设计成课堂上一个有意思的探究活动,即蔡伦为什么要从事造纸术的发明创造?蔡伦改进造纸术后,为何要马上向皇帝报告?皇帝为何对造纸术的改进如此重视?蔡伦改进造纸术对汉代文化教育的发展有何影响? 以上两例中,《解放宣言》及《后汉书》中蔡伦的传记是每个中学历史教师都能轻易找到的材料。只要拥有搜集基本史料的意识,掌握一定的解读史料的方法,教师就都能创造性地开展历史教学。 历史教育不能没有理想,历史教育也不能只有理想。在理想的指引下,我们还要从现实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路径往目标迈进。基本史料的提出与运用示例,是在当今我国历史课程设置和教育环境的基础上,朝着历史教育应有的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批判和历史意义而迈出的一小步。这一步只是开始,远远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当下,正在修订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史料高度重视⑤,这对历史教学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一场变革即将开始。因此,对历史教师而言,在课堂中运用史料已难以成为问题;但是,为什么要运用史料,运用什么样的史料,如何运用史料,史料运用与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解释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必将成为历史教育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基本史料的探讨,如果幸而成为这场变革的垫脚石,自然是笔者殷切的期盼。 ①第一篇可考的将“史料”与“教学”连在一起的是晋松《史料解析题与高中文科复习课的史料教学》,载《历史教学》1991年第6期。这篇文章显示,高考史料解析题的出现,推动了历史教学中史料的运用及史料教学这个概念的出现。 ②按照两位先生的意思,不用史料的教学不是真正的历史教学。 ③如奥立弗·A.约翰逊,詹姆斯·L.霍尔沃森编《世界文明的源泉》(上下卷),佩里·M.罗杰斯著《西方文明史:问题与源头》,丹尼斯·舍曼等著《世界文明史》,秦晖等主编《大学精神档案》(五卷本),质量都很高。 ④课件作者引用的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片断与《独立宣言》有关,但作者误以为与宪法有关。该片断是:“我梦见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实现它的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 ⑤《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把史料实证作为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之一提出来。虽然最终的文本会有所出入,但这足以说明课标制定者对于史料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