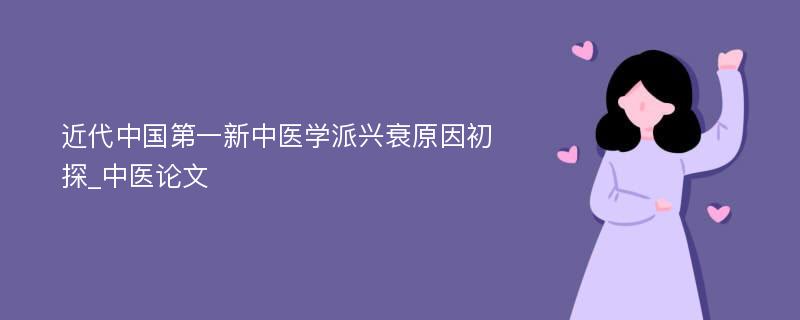
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中医学堂兴衰原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论文,一所论文,学堂论文,近代论文,中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1)11-0112-06
中医教育,源远流长,薪火传承,不绝如缕。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影响日盛,波及包括传统中医教育在内诸多教育领域。在此形势之下,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效仿西学,开办新的学堂。一些引入新教育模式的中医教育学校也在此形势下促动下产生,为传统中医教育开启了一扇新的门窗。这种在西学东渐之风催动下产生的中医教育院校与以往的传统中医教育究竟有何本质区别?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在办学宗旨上,主旨是保存与发扬国粹[1];其二在教学管理上,模仿西医教学模式,设置教学大纲,尝试编写与古代医学经典不同的教材,引入中医课程之外的其它内容,其三在学生管理上,集中管理、集中授课,有明确的学习年限及毕业要求,其四在学科建设上,创办学术刊物,开展学术交流。
然而,现代中医教育学校究竟谁为嚆矢,学界所言莫衷一是。如陕西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国医学史》认为到了民国各地才开始创办中医学校;贾得道主编的《中国医学史略》也认为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最早的中医学校;陈邦贤认为清末创办的具有中医教学内容的医学堂是京师大学堂的“医学馆”,创办于1903年,停办于1907年[2]。而笔者根据所阅史料分析,认为1885年创办于浙江瑞安的利济医学堂应为现代中医教育之滥觞。对此观点,林乾良虽然早在1980年发表的《我国早期的中医学校》一文中已经提出[3],但所述过于简略,使人难见我国第一所现代中医教育学校之概貌。为此,笔者已另撰文介绍其基本情况,指出其创建最早,有史可考;名为医院,实为学堂;教学管理,颇有新意。本文则着重从科技社会学角度对其兴衰原因进行一些分析。
利济医学堂由陈虬与陈介石、陈葆善等人于光绪十一年(1885)创办于浙江温州瑞安,系全国最早的一所新式中医学校。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中医学校最早兴起于温州,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地域原因和基础的。
一 利济医学堂的创办原因分析
(一)事功学派成其文化背景
瑞安历来文风鼎盛,夙有“理学名邦”、“东南邹鲁”之誉,在这个土地上还产生了对现在的经济发展都有深刻而广泛影响的浙东事功学派。任继俞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曾辟有专章讲述浙东事功学派,认为其是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流派。这一观点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看法。经世致用之学是和汉学(考据)、宋学(义理)对立的社会改革之学,它发端于宋代永嘉事功学派,理学家陈傅良学重“经世致用”,开永嘉学派之先声,叶适集永嘉学派之大成。陈傅良和叶适均是瑞安人。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所处的时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的时期,山河破碎的现状,激起了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在研究历史,考察古今成败教训时,他们认为统治者只有奉行济世安邦的政治路线,才能使国力强盛,而空谈心性道德理学,则于事无补,最后只会使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所以他们的思想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主要表现在唯物疾虚、事功务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特点。他们认为“读书不知接统者,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总之“经世致用”之学,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切忌空谈。这一点对浙东后来的学者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晚清之际,自孙氏(指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之父孙衣言及其弟孙锵鸣)兄弟提倡陈叶之学,校刻永嘉丛书,斯学遂盛,先生(指宋恕)复从而和之,一时如陈介石等亦以文史学鸣于世,而世人复知有永嘉之学矣[4]。”恰好清末社会矛盾也日益激化,与南宋时期山河破碎的现象十分吻合,他们以救国教民为己任,积极寻找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办法。“学無新旧,但求其是,時有古今,适应者存。自西学东渐,而传统文化,遂起动摇,笃旧务新,各趋极端,互相排挤,冰炭不容,终无补于神州之劫运。……凡百政学,有足以救亡图治者,靡不称引,观其会通,一以贯之,固不問其为东西新旧否也”[5]。
(二)经世致用躬亲社会实践
宋恕、陈黻宸与陈虬私交甚密,人称“东瓯三先生”。虽然宋恕没有参与过利济医学堂办学过程,但对陈虬等人的办学过程始终持支持态度,对陈虬个人的学识文章也是赞赏有加。在清末永嘉之学复兴之时,东瓯三先生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对西方的制度、社会、文化等又有一定的了解,加之受永嘉之学的影响,为社会做一点实事会成为他们的人生不二选择。“学校议院报馆三端,为无量世界微尘国土转否成泰之三大纲。……三大纲领既举,則唐虞三代之风,渐将复见,英德法美之盛,渐将可希矣。”[6]由此可知“办学办报办议院”,是他们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利济医学堂的创始人无不用很大的精力甚至是终身的心血实践着这三种他们认定的治国方略。利济医学堂及利济学堂报无疑是他们为这付诸的实践,陈虬还与章太炎、宋恕等主编《经世报》,该报是戊戌变法运动期间浙江维新派的报刊,1897年8月在杭州出版,出刊十余期即停止[7]。陈黻宸一生除了主要从事教育,在多家书院任教,还主编过《新世界学报》并任户部主事、浙江咨议局议长、民国首届国会议员[8]。总之浙东事功学派是利济医学堂创办的文化原因,创始人们都深受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三)西风东渐启发办学思想
陈虬(1851-1904),原名国珍,字志三,号蛰庐,自称皋牢子。是利济医学堂的主要创办人。据林炜然(陈虬是其母亲的姑父)回忆,陈虬除应科举外,还精读医典,钻研唯识。为深入研究,曾跟天童某法师学梵文,稍后又贪读汉译西书。在接受西方知识体系以后,陈虬似乎找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原因,办学堂、启民智,方能国力日强。“近者,泰西各国,智学飚起,士农兵商,妇女僮孩,八龄以内,罔不入塾,偶违公例,罪其父母。是以教盛于内,威溢于外。英土学校,三万六百有余,法域学校七万五千有余。即东邻三岛之地,亦二万七千五百。”[9]
其时西方的医书已较为系统,如英国传教士合信其著作《合信氏医书五种》较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方医学。其中《全体新论》于咸丰元年(1851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内有大量人体解剖图。
据《中华年鉴》统计,1859年全国教会医生28人,1876年已有教会医院16所,诊所24个,1897年教会医院为60个,1905年教会医院已达166个,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人。
(四)社会责任促成寻找报国之门
陈虬是一个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他的著作涉及社会很多方面,其主要著作有《治平通议》六卷,即《治平三议》一卷、《经世博议》四卷、《救时要议》一卷。《经世博议》是陈虬维新变法思想的奠基之作,其中都察院“设议员三十六人”,地方各县设议院,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出设议院的政治改革主张。其他如提出明律师、设公司、开新埠、通贸易及招华商等变法主张,则更使陈虬的思想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救时要议》是陈虬提出变法改制的基本纲领,包括富策14项、强策16项、治策16项。《博议》着重从历史上、理论上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要议》则从时代的紧迫性出发,提出变革的具体内容。陈虬为了推行其政治主张,也曾四处游说,如1890年谒山东巡抚张,提出“创设议院”等条款,但能接受并实践他的理想的机会却不多。所以开学堂成了他传播其思想的重要手段。“欲开其闭,术匪一致,而学堂其基础也。古昔圣王,推本学校以基治理,于是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诸侯则有国学,天子则有太学。”[10]
(五)精研医学造就良医
陈虬从办医学堂入手实践事功理想,还与他有较为扎实的医学功底有关。中国历史上很多名医因病学医或功名不第,转而学医,陈虬学医恰包罗了这样两个原因。“庚午、癸酉、丙子历应省试,历荐不售。己卯复应省试,……又不弟。时先生年已三十,乃专心经世,以过劳咯血,旁攻岐、黄,特与何明经志石、陈主政介石、陈上舍栗庵建利济医院于瑞安”[11]。这一说法易造成歧义,认为陈虬三十岁才“旁攻岐、黄”。事实是陈虬二十岁那年,因治学过劳,“得咯血不寐疾”,兼且秋试不第,受到很大刺激,便决心学医。二十四岁开始,“排日自课”习医,两年后,开始出议方药,步入医师之列。1877年秋冬地方发生疫疠,陈虬在治疗中成效显著,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善于治疗疑难杂症的名医。光绪二十八年夏“东瓯霍乱大行,死亡接踵。是证一起,医流稍矜贵者皆匿不出。先生体素癯,独昕夕出诊,不避艰险,存活甚夥”[12]。1880年,陈虬从历年病历中整理典型的医案共二十例,撰成《蛰庐诊录》两卷;1895年撰写了《霍乱病源方法论》,经过1901年夏“瓯郡霍乱盛行”时“投剂立起”的检验,终于在1902年总结为《瘟疫霍乱答问》,其后作为名著,被收入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丛书之中。
陈虬所处的时代庸医害人事件时有所闻,这一现象也使陈虬感到不安“今之死于病者什一,而死于医者乃什九也!悲矣!”[13]他形象而深刻地刻画这一现象:“近俗日靡,浮浅庸奴,学无师承,略视方书十数部,辄率尔悬壶,持长柄油伞,步行烈日中,望门投入,昵妇妪若家人,盐汗交流被两颊,吮笔叉手,书方如扶乩,仓卒以十数。暮归计囊金,较日常多聚,妻孥大欢笑,环问日来从谁?某某何病?病何治?则蒙然张口,漫不记忆”,“借名流揭医招,故自高声价,设拔号,坐飞轿,奚奴前道,悍然自命为名医。叩以寒热攻补,标本佐使之旨,囫囵恃两端,声嘤嘤蓄鼻间。处方,欠呻,登轿,逐逐去矣!甚矣,其偷也。”在医技日渐成熟之后他更感到“人有必无可医之病,医有必不能医之时”,惟恐自己不免为庸医之归,希望尽心达成“与病家两无恨”的效果。此时的陈虬仍处于力求使自己成为一个良医的境界,其认真总结行医经验集成医案的目的也是为了“备温故知新之助”。但对整个社会医患之间存在问题的思考,对社会整体健康卫生状况的忧虑,也逐渐使他的思想进一步升华,让更多的医生成为一代良医可能是陈虬创办医学堂的动力与出发点。“自种类之将瘠、将弱、将殄、将绝,冥冥之间隐受其荼毒者已非一日,智者不加察,愚者乐于所安,遂使生养休息听其自澌自惫,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种者,国之所与立也。种荣则国昌,种悴则国懦。于是悼大局之糜烂,愤异族之凭凌,慨然思兴医学,为保种之基础。”[14]
二 利济医学堂解体原因分析
(一)个人办学难成规模
十九世纪末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虽然也有政府出资兴办职业教育的做法,但中医教育始终未能得此恩惠。虽然利济医学堂初创之时,其社会环境要好于民国时期,即未受到西医的明显排斥,也没有政府废医打击,但总的来说办学者必须有殷实的家底方可支撑起学堂的开支。清末浙江各地的书院,府、州、县学,村、族办的村塾、族塾、义塾,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田,书院也称院田。学田有田、地、山、荡等,从二十几亩到上千亩不等。陈虬曾与好友数人共同出资购买滩涂地出租,其租金用来开办“心兰书社”,在资料中已显示陈虬在办学过程中自己支出了大量的财力,并提到过医院的“涂产”,可能与其拥有的滩涂地有关。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颁诏废除书院,改设学堂。办学经费来源已有多种渠道,如经费不足者,或由官府拨给,或由地方公款提充,或由募捐解决,或兼而有之。如杭州蚕学馆,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布政司拨银36000两,其中建馆舍、置桑园用银10300两,购办仪器设备用银3000两,宣统元年“奉旨改升高等,添置经费24000余元”[15]。其时利济医学堂已是入不敷出,经费问题仍影响着利济医学堂的正常运转。所查资料中未曾发现陈虬企图获得朝廷帮助的任何努力,利济医学堂经费来源十分有限,如果此时利济医学堂也能和其他职业教育一样得到官府拨款,对它的维持与发展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二)关心国事影响潜心办学
办学过程中,陈虬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了与医学教育无关的事情上。投身政治,中举、三次会试,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办学堂,办医院,办报刊,成其践履躬行维新事业之一绪,虽也撰写《利济元经》等医学理论著作,但已无暇参与具体的医疗活动,陈虬亦自叹息:安得潜心医学者,与之参究其间哉!如1898年,陈虬赴京会试,康有为发动成立保国会,陈虬题名参加,并倡导浙籍人士成立保国会的分会——保浙会,起草了《呈请总署代奏折稿》,认为“自强之道在厚集民力以固人心。……必使人人有保其身家性命之权,而后国家可收其臂指腹心之效。”但在顽固派的反对下,保国会及其分会还来不及发展就有人奏请查禁,而被宣布为非法。6月12日,陈虬无可奈何地归抵上海。戊戌八月政变,陈虬因未参加百日维新而未被列入缉捕对象。但是人心扰动,加上跟黄体芳、孙诒让之间的夙嫌,在家乡难以安居,便转赴外地。正如陈虬的学生在他五十寿序中写到“不意戊戌变政,风潮反对,罢学堂,闭报馆,云散二百徒,累败八千金”,虽然陈虬面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困难有百折不回的勇气,但也不得不面对“世之诬谤、笑忌、倾挤”的困境。
陈虬的专著中,1880年完成《蛰庐诊录》、1884年2月完成《治平三议》、1892年完成《经世博议》(该文是陈虬变法维新和社会变革主张比较全面的阐述)、1892年完成《救时要议》、1893年完成《报国录》、1894年8月完成《利济教经》以及卷七《杂著一》中涉及内容宽泛,三十三篇文章中与医学有关的共四篇,即《医院议》、《零乱病源方法论》、《医历表》、《利济元经》。卷八《杂著二》文章三十五篇中共涉及医学的有《利济学堂报例》、《祷医圣文》、《利济医院习医章程》、《保种首当习医论》、《医医》、《白喉条辨》六篇。这六篇文章中《祷医圣文》、《保种首当习医论》、《医医》并不是探讨有关医学理论与实践,而是借医论政,鼓吹他的改革与维新思想。1880年完成的《蛰庐诊录》是他从二十岁学医到几年来诊病的经验总结,其后的专著大都与医学无关,或者不仅仅为医者言。如刊刻《利济教经》目的是以惠医流,但其“举凡古今中西学业规制以及世间一切人事,皆标举指要,事繁语赅,以期急就。每逢讲期,按章详说,颇益学子”[16]。教经共有三十六章,其中医道章、生人章、医统章中涉及医学内容与历史,生人章中主要介绍人体中的阴阳、五脏六俯、五官七窍、气血及精气神等。可见从章节内容上看,其医学内容仅占授课部分的十二分之一。其中医学内容最为翔实的应是《利济元经》。用陈虬自己为此书作序时说“瑞安始创利济医院,不材叨主讲席七阅寒暑,甄录医籍,……勒成一书,得卷者八:曰运气、曰藏象、曰经脉、曰病因、曰本草、曰针灸、曰死生。凡表者五十有二”。可见《利济元经》陈虬为利济医学堂所编教材,共耗去七年时间,参阅了大量的医学经典著作。全书分为八章,共五十二节。”“念医始炎、黄,道存《灵》、《素》,遂以内经课其徒。曰:“内经者,古之三坟也。举凡天星、历律、地理、人事无不赅,羲皇康济天下之法尽寓于是,苟能明其道,虽致世界大同,不难也。若徒作活人书读,则隘矣!”[17]。此处也明确地显示了陈虬认为学医如果只为了治病则目的太狭隘了。陈虬的思想可能深受传统中医“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影响,故在利济医学堂的创办过程中,他的行为、著作、开设课程等都不是简单为了培养医生而为之。这一出发点当然是站在“医国、医人”的高度,但由于大量的精力用于与医学教育无关的内容上,对利济医学堂的发展势必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新式中医学堂初设经验不足
陈虬籍医论政,企图用培养医生的方法实现为国家培养国手,以实现他报国之愿。在这个基础上,陈虬办医学堂,并没有按照医生培养规律来设定课程,兼学别样以至于冲击了医学主题。如陈虬从事文字改革,编写了《新字瓯文音释》、《瓯文音汇》。前者是陈虬的新字教科书,他用了30多年研究用温州话为新字注音,为一拼音文字。他不但教学生学习,医院里的其他人员甚至轿夫都要参加学习。主张无论文武贫富,老老少少,都要学习新字,要求“明公理发热心有大力量的人,能帮助推广劝说人们学习”,“学好一个,去教一家。使数年之内,吾们黄种四百兆同胞,没有一个不识字”。使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能学会写信记账,再略加些功夫,即能读书看报,同时还要表音正确,字母齐全,做到有音即有字。他把文字改革和国家富强联系起来,他说:“现在我们大清国的病,是坐在富强药方的本草上,只有富强是个对症的方儿。因此造出新字,当那富强方的本草”。主张中国和西洋一样,用拼音文字,就可以无干戈之患。他把中国的积贫积弱归结为中国文字,竟想用温州土话作为国家的普通话加以推广,并用大量的时间要求利济医学堂的学生甚至工作人员、勤杂人员都来学习。这一做法也暴露了当时学堂开设课程是很随意的,与陈虬的个人兴趣有着极大的关系。进医学堂学医的人,应该已粗通文字,否则无法阅读医学典籍,陈虬仍要求他们去学习另一种文字,对医学知识的学习应是有影响的,这或许可能也会影响到人们来医学堂学习的热情。
(四)力图挽救难改败局
陈虬在推行政治主张过程中四处碰壁后,深感怀才不遇,心情极为沮丧。“中日役兴,朝廷亟议变法。先生以公车赴都,与海内志士上书首倡保国,旋为顽锢所阻。先生年逾四十,知天下事不可为,乃东归,一意于医。乙未,遂与志澈创办郡城利济医院,建药房,设学堂,开报馆。”。陈虬年逾四十已是1890年以后,收心于利济医学堂,应该说是做了很大的努力的,如他又在温州开办利济医院分院及发行利济学堂报,仅设立售报处多达69处,分别是本郡:郡城、瑞安、永嘉、乐清、平阳等二十三处。本省:杭州、湖州、嵊县、宁波、萧山、诸暨、台州、海门、金华、兰溪、衢州、黄岩等二十六处。京都:较场五条胡同温州新馆、琉璃厂松竹斋南纸店、天津城南估衣街清秘阁南纸店等三处。外省:上海、苏州、扬州、南京、芜湖、汉口、武昌、福建、广东、澳门等十七处。报纸内容为“凡学派、农学、工政、商务以及体操、堪舆、壬遁、星命、风鉴、中西算术、语言文字暨师范、蒙学等类,区为十二门:(一)利济讲义;(二)近政备考;(三)时事鉴要;(四)洋务掇闻;(五)学蔀新录;(六)农学琐言;(七)艺事稗乘;(八)商务丛谈;(九)格致卮言;(十)见闻近录;(十一)利济外乘;(十二)经世文传”。并强调“医学独详”。其中与医学相关之处主要在“利济讲义”一门,主要内容来自教师与学生对医学内容的探讨,对学生的学习大有裨益[18]。但其中也不乏在当时被认为极不恰当的内容。从谭嗣同曾对利济学堂报评价可见,利济学堂报与当时的时代潮流相左,与陈虬个人的兴趣、特长等相吻。谭的评价是“《利济学堂报》乃缘《时务报》已登告白,故买阅之。今寄到,不意中多迂陋荒谬之谈,直欲自创教,不关于学术。彼即刊本,自可拆购,现寄到四本,即请自此截然而止。……非嗣同敢为反复,致劳清神,实虑此报为害不浅。其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命诸说,本为中学致亡之道,吾辈辞而辟之犹恐不及,若更张其焰,则守旧党益将有词,且适以贻笑于外国,不可不察也!”[19]
谭嗣同与陈虬关系应该不错,从陈虬参加康有为的保国会可证,而且他们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也使他们应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但对于陈虬的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命诸说仍认为为害不浅,唯恐避之不及。这一点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格格不入,对报纸的发行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陈虬的二哥国桢以易象数学著称于时,“虬兄国桢(仲舫)治易象数学兼禅学”[20],又是陈虬的启蒙老师,受他的影响,陈虬不免喜欢谈五运、风水和星命。
陈虬生活的时代是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时代,他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大量吸收西方的知识、理念,在他的身上既有包容并蓄的特征,又不免带有封建迷信的思想,他一生虽深感不得志,但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多个第一: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心兰书社),第一个现代中医学校,第一份校报,第一个编写中医教材,这些平台既是晚清温州维新思想的产物,也推动了维新思想的开展;既是维新实业的模范,又开医学教育风气之先,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对近代温州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其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医学史和医学教育史上留下了绝无仅有的一笔。
致谢感谢李伯聪教授对本文写作给予的支持和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