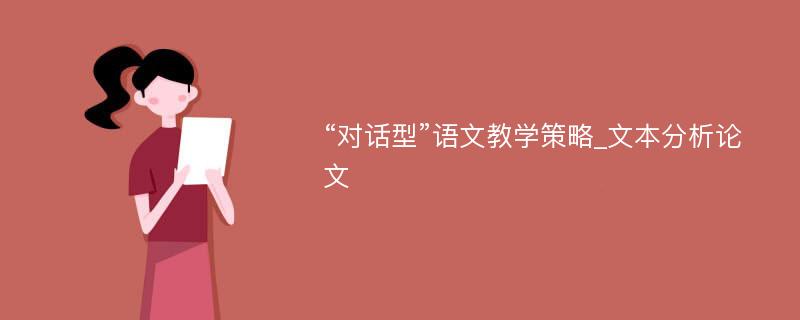
“对话型”语文教学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论文,教学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话和教育似乎有着宿命般的对立,谁想去调和,谁都将冒着或者背离对话或者放弃教育的风险。伽达默尔说:“虽然我们说我们‘进行’一场谈话,但实际上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它就越不是按谈话者的任何一方的意愿进行。因此,真正的谈话决不可能是那种我们意想进行的谈话。一般说来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即我们陷入了一场谈话,甚至可以说我们被卷入了一场谈话。”[1] 可见,对话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指示,不可预设的,只能由对话本身所推动,其内容其成果都是在对话过程中生成,不受对话主体所控制和引导,对话主体只是“陷入”其中而已。但是,不可否认也必须坚持的是教育必定有目标有指引,教育必须有教育性。“教育作为人类的活动,相对于个体的经验而言,在内涵上丰富得多,它对个体总是具有塑造性和引导性,而个体总是要接受教育的引导和塑造。”[2] 显然,在理论上对话与教育难以调和。这种对峙也为教学实践带来了混乱和纷争。
2001年,笔者曾撰文提出要将对话理论引进语文教学领域,(注:参阅王尚文.关于“对话型”语文教学的对话.语文学习,2001.7-8) 到今天,它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许多研究者正在努力推动着这一研究向纵深发展。笔者现在想补充说明的是,“对话型”教学不是要把语文教学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百分之百地变成对话,而是要使语文教学具有对话性。“对话型”教学是对话理论和语文教学对话的结果。它已不是原来的对话理论的克隆,也不是传统的语文教学穿上“对话”的外衣,而是在两者的对话中产生了新质。语文教学汲取对话理论的营养,不但不会改变反而还会加强自己的教育性。与传统的语文教学相比,“对话型”教学的对话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学的目的主要不是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而是让学生在对话中学习对话,学会对话。读写听说可以是对话,也可以不是对话。“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都是阅读,但都不是对话。对话性的阅读就是和文本展开平等真诚地交流,通过和文本的视野交融,共同建构新的意义,共同进入新的境界。其次,教学的内容由“训诲型”教学的教圣贤之道,由“传授型”教学的教语言知识、写作知识和阅读知识等转变成为让学生在读写听说的实践中学习对话,激发对话的热情,养成对话的态度,掌握对话的规则,等等。第三,教师的角色,由训诲者、传授者变成对话活动的参与者。他是平等者中的首席。以阅读教学为例,他不是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教给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与文本对话。为了实现培养学生对话的态度和能力这一教学目的,“对话型”教学并不排斥教师的“教”,而是强调“教”的功能的转变;不是排斥训诲和传授,而是将训诲和传授转变为学生学习对话、学会对话的必要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对话型”教学中教师要勇于教、善于教,否则就是严重的失职。
二
教什么,怎么教?我这里尝试着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引导学生在读写听说的活动中树立对话的态度,要让学生明白,对话不仅仅是发言,也包括倾听,而且首先是倾听,倾听才是关键。文本是个潜藏着巨大可解释性的主体,可是读者在对它作出自己的解释之前必须向文本敞开自己,用心听听文本向他说了什么。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谁在倾听,也就随之而听到了更多的东西,即那些不可见的以及一切人们可以思考的东西。”[2] 与文本对话,既不能以文本为中心,也不能以读者为中心,只有将文本搁在与自己的我一你关系中,只有真诚地与文本交往,充分尊重文本的主体性,才有真正的理解。如果学生惟书是从,以为阅读就是复制文本的意义,显然不是对话;如果学生只是唯我独尊,以为阅读只不过是将自己的主观意愿投射在文本中,也不是对话。由此,教师就必须进行引导、说理甚至训诫——这是教师的教学权利也是教学职责。在课堂上还有一种对话,是在学生与学生之间展开的。也以阅读教学为例,当学生将自己的阅读心得与其他同学交流时,教师应该意识到这是对话。由于很多人误解了语文课程标准提倡的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和个性,于是在许多阅读课堂上,学生经常是各说己话,互不相让。对此教师就应该教育学生,使他们知道对话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是在交流中共同前进,取得可共享的意义,从而共同提升。越是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对话,主体间的空间就越大,对话的成果也越大。戴维·伯姆说:“对话并不仅仅局限于两人之间、它可以在任何数量的人之中进行。甚至就一个人来说,只要他抱持对话的思维与精髓,也可以与自己进行对话。这样来理解对话,就意味着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4]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新的理解和共识”的“萌生”,其前提同样也是倾听,同样也需各方敞开自己。为了树立对话的态度,在教学中可以有引导,也可以有教训。该鼓励则鼓励,该批评则批评,教学中有微笑,也有严肃。可是很多时候教师不仅没及时作这样的引导,甚至还得意于学生缤纷的“创造性阅读”成果和他们维护各自成果的努力,于是阅读教学培养了一群焦躁的阅读者,他们急于言说,却懒于倾听。可以断言,如果教师不首先让学生明白倾听的重要性,那么在教学中很容易培养学生的反对话态度。
其次,基本的对话规则是对话得以进行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对话是自由的但不是任性的,恰恰是在对规则的遵循中自由才有可能。规则之于自由便如河床之于水流,是成就而非阻碍。可以说,只有合规则的才是自由的,从而才是对话的。例如,你不能将虚构的作品当写实的来读。听说有人从武松打虎中读出动物保护问题,并以此诟病《水浒》;也有人读寓言时却较起真来,说当鹬的嘴巴被蚌咬住时怎么还能讲话。此类读法显然没有尊重文本的文体性质。又如,文本产生的时代要受到关注。每个文本都是历史性的,当我们以现时的视点阅读它时不能无视那个时代的相关特征从而作一厢情愿地解读。不是有人从《背影》里读出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吗?显然他没想到交通规则是有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再如,要尊重文本的整体性。因为“作为阅读者,在理解中总是已经面对言说之整体”。[3] 文本的整体性来自它结构的有机性,你不能抽取某个要素孤立地来说事。当然阅读规则还有很多,构建系统而具体的规则不是本文的重点也不是这样的小文力所能及的,此处仅为举例而已。“对话型”阅读教学主要应该指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以及读者之间(包括教师)就文本解读展开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实现以及学生在对话中学习对话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规则的掌握和运用情况。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讲授一些解读学知识。无可否认,对文本的理解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在现代解释学上来讲更多的是个人体验,在体验中建构意义。但作为一个不成熟的读者,在学习阶段,一定的解读知识的掌握会有助于与文本展开更深层次的对话。因为一个新的概念一套新的话语系统将会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视野。以什么样的语言来说话意味着以什么样的语言来倾听,也规划着相应的方式来思维。无疑,学习一些解读学知识将有助于提高在对话中学习对话的效率。在“对话型”教学中,教师的角色是双重的,他既是一个读者,一个对话者,他更是一个教育者引导者甚至管理者,是规则的传授者和守护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不一定是对话者,他的教育行为就不是对话的。同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可以去引导和传授。
其三,有效对话也离不开知识的支持。现代哲学解释学认为,所有的理解都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展开的。那么前理解的品质自然会影响理解的品质。虽然我们不能说知识的丰吝必然决定体验的深浅,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两者是相关的。比如,我们读鲁迅《一觉》中的一段:
飘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如果我们依然记得《诗经·静女》中的“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那么对于理解和体验鲁迅的话是会有帮助的。《诗经》的记忆对于《一觉》的理解来说,就是前理解中的知识构成。如果我们进而得知,其实在文本的世界里,这样的互文关系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显然我们眼前会豁然打开一片理解的视阈,在眼前的文本与历史上的文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本的联系中,理解将更加深邃。再比如,读海子的《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如果我们知道了海子在写完这首诗不久就卧轨自杀了,而且年纪轻轻,那么对于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明天”一词所蕴含的悲苦将会有更深切的体会。对海子的人生经历的了解就是理解《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的前理解。构成前理解的知识并不是教学的目的,但它们是理解文本的必要的辅助手段。学生如果缺乏这些知识,就会妨碍与文本的对话,此时教师就应该加以补充。比如,“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中的“坐”字,与现在使用中的意义差距很大,有关知识就必须加以补充。补充的方式可以是传授讲解,也可以是要求学生自己查阅相关资料,怎么有效率就怎么做。比如,有人在教《论语》时,想先让学生了解孔子。他问学生是否知道孔子是哪里人,学生说不知道,教师就让学生在小组内讨论。我觉得教师还不如直接告诉学生孔子是山东人就是了。“对话型”教学,并不是不教知识,只是不将知识的教授当做终极目的,而主要是将之看成促进学生与文本对话的手段。
最后,教师要有意识地与学生共享阅读成果。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教师要勇于与学生共建意义。为什么这里要用“勇于”一词?是因为笔者发现在当前一些所谓的对话型阅读课堂上,教师似乎越来越不敢说出自己的阅读心得,似乎一发表意见就违背了对话原则。于是满堂课都是学生自己在说,反复地说,交替着说,也不见对文本的阅读有什么推进。其实,一般来讲相对于学生,教师是较为成熟的阅读者,他的视野他的前理解一般要大于学生。在与教师的对话中,学生将获得更大的促进。因为对话能力只能在对话的实践中培养。学生是与一个成熟的阅读者对话,还是与一个同样幼稚的阅读者对话,当然会影响他的实践效果。所以教师有能力有义务与学生就文本展开对话。另一层意思是,教师与学生不是简单地交流各自的阅读结果,而是共享自己与文本的对话过程。一方面,理解就是一个过程,过程本身具有教学的本体价值,课程标准就将“过程”作为语文阅读教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过程展示也有很高的方法论意义,是教师作为相对成熟者在与作为相对稚嫩者的学生的对话中培养学生文本解读能力的好方法。面对文本,师生是平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解能力是相等的,并不意味着他们与文本对话的过程是同等品质的。对于“对话型”阅读教学来讲,对话过程的价值要大于对话的结果。某人分析《再别康桥》前两句时写道:“可谓情的俱现地传达出诗人的袅袅情思,与感伤沉默的哀伤情态。”这是他作为读者与文本对话的结果,对于学生来说,告知结果虽然不能说毫无意义,但正如有些批评所言,让学生分享情的是“如何‘俱现’的”[5] 无疑具有高得多的教学价值。笔者以为“对话型”教学并不一概排斥教师作这样的启发性的分析。
现在我们再重申前文的观点。(1)“对话型”教学必须坚持对话,学生和文本间的对话实践是培养对话态度和能力的基本途径。对话,是两个平等主体间的真诚交流,要强调的是“主体间”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方。任何突出学生或突出文本的做法都是反对话的。其实强调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关系,不仅仅是出于阅读技能培养的考虑,作为教育活动,还是完善人格的需要。因为人,“只有通过与‘你’的关系,‘我’才实存”。[6] (2)对话的态度和能力是需要教的。教师的职责和教学的任务就是教学生学会如何对话。因此同样也是作为教育性活动,教授和引导是必然存在的。但是这种“教”和“导”的目的和内容与以前的教学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对话教学中的“教”和“导”不是为了替代学生与文本的自主交往,而是促成这种交往。因此,“对话型”教学并不是淡化教师的作用,而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把学生的读写听说活动提升为对话实践,并置身其中,教学生学会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