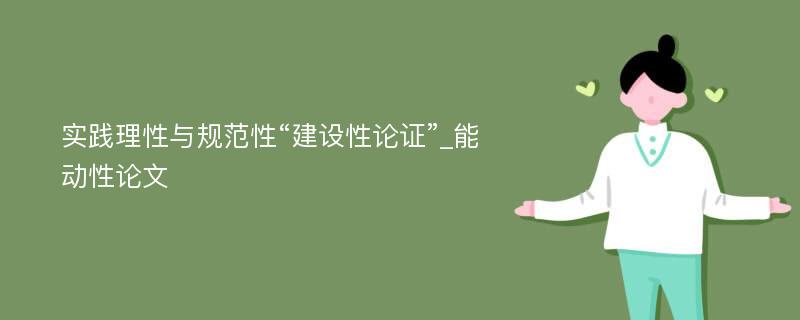
实践理性与规范性的“构成性论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范性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代实践理性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有关规范性的完整说明,必须依赖于一个完整的关于行动以及能动性概念的哲学说明。这就是有关规范性本质的“构成性论证”。构成性论证在当代有两位重要支持者,一位是C.考斯伽(Christine Korsgaard),她最为系统地提出了“构成性论证”;另一位则是D.威勒曼(David Velleman),他关键性地修正了考斯伽的方案。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对他们的工作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作出考察。
人类行动者是能够根据理由来行动的存在者。这个通常被称为“理由响应”(responsiveness to reasons)的特征,被认为是人类行动者的一个典型特征。拥有“理由响应”的能力,就意味着有能力去将某些考虑视为是可以据之以行动的理由。对于某些类型的行动理由来说,它们则更具有一种独特性,以至于一旦行动者拥有了这个理由,那么,行动者就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去据之以行动。包含了这种“应该”涵义的理由,也就是规范理由。
探讨规范性的本质,就是要探讨(1)“实践理由是不是具有规范性”以及(2)“实践理由的这种规范性如何获得确凿的根据”。很显然,第二个问题能不能得到回答取决于第一个问题能不能得到回答。然而,问题在于,围绕第一个问题本身,已经产生了一种否定性的回答。这个否定性回答主要是由伯纳德·威廉斯提出的。
威廉斯论证说,如果一项考虑能够成为行动者的行动理由,这项考虑必须是行动者能够在自己的主观动机集合中相应地找到激发性因素、并通过某种慎思路径来将其内在化的。否则,这项考虑就不可能成为行动者的行动理由。①威廉斯的这种观点,也被称为是一种“内在主义观点”。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如果威廉斯的内在主义观点只是一种有关理由给予(reason-giving)的解释性说明,那么,这个观点当然没有什么错误。但它不过是在阐述一个微不足道的真理。只是,威廉斯的雄心并不限于此。出于对经典的休谟主义的承诺,威廉斯试图将内在主义观点设想为一个有关行动理由如何获得辩护这个问题的说明。如果威廉斯是对的,那么,除非一项考虑能够在行动者的主观动机集合中找到激发性因素,否则,这项考虑就不能在获得辩护的意义上成为行动者的行动理由。
由于将内在主义观点当做一种辩护性说明,威廉斯实际上就承诺了这样一个主张:除非一项考虑能够在行动者的主观动机集合中找到激发性因素,否则,行动者就不在任何意义上“应该”去将这项考虑作为自己的行动理由。这样,威廉斯实际上就通过采取经由激发性来说明规范性的策略,取消了规范理由存在的可能性——实践理由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这就导致了一个被考斯伽称为“实践理由的怀疑论”的主张。②
为了理解为什么对于实践哲学家来说实践理由的怀疑论是一个严肃的挑战,我们就需要去搞清楚,在现代道德哲学的框架下,规范性概念究竟被期待去承载什么样的功能。现代道德哲学具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形式:立法模式。正是由于采取了立法模式,道德原则或实践规则中所蕴含的“应该”思想,就一方面成为奠定整个现代道德哲学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另一方面又亟待获得说明。规范性概念在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扮演辩护这种“应该”思想的功能。按照规范性概念的涵义,某些实践规则(比方说道德规则)必须是具有律令性(imperativeness)和普遍性(universality)的。现在,如果威廉斯是对的,那么,一方面,任何可以被刻画为行动者的行动理由的考虑,都必须是在行动者主观动机集合中已经存在激发性因素的考虑;另一方面,任何主观动机集合实际上都是一个针对特定行动者而言的。因此,任何一个行动理由也就都只有相对于特定的行动者来说,才具有理由给予的地位和力量。这么一来,就没有哪项行动理由是能够一般而论地针对所有行动者而具有律令性的,因为任何行动理由的给出理由的力量都取决于个别行动者自己的主观倾向;也没有行动理由是能够具有普遍性的,因为每一个行动者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主观动机集合。因此,一旦规范理由不能独立于激发性理由而获得辩护,那么,整个现代道德哲学所要求的那种律令性和普遍性,就成了无所依靠的东西,整个现代道德哲学的大厦也就轰然倒塌了。③
现在,为了真正避免实践理由的怀疑论,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彻底颠覆威廉斯所采取的那个经由激发性理由来说明规范理由的策略。如何来获得这个说明呢?为了获得这种说明,哲学家必须要同时达到两个论证目标:一是,他们必须表明,规范理由同时也具有动机上的激发性;二是,他们也必须表明,存在着一个独立于行动者具体主观动机的有关实践理由规范性的说明。考斯伽本人已经为此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论证。
按照考斯伽的思想,要想同时获得这两方面的说明,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分析“理性行动者”这个概念本身。④一个“理性行动者”的概念,内在地包含了“符合理性”(rational)和具有“能动性”(agency)的思想。作为一个人类理性存在者,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主观倾向和动机,将这些动机概括起来说,就是“按照深思熟虑的合理性(rationality of prudence)的要求来开展生活”的动机和“按照道德的合理性(rationality of morality)的要求来开展生活”的动机。在考斯伽看来,“符合理性”的概念和“能动性”的概念本身已经蕴含了这样的思想: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人类行动者必然能够去回应合理性的要求、也必然应该去回应合理性的要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行动者”(be agent)的概念就已经蕴含了行动者有一个“应该回应合理性的要求”的动机、并且根据合理性的要求来调节主观动机和倾向的涵义。这样,考斯伽就满足了第一个方面的论证目标。
进一步地,“合理性的要求”不是一个针对个别行动者而言的东西,相反,它是一个针对理性能力本身而言的东西——因此,尽管个别行动者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比方说意志软弱)而疏于去回应“合理性的要求”,然而,只要他仍然是一个行动者,只要他仍然具有理性能力,“合理性的要求”就仍然适用于他。进一步地,“符合理性”是能动性的一个构成性特征,而能动性则是界定一个人类行动的定义性标志——按照考斯伽的观点,考虑一个活动(activity)或者行为(behavior)是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血肉丰满”的人类行动,关键的指标就在于行动者有没有通过充分发挥能动性来介入这个活动或行为。准此,“符合理性”的要求作为一种实践理由或者说实践要求,就针对每一个人类行动者,构成了一个规范理由或要求:只要你还算得上是行动者,只要你的行动还算得上是“血肉丰满的行动”,那么,“符合理性”的要求就针对你而提出了一项具有规范性的理由。这样,考斯伽就满足了第二个方面的论证目标。
我们已经看到,考斯伽实际上是要通过分析行动和能动性的构成性特征,来揭示规范性的本质。考斯伽的这个说明模式之所以能够满足上面提到的那两个论证目标,是因为她将一个已经具有“规范判断”色彩的思想嵌入了行动和能动性的概念本身之中——作为一个行动者,为了调动和发挥能动性去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就“应该”去接受“符合理性”这个实践要求的调节。对于许多人来说,考斯伽的这个论证模式开辟了一条论证规范性本质、从而彻底颠覆实践理由的怀疑论的新路子。
当考斯伽论证说行动和能动性存在一个构成性特征时,她实际上拥抱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包含两个基本的观点:(1)行动和能动性的发挥必然存在着某种目的(telos);(2)更进一步地,之所以行动和能动性的发挥存在着某种目的,是因为构成行动和能动性的那种特征本身具有一个将行动和能动性的发挥导向这种目的的功能(ergon)。概括起来说,这种观点在假设了关于行动和能动性发挥的某种目的论观点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有关行动和能动性的构成性特征的“功能论证”,来将这个构成性特征理解为是使得某些行动理由具有规范性的根本原因——由于行动和能动性在构成上具有某种功能,行动和能动性就“应该”被这种功能所引导,以实现某种内在的(intrinsic)目的。就像我们熟知的,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最早提出了这个“功能论证”。⑤
威勒曼就规范性的本质这个问题所采取的论证,在根本上来说,沿袭了这个功能论证的结构。也正因此,他同意考斯伽的基本主张,认为为了理解规范性的本质、彻底挫败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最好的论证方案确实就是通过说明行动和能动性所具有的某种构成性特征,来说明规范性的存在并揭示规范性的本质。不过,尽管在基本论证目标方面存在共识,威勒曼的思想也从一个关键的地方开始不同于考斯伽的观点。
我们已经知道,采取功能论证这个论证结构的条件之一,是要去论证说,行动必然存在着某种目标。对于考斯伽来说,行动的目标显然就是“符合理性”。我们也已经看到,采取功能论证的另一个条件,是要去论证说行动和能动性的发挥具有某种构成性特征。对于考斯伽来说,行动的构成性特征显然也是“符合理性”。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了考斯伽的说明中的一个致命缺点:在回答某些实践理由是不是具有规范性这个问题时,考斯伽试图说,某些实践理由是具有规范性的,因为任何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类行动都必须导向“符合理性”这个目标;在回答“实践理由为什么具有规范性”这个问题时,考斯伽则试图说,这些实践理由之所以具有规范性,是由行动本身所具有的“符合理性”这个构成性特征所决定的。考斯伽的整个论证依赖于一个“一般而论的‘符合理性’的理由”(reasons for being rational as such)。但是,这个说明是空洞的,因为它只是一个一般性(generic)说明。然而,真正能够被规范理由所调节和引导的目标和理由是且只能是“具体化的”目标和理由。即便任何一项“血肉丰满”的人类行动,都必然包含构成性的行动目的,这些目的也依然是需要被具体化加以描述,才能得到理解东西。否则,这个构成性由于内容上太过抽象,根本就不能在具体实践中发挥引导行动(action-guidance)的功能。⑥
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下棋”这个行动存在着一个一般性的构成性目标:“去赢”;这个构成性目标也为你的每一轮走棋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规范理由:“应该去赢棋”。如果你的“下棋”活动不是受到这个规范理由调节的,那么你根本不算是在下棋,而是在“挪棋子”或者干别的什么活动。即便如此,你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这个一般性的构成性目标及其所提供的规范理由的存在,而开展一项“下棋”行动。因为(1)假设你不是一个“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也就是说,假设你接受将“去赢”这个理由视为具有规范性地位的理由,并且试图在整个行动历程中受到这个规范理由的调节,但是,面对“去赢”这个规范性目标,你仍然无法开展一个行动,因为你并不知道一项行动如何才能算得上是在受到“你应该通过走棋去赢”这个规范性理由的调节,除非你知道什么才能算得上是有关“去赢”的具体化描述;(2)如果你确实已经是一个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你不仅不会情愿接受将“去赢”当做“下棋”的构成性目标,并采纳它所提供的规范性理由,反而恰恰会对此产生质疑:到底是什么为“去赢”作为“下棋”这个行动的构成性目标提供了辩护?更进一步,如果“去赢”这个构成性目标本身需要去获得辩护,那么,就算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辩护,这个新的辩护根据本身也是需要进一步辩护的。如此,你的实践理由的怀疑论不仅没有因为“下棋”行动存在着构成性目标这一点而受到挫败,相反还将整个构成性论证带进了一个“辩护的无穷倒退”。⑦
作为构成性论证的支持者,威勒曼注意到这个危险。不过,他认为,解决这个“辩护的无穷倒退”的关键,就在于要去抛弃考斯伽在一般性层面上去讨论实践理由是不是具有规范性以及为什么实践理由具有规范性这两个问题的做法。威勒曼认为,一旦我们首先将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具体化到个别行动(individuated action)的层面,然后再在这个具体化的层面上去重新引入考斯伽有关“符合理性”是行动和能动性的构成性特征的观点,那么,构成性论证本身就有机会获得成功。因为,采取这个修正后,“符合理性”这个行动和能动性的构成性特征,就面向每一个人类行动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由于每一个个别化行动都存在着一个判断行动是不是成功的标准(criterion of success),因此,每一个个别化行动都可以在行动和行动理由是不是符合那个成功标准的意义上被评价为“符合理性”或者“不符合理性”。这样,就每一个具体的行动而言,行动者都“应该”去遵循那个业已受到相应成功标准辩护的具体的构成性目标的调节,以便开展一个“符合理性”的行动;否则,这个具体的行动就是不合理的(irrational)。⑧
我们很容易看到,威勒曼的策略对于捍卫构成性论证以及挫败实践理由的怀疑论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因为(1)如果你并不是一个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你就能够按照这个具体构成性目标的规范调节,去相应地开展具体行动;(2)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你也不可能通过质疑这项具体的目标和理由的规范调节地位而整个地去质疑规范性理由的存在,而且,一旦有进一步的理由表明,你甚至不得不去接受这一项具体构成性目标的规范调节地位,并且,出于相同的原因,你也不得不去接受任何一项具体构成性目标的调节性地位(regulative status),那么,你就不可能再去坚持实践理由的怀疑论主张。
我们现在仍然以“下棋”为例来对此作一些解释。假设你在开展“下棋”活动,并且假设你下的是中国象棋。“下中国象棋”这个个别行动的构成性目标不仅仅是“去赢”,而且被具体化为“将死对方从而去赢”。这样你就拥有了一项具体的规范理由,通过调节你的行动策略来将死对方。比方说通过牺牲一个“卒”。准此,(1)如果你不是一个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在“下中国象棋”这项个别行动中,你就获得了一个具体的规范性理由,并且在它的调节下,通过发挥你的能动性,引导你的行动朝向“将死对方”这个具体构成性目标的实现;(2)如果你已经是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你不可能质疑“将死对方”是“下中国象棋”的构成性目标,因为就“下中国象棋”这个概念的全部涵义来说,它确实是以“将死对方”为构成性目标的;你也不可能质疑“将死对方”这个构成性目标对你提出了具体的规范性理由,或者否定这个理由是能够对你的行动施加规范调节力量的,否则的话你就根本不是在“下中国象棋”,而是仅仅在(比方说)“挪棋子”。进一步推广开来,按照构成性论证的思想,对于所有的具体人类行动来说,都存在着各自的构成性特征,并因此而导致所有的具体人类行动都存在着各自的具体构成性目标以及相应规范性理由。因此,就像你不能质疑在“下中国象棋”这个个别行动中存在着相应的具体构成性目标和规范性理由、否则就会导致你的行动不“符合理性”那样,你也不能质疑说在任何个别化行动中也都存在着相应的具体化构成性目标和规范性理由、否则就会导致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不“符合理性”。于是,就每一项具体化的个别行动而言,实践理由的怀疑论都将是一个不可信的主张。
很显然,威勒曼之所以要采取上述这个论证,是希望在保留考斯伽的论证所承诺的构成性观点的基础上,同时达到她的论证没有很好获得的两个效果:避免“辩护的无限倒退”和挫败“实践理由的怀疑论”。不过,尽管威勒曼所采取的通过针对每一个个别行动来具体化构成性目标的策略,确实有助于避免辩护的无穷倒退,但是,这个策略并不能直接彻底挫败实践理由的怀疑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威勒曼的策略,只能在每一个个别行动的层面上,去挫败实践理由的怀疑论。然而,在每一个个别行动的层面上挫败实践理由的怀疑论,并不等于在全局的意义上挫败实践理由的怀疑论。威勒曼的论证实际上所表明的是,一个已经介入到个别行动当中的行动者,确实不可能再去质疑这个行动的构成性目标,否则的话,他就压根不是在开展那个行动。但是,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可以争辩说,他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先去介入一个具体行动,然后再去考虑这个行动具不具有构成性目标;而是,他们要彻底否认行动存在着构成性目标这么一回事,从而达到彻底否定规范性理由存在的目的。所以,这些人可能会说,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从局部到全局”的怀疑者:这种怀疑论者是通过怀疑个别行动具有构成性目标,来达到怀疑一般而论的行动(action per se)具有构成性目标;另一种是“从全局到局部”的怀疑论者:这种怀疑论者是通过一般而论地怀疑行动具有构成性目标,来达到怀疑个别行动具有构成性目标。威勒曼此外的论证针对“从局部到全局”的怀疑论者显然是有效的,但是似乎确实不能针对“从全局到局部”的那些怀疑论者。
那么,威勒曼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看到,之所以构成性论证有希望为理解规范性的本质提供说明,是因为构成论者相信,人类行动和能动性具有某种构成性特征,它使得行动和能动性的发挥具有一种目的论式的功能导向。很明显,威勒曼只要去找出一个类似的普遍功能机制来,他就能够去进一步挫败那些“从全局到局部”的怀疑论者。在这个关键点上,威勒曼试图通过重新理解“行动”概念本身,来满足这项论证要求。为此,我们就需要进入到他在行动哲学方面的一些说明中去。
在对行动概念的讨论中,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无法避开唐纳德·戴维森的工作。这是因为,所谓的“行动的戴维森模型”通过一个因果解释机制,关键性地将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activity)同因果世界中各种各样的事件串联区别开来。⑨根据这个模型,任何人类活动都是意向性的活动。所谓意向性,按照经典的看法,是一个由信念和欲望所构成的心灵状态组合。⑩因此,为了解释一项具体的人类活动,恰当的做法,就是通过追踪这个活动所体现出的行动者意向性,来分析出引起这个活动的相关信念和欲望,从而将行动者的激发性信念和欲望视为是行动者开展这样活动的首要理由。
戴维森模型的要害,在于它确实捕捉到了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人类活动是“响应于理由的”。但是,这个因果解释模型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11):按照这个模型,解释一项人类活动的最终解释因子,只是两个心灵状态。这样,在整个解释结构中,行动者本身是缺席的。因此,这个模型在解释有意识的行动和无意识的行动时,不能做出有意义的区分。一旦戴维森模型在解释有意识的活动和无意识的活动之间不存在差别,那么这个模型对行动的设想就不能被构成论者所采用了:对于构成性论证的支持者来说,他们必须要通过分析“血肉丰满”的行动才能获得对行动构成性特征的恰当说明,因为只有在开展这种“血肉丰满”的行动时,行动者的能动性才能真正的发挥调节性作用。对于构成性论证的支持者来说,只有那些有意识的活动,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血肉丰满”的行动。(12)
现在,对于构成性论证的支持者来说,为了获得对人类行动的构成性特征的恰当说明,就必须首先在“行动”和“活动”之间作出恰当的区分。唯一能够满足这个区分要求的因素,就在于行动者本身之中。因为,对于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类行动来说,行动者由于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能动性,才因而能够被视为是自己行动的真正作者。这样,对真正意义上的行动的恰当解释,必须能够最终追踪到行动者本身之中去(而不仅仅是行动者的某些心灵状态)。
为此,威勒曼论证说,存在着一个普遍动机,这种普遍动机构成了每一个人类存在者得以成为人类行动者的条件——如果你在根本上是不受这个普遍动机所驱动的,那么,你实际上就没有能力成为一个行动者。很显然,任何动机都是命题性态度,任何命题性态度都有相应的命题内容。那么,如何理解威勒曼所说的普遍动机的命题内容呢?威勒曼为此提供了一个“知识论说明”:为了成为一个自主的行动者,每一个行动者就都有一项动机去通过开展行动来实现对某种自我知识的把握。换句话说,在威勒曼看来,自我可理解性(self-comprehensibility)的获得,既是人类行动的构成性目标,也是人类能动性的定义性功能——人类行动因此应当被视为是以有意识地掌握自我知识、实现自我理解为目的的活动。这样,为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行动者,就必须去采纳这个普遍动机,并且有意识地受到这个普遍动机的调节;一旦一个人真正成为这个意义上的行动者,那么,他也就获得了自主性。由于这种普遍动机是每一个人类存在者为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者所必须去采纳的命题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就成为了一个“血肉丰满”的行动的构成性动机。对任何一个“血肉丰满”的行动的解释,正是经由追踪这个构成性动机,来追踪到行动者本身之中的。
终于,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说明中,使得人类存在者得以成为行动者的那个构成性特征,就在于对这个普遍动机的采纳和有意识地使能动性受到这个普遍动机的调节。因此,对于那些“从全局到局部”的怀疑论者来说,只要他们接受这个普遍动机的存在,只要他们接受自我可理解性既是行动和能动性发挥的一个功能、也是它们的一个构成性目标这个观点,那么,他们就必须承认人类行动在根本上受到某种规范理由的调节,因为规范性的根源,就在于人类行动者对在一个个具体行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个个自我知识和自我理解的追求之中。进一步地,在每一个具体行动的层面,对于那些“从局部到全局”的怀疑论者而言,针对每一个具体行动而言的“符合理性”的实践要求,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普遍动机指引行动者通过具体行动来获得自我知识和自我理解的要求,因此,每一个具体行动在根本上来说,也是受到普遍动机的规范调节的。于是,实践理由的怀疑论就通过威勒曼的构成性论证,最终在“从全局到局部”和从“局部到全局”两个层面上遭到了失败。并且,由于自我可理解性被确立为规范性的根源、获得自我可理解性的动机是适用于所有的行动和能动性的具有普遍性的动机,说明规范理由具有律令性和普遍性的任务,也就得到了满足。
尽管威勒曼的构成性论证在挫败实践理由的怀疑论方面具有一些优势,不过,在这里,我们仍需保持谨慎。因为构成性论证本身的威力有多大,实际上取决于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的野心有多大。
如果说明规范性的本质这个问题就是要说明规范性所具有的律令性和普遍性,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威勒曼的构成性论证可以满足这个任务;如果“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所要怀疑的是为了开展一项人类行动,是不是存在具有律令性和普遍性的理由,那么,也很显然,威勒曼的论证成功表明,为了真正地去开展这个行动,你就不能去质疑行动的构成性目标所提供的规范理由的律令性和普遍性。在这些意义上,威勒曼的说明是成功的。
但是,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也许有一个更大的野心:他们有可能不仅仅是要去论证说,假如行动存在构成性目标的话,规范理由是不是存在;而是要去论证说,压根不存在实践规范性这回事。(13)如果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持有这样的野心,那么,为了论证规范性的本质,哲学家首先要去论证的,就不是“假如行动存在构成性目标,这种构成性本身是不是可以成为规范性的源泉”,而是,他们必须首先去论证说,“假如行动存在构成性目标,行动者到底有什么理由去将这个构成性目标当成自己的行动目标”。一旦面临这样的论证任务,构成性论证的支持者就不能针对怀疑论者说:“如果你不将这个构成性目标当作行动的目标,你就不是一个自主的行动者”,因为怀疑论者正要对此质疑说“这又能怎么样?”——怀疑论者在这里所质疑的,恰恰是“自主性行动者”这个现代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本身。为了确证这个核心概念,哲学家们就需要去诉诸某种规范实在论的主张,从而刺破构成性论证的理论框架。(14)如果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者的野心大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构成性论证就不可能盛装得下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构成性论证并不能为说明规范性的本质提供一个最终的完整说明。
注释:
①参见Bernard Williams,Moral Luc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01-113。
②参见Christine Korsgaard,"Skeptic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6,83:5-25,pp.5-8。
③需要注意的是,新休谟主义(neo-Humean)的主张与威廉斯所持的经典休谟主义的主张不同。新休谟主义不否认规范理由的存在,它承认某些实践理由具有律令性和普遍性,并认为,“手段—目的”这一工具合理性原则是唯一具有普遍律令性的规范理由。一个例子,参见James Dreier,"Humean Doubts about the Practical Justification of Morality",in Cullity,Garrett & Berys,Gaut eds.,Ethics and Practical Reason,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pp.81-100。
④考斯伽的相关说明,主要体现在Korsgaard,Christine,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The Constitution of Agency:Essays on Practical Reason and Moral Psych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Self-Constitution:Agency,Identity,and Integr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⑤参见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Crisp,Roger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0-13。
⑥参见David Velleman,The Possibility of Practical Reas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3-176。
⑦Peter Railton,"On the Hypothetical and Non-Hypothetical in Reasoning about Belief and Action",in Facts,Values,and Norms:Essays toward a Morality of Consequ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293-321.
⑧参见David Velleman,The Possibility of Practical Reas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6-179。
⑨关于戴维森模型,参见Donald Davidson,"Actions,Reasons,and Causes",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63,60:685-700。
⑩参见John Searle,Intention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1。
(11)参见David Velleman,The Possibility of Practical Reas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31。
(12)参见David Velleman,"What Happens When Someone Acts?" The Possibility of Practical Reas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23-143。
(13)参见David Enoch,"Agency,Shmagency:Why Normativity Won't Come from What Is Constitutive of Action",Philosophical Review,2006,115:169-198,pp.185-192。
(14)起码对于实践理性的康德主义者来说,规范实在论的观点与构成论观点之间是互相排斥的。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证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