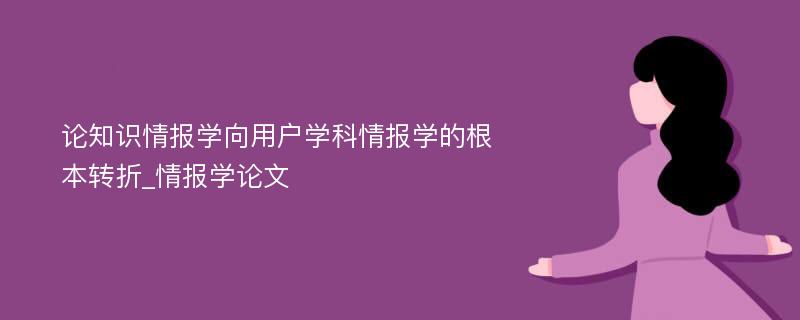
论知识情报学向用户主体情报学的根本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主体论文,知识论文,用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献工作和科技情报工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情报学,是以各种文献和各类信息为前提和基础的学科集合体。尽管论者有不同的研究课题和个别的研究取向,但大多把知识作为情报的本质内涵,或把知识定义为情报的属概念。这种围绕知识来展开情报学研究的思想体系,具有与现实生活关系上间接、服务上盲目、方向上背离的倾向。只要稍微翻阅一下反映学科动态的有关刊物,就可看到我国图书情报界在总体上还未感悟到知识情报学向用户主体情报学,即社会实践主体情报学的根本转折。认清这一转折的实质,对于当今情报学的发展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当代情报学的发展趋向
图书馆是古今中外各类文献最为集中的地方。以图书馆文献知识为前提和基础而生长起来的情报学理论,把检索所获得的文献目录及分析所得的知识单元直接说成是情报,并把情报研究和这种文献知识情报合二为一,并称这样的情报学为知识情报学或图书馆情报学,其核心是知识。
无论是布鲁克斯的知识情报学派,还是米哈伊洛夫的交流情报学派,或萨瑞维克的通讯情报学派,还是约维兹的决策情报学派,也都以文献知识为前提和基础,只是截取的横断面不等,视点不同而已。其实质都是图书馆情报学或知识情报学。
我国的情报学研究起自国外,引进国内,一脉相承,一度轰轰烈烈,但是至今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形成统一的认识。以后,一些同志为了突破知识情报观,尤其是科技情报观这一小情报观的局限,不但从科技知识扩展到社科知识,还广泛地包容了诸如情况、消息、事实、信息,乃至天地间所有的情报对象源,人们又相对地称之为大情报观。其结果却使情报概念更加处于居无定所的境地,或飘忽于广袤的天地间,或淹没于信息的海洋中。《为信息时代的情报危机鸣警》[1], 则以明澈的见解,强烈的责任感,警示了情报危机。这种指情报对象源为情报核心的情报学研究,在自身基点的无限扩展中,导致学科研究的泛化和失落。
有些研究人员则一般地对研究型、教育型、管理型用户的情报需求进行研究,而不是直接地从公司、企业、农民、市民等广大社会实践主体的情报需求这个系统的基础和核心出发,对情报系统的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因此,需求研究盲目被动,需求导向不够突出,弊病很多[2]。 情报学科、包括情报刊物的定位问题,也就长期地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
另一些同志则从情报对象源研究开始,经过情报检索与传递的研究,发展到情报用户的研究,甚至可贵地提出了“用户中心”的观点。这种本来可以使传统情报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理论走向,由于未能摆脱情报对象源为中心的思想束缚,便提出了情报系统“双中心”的观点。而由于仍把“用户中心”置于“系统的末端”,作为“最后一个环节”,这就仍然等于否定了用户在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由此可见,我国的情报学研究,正在迫近“用户中心”这个真正的学科基础的时候,却又一次后退了。难以进展的症结就在于未从根本上摆正用户的位置,调正情报对象源与用户主体的关系,并认识它的本质。我们认为:情报用户原本不光是情报的用户,而且是情报的主体,不光是情报系统的环节主体,而且是产生情报、开发情报乃至主宰着各家情报系统运行和发展的原型情报主体。如果我们不能毅然通过学科基础根本转折的这个重要关口,仍然模糊甚至颠倒产生情报的因果关系,乃至割裂产生情报的这个基本条件。自以为一览无余而各执旧说,不更新观念而继续混战,就难以使情报学由“准科学”和“前科学”的状态跃上常规科学的台阶。
中国情报学当然不能没有自己的基础,人们对文献知识基础的情报争鸣,正使属于情报本身的基点越来越高耸突兀在人们面前。一些不满足于学科现状的研究人员分散地、然而果敢地各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向着学科研究的这一制高点不懈地攀登,并在揭示原型主体情报需求作为学科基础和前提的研究取向问题上尽己所能,不断拼搏,已然显示出情报理论取向上的根本性超越。
比如:波兰情报学家曾经前后对比着说,先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英国,“曾流行过这样一种观点:情报系统的中心点是文献,而不是用户。目前这种观点已经改变,开始把用户看作情报业务的主体”[ 3] 。西方国家近20年来的有关成果认识到情报学“从图书馆的围墙内转移到了用户的大脑中”,从系统观走向认知观“实质是关注(人)而非客体(系统)的一种研究范式”[4]。
中山大学卢泰宏教授曾经深入地说:“从情报源为出发点的传统框架走向以用户为出发点的新框架,即理论体系的头足倒置”[5]。
北京大学王万宗教授也认为:“用户需求是情报系统存在的根据和核心构成部分……不仅决定了情报工作的产生,而且决定着发展[6]。
笔者在《论情报的本质关系》[7]一文中, 把用户情报需要贯穿于情报系统的始终,并使它进入情报之中,积淀于情报之内,从而说明了情报系统核心内涵的根本转折。而在《论重点情报领域的历史转移及情报系统的标志》[8]一文中, 把原型情报主体作为产生情报主体系列的母体,作为管理整个情报系统的中心,从而说明原型情报主体是重新组建学科体系的前提,是使整个体系不再朝令夕改,不再被风一吹就跨的基础。这种情报理论中的基础和核心,与实践系统中的具体用户和效益之间具有高度统一的逻辑关系,因而是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聚焦之点。
李国秋同志则直接呼吁情报学“应该大胆更新学术观念,而代之以人为中心的,以问题解决为核心的学术观念”[9]。当然, 这里的更新其实是回归,是返本开新,是向用户主体情报学即社会实践主体情报学的根本转折。正如天文学历经的变革那样,这种学科研究范式的变革,并不是情报学学科名称的更改。
2 基础和核心是学科转折的焦点
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建立都有一个属于学科本身的基础和核心,有人称之为“硬核”,就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从此出发,形成体系的轴心和主线,贯穿于整个体系。因此,学界研究的目光,重新集中在这个基础和核心问题上,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首先,是因为这一关于基础和核心的问题研究居于整个学科的前提性的基础层面上。情报事业的定位和理论体系的发展,都必须以此为前提。如果基础不牢,整个大厦就会在一瞬间倒塌。要是核心有误,整个体系就难以形成。记得当时一夜春风,时髦的情报概念进入图书馆,并构成图书馆情报学。后来国家科委的一次会议研究决定,情报改信息,情报学科又转换成信息管理学,为之奋斗数十年的情报学大厦在大摆大摇中倍受震荡,面目全非。于是,探寻学科自身的基础和核心,激起学界进行深层思考,当属必然。
其次,中国应该建立起自己的情报学。情报用户作为情报实践的原型主体,作为社会实践主体情报学的基础和核心,同样需要论证,需要学界同仁利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思维方法加以辩证。这一辩证过程,必将使情报研究中最基本的这个前提问题,上升为一个关于学科命运、方向和前途研究的焦点问题。而这个基础与核心的转折,犹如天文学坐标系从地球转移到地球之外的恒星,21世纪的中国情报学需要这个坐标系的根本转折。
第三,由于情报重点领域的历史转移和情报事业系统向社会诸领域的深入和展开,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情报用户——这个置身于社会实践关系中的原型情报主体是产生情报事业系统的直接根源。但是,未来信息技术及整个信息学科的快速发展,又容易忽视和模糊情报学发展的这个前提。为使当代情报学研究顺应社会,形成科学合理的逻辑体系,理论界将不断返回这个学科理论的前提,并以此不断审视学科体系的逻辑发展。这样就可以在把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技术纳入自己的体系时,情报学体系的本质根据就不会因此而丧失,人们对情报学基础和核心问题的探讨也将不但不会淡化,而且仍将会得到加强。
可见,当代中国情报学通过基础和核心问题的关注,终将形成共识,率先在自身基础上建立情报学,并耸立起情报学大厦。
3 重视这一根本转折的启示
由于我国流行情报观点的总体思路曾经深深地受到了苏联的米哈伊洛夫、英国的布鲁克斯等情报学观点的影响。不是包括、而是局限在图书馆的文献知识中;不是把它作为情报对象源,而是把它作为系统的基础和核心;不是进行完全的系统研究,而是掐头去尾地远离产生情报和使用情报的环境和主体,从而使情报学研究在不短的时期内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因此,人们通过深入领悟情报学研究中基础和核心问题上的这个根本转折,首先将对情报的系统现象和情报的概念本质,从一个更为合理的角度获得全新的理解。以前把文献知识理解为情报学的前提,从而把研究的重心局限于对文献知识的检索和交流。而这在电脑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已不再时髦。在另一方面,更为确切的“信息”称谓取代由“文献”变异而来的“情报”称谓,正已成为不可逆反的事实和趋势。把包括文献知识在内的一切情报对象源,经过情报主体的改创形成主体情报,从而形成以社会实践主体情报需求为基础和核心的情报观将被广泛接受,进而改弦更张,完成图书馆情报学、或文献情报学、或知识情报学向用户主体情报学、或原型主体情报学、或社会实践主体情报学的根本转折,使当代中国的情报学研究出现新的转机。
第二,这样,人们对国家科委始自1992年把“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的深意,更能通彻领悟。原来的知识情报观完全是沿着信息技术的路径发展开去的,这种在信息的轨道上发展着的“情报学”,其实是把情报学异化成信息学了。人们也将豁然明白,在对“什么是情报”这个基本问题上的歧见进行切磋疏解和发展中,确实包含着产生中国情报学的契机。
第三,人们由于发现学科研究的最新突破,而将不再热衷于经院式的探讨和交锋,走上新路,改弦易辙,长入社会,进入公司,深入企业,提供参考决策的智力支持。关注当今变化了的社会生活,从社会实践主体的情报需要这个基点出发,开辟情报事业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