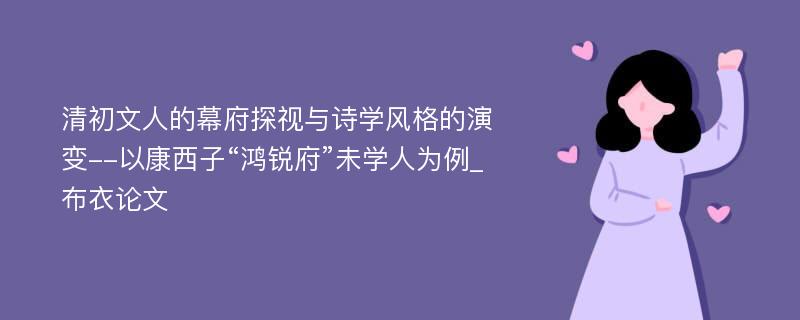
游幕与清初士人心态及诗风演变——以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布衣处士士人群为考察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诗风论文,鸿儒论文,处士论文,清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33(2012)03-0055-05
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为了笼络明遗民,康熙帝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科,令在京官员、在外督抚及学政推荐举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有无官职,是否秀才,一律到京考试。到康熙十八年三月,各地共举荐了一百九十多人,最终到体仁阁参加考试的共一百四十三人。这一百四十三人,经历不同,身份各异,按照博学鸿儒科前他们对清朝政权的态度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坚决辞试的故明遗民、游离于故国与新朝之间的布衣处士及业已在清取得功名的“新朝士人”三类。这其中,以博学鸿儒科“四大布衣”为代表的布衣处士士人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与遗民相比,他们并未在明朝入仕为官,不受儒家传统忠节观念的束缚,因此无需对前朝负有守节的责任。入清之后,虽主动放弃科举入仕的道路,但他们毕竟缺少持久的“忠君报国”、“不仕二姓”信念的支撑。另一方面,他们拒绝通过科举入仕,与以科举为依归的士子相比又缺少终极人生价值的追求。这样的特殊处境决定了,在清初“旧巢覆破、新枝难栖”[1](P5)的社会状况下,布衣处士士人群是典型的精神上失所无依、彷徨失落的一群。
布衣处士士人群,以被称为博学鸿儒科“四大布衣”的朱彝尊、潘耒、严绳孙、李因笃为主要代表,还包括孙枝蔚、邓汉仪等人。清初,布衣处士士人群与明遗民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心系天下,坚守气节,志图恢复,与清朝政权的关系上,则呈现出“疏离”的态势。这种“疏离”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身世、性格决定的。四布衣中,朱彝尊(1629-1709,字竹垞,号锡鬯,浙江秀水人)为明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朱国祚的曾孙,嗣父和叔父都是复社中人。受家庭成员和家族观念的影响,朱彝尊在甲申国亡之后,怀有深沉的亡国之痛,早年曾秘密参与过抗清斗争,有过一段“五陵结客”的生涯。严绳孙(1623-1702年,字荪友,号秋水,江苏无锡人)为明刑部侍郎严一鹏之孙,明亡后“弃诸生”,表现出不与清朝合作的姿态。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又字稼堂,江苏吴江人)的兄长潘檉章因“明史案”牵连被杀,严酷的文字狱致其家破人亡。家破后,潘耒曾师事徐枋、顾炎武等明遗民,义不仕清。李因笃(1631-1692,字子德,号天生,陕西富平人)于明亡后“弃诸生”,曾“走塞上,访求勇敢士,召集亡命,歼贼以报国”[2](卷一),虽未成功,却也是怀有忠君报国之志的。孙枝蔚(1620-1687,字豹人,号溉堂,陕西三原人)在明末曾组织勇士抗击李自成农民军,虽未与清朝发生过正面冲突,但其逃亡扬州几十年间不参加科举考试,专意读书著述,多与明遗民交往,亦是持守气节的一种形式。
可以说,明清易代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布衣处士士人群的思想、行为基本上是等同于明遗民的。与顾炎武、傅山等抱道守节、拒不仕清的明遗民不同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布衣处士士人群在顺治后期到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召开这一段时间里,大多处于奔波四方、为人作幕的生活状态中。
一、谋食四方——清初布衣处士士人群的游幕经历
清初士人游幕的初衷,大多为“谋食”的无奈之举。封建社会的士人,手无缚鸡之力,不务农,不经商,失去了科举入仕这条道路,只能靠“依人”来维持生存,而“依人”的途径,则或处馆,或游幕。己未博学鸿儒科“四大布衣”皆有过游幕经历,朱彝尊是清初游幕时间较长、范围最广、入幕次数较多的士人,他的游幕经历在布衣处士士人群中颇具代表性。顺治十三年,朱彝尊结束了“五陵结客”的生涯,做客岭南,为广东高要县知县杨雍建子塾师。顺治十七年,经曹溶推荐,客山阴宋琬幕。康熙元年底,因“通海案”发,往浙南避祸,于永嘉县令王世显署中做记室。此后的十余年间,朱彝尊又先后在山西按察副使曹溶、山西左布政司王显祚、山东巡抚刘芳躅、潞河通永道佥事龚佳育等处为幕宾直至康熙十七年入京应诏博学鸿儒科。游幕期间,为生计存,甚至于一年数易主。就算遗民情结比较浓厚的李因笃也曾游雁平兵备道陈上年(?-1677,字祺公,直隶清苑人)之幕,为其课馆教子,追随左右达八九年之久。康熙六年,陈上年裁缺归里,失去生活来源的李因笃又游富平县令郭传芳(郭九芝)之幕,时间长达七年。客居扬州的孙枝蔚也常年以游幕为生,“豹人年五十,浮客扬州,若妻妾、子女、奴婢之待主人开口而食者且三百指。世既不重文字,身又不能力耕田以自养。长年刺促乞食于江湖。”[3](魏禧《溉堂续集序》)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子,即便再穷困潦倒,也是不屑于躬耕自养的,而卖文售画又不能持久稳定的为士人提供生存所需资源,而游幕所得基本可以养家糊口,而且与“游客”相比,“入幕虽卑,犹自食其力。”[4](卷三《复顾先生》)但对拒绝科举出仕的布衣处士来讲,游幕乞援不失为维持生存的权宜之计。
“有负悬弧射四方,依人但愿主人强。归逢邓禹贤苗裔,羞说艰难已备尝”[3](《次韵答邓孝威》其二)。在封建士人看来,游幕是有失儒道尊严的降志辱身之举。“食贫居约而获游于贵要之门,常人之情鲜不愿者”[5](《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P166)。虽然与务农、经商相比,游幕作为生存手段是布衣处士的上佳选择,但游幕与顶天立地的“修齐治平”是有天壤之别的。为人作幕、代人歌哭的屈辱感一直困扰着游幕士人。朱彝尊说,“仆频年以来,驰逐万里,历游贵人之幕,岂非饥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己降矣,尚得谓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娱,岂非其道义不敢出;今则徇人之指,为之唯恐不疾。”[6](卷三十一《报周青士书》)孙枝蔚也感慨游幕为“穷途”,“改服游江皋,适戎学老子。穷途将安之,乞食焉知耻。平生尚耿介,为儒昧生理。……君非孟尝君,我岂门下士。口腹累安邑,惭叹何时已?”[3](《发扬州至京口》前集卷二P127)何况,游幕虽不算出仕,但也不再是为明朝守节尽忠。而常年游历在外,又无法对父母尽孝。为人作幕可谓“不隐不仕”,不忠不孝。潘耒在参加鸿博特科前,曾游京师柯都谏家,当时柯的同乡郑文谷以潘耒夙有高尚名,有诗句“夷齐陆续到皇畿,日向朱门乞蕨薇”[7](卷四《燕觚·诮郑》)嘲笑潘耒,可见时人对“不隐不仕”的游幕者的态度。至于游幕造成的“不孝”,李因笃痛心疾首,倍感屈辱:“男儿有去就,大义浮乾坤。焉能弃所好,浪迹如穷猿。况我白发母,倚闾朝复昏。数緍不救饿,衔恤鞠诸孙”[8](卷十五《喜子祯先生至武昌叙旧述怀四百字》)。况且,游幕虽然暂时缓解了布衣处士们的经济压力,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诗人穷困不堪的生存状况。“偶效古人尝自愧,频从道路叹流年。杜陵老作诸侯客,彭泽饥知漂母贤。病妇寄书愁药饵,娇儿见父问山川。归来破屋烦修葺,从此埋头理旧编”[3](卷七《归来》),“囊中羞涩还如故,赢得霜华上鬓须”,游幕实在是“穷途末路”,是士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径。
二、“诗必游而后工”——游幕对布衣处士士人群诗词创作的影响
“诗穷而后工”,游幕带给诗人“穷途末路”的感觉,反而有助于诗人诗歌的创作。游幕士人“蓄其所有而未得施于行事,因舟车所更涉,历揽山川之雄秀,城阙之壮丽,人物之英伟,故迹之苍凉,感其郁积,往往形诸歌咏,以写伤今怀古、思亲念旧、嗟老叹卑之意。性灵所寓,墨光照耀,洵非桅言蜡貌而为欢娱之词者所可及也。”[9](卷六《燕游草序》)游幕开阔了诗人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阅历,也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源头之水。王泽弘为《溉堂集》作序,阐述了奔走四方、乞食游幕对孙枝蔚诗歌的影响,“嗟乎,先生秦人也,寄居广陵,穷老无归以谋生,不暇日奔走于燕、赵、鲁、魏、吴、越、楚、豫之郊。其所阅历山川险阻,风土变异及交友世情向背厚薄之故,皆一一发之于诗以鸣不平而舒拂郁。”[3](《溉堂后集·王泽弘序》)有多次入幕经历的清初学者陆元辅曾言:“诗必游而后工,必穷者之游而后尤工。”“穷者之游”激发了诗人的“不平之气”,促使他们创作出了更为深沉和饱含真情的诗歌。反过来,游幕士人创作出来的诗歌又成为“怨”的载体,承载了作者的哀怨悲苦,成为发泄舒郁的途径。
诗风与诗人的人生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游幕还造就了诗人“悲歌总挟清霜气,掘笔都无典丽风”[10](卷三《写怀十首》P202),悲愤慷慨与凄怨哀婉并存的诗歌风貌。这种“清霜气”多通过清冷色调的意象,如冷月、孤城、荒烟、雨雪等来表达和渲染。康熙四年,朱彝尊与其幕主曹溶同游雁门关,作《滹沱河》:“滹沱河上流澌急,骑马春冰滑可怜。百尺浮桥空断板,孤城哀角动荒烟。愁颜送老饥寒日,绝塞因人雨雪边。转忆江乡多乐事,花浓齐放五湖船。”[6](卷六P465)春冰、孤城、哀角、荒烟、雨雪等意象无不昭示着作者因游幕乞食和思乡怀人所生发的孤冷愁苦之情。过滹沱河之前,竹垞作有《晚次崞县》一首曰:“百战楼烦地,三春尚朔风。雪飞寒食后,城闭夕阳中。行役身将老,艰难岁不同。流移嗟雁户,生计各西东。”[6](卷六P465)诗歌描述了春寒料峭时节崞县黄昏的苍凉清冷,诗人身处此境,感慨孤老穷愁,无比心酸伤感。严绳孙游蓟北途中所作《天津》诗云:“潦倒江湖中酒频,又携长铗向天津。神臯木落关河在,列戌霜高鼓角新。安往不成悲白发,至今犹自恨黄巾。秋风一夜相吹急,失路何人念景真。”[11](卷四)诗歌运用了落叶、关河、秋霜、秋风意象,表达了作者的失所无依、清苦孤伶之感。
“感物咏怀常与悲慨人生苦短、不得尽欢的嗟怨相结合,伤春悲秋不仅仅是对自然变化的伤感,更多的是寄寓了诗人们观物反思,对社会人生的广泛思考。”[12](P46)“悲秋”本就是封建文人常有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在游幕为生,“不隐不仕”的布衣处士身上则表现地更为深刻。严绳孙将其诗集命名为《秋水集》,其诗作中的“秋”字触手可及,比比皆是。“满山芳草寻不得,未曾风雨亦零秋”(《梧桐园》),“鸟啼何处不胜秋”(《燕台杂诗》),“老僧莫问悲秋意,今古西山下夕阳”(《寓敬业寺》),“弯弓羽林子,驻马早惊秋”(《刘富川诗》)等等。《秋日杂感》则记载了作者在万物凋零的秋季的穷愁之感,“秣陵宫阙旧神州,桃叶听歌记昔游。紫禁月沈琼树夕,沧江枫冷石城秋。天门无复交仙仗,海气真成结蜃楼。总是兴亡千古地,莫教潮汐送闲愁。”[11](卷一P531)身处明太祖的兴起之地南京,秋月、冷枫、沧江、夕阳等凄冷景物浸染着作者的愁绪,千古兴亡,悲从中来。李因笃诗作中也频频出现“秋月”、“秋风”等意象。“中秋无寐独沉吟,百感蹉跎已至今。……白云频寓秋来目,香草还怜岁暮心。”[8](卷九《河曲中秋待月二首》P13)“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孤独无依、嗟老叹卑的心境在中秋佳节之际更为沉郁浓烈。“余愁何所为,落涕倚双扉。万里暮云影,千家秋月辉。时犹多战伐,客欲早旋归。不必玉关外,临风俱揽衣。”[8](卷五《闻砧》P494)秋夜闻砧,临风揽衣,时光流转、事业无成的伤感郁结于诗作之中,思亲盼归之情在暮云和秋月的笼罩之下萦绕心头,久久难消。士人广泛游幕时期的诗歌创作与顺治初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顺治初年,诗作内容多为表达家国之思,关注民族兴亡的悲愤慷慨之音。士人游幕时期的诗作则多为关注个人际遇的嗟老叹卑之作,风格也少了焦杀之音,多了几分清婉之气。
虽说游幕在士人看来是一种降身辱志之举,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士人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生活保障和相对安定的读书著述的环境,游幕期间,很多士人在文学和学术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雁门游幕数年,李因笃“益发愤读六经及关闽诸大儒书。所著诗文高古深邃,名播海内,一时骚人词客,趋之若鹜,至邸舍不能容。”[13](P416)这一时期,李因笃结交了顾炎武、傅山、李顒、王弘撰等大儒,砥砺气节,酬唱往来,交情甚笃。李因笃的学术成就和诗文创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广泛的交游更是使其名播四海。朱彝尊的文学成就亦与他的游幕经历息息相关,游幕对其学术交游和文学创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少日不喜作词,中年始为之”[6](卷五十三《书东田词卷后》)。朱彝尊作词是在曹溶幕中受其影响开始的。康熙三年秋,朱彝尊至山西大同,入曹溶幕为幕宾。游幕期间与曹溶相唱和,之后竹垞作词日渐多起来。曹溶崇尚醇雅的词学理论对朱彝尊影响很深,他进行《词综》的编选也与曹溶相关甚密。朱彝尊曾称:“余壮日从先生(谓曹溶)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登池,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有井水处,辄为银筝、檀板所歌。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禩,词学失传,先生搜辑遗集,余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14]可见,浙西词派的领袖为朱彝尊,而其渊源所自则出于曹溶。除了曹溶,朱彝尊游幕京师之时,与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陈维崧、曹尔堪、曹贞吉、顾贞观等人相识相知,谈艺论词,思想碰撞融汇,对其词学创作及词学理论的形成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从游幕到“立功”、“立言”——布衣处士士人群身份及心态的变迁
游清朝官吏之幕,已经间接参与到清朝政权体系之中,改变了布衣处士们的身份,使其成为“不隐不仕”的政治边缘人。游幕士人身在官府,耳濡目染,与清代权力执行者近距离接触,甚至为幕主佐理政事,使他们对现实的认识更加清楚。这对于他们转变思想,出仕清朝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布衣处士士人群对清朝政权早已持默认的态度。毕竟,到康熙十七年,离“甲申国变”已经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老百姓只要能安居乐业,对谁主宰国家政权并不非常在意。而封建士人,只要能在政权体系中实现人生价值,也就抛却了所谓的“夷夏大防”,接受了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自视为社会精英的布衣处士士人群,单靠为人作幕、代人歌哭已不能满足他们的抱负和追求,只有通过出仕才能实现“立功”、“立言”的愿望。但到康熙年间,朱彝尊、李因笃、孙枝蔚等人身负处士清名多年,即便是有心摆脱游幕为生的尴尬处境,也已经不便出山应试。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的几率是很低的。一旦落第,被人耻笑不说,一世处士清名也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为布衣处士改变现实处境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博学鸿儒科是在征召“山林隐逸”的口号下进行的,布衣处士在“被征”而非“自愿应征”的掩饰下,追求“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明遗民一样,被征博学鸿儒科之初,布衣处士士人群是怀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的。虽然有游幕的经历,但布衣处士士人多年不受官场束缚和羁绊,野性未驯。而且,他们珍视持守多年的处士清誉,一旦应试,三十年来积累的声名和威望一朝之间付之东流。再有,“试而兼黜,为不知者所姗笑”[15](卷四《严中允传》),怕考不中被人嘲笑。尽管如此,在抛却“夷夏大防”的情况下,封建士人不但要“谋食”,还要“谋道”、“修齐治平”。因此,布衣处士对“出”还是心痒的。朱彝尊在博学鸿儒科之前已有“出”的心思。邓之诚谓其:“论者惜其轻于一出,终伤铩羽。然观其所作《吊李陵文》,早已决心自献矣。”[16](卷七丙编P747)与朱彝尊同时代的屈大均也讽刺朱彝尊早有归附之心曰:“鸳湖朱十嗟同汝,未嫁堂前已目成”[17](卷七《赋寄富平李子》)。对“出”怀有较大热情的不仅有朱彝尊,连年事较高者如孙枝蔚得知被举荐之后也是喜形于色。杜濬《与孙豹人书》描述当时的情景曰:“乃数日以来,人言藉藉,至谓豹人喜动颜色,脂车秣马,惟恐后时。”[18](卷四)虽然杜濬“毋作两截人”、“思痛以忍痒”的告诫代表了遗民社会给予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在“出”已经成为主流的社会潮流下,已经显得微不足道。
博学鸿儒科考试后,孙枝蔚、邓汉仪以年老特授内阁中书舍人放归。李因笃、朱彝尊位列一等,潘耒、严绳孙位列二等。李因笃以“母老”为由上书三十七次求归,放归之时作诗云:“帝性孝而仁,深宫照无忒。怀归悯小臣,念母情凄恻。诘旦沛殊恩,还山忽已得”[8](卷二十二《留别吴侍讲卧山》),以“小臣”自居,对康熙帝感恩戴德,全无昔日之傲骨。而简傲如严绳孙,博学鸿儒科前后简直判若两人,“藕渔先生初以不完卷为欲全高节,逮即以破格见收,则感恩知己,不啻若是其口出矣。”[19](《己未词科录外录》P505)朱彝尊、潘耒等人的行径自不待说,“献赋承明,校书天禄,文避北山之移,径夸终南之捷。甚至轺车秉节,朵殿承恩”[20](刘师培《书曝书亭集后》转引自《清诗纪事·康熙朝》P2708),任职翰林院,担任修史官,自觉承担起了为“圣朝”鼓吹修明的任务。博学鸿儒科后,诗歌创作主体缙绅化,诗风也朝着鼓吹盛世、黼黻太平的清雅醇厚之音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