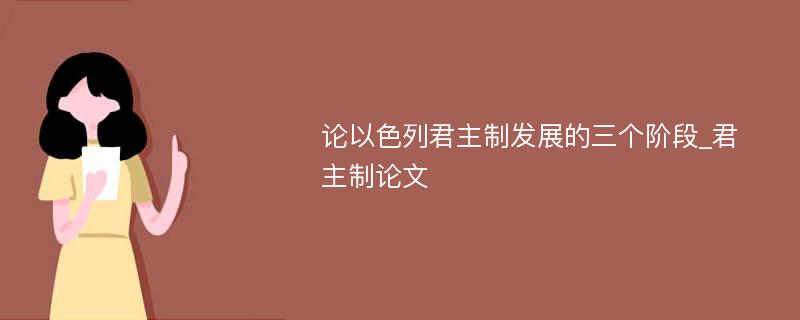
论以色列君主制发展的三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色列论文,君主制论文,三个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古代以色列民族历史的研究相对薄弱,近年来虽出现一些介绍犹太文化的著作和文章,亦多少触及以色列君主制及其产生前后的历史,但明显缺乏集中深入的论述和史学意义上的考辨,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认识。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对古代以色列君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特点认识不清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本文的目的即是想就此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方家。(注:本文所引《圣经》资料采用我国学术界通用的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译本,个别引文参照马索拉文本希伯来文《圣经》(M.T.Printed by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92)。经文章节出处按通用缩写形式在文中标出,所代表的各卷书名如下:创:《创世纪》、出:《出埃及记》、利:《利未记》、民:《民数记》、申:《申命记》、书:《约书亚记》、士:《士师记》、得:《路得记》、撒上:《撒母尔记上》、撒下:《撒母尔记下》、王上:《列王纪上》、王下:《列王纪下》、代上:《历代志下》、代下:《历代志下》、诗:《诗篇》,不再一一注出。必须说明的是,希伯来《圣经》并不单纯只是一部宗教经典,它亦是研究古代以色列民族史最重要的文献。)
古代以色列民族在伽南(今之巴勒斯坦)建立君主制王权统治始于公元前11世纪末,终于公元前586年。 西方学术界把这段历史分为“统一王国时期”和“分国时期”两个阶段。根据一般推算,以色列的第一王扫罗称王是在公元前1028年(注:另一说为1020年,本文不敢此说。),至第三王所罗门统治末年的公元前933年为以色列统一王国时期,共约98年。分国时期的北方以色列王国从耶罗波安一世(933—912BC)始至亚述王撒尔贡攻陷撒玛利亚时的末王何细亚(733—722BC )止,历19王凡212年。南部犹大王国自罗波安(933—917BC )始至耶路撒冷陷落时的末王西底家(597—586BC)止,历20王凡298年。 从君主制形态与王权特征等内在根据上分析的话,这一历史过程也可分为三个阶段:氏族部落制遗风大量保留的扫罗王朝阶段;君主制走向集权的大卫——所罗门王朝阶段;秉承不同君主制传统的南北分国阶段。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以色列民族因早年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经历,形成了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文化传统,即妥拉(注:妥拉(Torah,意为“律法”,音译作“妥拉”)是希伯来《圣经》三部分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即所谓“摩西五经”,指希伯来《圣经》的头五卷书。另两部分为“先知(书)”(Navim)和“文集”(Kotvim)。三者以首字母缩写为TNK,读音为“塔纳赫”(K在词尾变清辅音),即为犹太人对希伯来《圣经》的称谓。犹太教后来也用“妥拉”一词指称整部经书,本文取其狭义。妥拉最后编定约在公元前5世纪,此前长期在民众中口耳相传, 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丰富完备起来的,但其中的某些部分则有相当古老的根源。)律法传统,其君主制的产生和发展特点是建筑在这一既定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之上的。
一、从王权产生到君主制的初步确立——扫罗王朝(1028—1013BC)
在王权出现前的士师时代,以色列是个松散的氏族联盟,各支派(氏族)各自为政,甚至兄弟阋墙,相互残杀。面对周围异族、特别是非利士丁人咄咄逼人的进攻,以色列人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情况最危急的时候,竟连约柜(注:约柜(Aron ha-Berit):犹太教圣物, 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特殊关系的象征。)都被敌人掠去(撒上·4:1—11 )。正是因社会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因为抵抗异族侵袭的迫切情势的需要,以色列王权应运而生。《圣经》中记载了以色列人立扫罗为王的过程:“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尔(注:撒母尔是士师时代末期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和士师,地位高过《士师记》中的其他12位单纯作为军事首领的士师。),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上·8:4—5)。于是撒母尔以耶和华神的名义膏立扫罗为王(撒上·9:15—17)。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经》的另一处记载中,寻求立王的行为又被视为对神不够诚信的表现(撒上·8:7)。 以色列人亦对此诚惶诚恐:“众民对撒母尔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上帝,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求立王的事,乃是罪上加罪了”(撒上·12:19)。 这看似歧义的记载是以色列民族在社会进程的转折关头对是坚持传统的氏族部落民主制还是接受君主制两种不同思想的激烈交锋的反映。由此可见,扫罗称王实是大敌当前一种别无选择的结果,是在否定权力垄断的氏族氏主观念与现实对王权的需要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登上王位的扫罗,其王权必然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扫罗登基时年40岁,在位约15年。纵观这十余年的历程,可以看出扫罗只是初步奠定了君主制的基础,他虽然拥有王的称号,但实际上距一位享有充分权力的国王的标准还差得很远。
1.扫罗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率军征战方面。以色列人立王的原因首先是军事上的:“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上·8:19)。扫罗作王的主要功绩也是军事上的,他南征北战,抵御四邻之敌,最终战死沙场。
2.扫罗保留着士师时代注重氏族本家的习惯和士师作战的特点。以色列立国是在吉甲(撒上·11:14), 该城位于玛拿西支派的境内西部,但出身于便雅悯支派的扫罗却不愿将此城作为真正的首都,而将其常驻之地设在便雅悯地北部与以法莲地交界处的密抹和伯特利山,有时也住在便雅悯地境内的基比亚,扫罗王朝根本没有固定的设防都城。在军事上他只有常备军三千人,每逢战事均需临时召集百姓(撒上·17:25)。
3.扫罗的政权机构不完善,除元帅押尼珥、长子约拿单外,未见司职其他工作的重要官吏,而且这两人也均为军事首领。
4.氏族部落民主制的权力基础未被触动,民意仍不可违。扫罗欲降罪于约拿单,百姓却口气强硬地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作事”(撒上·14:45)。
5.王权受到神权的极大限制,撒母尔常借神的名义对扫罗发号施令。与亚玛力人一战,扫罗未完全听从撒母尔的指示,后者竟“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撒上·15:35), 这等于撤消了对扫罗王权合法性的支持。正是撒母尔在扫罗仍在位的情况下,又膏立大卫为王,形成奇特的双王并存的局面。
6.扫罗无力解决王位继承权问题。不是他不想把王位传给儿子,他千方百计要剿灭大卫,个中缘由对约拿单说得再清楚不过:“耶西的儿子(大卫)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撒上·20:31),而是以色列人不接受王族血统神圣的观念。扫罗战死后,其子伊施波设在位仅两年即被两个军长利甲、巴拿所杀(撒下·4:5—7)。
总括上述各点可以看出,扫罗时代的以色列君主制还保留有大量氏族部落制的残余,王权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扫罗王实际上是一个拥有王号的统一国家的大士师的角色。以色列在扫罗的君主制下,不过是将各支派以国家的名义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权力结构并未发生质的变化。扫罗时代君主制的这一特点,与以色列进入君主制前已形成的妥拉律法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希伯来——以色列人在由氏族、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从美索不达米亚接受了契约观念,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改造、推演为人与神的契约关系,即所谓“圣约”。与神立约的记载存在于这个民族早期发展的各个阶段。族长时代,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出埃及时期,摩西在西奈与神立约,西奈立约被视作以色列民族真正形成的开端,以色列独特的民族性至此展露而出。约书亚完成对伽南的征服后,率众在示剑与神立约(书·24:25—26)。 与神所立的约以最初的律法形式在得地定居的以色列人中固定下来,如西奈立约便形成了以“摩西十诫”为核心的律法。在“十诫”之外,《出埃及记》的第21—23章被认为是妥拉律法中最早出现的部分,即所谓“约书”(The Book of the Covenant),除23章20节以下部分是神再次应许以色列民进占伽南的内容外,“约书”的律例显示出的是以色列定居初期的社会特征,可见在以色列进入君主制社会前,就已有了约定俗成、为各支派(氏族)所接受的律法。一个民族的法律观念与其所处的社会阶段应是一致的。实行军事民主制的以色列人,其律法也必然具有民主化的色彩。在《民数记》中载有两个颇具说服力的事件,它们表明了在以色列民族形成过程中对权力垄断的否定性观点。其一是可拉一党对摩西和亚伦权威的挑战。这是一场“以色列会中二百五十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起而反抗摩西、亚伦专权的举动,其理由是“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民·16:1—3); 其二是摩西本人否定了由七十个长老垄断发预言的记载(民·11:24—29)。按《圣经 》学界普遍接受的“五经底本说”理论(注:“五经底本学说”是一种将文学考据(Literary Criticism),即对文献进行语言、文体风格等方面的考辨,与历史分析相结合,从而辨析“五经”中不同章节的资料来源,最终确立“五经”构成的理论。它认为“五经”是由以“耶和华”(Jehovah)为神名的第一种底本、以“神(上帝)” (希伯来文作Elohim)为神名的第二种底本、以《申命记》(Deuteronomy )为代表的第三种底本和内容注重描写献祭仪轨、家谱世系,风格带有祭司(Priest)体特征的第四种底本结合而成,简称为“JEDP四底本说”。),这两个故事均属J底本(注:J底本为四底本中最先完成的一种,为分国时期犹大史家所撰的历史书卷,约完成于公元前9世纪中叶,不像D、P 二底本集中反映祭司阶层的观点。),资料来源相同,发生的历史时期一致,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应有较强的可靠性。它们不仅对早期律法关于权力的认识作了注脚,而且作为口传历史的一部分后来被记入妥拉,其自身亦有了律法传统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在氏族部落时期的认识方式和认识水平上,以色列人对律法产生的认识并不准确,在他们看来律法不是这个民族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的,而是由神所“启示”的:这“启示”不是针对民族领袖(包括后来的“王”)或一小撮特权阶级,而是针对整个民族的。在这一特殊的契约中,立约双方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神是立法者,人是遵行者,恪守律法将蒙神保佑和祝福,违背律法破坏契约则将受到神的惩罚。契约所带有的强制性色彩,决定了妥拉传统在以色列民族进入君主制时代后仍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与上古时期许多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妥拉传统中内含两个独特的观念。其一:我们可称之为“世俗之民与世俗之王”的原则。希伯来—以色列人不曾将民族的根源与神的神圣血统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民族留下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中,很少能找到民族优越的内容,相反,他们倒是常常表明自己卑微的地位,把成为“上帝的选民”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所谓“神的恩典”。这一原则在以色列人与神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就不会去神化自己的领袖或王——他们不是神的儿子或后裔,如自称拉神和阿蒙神之子的埃及法老或“天子”的中国帝王,甚至也不是道德上完美的圣徒,而只是具备尘世之人一切弱点的凡夫俗子。不独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诸士师是如此,以色列进入君主制时期后的诸王也是如此。其二可称之为“民族之约”的律法思想。《撒母尔记·上》10章25节载,当撒母尔立扫罗为王时,“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这“国法”(注:“国法”, 希伯来文作Mishpatha-Meluchah,直译应为“(神对)王国的审断”,其意在强调有关律例的不可更改。)的内容是自摩西时代传承下来的律法。实行军事民主制的以色列人,其契约观念必然也是以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民主思想为基础的,作为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全民族的领袖,摩西确立的律法传统正折射出了这一观念。我们不妨作一个小小的比较。同样是颁布法律,《汉谟拉比法典》的“导言”部分充斥了汉谟拉比王的自我夸耀,并明确指出:“当马尔都克命我统治万民并使国家获得福祉之时,使我公道与正义流传国境,并为人民造福。自今而后:……”(注:《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74年重印版,第62页。),其逻辑是蒙神赐王权,我颁布如下法律。而妥拉律法简短的开场白却是:“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出·20:1)或“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出·25:1)因此所谓Torat Mosheh——“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人看来实际上是耶和华的律法,百姓从根本上说是对神而非对摩西负责。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是否恪守律法是神评判人的唯一标准,无论他是首领——王、祭司、还是普通百姓。妥拉律法传统将宗教祭祀权与军事统率权、民事裁判权分开,使得未来的以色列民族诸王不可能将神权与王权集于一身,成为哈里发式的绝对集权的君主;又将所谓“受神感动发预言”的权利赋予了每一个会众(注:以色列历史上的“先知”多为各阶层的普通百姓,而非出自祭司阶层。),同时剥夺了祭司集团(包括作祭司的亚伦及其子孙和作圣幕之工的利未人)的经济基础(注:按妥拉律法,亚伦一脉和利未支派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其日常所需由其他支派按所出的十分之一供奉(民·18:20、23—24)。史载以色列人征服伽南后,只11个支派分地, 利未支派散布于各支派中,所得仅是居住和生活的几座城邑。),这就避免了神职集团辖制百姓,或出现美索不达米亚那种神庙经济势力强大辖制世俗统治权的局面。由此可见,妥拉传统否定绝对的专制集权,作为现实局面与妥拉律法传统妥协而产生的以色列第一王扫罗,其王权受到限制,王朝只是初具君主制的特点实属必然。
二、走向集权的君主制——大卫—所罗门王朝(1013—933BC)
君主制真正作为国家政体被接受和确立始于大卫统治时期(1013—973BC),大卫是个能够审时度势的成功的政治家。 与扫罗称王的过程不同,尽管有撒母尔膏立的记载,大卫主要是通过自己军事上的成功,以强力登上王位的,它实际上经历了从与北部的扫罗对峙到统一南北以色列全地、迫使北方各支派承认他的统治地位的曲折过程。大卫彻底根绝了以色列的外患,而且将扫罗时期的以色列版图扩大了三倍,使以色列一跃成为西亚的地区性大国,这是他能够对内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强化王权的基础。在大卫王朝,君主制的优越性才开始真正体现出来。古老的传统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
大卫30岁登基,在位40年,在统一以色列全境后,除晚年因姑息三子押沙龙导致其掀起一场几乎危及自己王位和性命的大叛乱外,他采取的各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而且均带有集权化的色彩。
1.定都耶路撒冷,使之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扫罗时代以色列没有真正的首都,政令不畅。大卫统一全国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攻取耶路撒冷,将王国政权机构设立于此,并拓展和加固城防,提高它在全国的地位,使政令集中(注:大卫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举措颇具匠心。此城本为耶布斯人之地,以色列人征服伽南时未能攻陷,成为以色列境中一块异族人的飞地。该城为一座山城,位于犹大山地北部中央,城东隔汲沦溪与橄榄山相望,城南和西南则有欣嫩子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南扼通往犹大山地的主要贸易通道,北出以法莲山地与北方各支派相接,战略、交通和经济地位均十分重要。另因该城本不属以色列任何一个支派,不易引发争地矛盾;而它又处在犹大地内,使出自犹大支派的大卫处于对内对外均十分有利的地位。)。
2.迎“约柜”入耶路撒冷(注:约柜自撒母尔时代起一直在以法莲地的基列耶琳。),建立全国性宗教中心。此举一是为加强全国的凝聚力,二是为避免宗教中心与政治中心争权的局面出现。
3.设立百官,健全政府机构。在征服之地委派国家官吏,同时给诸王子以特权,增强王室家族的势力。
4.控制宗教管理权。大卫设祭司长职位,但又将祭司长列于廷臣之内,实际上等于置教权于王权之下。心思绵密的大卫立撒督和亚比亚他(亚西米勒)两人同为祭司长,以使他们相互制衡,不致坐大(撒下·8:16—18、20:23—26,王上·2:27 )(注:关于祭司长的记载在不同章节略有出入。除《撒下》8:17记撒督与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同作祭司长外,《撒下》20:25和《王上》2:27均作撒督与亚比亚他同为祭司长。以色列的传统是祭司职位世代相传,亚西米勒子承父职从理论上讲是有根据的,但既然所罗门登基时亚比亚他仍为祭司长,亚西米勒在大卫王朝就不可能已是祭司长。《撒下》8章和20 章出现两个大同小异的大卫诸臣职官表,故两处祭司长人选的差异基本可断定为因两种不同资料来源所致。又,大卫以两祭司长相互牵制的策略是有效的,撒督与亚比亚他的矛盾在拥立不同的王位继承人的斗争中暴露无疑。)。
5.强化军事机器。大卫王朝的国家常备军的确切数字虽无记载,但无疑颇具规模,而且训练有素,因为元帅以下尚有“众军长”统领军队(撒下·24:4),且每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军队常常出征(撒下·11:1),鲜有败绩。这支军队成为大卫对外开疆拓土,对内施行集权化统治的有力保障。
6.以谋略清除隐患,安抚北方支派。扫罗王出自北方支派,死后影响犹存。大卫对已构不成威胁的扫罗之孙、约拿单的残废儿子米菲波设施以恩惠,令其住在首都,与王“同席吃饭”(撒下·9:7); 却借基遍人之手将扫罗的另两个儿子、五个外孙尽数除灭(撒下·21:1—9 )。
7.确立王位继承原则,将王权顺利地传给儿子所罗门。
以上几个方面充分反映出,大卫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扫罗王朝时强大的氏族势力遭到有效的抑制,祭司阶层的权力被架空,王权成为凌驾于氏族权力之上的国家意志的代表,一种具有集权化特征的君主制度终于产生。
大卫强化王权的政策为所罗门(973—933BC)所继承,这位在以色列历史上以智慧著称的国王,书写了以色列王国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但也为君主制的由盛而衰埋下了种子。
所罗门初登王位之时,根基并不牢固。王族内部有得到元帅约押和祭司长亚比亚他等人支持的异母兄长亚多尼雅觊觎王位,地方上宗族势力则有抬头的倾向。为了巩固统治基础,所罗门王毫不手软。以亚多尼雅谋求曾侍奉大卫王的亚比煞为妻作借口诛杀亚多尼雅(王上·2:25);按先王密诏将老帅约押杀于圣幕之内(王上·2:31—34),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扫罗一族的长老示每(王上·2:39—46);废亚比亚他的祭司长之职(王上·2:25);王位既固,所罗门开始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对地方的控制。他将全国划分为12个行政区,由朝廷直接任命政府官吏、而不是委派氏族长老施行管理,保证国家收取足够的赋税(王上·4:7);在全国建基色、夏琐、米吉多等六座防城, 又在各地营造积货城、军马和战车储备地(王上·9:17—19)(注:所罗门王在米吉多建要塞城防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 参The Glory
of The OldTestament,p.135,ed.by Georgette Corcos,Atomium Books Inc.U.,S.A.1990.);拓展首都属地,扩展耶路撒冷城墙,在城中建起庄严的圣殿和富丽堂皇的王宫建筑群(王上·6、9:17—19、代下·3)。
所罗门内政外交上的政绩带来了后世以色列人念念不忘的“黄金时代”(注:史载所罗门王朝时期经济、文化发达,国富民强,国际地位提高。以色列发展起金属冶炼和航海业,船队依托以旬迦别港(今之伊拉特港),入红海和地中海,甚至远达非洲和俄斐(此地具体指何处不明,一说是印度)进行贸易;示巴女王率大批官员来觐;多国敬献贡物。另,所罗门王的辖地亦扩展到叙利亚之北。),他为巩固王权所采取的某些政策,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产生了双重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他秉承大卫的遗愿建起圣殿,(注:又称“第一圣殿”,以区别于回归后所建的“第二圣殿”和大希律所建的“第三圣殿”。)巩固了耶路撒冷的圣城地位,进一步凝聚了全民族的向心力,这不独在当时有利于王权的巩固,约九百年后,当这个民族最终开始开始向世界各地流散时,对“圣城”的回忆和向往长久地保存在犹太人的意识中,耶路撒冷成为民族家园和民族信仰的象征。圣殿的宗教权威逐渐造就出了在社会生活中作用日益明显的、以大祭司为首依附于圣殿的祭司贵族阶层,同时也为他们的没落、为日后宗教生活的转型埋下了伏笔。(注:公元70年,当“第三圣殿”最终毁于罗马人之手时,以主持献祭仪礼为业的祭司集团失去了对民众精神生活的控制特权,犹太人的宗教生活由此进入“拉比犹太教”时期。)另一方面所罗门王废亚比亚他祭司长职位,专立撒督为大祭司,以及他宠爱“外邦女子”的行为(王上·11),从长远观之则对民族凝聚力产生了不利后果。所罗门娶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又广立摩押、亚扪、以东、西顿、赫人女子为妃嫔,她们将各自民族的宗教信仰带入耶路撒冷;所罗门甚至同意“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扪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王上·11:7)。显然,作为政治家的所罗门无论是与埃及和亲,还是立征服地的公主们为妃,都是出于统治国家的需要,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外交策略,但客观上带来信仰的驳杂。撒督与亚比亚他本代表不同的祭司系统,撒督一派具有宗教调和主义倾向,亚比亚他一派则强调耶和华信仰的独一性。后者见逐的结果,遂使异教信仰、风俗在以色列流行,其恶果在分国时期的民族历史上得到突出的体现。
较之扫罗王朝,大卫、所罗门两代国王对君主制进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革新,以色列君主制的形态和内涵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的权力集中到了王的手中,对王负责的国家官吏取代了对宗族负责的地方领袖。如果说大卫时代还能多少看到对氏族长老权力的尊重的话,到了所罗门时期他们的活动已较少见诸于史了。在这一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过程中,权力结构的改变使弱小的以色列民族迸发出巨大的活力,成为国富民强的地区性大国。但我们必须看到,大卫和所罗门的集权化君主制的建立和强化,只是相对而言的,否定权力垄断的律法传统虽遭到无情的破坏,但“圣约”观念却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理论上和人们的意识中,王所拥有的权力仍然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宽容,王的行为的好坏要以神所体现出的绝对的“公义”为标准。因此王的权力的合理性是不断受到质疑的(注:“公义”,希伯来文作tsedek,意为“正”、“适当”,按妥拉精神,完全依律法要求行事方为“公义”。),不存在“君王无谬”的理论(注:如《撒下》12:7—14载,大卫与拔示巴私通并以阴谋手段杀害其夫乌利亚,大卫的廷臣拿单无畏地以神的名义对他宣示了“判决”。又,绝对权力属神之思想,亦反映在如下的诗句中:“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记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诗·103:17—19);“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127:1)。这两首诗的作者, 传统上分别被归于大卫和所罗门,但无法得到确证。然就诗的内容分析,产生时间在大卫、所罗门时期应无问题。)。这与同时期埃及法老的集权君主模式显然有别。
三、分国时期两种不同的君主制类型(北国:933—722BC;南国933—586BC)
所罗门王崩,其子罗波安继位,统一的以色列王国迅速分裂为南北两国。统一王国分裂的导火索是政治上不成熟的罗波安企图以威权压服北部百姓(王上·12:4),另外早在统一王国时期,大卫、所罗门实行偏袒南方的政策,使犹大和北部诸支派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都是造成分国的原因。分裂后,南国犹大仍都耶路撒冷;北国以色列经数迁都城最后定都撒玛利亚。分国后的以色列和犹大两国虽都实行君主制,却表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君主制形态,北方以色列王国是以氏族权力为基础的君主制,南方犹大王国是以王室统绪为基础的君主制。
南北君主制形态决定了两国政治传统的差异。(参看文末以色列与犹大两国王朝承续表)。其一是北方以色列王朝更迭的频繁和南方犹大王权继承的稳定。在北国256年的历史上,曾经历了九次改朝换代; 而在南国445年历史上却只有一次篡位的记录。 其二是北国王室统绪的混乱和南国统绪的一脉相承。以色列的九次王朝易主实际上是由不同支派背景的九位强人实现的;而犹大诸王则几乎都是大卫王室的直系后裔(注:唯一的篡位者亚他利雅是犹大王亚哈谢的母亲,不属犹大支派;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立之王西底家为约雅斤王之叔父;其余犹大诸王均为父子相传。)。犹大王国只有一次重新立王的记载,即亚他利雅篡位被杀后祭司耶何耶大膏立约阿施为王(王下·11:12), 此举意在恢复中断的大卫王室统绪。这一切表明,以大卫王室血统作为立王标准和君主制基础的原则为犹大所接受而为以色列所否定。在这背后则是古老的妥拉律法思想在南北两地的不同命运。自大卫时代起,在以色列统一王国强盛现实的催化下,生发出一种我们可称之为“圣约”观念下的“特殊恩宠论”思想,即大卫王室的统治特权得到了耶和华神的特别祝福和恩准,这是对妥拉“全民立约”中平等观念的突破,这一思想在分国后的犹大被认可和强化,但却无疑遭到了北部以色列诸支派的拒绝(注:如《代上》17:7有耶和华命拿单告诉大卫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17:11:“你寿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这一“特殊恩宠论”最凝练的表述,出现于《创》49:10雅各对12支派祝福时, 对犹大支派的“预言”中:“王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此节属于P底本资料,与上述两种记述一道显然都是分国后的犹大国产生的。)。在涉及以色列诸王的史籍中,我们找不到维护正统王权的记载,相反,第一王耶罗波安和第六王暗利都是由民众拥立的;其他诸王凡能在王位上坐定的,也应该是得到了氏族力量的支持(注:如以撒伽支派的巴沙杀以法莲支派的前王拿答,作王24年(王上·15:27—28)。)。这表明,在北方以色列,人们不独是不接受大卫家族的统治,也不承认任何一个王室的统治特权,王权和君主制是建立在氏族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北方诸氏族(支派)的势力在大卫—所罗门时期无疑是受到极大的压制,但这两位有为君主的威权和政绩只是暂时掩盖了地方氏族分权与中央政府集权的矛盾,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大卫为王尽管是以强力实现的,但他最终得到北方的承认,仍经过了7 年之久(注:大卫在扫罗王死后先在希伯伦作犹大王,7年零6个月后,北方诸支派长老又接受他为以色列王。参《撒下》5:1—5节。),所罗门为王虽为大卫所圈定,但大卫在充分利用自己权威的同时仍然表现出对民意的尊重(注:遵照大卫王的旨意,祭司长撒督、先知拿单和军队首领比拿雅“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训。祭司撒督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王上·1:38—39)。)。所罗门之子罗波安在耶路撒冷继位,只表明他在犹大被视作王,并不意味着其王位的合法性已获得全国普遍的认同,于是“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王”(王上·12:1)(注:示剑位于12支派中最大的支派玛拿西在约旦河西岸的领地之内,与第二大支派以法莲领地相邻,自约书亚时代即是全民族的宗教圣地,在大卫定都耶路撒冷前其他地位冠全以色列地之首,统一王国形成后,亦为北部最重要的中心地之一。)。罗波安此行目的,就是要履行传统的与民立约登基仪式,以获得北方对自己的拥戴,但这位年幼无知的新王却“不听老人听从少年”,以恶语待以色列人,因而理所当然地被秉承妥拉传统不接受“特殊恩宠论”的北方百姓所抛弃(注:宫中长老的进言是:“现在王若服事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作王的仆人”(王上·12:7)。换言之,王只有事民如仆,才能换来民事王如仆,这是“全民立约”中的民本思想的反映。而与王一同长大的宫廷贵族少年们的进言却是:“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上·12:10—11)。 罗波安依此言而行,说明他对以色列民族的社会权利基础一无所知。以色列众民于是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儿呢?与耶西的儿子(耶西为大卫之父)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王上·12:16)。)。 至于犹大王国为什么能接受“特殊恩宠论”其实不难回答。首先是犹大支派是犹大王国的主体,而大卫家族攫取了对犹大支派的控制权(注:《代上》27章记各支派的领袖,犹大支派的领袖是大卫的一个哥哥以利户(见27:18节)。), 也就是说氏族权力与王室权力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其次是大卫、所罗门的功绩令犹大人充满自豪感,使他们对耶和华与大卫家同在的信念坚定不移。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氏族势力在以色列进入君主制后虽时强时弱,但却始终未曾失去其影响,而统一王国建立前即已形成的妥拉律法中有关权力的思想传统在以色列民族中一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在南北两国的不同命运使犹大和以色列王国的君主制具有了不同的特点。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为什么在近四百年的君主制时期内,氏族势力始终存在,而妥拉传统也一直被继承下来呢?这是因为以色列民族的土地占有制度是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层层分割的土地所有制,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是以色列氏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妥拉律法传统得以流传的必要条件。从希伯来《圣经》提供的资料来看,约书亚时按支派(氏族)为单位分地,各支派内又以宗族为单位分地,宗族之内再以家族为单位分地,各支派的地产受到律法的保护,不得随意在支派之间转让(注:为此,律法甚至规定凡承袭地产的以色列女子只能嫁与同宗支派的男子(民·36:8—9)。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一规定不可得到严格的遵守。)。士师时期,土地在宗族内部的转让须按血缘关系的远近进行,只有在近亲放弃购买的情况下,土地才能转让给远亲(得·4:3—4)。这种血缘意识浓厚的土地占有制直到君主制时代仍是这个民族土地制度的基础。《利未记》17—26章是该卷书中具有相对独立的一组律法,被称为“圣典”(The Holiness Code),其形成年代,学术界向有争论,但综合各家所言,则最早不早于犹大王玛拿西时期(约692—638BC),最迟不晚于自巴比伦回归前后(注:Fohrer认为“圣典”晚于公元前700—650年间形成的“申典”,但早于流放巴比伦时期; Elliott —Binns认为早于“申典”时期,具体时间或许在玛拿西当政时期;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是流放时期形成的。参Otto Eissfeldt, The Old Testament: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Old Testament.Tr.by Peter R.Ackroyd,Oxford,Basil Blackwell,1974。 笔者认为考虑到“圣典”受祭司观点的影响,应是在“第二圣殿”时期最后形成。)。“圣典”中在“禧年”的律法中有关于地产的律例,其意在于保护各家族以及氏族的土地所有权,限制土地的集中(注:如,“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利·25:10);“地不可永卖, 因为地是我(耶和华)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利·25:23—28 )。),既然这个民族在君主制后期乃至回归时期仍然接受并强调这些律例,则说明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个君主制时代至少在理论上仍得到肯定,是其土地制度的基础。当然在那时社会条件下权贵对普通百姓土地的巧取豪夺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仍有两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土地的兼并似乎很少越出氏族的范围,分国时期以色列王亚哈欲得拿伯在王宫附近的葡萄园,被拿后以神的名义拒绝,只好通过王后耶洗别串通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害死拿伯,霸占其葡萄园。这暗示出身为国王的亚哈其夺地之举是因得到氏族贵族的支持而得逞的。其次,王室在法律上似乎并没有任意占有本氏族内部或其他氏族土地的权力依据。大卫王只将他从耶布斯人手中攻取的耶路撒冷视作自己的产业,称其为“大卫城”(撒下·5.9);暗利作北国以色列王时, 为将首都从得撒迁往撒玛利亚,特意以二他连得银子从主人撒玛手中购得此山。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氏族土地所有制仍然是以色列民族君主制时期的根本土地制度。只要氏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不改变,氏族势力就不会消失,古老的律法思想也就不会失去存在的土壤。大卫、所罗门的改革主要是限制氏族领袖和宗教祭司阶层权力的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新,并没有变革氏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氏族贵族的权力只能因一定时期内王权的强大而受到压制,却并未失去其在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地位。缘此,古老的妥拉律法传统才一直拥有深刻的影响,分国后的以色列和犹大才出现了两种不同形态的君主制,以色列民族在君主制发展的三个阶段才始终不曾产生绝对集权的君主制。
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在统一王国时期的辉煌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大卫——所罗门时代的繁盛固然与集权化倾向带来的国力的增强有关, 但也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对以色列极为有利密不可分。 公元前11世纪末至10世纪后半叶,西亚北非无强国,曾经强大的埃及已是昨日黄花,再无力对外进行有效的扩张;加喜特人统治下的巴比伦尼亚内争外患不绝,国力难以凝聚;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已为“海上民族”所摧垮;亚述则正处于由中期王国向后期帝国转变的积蓄阶段;米底——波斯尚未兴起,这一切给了以色列人的发展以天赐良机。自公元前10世纪末叶起,亚述重新走上对外征服之路,两世纪后,建立起强盛一时的亚述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首当其冲。因此,分国后势力大衰的以色列与犹大王国尽管间或有个别统治者政绩不俗,但夹在野心不死的埃及和正在崛起、必欲称霸的亚述之间,已不可能有大的作为。然而,南北两国君主制的不同特点以及所实行的不同宗教政策,却直接决定了各自最终的不同命运。以色列既不接受“特殊恩宠论”的王位继承统绪原则,也未真正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国中除原有的对耶和华神的崇拜外,亦流行对伽南诸神的崇拜,造成极大的混乱。因此,当公元前722年以色列遭亚述灭国,百姓被迁至亚述境内后, 这些亡国之民失去了任何可资凝聚在一起的基础,不可避免地被同化,成为消失于茫茫人海中的“十个丢失的部落”。而犹大在所罗门王后,即确立了以大卫王室血统为标准的王位继承制度,“大卫家”后来成了犹大的代名词。此外,虽然异教信仰也流行于犹大,但毕竟圣殿和祭司阶层始终存在,即便在宗教调和主义思潮泛滥之时,对耶和华神的崇拜依然不失为百姓信仰的凝聚中心。特别是在希西家王(720—692BC)和约西亚王(638—608)时期,犹大经历了两次清除异教的行动(王下·18:4—5、23:4—15),约西亚王在公元前621年的那次做得尤为彻底,被史家称为“621宗教大革新”,这些都有效地加强了民族统一的信仰基础。 公元前586年,犹大为新巴比伦所灭,众民被掳至异邦, 沦为“巴比伦俘囚”的犹大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族凝聚力,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对大卫王室所象征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怀念,无疑是形成这一凝聚力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篇第137 首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同仇敌忾和对故国家园的深沉思念,诗中有“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起锡安就哭了”,“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等句。约50年后的波斯时期,犹大人获准回归耶路撒冷,尽管恢复大卫、所罗门盛世的愿望此后只能化作梦中无尽的期盼,但随着“第二圣殿”的建立,作为民族文化之根的独一神信仰犹太教终于形成。在罗马帝国时期,当他们再一次失去生活于自己家园的权利时,正是这样一种民族文化,成为维系流散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纽带,使他们避免了数百年前北国以色列同胞所遭到的命运。
与其他民族一样,古代以色列民族经历了由氏族部落阶段到君主制国家阶段的历史进程,但整个民族君主制的发展轨迹又带有自身鲜明的特点,这个民族发轫之初即已形成的特殊的宗教观点作为其社会生活中“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页。)的重要部分, 对其君主制的发展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我们已经指出以色列的民族信仰在几百年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古代伽南那样一个多元文化荟萃的人文环境中,以色列人固有的文化、包括宗教实践亦受到了不断的挑战,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的妥拉律法传统,对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王权思想的内在影响却一直持续下来。不过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82页。)妥拉律法传统与君主制王权思想归根结底是由古代以色列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附表:
以色列王国
王名 在位年限
王位由来
耶罗波安一世22年 民众拥立
拿答 2年
继位
巴沙24年
篡位
以拉 2年
继位
心利 7天
篡位
暗利12年 民众拥立
亚哈22年
继位
亚哈谢
2年
继位
约兰11年
继位
耶户22年
篡位
约哈斯 17年
继位
约阿施 16年
继位
耶罗波安二世41年
继位
撒加利亚 6月
继位
沙龙 1月
篡位
米拿现 10年
篡位
比加辖
2年
继位
比加20年
篡位
何细亚
9年
篡位
(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亡于亚述)
犹大王国
王名在位年限
王位由来
罗波安 17年
继位
亚比央
3年
继位
亚撒41年
继位
约沙法 25年
继位
约兰 8年
继位
亚哈谢
1年
继位
亚他利雅女王 6年
篡位
约阿施 40年
继位
亚玛谢 29年
继位
乌西雅(亚撒利亚)52年
继位
约坦16年
继位
亚哈斯 16年
继位
希西家 29年
继位
玛拿西 55年
继位
亚们 2年
继位
约西亚 31年
继位
约西哈
3月
继位
约雅敬 11年埃及法老立
约雅斤
3月10天
继位
西底家 11年巴比伦王立
(公元前586年犹大王国亡于新巴比伦)
说明:本表据《王上》、《王下》和《代下》三卷书列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