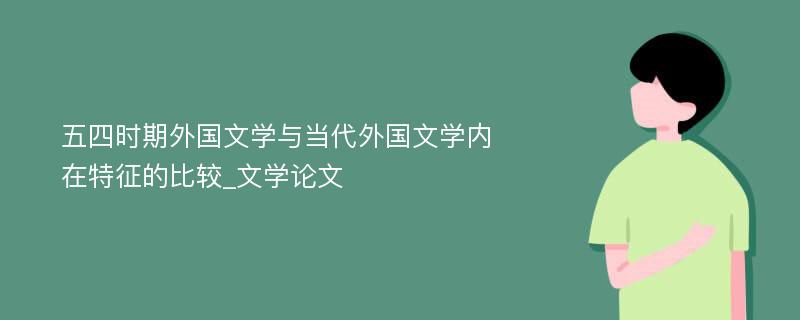
“五四”时期域外文学与当代域外文学内在特征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域外论文,文学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晚清至当代百余年来,伴随着中国民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坎坷与延宕,域外文学创作亦时断时续,间盛间衰,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与审美特征。
晚清时期以留学出洋为契机,拉开了中国人了解西方社会、认识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化的历史帷幕。但是这一时期域外文学的作品数量较少,文学的审美因素也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现,真正成熟的域外文学创作尚未出现。直到“五四”时期,域外文学才逐渐走上创作的发展以至繁荣阶段。以日俄留学生、英美留学生和法德留学生为代表的“五四”创作群体,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独特的审美体验。他们在作品内容上的拓展,特别是对异域中国人特殊情感的表现和对故国文化的审视沉思,以其视点的特异性和高度的历史涵盖性,成为中国域外文学创作的“母题”。虽然在建国后,这种带有个人异域生活经历的纪实性文本几近绝迹,只有港台地区的留学生文学创作处于繁盛阶段。但因为特殊的历史际遇与文化背景,他们吟咏的是一曲曲“无根一代”的文化乡愁与浪子悲歌。及至八十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才欣起新一轮的出国狂潮,从而刺激了新时期域外文学的再度勃发。这一时期的域外文学创作一方面承继了“五四”时期的文学“母题”,另一方面又凭添了开放时代的鲜明特征,打上了当代社会文化迁变的深刻烙印。
本文暂不论及港台地区的留学生文学创作,也不对百余年来的域外文学予以历时性的评说,而是选取“五四”时期与开放时期的域外文学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试图阐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审美特征的相殊性,从中透析域外文学创作中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文化蕴味。
一
“五四”时期,由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和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出现了自叙传小说盛行的文学风气。郁达夫甚至一再重申:“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1 〕这种自叙传文学往往带着作家个人的人生体验和身世之感,具有强烈的情感性或主情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而开放时期则多选择纪实这种准新闻文体进行报导性的或自述性的写作,试图传达当下人们对于虚构艺术教化与劝谕功能的厌倦或消解,带有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尽管二者在文体风格上存在着差异,艺术观念与社会观念也不尽相同,但却都是以对个人生活的切近作为它们显著的共同特征;而且域外文学无论采用传统手法,抑或创新的形式,都力图赋予个人以丰富的寓意,在个人经历的叙述与个人情感的抒写中,寄寓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深刻的文化情结。
“五四”时期的域外文学主要体现在日俄派与英美派留学生群体的创作中。日俄派以留日的创造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客居异域的生计压迫与性爱苦闷,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们身后那古老故国的陆沉,源于文明衰落后那深重难遣的民族自卑。所以,他们的创作都将个人忧郁与民族患难作为不可分割的情缘,以一种奇特的、有时甚至是病态的方式编织在一起,发抒自己作为中国人沦为弱国子民的怆痛怨愁,即便是描写青春期最为敏感、最富浪漫幻想色彩的爱情,也全力倾诉因背负着民族的衰败而遭受歧视、委屈和耻辱的情绪。郁达夫就曾这样描述他在异国的感受:“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情毒箭的一刹那。”〔2〕可以想见, 郭沫若“行路难”的种种感慨和郁达夫“沉沦”游子的声声呼唤,就寄寓了多少历史的怆痛与民族的耻辱。
与创造社的激烈峻急风格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英美派留学生群体的域外文学创作。他们主要以异域文化作为参照,审视故国传统,带有渐进稳健的文化色彩和从容宽厚的个性特征。老舍在小说《二马》中就以对狭隘民族意识的超越,达到对传统文化的省思目的。他借西方观念批驳中国古老文化中的陈规陋习,在对中英两国民族性的比较中,深化了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显露了作家眼光的犀利与胸襟的开阔。虽然“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这样的说法本身未免失之简单,但老舍在创作思想方面的突破,显然是与中国门户开放与文化交流的历史初衷相一致的。
“五四”时期的这两类域外文学创作,在审美倾向上一个偏于主观,一个重于客观;在情感特征上一个略见偏激,一个稍显宽容;在文化选择上一个多有批驳,一个则多有认同。这是他们作为独立的创作群体不同文化特征的具体表现。尽管如此,他们都站在一个相同的立足点上并找到了共通的东西,构筑了“五四”域外文学有机联系的整体。这个立足点就是以期冀祖国强盛、民族复兴作为其共同的创作主旨,显示了一代文学先驱独特的文化心理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展现了一代爱国知识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意识。
不可否认,开放时期域外文学创作是与“五四”时期保持了某种内在延续性的,相当程度上还是继承了“五四”时期域外文学对异域中国人特殊情感的表现和对故国文化的审视沉思这一创作“母题”。时至今日,那些客居异域的游子当然不再会感受到昔日祖国被列强宰割而造成的民族耻辱,但是国家之间经济力量的对比与民族文化意识的差异,是不可能在目前情况下迅速趋于一致的。因此,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纠结依然难以分解,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难以弥合,而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制约着客居国华人群体的地位,影响着他们对于异域文化的体认和对于故国文化的反思。表达个人在文化困境中的自我挣扎以及个人命运与社会、民族命运的关联,作为开放时期域外文学主题的一个支脉,依然在延续着。为此,开放时期的域外文学主要以两类作品对这一主题加以具体阐释。一类是以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等一系列作品为代表,在描写激烈的生存竞争和物欲挤压下的内心焦灼之外,更多感受的还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困挠。在文化抉择的两难境地中,尽管他们找到了许多物质上的满足,最终却发现一切都与他们寻找的初衷相背离,物质的所得又相随而来精神的所失,成为对自身的一种嘲讽。另外一类作品,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巫宁坤的《沧海一泪》、张戎的《鸿:中国的三个女儿》、亚丁的《不周天》,则多以记录自己的文革经历而呈现出一种浓重的历史反思色彩,而且由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濡染,他们更多地是以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道主义作为审视“文革文化”的基本原则。这些作品都从各自不同的写作动机和立场出发,映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必然联系以及置身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边缘人的尴尬与反思,不同程度地带有知识分子化的精神特征和思想印痕,代表了开放时期域外文学的较高水平。
但是,体现了开放时期鲜明时代特点的、在读者中间引起较大轰动的而且占一定数量的是带有淘金色彩的域外传奇纪历,就是那些新一代移民们以纪实风格讲述的背井离乡、孤军奋战、闯荡天下的老故事。他们的言语之间已不再有明显的历史屈辱感,民族情绪也不十分愤激而强烈,表现较突出的是第三世界处境下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因物质上的差异而造成的新一代海外漂泊者的心理失衡。他们对生活的感激或怨愤首先来自于物质上的满足或欠缺,因为游离故土投奔异域的目的就是要在第一世界的“丰裕”中寻找到第三世界所不能提供的一切,并通过寻找的过程或结果来实现自我生存和个人价值的重新定位。但是,在他们失败的诉说与凯旋式的告白中所显露出的文化欠缺与精神萎顿,正日益被人们所认识,而这也正是它们日渐被昔日读者冷淡拒之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作为一种时代现象的实录和异域漂泊生活的写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我们对于当下社会现实中物质欲求与精神价值的沉重思考,仍使它不失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二
“五四”时期与开放时期域外文学创作主体的文化特质,既代表了两个时期域外文学的不同特点,同时也是形成这些特点的主观动因。他们的文化学养、文学造诣、人生经历以及所承接的社会影响等众多因素,都将直接作用于他们文学创作审美内涵与审美方式的选择,使之具有各自独特的审美特征。
从文化背景看,域外文学创作者群体呈现了新的社会环境下所具有的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域外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大都是离开故土而自由流动的,他们往往集中于都市中心,对于现代世界的信息和知识特别敏感,并由之而产生强烈的变革愿望。第二,域外知识分子的人际关系和活动范围大部分集中于学校、文化界和自愿结合的社会团体内,因此他们相对于政治权势具有一种独立意识,从而采取客观的认知或批判态度。第三,域外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具有必然的或绝对的认同感,他们的文化视野和知识结构已开始呈现多元化倾向。这些特征在他们的异域经历以及域外文学创作的目的与内容上,都得到了较为明显的反映。但应该看到,这些特征只是我们作类的界分时所发现的共性的一面。对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群体而言,具有自身的相对特异性应该是在所难免的。
“五四”时期的域外文学创作者群体,是在中西文化纵横交错的历史变革时代成长起来的。作为清朝最末一代的私塾学生,他们在童蒙时代都经受了极其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于经史子集等传统典籍以及从儒学到乾嘉汉学的传统治学方式,他们都同样相当完整地接受过。出于自身叛逆性格的影响,加之传统文明日渐式微的时代气息的熏染,他们又比旧式文人更为广泛地涉猎了被传统文化观念视为“野狐禅”的野史笔记、小说戏剧以及存留于下层社会的民间文化。正是因为秉赋了丰厚深广的传统文化精粹,所以在他们身上相当程度地聚集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特征。尤为难得的是,在国内时他们已受到最初的新式教育以及“欧风美雨”的冲击,在他们理性精神和革新意识都日趋自觉的青年时代,又亲身来到英、美、法、德等欧洲国家及作为西方文化东渐媒介的日本留学,全面感知、选择和吸收西方文化的信息。因此,当他们踏入异域,为自身的文化构成注入新的价值因素时,求新与守旧、传统与现代等诸种文化因素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和冲撞。作为新文化主要载体的“五四”作家群,终于能够以一种清醒而宽容的理知精神,丰厚而深广的文化禀赋,成为既以现代精神面对世界、同时又与民族传统保持深刻联系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笔端所传达的爱国思想、民族情绪、文化意识以及社会批判精神,正体现了“五四”一代知识者、文学家所独具的精神特征。
对开放时期的域外文学创作者群体来说,影响并形成他们精神特质的重要因素,也许应该归于那个特定的时代,尤其是“文革”的影响。那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处于双重匮乏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当时年轻一代所遭逢的历史缺憾也可想而知了。就西方文化这一对象而言,由于那一时代文化与意识形态对西方的拒斥,处于求知阶段的年轻一代对西方文化不仅无从感知和了解,而且处于一种误读的状态之中,更无法谈及对文明与进步、科学与民主、人文理想与道德精神的体认。从文化传统而论,那个时代在盲目弃旧破旧的同时,也无情地斩断了传统文化的链环,被摧折的教育体制更无力承当重建传统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任。相较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学人来说,生长于这一社会背景的年轻人距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都尤为疏远。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知青”一代,虽然不断领受主流意识的激励与动员,但最终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实质性的精神收益,更多的是各种政治风云留给他们的充满苦难和迷茫的青春记忆。而时下正日益受到思想界普遍重视的“六十年出生”一代,由于当时年纪尚轻,与成人世界有很大隔膜,因而得以更多地游离于各种政治运动之外而自由生长,精神上所受的限制相对较少。但是由于整体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文化积累很少,社会意识也较为薄弱,终致成为“二十世纪虚无主义精神链上的最后一个环结”。〔3 〕虽然历史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对他们寄予了一定的厚望甚至进行精神的补偿,但已不可能抹去动荡时代留在他们身上的精神匮乏的印记。
八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他们得以置身于异域的多元文化环境当中,从而促成了这些域外游子对西方文化价值的真正体认。当他们亲眼目睹了西方社会如同神话般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并感同身受地濡染了西方价值观念之时,对于故国文化的反思以及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就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动机和主题。由他们自身经历、自我体认所带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选择就是:对昔日灾难性生存状况的反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对自我生存价值的重新发现与界认。
同处于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层面,但是“五四”时代与开放时代两类域外文化人的选择却显现了视点与动机的不同。一个侧重于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的弘扬,试图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中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个则侧重于自我意识与个人价值的重构,试图在跨文化的时空域境中自我定位和求取生存。在这种文化选择和审美意识的相异性背后,除了各自文化气质和文学动机的差异之外,显然还有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
三
“五四”时代域外文学创作者的文化批判意识与文学审美精神,是近代以来民族命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共同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威逼与入侵,天朝帝国屡经丧权辱国的苦难,古老文明逐渐步入衰落的历史厄运。面对民族危机与文化存亡的现实,中国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新式知识分子率先肩负起寻求国富民强的历史重任,并萌生了“别求新声于域外”的强烈愿望。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伴随洋务运动开始的门户开放,一部分知识分子暂时脱开了暮气沉沉的族体文化的强大桎梏,得以在一种呼唤维新的社会氛围中,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并将所感所学投之于民族自强道路的实践。但是,这种历史机遇所带来的最大结果却是国民精神的一次裂变。梁启超声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4 〕甲午一战,“格致制造”之途终归失败,由技术器用的层面又转向文化的反思,而文化的反思又必然引入思想的启蒙。这种转折标志着中西文化的交融和碰撞进入了更深的层次。
早自魏源编成《海国图志》这部史地巨著时,他就多少感到了“人心积患”的严重性,并重申了“欲平海上的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的名言。〔5〕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更以浩荡的生气掀起了文化革命与思想启蒙的历史波澜,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幕。它之所以要打倒旧道德而提倡新道德,推行新文学而摒弃旧文学,仍然是基于深重的民族危亡感和文化危机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题,只是在行动的指向与方式上以摧毁旧传统、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特点,通过鉴借西方文明来对传统文化施行自我突破和改造。新文化运动在提出“科学”的同时,又标举“民主”的旗帜,显然将伦理革命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因为伦理是文化革命和思想启蒙的重要基础,它将有力地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带来人文观念、价值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可以说,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图景和社会现实,为域外文学创作者提供了文化省思的基本视点,而“五四”时期人文意识的觉醒,则为创作者的文学题旨和批判精神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滋养。郁达夫对故国的声声呼唤,老舍对国民劣根性的层层剖析,正是从民族历史命运与人的意识觉醒这两个层面上,寄寓了“五四”时代文学家与启蒙者深沉的文化意识,以及从两种文化交汇处寻求中国文化出路,企望民族复兴的深切愿望。
开放时期作为民族历史发展中的崭新一页,带有当代社会多维价值、多元文化并存的鲜明特征。具体地说,开放时期的域外文学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征,尤其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商业化社会的诸多特点。
对于有着强烈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第三世界而言,物欲的压抑和理性的无奈,已深入到第三世界的文化特征中心,而物质匮乏与价值贫困正是这些国家面临的最直接亦最尖锐的挑战。开放时期那些出走异国者,多数也正是出于对第三世界文化处境的逃离或退隐而进入第一世界文化边缘的。他们迫切期望在新的世界里实现个人对物欲的梦想,找寻自我的生存价值,并试图以此洗刷由于母国文化物质方面的多重匮乏而造成的屈辱感和自卑感。这种观念与“五四”时期那种鲜明的启蒙和救亡意识截然不同,两个价值层面的对比似乎意味着当今时代域外文学人文精神的衰减和民族意识的消退。
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一个商业化的时代正在来临。务实精神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其负面影响使得理想主义和人文热情被视为空洞的语言幻觉而日趋消解,后现代更如一柄双刃剑,“在否弃一切独断专制与一切固执偏向的过程中,却体现着自身的固执偏向,那就是虚无主义”。〔6 〕而这正是我们在开放时期的域外文学中频频目睹的对物的崇拜和占有,并因而自沾自喜、自我炫耀的原因所在。由于这种倾向性,开放时期的域外文学一再遭到严肃批评家的抨击和指斥,而查建英以她的《丛林下的冰河》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佐证。这篇小说所触及的中心就是中国现阶段理想主义的终结。对于现实世界日渐突出的世俗化困境,理想主义显然已无力拯救。查建英满怀忧伤地为理想主义写下了最后的挽歌。感伤与凭吊之外,惟余随俗的无奈。
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化带来的媚世与媚俗在消解意识形态、折解颠覆同一性的同时,正悄然滋生起一种对个体主义,包括个体享乐主义的认同思潮。当然,这种个体主义思潮在对所谓“幸福”的追求中已日趋世俗化、平庸化,完全逸出了精神追求的轨道。但它又同时传递出对文化守成思想的叛离和对个人价值的呼唤这样一种进取精神。那些传奇纪历中一再显示出的依靠个体独立奋斗、勇于冒险、尽情享乐的文学特质,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更为真切的写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另一类式样,是对外开放和交流所带来的新的文化困惑。
“五四”时期与开放时期是中国域外文学整体构架中的两个历史分段。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变化以及两代人文化特质的差异,呈现了不同的审美特征和思想倾向性。而历史发展进程的连续性,又造就了其文学创作主题在某种程度上的内在联系。因此,两个阶段既各具特色,又不乏共通之处。只是,当我们试图在文学的领域里阐释两个历史时期域外文学的文本特征时,却常常被带进历史的忧患与现实的困境当中而深感难以负载。面对“五四”一代文化先驱的理想主义和参与热情,面对他们的批判精神与拯救意识,当代文学在精神和语言两个方面的匮乏或退化,是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深思了。当然,应该看到,开放时期的域外文学在关注功利物欲的同时,正孕育着人们思想上进行突破或飞跃的一种可能。对于物质与精神、金钱与良知、灵与肉的种种冲突的感知体认,终将导致人们对人类终极依托的思考,从而引领文学走向更超越的文化、文明这一世界文学主题。
注释:
〔1〕郁达夫:《过去集·创作生活的回顾》。
〔2〕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4卷第93页。
〔3〕郜元宝:《匮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60 年代出生作家群印象》,《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页。
〔5〕魏源:《海国图志叙》。
〔6〕尤西林:《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知识分子》,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