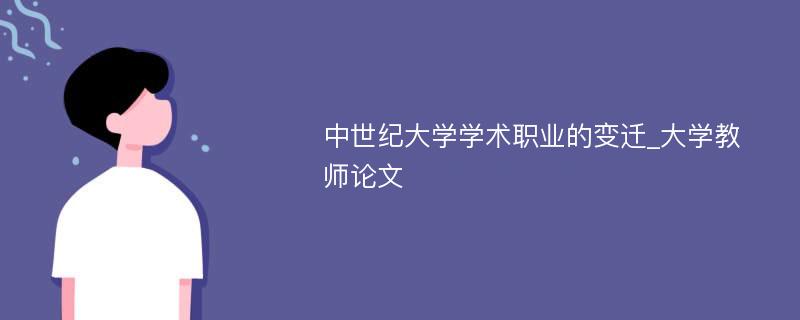
中世纪大学学术职业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世纪论文,学术论文,职业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1)02-0069-06
学术职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学术职业泛指一切从事学术活动的职业群体,比如医生、律师、建筑师、大学教师等。狭义的学术职业专指大学教师这一特定职业群体。哈斯金斯认为,狭义的学术职业发端于中世纪大学[1]。中世纪大学是由一群为学术而学术的大学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如博洛尼亚大学因爱尔纳留斯及其学生创立,巴黎大学因阿伯拉尔及其学生创立[2](P287)。在中世纪大学由盛而衰的转变过程中,学术职业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从学术职业的三个维度——专业活动、专业组织、专业地位出发,探析中世纪大学学术职业的变化,以此管窥学术职业的意蕴。
一、中世纪大学之盛:大学教师以学术为业
在中世纪早期,大学教师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出现并不断壮大。他们组建了大学社团,把学术当成自己毕生的追求。他们犹如一道神圣之光让黑暗的中世纪闪亮耀眼[3],体现在:
1.专业活动的神圣性
专业的英文是“Profession”,它具有宗教的神圣性,具有天职、圣职、神职的意思。它不仅仅是为了谋取一定的物质财富,也是为了向上帝皈依。在中世纪,大学教师成为一个专门化的职业,即专业,在于其活动具有了专业的神圣性。
首先,在中世纪,世间万物被认为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的智慧蕴含在世间万物中。明晓世间万物,也就明晓上帝的全知全能。因此,一切知识都是关于上帝全知全能的摹写。于是,大学教师把知识当成上帝的赐予,一旦像商品那样出卖知识就是对上帝的不敬。为了与上帝交流,他们将探索新知作为上帝赋予的时代使命,希望通过研究更好地传达上帝的旨意。这样,大学教师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产生了。由此,他们的学术活动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而“那些把科学占为己有,并阻碍自己和别人去使用它的人,都是些庸人市侩”[4](P57)。
其次,大学教师也是教士。一方面他们矢志不渝地敬仰上帝,如经常参加当时风行一时的圣餐礼拜和“基督复活”的游行活动;另一方面,大学教师通过对圣母玛利亚的歌颂表达了献身基督教的意志。13世纪初,中世纪大学广泛流传着专门献给圣母玛利亚的诗篇和祷文[4](P75)。
最后,在大学教师看来,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是可以通过理性加以阐释的。这种观点使得他们试图通过探究式的逻辑推理理解全知全能的上帝。除了精确阅读《圣经》,他们认真思考有关上帝、自然和人类自身的问题,并试图从大量文献中找到答案。“信仰寻求理智力”[4](P82)是中世纪大学教师的行动准则。此时,信仰与理性是统一的,信仰是对上帝的虔诚,而虔诚得靠理解上帝这个最高的理性存在者加以保证。①
2.专业组织的严密性
大学教师为了更好地研究与教学,仿照当时的行会形式组建了自己的法团,即“University”。涂尔干认为,“University”一词取自法律用语,指拥有一定程度一致性和道德一体性的集合。这个法团首先是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一种联合,接着是研究与研究之间的联合[5](P125-127)。在大学内部,不管是新教师的任命、领导人的遴选还是教学活动的管理无不体现出专业组织自身的严密性。
首先,专业组织对新教师严格选拔。中世纪大学一般有四个院部:艺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和神学院。艺学院授予普通教育的学士学位,获得了此学位就能在艺学院任教。学士学位的获得必须首先通过由四位教师组成的委员会主持的考试,获得主事授予的执教权。在半年之后,候选人要在同乡会上发表就职演讲才能通过[5](P176-178)。如果他还想拿到博士学位,须进入其他三个学院学习。中世纪博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位,而是一种任教资格,博士的培养目标是为大学输送教师。获得博士学位必须要经过两次考试:个别考试和公开答辩。在考试之前,申请人需要经过八年的学习才能被推荐给副主教。在个别考试阶段,申请人从主考官那里领取两份供评注的文献回家研读,在当天的晚些时候,他们面向考官和副主教在公共场合宣读并接受提问。不仅如此,申请人必须要在第二阶段的公开答辩通过之后才能被授予博士学位,获取授课资格[6]。通过严格的教师选拔方式,中世纪大学不但为学术职业吸纳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人才,而且保证了教学质量。
其次,专业组织规范管理。(1)校长的决策来自教师的表决。校长一般由艺学院的院长担任,全权负责大学的运转。但决策的制定并不是由校长说了算,通常要召开全校的教师集会,并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公开表决。只有在出席集会的大多数教师赞成的情况下,决策才能通过。(2)院长选拔严格。院长的录用条件包括至少五年的法律学习,同时每两年更换一次,而且必须由前任校长、新任教师和一定数量的教师代表选举产生。(3)学监的任务明确。在大学里,学监负责组织全校师生在校长面前宣誓,捍卫宣誓的承诺和大学的法规;负责执行对违反法规教师的审判;负责召集全校的教师集会;负责统计各种选举的票数并公布结果[7]。
第三,专业组织严格管理。大学教师的教学时间受到严格的规定。他们每周至少要上三次课,请假必须征求学生和校长的同意;当上课钟声响后,教师必须开始上课,对于违反规定者将处以20先令的罚金。到了下课的时间,教师不能拖堂,否则教师不但要缴纳罚金,学生也要上交19先令的罚款。为了使大学教师严格遵守这些纪律,校长任命学生委员会监督他们的日常行为,并定期向他汇报[2](P196-197)。课堂被划分为“普通”和“特殊”两种类型,普通讲座一般在上午进行,特殊讲座在下午进行。如果在普通讲座中听讲人数少于5人或者在特殊讲座中少于3人,教师得交一定的罚金[2](P205)。如果教师打算离开所在的城镇,他必须向学校提供一定的保证金以确保能够按时归来。此外,艺学院的教师组成了同乡会,该组织能在生活上给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避免遭受他人的盘剥和其他不友好举动。
3.专业地位的崇高性
中世纪大学教师由于只听从上帝的感召,再加上其专业组织为其活动提供保障,勇敢地为了真理不懈地同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抗争,从而在中世纪享有崇高的专业地位。“没有任何人比教师更重要和更有影响了”,因为只有教师才能“引导人们到耶稣那里,并了解他的天国和人所具备的标准才能”[8]。
首先,大学教师的身份独立。中世纪大学教师既可以选择从学生那里得到酬金,从世俗权力机关得到报酬,也可以从教会获得薪俸和领地。然而,为了不依靠教会势力和世俗势力,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学生支付的报酬为生。他们坚持“靠自己的双手劳动,绝不要向别人讨东西”[4](P93)。许多大学教师当时的经济状况都很差。例如,在15世纪的帕维亚大学,根据不同年份,30%~50%的教师得到的收入平均不足50弗洛林,这仅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9](P156)。尽管生活清贫,他们却保持着那份独立,努力摆脱成为其他势力附庸的危险。
其次,为求知而流浪。在13世纪早期,中世纪一些比较著名的大学如巴黎大学授予的学位在欧洲所有国家均有效,由此很多人往往背井离乡去学习[5](P96)。同时,“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写照,很多人为求知而选择在异国他乡流浪。例如,中世纪最伟大的大学教师阿贝拉尔年轻时曾满怀激情到世界各地学习逻辑学和哲学[10]。
第三,拥有独有的知识体系和技能——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不仅指一套完善的信仰知识体系,还指一种理性的研究和教学方法:(1)大学教师将经院哲学的探究建立在辩论的基础上,他们通过对反对者的质疑进行申辩,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论据。“经院哲学在大学范围内,通过它特有的评注方式发展起来”[4](P82)。(2)虽然经院哲学依赖于《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但大学教师并不是盲从权威,而是借助于这些材料,努力构建自己的思想。他们坚信,“在我们之前写作的人,对我们来说不是主宰,而是向导”[4](P81)。正因为大学教师拥有独一无二的知识体系和技能,所以被看作是上帝的代言人,获得人们的尊重。
最后,大学教师团结一心。作为教会势力和世俗势力竞相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大学教师利用两者的矛盾,获取了诸多特权和豁免权,如教学权、学位的考试和授予权、自治权、独立审判权、租赋和税收豁免权。当大学的利益受到外部侵犯时,他们团结起来,凝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之作斗争。例如,12世纪的某皇室人员和警察暗自屠杀了许多巴黎大学的师生。此事曝光后,巴黎大学的师生以罢课、游行、迁校的方式表示强烈抗议。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被迫给予皇室人员和警察以严惩,并颁布法律以保护大学。这个法律标志着第一部大学宪章的建立[11]。
二、中世纪大学之衰:大学教师不以学术为业
当中世纪大学从辉煌走向衰落之时,中世纪大学教师不再以学术为业。这主要表现在:
1.专业活动不再神圣
从词源看,只有具有神圣意味的职业才是专业。在中世纪,人们想要通过增加知识皈依上帝,从而诞生了以学术为业的大学教师。就是说,大学教师称谓自古有之,但只有到中世纪,大学教师从事的不再是教书匠的职业,而是学术职业。在中世纪晚期,大学教师的活动不再具有专业的神圣性。
首先,科学知识取代了神学知识。在中世纪晚期,大学教师对知识的探索与研究不再是建立在对上帝智慧的神圣摹写之上,而是开始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他们批判神学知识无视现实经验,与人类生活失去了联系。而且,随着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神学教学已经显露出僵化和衰落。
其次,大学教师荒废学术。从13世纪末开始,大学教师不但成为教皇集权下的特权人员,同时也是世俗势力扶持下的公职人员。大学教师接受了教会和世俗的高层职位,成了主教、副主教、教会机构人员、顾问或部长。他们系于教会和世俗统治集团的关联,不但丢弃了对真理的执著探索,而且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来迎合宗教和世俗势力的需要,“大学成员每天都劝告法兰西民众忍受与顺从国王和领主”[9](P155)。知识失去了神圣性,转而成为大学教师在世俗和宗教势力面前卖弄的资本。此外,由于被使馆、会议、主教会的琐事缠身,大学教师经常无暇顾及日常的教学工作。他们仅仅把教师行业当作进一步担任公共职务的跳板,对教学的漠不关心导致了教学水平的普遍下降。
最后,理性和信仰分离。在中世纪后期,上帝的全知全能只能靠信仰和盲从,而不能靠理性加以诠释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这导致大学教师要么不加批判地信仰,要么彻底举起理性大旗,对神学进行淋漓尽致的批判。由于上帝只能由信仰加以保证,无法通过理性加以证明,这样,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只是针对世俗之城,不再着眼于上帝之城。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也就意味着大学教师从此只能追求纯粹的理性,学术活动变得不再神圣。一位巴黎大学校长痛心疾首地说:“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将要消逝,认识这个世界的事物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在你们匆匆赶去的地狱,不会再有一门科学。省了你们这番徒劳的辛苦吧!”[4](P21)
2.专业组织不再严密
虽然先有大学教师才有中世纪大学,但大学教师的专业活动必然要在专业组织里开展。科班比较了博洛尼亚大学和萨莱诺大学的历史,认为前者能幸存后者却消亡的原因是,“萨莱诺大学没有发展一个保护性的和有凝聚力的组织以维持它的智力活动的发展”[12]。科班的观点也解释了中世纪大学衰落的原因,即专业组织丧失了保护大学教师从事学术的能力。
首先,专业组织的世袭性。大学教师保留了大量的职位赠予自己的家族或直系亲属,以试图在大学组织里形成裙带关系,排除敌对势力。例如,博士的儿子们更容易得到大学里的空缺职位,而且他们可以免费参加各种考试。博士如果属于某一个博士的父系世裔,就可以免费加入法学家学会[9](P110)这实际上也转变了教师对于知识的态度,知识被认为是一种私人占有,是一种个人财富,是教师家族遗产的组成部分,如同他们的房屋、土地、书籍一样[9](P146)。家族世袭使大学对新教师的聘任缺乏公正性,大学组织的管理越来越受制于教师群体的帮派势力影响。
其次,大学行政管理的妥协性。(1)向国王妥协,如剑桥大学校长威廉·塞西尔(任职期为1559~1598)和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劳德(任职期为1630~1645)都是由国王任命的。这样,国王才是大学的真正管理者,大学校长只不过是国王的传声筒而已。(2)向宗教妥协。在1219年,博洛尼亚一位副主教命令,未经教廷的同意,大学不能向学生授予博士学位。大学教师宗教信仰的正统性不仅是教师得以任命的决定因素,也是被解雇的主要原因。如哥本哈根从1604年开始禁止聘任曾在耶稣会学院学习的人[13](P89)。不仅教师向宗教妥协,学监也是如此。1213年,学监事实上失去了颁发授课准许证的特权,转而由距牛津大学120英里之外的林肯大主教主掌牛津大学的特权。
最后,大学教师丧失了治校权。中世纪末期,政府专员开始被派到大学核实大学教师的宗教正统性和工作的勤奋度,他们接管了对大学里教师的学术和宗教生活的管理。同时,大学教师所教的课程由政府指定,甚至被规定要使用哪本教科书;教师的著作要上交给政府的审核机构;教学资格要由政府来授予,个人荣誉要由政府来保管。因此,大学作为专业组织丧失了对内部教师的管理职能,大学不再自治,大学教师不再治校。
3.专业地位不再崇高
中世纪大学教师面对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毫不妥协,从而让大学获得了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当大学教师丧失了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人格时,中世纪大学也丧失了崇高的社会地位。
首先,大学教师迎合外部势力并走向贵族化。大学教师领取薪水的方式发生变化。补助金、薪俸、教士津贴逐渐取代了学生支付的酬金,过去收取学费的教师变成了领取薪水的教师。这样教师从学术王国的成员变成了国家的学者,崇尚学术自由的教师变成公职人员,他们听命于这些支付报酬的机构而丧失了从事学术活动的自由。随着外部势力对大学教师的影响不断深入,他们试图在社会中谋求上层贵族的地位。主要表现在:(1)大学教师衣着和装饰的奢华。大学教师的讲桌越来越多地装饰起华丽的华盖,大学教师身披长袍,披风的兜帽是昂贵的灰鼠皮做的。(2)大学教师的头衔成为身份的象征。在12世纪,学生尊称大学教师为“师长”,在13世纪为“拉比”(对主人的称呼),而在14世纪就直接尊称为“主人”了。中世纪末期博士头衔像骑士头衔那样成为高贵身份的象征,如1420年,阿拉贡国王向法国瓦朗斯大学的学位获得者授予贵族称号[9](P147)。
其次,大学教师不能自由流动。博洛尼亚1432年制定的大学法规明确规定,不管是市民还是外来者都不得将大学迁移出境,同时已获得博士学位的50岁以上的市民,未经城市管理者的允许不能离开博洛尼亚市,违背者都将判处死刑[2](P171)。统治者通过立法禁止大学教师到外国任教并要他们发誓不接受外国职位。此外,随着当地公民对重要的大学职位享有优先录用权,大学教师开始越来越具有地域性。例如,在博洛尼亚大学,可以获得高薪的职位都留给了本地市民。柯尼斯堡大学校长科尔夫抱怨说,“本地人不出去,外面的人进不来,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倦怠和自我陶醉”[13](P245)。
第三,经院哲学逐渐僵化。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不但在语言上咬文嚼字,而且在论证的内容上空洞无实,基本上是学者的夸夸其谈。随着经院哲学在大学里的腐朽和僵化,大学被描绘成由卖弄学问的教师所组成的机械辩论场所。马丁·路德则批评大学教师“除了把人变成驴子,是不能给青年人任何其他东西的”[13](P175)。
最后,大学教师不再团结。14世纪初开始,没有获得执教权的托钵会修士开始大量进入大学讲授神学。由于托钵会的教师以布道而非教学来维持生活,他们不参加罢课等活动维护大学组织的权利,而且还告诫世俗教师要盲目信仰上帝而不是寻求理智力。他们的行为惹怒了世俗教师,并引发了双方激烈的冲突。但是托钵会修士最终得到了教皇和教廷的支持,教廷指出,“上帝委托我们,并不是要我们掌握科学,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由于教团的兄弟们的举止和学说征求了无数的灵魂,他们将一直享有应得的特权”[4](P94)。
这样,随着大学教师不再以学术为业,中世纪大学逐渐衰落,知识要想传播就不得不在大学之外进行。十五六世纪的欧洲,几乎每一所意大利城镇都有一所或多所致力于哲学或科学研究的学园。德国启蒙运动的斗士克雷斯蒂安·沃尔夫把学园解释为产生和传播新的科学知识和发明成果的地方,以区别于中世纪大学[13](P501)。学园在整个欧洲的扩展,既加剧了大学在中世纪后期的衰落,也表明了大学教师专业地位的没落。
三、从中世纪大学盛衰体会学术职业的意蕴
在中世纪的教育长河里,大学是由一群学者组成的,学生求教于最有名望的教师,学生与大学教师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的全部[14]。中世纪大学盛衰演变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大学教师即学术职业。当大学教师以学术为业时,中世纪大学绽放了无限的活动;反之,中世纪大学步入“冰河期”。从中世纪大学发展过程看,学术职业包括如下三层意蕴:
1.信仰是学术之魂
在中世纪早期,信仰犹如灯塔为人们指明了通往彼岸世界的道路。基督教将精神信仰的教化转交给大学,使大学教师的专业活动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信仰,大学才成为富有内在生命力的精神实体而不只是外在的空壳;因为知识是上帝赠予人类的礼物,大学教师才认为通过教学和研究去感应上帝的智慧之光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正因为大学教师认为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是神圣的,他们才能在孤寂和清贫中从事学术活动。这也是中世纪大学教师留给后世的遗产。如果没有了对上帝的信仰,学术职业就好像丢失了灵魂的行尸走肉。其专业活动将不再以学术为重,理性的科学根本无法走进人们的内心。当教学和研究活动不再神圣时,专业自治和学术自由也变得可有可无。尤其是在贵族社会的侵蚀下,大学教师似乎离上帝越来越远,与宗教信仰所倡导的清心寡欲思想背道而驰。华丽的外表和精心的装束掩盖的是学术职业的腐化和堕落。
2.理性是学术之光
信仰毕竟是灵魂性的,不是实践性的,它只告诉大学教师要做什么,但如何做则超出了它的范畴。信仰之魂要生成,还得借助于理性。在中世纪,上帝是最高的理性存在者,在于他创造万事万物,在于他说有光就有光的理性。理性之光赋予信仰之魂以活力。那就是说,有了理性,专业组织制定了严格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盘散沙;有了理性,大学教师在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的干预下克服了盲从,学会在两者的夹缝中独立而艰难地生存;有了理性,大学教师才能够团结一心,通过与外界的斗争争取更多的学术自由和专业自主的权利;有了理性,大学教师走在学术的道路上逐渐独立研究和批判思考。离开了理性之光,专业活动对学术的追求和批判精神一扫而空,知识成为大学教师的一种私人占有和垄断物品;大学教师沦为教会势力和世俗势力的帮佣,独立自主的人格魅力不复存在,学术自由和专业自治的优良传统难以为继。面对这样的衰败景象,重振大学之精神,寻求理性之光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直到今天,大学教师还在享用中世纪大学教师遗留下来的理性之光,从而成为最具活力的创新群体。由此,大学一跃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3.学术是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中世纪是大学教师运用理性寻找信仰的时代,信仰并不等同于愚昧迷信,信仰要靠理性来追求,因此大学教师将对上帝的信仰与对世界知识的理性探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尽管不能完全认识上帝的无限,但他们凭借自己的理性尽量接近上帝的智慧之光。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大学教师看作为离上帝最近的圣人,把他的学问看作是上帝之光的显现。这就解释了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情境下,很多人仍愿意追随大学教师的原因。这些大学教师走到哪儿,学生就无怨无悔地跟随到哪儿。师生在哪儿对话,大学就在哪里产生。中世纪大学从辉煌走向衰落表明,学术职业既离不开对上帝的信仰,也离不开对理性的执著追求,“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的事物的憧憬”[4](P3)。正是遵从了理性,大学教师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批判之活力才能在学术活动中得以彰显。然而,理性要靠信仰来保证,理性只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信仰才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因此,理性与信仰不是离散的个体,而像人的身体与灵魂一样是充满活力的统一。只有理性和信仰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大学教师才能在专业组织上坚持自治,在专业地位上保持自立,在专业活动上崇尚真理。总之,信仰寻求理性的同时,理性也寻求信仰,当理性与信仰统一时,也是大学教师的学术成为专业时,更是大学繁荣昌盛时。
[收稿日期]2010-12-28
注释:
①在中世纪,动物是非理性的,上帝是理性的,人位于动物和上帝之间,因此是“理性的动物”。人通过上帝赋予的理性而皈依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