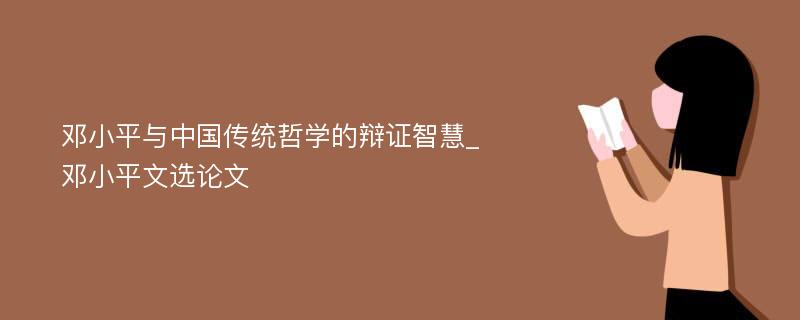
邓小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智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哲学论文,智慧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大思想家。他之所以成为大思想家,之所以给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以巨大的活力和杰出的贡献,不在于他是否写过专门性的哲学著述,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阐发,而在于他提出并实践了一套独创性的思维方式,以此来总揽全局,思考问题,解决矛盾,重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这一思维方式,从思想来源上看,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给予邓小平的影响,一方面来自他所长期生活的中国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则来自他所读过的中国古代学术典籍(注:邓小平与中国古代学术典籍的联系问题,由于缺乏文献的记载,长期以来是邓小平思想研究的一大难题。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邓小平的子女在回忆中说:“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家里有两套,其中一套是线装本。《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应该叫熟读。他通读《二十四史》,喜欢里面的前唐书和后汉书。老爷子还特别爱看《三国志》。”(《伟人家中的追忆--邓小平亲人访谈实录》,《光明日报》2004年8月15日)这就生动而具体地说明了邓小平与中国古代学术典籍的密切联系。)。这两种思想来源的结合,这两大智慧的融汇,使得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既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邓小平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继承、吸取与改铸,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并以此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与历史创造,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思维方式的中国特色和思想贡献。
一、毛泽东与邓小平:中国辩证智慧的两种类型
辩证思维方法的核心,就在于对矛盾的认识、把握与解决。列宁曾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12)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强调:“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299)他的哲学名篇《矛盾论》,就是专门阐发对立统一法则、探讨矛盾问题的。而与列宁不同的是,毛泽东在思考矛盾问题时,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国化了。邓小平则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思想家。但他不是重复毛泽东的思想,而是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可以说,毛泽东与邓小平分别继承、吸取、改铸了中国辩证思维的两种传统,分别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智慧的两种类型。
在矛盾问题上,邓小平与毛泽东都典型地表现出一种中国哲人所特有的辩证智慧,他们都认肯矛盾在宇宙人生中的普遍存在,重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现实的矛盾,反对以凝固的、僵化的、片面的眼光来看待、处理矛盾;但在对现实矛盾的把握与解决上,毛泽东重视矛盾双方的转化及其斗争在促成矛盾双方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中的作用,强调一方最后吃掉另一方。而邓小平则重视矛盾双方的联结,并使其达到谐和,由谐和来缓和矛盾、化解矛盾,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可以说,毛泽东与邓小平表现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两种不同类型。
毛泽东与邓小平在辩证思维上的同与异,都可以在中国辩证思维的历史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思想根源,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中国辩证思维的特点与传统。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辩证智慧,在思维方法上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以及那些聪明的政治家,往往都注意到对立面双方的“相反相成”;但对于这种“相反相成”,有的强调在斗争中促成双方转化,有的则主张求得双方谐和。前者凸出一个“争”字,要求人们在“大争之世”(《韩非子·五蠹》)“不畏其争”(《周易外传·未济》),通过斗争实现矛盾的转化。后者则凸出一个“和”字,要求人们既不要“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追求没有差异、没有矛盾的同一;又不要“反中庸”(《中庸》),使矛盾的双方因斗争而不可调和,非要一方吃掉另一方不可。毛泽东更多地受到前者的影响,邓小平则更多地受到后者的启发。
承认矛盾双方的“相反相成”,进而主张求得双方的谐和,以谐和来缓和、化解矛盾,这一辩证思维方法可以说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晚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著名命题,认为把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能产生新的事物,而把相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则不能产生新的东西。孔子进而把这一思想方法发展为主张“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强调“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力主“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以后,《中庸》更把中庸之道提到了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高度,作了相当明确的表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至北宋的张载,更有“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的说法,典型而系统地表达了这一辩证思维方法。这种和而不同、以和解仇的辩证思维方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智慧,但同时又多少蕴含有一些片面的因素和保守的成分。因为现实中的矛盾在性质上、结构上、演变上是极为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的矛盾双方都能“仇必和而解”的。试图用“仇必和而解”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矛盾,是不现实的。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而不同、以和解仇的辩证思维方法,邓小平结合现时代中国和世界的大势和现实,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重新加以了继承、吸取与改铸,化原有的片面的、保守的因素为全面的、积极的因素,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和解决现实矛盾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在长期的实践中,他把这种思维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切实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重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起了重大作用。
二、邓小平的辩证思维方法的历史形成
邓小平对于和而不同、以和解仇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继承、吸取与改铸,严格地说,并非始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目前公开发表的邓小平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早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激烈化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已经十分重视在矛盾双方的“相反相成”中求得矛盾双方的谐和,以谐和来缓和、化解矛盾。
在写于1941年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中,邓小平对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三三制政权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生动地体现出他的这种辩证思维方法。邓小平指出:三三制政权,其实质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8)然而,在三三制政权中,在共产党员、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各占三分之一的行政机关和民意机关中,如何看待和处理其中各阶级各派别间的矛盾问题,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对此,邓小平并没有掩盖其间的矛盾存在,也反对仅从消极方面来看待这些矛盾,而主张以和而不同、以和解仇的辩证思维方法来对待这些矛盾。他指出:“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既是在政权中有各个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9)在对待参加三三制政权各阶级各党派的政策上,他主张“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级,还要照顾那一阶级……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9)对于行政机关和民意机关的党团工作,他提出了“要民主”和“要能团结人”的要求,认为:“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一般问题也要尽量征求非党干部的意见,取得大家的同意。”(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7)“每个党员都要接近非党员,在政治上去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同他们一块工作,一块学习,一块讨论问题,避免过去党员与非党员格格不入的现象。特别对于中间分子士绅名流,尤为重要,过去我们同志对进步分子都团结不好,对他们更差了。我们同志的态度要谦和,要诚恳,要尊重其人格,尊重其意见;不要锋芒毕露,自以为是政治家,而要善于根据不同对象去进行政治解释工作。感情的联络也是必要的,因为这对政治上的接近是有帮助的。”(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7)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善于和而不同、以和解仇,才能建设好三三制政权,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开辟道路。
在写于1943年的《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中,邓小平对建设根据地工作中的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关系的论述中也体现出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在团结地主阶级抗日的问题上,邓小平就反对对地主采取一味坚决斗争的方式。他主张,在经济上,“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在政治上,“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他说:“团结地主抗日,只靠方式上的讲究是非常不够的,主要应使之能够生活,能够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其合法的财权,否则即使我们态度很好,即使选他当了代表和参议员,都会无济于事。这点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应加以注意。”(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p.71-72)对于对待地主问题上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就“群众‘左’可怕不可怕的问题”作了专门分析,指出:“只有当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左’的现象时,‘左’才是不可怕的,如果让‘左’的东西发展到破裂统一战线的地步,那就是值得可怕的。”(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72)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从反对“左”的错误倾向的高度,阐明了在革命斗争实际中运用和而不同、以和解仇的辩证思维方法的重要性。
在1948年所作的《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中,他更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革命战争中的“左”的错误倾向问题。他尖锐指出:“‘左’的倾向,表现在土改中划阶级‘左’,把地主富农同样对待,侵犯中农,对中农采取拒绝态度;新区工作中犯急性病,打击面宽,工商业政策‘左’。这个‘左’由来已久,抗战八年,工商业政策就有‘左’,对中央的有关指示、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未能认真研究执行,结果是打击了我们自己。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偏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04)在报告中,邓小平专门就“杀人问题”讲了一段话,坚决反对“左”的错误倾向指导下的乱杀现象。他说:“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人,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失悔。说明错杀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03)在这里,邓小平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左”的错误倾向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反省,强调了即使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也不能简单地以一方吃掉另一方来解决矛盾。
邓小平的上述论述,都是以革命战争时代前线高级指挥员的身份讲的。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尖锐化、白炽化的战争时期,邓小平也总是尽可能地避免激化矛盾,避免用斗争和暴力解决矛盾,而力求尽可能地缓和矛盾、化解矛盾,从而达到更有利于革命胜利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独特的辩证思维方法,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当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在范围上、深度上都是有限的。在那个年代里,支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法,是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方法。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方法,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的需要,并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曾对自己的辩证思维方法做过调整,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终未能作一种根本性的改变。这就为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全面展示自己的辩证思维方法留下了空间。
三、邓小平辩证思维方法的全面发挥
邓小平独特的辩证思维方法的全面发挥,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他在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活动中,对自己独特的辩证思维方法做了多方面的阐发和运用,重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开拓了社会主义中国通向新的胜利之路,显示出他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位善于从中国全局和世界全局上把握矛盾、解决矛盾的能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高举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旗帜,要求恢复毛泽东当年提出但又未能实现的政治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44)“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44-145)在这里,他以自己独特的辩证思维方法,要求改造长期以来支配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法,即从实际出发,可以用谐和化解矛盾的方法决不用以斗争解决矛盾的方法,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的拨乱反正。而在以后的许多工作中,邓小平都力求以这一辩证思维方法来把握、解决矛盾。
在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上,邓小平提倡百花齐放,反对一花独放。在1979年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210)这一思想对于调整文艺政策、繁荣文艺创作,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新时期的经济生活中,邓小平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对立、水火不容的看法,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早在1985年,他就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p.148-149)在1987年,他又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203)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373)由此,而产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概念,促成了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
面对20世纪末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力图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一个较长的和平环境,力主寻找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途径。他认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比之用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仅有利于各方,而且有实现的可能。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49)因此,他反复申明:“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88)“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104)“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96)为了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他强调“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国与国的关系,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以对抗的方式、以双方互赢的方式而不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方式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正是这一新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现实运用,使得社会主义中国在20世纪末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成功地生存和发展起来。
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邓小平根据他的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作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途径。所谓“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58)换成邓小平的哲学语言来表达,就是矛盾的双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相反相成”的状态,谁也不“吞掉”谁,谁也不“吃掉”谁。这也就是用一种和而不同、以和解仇的方法来逐渐缓和、化解矛盾。而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现实根据就在于:“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59)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59)对此,邓小平作了许多相关论述,具体阐发了这一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构想。在台湾问题上,他说:“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59)“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30)“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49)在香港问题上,他说:“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58)“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221)他反复强调,“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决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将在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并以基本法的形式加以保障。他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215)这之后香港和澳门的胜利回归,都有力证明了邓小平这一构想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这一辩证思维方法的智慧光辉。
四、邓小平对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方法的改铸
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的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并不是简单地因袭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以和解仇。他固然凸出一个“和”字,强调矛盾双方谐和的意义,不主张以一方吃掉另一方来解决矛盾,但并不意味着因此而害怕斗争,更不意味着要以牺牲原则为代价来换得矛盾双方的谐和。在这里,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精髓,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以和解仇的辩证思维方法作了重新改铸,主张在求得矛盾双方谐和时不应作无原则的妥协与退让,在实现矛盾双方的谐和时必须使自己的一方处于优势地位,在矛盾双方的谐和不得已破裂时要敢于通过斗争解决矛盾。
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在强调建设三三制政权的同时,又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三三制政权中的领导权,指出在三三制的“和”中还存在着“争”。他对此做了具体的分析:“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所以产生了我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优势从何而得?一方面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这在三三制原则本身是包含着的;但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9)
又如,在新时期对外开放问题上,邓小平在强调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努力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附庸,申明中国决不屈服于西方国家的压力。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3)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面对西方国家以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的制裁,他坚定地宣称:“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329)“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359)在这里,邓小平同样凸出了一个“争”字。
再如,在“一国两制”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在香港、台湾地区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又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强调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性,坚持中央人民政府对特别行政区的某些权利。他明确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219)又指出:“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221)香港回归后的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这些论述确实是正确而深刻的。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辩证思维方法,并不是一味追求和而不同、以和解仇,而是在凸出“和”的时候又没有放弃“争”,在显出“柔”的时候又蕴含着“刚”,是和不舍争、柔中有刚,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就是“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p.348)。在这里,显示出邓小平的辩证思维方法与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方法之间又有着一种内在的继承性。看不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继承性,只看到他与毛泽东的差异性,是不能真正理解邓小平的辩证思维方法的。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方法与邓小平的辩证思维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积极成果,都是今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标签:邓小平文选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邓小平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毛泽东论文; 时政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