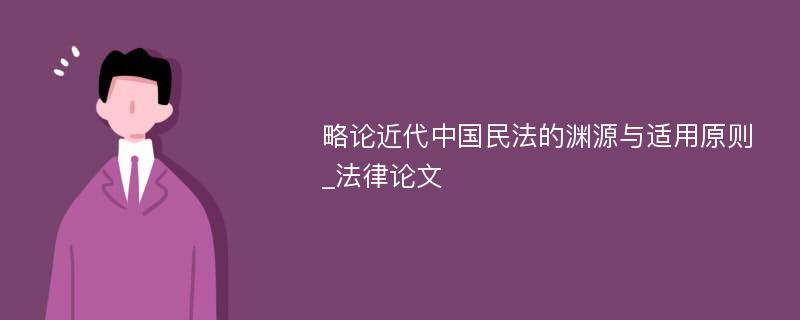
近代中国民法法源及其适用原则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法论文,原则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法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是我国由传统民法向近现代民法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们今日民法的发展方向。清末《大清民律草案》的修订,开启了我国民法近代化的先河,翻开了中国民法发展的崭新篇章。《大清民律草案》第1章《法例》第1条规定的第一个统领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关于民法法源及其适用原则。本文拟就此原则在中国近代民法史上的确立及传承发展过程作一探讨,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由此以总结此项原则发展沿革中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接引历史之烛光照当下之现实,从而为我国现今将制定的民法典提供历史的鉴镜。
一、《大清民律草案》关于民法法源及其适用原则规定
《大清民律草案》第1章《法例》第1条规定:“民事本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依条理”,从而确立了此项原则作为统领中国第一部民律草案的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依该条规定,我们可明晰《大清民律草案》将习惯法与条理作为制定法之外的重要的法律渊源,作为制定法之外的可资援用的重要补充。法律渊源是指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知道社会经济关系丛杂万端,法律规定纵详,亦难综括无遗,而审判机关又不可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审理民事案件,因此引入习惯法与条理作为制定法的重要补充非常必要。
《大清民律草案》第1条虽规定了习惯法与条理作为制定法之外的重要法源,但是何谓习惯法,何谓条理,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律文中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解说。“习惯法”与“条理”都是过于笼统与抽象的概念,因此在我们进一步探讨此原则的发展前有必要先对其有所理解和定义。
众所周知,丰富的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孕育了“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无论是封建法典的源头《法经》,还是成就中华法系的《唐律疏议》,及至封建法典之大成的《大清律例》,都是“以刑为主”,但中国古代毕竟还是有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其固然缺乏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独立的成文法,但这方面的习惯法还是相当丰富的。正如台湾戴炎辉先生所言:“各朝代的实定法偏重于刑事法,其关于民事法的部分甚少,大率委于民间习惯法。”(注:戴炎辉:《中国法制史·自序》,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
同时由于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无讼”一直是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因此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细故”、“细事”的“户婚田土”等事都由民间调处,而民间调处大多依据以“乡例”、“俗例”、“乡规”、“土例”等小传统表现出来的习惯法来调整。我国学者梁治平先生在对清代民事习惯研究后,认为习惯法乃是在乡民长期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地方性规范;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习惯法并未形诸文字,但并不因此而缺乏效力和确定性,它被放在一套关系网络中实施,其效力来源于乡民对于此种“地方性知识”的熟悉和信赖,并且主要靠一套“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有关的舆论机制来维护。(注: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与习惯法极易混淆的概念“习惯”。梅因认为,“‘罗马法典’只是把罗马人的现存习惯表述于文字中”。(注:[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页。) 就美国的普通法而言,法学家认为,“先例的背后是一些基本的司法审判概念……,而更后面的是生活习惯、社会制度……。通过一个互动过程,这些概念又反过来修改着这些习惯和制度”。(注:[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页。) 如前所述,在我国古代民法中民事习惯在维护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秩序中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制定法之外发挥着重要的调整作用。诚如一位学者所言:“习惯历来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一直受到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法律家、法学家的高度重视。”(注:苏力:《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习惯——一个制定法的透视》,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3期。)
那么习惯与习惯法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以下的论说中可以有所领会。“普通习惯只是生活的常规化,行为的模式化,习惯法则特别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关系彼此冲突之利益的调整。……普通习惯很少表现为利益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单纯之道德问题也不大可能招致‘自力救济’一类反应,习惯法则不同,它总涉及一些彼此对应对立的关系,……习惯法比较普通习惯更具确定性和操作性,也更适于裁判”。(注: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民事习惯’不等同于‘习惯法’,不具有普遍的规范效力。……被认证为‘习惯法’的民事习惯,在内容上,已经不是单纯的固有民法,其中包含了继受民法。‘习惯法’实际是固有民法与继受民法的复合体,是新的民事整合规则”。(注:张生:《民国初期民法的近代化——以固有法与继受法的整合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 关于习惯与习惯法的问题在下文中还将有所涉及,随着时间的移异,历史为我们展现了更好的理解与掌握其中差别的依照。
关于何谓条理,《大清民律草案》总则编第1章按语中的解说是“条理者,乃推定社交上必应之处置。例如:事君以忠,事亲以孝,及一切当然应尊奉者……”,由此可知《大清民律草案》的起草者认为条理就是情理,意在把条理解释成社会生活中处理事务当然之理。众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法学理论薄弱、司法实践贫乏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立法者在不知不觉间,将本民族的法律精神渗入到外来法的条文之中了。由此也可知《大清民律草案》的立法者将“条理”规定为制定法之外的补充,其实是旨在为传统法律入律提供便捷的途径。但“条理”在后来实际运用中的功能效用却与《大清民律草案》立法者的本意大相径庭,关于此点在后文中将继续讨论。
二、近代西方民法典关于民法法源及其适用原则规定
《大清民律草案》将习惯法与条理视为制定法之外的重要补充,一方面是由于民事习惯在我国古代民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多的原因则是其对当时的《瑞士民法典》的仿行,将条理作为法律的渊源之一更是这种仿行的重要表现,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本原则在西方的发展演进。
近代民法肇始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制定的民法典,尤以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为代表。法国于法典编纂前,习惯是重要渊源,立法运动后法典成为惟一的法律渊源。但随着法典的老化,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又重新恢复,现代法国学者则“把法律的第一渊源的位置让给习惯法,因为法的这一渊源具有广泛性、概括性甚至现实性”。由于“法律远不是一个凝固的系统,而且具有变化的固有属性,……用‘习惯法’这一词来表述这一不断改变社会关系的、既有破坏性、又有创造性的作用引申义并不过分。在这一广泛的含义中,习惯法在暗中制定新的法律,它是法律规则的生命力,它的应用范围是无限的。它并非是法律各种渊源中的一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法律的惟一渊源”。(注:[法]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德国民法典》对民事习惯的效力未作一般性规定,仅在第157条和第242条规定,解释契约和履行契约应顾及交易上之习惯。(注:该法第157条规定:“解释契约,应该按诚实与信用原则,并且顾及交易上之习惯。”第242条规定:“债务人有义务,在履行给付时,应按照诚实与信用原则,并且顾及交易上的习惯。”)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对极端理性主义的信仰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立法技术经验多种因素混合而成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部民法典制定时对民事习惯的态度或是漠视或是暧昧,实际上,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民事习惯仍起了重大作用。以法国民法典为例,立法者在编纂时极其注意成文法与习惯法“理智和平衡的调和”,并在其家庭法和继承法中广泛吸纳了民事习惯,尤其是巴黎的地方习惯。(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165页。)
19世纪历史学派学说渐盛,排除成文法万能的思想。20世纪的第一部民法典《瑞士民法典》首先规定了习惯法具有补充法律的效力。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1条规定:(1)凡本法文字或释义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2)无法从本法得出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习惯法裁判,如无习惯法时依据自己如作为立法者应提出的规则裁判;(3)在前一款的情况下,法官应依据公认的学理和惯例。《瑞士民法典》作者欧根·胡贝尔就第1条提出的立法理由这样说道:“诸国相互交融如同个人往来般重要,从而不应使内国立法如中国长城般地拒斥外国立法例之流入。”(注:黄建辉:《法律漏洞·类推适用》,台湾蔚理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这表明立法者在重视习惯法作为法源所发挥的重要补充作用的同时,还确认了由法官作为立法人并通过这一媒介引入外国立法例以弥补现存法律不可避免而存在的漏洞。对此有学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大陆法系第一次正式地、旗帜鲜明地承认了法官立法,……在大陆法系的历史中,它第一次公然地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司法过程中来,以补规则因素之不足,因而第一次采用了以民法基本原则处理法律局限性的模式”。(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 民事案件是千变万化的,不像刑事案件那样只限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那些种类。法律要把民事案件规定得没有遗漏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民事案件,法官又不能不办。《瑞士民法典》直接规定法官可以“作为立法者”规则并据以裁判。这确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规定。这个规定不仅在它以前和当时是没有的,就在它以后也没有,真可谓是“空前绝后”的。(注: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茨威格特和克茨虽然说,《瑞士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没有包含任何新意”,但终究不得不承认,这一条仍然是“令人惊异而赞赏的”,因为它“在清晰了然的位置,并以鲜明出色的语言形式表达了这种思想”。(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页。)
《瑞士民法典》第1条具有开创性的规定为后来许多民法所效仿。如,《土耳其民法典》第1条:“本法,支配本法文学上或精神上所包含之一切事项。于无可适用之法规时,审判官应依习惯法。习惯法亦无规定时,应依己身为立法者所应设定之法则裁判之。审判官应于其判决利用学说及判决成例。”《泰国民法典》第1条:“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第13条:“诉讼事件,无可适用之法律时,适用习惯。”此外1945年《意大利民法典》、1985年《荷兰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都是其的摹仿者。这些具有相似的形式和内容的摹仿综合说明了由于社会生活情状的变幻多姿,复杂万端,如欲以制定法穷尽所有社会关系,固不可能,因此还需相应的习惯法予以补充,同时也是对出于自然交往中形成的习惯的尊重,从而更好的调解调整社会生活。
三、我国近代民法对民法法源及其适用原则的传承与发展
民国初年,百废待兴。在清末修订的民法草案,在民国创立之后便被束之高阁了。但在民法典付阙的情况下,民国参议院于1912年4月3日开会议决:“嗣后凡关于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注:《中华民国民法制定史料汇编》(下册),台湾地区“司法行政部”1976年版,第2页。) 即依据《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处理。我们知道《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只简要地规定了户役、婚姻、田宅、钱债等民事内容,已经不能适应鸦片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多种繁杂的社会关系了。为此民国初期通过大理院的判例解释例要旨汇编,对其适用的民事法律渊源及各法源的援用次序逐一加以解说。大理院开院以来所为的第一个民事判例(大理院1913年上字第三号判决)就是关于“习惯法成立之要件”的著名判例,其判例要旨曰:“凡习惯法成立之要件有四:(一)有内部要素,即人人有确信以为法之心;(二)有外部要素,即于一定期间内,就同一事项反复为同一之行为;(三)系法令所未规定之事项;(四)无背于公共之秩序及利益。”(注: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会文堂新记书局1932年版,第29页。)
民国初期,条理作为次于制定法与民事习惯的第三顺序的法律渊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旧中国最高法院(即大理院)在它成立的第二年即1913年确立了一个原则,规定在无法律和习惯法可依的情况下,民事案件的判决必须依据一般法律原则(条理)。由于当时《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对于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民事关系,已不足用,而且固有传统一直在亲属法和继承法的某些领域禁锢人们的思想,在此种情况下,各级法院大量适用大理院判例,而大理院的这些判例即是大理院的法官们依据有效法律以及条理制作的。所谓条理,在此时已被赋予为大陆法系民法的原理、原则和立法精神的内涵,也就是根据《大清民律草案》里所体现的从大陆法系移植的法的理论。因此可以说条理在民国初期充当了一种媒介桥梁作用,它通过当时一些受过西方法学系统教育的法律家的学习接受,逐渐将西方民法的法律思想引入中国。通过法学家引入西方民法思想是一种具有合理性、妥当不生硬、略具柔性的引入方式,这种方式更好地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因此从此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条理是当时间接采用西方民法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输入西方民法为我所用的一种委婉的方式。前文提到《大清民律草案》按语中将“条理”注释为“事君以忠,事亲以孝”的情理,而此时其所负载的法律涵义已与当初制定者的本意完全背离了,成为西法入律的便捷途径。
由于制定法、习惯法与条理在具体的司法运作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竞合与冲突,大理院为具体适用《大清民律草案》第1条,还创制了法源“援用之次序”判例,其要旨曰:“法律无明文者,从习惯;无习惯者,从条理。苟有明文足资根据,则习惯及通常条理自不得援用。”(大理院1915年上字第122号)由此可知,《大清民律草案》第1条民法法源及其适用原则在民国初期是由大理院通过判例加以确认、适用的。
1925年完成的民国时期的第二部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删除了《大清民律草案》第1章《法例》,从而使得这一原则在正式制定的民律草案中芳踪难觅。有学者品评认为民法法源及其适用原则“内容虽然简短,却使民法典成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在法典没有明文规定的时候,可以引入习惯法、条理作为民法规则;……删除该条,将置民法典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无法从现时民事生活、私法学说中获得发展的动力”。(注:张生:《民国初期民法的近代化——以固有法与继受法的整合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186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的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大清民律草案》第1条在此部民法典中被稍作修改为:“民法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或虽有习惯而法官认为不良者,依法理。”并规定:“凡任意条文所规定之事项,如当事人另有契约,或能证明另有习惯者,得不依条文而依契约或习惯,但法官认为不良之习惯不适用之。”由此可看出中国第一部正式通过的民法典肯定了此项原则规定的价值,从而予以传承。其虽然对习惯有所限制, 但仍然予以重视并依旧列为制定法之外的重要法律渊源。 这部民法典一直适用于我国台湾地区,1982年台湾修正公布后的“民法典”,仍在第1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又在第2条中规定:“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台湾修订的“民法典”还在专门用以说明确立民法原则的理由中,强调了习惯的重要性:各国民法“要皆各按己国风俗习尚之情形,而异其编制。”并说明对习惯略加限制的理由:“谨按我国幅员辽阔,礼尚殊俗,南朔东西,自为风气,虽各地习惯之不同,而其适用习惯之范围,要以不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庶几存诚去伪,阜物通财,流弊悉除,功效斯著。此本条所由设也。”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第7条规定:“民事案件,无法律或国家政策可供适用时,适用社会公德和国家经济计划。”这两条规定了我国在制定法之外民事活动允许以一定范围的其他规范作为补充渊源。我国《民法通则》的制定借鉴了世界各国民事立法的先进经验,尤其借鉴了大陆法系各国成熟的立法经验。并且,由前述对外国关于法律渊源的规定,我们可看出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第7条的规定方式与泰国、我国台湾地区相同,不过前者规定的补充渊源为国家政策、社会公德、国家经济计划,后者规定的补充渊源为习惯、法理而已。(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这说明我国《民法通则》对《大清民律草案》民法法源及其适用原则予以一定程度地继受。
综上所述,民法法源及其适用原则自《大清民律草案》第1章《法例》规定以来,沿革至今,其具体内容虽然随时间的洗礼多有变迁,但其所具有的重要规范意义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效用,可概括为:(1)规定民事(私法关系)的法源及其适用次序;(2)就法律思想而言,综合汇集了分析法学派(法律)、历史法学派(习惯)及自然法学派(法理)对法及法律的见解;(3)就法学方法论而言,克服了19世纪的法实证主义,肯定制定法的漏洞。明定其未规定者,得以习惯或法理加以补充。法院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注: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页。)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称其为是民法典的生命源泉,只有有了此项原则的民法典才能适应不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同时兼顾到在一段时间内因客观发展规律而留存的民事法律关系。
自19世纪末叶以来,我国社会关系的变迁,日益加剧,仅凭有限的民法法条,终难适应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与其削足适履,毋宁使执法者于法律之外,通过习惯与法理寻求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适当的行为准则。如学者所言,“民法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准则,传统习惯中含有许多为民众世代相传的生活准则,这些准则具有稳定性和深入性的特点,吸人民法之中,有利于民法深入人心,为大众所接受掌握。当然,传统习惯又多具有滞后性和保守性的缺陷,有的还具有分散性缺点。这些缺点不适应人民群众生活发展的需要,甚至会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这又是我们制定和修改现代民法时所应注意的。(注:刘广安:《中华法系的再认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通过在民法典中设置民法基本原则的方式,规范其它民法法源拾遗补阙民法有限法条的漏洞,并对其具体适用的次序加以规范。同时对于所采法源予以界说与甄别,严密规范与界定,谨忌扩大原则本身所固有的弹性,最终达到丰富民法典的内涵与适用价值的民事立法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