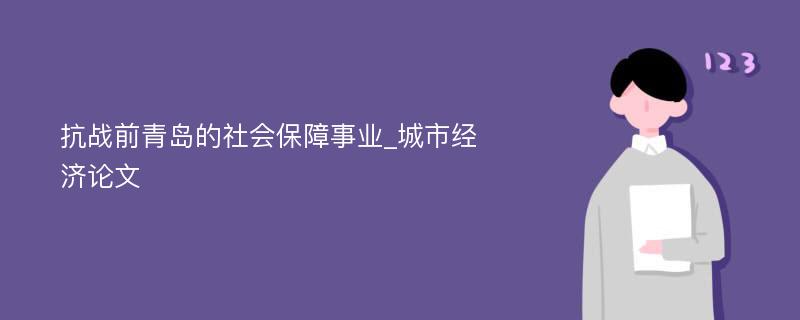
抗战前青岛的社会保障事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岛论文,社会保障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工商业是近代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话,那么社会保障则是缓解风险、促进公平的一种稳定机制,两种机制交互作用,促进了城市的和谐与发展。青岛是德国人占领之后,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建立起来的一座近代城市,社会保障事业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是同步的,其特殊的城市发展道路决定了其社会保障模式的典型性。本文拟结合青岛的社会变迁概况,论述1898—1937年间的社会保障事业,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出社会保障也是城市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
一、动因和条件
“一种制度的确立与变迁,往往服从于特定时代的需要”。[1](P1) 近代社会保障事业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背景之下。一开始就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青岛,1898年开埠后,很快就从一个荒僻渔村成长为数十万人口的通商都会,建立近代社会保障的条件也逐渐成熟。
1.建立近代社会保障的必要性
近代中国沿海城市经历了由封建性的商业贸易口岸到半殖民地性质的商业贸易港口城市、再到工业港口城市的轨迹,只是青岛历史的逻辑发展进程更短些、更快些。在城市转型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对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许多人不可避免被抛离正常的生活轨道,陷入困境。但这对于青岛并不明显,其病态现象更多地表现为外来性。近代山东乡村经济破产、社会失衡、贫民生计艰难,辗转谋生,加之各地灾祸连连,灾民流离失所,四处逃难。青岛因地理和交通便利,自然成为他们的避难所和闯关东的中转站,其中一些人或乏川资或不堪旅行等而不得不“羁留于此”。但城市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毕竟有限,致使大量的结构外边缘人口无法被近代工商业所吸纳,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1930年,市公安局曾对马虎窝等9处外来贫民集中的地方做过调查,其中极贫和次贫几近千户,极贫者大多乞讨为生。[2]
外来谋生者的不断涌入,不可避免地带来失业、贫困以及拥挤等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城市病。近代青岛埠头繁盛,工厂林立,工人“一经失业,动数万计”。1929年7月,日资钟渊、内外棉等六家纱厂工人因整理工会运动引起了资方的嫉恨,随酿成罢工风潮,被解雇者200余名,暂时失业者则达数千人之多。[3](P1) 而且,各企业均奉行低工资政策,许多工人无法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要靠妻子或儿女工作才能维持;至于数万名手工业工人、矿工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劳动条件艰苦,所得一般低于产业工人,收入微薄,生活处于绝对贫困的境地。[4](P675)。
平民住宅缺乏也是青岛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顽症。住房不仅仅是个遮风避雨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既可以提供和“家”连在一起的安全感,也可以促进移民与社区、邻里的融合以及归属感,增强人们的城市认同感和责任感。最初当局只着眼于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未认真考虑平民住宅问题。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人多房少的矛盾日渐突出,致使房屋租金高昂。1920年代,房租每间每月达4~5元,一般工人和职员等尚感吃力,至于苦力、摊贩以及其他无固定职业者更是不敢问津,只好于偏僻污秽之处搭盖窝棚暂且栖身。正如《胶澳志》记载:“市内贫民,大部麇居于台西镇之挪庄、西广场等处,矮屋一椽,仅能容膝,起卧炊涤胥在其中,甚者支板为棚,合居三四,既虞火患,更碍卫生”。[5](卷三,民社志P73) 尽管棚户区不像上海那样鳞次栉比,但若考虑到青岛的城市规模,确实也非常可观。
2.建立近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可行性
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青岛开埠后迭经内外战乱,缺乏持续发展的环境,但毕竟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的资源、广大的经济腹地和较好的商业贸易基础,开埠后三四十年时间内就迅速发展成为山东的经济贸易中心、全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以及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整个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加之青岛地位特殊、外侨众多,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吸聚效应”,吸引着各地资本的流入,从而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而近代经济的滋长,意味着社会分化的加快,贫者愈贫,富者愈富。1929年,该市社会局就指出:“我国素称贫富悬殊,而青岛为最,富者高楼大厦,丰衣美食,贫者号寒啼饥,不得一椽之庇”。[6](P24) 若不加以适当的调节,则势必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而社会保障制度则是基本的稳定手段之一。
如果说乡民更多地认同血缘组织的话,那么逐渐摆脱了血缘羁绊的移民,在重新寻找自身利益的承载体时,就自觉不自觉地视结社为化解生活风险的重要手段。于是青岛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城市互助活动的开展。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和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进步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尽管青岛报刊均属地方性的,发行量小,影响范围有限,政治倾向也各不相同,但对于社会事业均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发挥着社会动员的功能。诸如报道不幸者的悲惨状况、呼吁社会资助等。[7]
在传统社会,赈灾与济贫等不过是在恩恤和慈悲观念支配下的一种施舍行为。近代以来,西方主权在民的思想经过辛亥革命的实践进一步深入人心,国家逐渐承认了获得救济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尤其是南京政府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相标榜,先后颁布了一些社会政策和法规。责任与义务等也频繁出现在地方当局的话语之中。1929年,青岛市社会局在谈及保障问题时指出,社会稳定以及社会和谐“宜以人群之生活为前提,救济事业,即为最低之生活不能维持,不得不予以援助,以期造成健全社会”,政府“应本总理普救之真义,谋全市社会之幸福”。[8](P5)
青岛移民以青壮年为多,长期的殖民统治和二等公民的地位,增强了其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救济思想不再仅仅停留在道德和宗教的层面上,而是逐渐升华至爱国主义的高度。每届募捐,发起者就张贴标语,其内容如“捐款助赈为国民应尽的义务”、“救济被难同胞是我们应尽的天职”等。[9] 事实证明,爱国情结和同胞观念确实也激发起了市民的捐献和参与热情。很多人还从社会连带责任的角度指出,扶危济困不只是个人的善举,也是一个“民族之文野”的重要标志,若要加快整合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社会事业就须“尽量的发展”。即使以营利为目的工商企业,也接受了近代的社会平等理念。青岛华新纱厂就认为,生活提高乃人生之幸福,“但必须为普遍之进步,而非畸形之发展”。工厂不能把工人当作生产工具,应视“其同为国民一份子,或出资或服役,或劳心或劳力,所事不同,而同为国家服务,为民族服务”。[10](P55)
二、多元的保障主体和措施
近代社会保障是由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所组成的体系,迥异于传统的慈善救济事业,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青岛并未认真推行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保险事业,济贫、互助和福利等方面则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色。
1.积极济贫、教养并举
政府是济贫的责任主体。殖民统治时代,当局于中国人的福祉并不热心,1922年中国政府接收后,市政当局加快了社会事业建设,专门的救济机构逐渐设立,促进就业和减少贫困的政策发挥相继颁行,济贫活动日渐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作为传统的救济力量,善团广泛存在于任何地区,不过青岛的善团成立时间晚、数量少,从1914年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成立伊始,到抗日战争前夕也仅有数家而已,且不说无法与省城济南相提并论,甚至还不如济宁、临清等日趋衰败的运河沿线城镇,但各组织会员众多,且多出身于工商界,募集善款相对便捷,这是省内其他地方的善团所难以企及的。1933年,世界红万字会青岛分会共收到会员以及各界捐款75000余元,其中商界领袖、该会会长丛良悟一次就捐助大洋5000元。[11](P1—19) 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流行,青岛女性的社会参与意识也日渐高涨,并选择了慈善活动作为突破口。1930年,丛世俭等人发起成立世界妇女红万字会青岛分会,“以维女权而利慈务”,到抗战爆发时,会员(包括女道德社社员)已达500余人。[12](P242)
青岛一开始就定位在工商业和港口上,近代都市化、工业化和商人阶层的形成几乎是同步的,与传统城市中官僚与士子占据统治地位,商人被排挤到不被重视的角落相比,青岛商人阶层及其代表商会不但是市民社会的中坚,且在慈善公益事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8年6月,总商会鉴于游民充斥市面,“对外观瞻,殊觉有碍”,于是发起创办贫民习艺所,收容市内青年无业游民,授以工艺,“俾克自谋生活”。1926年5月,经商埠局批准,在帆船(或称风船)、屠宰、 煤炭和火车装运业项下征收慈善附捐,1931年后,商会以“事关公益、且系成案”,决定继续征收,并另案存储,“专备拨充各项慈善款项及协助救济院之用”。[13] 这些都是济南商会所从未做过的,充分显示了青岛商会在社会保障事业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局有意识地让渡活动空间,则进一步增强了其在社会保障事业上的发言权。德国占领期间,殖民当局就授权中华商务公局就华人之房“酌收捐资”,办理慈善事业等。[14](P9) 1922年后,市政当局仍对商会寄予厚望, 甚至连刚成立的官办救济机构也转交与商会来管理,并通过授权的方式,明确了其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国民党当局虽然制定了比较详细的社会保障发展规划,但这并未削弱商会在社会事业中的主体地位,一般的救济活动仍尽量委托商会办理。
当局以及社会各界也意识到,单纯的散衣给食只能救济于一时,根本无法提升弱者的生存能力,甚至会给社会造成负担,要想“救人救彻”,就应培养其谋生本领。因此,救济院对于所收养的孤老、残疾、幼弱以及不幸妇女等,除供给衣食外,根据各自的生理特点,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等,妇女从事纺织、缝纫,孤儿则授以织袜、木器、毛巾等工艺。[15] 这样,他们感到不再是社会的累赘,获得了做人的尊严。
在近代城市中,有职业即有保障,失业是劳动者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促进就业、减少失业就是济贫的第一要义。市政当局先后设立非盈利性质的职业指导所、职业介绍所和失业工人传习所等,并与职业补习学校合作,对缺乏职业技能者进行培训,以提高其求业能力。针对不少贫民做小本买卖谋生、但又缺乏资本的现实,一些救济机构开办了小本贷款业务。1927年,世界红万字会青岛分会创设因利局,“放借资本”,小本营生者每次可借3元,整借零还,“概不收取利息”。[6] 1932年1月,市政府筹集基金1万元,在救济院内设贷款所,凡小本营业者每人每次可贷1至10元,借期3个月,分期偿还。1935年1月,市政府又拨款3万元,银行借拨12万元,组成小本借贷处,低利借给本市小本工商业者。[17](本市法规P2) 筹设公典“以便利贫民,抵制外商高利”。典当原为宗教机构所创办,最初本属慈善事业的一种,后富商大贾见有利可图,竞相开设,于是沦为盘剥贫民的工具。作为一个商贸城市,青岛的银行和钱庄等金融机构并不对贫民放款,贫民只好靠典当来应急,尽管利息高、条件苛,但它对物信用,人们可随时质当,比较方便,若加以整理,限制利息,仍不失其救济之价值。不过,张宗昌祸鲁时期,滥发钞票,擅加当税,青岛华人当铺相继歇业,日商见有利可图,乘机开设,月利最高竟达7分,期限仅有三个月,“压迫贫户,莫此为甚”,贫民为生存计,又不得不饮鸩止渴。筹设公当,就有方便贫民、抵制日商欺压的双重目的。初市政府拟与当商合办,“辅以官款”,名曰“公典”,后商会鉴于合办之弊端,乃自行集资6万元,呈请改为商办,在“不悖公典宗旨”的原则下获得了当局许可。[18](训令P36)
2.社会互助
在中国传统社会,血缘和地缘是建立一切信任关系的基础。青岛移民来自四面八方,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流动频率加快,成员之间的异质性不断扩大,血缘关系日益让位于以业缘、趣缘为主导的新型社会关系,加之社会阶层之间、同一阶层内部的差距拉大,乡村社会中那种一家有难、邻里或宗族伸手相助的风气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而公共救济资源又十分有限,人们一旦陷入困境,往往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以互助的方式、以集体的力量来抵御各种风险则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
一是同乡组织。青岛各地移民出于生存的需要,很快就自发地按籍贯组成了同乡组织。据调查,1927年有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广东会馆、宁波旅青同乡会、高密旅青同乡会、平度、即墨、临沂等19个同乡会。1930年代初,又增加了两湖、江西、河南、河北、兖济等同乡会。各组织无不将“敦睦乡谊”,办理慈善,援助失业同乡和举办社会公益等列为主要活动。[19](第五编公益性政P6—8) 同乡会在极力为同乡谋利益的同时,还同官方配合、参与社会公益活动。1910年,德国殖民当局即将湖岛子义冢转与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和广东会馆分别轮值。[14](P64)
二是业缘和趣缘性的互助团体。五四以后,青岛职业分化速度加快,社会下层的劳动者为了生存,则按行业结成了互助性的小团体,如木工的鲁班会,铁匠的老君会,以铁路工人为主的圣诞会等,他们无不以“互结、互助、互爱、互学”为宗旨。规模最大的职业性互助团体当属警察共济社,该社于1930年7月成立,当时全市警察系统已近4000人,此前内部即有“集议会”之设,遇有员警死亡,则按薪俸多寡纳赙,“然无具体办法,仅有此义举而已”,除了死亡抚恤外,“若残废、乏资、遣归,均须在在补助”,于是全市警察共同组成共济社,筹集基金,[20] 救助身故、久病、贫苦或残废的员警等。而专门的下层互助团体也开始出现。如互助赙金的同仁寿缘会(俗称老人会),1934年5月正式成立,会员多达500余人,其加入者多为码头工人、邮差、苦力、下级公务员及小商贩之家长等,希冀死后能得一笔丧葬费,“免令子孙临时呼吁”。[21](指令P47)
三是合作社。与民间自发的互助团体不同,合作社是由西方传入的,以相关法规和政策为基础、自上而下地推动而组织的,更具备近代的经济伦理精神。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共同体,青岛的合作社出现时间稍晚,1933年2 月市政府才颁布《青岛市职工合作社通则》,确定了“以互助、普利、改良生活为目的”的原则,不过市民素质较高,对于互助的认识也远比农民为深刻,社会效果自然显著,这可以从社员人数和经营活动上反映出来。如市政府和胶济路职工消费合作社分别有社员1034、5130人,股金1100、73130元,年营业额18000、70余万元。[19](第四编 合作行政P13) 该市的合作事业体现了城市社会的特征,即以消费合作社为主,运销、生产、利用和信用等类型甚少;再就是社员入社须交纳股金,且相互负连带责任,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条件相差无几的人们才倾向于这种合作方式,这是该市合作社多为机关和企业职员的主要原因之一。
各互助组织均是建立在权利义务对等、互惠、互利原则基础之上的,主要为内部成员提供庇护和福利,表现出了较强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色彩,无论是救济的对象还是资金的筹集,都不一定局限于团体内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青岛当局保障能力的不足,大部分移民依靠这种方式,化解了城市生活的一些风险,增强了城市认同感。
3.积极兴办福利事业
近代青岛的福利事业大体可分为职业性和大众性的两种。职业福利主要由企业等提供的,基本上面向内部员工,属于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激励措施。五四以后,青岛工潮迭起,尽管绝大多数被镇压下去,但一些资方也逐渐意识到,在遵循成本核算法则的前提下,主动向员工提供少许福利,可以降低经营成本,减少劳资冲突,符合企业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青岛华新纱厂就颇有远见地指出,企业以营利为目的,自无可讳言,虽不能舍利而言义,但若工人程度幼稚,“亦易因利益发生纠纷”,劳资双方均受其害,在不背股东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而谋职工之福利,劳资之协调,所谓大利之道,趋于两利”,于是筹划慰劳金以谋员工养老,设立医院以重卫生而谋救护,置公墓所以利殡葬,粮价高则有平粜之举等。[10](P11) 当局也制定政策,鼓励企业举办职工医院、食堂、托幼机构以及学校等福利设施。
在各种福利设施中,职业教育对于提高工人素质和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等都有重要的价值,近代青岛的发展也急需大量受过现代教育的劳动者,而供给的却大多是从农村涌来、无文化知识和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如工人、苦力、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家庭服务人员、无业游民等,其生活的艰辛决定了文化程度极为低下。调查显示,工人中识字者仅在30%左右,而苦力十有八九是文盲,极少数人不过略识几个字而已;至于工人子女的入学情况也不容乐观,不少工人家庭节衣缩食供子女上小学,但随着学费提高,能继续供应子女入中学的就已寥寥无几。1930年,该市社会局统计,在2000多个工人子女中,16岁以上仍能坚持读书者仅有3人,[22](第四编劳动行政 P129) 即能读中学者已属凤毛麟角,大多数工人子女只得重复其父辈的老路,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这种状况无论是对劳动者本身还是对于企业和社会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1931年3月,该市教育局、社会局、市党部共同组织了“青岛市职工教育委员会”,并督促各工厂设立分会及职工学校,到次年11月,先后成立17所,计59个班,学生3000余人。为督促职工进修学习,该委员会还拟订了《职工补习学校学生奖惩暂行规则》,对于无故缺课、退学等情事,则分别给予记过、暂停工作、罚薪等处分。[23](第三编,劳动设施P134) 这种通过立法强制工人接受教育的做法,对于提高产业工人的文化水平,改善其素质结构等都是很有益处的。
兴建住所,廉价租给符合条件的平民。1929年后,市政当局着手整理市容,棚户以及杂院等则是清理的重点,但调查后发现,棚户和杂院住户也承认居住环境恶劣,但由于收入有限,又“无廉价居所可供迁移,不得不忍痛住此”,若无合适住房,只“勒令拆除,不无困难”,决定将拆迁、改造与建造平民住所结合起来,并尽可能照顾到其谋生需要。1933年春,当局整修四川路,在处理“适占马路边沿”、影响工程进度的100余棚户时,不是迁徙他处, 而是针对其多在附近从事旧货营生的现实,就地安置,把四川路预备填海地划出一段,建筑海堤,供其建房之用,其他诸如挪庄、马虎窝等地方也均就地建筑,以免影响贫民生计。至于市区则采取集中、统一建设的原则,“俾便管理”以及敷设公共设施等。为尽快改造棚户区,当局还规定棚户有力者可按照市工务局图样,就地自建,并豁免地租和租权金等,这就大大减轻了政府的经济压力。[24] 当然,平民住所为体恤贫民而建,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通过道德和经济上的筛选,尽先满足了“充当佣工、苦力与摊贩、小商及贫苦妇女”的居住需要。
三、成效与不足
青岛的社会保障建设起步虽晚,但在各界的努力下,仅仅数十年的时间,就大致构筑起了以济贫为核心、以社会福利为发展方向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随着一系列措施的推行,一度紧张的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民众受益良多。作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性反应,社会保障确实发挥了减压阀的功能,至于如何具体评价,本文试从下述两个方面作些探讨。
1.社会保障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渐进性,社会效果明显
近代中国仍以农业为主,自然灾害频繁,赈灾是最主要的保障形式。而青岛则结合城市实际,逐步确立了与工业经济相适应的、以济贫和职业福利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到抗日战争前夕,青岛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民间互助为主体、以员工福利为补充的多元保障体系。当局对保障事业的介入愈来愈积极和主动,诸如制订社会法规、兴办福利救济机构、规范慈善公益社团的活动等,并最大限度地动员各阶层参与;民间则抱着当仁不让的态度,积极参与社会保障事业。而且,社会保障形式日趋多样化,受益群体逐渐大众化。在维持生理性弱者生存的基础上,愈来愈多的市民也被纳入到了保障范围之内,非物质性的保障措施日益盛行,如举办民生工厂、简易工厂,对无业和失业者进行职业培训,设立年金以为工人养老之用,为社会下层的孩子接受教育创造条件,对童工、女工以及不幸妇女实行保护等,这都是传统的善举所无法比拟的,也是近代青岛社会保障事业的闪光和进步之处。
另外,不少保障措施也颇见成效。以救济院贷款所为例,从开办至1933年9月,总计贷出1543户,共14569元,1934年贷给995户,计12218元,[25](P2486)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民的燃眉之急。作为一种成本低、效果佳的济贫措施,确实值得推广。再如平民住所,至1935年底,该市共建成16处,计3000余间,租户近2900户,这对于只有三四十万人口的青岛来说,所能安置的人数确实非常可观。住所内生活设施相对齐全,租金相对低廉,减轻了租赁者的经济负担,对于本市房租也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如台西镇境内的数处平民住所和简易住所建成后,民房房租则由原来的每间每月4元左右降到2至0.8元不等。[26](指令P20) 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补救措施,这一政策虽非出于满足“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但在不给政府增加多少经济负担的前提下,改善了平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其生活质量,维护了城市的形象。平民住所政策的成功,还引起了国内不少城市的兴趣,有的甚至还派员前往参观取经等。
2.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总体上,青岛的社会保障仍属于补缺型的,即以个人、家庭、市场和社会互助为主,政府提供的保障项目十分有限,且缺乏连贯性和完整性。而近代中国天灾连绵,战乱频繁,政治窳败,在这种环境中,青岛当局也不可能制定完整的社会保障政策并一以贯之下去。主观上,中央政府缺乏建立社会保障的诚意,地方当局自然也就敷衍塞责,就事论事。有关法规林林总总,但缺乏连续性、稳定性,不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且往往停留在纸面上,付诸实施者少。对于近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社会保险问题,当局认为劳工保险诸如失业、健康、疾病和养老等关系至巨,“苟不谋保障,则害之所及,将贻社会以无穷之忧”,[6](P14) 但保险费从何而来,自愿还是强制,却语焉不详。在工人的工作条件和保护上,当局的监督检查或流于形式,或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近代青岛经济发达,但若与西方相比,还是“瞠乎其后”的,财政有时还入不敷出,需要国家补助,难以支撑起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庞大的社会下层群体则进一步增加了保障的压力。本来,正常的社会结构应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但近代青岛却呈现出金字塔形,即除少数人居于社会上层外,绝大部分属于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1929和1930年的华新、钟渊等六纱厂4768名工人中,收支相抵者仅873人,入不敷出者竟达1741人之多。[22](第四编,劳动行政P129) 经济状况稍好的产业工人尚且如此,至于那些没有固定收入的苦力、小摊贩以及无业者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所谓的社会保障只能以保命为主。
另一方面,青岛财政窘迫固然是事实,但财政支出不合理则制约了保障事业的发展。社会本身要求资金来源渠道必须畅通和稳定,资金直接决定着保障水平的高低和受益人数的多寡。社会保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社会福利也并非全是“免费午餐”,社会互助则是建立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基础之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轻,相反,只有加大财政投入才能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在济贫活动中,资金具有单向流动和消耗性的特征,必须依靠政府拨款来维持。然而,青岛的绝大部分财政收入用在了行政和治安方面,用于保障方面的经费不过杯水车薪,致使许多保障计划难以落实,即使是低层次的济贫,所能受益的人数也十分有限,根本做不到“应保尽保”。另外,社会的动荡,军阀的竭泽而渔等又进一步削弱了民间的自救能力。1920—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青岛至深且巨,商业萧条,失业增加,救不胜救的消极情绪弥漫于社会各界。慈善界人士就悲观地说,赈救之施,无岁无之,各届人士“甚至节衣缩食以为输助,罄囊尽箧以为赈济”,然市面上的贫民依然如故。[27](弁言)
就职业福利说,青岛众多的工商业户中,真正像华新纱厂那样本着互助平等的理念并付诸实践的为数无几,多数业户目光短浅,或者提供一些小恩小惠而已。如职工补习学校本属于劳资两利的一种措施,一旦涉及到经费问题,厂方就往往敷衍不办,若与工作发生矛盾时,不是积极协调,提供方便,而是设置障碍,加以阻挠,职工“因而缺席者愈多”,以至于不少职工学校有名无实。[28(P82—84) 再,近代外资企业操纵和垄断着青岛的工业经济命脉,所雇中国工人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没有,遑论享受福利了,当局往往不敢过问,这就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整性和严肃性。
总之,近代青岛虽搭起了社会保障的主体架构,但要使它实用、有效,还须充填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否则只是空中楼阁、华而不实。只有以经济为基础,以民权为原则,以社会和政治稳定为前提,以政府为主导、以民间力量为补充,才能真正构建起宽领域、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满足市民的基本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