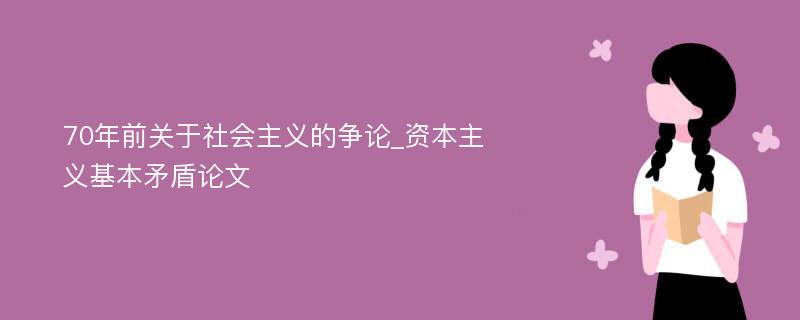
七十年前关于社会主义的一场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七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是中国进步思想界进行方向转换的重要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发生了一个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在开始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新文化运动,并且逐步地发展成了这个运动的主流。当时,评介社会主义多种流派观点的文章,在许多报刊上随处可见;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更常常引起人们“无限的兴味”(瞿秋白:《饿乡纪程》)。谈论社会主义,一时似乎成了一种时髦。
不过,并不是所有谈论社会主义的人,都成了社会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用心的。比如,戴季陶就曾对社会主义和劳动问题一度表现过热情。他承认,他之所以谈论社会主义问题,是为了让“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工人,“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免得他们“将来纷纷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也就是说,是为了把刚刚开始的“工人直接参加社会政治运动的事”引向“与雇主阶级的调和”,而不至“发生出动乱来”即不至走到革命的道路上去(《星期评论》第3号、第13号)。又如,梁启超也说过,“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不过,“应该采用那一种(社会主义),采用的程度如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状况”。他“主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以便“避了那迷人的路,用了那防病的方”,从而“免掉”将来社会革命的险关”(《欧游心影录》)。又如,张东荪也一度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第三种文明》)。他谈论社会主义,并不是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而是为了“防遏过激主义”。1920年夏,当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举行多次座谈会酝酿筹建共产党时,张东荪参加了一次座谈之后即退出了,戴季陶也借口不能与孙中山、国民党断绝关系而声明退出了。不久,张东荪就卸去了“社会主义”的外衣,公然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并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9月,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 罗素去湖南时,张东荪曾陪同前往。在讲学中,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而“根本的永久的解决方法,自然惟教育是赖”。他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同时又说,它“只适用于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实业不发达的国家”。在他看来,中国甚至连谈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罗素给了张东荪等人以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1920年11月6 日,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声称罗素关于“中国除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的主张,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的,中国当前的问题是要使中国人都过上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社会主义”等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等曾先后著文予以反驳。12月1日, 陈独秀将论战双方的文章汇集起来,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为题,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当月,张东荪发表《现在与将来》的长篇文章,系统地论证了自己的反社会主义思想。次年2月, 梁启超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长篇文章,支持张东荪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并加以补充或发挥。张东荪、梁启超的观点,遭到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严厉批评。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达的《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施存统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是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严肃的思想斗争。
张东荪等人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所以,“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这样才能“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中国的问题“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按即布尔什维主义)等等”可以解决的。“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
是不是张东荪们真的只谈发展工业、不谈主义呢?不是。他们只是要人们不谈社会主义,他们要谈的是资本主义。他们说,“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然不以资本主义之方法,决不能竞存于现在经济制度之下”。他们引证罗素的话,发展实业,有三个办法:或者靠资本家,或者靠国家,或者靠劳动阶级自身。但“中国政府如此腐败”,是“靠不住”的;劳动阶级“程度太低,不能得良好的结果”;“结果仍归到资本家”。他们说,“在中国现状之下,真正的政治集权共产主义,如俄国劳农制度,决不能发生”。而“资本主义以外国势力的后盾与固有的基础”,是“必定发展的”。当前的中国,还不是从资本主义下解放劳工的问题,而是许多人求为劳工而不得的问题,所以,“即使资本主义的企业发达,终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所以,“什么人合宜于现在呢?”那“就是绅商阶级”。“资本阶级将兴于中国,其机运殆于成熟,断非吾侪微力所能抗阻”。即使“吾辈欲抗阻之,其事如不可能,亦且亦诚无抗阻之必要。”
张东荪们不赞成用革命的手段来摧毁旧社会制度,从而为中国的开发实业开辟道路。他们竭力掩盖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否认工农大众受压迫的基本事实。他们说,中国人的痛苦,主要是得不到工作,而不是得到工作以后受的剥削。“工人受苦固然是事实,但直接受自资本家的很少很少,而通通是受自工头的”。解决工人问题的办法,不是进行社会革命,而是“把制度逐渐改良”,“温情主义”才是“在现在中国为有益于工人”的。“至于农人,要晓得中国向例地主与佃户都是平分收入,甚至于佃户得六成地主得四,所以农民对于所受地主的痛苦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结论是:“工人、农民在今天所需要的,只是取得教育与改良生活”,而其方法,“总以平和的、渐进的为佳”。为了防遏阶级斗争,“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并应“对资本家采矫正态度”,以便“在现行经济制度下,徐图健实的发展”。
张东荪们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资格来讲社会主义。他们说,“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因为社会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去宣传社会主义,“真正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而伪的劳农革命恐怕难免”,其结果“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他们还引证马克思、列宁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如说“列宁之思想为梯阶之三段。曰由贵族国家至中产国家,曰由中产国家至无产国家,曰无产国家至无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方在萌芽”。“中国若想社会主义,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他们声称,“对于资本家当持何种态度,实今日言社会主义者最切要之问题”,今日为改造中国计,不“当努力防资本阶级之发生”,而应“借资本阶级的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
应当指出,张东荪等人关于反对在中国传播和实行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系统的。这些言论,后来曾被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们反复地论证和发挥过。这些言论,在当时也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给正在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正如《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6号上的一篇文章所说:“他们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虽不足以欺有识之人,然一班老顽固见了,必定欢天喜地,把它登在报纸上,借以骗钱,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把‘罗素博士之名言’登在报上骗钱一样;一班脑筋简单的青年见了,必定为它所惑,对于社会主义不肯加以研究;就是一般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见了,也未必不呈一种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进行驳斥,是完全必要的。
在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运用自己刚刚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张东荪等人所作的批判,不仅旗帜鲜明、有声有色,而且充分说理、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的方针,很重要”。如果不把它弄清楚,是会“贻误中国人”的。
他们指出,开发实业以增加富力,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这是没有人反对的;但“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而“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那是我们所不能赞成的。“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而“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少数人之所以能免于贫乏、过奢华的生活,正是以多数人免不了一般的贫乏为前提的。所以,“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受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而为了“要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还应该明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他们强调,“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幸而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
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中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人们必须具备世界历史的眼光,才能对中国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由于中国是一个受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国家,要想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到独立的、充分的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们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外国资本家在我国政治上处处占利益,交通输送他们都得到优越地位,本国的资本家处处分明劣于他们,照此说起来,怎么可以和他们竞争”。“要使中国的民族得到自由、平等,那么,非把资本国打倒是永无希望”。然而,要指望中国资本家“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如果“完全听着自然的Evolution而不加以人力的Revolution, 马上要在中国成立的Bourgeois阶级的是不是中国人”就是一个问题。 还应当看到,“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李大钊选集》下卷第454 页)。
对于中国是不是存在着劳动阶级,中国的工人农民是否受到残酷的压迫、要求革命这样一些问题,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答复是:“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的。全国四万万人(由某种意义说,都可算是劳动者),虽然有许多无业的游民,然而都可以叫做失业的劳动者。所以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而在此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这样,他们就揭示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存在着的深刻矛盾,实际上把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作为一项基本任务提到中国人民面前来了。他们指出,“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而随着工业的发展,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又纷纷走向破产;“加以近年来,国内武人强盗,争权夺利,黩武兴戎,农工业小生产机关,差不多完全破坏”。这样,他们也就揭示了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实际上把反对封建军阀作为中国人民的一项基本任务提出来了。他们明确地讲到,“我们受了武人强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掠夺和压迫”,“还要受国际资本阶级经济上政治上掠夺和压迫”,所以,我们“或者不得已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要等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达到一面可以和外资抗衡,一面可以尽数吸收国内的劳动者,其中要经过如何长的时日,恐怕那个时期未到,而我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且相索于枯鱼之肆了!”(《李达文集》第48页49页66—68页)在这里,他们为中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这个思想作了有力的论证和辩护。他们的结论是:“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俄国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于发展实业,实在有利无害。换言之,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李大钊选集》下卷第455页第445页)。中国人的悲惨境遇,“除了中国劳动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
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是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超越了马克思列宁所揭示的革命发展必经的梯阶”这一类问题,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作出了自己的答复,并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提出了若干有创造性的见解。
第一,他们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十分发展为前提”,这固然不错;但是,“要生产力十分发展,必须以改造经济组织才能实现,即只有靠社会革命才能实现”(新凯:《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也就是说,中国不应当等待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十分发展以后(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才进行社会革命;相反地,应当通过社会革命来改造经济组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为新的社会制度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
第二,他们指出,“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说,社会革命在资本制度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要实现的;然而也可以用他种人为势力——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促进他的速度”。这也就是说,社会革命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这个革命能否发生并赢得胜利,不单纯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而且取决于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比如,“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十数倍;英美两国的工会,比俄国的也要发达得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的缘故”(《李达文集》第56页)。
第三,他们指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从发动革命、夺得政权,到社会主义实现,中间不能不经过若干过渡的步骤。他们指出,“并不是说,一经革命之后,共产党有了政权的社会便是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不过是锯了向共产主义之路上的荆棘罢了。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还要再向前走才行”。他们指出,“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经过的长短,我看要以各国底经济发达状况和人民智识程度如何而定的。在俄国、中国这些产业幼稚、人民无知识的国家,过渡时期要比别国多一些时日也未可知。究竟要多少时日,我们固不能预定;不过共产主义不是一举而成的这件事实,我们是无疑的”(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
在论述上述思想时,他们还阐明了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们指出,“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决不应当‘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应当把那种学说那种主义的精髓取出”。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创立时“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总之,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不过如何才能实行,却全靠我们的努力了!”(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所以我们“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李达文集》第56页)。他们在这里所提出的关于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不必拘泥于枝叶政策的思想,关于必须在实践中逐步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思想,都是很可珍贵的,并且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
诚然,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上还并不成熟。他们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只能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他们也不懂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这是他们的两个明显的缺陷。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或者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的。他们在宣传自己的主张时,不仅从理论上进行论述,而且用中国社会的实际来加以证明。这也说明,以科学社会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有现实根据的。
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通过这场辩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思想阵地得到了扩展,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也进一步奠定了。朱务善的回忆提供了这方面情况的一个生动例证。他讲到,当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挑起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时,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利用这个机会,在沙滩大楼的一个大教室里,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分赞成和反对两派辩论,邀请李大钊同志作为辩论会的评判员。参加这次辩论会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学生和教员,听众很多”。辩论终结时,由李大钊作结论。“我还记得有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好像是费觉天)最后对我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李大钊同志的发言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竟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高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张东荪在受到共产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之后,感到自己的理屈词穷,不得不在1921年2月发表《一个申说》, 承认“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不过他又说,“现在各种社会主义都有缺点”,所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总当认为最后的目标,宜努力随着各民族的共同研究去创造”,“中国现在最不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Propaganda”(宣传)。虽然他声称不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他自己却又积极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最晚出的,所以他比较是最圆满的”。他企图以此抵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基尔特(Guild),即行会、同业、协会的意思, 它是既包括工人又包括资本家、雇主在内的一种组织。基尔特社会主义起源于英国,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主张这种学说的人宣传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把生产者的同业组合为经济组织的基础之一种社会制度”。“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方面实现产业的民主主义,——生产者自己管理他的生产——同时在他方面把所有一切重要问题,与国家共同管理,革除为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之危险”(虞裳:《基尔特社会主义》)。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他们指出,“惟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政治权力是现在社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非先夺了治者阶级的武器以除去障碍,再运用这个武器以增加前进的速度不可。”“无产阶级专政是压服有产阶级的一种手段,是强制有产阶级的一种手段,也就是消灭阶级的一种手段”。在一定时期内,它是必需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不然。“他们是不主张革命的”。他们的劳动组合“是安于现社会的”,“是想在现社会上一点一点的求管理权的”。“这种手段和跪在强盗旁边,求他少抢一点是一个样子的可笑!这种‘叫化式’的阶级斗争,先不必说他可耻不可耻,简直是办不到”(新凯:《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因为处于优越地位的治者阶级是“一定不肯”听从他们的劝告,实行“退让”,把管理权交出来的。
他们指出,“中国的需要不只是把管理权移之于劳动者就完了,并且还需要高度的生产,此高度的生产的造成非要大规模的生产不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主张大规模的生产。他们竟以(为)中国的手工业的小规模生产不必改变。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是立于大规模的生产上的。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的最要之点在乎生产工具公有。此种公有非大规模的生产一定不能办到”。既然要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国家的管理生产是当然的,也是必要的”;社会经济组织不可能也不应当只是一些不相关联的、规模狭小的“行会”。而这里所谓的国家管理,“无宁说是劳动者管理”,因为“共产主义的国家是以劳动者为基础的。国家是与劳动者息息相通的。劳动者是参与种种建设事业的”(新凯:《再论共产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
他们还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实质进行了揭露,指出“既说树立生产的新方式,而又不主张革命,则树立方法自然是舍资本主义以外别没有了。你们主张资本主义就主张资本主义好了,又何必带上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呢?骨子里主张资本主义而又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此种‘暗娼式’的行为,可怜亦复可恨!”(旋:《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通过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批判,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进一步宣传了中国必须走革命道路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扩大传播扫除了又一个思想障碍。
标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张东荪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学论文; 基尔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