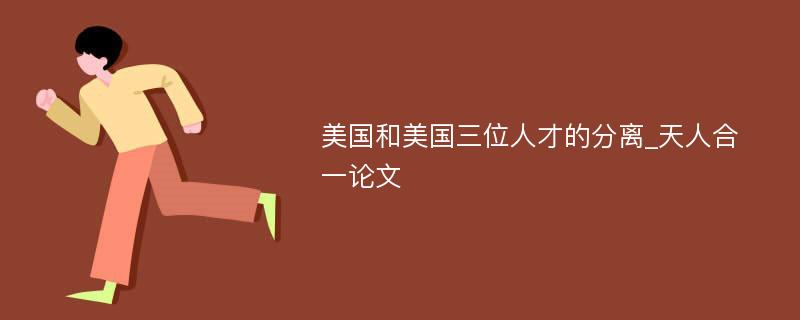
三才分合與美美異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假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①的説法有其合理性的話,那麼,每個時代也應有其特定的美學境界或審美境界,即該時代的人們以獨創的感興符號表意系統去傳達人生意義體驗並依託其本土傳統習慣的精神追求。如此一來,當代中國人應有自身的美學境界也就同樣帶有合理性了。當然,也許會有人反對做這樣被視爲大而化之的總體概括,認爲這種統一的而非多樣的概括是無意義的,甚至還會找出多種理由,諸如美學境界的多樣化以及見仁見智式言説現象理應得到尊重,“多元主義”或“非理性主義”之警示言猶在耳②,等等;但是,衹要人們內心仍然存在着從多樣而紛紜現象中梳理出簡明而清晰的意義認同模型的精神衝動,衹要這種衝動需不斷從本土文化傳統所主導的符號行爲慣例中吸取養分的話,那麼,適當意義上的概括性描述、慣例性歸納仍然是需要的。關於當代中國人眼中的人生境界或美學境界,實際上已出現過諸多不同的見解或相近的表述。其中,近二十多年來頗有影響力的就有錢穆(1895-1990,字賓四)、張岱年(1909-2004)、季羨林(1911-2009)、湯一介(1927-2014)等人闡釋的“天人合一”説③,張世英等人標舉的“萬物一體”説④,費孝通(1910-2005)的“美美與共”説(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⑤等,而尤以“天人合一”説影響最大,加入討論的專家爲數衆多。故這裏以對它作簡要評述爲導引,由此提出“三才分合”與“美美異和”之説。 一 從“天人合一”到“三才分合” “天人合一”説,原本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觀念;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它又在當代中國學術界及相關社會公共領域中有過特殊的影響力。1990年9月26日,《聯合報》發表了錢穆的遺作《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在文章中,他不僅“澈悟”到中國的“天人合一”論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而且認爲“天人合一”説可以救治以“西方文化”爲“宗主”的“人類文化之衰落期”徵候: 近百年來,世界人類文化所宗,可說全在歐洲。最近五十年,歐洲文化近於衰落,此下不能再爲世界人類文化嚮往之宗主。所以可說,最近乃是人類文化之衰落期。……以過去世界文化之興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僕屢起,故能綿延數千年不斷。這可說,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我以爲此下世界文化之歸結,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爲宗主。⑥ 這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結,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爲宗主”的見解,受到了其時在中國學術界、文化界地位崇高的季羨林的高度重視,他隨即撰文大力回應和倡導錢穆臨終前闡述的“天人合一”觀: 我認爲,這一件事情有極大重要的含義。一個像錢賓四先生這樣的國學大師,在漫長的生命中,對這個問題最後達到的認識,實在是值得我們非常重視的。……他講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認爲“歐洲文化近於衰落”,將來世界文化“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爲宗主。”這一點也同我的想法差不多。⑦ 於是,憑藉錢穆和季羨林的雙重影響力,“天人合一”論在中國大陸激發起熱烈的響應或爭議的浪潮。⑧ 前賢之所以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推崇本土傳統中的“天人合一”觀,是有其現實合理性的,但比較起來看,它的一種更加具體而細化的本土傳統表述方式——“三才”(天、地、人)觀念,或許更能體現當代中國人所秉持的“生態”、“生物圈”意識中有關人與自然關係的獨特體認,以及巨大的環境保護壓力下新的言行選擇。伸張“三才”理念,或許更有助於從中國視角對世界“生態”、“生物圈”建設做出應有的既具獨特性又具普世性的貢獻。同時,更爲重要的是,與“天人合一”之説建立在有關“天”與“人”之間終將實現相互同一性的境界的假定性知識型上不同,今天條件下再來談天、地、人“三才”之説,就不應當再走“合一”的過分天真的老路,而應當根據當代科技以及人類理智進展的程度,探討一種天、地、人三者之間既分又合的境界;也就是天、地、人之間在遭遇了分化的痛楚後,執着地探求分化中的有限度融合的可能性。這是一種新的當代中國人生境界或美學境界。 從人的特性或本性來看,人生而異,異而行,行則有所待、有所爲。所謂“人生而異”,是説人一生下來就與他人有不同,無論是兄弟姐妹之間,還是自身相貌、高矮、胖瘦、內向/外向、壽命等,都受制於遺傳等先天因素,儘管後天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力或許更爲重要。可以説,不僅人的出生受制於他者的中介(例如,其出生來自父親與母親的結合),而且其出生後的衣食住行等無一不來自於家庭及社會的供給。所謂人之“異而行”,是説相互之間存在差異的個人總會去做事或行事,通過行事而盡力彌補、克服或化解相互之間的差異,求得基本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尊重或尊嚴。然而,人之行,總是有所待的,即人的行事並不是無條件的,而是要等待、倚重、憑依來自自身之外的社會生存條件。這樣,人的每一行事都不得不倚重於來自他者提供的中介條件。但人之所以爲人,在於他不滿足於僅僅有所待即被他者中介,而是要力求有所爲,即通過行事而同時也對他者產生一种中介作用——成爲他者的中介。人在接受他人關懷的同時,也總希望有機會關懷他人,爲他人付出——不滿足於“取”,且同樣願意“與”。這樣,人在行事中被他者中介即“取”,同時也通過自己的行事而反過來對周圍他者構成中介作用即“與”。所以,人的行事既被他者中介同時也中介他者——既“取”也“與”。人與人、人與周圍世界就這樣形成一種互爲中介的關係。人生在世,實質上就是被中介和中介,也就是“取”和“與”。⑨ 人作爲中介性存在物,其行事及其有所待、有所爲之據以發生的基本場域,在於天、地、人三要素構造。儘管許多學者所標舉的“天人合一”論、“萬物一體”論頗有合理性,但“三才”(天、地、人)説與之相比,顯得更加具體、操作性更強。原因主要在於,“天人合一”説省略了“地”的因素,而“三才”説則不仅同時突出了“天”与“地”對“人”的重要性,而且致力於協調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對此,一些學者已經做了富有意義的論證與闡發工作。⑩ 這裏標舉“三才”説,並不意味着必然會因此而樂觀地暢想天、地、人之間的和諧景觀;相反,當前情勢下應當更多地看到天、地、人之間的分離現實及相互和諧的困難程度。所以,這裏不是把“三才合一”而是把“三才分合”作爲基本主張。与“三才合一”説過於天真地相信天、地、人三者可以实現完全的同一性不同,“三才分合”指的是天、地、人之間構成一種既分且合的關係:一方面,天、地、人三者之間相互不同,各有異質性;另一方面,三者之間也可以結成有限度的和諧或“和而不同”的關係。 二 “三才”觀念與“三才分合” 天、地、人“三才”的主張,可以上溯到《易經·説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這裏設定,貫串天、地、人的終極元素是“道”,而“道”在這三者之中又各自由兩種相互對立的元素組合而成。而“卦”正是象徵天、地、人中各種變化的一系列符號,它們以陽爻、陰爻相配合而成,三個爻組成一個卦,所以説“兼三才而兩之”成卦。如果説,天道爲陰陽、地道分剛柔、人道有仁義,那麼,這個世界就是由天、地、人與陰陽、剛柔、仁義品格所組成的活生生的生命世界。正如《易傳·繫辭下》所解釋的:“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11)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這個生命世界就是一個由“三才之道”構成的世界。 對天、地、人三才之間的關係及其差異的由來,漢代王符(約85-約163)在《潛夫論·本訓》中作了更加具體而細緻的解釋,對今日重新理解“三才”觀念具有啓迪意義。王符指出:“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併,混而爲一,莫制莫禦。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壹郁,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他上溯到“上古之世”及“太素之時”的“元氣”初始時段,指出“氣”之“清濁”之別而導致“陰陽”之分,從而產生天與地之分,並闡明“和氣生人”的道理。接下來,他又説道:“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機衡乃平。”這裏更細緻地區分了“三才”之間的差異,明確規定天道的本性爲陽,地道的本性爲陰,人道的本性爲介乎兩者之間的中和。 值得注意的是,王符在這裏清晰地提出了“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機衡乃平”的重要命題。“三才異務”,是説天、地、人之間不僅彼此不同或相互差異,而且各自有不同分工。“相待而成”,是説天、地、人各自都是不完善的,不能單憑自身而獨立存在,而是需要彼此等待對方的中介式協助,即互爲中介。“各循其道”,是説它們三者各自遵循彼此不同的規律運行,互不相擾。“和氣乃臻”,是説它們三者之間儘管各不相同,但可以形成相互和氣的關係,即共處於一個和諧統一體內。“機衡乃平”,是説天、地、人是相互依存的中介式存在體,也即是一個互爲中介的共同體。由於王符特別注意到天、地、人三者之間的相互差異及相互溝通的可能性,因而在前人基礎上是一次新的推進。 作爲一個互爲中介的共同體,天、地、人之間確實是相互構成中介條件的。天與地總是相對而言的,在上爲天,在下爲地,構成一對互爲中介的存在。而人則是天與地共同化育出來的存在,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乃至悲歡離合等環節,都無法離開天與地的合力中介而須臾獨存。 天、地、人這“三才”還是一個彼此有分而又有合的共同體。説“三才”有分,是説天、地、人三者之間各有其差異、各有其承擔,不可能求得完全一致。天有天道,道分陰陽,陰陽交融而構成天道;地有地道,地分剛柔,剛柔相濟而構成地道;人有人道,道分仁義,仁義相成而構成人道。説“三才”有合,是説天、地、人三者之間應當而且可以尋求融合;但這種融合並非完全一致或同一,而是各自攜帶差異而尋求暫時和諧或瞬間同一。因爲,“三才”之間歸根到底有不同,即便是融合也有其必要的前提。這就是,尊重各自的差異而尋求差異中的相互對話及和諧。 三 中國古代有關“三才分合”觀念的詩意探討 中國古代不乏“三才”分合觀念的詩意探討之作。陶淵明(約365-427)寫於中年的組詩《形影神並序》(12),抒發了他對“三才”分合關係的獨特體驗及理解:“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這表明,詩人由於深感營營衆生在世忙碌之苦,纔希望弄清人的身形、身影、心神之間的相互關係。而身形、身影、心神三者的關係,可以被視爲天、地、人三才關係在詩人生活中的具體呈現方式。 第一首《形贈影》:“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淒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君言,得酒莫苟辭。”這首詩在考察人的身“形”與身“影”關係時,是把人(才)放在天(才)與地(才)的三方關聯域中去衡量的。詩人以身“形”的名義想追問身“影”的問題是:你看那天與地都一樣地長久而不會淹沒,山川草木雖可易容但終不致發生根本改變,而咱們人這種“最靈智”的生靈,何以卻不能像它們那樣獲得永恆?剛剛還在世間相見的人,轉眼間就去到另一世界了,且永無歸期。這世界太大,少一人不會引起什麼改變,但親朋好友哪能不思念呢!面對逝者遺留的生前用品,衹能引起無限的傷感。我個人無疑是沒什麼騰化成仙的法術的,衹是希望你——我的影子,能聽從我的建議,得到美酒時萬勿推辭啊!這身“形”所耿耿於懷的是,前人明明把天、地、人三才並舉,但實際上,人才的命運何以遠不如天才和地才那樣長久?何以人的形體説沒就沒了呢?似乎衹有借酒消愁,纔是逃避人才的這種宿命的途徑。身“形”所痛苦、痛恨並想借酒澆愁的,正是天地長存而人體必滅這一慘痛事實。可以説,這首詩反映了詩人內心對人才不如天才和地才的命運,也即天、地、人三才有別狀況的痛切質疑或探究。 第二首《影答形》:“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身“影”在收到身“形”的贈詩後,做了及時的回答,並對借酒澆愁這種選擇提出了清醒而有力的反駁或勸阻:儘管像天、地那樣求得人生永恆已不現實,但維護生命也總讓人苦惱。我心裏想過遊歷崑崙山和華山,求得長生之道,無奈關山重重難以企及。我(身影)自從同你(身形)相遇時起,就變得形影不離了,無論悲喜都一道承受。其實我們在樹蔭下暫時分開而止於陽光下,也始終不會離別。但是,這種形影不離的同一關係其實是註定不能長久的,形和影也都會隨時間的流逝而一道滅絕。一想到假如身體滅絕而名聲也隨之消失,就內心焦慮不安。假如生前能多多做諸如立德、立功、立言等不朽的善事,就可以見愛於後人,爲什麼不努力爲之呢?飲酒號稱能澆愁,其實與此相比是太拙劣了。上述回答,顯示了身“影”對身“形”的一次成功的勸慰:人才誠然不能像天才、地才那樣獲得永生,但確實可以通過行善事而名聲不朽,這是遠勝於醉酒以忘憂的拙劣辦法的。這就爲人才之與天才、地才看齊而指明了一條坦途——“立善有遺愛”,也即行善而不朽。與人的身“形”、身“影”都終將滅絕不同,人之“名”卻是可以超越“形”和“影”的宿命而立於不朽的。這似乎顯示了人才的一種堪與天才和地才相媲美的超越性品格:立名而永恆。 但陶淵明的最終意圖卻不在此,也就是既不看重飲酒、也不看好立名,而是別有意向。於是,他寫了第三首《神釋》:“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既喜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這首詩設定以存在於個人內心的“神”的名義,對“形”與“影”的苦惱及其構想的化解之道而發言,試圖找到真正能夠彌補人才與天才、地才之間的差異的法門。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正式提出了“人爲三才中”的命題,實際上披露出詩人在組詩中對天、地、人三才論的個人體驗與反思意圖。它所構想的理由在於,天才、地才之所以能長生不老,正在於其沒有私心,並非出於強求,而是順任其本身的規律。而註定不能長壽的人,之所以還是能位列“三才”之中,恰是由於其擁有“神”的緣故。“神”雖然與“形”、“影”相異,但畢竟三者生而相依,難分彼此。既然三者相互依託而喜好同一,“神”又怎能忍看“形”、“影”爲其不得永恆而焦慮卻又不説點什麽呢。其實,長生不老的幻想是靠不住的,如“形”所説借酒澆愁之法,或許可以忘掉憂愁,但也難免損傷身體而導致減壽;同時,如“影”所説立善留名確實好,但當今之世憑誰來讚譽你的名聲呢?老是這樣耿耿於懷、於能否長生不老或流芳百世,太傷身子了,不如順任天命,聽其自然,放浪於大化之中,無需歡喜也不必憂愁。人(才)的命運終究取決於天(才),應盡則盡,就不必再爲此而多慮了。這裏,“神”的總結性答覆一舉否決了“形”與“影”先後給出的兩種提議(借酒澆愁和立善留名),而指明了一條新的超越性道路:還是把人命交給天命爲好,順其自然即是道、即是福、即是樂。 這裏既揭示了天、地、人三才之間的差異的必然性,同時又呈現了跨越這種差異而展開對話的必然性及其溝通途徑,從而表明了陶淵明內心對“三才分合”境界的自覺認同。人終究與天和地是有差異或區分的,這突出地表現在天与地都能長生,而人卻説沒就沒。但人之爲人的本性就在於,人能知天命,懂得順應天時地利而尋求內心宁靜与和諧。這應當正是陶淵明的組詩《形影神並序》所試圖傳達的一种“三才分合”觀念。 當然,“三才分合”觀念是可以有林林總總的體驗與闡發的,絕非陶淵明一家之言所可以總結的。唐宋時期,白居易(772-846)、蘇軾(1037-1101)也先後有相關詩作出現。(13)蘇軾儘管“獨好淵明之詩”(14),但還是在《問淵明》中對陶淵明的《形影神並序》所表達的“三才”觀念展開了直接的詰問并提出了自己的新主張。“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爲日星懸。我散而卑之,寧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永年。皇皇謀一醉,發此露槿妍。有酒不辭醉,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譽,饑人食饞涎。委運憂傷生,憂去生亦還。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事此言。”(15)這一詰問,實際上正體現了蘇軾個人內心有關“三才”觀念的劇烈矛盾的一種化解方式。在他看來,陶淵明內心焦灼的還是在於對“立名”而不朽的孜孜以求,也就是“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的問題。他針鋒相對地提出的化解之策在於,你大可以做善事而不必求得美譽,因爲善的精神自可以超越人的身形、身影的短壽而長留於天地之間。也就是説,人的“形”、“影”雖然不如天與地之長久,而是必然消滅,但人的行善的“神”卻自可以超越“形”、“影”的有限性而長留於天與地之間,與天地爭輝而不遜色。衹要有了這種“神”,還擔心什麼長久不長久呢,“應盡便須盡,寧復事此言”。確實,蘇軾的這些思考與陶淵明形成了共鳴、甚至是高度共鳴,儘管在具體看法和行爲選擇上又“與淵明詩意有別矣”(16),不過終究表明其內心對“三才分合”觀念的實際認同。 其實,中國古人在“三才分合”觀念的表達上,曾經創造過多種各不相同的審美與藝術形式。例如,王維(701-761)的《終南別業》中的一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這一聯歷來被視爲古典詩歌中的精妙之作,但又同時被視爲難解之謎。有人乾脆宣告:“‘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此十個字,尋味不盡,解説不得。”(17)它們是如此之意味深長,以致似乎任何解説都難以窮盡。但近人俞陛雲(1868-1950)堅持要展開解説:“行至水窮,若已到盡頭,而又看雲起,見妙境之無窮。可悟處世事變之無窮,求學之義理亦無窮。此二句有一片化機之妙。”(18)他從中看到的是雙“妙”:“妙境之無窮”和“一片化機之妙”。今人葉維廉則關注其中文字的轉折作用:“文字的轉折、語法的轉折和自然的轉折重疊,讀者依着其轉折越過文字而進入自然的活動裏。對讀者而言,是一種空間的飛躍,從受限制的文字跨入不受限制的自然的活動裏。”(19)這些不同的品評是各有其道理的,但假如從“三才分合”視角去嘗試解讀,或許會別有洞天。它反映的是一種“三才分合”的觀念:“行到水窮處”,是説人在大地上遊歷,一直游到水的無跡可尋、人的無路可走的盡頭了。這既是人在地上所抵達的極限,也是大地自身的極限。如果單憑這一點看,人才和地才就都自有其限度了。但是,詩人筆鋒一轉,“坐看雲起時”通過人的“坐”和“看”的行爲,居然就轉出了一種新“妙境”——一旦你停下匆匆的腳步,收起驛動的心,席地而坐,涵養起寧靜淡泊的心性,默然靜寂地仰望上天,就會見到一片薄薄的雲層正從大地與上天之間的交接處緩緩升起,它仿佛正是從剛剛消失在“水窮處”的地上水源轉化而來的新生事物呢!原來,在地才與天才之間,是可以息息相通和相互轉化的,是可以此起而彼伏、此滅而彼生的!而發現和推動這種美妙的自然節律的完成和呈現的,恰恰是人或人才。衹有人或人才,通過其扎扎實實的“行”、“坐”、“看”等接連不斷的行動,纔能發現天、地、人三才之間的相互差異並追求瞬間的和諧!面對天才、地才的無限和永恆,人才往往難免感到自身的有限性和短暫性,但他卻同時可以通過自己置身於天才和地才懷抱中的主动行動去加以轉化,從而實現自身與天才、地才的瞬間和諧。這,大約可以説正是詩人從其禪宗視角而對天、地、人“三才分合”觀念的一種獨到體驗和闡發吧。 四 “三才分合”視野中的“美美異和” 天、地、人之間既分又合的“三才分合”,還可以作爲通向當代中國美學境界的哲學基礎言説。具體而言,這涉及人與藝術的關係、藝術心賞屬性中“分賞”與“公賞”的關係,以及“美美與共”還是“美美異和”。 首先,人爲中介,藝即心賞。處於天與地看護下的個人,總是被天與地中的其他他者中介,同時也中介天與地中的其他他者,從而是一種中介性存在。關於這一點,德國思想家馬克思(K.H.Marx,1818-1883)有過精闢論述:“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20)把“人的本質”在“現實性”層面上的呈現規定爲“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正是表明個人是受制於“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的;而這“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其實正相當於個人所生存於其中的全部他者環境。當然,馬克思不僅認爲個人受制於社會環境,同時也認爲個人能夠改造社會環境:“哲學家們衹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21)個人當其懂得不僅參與到“解釋世界”的進程中、而且更應參與到“改變世界”的進程中時,他對於他者的中介角色就真正釋放出來。這裏的個人,無論是作爲藝術家還是作爲公衆,都是天與地之中的既被他者中介、也會中介他者的存在。 在當今全媒體時代,人所具有的中介性存在的特性,會由於他所須臾不能分離的以手機爲中心的國際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或互聯網+平臺的無所不在的作用,而變得更具實在性和可操作性。當今時代的個人不僅在天與地看護下的生活世界中起到特定的中介作用(既被他者中介,也中介他者),而且擅長於處處使用互聯網媒介使自己的生活更具中介化特性。也就是説,人不僅本身就是中介的存在,而且還善於創造有力的藝術中介——藝術媒介去傳達人生的意義,即運用藝術品這種符號表意形式去表達人生意義。藝術,按照馮友蘭(1895-1990)的觀點,是人對事物的“心賞”,正像哲學是人對事物的“心觀”一樣。(22)藝術的任務,不是滿足人對事物的物質賞玩需要,而是滿足人對事物的心靈賞玩即“心賞”需要。這裏的“心賞”,就是指一種精神性鑒賞而非物質性鑒賞。藝術品通過自身的中介或媒介的興發感動,正是要喚醒公衆的“心賞”熱情。 其次,分賞偏美,公賞中美。藝術作爲人對事物的心賞,長期以來存在着群賞和個賞兩種取向的分別。(23)如今,它們已經和正在蛻變爲公衆中的分衆各賞格局即“分賞”。這種藝術分賞的結果就是“分賞偏美”。偏,本義是不正、傾斜。偏美,是指公衆中不同的個人、家庭或社群,已然因日常的藝術傳媒接觸習慣的差異而發生趣味分化,分別鑒賞各自所偏愛、偏心、偏斜或偏離的美了。簡單地説,“偏美”就是分散的、偏心的、偏愛的、偏離的美。這是一種私賞。“分賞偏美”與費孝通十六字箴言中所謂“各美其美”相比,已有了明顯不同。如果説,“各美其美”可以理解爲各個個人、家庭或社群都有自身的獨立而完整的美,那麼,“分賞偏美”則是説各個個人、家庭或社群的獨立而完整的美已然失去其獨立完整性,發生了偏心、偏移、偏斜、偏離、偏執等偏離中心的變故。 面對這種藝術分賞及其分賞偏美格局,亟需呼喚“藝術公賞”及相應的“中和之美”。如果説,藝術分賞的結果是個人各自分別鑒賞各自以爲美的偏美,那麼,正是藝術公賞纔可能共同地實現對中和之美的鑒賞。“中美”是中和之美的簡稱,是指中和、中正、和諧之美的意思。這裏的“中美”與共同美有所不同。共同美突出並追求美的事物之間的同一性,而“中美”注重的是美的事物的多樣性或多變中的那種中和狀態,是多種美之間的相互調和或折中狀態。公賞中美,正是指通過提升公民的藝術公賞力而實現對中和之美的鑒賞。在這裏,分賞的偏美與公賞的中美有着不同。人們各自分賞其彼此偏離的美,這是偏美;人們也可以公賞各自可以接受的中和之美,這是中美。 過去的“藝術群賞論”尋求鑒賞以普通公衆爲主的群體的美,這自然是一種以俗趣主導雅趣之美,故稱之爲“俗美”;同時,過去的“藝術個賞論”主張鑒賞以文化人群體爲主的個性化的美,這必然是以高雅趣味主導俗趣之美,故稱之爲“雅美”。當今時代面臨藝術分賞困局,則必然地出現了偏美。我則主張公賞,意味着呼喚從偏美回歸到中美。 再次,公心互融,美美異和。要突破分賞偏美的困境而走向公賞中美,重要的是調動公民的“公心”,實現不同公民之間的“公心互融”,也就是“公心”與“公心”之間的相互交融。錢穆在把整個中國文化的特質歸結爲“人心”爲主的文化或稱“唯心文化”時指出,“人心”既有謀生的慾望,也有“道心”的一面。人們爲了謀生,難免相互爭奪,但人們更加珍惜的是大群體的共同生活,這依賴於心靈的作用,這就是標舉“道心”。這種“道心”在根本上是“大公”的:“大家同有,而又可以相通”,“人人之心合爲一心”,“一人之心,即可是千萬人之心。一世之心,即可是千萬世之心”。(24)這種“道心”實質上就是“公心”。“人類文化理想,主要衹能從人事上求,一切人事,主要衹能從人心上求。但亦不能從各人個別的私心上求,衹能從群體大我共同相通的公心上去求。”(25)假如人人都能以“公心”去待人處事,那麼,一個和諧的社會是可以期待的。這樣,纔可以實現“美美異和”。“美美異和”並非是指不同的個人與個人之間消除差異而實現完全的同一,也就是不等同於費孝通十六字箴言中標舉的“美美與共”,而是僅僅指在尊重和帶入相互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差異中的和諧。與“美美與共”相信人與人之間終究可以達成美的同一性不同,“美美異和”是指不同的美或審美對象之間也可以相互共存,形成差異中的和諧關係或不同的美之间的有限度契合。 最後,人順天地,三才分合。如果説,“美美異和”還主要是從人類內部去觀察美,那麼,正是“三才分合”理論爲在天、地、人這一更大的關係場中全面完整地考察美,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型基礎。從古老的“三才”知識型看,人或人類總是生活在天與地(自然)之間,也就是在天與地的懷抱中生存,“三才”同在。由此,人或人類決不應尋求單方面去駕馭或征服天與地,而應順任天與地的規律,去求得“三才”之間相互依存和相互協調的共在。按照《易經·説卦》的表述,天道爲陰陽,地道爲剛柔,人道爲仁義。這三種(對)道或價值理念之間的相互交融,特別是人道(仁義)之順任於天道(陰陽)和地道(剛柔),纔是人間之至道。 考慮到進入21世紀以來,“三才”之中人與天、地的關係已惡化到連人類自己都深感難以承受和追悔莫及的嚴酷程度,人道與天道、地道之間已很難形成中國古代所訴求的“天人合一”或“萬物一體”式同一性了,即使是人道內部,完全的同一也成爲遙不可及的夢幻,因此,轉而尋求“三才分合”——天、地、人三方之間的相互差異中的有限度契合,或許更顯務實態度。在當今地球“生物圈”,人需要重新學會與宇宙萬物和睦共處——不再是想征服宇宙萬物,而是與宇宙萬物共處於同一個“生物圈”中,共同建設或改善“生物鏈”,形成可持續的互動型生存。 綜上所述,如果對當代中國人所應追求的美學境界作一慣例性歸納的話,可以歸結出下面八點:人爲中介,藝即心賞;分賞偏美,公賞中美;公心互融,美美異和;人順天地,三才分合。簡約而撮其要,核心爲四點:分賞偏美,公賞中美,美美異和,三才分合。也就是説,公衆固然可以各自孤立地分賞偏美,但還是不如共同地公賞中和之美,達成不同美相異而和的情形,從而實現天、地、人三才在差異中的相互契合。 [編者註:該文係作者即將出版的《藝術公賞力》第十三章和“結語”的部分內容,經與作者協商,做適當修改後在《南國學術》先行發表。] ①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王國維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第1卷,第307頁] ②[美]保羅·法伊爾阿本德:《反對方法——無政府主義知識論綱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周昌忠譯。 ③張岱年:“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985);錢穆(遺作):“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聯合報》1990-09-26;季羨林:“天人合一新解”,《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1993);季羨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類”,《哲學動態》2(1994);湯一介:“讀錢穆先生《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之貢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995);張岱年:“天人合一評議”,《社會科學戰綫》3(1998);湯一介:“論‘天人合一’”,《中國哲學史》2(2005)。 ④張世英:《哲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張世英:“從‘萬物一體’到‘萬有相通’——構建之中的中國文化新形態”,《南國學術》4(2015)。 ⑤據瞭解,“美美與共”是費孝通約於1990年12月間提出,後來又在一系列著述中加以闡發[費孝通:“對‘美好社會’的思考”,《費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第12卷;費孝通:“東方文明和21世紀和平”,《費孝通文集》,第14卷;費孝通:“關於‘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費孝通九十新語》(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⑥錢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聯合報》1990-09-26。 ⑦季羡林:“錢穆的‘天人合一’觀——中國文化對人類的偉大貢獻”,《中國氣功科學》5(1996)。 ⑧季羡林:“關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中國文化》2(1994);相關論述還可見陳業新:“近些年來關於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研究述評——以‘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爲對象”,《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2005);劉笑敢:“天人合一:學術、學說和信仰——再論中國哲學之身份及研究取向的不同”,《中國哲學與文化》(桂林:灕江出版社,2012),第10輯,第71—102頁。 ⑨有關“取”與“與”的關係,引自馮友蘭:《三松堂全集·新原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4卷,第499頁。 ⑩周汝昌:“中國文化思想:三才主義”,《社會科學戰綫》1(2008);王利華:“‘三才’理論:中國古代社會建設的思想綱領”,《天津社會科學》6(2008);李晨陽:“是‘天人合一’還是‘天、地、人’三才——兼論儒家環境哲學的基本構架”,《周易研究》5(2014)。 (11)高亨:《周易大傳今註》(濟南:齊魯書社,1979),第592頁。 (12)袁行霈:《陶淵明集箋註》(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59—71頁。 (13)(16)袁行霈:《陶淵明集箋註》,第71頁。 (14)[宋]蘇軾:“與子由六首·五”,《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2515頁。 (15)[宋]蘇軾:“問淵明”,《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1716頁。 (17)[明]憚向:“道生論畫山水”,《中國畫論類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第765頁。 (18)俞陛雲:《詩境淺說》(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第11頁。 (19)[美]葉維廉:《中國詩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第158—159頁。 (20)(21)[德]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卷,第56頁。 (22)馮友蘭:“新理學”(1939),《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151頁。 (23)王一川:“通向藝術公賞力之路——以北大藝術理論學者視角爲中心(上)”,《當代文壇》5(2014);“通向藝術公賞力之路——以北大藝術理論學者視角爲中心(下)”,《當代文壇》6(2014)。 (24)(25)錢穆:“中國文化的特質”,《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第42卷,第66、69頁。标签:天人合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