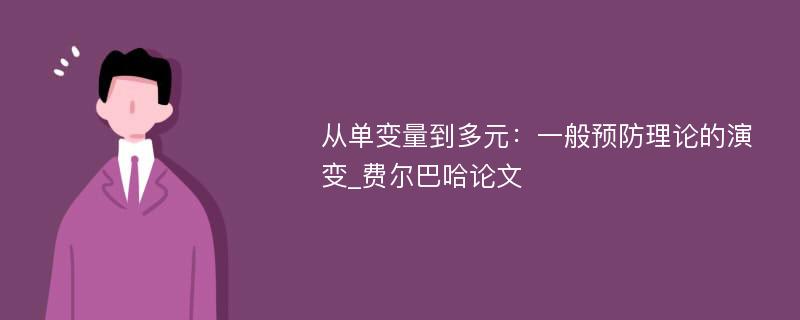
从一元到多元:一般预防论的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刑罚思想史上,一般预防论承报应论之先而启个别预防论之后。尽管作为一种系统的刑罚根据论,它的产生被认为是近代的事,但是,其思想源头却相当久远,而且,如果仅就对刑事实践的影响而言,作为一种思想的一般预防的历史地位远比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的一般预防显赫。(注:笔者认为,中国自西周至清末、西方自罗马法时代至刑法近代化止,整个刑罚体制处于受威吓理念所主宰的威慑刑时代。参见邱兴隆:《刑罚理性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第17-41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刑罚体制的演变史,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一般预防论的兴衰更迭史。
一、重刑威吓论:一般预防的初始形态
在中西方刑罚思想史上,以威吓为中核的一般预防思想曾受到格外青睐,并成为整个威慑刑时代的刑罚的指导思想。
就中国而论,一般预防的思想源头至少可以回溯至春秋时期。法家之典型代表人物商鞅与韩非子所力主的重刑威吓论,便是一般预防论的初始形态。在商鞅那里,重刑威吓论被表述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也”。(注:《商君书·说民》。)一言以蔽之,便是“禁奸止邪,莫过于重刑”。(注:《商君书·赏刑》。)与商鞅同出一辙,韩非子也主张刑罚重在杀一儆百的威吓。按他的说法便是,“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注:《韩非子·六反》。)在商鞅与韩非子对重刑威吓的推崇中,隐含着对刑罚的威吓作用及其作为刑罚的根据的正当性的笃信。
就西方而言,自古希腊以来便不乏类似于中国的商鞅与韩非子的威吓刑论者。古希腊执政官德拉古将重刑威吓奉为其立法的指南。在对人解释其立法为什么对大多数犯罪都规定死刑时,他声称:“轻罪理当处死,至于更大的罪,还找不到比处死刑更重的刑罚”。(注:普鲁塔克:《传记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页。)在这种轻罪重刑的立法方针的背后,刑罚以一般预防为根据的思想灼然可见。
相对于作为报应刑的初始形态的等害报复,(注:威慑刑是继报复刑之后兴起的刑罚进化形态。报复刑的主要特征是刑罚与犯罪等害。参见邱兴隆:《刑罚理性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6页。)重刑威吓论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因为一方面,重刑威吓奠基于对刑罚之遏制犯罪的功能的揭示之上,表明人类已摆脱机械决定论的束缚,完成了由将刑罚视为对犯罪的单纯的机械反动向将刑罚作为对犯罪的积极的遏制手段的转变,标示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已为人类所认识,这不失为人类认识论史上的一大飞跃;另一方面,重刑威吓蕴含着对刑罚的效果的追求,将刑罚的效果与刑罚的运用相联系,较之只求惩罚不求效果的同害报复,其进步性不言而喻。正是如此,重刑威吓论既有其产生与存续的历史必然性也有其相对合理性。
然而,重刑威吓论的不合理性又极其明显。首先,重刑威吓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严刑苛罚。因为在观念上,刑罚越严酷、威慑力便越大。正是如此,受作为一般预防的初始形态的重刑威吓论的指导,自奴隶制末期至资本主义初期,中外刑罚制度处于严酷的威慑刑时代。死刑、体刑等严刑峻罚种类繁多而适用广泛、罪刑擅断、刑及无辜、轻罪重罚与行刑恐怖成为此间刑罚体制的鲜明特征。(注:参见邱兴隆:《刑罚理性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7页。)相应地,刑罚因为从质到量都与犯罪联系松驰而很难有公正性可言。其次,正如挪威学者克里斯蒂所形象地指出的一样,“常识告诉我们,火炉不可碰,但并未告诉我们300度的火炉的威吓比200度的大多少”。(注:Nils Christie,Limits to Pain(Oslo,Norway:Universitets for Laget,1981)p.20.)刑罚的威吓效果的大小难以准确衡量,以其作为刑罚的根据,势必导致用刑施罚的盲目性与主观随意性。最后,重型威吓注重的只是刑罚对犯罪的吓止效果,将是否可以收到遏制犯罪之效作为了用刑施罚的唯一根据。这种只求产出不计成本的唯效果论,有悖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的效益法则,因此,且不说重刑威吓是否能收遏制犯罪之效,仅仅从为遏制犯罪而不惜刑罚成本的投入而言,它也是一种与效益观念相背离的不合理的选择。
正由于重刑威吓论的合理性不足而不合理性有余,自启蒙时期开始,其便遭到了普遍的评击,不但被报应刑论者所唾弃,而且为新的一般预防论所取代。
二、古典功利论:一般预防的近代形态
启蒙时代对重刑威吓论指导下的刑事实践的否定,导致了重刑威吓论本身的崩溃,也带来了一般预防论的转型。作为这种转型的标志的便是以立法威吓为核心的古典功利论的崛起。
古典功利论在近代的代言人非贝卡里亚、边沁、费尔巴哈与史蒂芬莫属。虽然严格说来,贝卡里亚、边沁、费尔巴哈与史蒂芬并非单纯的一般预防主义者,因为贝卡里亚与边沁主张刑罚的目的不但在于一般预防,而且在于个别预防,而费尔巴哈与史蒂芬甚至在一般预防之外还有几分报应论的色彩,但是,他们注重的是一般预防,将一般预防作为刑罚的主要目的。而且,他们有关一般预防的论述远比其它论述深刻,其一般预防论的影响远大于其它理论,相应地,将古典功利论归于一般预防论,未必失当。
无论是贝卡里亚、边沁还是费尔巴哈、史蒂芬,都强调一般预防是刑罚的首要目的。在贝卡里亚看来,“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注:(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并认为“对其他人的威慑”,“是刑罚的政治目的”。(注:(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按照边沁的论述,虽然“刑罚之直接的主要目的是控制人的行为”,即“不只是控制因违法被判刑后正在服刑的人的行为,而且控制一旦违法便应受惩罚的人的行为”,(注:参见J.Benth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J.Bubrns and H.Harteds.1970)p.158n.1.)亦即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但是,“刑罚的主要目的是一般预防,因为它是刑罚的真正的目的”。(注:J.Bentham,I Works(edited by Bowring),p.390.苯对边沁的刑罚目的论是如此介述的:“边沁认为刑罚的直接的主要目的是控制行为。边沁说,这种行为要么是罪犯本人的,要么是其他人的:对罪犯的行为的控制是通过刑罚对他的意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刑罚被说成是通过改造的方式起作用;或者是通过对其身体能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刑罚被说成是通过警戒的方式起作用。后者更为重要。philip Bean.Punishment:A Philosophical and Criminological Inquiry,Oxford:Martin Robertson,1981,p.32.)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主张法官的任务是使犯罪人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即让法定的刑罚变为现实的刑罚,因而颇具报应意蕴,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司法报应的前提是立法威吓,即是说,刑罚之在立法上的存在为的是威吓一般人,使之不敢犯罪,司法上的依法用刑只不过是促成与稳固人们对刑罚的立法威吓作用的确信,因此,在费尔巴哈的刑罚根据论中,以立法威吓为内容的一般预防论占主导地位。(注:参见张卫平、邱兴隆:《费尔巴哈早期刑法思想剖析》,载《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1期。)史蒂芬虽然因为写下了“刑罚之于复仇欲有如婚姻之于性欲”(注:James Fitz Jamaes Stephen.LL A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Law in England,London:Macmillan,p.80.此句根据原文直译应该为:“刑罚之于复仇欲之间的联系与婚姻之于性欲之间的联系酷似”。然而,将其意译为“刑罚之于复仇欲有如婚姻之于性欲”似更为言简意赅。因此,笔者曾采取后一译法。参见邱兴隆等:《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鉴于此译法已广为国内学界所接受,在此予以沿用。)这一格言而往往被人误以为是报应主义者,但实际上,其论述的是,正如没有作为满足性欲的手段的婚姻便会导致性的随意发泄一样,没有作为满足复仇欲的公力手段的刑罚便会导致私刑的泛滥。哈格就史蒂芬的这一比喻所作的如下阐释,对史蒂芬的本意作了最好的说明:“如果报复的动机有史蒂芬所暗示的一样重要,法定报应的废除不会有如此经常地被期望的一样温和的效果。这种废除对于受报应规制而满足的‘复仇情绪’的减轻的可能性,不会大于婚姻的废除对于受婚姻规制而满足的‘性欲’的减轻。婚姻与报应二者均服务于控制非此便可以更有损社会的方式满足的刺激。当法定报应未因被感到是错误的东西而适用的,或当报应被感到轻于罪有应得之时——当其被感到不满足,即不严密、不确定或不够严厉之时——公共控制便摇摆不定,‘复仇情绪’便倾向于会以私的方式满足。当美国西部殖民者认为其法律机构太软弱,无法保护其财产时,他们求助于‘私刑正义’,以不拘泥于审判形式地惩罚殖民者希望抑制且他们要求予以报应的被认为犯了偷牛之罪或其他行为之罪的个人。由于这可暂时有效地抑制犯罪,此类非正式的刑罚化易于蜕变。确定嫌疑人与其罪过的程序很随意,而且刑罚很野蛮。没多久,私刑不再维护公共秩序,而是被用于个人复仇或强化小恶霸们的道德命令并用以对社区而不是对罪犯进行恐怖。最有效的补救是设置通过有效地保护其秩序并满足其正义感而应该且确实得到社区信任的司法体制。不可避免地,在社区的法律体制未有效地实施的地区,某种私刑正义便会出现或再现”。(注:Ernest van den Haag.Punishing Criminals:Concerning.A Very Old and Painful Question,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5,pp.12-13.)可见防止私刑只不过是防止犯罪的代名词。因此,史蒂芬的刑罚根据论仍未超出一般预防论的范畴。(注:帕克认为,史蒂芬的比喻“是一种吸引人的比喻,但是,这并非表达一种纯粹的复仇理论。取而代之的是,它传递了一种伪装的功利论:刑罚之所以可以证明是正当的,是因为它提供了对情绪的一种有序的发泄,否定它,便会以某种更难以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式表达自身。”Herbert L.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37.)这从史蒂芬关于威吓的重要性的如下论述中更是一目了然:“废除狱卒与绞刑吏,你们的刑法便成为一纸空文……将人视为一群独立的单位,问题便出现:他们如何能被维系成整体?凝聚的原则必须是什么?明显地,必须提供对所有人同样起作用的某种动机。实际上,这意味着最后所凭借的人身惩罚的威胁。那么,在任何可以勉强维持的秩序中保持我们在一起的骨架最终是对力量的害怕,抑制这种力量,你便会被压垮。因此,(诸如绞刑一样的)一种制裁的存在在每一社会都是基本的,或者正如它可以被简言之的一样,社会取决于威胁。”(注:转引自 Sir Leslie Stephen,The Life of Sir James Fitz james Stephen,Bart,K.C.S.I.,A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London:Smith,Elder,1895,p.318.)
前文已述,罪刑擅断是重刑威吓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与重刑威吓论殊异,古典功利论反对罪刑擅断而强调罪刑法定。这在贝卡里亚与费尔巴哈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贝卡里亚虽然主张威吓是刑罚的首要目的,但是,其不但明确反对罪刑擅断,指出“任何司法官员……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该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出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而且旗帜鲜明地力主罪刑法定,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注:(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而费尔巴哈更因主张立法威吓而被誉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奠基人。(注:参见马克昌主编:《近现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8页。)他认为,“刑罚通常意味着痛苦”,它可以通过“心理强制”而使意欲犯罪的人自我抑制违法的精神动向,使之“不发展为犯罪行为”,这就要求市民确信“痛苦与犯罪不可分”,即确信一定的违法行为必然招致一定的刑事制裁。而使刑罚与犯罪相联系的唯一中介是用法律进行威吓,亦即要使“人们确信痛苦与刑罚不可分”,“痛苦与犯罪的联系必然是由法律进行威吓。”正是基于这种立法威吓论刑罚目的观,费尔巴哈提出了以“确定的刑罚法规绝对”为中心的罪刑法定思想。他指出:“一般说来,如果刑罚不是按照刑法法规来科处,而是按照预防、威吓(指司法威吓——引者注)来科处,那么,刑罚法规还有什么目的呢?……如果以预防、威吓的原理为根据,那么,所有的刑罚法规(在这里,我指的是确定的刑罚法规)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以此为前提,费尔巴哈进一步明确主张,法官只有依法用刑的义务,而没有罪刑擅断的权力:“刑罚法规赋予法官按照刑法法规处罚犯罪的全部义务,”“法官是为该法律服务的仆人。法官只有严格遵守法律,才是名副其实的仆人。”(注:张卫平、邱兴隆:《费尔巴哈早期刑法思想剖析》,载《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1期。)可见,古典功利论因强调立法威吓,反对基于威吓的需要的罪刑擅断,而构成对重刑威吓论的扬弃。
古典功利论的第二个特征是将刑罚的基点由刑罚的效果转向了刑罚的效益。前文已述,重刑威吓论只求效果而不求效益。与此不同,古典功利论并不主张凡是有效的刑罚都是正当的刑罚,而认为刑罚应该以遏制犯罪为必要,也只能以遏制犯罪为限度,不能遏制犯罪以及超出遏制犯罪的需要的刑罚都是不正当的刑罚,从而将刑罚的效益而不是仅仅将其效果作为刑罚的决定者。这在贝卡里亚与边沁的有关论述中体现得极其明显。贝卡里亚所称的“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注:(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是对刑罚应该以足以遏制犯罪为必要的揭示,而其所谓的“如果刑罚超过了保护集存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它本质上就是不公正的”,(注:(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注:同注⑨,第47页。)所揭示的则是刑罚应该以保护社会利益亦即遏制犯罪的需要为限度。较之贝卡里亚,边沁有关刑罚的效益性的论证更为全面而系统。他明确地把刑罚作为一种恶或者“代价”,而把刑罚所能收到的遏制犯罪之效视为一种善或者“收益”,强调刑罚的善即收益必须大于其恶亦即代价,从而不是把刑罚的效果而是把刑罚的效益作为所追求的目标。他认为,“所有刑罚本身都必定是可憎的,要是它本身不是可恶的,它便不会促成其目的。”(注:Sir W.Moberly,The Ethics of Punishment,Faber and Faber,1968,p.50.)尽管其可能可憎,但是,应该被节俭地使用,因为“所有刑罚都是损害:所有刑罚都是恶……根据功利原理,如果它终究应该得到承认,那么,便只有在它有希望排除某种更大的恶的范围内才应得到承认。”(注:Sir W.Moberly,The Ethics of Punishment,Faber and Faber,1968,p.281.)在这一总的原则指导下,他进一步具体提出了刑罚必须遵循有效性、必要性与适度性等规则,反对“滥用之刑”、“无效之刑”、“过分之刑”与“昂贵之刑”。(注:(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原理——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8页。)如果说重刑威吓论因只求效果不顾刑罚的限度而使严刑苛罚在所难免,那么,古典功利论对刑罚的投入产出比的注重则是立足于效益观念而对刑罚权的限制,无疑可以大大宽缓刑罚的严厉性,从而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严刑峻罚。
古典功利论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以对人的理性的假定为前提。在他们看来,人是趋利避害的理性动物。人之所以犯罪,要么是为了追求犯罪所可能带来的快乐或利益,要么是为了减轻不犯罪所造成的压抑或痛苦。而刑罚作为给犯罪人以痛苦与损失的手段,可以使意欲犯罪的人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而放弃犯罪意念,抑制犯罪行为。所有古典功利主义者莫不将这种人的理性模式作为其立论的基础。贝卡里亚认为“欢乐与痛苦是支配感知物的两种动机”,(注:(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由于“个人能从自己的越轨行为中捞到好处,增强了犯罪的推动力。因此,加重刑罚也就变得越来越必需了”。(注:(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如果说在这里,贝卡里亚关于理性人的论述尚欠清晰,那么,边沁与费尔巴哈则将权衡利弊、精于算计的理性人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边沁认为,“痛苦与快乐是人类行动的巨大动机。当一个人意识到或者推测痛苦是一种行动的结果时,他便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行动,以致趋向于似乎可以一种特定的力量将其从实施该行为中拉回来。如果痛苦的明显的分量大于所预期的快乐的分量,他便会绝对被防止实施这种行为。”(注:J.Bentham,Collected Works,edited by J.Bowring,Russell and Russell,1962,p.369.)费尔巴哈以对人的理性的假定为根据提出了其著名的心理强制说。他认为,“所有违法行为的根源都在于趋向犯罪行为的精神动向即动机形成源”,“它驱使人们违背法律”。而人之所以形成违法的精神动向,是因为受了“潜在于违法行为中的快乐”与不能得到该快乐时所潜在的不快的诱惑或驱使。只有顺应人“趋乐避苦”的常情,使违法行为中蕴涵某种痛苦,才能使具有违法的精神动向的人在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乐与苦之间进行权衡,并因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苦大于可能带来的乐而自我抑制违法的精神动向,使之“不发展成为犯罪行为”。而“刑罚通常意味着痛苦”,因而构成对意欲犯罪者的一种心理强制,即阻止其违法的精神动向转化成犯罪行为的心理障碍。(注:参见张卫平、邱兴隆:《费尔巴哈早期刑法思想剖析》,载《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1期。)
对罪行擅断的排斥与对刑罚的效益性的注重使古典功利论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重刑威吓论的两大痼疾,而以对人的理性的假定为前提又使古典功利论不象重刑威吓论仅仅是一种肤浅的思想,而成为了一种自成一体的理论。哈格认为,“任何实际的‘理论’必须就世界或它的任何部分象什么或曾经象什么或将象什么作出解释,或者至少,一种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世界的任何部分是、曾经是或将是,无论该理论称其是或者曾是抑或将是什么。一种理论必须以最终能由经验或考察加以检验以致理论被认为正确或不正确的方式告知或解释某种东西。”据此,他认为报应论不是一种真正的刑罚理论。因为它“根本未做这些事”。“相反,遏制理论,无论其正确与否,都是一种理论:它追问刑罚的作用(它降低犯罪率吗?)并作出可以检验的判断(相对于没有惩罚之可信的威吓,惩罚降低犯罪率)。”(注:Ernest van den Haag and John P.Conrad.Death Penalty:A debate,New York:Plenum Press,1983,p.28-29.苯也认为,一般预防论之所以成其为一种理论,是因为“它是一种一般的社会功利理论的一部分,并能够在该理论的框架内得到评价”。Philip Bean.Punishmont:A Philosophical and Criminological Inquiry,Oxford:Martin Robortson,1981,p.44.)因此,相对于重刑威吓论,古典功利论是一般预防论的一大进步。然而,古典功利论的合理性也主要限于其相对于重刑威吓论的历史进步性,如果我们撇开这种历史进步性,其理论缺陷也极其明显。
首先,古典功利论将所有犯罪都视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有失片面。前文已述,将所有人都视为趋利避害的理性动物,将所有犯罪都视为人精心算计、仔细权衡的结果,是古典功利论的理论前提。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古典功利论者成为了众矢之的,至少受到了个别预防论者的一致批判。美国学者霍顿与莱斯莱尔写道:“……被错置的对惩罚的信念可能奠基于这样的不现实的假设之上,即人们有意识地决定是否成为罪犯——亦即他们考虑一种犯罪生涯,合理地权衡其相对于其奖赏的危险,并达成一种奠基于此种苦乐计算之上的决定。它在假想上信奉,如果痛苦因素被严厉的惩罚提高,人们将从犯罪转向正直。略加思索便可揭示这种见解的荒谬性。”(注:Paul B.Horton and Gerald R.Leslie,The Sociology of Social Problems,4th Ed.,New York:Appleton Century Crofts,1970,p.167.)另一美国学者戈丁纳也认为:“对遏制的价值的相信奠基于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我们是总在行动前思考的理性动物,并且我们将我们的行动奠基于对所涉及的得与失的仔细计算之上。被许多法学家所热衷的这些假设在社会科学中已长期被抛弃。”(注:"The Purposes of Criminal Punishment,"21 Modem L.Rev.,1958,p.17.)虽然正如帕克所指出的一样,完全否定古典功利论关于犯罪是罪犯的算计与权衡的结果,有失绝对:因为“边沁的模式很可能是对趋利型的罪犯(夜盗、贪污者与骗子)的一种更近似于精确的描述。也许,当代最纯粹的例子是逃避其所得税的人。虽然我们不应忽视非理性动机在象这些一样如此仔细地计划的犯罪中的意义,似乎仍然清楚的是,它们有一理性的享乐主义的成分。边沁的模式对于此类案件具有值得注意的中肯性。这些中肯性——虽然其未必统制着犯罪活动的领域——不能被安然忽视”,(注:Herbert L.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41.)然而,对古典功利论将所有犯罪都视为人精心算计、仔细权衡的结果的假定的批判,至少揭示了它的片面性。毕竟,正如某些犯罪是犯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一样,诸如激情犯罪、过失犯罪之类为数不少的犯罪只不过是犯罪人一时冲动或疏于注意的产物。假如精心算计、仔细权衡是犯罪人的理性所在,那么,一时冲动或疏于注意则恰恰表明了犯罪人的非理性。相应地,将一般预防奠基于对犯罪人的理性假定之上,一般预防便充其量只能对部分而不可能对所有犯罪有效。既然如此,将一般预防作为对刑罚正当根据的主要乃至惟一解说的古典功利论的片面性也就不言自明。
其次,固然古典功利论因强调刑罚的效益而构成对严刑苛罚的一定限制,但是,效益毕竟是以效果为分子、以刑罚的量为分母的一种投入产出比,因此,刑罚量的加大如有相应的刑罚效果的加大相伴随,在古典功利论者看来便是正当的。与此相适应,古典功利论指导下的刑事实践,因脱胎于重刑威吓论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后者的胎印,不可能完全根除严刑苛罚的可能性。边沁所主张的“刑罚的确定性越小,其严厉性就应该越大”,“罪行越重,适用严厉之刑以减少其发生的理由就越充足”,(注:(英)吉米·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0页。)便明显地包含为求更大的遏制犯罪之效而施加更为严厉的刑罚的可能性,从而给严刑苛罚留有余地。因此,与重刑威吓论一样,古典功利论固有着导致严刑苛罚的危险。
最后,固然古典功利论因强调罪行法定与立法威吓、反对罪刑擅断与司法威吓而对法官司法的盲目性与随意性构成较大的限制,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排斥立法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因为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的大小无法准确衡量,实现刑罚的效果所需的刑量投入缺乏可靠的标准,相应地,立法上刑量的分配无据可依。因此,如果以立法威吓为核心的古典功利论对司法的盲目性与随意性的遏制是其相对于重刑威吓论之长,那么,其无法克服立法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则不能不说是其固有之短。
三、多元遏制论:一般预防的当代形态
古典功利论所固有的局限性与不合理性招致了报应论与个别预防论对它的共同否定。因此,随着个别预防论的日益得势,古典功利论在现代一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个别预防论的反思以及对其指导下的刑事实践的不满,导致了对一般预防论的兴趣的复苏。于是乎,作为一般预防论的当代形态的多元遏制论便应运而生。
多元遏制论的旨趣在于,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不只是包括威吓,而且包括加强道德禁忌等其它功能。此论在当代西方已成一般预防论之主流。其代表人物遍及欧美诸国。
也许,挪威学者安德聂斯是多元遏制的首倡者。(注:史蒂芬曾写道,“有的人可能因为害怕如果他们犯谋杀罪,其便会被绞死。而成千上万的人避开谋杀是因为他们视谋杀为可怕。他们为什么视谋杀为可怕的重大理由是谋杀犯被绞死”。J.F.Stephen,A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Law in England,London:Macmillan,1883,p.99.安德聂斯与哈格据此认为,史蒂芬实际上区分了一般预防的两种不同作用方式,亦即“害怕被处绞刑”——威吓作用,以及“视谋杀为可怕”——形成习惯的作用。(挪威)安德聂斯著、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Ernest van den Haag.Punishing Criminals:Concerning A Very Old and Painful Question,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5,p.68-69;Ernest van den Haag and John P.Conrad,Death Penalty:A debate,New York:Plenum Press,1983.p.99.如果这样,应该认为,早在古典功利论中便孕育了多元遏制论。)在1952年,安德聂斯发表了《一般预防是幻想还是现实?》一文,提出“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有三:恫吓;加强道德禁忌(道德作用);鼓励习惯性的守法行为,”(注:(挪威)安德聂斯著、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从而将一般预防由仅仅局限于威吓的古典功利论拓展为三元遏制论。此后20余年,安德聂斯一直致力于对一般预防的研究,论证了一般预防不是威吓的代名词,在一般预防的概念中还包括有刑罚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影响。
在美国,帕克与哈格均是多元遏制论的力主者。帕克从对古典功利论的分析入手,指出了作为一般预防功能的威吓的客观性与局限性。关于一般预防存在的客观性,帕克指出:“刑罚的威吓被要么通过立法的废除要么(就象通常所发生的一样)通过执法机构的懒惰而取消或者减弱时,以前被镇压……的行为倾向于上升。我们对这种现象是如此熟悉,以致可能不存在比这更令人信服的对威吓的有效性与遏制性的说明。例如,当镇压某些类型的性行为的法律不再有任何规律地适用之时,相关的问题被提出来,不只是因为人们感到一种威吓被废除,而且也许更有意义的是还因为通过犯罪耻辱化的惯例的强化价值的鉴别程序被终止。”(注:Herbert L.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44.)关于一般预防的局限性,帕克写道:“遏制有其局限性,对这些局限性的无视毫无疑问地促成了对它的不信任。从最明显的一点说起,遏制并非我们唯一可以利用的预防手段,对其在犯罪预防体系中的地位的任何最终评价必须有待其它可能的模式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出现以及对它们使用与遏制不一致的技术、对与遏制所特有的目的不一致地起作用的目的的范围的考察。除此之外,清楚地,刑法的遏制作用主要是对服从当代占优势的社会化影响者有效。对他们的有效是刑法的强项,而对其他人的无效则是其抵消作用的弱点。遏制不对其生活的命运已经悲惨得超出希望点的那些人构成威吓”。(注:Herbert L.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45.)可见,帕克认为完全否定刑罚的威吓作用的存在或者贬低或高估其意义,都是不客观的与片面的。刑罚的一般预防不仅在于对人的有意识的行为而且还在于对人的无意识的行为的控制:“我们关于一般遏制的运作的假设应该被扩大到还包括刑罚……对支配着在社会中的人的行为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动机的整体的效果。在无意识方面,道德准则得以学会,而且,这种学得通过如果那些规范被无视便会随之而来的不愉快的后果的威慑所强化。准则被接受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制威吓被就其作出的逼真性。而且,产生这种印象的不只是刑罚的有形的不快——生命的丧失、自由的丧失、财产的丧失。源于被作为罪犯受到惩罚的社会耻辱的羞耻感也是人们所恐惧的。而且,受遏制力所触动的不只是边沁的理性享乐主义者,而且是被足够社会化而对违犯社会规则有罪以及其经历导致其将有罪感与刑罚的形式相联系的所有人。可以退一步承认,其道德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受遏制力影响的是守法者。”(注:Herbert L.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42.)因此,帕克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两元遏制论,认为刑罚对人的有意识行为的遏制作用表现为威吓,而对人的无意识行为的遏制作用则表现为强化道德准则。
与安德聂斯相似,哈格也提出了一种三元遏制论。他认为,一般预防既包括刑罚的直接作用也包括刑罚的间接作用。刑罚的直接的一般预防作用在于威吓。它指的是“惩罚罪犯通过告诫其他人‘如果你违法,你便会遭此下场’而遏制其他人,”(注:Ernest van den Haag.Punishing Criminals:Concerning A Very Old and Painful Question,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5,p.60.)亦即刑罚通过其痛苦的代价而使意欲犯罪的人不敢犯罪。这种威吓作用并不象古典功利论所假定的那样以潜在犯罪人基于刑罚之害大于犯罪之利的算计为前提,而只是对受惩罚之苦的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回避性反应。哈格虽未直接提出刑罚的威吓只需条件反射式的回避反应便足以实现,但是,他认为,“将来的罪犯在受奖赏或惩罚手段的指导而走出迷惑时,并不比老鼠需要更多的理性。实验者必须计算他们期望的效果以及与取得效果相适应的手段。立法者也必须如此。但老鼠并不计算,立法的国民也不需计算。众所公认,人与老鼠之间存在区别,在某些情况下,区别重大。但是,无论是人还是老鼠,要对刺激或抑制作出反应,都不需要理性的计算,虽然与老鼠不同,人只要愿意便能够计算。只要受威吓的那些人能够对威吓作出反应(无论能否理智地把握威吓),立法威吓便可以因互相学习与形成习惯而有效。遏制取决于可能性,并取决于人对危险的反应的规律性,而不取决于理性。经验表明,人类在对威吓的反应方面要比动物强,在互相学习方面则要强得多。”(注:Ernest van den Haag,Punishing Criminals:Concerning A Very Old Painful Question,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5,p.113.)刑罚的间接的一般预防作用包括耻辱与形成习惯的作用。耻辱指的是刑罚通过惩罚犯罪人而向社会宣告犯罪是可耻的,从而使人们因恐惧惩罚的耻辱而不敢犯罪。关于耻辱对犯罪的遏制作用,哈格写道:“惩罚的遏制作用不只取决于实质性的痛苦,而且取决于耻辱化。”“惩罚不只是表明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是错误的,它还把违法与违法者评论为可恶的,‘可耻的’。惩罚的这种象征作用有助于形成所有重要的内在障碍,它们使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加有意识的思考地、不加权衡也抑制违法。对惩罚的耻辱的恐惧,无论如何不完全,都与对实质性的痛苦或剥夺的恐惧一样大地构成一种抑制力。只有对很少有可丧失的东西的人,惩罚的谴责作用才不具有遏制力。”(注:Ernest van den Haag,Punishing Criminals:Concerning A Very Old and Painful Question,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5,pp.63-64.)所谓形成习惯的作用是指刑罚的存在可以强化人们的守法意识,促使其形成守法的习惯。拿他本人的话来说,便是“所威吓的刑罚,即使在其不明显而直接地影响决定之时,很可能构成或至少强化人的个性中引导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避免犯罪的抑制因素。”(注:Ernest van den Haag.Punishing Criminals:Concerning A Very Old and Painful Question,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5,p.67.)
由以上介述可知,多元遏制论已在如下方面逾越了古典功利论:
首先,多元遏制论虽然肯定刑罚的一般威吓作用,而且将其作为一般预防的首要功能,但不再将其作为唯一的一般预防功能。尽管多元论者在一般预防究竟包括哪些要素上未能达成一致,但是,无论是安德聂斯与哈格的三元论还是帕克的二元论,都不再把威吓当成一般预防的唯一要素。相对于将威吓作为一般预防的代名词的古典功利论,多元遏制论更接近于对一般预防的机制的正确揭示,尽管其未必是对真理的穷尽。因为一般预防的对象不只是潜在的犯罪人,而且还包括其他守法者。而其他守法者因为不存在犯罪的意念而不可能产生对刑罚的恐惧,刑罚对其不生威吓之问题。但是,他们是作为社会成员而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刑罚以及运用刑罚的实践的影响。正如帕克所形象地指出的一样:“刑事审判的仪式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种道德剧,在其中,我们代理性地上演一场道德剧,在剧中,无辜者受到保护,损害得到报复,而犯错误者受到惩罚。促成遏制效果的不只是刑罚的威吓或者其实际的适用,而且还有作为善恶准则而确立的整个刑事司法程序,在其中我们受到了远比为恶者不得得势的书面威吓更为微妙的方式的警告。”(注:Herbert L.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43-44.)诸如此类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无论是立竿见影的还是潜移默化的,都不同程度地有助于稳固守法者的守法意识,收到遏制犯罪之效。肯定刑罚对潜在犯罪人与守法者的不同作用,既避免了将威吓作为一般预防的唯一要素而导致的以偏概全,也避免了因对威吓之外的因素的无视而对一般预防的贬低。(注:安德聂斯认为,因为“不少怀疑一般预防的人只看到恫吓效果”,所以,必须强调恫吓之外的一般预防功能即“加强道德禁忌”与“鼓励习惯性守法行为”。“即使有时不存在对刑罚的恐惧心理,也不能认为刑罚的次要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对立法者来说,最重要的不仅要达到恫吓的目的,而且要树立道德禁忌和习惯。”(挪威)安德聂斯著、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其次,多元遏制论不以犯罪是人权衡利害的结果为唯一前提。多元遏制论虽然并不排斥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犯罪是基于对犯罪之利与刑罚之害的权衡,(注:帕克认为,“边沁给了我们对真理的一丝把握。这一把握不应仅仅因为它是片面的便予以放弃,尤其是如果人们定论对真理的完整的看法无法获得。”Horbort L.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41.)但又并不把这种理性的权衡作为一般预防的唯一前提。这促成了对刑罚的威吓功能赖以发挥的前提的新的认识,克服了古典功利论将所有犯罪都作为利害权衡的产物的片面性,避免了立足于并非所有犯罪都是利害权衡的结果而对威吓功能的怀疑乃至否定。
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是,多元遏制论并不排斥报应作为刑罚的根据之一的正当性。古典功利论之所以倍受责难,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将报应完全排斥在刑罚的正当根据之外,将功利乃至一般预防作为了刑罚的唯一根据。与此不同,多元遏制论在肯定一般预防作为刑罚根据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也承认报应作为刑罚的根据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换言之,多元遏制论是将一般预防作为刑罚的根据之一而不是将其作为刑罚的唯一根据予以肯定。正是如此,当代一般预防论者几乎无一不是一体论者。鉴于刑罚一体论是有待另文专门评述的一个主题,关于多元遏制论者对一般预防与报应以及个别预防的关系等的认识,在此且不详述。需要强调的仅在于,在多元遏制论者看来,一般预防并非与报应互不相容的两个概念。多元遏制论对报应的兼顾使多元遏制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来自报应论的责难,构成其在当代赖以立足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