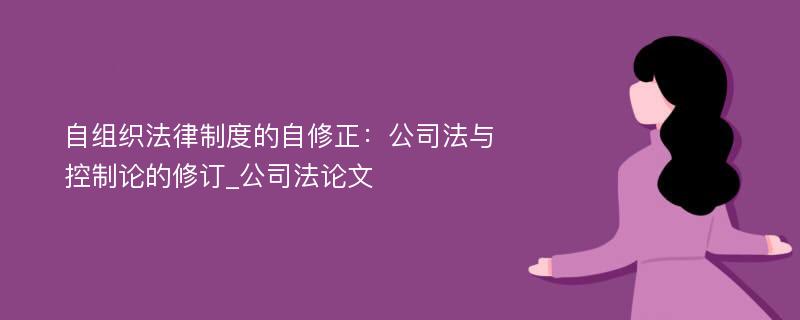
一个自组织法律系统的自我修正——《公司法》修订与控制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控制论论文,公司法论文,自我论文,组织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控制论是现代系统论的重要理论之一,是一门研究系统自动控制规律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如何通过控制信息的变化和反馈作用,使系统自动按照人们预定的程序运行并最终达到最优目标。控制论的诞生为人们对系统的管理和控制提供了一般方法论的指导。当控制论开始由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向经济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发展后,控制论开始被运用于对法律的研究。法律本身既是一个系统,又是对社会系统实现控制的重要序参量,是一种令社会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重要控制信息。很显然,这种控制信息的发布和修正,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进化产生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引起社会经济系统的某些结构性突变。因此在一个法治社会,立法者的每个立法举措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系统的极大关注。作为规范市场经济“基本细胞”的基本法,公司法的本次修订就是这样的一个立法举措。
一、公司法修订频度与反馈控制方法
从1993年制定颁布以来,除了在1999年被当时的所谓“新经济”“撞了一下腰”而小修了几处外,我国《公司法》十年来基本未曾修正。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立法现状在中国并不少见。许多人坚持认为,法律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否则将有损于法律的权威。从控制论方法来看,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当公司法作为正式的控制信息向社会经济系统输入后,立法者必须时刻关注系统对于该信息的反馈。如果立法者输入的负反馈控制信息未能适当和有效地抵消系统的内熵,(注:所谓的“熵”(Entropy)就是系统无序化的量度。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由于每个事物都要实现自己最大的多样性,因而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由有序走向无序,系统熵值不断增加,最终归于“热寂”,即系统自我崩溃。系统减熵的可能性在于系统的开放性,一个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的能量和物质交换,向环境输出正熵流并从环境引进负熵流以抵消系统内熵的产生,形成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使系统内部熵值处于递减状态,系统就能通过涨落达到有序。这种现象可称为系统的自组织。) 那么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就会面临系统崩溃的危险。因此立法者必须及时整理并破译收集到的系统正反馈信息,适时调整负反馈控制信息,这就是法律的修订。而如果输入的负反馈控制信息适当地抵消了系统的内熵输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就可能暂时地呈现出平稳的良性循环状态,法律控制的目标暂时地达到了。但是即便如此,人们也不能弹冠相庆,欢呼法律从此不用修改了。因为作为一个开放式的系统,外界环境的变化也将必然地引发系统内熵的变化,当这种变化达到了一定的临界点时,法律输入的固有控制信息很可能就不再适当甚至不再正确了。这时法律依旧面临修改压力。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暂时抛弃对法律的崇拜,而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控制信息来看待,就可以知道,公司法绝不是一次性消费的纸巾,也不是数十年不变的耐用消费品,它应该是一股往复循环、不绝不断的信息流。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速度决定了中国公司法的修订应该具有一定的频度。
即使没有控制论方法的支持,这也是一个明显的道理:如果公司法的规定不再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那么为什么不修改?所谓的法律权威应该靠立法时的科学审慎,尽可能制定出一部适应社会经济生活需要的良法,才能有效地防止出现频繁修改的现象。如果当初就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应该适时地去修改它,以令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讲,社会经济系统需要我们调整多少次控制信息,我们就应该调整多少次;社会需要我们修改多少次公司法,我们就应该修改多少次。这个观点看上去似乎有些偏颇,但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公司法的修改的确一直十分频繁,几乎是一年一改,日本公司法甚至会一年修改多次。而中国的公司法则是十年一张不变的脸。其实从1994年开始执行后不久,我们就发现公司法中存在着许多十分“低级”的瓶颈:比如公司转投资比例不得超过50%的规定极大地束缚了市场投资行为;比如禁止非国有独资的一人公司,但是实践中实质的一人公司却比比皆是,各种挂名股东和“夫妻老婆店”无法禁绝;又比如原公司法中一直为人诟病的注册资本高门槛,以及屡屡出现的由于过分强调人合性而给无数股东带来深切痛苦的公司治理僵局,都可以称得上我国公司法的十年痼疾。然而对于这些我们很早就已经看清的问题,公司法却没有及时予以修订。十年来,我们就这样困守着一部千疮百孔的旧法,一心期待着理想中全面修订契机的带来,却不惮于坐看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在不当控制信息的纵容和误导下面临动荡和僵化的危险。相信本次公司法的修订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公司法的定量分析与统计力学
在我国公司法中,数字标准随处可见,其主要体现在金额、期限和比例等方面。本次修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原有部分标准进行了修正。比如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从10万元降到了3万元,股份有限公司从1000万元降到了500万元;又比如从无形财产出资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0%,改为货币出资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30%;至于各种“30日内答复”、“2至50人”、“20万以下罚款”之类的规定,在修订后的公司法中更是比比皆是。
可能许多人已经熟视无睹,然而如此之多的数字化标准出现在一部法律中,是否应该问问:这些数字怎么来的?或者通俗地讲:为什么是3万,而不是5万?为什么是30%,而不是50%?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法律的量化命题。从牛顿时代开始,西方科学先驱们就曾梦想实现法律的科学化和纯量化,以排除人为的不当干扰,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这只是一个幻想。然而,尽管法律在本质上依旧是一个定性判断的产物,但随着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法律的确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数字标准。定性的法律似乎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定量的彼岸。
为法律进行定量分析的确困难,如果没有取得科学方法的支持,我们永远都只能在随心所欲与束手无策之间徘徊。控制论中的黑箱理论对此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所谓黑箱,就是指那些不能打开箱盖,又不能从外部观察内部状态的系统。而黑箱方法就是通过考察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关系来认识系统功能的一种研究方法。对于人们来讲,这个极其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系统,就像一个无法揭开又难以观察的大黑箱。法律被制定了,但是在输入这个社会系统后,就无从知晓这些控制信息是如何在系统内发挥作用的。法律的制定活动有时更像是一种比赛想像力的游戏。在某些先验或个别经验的前提假设基础上,大家对社会经济系统这个魔术师的大黑箱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展开了一场猜想比赛,然后在这个猜想的基础上编造我们的法律,最后将其往黑箱子里一扔了事。这真是个可笑而无奈的现实。
黑箱理论自然也还不足以帮助人们真的揭开这个大黑箱,但是它将人们指引到了一条相对正确的道路之上。黑箱理论提醒人们,既然无法揭开和透视这个黑箱,那么就应该耐心观察一下它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法律是无法完全洞察每一个主体的内心活动的,黑箱子在微观系统与宏观系统之间制造了巨大的鸿沟。而统计力学理论的诞生则为我们架构了一座从微观走向宏观的桥梁。当年人们认识到气体由相互作用的亿万个分子组成,尽管对一对分子的相互作用规律比较清楚,但是由于分子太多,对于这亿万分子的整体系统——气体的性质,却一直无法取得突破。统计力学认为,实现从微观走向宏观的奥秘在于: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知道每个分子的运动,才能知道作为整体的气体的性质。宏观知识不要求知道那么多细节,它只要求得到整体分子的平均行为。统计力学的启示是,研究复杂的系统应该多采用统计的方法,才能透彻地看到局部和整体的过渡,才能避开不必要的细节,把握住主要的现象。(注:钱学森:《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资料来源:http://www.hyswz.com/lh/Articles/ShowArticle.asp? ArticleID=901,访问日期为2005年12月1日。)所以,立法也必须善于采用调查和统计方法,才能更准确地把握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也才能进行相对精确的控制。无法实现纯量化并不能成为立法工作闭门造车的挡箭牌。
由此可见,从“需要数字标准”到“这个数字标准”,这中间应该还有一段十分漫长的路要走。既然前方的目的地是数字化的,那么这条路本身也应该是数字化的。简明扼要地说,我们主张在一个数字标准的背后应该由一群数据来作支撑,而不是一两句模糊的定性语言。因为我们相信,一定程度的定量化分析是防御藏身于定性语言背后那份随心所欲的最好武器。这群数据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采集。如果我们要规定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额,我们可以委托民意测验机构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民众对不同注册门槛的支持概率;我们可以统计分析创业者创办公司时的平均资产和融资能力,以对普通创业者的资本承受力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即便你无法进行任何数量化分析,那么充分博弈也是一种准数量化方法。这好比购物,其实消费者对商品的真实成本一般也不太清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依靠讨价还价获得一个相对均衡的价格。我们完全可以遴选一定数量的代表进行立法听证,统计不同意见并作出平衡;我们还可以在官方网站上设立投票箱,让全社会的观点就此展开充分的博弈。
笔者相信这些数量化的努力绝不可能使立法达到完全的精确。但是笔者同样相信,如果一个数字标准的诞生是建立在对众多数据的充分采集和合理分析的基础上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对那些也许永远无法消弭的模糊空间抱以最大程度的宽容。
三、公司法修订意见征求与功能模拟方法
所谓的功能模拟方法,就是用功能模型来模仿客体原型的功能和行为的方法。比如猎手向猎物开枪之前的瞄准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功能模拟。功能模拟法为仿生学、人工智能、价值工程提供了科学方法,也为我们立法活动的科学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功能模拟方法告诉人们,为了达到精确的控制效果,立法者应该尽可能在发出正式的控制信息之前,向系统输入一个模拟的正反馈信息,然后根据系统的负反馈信息来评估和调整正反馈的信息量,最后才向社会经济系统发出正式的控制信息。通过这样的信息反馈的反复运动,来达到对系统的最优控制。在立法中,尽管我们可以采用直接的控制信息输入和调整的方法实现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直接控制,但是由于法律这种信息的社会关涉度十分巨大,一旦输入错误信息,将可能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结构造成严重损伤,从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因此当立法者酝酿控制信息尤其是重大控制信息的时候,应尽可能地经过功能模拟的环节,将错误控制的隐患减到最低程度。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一部重要的法律或政策往往突然间出台,社会经济系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承受这种因利益格局的突然变动带来的冲击。这种未经功能模拟的立法活动好比不瞄准就开枪的行为,其危害性很大。由于模拟环节的缺位,我国立法史上并不乏不当乃至于错误的法律和政策。这一方面损伤了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结构,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控制信息的权威性和确定性。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我国的立法程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甚至规章和政策出台之前,立法部门往往会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向全社会发出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有时还经过多次的反复过程或者多个起草小组齐头并进的立法话语权竞争过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功能模拟方法。很显然本次公司法修订就是这样一次成功的立法活动。从公司法决定修订开始,政界、学界到业界都纷纷建言献策,深度参与公司法修订。而立法机关也深入进行立法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公司法修改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在认真分析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议案和提案的同时,通过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广泛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部分地方政府、有关行业协会、企业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并委托有关研究机构对有关重要问题作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印发给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部分地方政府、有关行业协会、企业和专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工作小组还到广东、广西、上海、重庆、山东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直接听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和专家的意见。同时在上海召开了国际研讨会,邀请美、德、日、韩等国家和香港特区的公司法专家共同就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讨。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形成了修订草案,国务院专门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法工委汇报后,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总理签署后,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审议程序。本次公司法修订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与立法意见的充分征求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一个法律自组织系统的自我修正
公司法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法律系统。作为一部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公司塑造模拟人格的法律,公司法的核心任务就是将公司打造成一个市场的类生命系统,令其具备自我思维、自我执行、自我发展和自我纠错的能力。本次公司法的修订,就是这个自组织法律系统蓄势多年后的一次比较成功的自我修正,它的浴火重生必将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