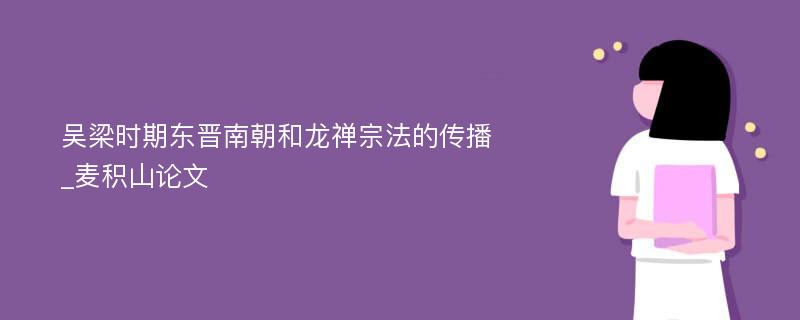
五凉时期河陇禅法在东晋南朝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南朝论文,时期论文,河陇禅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10-0120-10
永嘉年间,“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河陇尤其是河西成为中原移民的迁入区,使五凉时期的河陇,成为北中国的文化中心。① 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魏军破姑臧,沮渠牧犍降,北凉亡。《魏书·世祖纪》载:“(太延五年)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馀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馀家于京师。”如果按每户五口计算,估计至少有十五万人从凉州被迁往平城。② 北魏平定凉州之后,把大量河西士族迁往平城,其学术典章制度也被完整地转移到了北魏首都平城。之后几经辗转,最终成为隋、唐学术典章制度的渊源。有学者更是有意无意地认为,河西学术的传播只是东传平城而已,而由河西迁移到南方的人口几乎为零,其学术对长江流域的影响也很有限。似乎仍然看不出两晋南北朝时期,地处西北的北中国学术中心——河陇,与东南移民新开发区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文化交流。
然而,五凉时期的河陇,高僧辈出,除了那些当时知名的高僧被迁往平城,而留在当地,还有一些不知名但却学养丰厚的年轻后生,亦能在日后南下江左的过程中,继续传播河陇禅法这一使命。因此,河陇文化既有转移保存于北魏的情况,也有转移传播于南朝的事实。相比而言流寓南朝的河陇士人的情况,见于史乘者少之又少,以至于这个论题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本文正是通过对禅修僧人流徙的研究,来揭示魏晋以降的河陇文化的外播。
一、河陇禅法的译介与修习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陇佛学在两个方面最有建树,一是凉土译经,二是凉州禅法。五凉时期的河陇,成为禅法传播和修习的最发达地区。从地域上来看,五凉时期河陇禅法有两个中心,一是河西的姑臧,主要是西国高僧和河西本土高僧在这里弘法;二是陇右天水的麦积山,主要是关中来的高僧在这里弘法。
在姑臧传播禅法的高僧有昙无谶和沮渠京声。昙无谶在弘扬禅法方面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译经方面。《高僧传·昙无谶传》载:
十岁,同学数人读呪,聪敏出群,诵经日得万余言。初学小乘,兼览五明诸论,讲说精辩,莫能詶抗。后遇白头禅师,共谶论议,习业既异,交诤十旬。谶虽攻难锋起,而禅师终不肯屈,谶伏其精理,乃谓禅师曰:“颇有经典,可得见不。”禅师即授以树皮《涅槃经》本。谶寻读惊悟,方自惭恨。以为坎井之识,久迷大方,于是集众悔过,遂专大乘。至年二十,诵大小乘二百余万言。
白头阐师授予昙无谶的树皮《涅槃经》,即《大般涅槃经》,是昙无谶为河西王沮渠蒙逊所译十一部佛经之一,也是昙无谶所译佛经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谶以《涅槃经》本,品数未足,还外国究寻,值其母亡,遂留岁余。后于于阗,更得经本《中分》,复还姑臧译之。后又遣使于阗,寻得《后分》,于是续译为三十三卷。以伪玄始三年(414年)初就翻译。至玄始十年(421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袠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谶云:‘此经梵本,本三万五千偈,于此方减百万言,今所出者止一万余偈。’”③《大般涅槃经》倡导如来常住、涅槃常乐我净、众生悉有佛性乃至阐提成佛等佛教义理。故凉州释道朗《大涅槃经序》云:“大般涅槃者,盖是法身之玄堂,正觉之实称,众经之渊镜,万流之宗极。……是以斯经解章,叙常乐我净为宗义之林。开究玄致为涅盘之源。用能阐秘藏于未闻、启灵管以通照。拯四重之痈疽,拔无间之疣赘。阐秘藏则群识之情畅,审妙义之在己。启灵管则悟玄光之潜映,神珠之在体。”④
昙无谶在弘扬禅法的同时,还在河西带出一批禅法弟子:
初谶在姑臧,有张掖沙门道进,欲从谶受菩萨戒,谶云:“且悔过。”乃竭诚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诣谶求受,谶忽大怒,进更思惟,但是我业障未消耳。乃勠力三年。且禅且忏,进即于定中,见释迦文佛与诸大士授己戒法,其夕同止十余人,皆感梦如进所见。进欲诣谶说之,未及至数十步,谶惊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当更为汝作证。”次第于佛像前为说戒相。时沙门道朗,振誉关西,当进感戒之夕,朗亦通梦。乃自卑戒腊,求为法弟,于是从进受者千有余人,传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谶之余则。有别记云,《菩萨地持经》应是伊波勒菩萨传来此土,后果是谶所传译,疑谶或非凡也。
其弟子中最知名的是河西高僧道朗和沮渠京声。《昙无谶传》载:“蒙逊有从弟沮渠安阳侯者,为人强志疎通,涉猎书记。因谶入河西,弘阐佛法,安阳乃阅意内典,奉持五禁,所读众经,即能讽诵,常以为务学多闻,大士之盛业。少时求法度流沙,至于阗,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师佛驮斯那,谘问道义。斯那本学大乘,天才秀发诵半亿偈,明了禅法,故西方诸国号为人中师子。安阳从受《禅秘要治病经》,因其梵本,口诵通利。既而东归,向邑于高昌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晋文。”⑤
河陇禅法的流播,浮驮跋陀禅师起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浮驮跋陀,即浮驮跋多罗(Buddhabhadra),又译作觉贤。浮驮跋陀能够东行中土,与凉州僧人智严的真诚邀请不无关系。关于智严的身世以及他请得浮驮跋陀东归的情况,《高僧传·智严传》载:
释智严,西凉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纳衣宴坐,蔬食永岁,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遂周流西国,进到罽宾,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谘受禅法。渐深三年,功踰十载。佛驮先见其禅思有绪,特深器异。彼诸道俗闻而叹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门矣!”始不轻秦类,敬接远人。
时有佛驮跋陀罗比丘,亦是彼国禅匠,严乃要请东归,欲传法中土,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⑥
智严“精懃”和“禅思有绪”,为他请得浮驮跋陀东归打开了一扇大门。由“‘秦地乃有求道沙门矣!’始不轻秦类,敬接远人”,可以看出,尽管佛法流播中土已有些时日,但与西国相比,还是有不少差距,因此浮驮跋陀禅师的到来就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踰沙越险,达自关中”不久的跋陀,“横为秦僧所摈”,但还是给凉州带出一批禅法弟子。如弟子宝云,凉州人。“少出家,精懃有学行,志韵刚洁,不偶于世,故少以方直纯素为名,而求法恳恻,亡身殉道,志欲躬覩灵迹,广寻经要。遂以晋隆安之初,远适西域。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涉履流沙,登踰雪岭。懃苦艰危,不以为难。遂历于阗、天竺诸国,备睹灵异。乃经罗刹之野,闻天鼓之音,释迦影迹多所瞻礼。云在外域,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诂训,悉皆备解。后还长安,随禅师佛驮跋陀业禅进道。”⑦
其实,受浮驮跋陀禅师影响最大的还是麦积山玄高僧团。玄高,俗名魏灵育,姚秦弘始四年(公元402年)生,冯翊万年(今陕西省万年县)人。《高僧传·玄高传》载:
至年十五,已为山僧说法。受戒已后,专精禅律。闻关中有浮驮跋陀禅师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师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叹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于是卑颜推逊,不受师礼。
玄高是否师承浮驮跋陀,疑点颇多,汤用彤说:“浮驮跋多罗在弘始十三年已经离长安南下,其时玄高只十岁。而浮驮跋多罗亦未闻住石羊寺,则此所谓浮驮跋陀者,不悉指何人。若系觉贤,则《高僧传》谓高于弘始四年生,必有误也。”⑧ 还有一种可能是,因浮驮跋多罗“在长安,大弘禅业,四方乐靖者,并闻风而至”⑨,后生之玄高只是受了浮驮跋多罗禅法的影响,或者是浮驮跋多罗的再传弟子,因此就有了所谓的“师承”的关系。其实从浮驮跋陀“卑颜推逊,不受师礼”,已经点明了他们之间并没有举办过具有象征意义的拜师礼,所以算不上是师生关系。但无论哪种情况,玄高受过浮驮跋陀禅法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退一步讲,即便玄高在关中时受浮驮跋陀的影响有限,那么日后驻锡麦积山则一定会使其禅法精进。据《高僧传·玄高传》载:
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在此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时乞佛炽盘跨有陇西,西接凉土。有外国禅师昙无毘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陇右之僧禀承盖寡。高乃欲以己率众,即从毘受法。旬日之中,毘乃反启其志。时河南有二僧,虽形为沙门,而权侔伪相。恣情乖律,颇忌学僧,昙无毘既西返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谗构玄高,云蓄聚徒众,将为国灾。曼信谗便欲加害,其父不许。乃摈高往河北林阳堂山。山古老相传,云是群仙所宅。
可见,麦积山的条件对玄高的习禅弘法颇为有利:其一,在玄高到来之前,已经有长安沙门昙弘隐居于此,估计早已经把长安禅法传至麦积山;其二,“有外国禅师昙无毘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玄高“以己率众,即从毘受法。旬日之中,毘乃反启其志”;其三,玄高曾进游北凉禅学中心姑臧,“沮渠蒙逊深相敬事,集会英宾,发高胜解”,多方交流,有助于麦积山禅学的提高;其四,乞佛炽盘跨有陇西时,麦积山无疑是其国家宗教中心,各方面的条件一定不会差的。诸多因缘际会,大大提升了麦积山的禅学境界,使其成为陇右禅法修习的中心。玄高还在麦积山带出了一批禅法弟子:
高徒众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禅慧弥新,忠诚冥感,多有灵异。磬既不击而鸣,香亦自然有气。应真仙士,往往来游。猛兽驯伏,蝗毒除害。高学徒之中,游刃六门者,百有余人。有玄绍者,秦州陇西人。学究诸禅,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净,倍异于常。每得非世华香,以献三宝。灵异如绍者,又十一人。绍后入堂术山蝉蜕而逝。⑩
玄高在麦积山弘扬禅法时,规模宏大,弟子众多,甚至对“河南王”西秦乞伏炽槃的皇权都构成一定的威胁。其中如玄绍这样“学究诸禅,神力自在”的弟子多达十一人。
二、东晋南北朝时期河陇禅法的外播
河陇地处边塞,是一个移民频率极高的区域。永嘉丧乱(307—313)之前,河西和关中同为佛教发达区,因此,如月支高僧竺法护以及在河西本土成长起来的众多高僧,主要往来于河西与长安之间,译经弘法,南下江左的人数少之又少。
永嘉之乱至公元439年之间,河陇移民迁入与迁出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西部,远离中原乱世的河西是移民迁入区。《资治通鉴》载:“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1) 除了一些中原士人和僧人进入河西外,河西还是西国胡僧汇聚的一个区域,如西域高僧佛图澄,天竺高僧鸠摩罗什,罽宾沙门昙无谶等,都是这个时候来到河西的。可谓“鸿风既扇,大化斯融。自尔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传度经法,或教授禅道,或以异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本土桑门也是“含章秀起,群英间出,迭有其人”。(12) 东部,由于一些士人无法接受异族统治的事实,抱着“我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的心态归于江东(13),结果使地近关中的陇右以及宁夏平原,成为移民迁出区。移民中的名门望族有北地灵州的傅氏和安定朝那的皇甫氏等。
北魏平定凉州之后,是河陇移民星散的一个时期。尤其是高僧,他们西入西域,东迁平城,南下江左。由于西入西域的禅僧主要以来华的西域高僧的回归为主,如浮陀跋摩“避乱西返,不知所终”,因此本文探讨河陇禅法在长江沿线的外播。
河陇僧人和士人南投江左,在永嘉之乱后就已经开始。北地灵州傅氏家族的傅亮等,永嘉丧乱后南迁,入刘宋朝为官。(14) 亦有一位傅氏家族出产的高僧,也在此时南投江左,弘扬禅法,即竺僧显。“竺僧显,本姓傅氏,北地人。贞苦善戒节,蔬食诵经,业禅为务。常独处山林,头陀人外。或时数日入禅,无饥色。时刘曜寇荡西京,朝野崩乱。显以晋太兴之末(321年),南逗江左。复历名山,修己恒业。”(15) 竺僧显“复历名山,修己恒业”,一定把河陇禅法带到了江左,只是他游徙不定,其具体影响已无从可知。
河西高僧竺昙猷亦在永嘉之乱后驻锡扬州始丰(今浙江天台)赤城山,弘扬禅法,成为南派禅学的开创者之一。(16) 竺昙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石城山是竺昙猷入扬州后的第一个驻锡处,即今浙江新昌县南明山,“后移始丰赤城山石室坐禅”。赤城山是竺昙猷终老之处,“赤城山山有孤岩独立,秀出干云。猷抟石作梯,升岩宴坐,接竹传水,以供常用,禅学造者十有余人。王羲之闻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反”(17)。竺昙猷以太元之末(396年)卒于山室,尸犹平坐,而举体绿色。
河陇禅僧南投的路线,一般是假道梁益,顺江而下,东适江左。因此沿江形成了成都、荆州、庐山和建康(今南京)等多个驻锡中心,其中到达建康的高僧最多,荆州次之,驻锡庐山的僧人则以南渡河陇士人的第二代为主。
——建康 为东晋、南朝都城。永嘉之乱起,相对安宁的建康及周边地区,成为北方土族移民的首选目的地。河陇禅僧亦不例外,最先到达建康的是凉州禅僧宝云。公元411年,驻锡长安的佛驮跋陀横为秦僧所摈,徒众悉同其咎。佛驮跋陀“率侣宵征,南指庐岳”,因“姚兴敕令追之”,故宝云在中途奔散。
后来,宝云与南投后曾辗转驻锡于庐山和江陵的佛驮跋陀,“共归京师安止道场寺”。在道场寺时,“众僧以云志力坚猛,弘道绝域,莫不披衿谘问,敬而爱焉。云译出《新无量寿》,晚出诸经,多云所治定。华戎兼通,音训允正,云之所定,众咸信服。初关中沙门竺佛念善于宣译,于苻姚二代,显出众经。江左译梵,莫踰于云,故于晋宋之际,弘通法藏,沙门慧观等,咸友而善之”。出于习禅僧人的习惯,“云性好幽居,以保闲寂,遂适六合山寺,译出《佛本行赞经》。山多荒民,俗好草窃,云说法教诱,多有改更,礼事供养,十室而八。顷之,道场慧观临亡,请云还都,总理寺任,云不得已而还。居道场岁许,复更还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四”。(18) 从中不难看出,宝云南投之后,辗转于道场寺和六合山寺之间,在译经的同时,还对白、黑两界教化颇多。
智严虽然师承于佛驮先,但请得佛驮跋陀东归后,在长安“常依随跋陀”,因此当佛驮跋陀南投时,智严也与其分散了。《高僧传·智严传》载:
顷之跋陀横为秦僧所摈,严亦分散,憩于山东精舍,坐禅诵经,力精修学。晋义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长安,克捷旋斾,涂出山东。时始兴公王恢从驾游观山川,至严精舍,见其同止三僧,各坐绳床,禅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觉,于是弹指,三人开眼,俄而还闭,问不与言。恢心敬其奇,访诸耆老,皆云:“此三僧隐居求志,高洁法师也。”恢即启宋武帝,延请还都,莫肯行者。既屡请恳至,二人推严随行。恢怀道素笃,礼事甚殷,还都,即住始兴寺。严性爱虚靖,志避諠尘。恢乃为于东郊之际,更起精舍,即枳园寺也。
南投后的智严,于枳园寺静心译经,“严前于西域所得梵本众经,未及译写,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门宝云译出《普曜》、《广博严净》、《四天王》等”,智严“不受别请,常分卫自资,道化所被,幽显咸服”。但因智严“清素寡欲,随受随施,少而游方,无所滞着。禀性冲退,不自陈叙,故虽多美行,世无得而尽传”。(19)
智严、佛驮跋陀以及其弟子宝云、慧观等驻锡于建康,为北魏平定凉州后河陇禅僧驻锡京师创造了条件,凉州禅法高僧慧览就是此时驻锡京师的。《高僧传·慧览传》载:
释慧览,姓成,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罽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要。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览还至于填,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移罗浮天宫寺。宋文请下都止钟山定林寺。孝武起中兴寺,复勅令移住。
慧览南投,途经吐谷浑(今青海东部)的领地,东南入益州,顺江而下至建康,是河西政权与东晋、刘宋政权往来的主要路线。慧览驻锡京师中兴寺时,“京邑禅僧皆随踵受业。吴兴沈演、平昌孟顗并钦慕道德,为造禅室于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余矣”(20)。
元嘉二十二年闰(445年)五月十七日从平城逃出的玄畅,以八月一日达于扬州。《高僧传·玄畅传》载:
洞晓经律,深入禅要。占记吉凶,靡不诚验。坟典子氏,多所该涉。至于世伎杂能,罕不必备。初《华严》大部,文旨浩博,终古以来,未有宣释。畅乃竭思研寻,提章比句。传讲迄今,畅其始也。又善于《三论》,为学者之宗。宋文帝深加叹重,请为太子师,再三固让,弟子谓之曰:“法师之欲弘道济物,广宣名教。今帝主虚己相延,皇储蓄礼思敬,若道扬圣君,则四海归德。今矫然高让,将非声闻耶?”畅曰:“此可与智者说,难与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觉自尔。迁憩荆州,止长沙寺。时沙门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经》等,畅刊正文字,辞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测也。(21)
以上南投的诸位禅僧,都是与佛驮跋陀有关,不是他的弟子便是他的友人。值得注意的是,昙无谶本人虽没有涉足江左,但其主持的河西禅法同样流播至京师。元嘉中昙无谶所出诸经,传至建康,其中就有《大般涅槃经》。“晋末初宋元嘉七年,《涅槃》至阳(扬)州。尔时里山慧观师,令唤生法师讲此经也。”(22)《大涅槃经》初至宋土,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措怀”(23),京师道场寺慧观“志欲重寻《涅槃后分》,乃启宋太祖资给,遣沙门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24),未果。后慧观、慧严与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25)。竺道生得到《大般涅槃经》后,既于庐山开讲。《高僧传·竺道生传》载:“《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称禅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生既讲说,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26) 从此南北各大家,都提倡《涅槃》,讲疏竟出,直到唐初不衰。
昙无谶的弟子——沮渠安阳侯,也在北魏平定凉州后南下建康。《高僧传·玄高传》载:“及伪魏吞并西凉,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人世,常游塔寺,以居士身毕世。初出《弥勒》、《观音二观经》,丹阳尹孟頭,见而善之,深加赏接。后竹园寺慧濬尼,复请出《禅经》,安阳既通习积久,临笔无滞,旬有七日,出为五卷。顷之,又于钟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泥洹经》一卷。安阳居绝妻拏,无欲荣利,从容法侣,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后遘疾而终。”(27)
——庐山 为南朝的佛教中心。驻锡庐山的河陇僧人,主要是南渡后的皇甫氏。永嘉之乱后,著名学者,安定朝那皇甫谧的儿子皇甫方回避乱荆州。《晋书》载:“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征,不起。避乱荆州,闭户闲居,未尝入城府。蚕而后衣,耕而后食,先人后己,尊贤爱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28) 皇甫方回迁居荆州襄阳后,其家族中共出产三位高僧,即道温、慧虔和僧慧。他们都与庐山有关。
道温,“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谧之后也。少好琴书,事亲以孝闻。年十六入庐山,依远公受学。后游长安,复师童寿。元嘉中还止襄阳檀溪寺。善大乘经,兼明数论”(29)。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确然。憩庐山中十有余年。道俗有业志胜途者,莫不属慕风采。罗什新出诸经,虔志存敷显,宣扬德教。以远公在山,足纽振玄风。虔乃东游吴越,嘱地弘通”(30)。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谧之苗裔,先人避难寓居襄阳,世为冠族。慧少出家,止荆州竹林寺,事昙顺为师。顺庐山慧远弟子,素有高誉,慧伏膺以后专心义学。至年二十五,能讲《涅槃》、《法华》、《十住》、《净名》、《杂心》等。性强记,不烦都讲,而文句辩折,宣畅如流。又善《庄》《老》,为西学所师”(31)。可见,居住在襄阳的皇甫氏,“世为冠族”。家族中出家人,主要在庐山及周边地区弘法。自太元九年至义熙十二年,慧远驻锡庐山,凡三十二年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32) 故此三人都与慧远有联系。其中道温跟随慧远问学。慧虔“憩庐山中十有余年”,因“以远公在山,足纽振玄风”,才“东游吴越,嘱地弘通。以晋义熙之初,投山阴嘉祥寺。克己导物,苦身率众,凡诸新经,皆书写讲说”。而僧慧则属于慧远的再传弟子。
——荆州 荆州之江陵,南临长江,是长江中游东西南北水陆交通枢纽。玄高弟子僧隐南下后,即驻锡江陵琵琶寺。僧隐,姓李,秦州陇西人。“隐年八岁出家,便能长斋。至十二蔬食。及受具戒,执操弥坚。常游心律苑,妙通《十诵》,诵《法华》、《维摩》。闻西凉州有玄高法师禅慧兼举,乃负笈从之。于是学尽禅门,深解律要。高公化后,复西游巴蜀,专任弘通。顷之东下,止江陵琵琶寺。咨业于慧彻。彻名重当时,道扇方外。隐研访少时,备穷经律,禅慧之风,被于荆楚。州将山阳王刘休祐及长史张岱,并咨禀戒法。后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税驾禅房,屈膝恭礼。”(33) 玄高的另一个弟子僧印亦南下荆州弘扬禅法。僧印,姓樊氏,金城榆中人(今兰州市渝中区)。“释玄高弟子,性腹清纯,意怀笃至。与之久处者,未当见慢忤之色。下接庸隶,必出矜爱之言。振恤贫餧,有求无逆。心道聪利,修大乘观,所得境界,为禅学之宗。省削身口,具持净律,尝在江陵,教一比丘受禅,颇有所得。”(34) 曾分别师承智猛和玄畅的禅僧法期,“十四出家,从智猛谘受禅业,与灵期寺法林同共习观。猛所谙知,皆已证得。后遇玄畅,复从进业。及畅下江陵,期亦随从。十住观门,所得已九。有师子奋迅三昧,唯此未尽。畅叹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东探禹穴,南尽衡罗。唯见此一子,特有禅分’”(35)。后卒于荆州长沙寺,春秋六十有二。凉州高僧僧朗,在北魏平定凉州时,“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便随道自进,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不测其终。”(36) 可见荆州亦有凉州禅法传入。
——广汉和成都 早在三国时,河陇已有很多士人入蜀汉就业。这固然与陇右和巴蜀毗邻有关,最主要的还是河陇“六郡良家子”以儒学为重,故统治者“正统”与否,常常成为他们择主而事的标准。永嘉之乱后,有两位河陇禅僧驻锡广汉,其一为阎兴寺的东晋贤护,姓孙,凉州人,“常习禅定为业,又善于律行,纤毫无犯”(37)。其二为法成。法成,凉州人。“十六出家,学通经律。不饵五谷,唯食松脂,隐居岩穴,习禅为务。元嘉中,东海王怀素出守巴西,闻风遣迎,会于涪城。夏坐讲律,事竟辞反。因停广汉,复弘禅法。”(38)
高僧智猛,“禀性端明,励行清白,少袭法服,修业专至,讽诵之声,以夜续日。……以伪秦弘始六年甲辰之岁,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西入流沙”,遍历西国后,“于凉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传记所游历。元嘉末卒于成都”。(39) 驻锡成都的禅僧还有敦煌人道法。道法“弃家入道,专精禅业,亦时行神呪。后游成都,至王休之、费铿之,请为兴乐、香积二寺主,训众有法。常行分卫,不受别请及僧食”(40)。玄高弟子玄畅晚年亦入蜀弘扬禅法。《高僧传》载:玄畅“迄宋之季年,乃飞舟远举,西适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画作金刚密迹等十六神像。至升明三年,又游西界,观瞩岷岭,乃于岷山郡北部广阳县界,见齐后山,遂有终焉之志。仍倚岩傍谷,结草为庵。弟子法期见神人乘马,着青单衣。绕山一匝,还示造塔之处。以齐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齐兴。正是齐太祖受锡命之辰,天时人事,万里悬合。时傅琰西镇成都,钦畅风轨,待以师敬”(41)。
由此可见,进入南朝的河陇高僧,无论从数量还是影响方面都远远超过东去平城的高僧,何况平城的高僧玄高不久就死在北魏拓跋氏的屠刀之下了,而他的得意弟子平城玄畅、陇右僧隐等,又都转道南渡。因此河陇禅法几乎完整地传播到了长江流域。
三、促使河陇禅法南播的原因
《高僧传·习禅》对中国早期禅法的流播状况作了如下总结:“自遗教东移,禅道亦授。先是世高、法护译出《禅经》。僧先、昙猷等,并依教修心,终成胜业。故能内踰喜乐,外折妖祥。摈鬼魅于重岩,覩神僧于绝石。及沙门智严躬履西域,请罽宾禅师佛驮跋陀更传业东土。玄高、玄绍等亦并亲受仪则。出入尽于数随,往返穷乎还净。其后僧周、净度、法期、慧明等亦雁行其次。”可见,以竺法护,竺昙猷、智严、玄高、玄绍和法期等为主的河陇习禅僧人的东向迁徙过程,也是禅法传入东土后,自西北向东南、由边郡向内郡的传播过程。
由于禅法的修习,非常注重师承,可谓“人在山中学道,无师,道终不成”,因此禅法的外播是以高僧为载体的。虽然一路可以化缘,又有寺庙可供歇脚的僧侣的迁徙能力,要强于拖家带口的庶民百姓,但他们迁徙仍然不出移民史的研究范畴,适合用人口学的方法分析他们南迁的内在原因。从人口学的角度而言,一次移民事件的发生,涉及三个必备的条件,一是移民迁出区要产生足够的推力,把移民从出发地推出来;二是迁出区与迁入区之间要有通畅的交通条件;三是迁入区要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才有可能成为移民迁移的目的地。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影响河陇禅法南播的历史因素。
(一)迁出区对河陇禅法南播的推力
其一是永嘉丧乱。西晋“八王之乱”以及匈奴、氐、羌、羯、鲜卑等部族的内侵,使晋室多故,人神涂炭,“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42) 为了逃避战争,大量中原汉人举族南迁。在永嘉南迁大潮中,尽管有安定朝那的皇甫氏和北地灵州傅氏等陇右士族,以及北地灵州竺僧显、河西竺昙猷等高僧,南迁长江流域,但因远离“中州兵乱”的河西地区,在张规、吕光、秃朆乌孤、李暠和沮渠蒙逊等所领导的五凉政权的治理下,社会相对安宁,因此不仅不是移民迁出区,反而成为移民迁入区,故《资治通鉴》载:“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43) 迁入河西的移民还包括周边的少数民族以及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胡和西国高僧。因此永嘉之乱,尽管对陇右士族南迁影响较大,但就整体而言,还不是河陇僧人南迁的第一推动力。
其二是北魏平定凉州。北魏平定凉州时,对河西和陇右僧人所产生的推力有所差异。对河西僧人的推力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河西禅僧领袖昙无谶与北魏政权交恶,河西僧人因参加凉州城的保卫战,是北魏惩处的对象。另一方面,尽管河陇禅法的兴起与其地处汉文化圈内边塞地带,为道流东国的首站有关。但不得不承认是五凉小国礼佛对河陇佛教的繁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谓“不依帝王,佛法无行”。因此北魏平定凉州,就等于断了河西佛教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基础,所以寻求可以继续依附的政治团体,也是高僧散走的内在驱动力。相反麦积山玄高僧团则是北魏政权的座上宾,因此,北魏平定凉州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甚至可以说是从中获利,如在麦积山时,玄高一度是西秦乞伏炽槃排挤的对象,而在平城则贵为太子师和佛教领袖。
其三是北魏太武帝灭佛。这次事件对河陇禅法的外播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44),永嘉之乱时躲过一劫的河西,没有躲过北魏平定凉州的灾难。永嘉之乱时受到一定影响的陇右禅僧,在北魏平定凉州是却渔翁得利。太武帝灭佛这一劫,河西和陇右的僧人都没有躲过,而且这次劫难距离北魏平定凉州的时间间隔很短,可谓雪上加霜,几乎把前两次事件中遗留下来的河陇高僧悉数驱赶到南方。
(二)五凉政权与迁徙禅僧的文化认同
河陇禅僧迁往何处的意愿,涉及禅僧以及他们所依附的河陇割据政权的文化认同问题,即在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中,哪个国家代表着华夏正统。有了正统认同之后,“正统”之华夏与“倒悬”之凉州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关系如何,则成为禅僧能否顺利迁徙的保障条件。
虽然河陇民族众多,但自西汉移民实边之后,汉族就成为这一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所以无论是汉人张轨、李暠所建立的前凉和西凉,还是氐族吕光、鲜卑秃朆乌孤、匈奴沮渠蒙逊等建立的后凉、南凉和北凉,都不约而同地视东晋南朝为华夏正统。因此当陇西人李俨,诛大姓彭姚,自立于陇右,“奉中兴年号,百姓悦之”。(45) 可见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东晋南朝才是华夏正统。
河西民众的这一文化认同传统,在张规及其子孙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晋书·张规传》载:“光禄傅祗、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京师饥匮,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辟如、仪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弥遂逼洛阳,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没于贼。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46) 张规在世时,著勋西夏,“顷胡贼狡猾,侵逼近甸,义兵锐卒,万里相寻,方贡远珍,府无虚岁”。(47) 在中原乏主,群雄角逐,日寻干戈,未知鹿死谁手之时,各凭才智,遂至蚕食不休或割据一方的乱世中,张规这样的举措是很难得的,甚至在其临死之日还不忘告诫后人说:“吾无德于人,今疾病弥留,殆将命也。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善相安逊,以听朝旨。”(48) 因此,张规的后人,一直奉西晋正朔。公元318年,“元帝即位于建邺,改年太兴”。张规的儿子张寔“犹称建兴六年,不从中兴之所改也”。(49) 建兴为晋愍帝时的年号。
这样的一幕,在张规的弟弟张茂身上重演。太宁三年(325年)张茂卒,临终,执侄子张骏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见称。自汉初以来,世执忠顺。今虽华夏大乱,皇舆播迁,汝当谨守人臣之节,无或失坠。吾遭扰攘之运,承先人余德,假摄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负晋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议,苟以集事,岂荣之哉!气绝之日,白帢入棺,无以朝服,以彰吾志焉。”(50)
张骏始终遵从父亲和叔叔的遗训,“太宁元年,骏犹称建兴十二年,骏亲耕藉田。寻承元帝崩问,骏大临三日。会有黄龙见于胥次之嘉泉,右长史汜祎言于骏曰:‘案建兴之年,是少帝始起之号。帝以凶终,理应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问隔绝,宜因龙改号,以章休征。’不从”(51)。因此在河西“刑清国富,群僚劝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骏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52)。之后张祚曾僭称帝位,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但张玄靓即位后,“废和平之号,复称建兴四十三年”(53)。张规子孙奉西晋正朔的行为,使在西晋只存在了4年的建兴年号,在河西却被使用了48年。这固然有张规家族立足河西的政治需要,但其对东晋政权的忠诚,也彰显无遗。因此《晋书》卷86史臣曰:“茂、骏、重华资忠踵武,崎岖僻陋,无忘本朝,故能西控诸戎,东攘巨猾,绾累叶之珪组,赋绝域之琛賨,振曜遐荒,良由杖顺之效矣。”(54) 其中“西控诸戎,东攘巨猾”正是两晋南朝政权羁縻河西豪族所希望得到的。因此,即便东晋、南朝远在江左,亦不停地加封河西割据者,如对北凉的每一个皇帝都予以册封。
河陇割据政权与东晋南朝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体现在“正统”的认同上,还体现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方面。从经济上讲,张规在世时,就不停地给朝廷贡献。“于时天下既乱,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轨遣使贡献,岁时不替。朝廷嘉之,屡降玺书慰劳。”不仅贡献方物,还贡献兵马,如张规曾“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55) 公元459年,西逃高昌的沮渠安周,被宋孝武帝册封后,仍然向其“奉献方物”(56)。
文化上的交流也较为频繁,张寔在河西时,即“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57)。元嘉三年(426年),北凉沮渠蒙逊世子与国“遣使奉表,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58)。元嘉十四年(437年),沮渠茂虔奉表献方物于刘宋,“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匪攵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晋、赵匪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59)。这其中有许多著作出自凉州本土士人之手。
除了上述主动、直接的文化交流外,被动、间接的文化交流也时有发生。《清乐》被辗转于河西、关中、江南,最终成为隋朝国乐《九部》之一,即为一例。《隋书·音乐志》载:“《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虽赏逐时迁,而古致犹在。可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60)
上述主动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于东晋南朝诸国来说,目的自然是为了“招怀四远”;五凉割据者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寻求大国庇护,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河西豪族尤其是汉族士人中,昭显自己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但这些举措却强化了普通河西民众心目中东晋、南朝即华夏正统的民族认同意识。因此那些南投的僧人和士人,尽管事实上是背井离乡,而内心中却有“回家”的感觉,此即文化归属感使然。
(三)迁入区——东晋南朝对河陇禅法高僧所产生的引力
长江流域,一方面经过蜀汉和孙吴的开发,生活经济条件已有长足进步,另一方面,远离北方战乱,社会安定,加之司马睿南渡后,建立东晋政权,成了华夏“正统”之所在,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北方移民。
相对于北魏建国初期佛教信仰的边荒状况,南朝的佛教信仰则已相当普及,并有广泛的信众基础。首先表现在东晋南朝帝王大多尊信佛教。如晋明帝司马绍,“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于岩隐,玄祖畅乎无生”(61);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六年春正月“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62);安帝司马德宗“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63)。又如宋武帝刘裕南伐休之,至江陵与“慧观相遇,倾心待接,依然若旧。因勒与西中郎游,即文帝也。……元嘉初三月上巳,车驾临曲水燕会,命观与朝士赋诗。观即坐先献,文旨清婉,事适当时”(64)。文帝刘义隆在位时,与高僧慧严“情好尤密,每见弘赞问佛法”(65)。
不仅帝王如此,地方要员和文人雅士,亦对南投的高僧礼遇结赏。如竺昙猷驻锡赤城山时,“王羲之闻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反”(66)。高僧慧观在荆州时,“琅琊王僧达、庐江何尚之,并以清言致欵,结赏尘外”(67)。元嘉中,高僧法成驻锡广汉,“东海王怀素出守巴西,闻风遣迎,会于涪城。夏坐讲律,事竟辞反”。(68)
此外,从南渡僧人的个人学养来看,他们或游学域外,见多识广;或从事译经,具胡、汉双语能力;或专修禅业,师出名门,故他们的佛学修养,与长江流域诸僧相比,无疑要高出许多,因此所到之处,黑白咸敬而嘉焉。这种受人礼遇的环境,与北朝灭佛的环境相比,可谓云泥霄壤,故禅僧之南下,势不可遏。
四、结语
通过对河陇禅法外播过程的考察,我们清楚地看到,从永嘉丧乱起,河陇禅法僧人和士人的南渡就络绎不绝。至北魏平定凉州后,大量的河西士人和僧人被迁往平城,他们对北魏学术文化虽有一定的影响,但因他们在平城生活的时间短,如高僧玄高、士人段承根、宗钦等,到达平城没几年就被北魏统治者所杀。得以终老平城的河西士人大多也是食不果腹,生活困窘。估计如高僧玄畅一样,从平城出发,历尽艰险,奋力逃向南方的河陇僧人和士人一定不在少数。故对北魏的贡献非常有限。加之魏太武帝灭佛,使本来已成为北魏征服者的僧人的生活雪上加霜。相反,由于东晋南朝社会稳定,又代表着华夏正统,为中国衣冠礼乐之所在,因此许多僧人和士人抱着“我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的心态南渡。统计表明,出生、驻锡于河陇的高僧,其中的74%都向南进入了长江流域。再加上五凉政权频繁地向南朝贡献“经史图籍”等,可以肯定地说,五凉时期的河陇文化随着南下的士人和僧人,还被转移保存于东晋南朝,而不仅仅是东迁平城。仅从禅法的传播来看,河陇禅法主要被南渡高僧转移保存于东晋南朝的长江流域,而不是北魏的首都平城。
从禅学传播的影响来看,河陇禅法大量输入东晋南朝,为其禅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河陇禅法僧人南渡后的主要驻锡地建康、荆州、庐山和成都,不仅当时是禅法修习的中心,日后也都成为中国禅宗的发达地区。换而言之,禅法由中国西北边塞向南方传播的过程,也是佛教汉化的一个时空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是双向往复的。值得注意的是,凉州这个五凉时期北中国的文化孤岛,在北魏平定凉州后,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但其融合东、西的独特地域文化,却如同被西北风吹起的蒲公英种子,散播在大江南北。因此河陇不仅仅是丝绸之路的走廊地带,河陇民众还是东、西文化的传播者。
注释:
① 有关这一中心对北中国学术典章制度转移保存方面的作用,陈寅恪曾指出:“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西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6—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② 但《太平御览》卷124《偏霸部》八所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则说被强迫迁移的沮渠牧犍的宗室、士民为十万户:“九月,面缚出降,魏释其缚。徙虔及宗室、士民十万户于平城。”这个庞大的移民队伍中,还有在河西的粟特商人,《北史》卷97《西域传》粟特国条记:“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掠。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
③⑤ 《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第76—78、76—80页。
④ 《出三藏记集》卷8《大涅槃经序》,第313页。
⑥ 《高僧传》卷3《智严传》,第98—99页。
⑦ 《高僧传》卷3《宝云传》,第102—103页。
⑧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65页,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⑨ 《高僧传》卷2《佛驮跋陀罗传》,第71页。
⑩ 《高僧传》卷11《玄高传》,第409—410页。
(11) 《资治通鉴》“宋纪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第38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 《高僧传》卷14《高僧传序录》,第523页。
(13) 《晋书》卷89《辛恭靖传》,第23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 《宋书》卷43《傅亮传》,第13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 《高僧传》卷11《竺僧显传》,第401页。
(16) 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第1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7) 《高僧传》卷11《竺昙猷》,第403—404页。
(18) 《高僧传》卷3《宝云传》,第102—103页。
(19) 《高僧传》卷3《智严传》,第99—100页。
(20) 《高僧传》卷11《慧览传》,第418页。
(21) 《高僧传》卷8《玄畅传》,第314—315页。
(22) 《三论游意义》,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5,第122页中。
(23) 《高僧传》卷7《慧严传》,第262页。
(24) 《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第80页。
(25) 《高僧传》卷7《慧严传》,第262—263页。
(27) 《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第256页。
(27) 《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第80页。
(28) 《晋书》卷51《皇甫谧·子方回传》,第1418—1419页。
(29) 《高僧传》卷7《道温传》,第287页。
(30) 《高僧传》卷5《慧虔传》,第209页。
(31) 《高僧传》卷8《僧慧传》,第321页。
(32) 《高僧传》卷6《慧远传》,第221页。
(33) 《高僧传》卷11《僧隐传》,第432页。
(34) 《名僧传抄》卷1《僧印传》,载《卍新纂续藏经》,第77册。
(35) 《高僧传》卷11《法期传》,第419页。
(36) 《续高僧传》卷25《僧朗传》,第646页下—647页上。
(37) 《高僧传》卷11《贤护传》,第407页。
(38) 《高僧传》卷11《法成传》,第417页。
(39) 《高僧传》卷3《智猛传》,第125—126页。
(40) 《高僧传》卷11《道法传》,第420页。
(41) 《高僧传》卷8《玄畅传》,第315页。
(42)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9页。
(43) 《资治通鉴》“宋纪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第3877页。
(44)(47)(49)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9、2227、2230页。
(45)(53) 《晋书》卷86《张玄靓传》,第2248、2248页。
(46)(48)(54) 《晋书》卷86《张规传》,第2225、2226、2253页。
(50)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2—2233页。
(51)(52)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4、2235页。按:东晋明帝太宁元年为公元323年,前凉张俊建兴12年为公元323年,两者年代不一致。
(55) 《晋书》卷86《张规传》,第2223—2224页。
(56) 《宋书》卷98《氐胡·沮渠安周传》,第2818页。
(57) 《晋书》卷86《张寔传》,第2227页。
(58) 《宋书》卷98《氐胡·沮渠蒙逊传》,第2415页。
(59) 《宋书》卷98《氐胡·沮渠茂虔传》,第2416页。
(60) 《隋书》卷15《音乐志下》,第377—3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61) 习凿齿:《与释道安书》,见《弘明集》,卷12,四部丛刊景明本,第596页。
(62) 《晋书》卷9《孝武帝纪》,第231页。
(63) 《晋书》卷10《安帝纪》,第207页。
(64)(67) 《高僧传》卷7《慧观传》,第264—265、265页。
(65) 《高僧传》卷7《慧严传》,第261页。
(66) 《高僧传》卷11《竺昙猷》,第403—404页。
(68) 《高僧传》卷11《法成传》,第417页。
